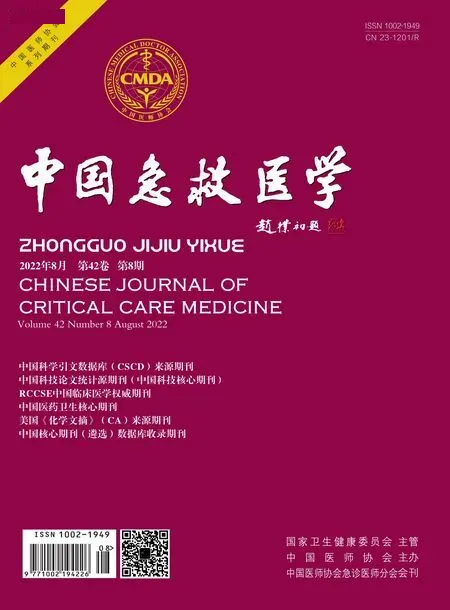血小板反应性对PCI术后远期心血管不良结局影响的研究进展
尹江燕, 聂倩文, 郇 轩, 田梅香, 包 鑫, 张正义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是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患者血运重建的主要治疗技术。但PCI术后一定时间内,由于支架贴壁不良、血管内皮受损、高凝状态等引起的高血小板反应性(high platelet reactivity, HPR)导致局部血小板血栓形成[1-2],而血小板血栓形成是患者PCI术后发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的重要原因。研究[3]发现,ACS或稳定型冠状动脉疾病(stabl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SCAD)患者行PCI治疗后,HPR与长期MACE相关,可作为PCI术后发生MACE的独立预测指标。双重抗血小板是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患者的治疗基石,尤其是接受PCI的AMI患者[4],然而,目前抗血小板治疗的启动时间,药物作用的持续时间,适宜的、个体化的P2Y12抑制剂选择等仍然存在争议[5]。HPR不仅与PCI术后发生MACE相关,也和大量抗血小板药物疗效降低相关[6]。本文对PCI术后发生MACE及抗血小板治疗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做一总结,旨在进一步探讨HPR对PCI术后发生MACE的预测价值和抗血小板的临床指导价值。
1 PCI术后发生HPR的原因及机制
PCI被认为是ACS患者预防血栓性心血管事件的首选治疗方法[7],主要是利用支架打开狭窄或闭塞的冠状动脉,使得病灶血管再通,但支架的置入也会破坏血管内皮的完整性,加重血管内皮损伤、易损斑块破裂,进而刺激机体释放大量的细胞因子,导致机体呈现HPR,诱导支架内血栓形成[8-9]。其机制可能包括:PCI诱导血管损伤加重血管内皮下基质的暴露,从而促进血小板的黏附和激活,由于血小板活化后释放的血栓素A2(TXA2)和二磷酸腺苷(ADP)的协同作用,糖蛋白Ⅱb/Ⅲa受体持续激活和血小板血栓形成[10]。另外,暴露于血管损伤部位的组织因子有助于凝血酶的生成,从而进一步增强血小板反应性(platelet reactivity, PR)和凝血过程,凝血酶还可通过凝血级联反应生成纤维蛋白网,稳定富含血小板的血栓[11]。通常情况下,只有PR升高才能使血小板在血管损伤部位黏附和聚集,从而维持止血状态。然而过高的PR又会导致血栓的形成。因此,尽管PCI治疗使AMI相关的心外膜冠状动脉再通,但PCI期间医源性血小板的过度激活引起的HPR仍会导致微血管阻塞和心肌缺血、梗死。
ACS患者在PCI术后早期发生缺血和血栓性并发症的风险最高,可能的原因是PCI过程中机械刺激引起的高凝状态和血管内皮功能障碍[8]。Gurbel等[12]的研究发现,PCI术后2 h PR立即增加,5 h恢复到基线水平。Mangiacapra 等[13]研究表明,与接受血管造影(coronary angiography, CA)的患者相比,接受PCI术或冠状动脉腔内斑块旋切术(rotational atherectomy, RA)加PCI术治疗的患者PR升高更显著。该研究(n=65)分别对比了接受CA的患者(n=15)和PCI术的患者(n=40),以及RA+PCI术的患者(n=10)的PR变化,结果显示,PR在CA组下降(P<0.0001),而在PCI组和RA+PCI组术后即刻显著增加(P<0.0001),并在24 h降至基线水平,且PR的升高与置入支架的长度直接相关。
2 PCI术后HPR与MACE的相关性
尽管抗血小板治疗在心脑血管疾病中被广泛使用,但ACS和SCAD患者接受PCI治疗后仍面临着相当高的血栓再发生的风险,这可能与抗血栓药物不足而导致残留HPR或PCI时医源性激活血小板所致的血小板生成加快有关[14]。早期研究[3]发现,HPR与PCI术后MACE显著相关,且网织血小板分数(reticulated platelet fraction, RPF)对PR变化最具敏感性。该研究前瞻性地纳入486例接受PCI治疗的患者,同时检测多项与血小板功能相关指标,包括平均血小板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e, MPV)、血管扩张剂刺激磷酸蛋白磷酸化试验(vasodilator stimulated phosphoprotein phosphorylation, VASP-P)和血小板功能测试多电极聚集法(multi-electrode aggregation, MEA)等。在6个月后的随访中,10.7%的患者发生了MACE,结论是RPF和MPV是MACE的单变量预测因子,而VASP-P和MEA不能预测MACE。随后,有研究[15]通过对477例PCI术后患者连续随访5.8年证实,HPR与PCI术后长期MACE相关,HPR可能是PCI术后预测血栓风险的一个新的指标。
此外,HPR与MACE的独立相关性也可能受到年龄的影响。De Rosa等[16]研究纳入1053例接受PCI治疗的ACS患者,其中老年患者311例,分别检测基线、出院、PCI术后1个月的PR变化,结论仍是HPR与MACE风险增加独立相关(出院时HPR:HR=3.191, 95%CI1.373~7.417,P=0.007;1个月HPR:HR=3.542, 95%CI1.373~9.137,P=0.009),且PR升高老年人(≥75岁)与PR升高非老年人(<75岁)及PR正常的老年人相比,其发生MACE的风险增加了4倍。事实上,老年人发生缺血和出血的风险更高。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止血系统相关因子(如纤维蛋白原、因子Ⅷ和纤溶酶原激活抑制剂-1)的失调和血液黏度的增加提供了血栓形成的环境,而内皮功能障碍、炎症和氧化应激的增加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加速血栓形成[17];另一方面,生理器官的改变(肾功能降低、肝细胞色素活性降低及肌肉萎缩等)导致了抗血小板药物反应的个体间差异,并可能增加药物的毒副作用。因此,HPR可能是评估PCI术后发生MACE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年龄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心血管疾病患者常用的全球急性冠状动脉事件注册评分(GRACE)是经过验证且广泛认可的心血管风险分层标准,而在GRACE风险评分基础上增加PR,可显著提高其对ACS患者行PCI后心血管风险评估的准确性。有研究[18]随访了230例行PCI治疗的ACS患者,在1年的随访期间里有72例患者发生了MACE,且这些发生MACE的患者PR(244.6±50.9 vs. 203.7±52.0,P<0.001)和GRACE评分(185.2±45.6 vs.149.7±40.1,P<0.001) 与未发生MACE的患者相比均显著升高。此外,PCI术后发生MACE的影响因素众多[如糖尿病、慢性肾病、年龄、ACS或非ACS及PCI术后的时间(早vs.晚)等],而HPR对MACE的预测也应与这些影响因素综合考虑。
3 HPR对PCI围手术期抗血小板治疗的临床指导价值
最佳的血小板抑制状态是预防PCI患者发生血栓性并发症的关键[19],目前临床常用的抗血小板药物有环氧化酶(COX)抑制剂、P2Y12受体拮抗剂、血小板糖蛋白Ⅱb/Ⅲa受体拮抗剂(GPI)等,这些药物在PCI围术期均有使用。然而,关于PCI前抗血小板治疗的益处、风险和持续时间,以及各种抗血小板药物的起效时间和抗血小板强度与临床转归之间的确切关系仍存在争议[20]。影响抗血小板药物疗效的因素有很多(如临床特征、遗传因素等),但是HPR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因素[21]。到目前为止,根据PR变化调整的抗血小板治疗的临床获益性还未被证明,因此,在后期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PCI围手术期PR的变化及其与预后的关系,可能有助于开发更有效和更安全的抗血小板治疗方案。
3.1COX抑制剂 COX抑制剂如乙酰水杨酸(acetylsalicylic acid, ASA)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血栓事件使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ASA的药效学作用主要是吸收后立即在门静脉血中起作用,通过对血小板COX-1的丝氨酸残基乙酰化,导致酶的不可逆抑制,进而抑制TXA2的生成。到达体循环后,ASA进入骨髓,抑制巨核细胞中与血小板相同的靶酶。通常情况下,血小板不能再合成新的COX来取代乙酰化酶,只有在血小板周转率增加使得血小板不断更新的情况下才能恢复酶的活性[22]。换言之,尽管ASA不可逆地抑制血小板COX-1,但是由于新的血小板不断生成,血小板功能可在24 h给药间隔内恢复[23],PCI术后引起的HPR可能是ASA在标准24 h给药间隔内抗血小板疗效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前期研究[24]显示,在PCI术后PR升高的患者中,ASA抗血小板疗效显著降低。而关于PCI术前长期使用ASA的益处也已被证明,PCI术前未长期使用ASA治疗的患者其死亡和卒中风险升高,而在接受慢性低剂量ASA治疗且择期行PCI术的患者中,PCI前给予负荷剂量的ASA可降低血清中血栓素B2的增加,从而改善心脏再灌注和心肌损伤指数[25]。ASA在抗栓中的益处于1974年首次被证明[26],距今40多年仍在临床广泛使用,早期ASA主要用于心血管疾病的二级预防,近年来,ASA在心血管一级预防中的作用也受到广泛关注,充分证明了其对抗血小板的重要性[27]。对于服用ASA的患者,定期监测PR的变化可能进一步提升其抗血小板的作用效果。
3.2P2Y12受体拮抗剂
PR的升高与PCI手术的复杂程度直接相关,如大量的球囊扩张、广泛使用支架及冠状动脉腔内斑块旋切术等均是PR升高的重要诱因。同样,在常规使用氯吡格雷治疗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患者中,PCI也可诱导PR的升高[28]。
氯吡格雷是一种传统但仍广泛使用的P2Y12抑制剂。研究[29]表明,PCI术后规律口服氯吡格雷的患者仍然检测到HPR,而目前临床上对于这些患者并未常规监测PR的变化。一项对比普拉格雷和氯吡格雷对PR影响的研究[30]发现,在PCI术前12 h,将40例CAD患者随机分配到负荷剂量普拉格雷60 mg (n=20)或氯吡格雷600 mg (n=20)两组中,结果[31]显示,普拉格雷组PR降低更显著。氯吡格雷的抗血小板作用受到PR日变化的影响,PCI术后口服氯吡格雷的患者PR有可能持续升高且容易发生支架内血栓和心肌梗死(MI)[32]。近期“药物洗脱支架植入后双抗血小板治疗评估”的研究[33]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另外,一项纳入14项研究[7]的Meta分析得出,新型P2Y12受体拮抗剂(普拉格雷和替格瑞洛)在接受PCI的ACS患者中临床疗效优于氯吡格雷,且替格瑞洛治疗组患者的PR低于普拉格雷治疗组。
目前,关于P2Y12受体拮抗剂影响PR变化的具体机制还在探索中,有研究认为,PR的变化可能与药物半衰期有关。氯吡格雷作为一种不可逆的血小板抑制剂,在循环中存在的时间很短,随着这种药物的标准日剂量被迅速代谢,随后进入血液循环新形成的血小板将不受抑制,直到下一剂药物被服用。相反,替格瑞洛作为P2Y12受体的一种作用时间更长(血浆半衰期≈8 h)的可逆性拮抗剂,可抑制外源性增加的血小板(PCI时血管损伤)对ADP的反应[34]。此外,替格瑞洛还可降低红细胞对腺苷的摄取,降低血浆浓度,抑制血小板聚集[7]。也有研究[35]认为,抗血小板治疗期间PR的变化与血小板亚型的内在特性有关,而这些药物与P2Y12受体的结合特性可能是理解其与PR关系的关键所在[30]。
3.3血小板糖蛋白Ⅱb/Ⅲa受体拮抗剂(GPI) HPR可以促进更多血小板表面受体的表达,如GPⅠb或Ⅱb/Ⅲa[36]。一项“基于PR指导PCI术后个体化抗血小板治疗”的Meta分析[37]表明,对于接受PCI且PR升高的患者,PCI围术期使用糖蛋白Ⅱb/Ⅲa受体抑制剂(GPI)不仅能够降低血栓事件,更重要的是不会诱发出血。GPⅡb/Ⅲa抑制剂曾经被广泛用于快速抑制血小板,特别是对行PCI治疗的高危患者,与二十年前相比,目前GPI在高危患者中的应用逐渐减少。近年来,坎格里洛(Cangrelor)似乎成为PCI期间调节HPR的新策略,作为一种静脉P2Y12受体拮抗剂,起效非常快,在PCI围手术期可获得充分的血小板抑制[20]。此外,对于ST段升高且出血性风险较高的患者,在不增加出血性事件的同时降低不良缺血的可能性,替罗非班可能是PCI围术期安全、有效地抗血小板药物[38]。
4 PR的监测
早期研究[39]发现,网织血小板分数(reticulated platelet fraction, RPF)有助于监测PR的变化,这可能与网织血小板(reticular platelets, RP)在血栓形成前过度活跃且更具反应性等特点有关。RP作为从骨髓最早释放出来的最幼稚的血小板,是骨髓中巨核细胞成熟和PR变化的敏感指标[40]。1969年RPF的检测首次被提出,但由于技术的限制在此期间并未推广,直到1988年随着细胞质RNA自动检测技术的引入[41],升级的全自动RNA检测设备Sysmex 2100 XE被用于检测RPF。自动RNA检测设备具有高度标准化和可重复的特点,与之前噻唑橙染色的流式细胞术相比,其效率高且成本低[42],可精确量化RPF, 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分析相关的变异性,排除了RNA染色过程中,染液的类型、浓度、时间、温度、离心速度等因素对RPF检测精度的干扰[43]。在发达国家,RPF与MPV等指标一样常规用于临床,且越来越多的研究[44]表明,在识别HPR或血小板生成增加的相关指标中,RPF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尚未推广。
综上所述,对于行PCI治疗的ACS或SCAD患者,HPR与MACE风险增加独立相关,监测PR的变化,可有效预防MACE的发生,PR有望成为PCI术后患者长期心血管风险的新型标志物。目前,抗血小板药物影响PR变化的具体机制研究仍在进行中,但PR与抗血小板药物产生耐药的相关性已经被证明。此外,自动化血液分析仪的引入为临床监测PR提供了可能。因此,在个体化用药时代,对于动脉粥样硬化的高风险患者,动态监测PR变化有助于精确且及时地调整抗血小板的治疗方案。随着研究的深入,PR在PCI术后血小板血栓形成中的作用及对抗血小板治疗的指导价值期待进一步被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