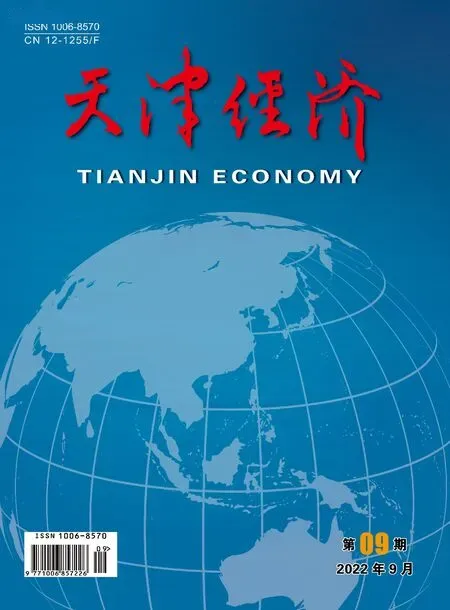个人所得税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优化研究
◎文/卫纳斯
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在2018年12月份正式出炉,作为费用扣除制度改革的亮点之一,是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国家对民生、教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关注。围绕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支出领域,在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6项专项附加扣除的基础上,又加设了一项,即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立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国务院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操作办法》)等文件做了进一步细化规定。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对具体的扣除政策及税制要素进行设置,包括扣除主体、扣除标准、扣除范围、办理程序等,充分地考虑了个人负担的差异性,体现了税收量能负担原则。但是,专项附加制度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实践中发现不足,及时调整,逐步优化,逐渐完善,才能更好地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匹配。切实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良好发展的作用。随着看病贵、看病难等社会问题凸显,让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是夯实民生之基的重点所在。将治疗疾病的部分费用作为专项费用予以扣除,进一步维护了税收公平,体现了税收政策的人文关怀,社会公众对此政策也寄予了较高期望。
一、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之法理分析与构造原则
共同富裕的目标,应当是建立在保障公民生存权的基础上,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现象。因此,推动医疗体制的改革,保障公民的“就医权”,特别是大病“就医权”就尤为重要。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大病医疗费用支出应当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课税禁区,予以税前扣除。
第一,对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范围的确定应当基于对居民的生存权、健康权的保障。这些基本的权利在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第45条予以明确。大病患者作为社会中较弱势的群体,其生存权和健康权更应获得关注,在个人所得税的计算中于税前进行扣除。增加费用扣除项目,直接损失的就是税收收入成本。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增加大病医疗专项扣除正是基于保障公民的生存权益,基于税收公平原则,不应当由于各地医保政策的差异性导致纳税人享有的扣除标准不同。
第二,个税大病医疗专项扣除要与其他医疗体制改革共同推动。大病医疗专项扣除政策的出台,对于优化当前医疗体制有一定的作用,但也要认识到,由于费用扣除发挥作用的局限性,该政策只能成为医疗体制改革的辅助手段,并不能成为主要手段或关键手段。究其原因,一方面,“有个税才有扣除”,即可以进行专项附加扣除的前提是缴纳个人所得税,这就导致未达到个税缴纳标准的部分群体,无法享受该政策。另一方面,对于缴纳个人所得税可以享受扣除政策的这部分人群来说,如果需要支付的医疗费用过于庞大,在现行的扣除标准下,扣除的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因此,缓解大病医疗带给病人和家庭的负担,根本上还是要依靠医疗体制的改革才能实现,大病医疗专项扣除政策只能缓解非常有限的压力。税法中专项扣除的政策设计,要与其他医疗体制改革共同推动,不能盲目扩大其作用。
二、个税医疗专项费用扣除之应然构造
通过对现行大病医疗专项附加的规定进行剖析,并结合共同富裕目标下,保障居民生存权及健康权,辅助医疗体制改革的定位,对大病医疗专项扣除应当从以下四个基本要素进行完善,具体构造如下:
(一)扣除范围之应然构造
《暂行办法》的第11条对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的范围做出了规定:只有医保目录范围内的大病医疗支出才可以扣除,并且应当先行减去由医保报销的费用,剩余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支出才可以进行扣除。这个规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有可完善细化的部分。大病医疗专项扣除的范围首先应当扣除医保报销部分,再扣除由个人自负的部分。这是源于医保报销范围以内的费用已经由国家或政府买单,个人无需承担。同时,大病医疗的扣除范围是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要求应当维持。这是基于大病治疗费用品类繁杂,通过目录进行规范可以减少费用造假的可能性,但需要及时对目录进行更新维护。
大病医疗的扣除范围应当在国家层面进一步细化。这主要是在实践中,纳税人患重大疾病所需的治疗项目种类繁多,包括必须的诊费、药费、治疗费,还可能包括病房或病床费、护理费、食杂费等等。按照现在的医保政策,虽然都是患重大疾病所必须的支出,但这些费用有很多并没有列入医保报销范围,是不能报销的。因而,对大病医疗费用扣除应当根据不同重大疾病的治疗需要确定,不能仅限于医药费用。2019年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国保 发〔2019〕46号)以及2020年中国保险协会发布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修订版》等文件,调整了相关药品目录,对重疾定义完善扩展,同个人所得税大病医疗专项扣除制度予以衔接。但是没有对费用目录进行细化,各地区医保目录的差异明显。以上海为例,其确定的药品目录4505个,远超国家确定的2643个。而北京确定的甲级药品数量2039个,是上海确定的889个的两倍。从上述数据看,不同地区对于大病医疗专项扣除的差异损害了我国居民的平等生存权和健康权,应当从国家层面进行细化和规范。
(二)扣除标准之应然构造
《暂行办法》第11条对大病医疗专项扣除的数额也做出了限制,即对个人自费金额超过15000元、不超过80000元的区间限额扣除,采用据实扣除方式。当前,国际上对于大病医疗的扣除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限额扣除,也是当前我国采取的做法,第二种是比例扣除,第三种是二者并行。
相较于比例扣除,限额扣除更具有刚性,执行简便。基于当前的征管现状以及纳税人的涉税问题处理能力,采取限额扣除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可以从提升限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入手。目前我国现行的基本费用减除标准已达年60000元,而我国2020年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2188.8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于五等分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类,只有最高收入的20%才能再扣除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的基础上享有大病医疗专项扣除。再加之15000元的限额标准,可能导致大病医疗扣除成为少数高收入人群特享的减除。最高上限的设计在征管中可以避免一些纳税人超标准超额消费,有一定的合理性。 盛 常 艳、 薛 兴 华 等(2018)的研究认为大病医疗扣除的上限可以提升至10万元,这个数额是参照2017年保监会规定的重大疾病治疗康复费用标准提出的。而大病医疗扣除的下限则应当予以取消。笔者赞同其观点,认为在既有框架下,应当取消大病医疗扣除的下限,而上限的具体设置还应当进行科学运算。
(三)扣除时间的应然构造
《暂行办法》第11条及《操作办法》第3条第3款明确了大病医疗专项扣除的扣除时间,即要在支付医疗费用的一个纳税年度内申报。这种做法可以降低征管成本,但不能结转扣除,违背了大病医疗扣除的法理原则。大病的治疗周期通常超过一个纳税年度,而且在进行手术等集中治疗的年度往往发生大量支出,之后的保养或康复治疗的费用较低。因此,应当确定允许大病医疗治疗费用结转扣除。具体的扣除年限可以根据纳税人的收入水平进行差异化,高收入者可结转年限短,低收入者结转年限长。例如,规定对超过扣除限额的部分可以进行结转,在以后的五个纳税年度限额扣除。
(四)扣除主体的应然构造
《暂行办法》第12条明确了扣除主体,即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的父母一方。这种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家庭负担的理念,但仍有与我国具体国情相冲突的方面。
第一,父母的大病医疗扣除存在空白。按照当前《个人所得税法》及其配套制度的规定,退休人员所获得的养老金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其发生的大病医疗扣除无法抵扣。而我国有着养儿防老、乌鸦反哺的传统,很多老人的大病医疗支出的实际负担人是子女所在家庭,特别是占我国人口40%左右的农村,很多老人收入微薄,发生大病需要子女所在家庭共同或者主要负担。
第二,已成年无收入未婚子女的大病医疗扣除存在空白。全日制攻读本科、研究生等学历的人员,他们在读书期间没有收入或很少取得收入,一旦发生大病,负担起治疗费用的父母或者其他人员却无法扣除。而对于因病无法工作的未婚成年子女的大病医疗费用,负担起治疗费用的父母或者其他人员却无法扣除,无疑无法改善甚至恶化其家庭成员的处境。
第三,单方扣除并不科学。对于未成年人的抚育是父母双方的义务,而重大疾病的治疗费用通常是高额的,单方抵扣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抵扣不足的情况。
综上,基于我国通常家庭来承担家庭成员大病治疗费用的现状,应当进一步扩大和完善扣除主体的设置。
三、配套机制措施的构建
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完善,影响面大,牵涉主体多。涉及到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利益让渡,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给我国的税收征管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体系建设还有待加强,只有《税收征管法》《个人所得税法》等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大病医疗专项附加费用扣除制度才能发挥其更深层次的作用。按照《暂行办法》第26条规定,公安、卫生健康、民政等多个部门和单位,有责任和义务向税务部门提供或核实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有关的信息,其中就包括医疗保障部门。只有医疗保障部门将医药费用等信息与税务部门共享,扣除制度才能真正落实落地。
税收征管法重构涉税信息共享制度框架。2015年,税收征管法草案的起草说明中强调,“涉税信息获取能力不足、税收治理能力不强”是本次税收征管法大修的重要原因。所以,只有通过征管法的修订,为涉税信息的管理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涉税信息共享制度才能得到进一步完善。新个人所得税法确立的综合计征模式倒逼政府部门之间互联互通涉税信息,打破了涉税信息共享的僵局,税收征管法和发票管理办法的修订为涉税信息共享制度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为此,应当从立法层面重构以税收征管法为依托,多税种实体法为保障的涉税信息共享法律规范体系,建立健全涉税信息共享制度,为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实施的税收共治,提供畅通的信息渠道和规范的法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