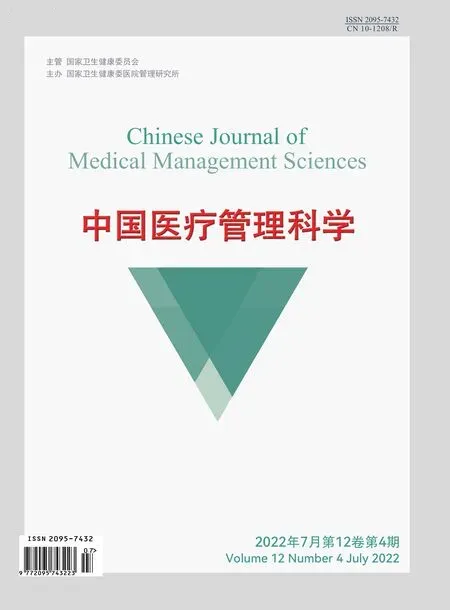上海市嘉定区社区精神卫生工作SWOT 分析和对策探讨
熊伊然 田源 赵姣文
根据WHO 数据显示,全世界每4 个人中就有1人在其生命中的某个时间段产生过某种精神障碍。伤残调整生命年指标分析结果显示,全球疾病负担中,精神疾病占7%。《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 年)》要求2020 年有50%以上的居家患者接受社区康复服务。截至2021 年底,上海市嘉定区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数量为7 401 人,其中6 507 人都是在社区居家进行生活和康复,占到患者总数的87.92%。可见社区精神卫生工作责任大、任务重。近年来,嘉定区以国家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以及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为契机,不断探索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综合性、多元化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模式,取得一定成效,但存在部门协作不通畅、社会参与服务机制不健全、工作成效不明显等问题与阻力。
SWOT 分析又称态势分析,即探讨和整理研究主题的内部优势(strengths, S)、劣势(weaknesses, W)和外部机遇(opportunities, O)、威胁(threats, T),并以矩阵形式排列,最后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从而得出决策。基于SWOT 的结构化和系统性的特征,在卫生政策研究领域应用广泛。本文基于SWOT 分析方法,结合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工作实际,探索和优化社区精神卫生工作机制,为提升区域精神卫生工作成效、促进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康复提供依据。
1 内部优势(S)
1.1 健全服务体系
在政府及社会的支持下,上海市嘉定区逐步形成精神疾病社区三级管理网络。由各级政府牵头,卫生、残联、公安、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人社等17 个部门组建精神卫生联合办公室,齐抓共管,分工协作,负责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和管理,并定期召开例会沟通信息、解决难题;在技术层面上,成立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分中心,凭借精神卫生中心的专业力量,对社区精神卫生工作进行业务指导、技术培训、专业教学和科研;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则承担社区精神服务的具体工作,向全区居民提供最基本的精神卫生服务。
1.2 完善服务模式
引入社工,探索专业社工服务与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结合的工作模式。同时,有效整合专科医疗机构和社区医防资源,组建由医疗、护理、预防、康复、行政管理人员共同参与的具有嘉定特色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团队,提供随访技术指导、个案管理、康复指导、健康教育等“下沉式”服务。
1.3 优化康复服务
1.3.1 项目化服务2015 年,嘉定区立异创新,首次尝试与社会组织合作,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全面、科学、人性化地为社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系统的康复服务。
1.3.2 阳光心园
各街镇充分利用社区资源,组建精神疾病患者日间照料站,统一冠名“阳光心园”,由各街镇残联负责机构的日常运作及管理,区精神卫生中心及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期派医务人员到机构内指导康复工作。
2 内部劣势(W)
2.1 资源配置不足
截至2021 年底,上海市嘉定区登记在册的精神疾病患者7 401 人,而嘉定区精神卫生机构核定床位360 张,实际开放床位550 张。也就是说,全区只有不到10%的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接受治疗,超过90%的患者都是在社区管理。而截至2021 年底,嘉定区全区常住人口1 596 000 人,参与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为1 259 人,占全区常住人口总数的0.79‰,精神科专科医师39 人,平均2.44 人/10 万,显著低于2020 年13 人/10 万的世界平均水平;社区基层精防工作人员医学背景、技术职称、工作能力均处于较低的水平。精神卫生服务内容越来越多,工作量越来越重,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人员往往身兼数职,但却未能获取相应的收入和待遇,直接导致职工工作积极性普遍不高,出现频繁跳槽和离职,社区精神卫生服务队伍更替频繁,进一步加重了社区精防人员素质不高,服务质量欠缺的状况。
2.2 信息交换欠通畅
治疗与随访尚未形成有效互动,医院转社区、社区转医院等服务衔接欠流畅,未能实现康复服务与家庭、医疗、社会等方面的信息交换和资源整合;同时,在精神康复服务提供过程中,未能将家庭支持与康复者各阶段的康复需求有效连接,导致患者院内康复过程中家属的参与度不够,影响康复效果。
2.3 出入院“两难”情况
专科医院符合出院指征的患者滞留医院情况严重,使得医院的床位紧张,医疗资源不能得到高效利用,新发病患者入院困难。出院康复患者回归社会后因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不到位,如责任心不够、监护力不够、监护人缺位等多种原因,对出院康复患者看护不力,造成患者服药不规律,导致病情复发,需要反复住院,加剧了入院困难的问题。
3 外部机会(O)
3.1 需求增加
一方面,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生存与竞争压力加剧,心理应激因素日益增加,心理疾病发病率升高,患者数量增加。1982年和1993 年,我国分别组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15 岁人口各类精神疾病总时点患病率由1982 年的9.11%上升至1993 年的11.18%。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 大类精神障碍患病率为9.3%,其终身患病率为16.6%(均不含老年期痴呆),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生活品质要求不断提升,更加重视心理健康。2002 年上海市市民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调查结果显示,居民精神卫生基本知晓率为17.09%。2012 年上海市居民精神卫生知晓率调查结果显示,居民精神卫生基本知识知晓率平均为65.7%。2016 年上海市社区居民精神卫生知识总体回答正确率为59.84%,对比2012 年知晓率调查中相同的6 个条目市民正确回答率,结果显示,上海市市民精神卫生知晓率有所提升。居民心理健康素养增强,加之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对于精神卫生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
3.2 政策支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精神卫生工作。近年来,《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 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的颁布,从国家层面对心理健康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上海市陆续出台《上海市无业贫困精神病人免费服药项目实施方案》《上海市残疾人居家养护实施方案》《残疾劳动者就业促进专项计划》《关于促进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的实施意见》《上海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上海市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和信息登记管理办法》等政策,为患者能及时接受所需的治疗和康复提供保障。嘉定区贯彻国家和上海市相关文件精神,制订了《上海市嘉定区实施以奖代补政策落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责任的暂行办法》《嘉定区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人社会保障的实施办法》等政策文件,针对区域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开展了系列救治救助举措。
3.3 保障力度加大
2012 年,由原嘉定区卫生计生委、财政局、发改委等5 个委办局共同制订《关于嘉定区进一步完善政府卫生投入的实施意见》,文件规定,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增长幅度。2020 年卫生事业费投入占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例为6.9%。截至目前,精神卫生工作经费已由最初的户籍人口0.1 元/人逐年增加到常住人口4.8 元/人,用于保障精神疾病预防与控制工作的开展。2015 年,嘉定区被列为首批国家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区,以此为契机,政府加强对试点工作的财政经费投入,在常住人口4.8 元/人精防工作经费的拨付基础上,2016 年—2021 年间,平均每年划拨196 万元作为试点专项经费,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属护理教育、患者社区融入、心理援助热线建设等工作,不断拓展心理健康服务内涵,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服务网络。
3.4 综合性医院心理门诊的开设
《精神卫生法》规定:综合性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开设精神科门诊或者心理治疗门诊。2019 年,嘉定区作为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地区,提出50%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开设精神科或心理科门诊的要求,截至2021 年底,区域内5 家综合性医院有60%完成了精神科或心理科门诊的建设,进一步提高了区域精神障碍诊疗、预防控制及管理能力。
4 外部威胁(T)
4.1 投入不足
2007 年,国外研究者通过对精神疾病负担的测算,提出中低收入国家在精神卫生服务的财政投入应为每人3 ~ 4 美元/年,折合人民币为每年24 ~ 32 元(以2007 年汇率计算)。2008 年上海市19个区县精神卫生服务筹资状况调查结果显示,19 个区县中只有松江区人均精神卫生投入达到此水平,嘉定区人均投入为14.67 元,与建议差距较大。根据WHO《2020 年世界精神卫生地图集》(Mental Health Atlas 2020)结果显示,全球人均精神卫生支出中位数为7.49 美元,按照2020 年平均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51.68 元;低收入国家人均精神卫生支出经费平均为0.08 美元,折合人民币0.55 元;中低收入国家人均精神卫生支出经费平均为0.37 美元,折合人民币2.55 元;中高收入国家人均精神卫生支出经费平均3.29 美元,折合人民币22.70 元;高收入国家人均精神卫生支出经费平均52.73美元,折合人民币363.82 元。2020 年嘉定区人均精神卫生支出经费为76.58 元/人,超过中高收入国家人均水平,但是与高收入国家尚存较大差距。
4.2 人口构成倒挂
根据《嘉定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数据显示,2020 年嘉定区共有常住人口183.4万人,其中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为103.7 万人,嘉定区户籍人口79.7 万人,外来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例大约为1.3 : 1,户籍人口与外来常住人口呈现倒挂的现象。外来常住人口往往流动性强,居民基本信息较难收集,管理难度大;健康风险多且情况更复杂,而往往得不到同等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其医疗保障水平也低于本地居民;同时流动人口相对文化程度较低,接受相应的健康教育和指导水平较低,易发生肇事肇祸事件,对于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带来更大的挑战。
4.3 居民精神卫生健康素养有待提高
我国精神障碍患者约有1.8 亿人,但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不足。既往研究显示,居民普遍对精神卫生相关知识了解不多,普通人群对精神卫生与心理卫生保健的知晓率为60.32%,城市居民知晓率高于农村,社区医务人员对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为78.81%,其中精神和心理公共部分最高,为84.45%,精神疾病知识部分最低,为70.59%。由于精神卫生知识宣传力度不够,宣传途径单一等,导致大多数人对精神类疾病认识不足,对精神疾病患者存在误解、偏见和歧视,患者自身也常因病耻感而延误治疗。
4.4 精神疾病患者的特殊性
精神疾病往往伴随着认知行为能力的改变,具有冲动和危险行为的特点,精神疾病患者也成为被回避、被污名的对象。一方面,与其他慢性疾病患者相比,精神障碍患者的防治有其特殊性,其治疗过程漫长,由于近年来逐步推进精神卫生“去医院化”管理理念,使大部分患者回归社区。而回归社区的患者自我管理不力,患者常因自身产生病耻感而延误治疗。一旦对社区精神疾病患者的管控不当,出现肇事肇祸,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谐,造成损失。另一方面,大部分精神疾病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病耻感,患者不愿就医或者延迟就医,拒绝或不配合随访,导致患者的预后、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差,形成治疗和康复随访缺口。
5 讨论与建议
5.1 落实政府主体责任
国外研究者指出,每投入1 美元用于治疗焦虑症、抑郁症,就能在健康促进等方面取得4 倍的回报。政府应落实其主体责任,加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增加政府财政投入,鼓励社会资本介入,加强对精神卫生服务人员的经济保障,加大对医疗机构基础设备的投入,构建可持续的日常医疗服务与运行的财务支持保障机制,促进区域整体精神卫生诊疗和康复能力。
5.2 落实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
明确各部门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落实问责,加强横向合作和沟通,回归社区的精神障碍患者的日常医疗救治工作由卫生健康部门承担;社区随访工作要有村居委会参与;社区康复要有民政、残联等部门参与;社会保障和财政补贴要由财政和社会保障部门落实;患者住院医疗费用、社区康复、居家精神心理上门巡视服务与指导的费用应由医疗保障局负责研究解决;当出现患方肇事肇祸时公安部门要及时介入。当患者有出院指征时,公安、民政、社区等多部门要共同努力,尽快为其办理出院手续,解决其社区安置问题。政府主管部门要做好协调工作,树立合作意识,形成有效联动。
5.3 建立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
加大对贫困群体的保障力度,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扩大社会保障对社区精神疾病保障范围,将精神疾病的社区康复纳入到医疗保险中,提高社会对精神疾病患者的保障水平。社保体系要逐步向外来人口延伸,缩小不同患者群体的保障差距,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
5.4 加强精神卫生才梯队建设
加强人力资源的配置,重视对精神卫生人才队伍的建设和保障,对现有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创新,改变过去单一的教育培训模式,可以进行多种形式的业务技能培训,提升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服务能力。
5.5 转变社会、患者及家属的病耻感观念
政府领导带头转变社会、患者及家属的病耻感观念,通过普及科学的精神卫生与心理疾病防控知识、人文关爱理念,大力弘扬社会对精神心理障碍患者的尊重仁爱情怀,构建无病耻感的文化与氛围,开展多种形式的宣教,组织开展患者俱乐部,并让患者家属参与其中,定期为患者及家属提供交流的机会,让患者及家属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温暖,在日常生活中消除或减少病耻感;社区要尽可能地为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工作机会,减轻家庭负担,提高其生活适应性,以利于精神疾病患者重新回到社会。
5.6 加强信息化建设
尝试基于“互联网+”服务技术,通过对服务管理方、供给方、需求方充分的调研,围绕患者和社区居民的需求开发手机APP 软件,各方通过下载安装使用,有助于及时有效地完成医医、医患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各部门间的信息传递。在确保网络安全的情况下,其APP 数据可与政府系统对接,以利于多部门联动机制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