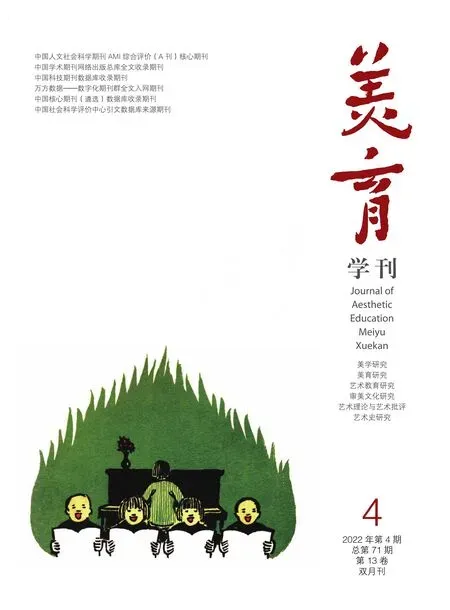论“作为艺术品的儿童生命”
——以尼采与德勒兹为进路
王 丽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作为艺术品的生命”是尼采美学的代表性观点,且在德勒兹的美学致思中得到继承与发展。在论述该主张时,无论是在尼采还是德勒兹的文本中,“儿童”意象均备受青睐。可以说,当美学之维成为思考“生命之所是”的重要向度时,“儿童”成了尼采和德勒兹诠释“作为艺术品的生命”的重要意象。“儿童”的凸显,使得单独且郑重地提出内蕴于“作为艺术品的生命”中的“作为艺术品的儿童生命”这一议题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本文立足儿童教育的视域,循尼采与德勒兹的进路,追问“儿童”何以与“作为艺术品的生命”这一命题密切相连,即从“作为艺术品的生命”出发,对“作为艺术品的儿童生命”进行审思。此过程,是彰显儿童教育的美学根性的重要前提。
一、尼采美学与“作为艺术品的 儿童生命”的提出
尼采对审美和艺术现象的哲思贯穿一生。至晚期写作《权力意志》期间,尼采仍在强调艺术的重要地位,形成了以权力意志为基石的生命美学。他始终如一地肯定生命的审美化,认为“唯有作为审美现象,此在与世界才是永远合理的”。他提出,生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人不再是艺术家,人变成了艺术品:在这里,在醉的战栗中,整个自然的艺术强力得到了彰显,臻至‘太一’最高的狂喜满足”。如果说“作为艺术品的生命”是酒神精神满溢的生命,也是“生命审美化”的应然状态,那么,儿童何以成为其阐释“生命审美化”命题时的重要意象?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来自赫拉克利特“世界是一个游戏的儿童”的启发与触动。
(一)儿童——生成游戏中的酒神精神
在希腊哲人中,尼采对赫拉克利特情有独钟,几无半句非议,始终视其为哲学史上与自己亲缘关系最近的人。可以说,赫拉克利特是尼采悲剧思维方式的源头活水。谈及酒神哲学的渊源时,尼采曾表示,在自己之前,没有人把酒神精神变成一种哲学激情。在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中,“多”是指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一”则是这些事物的本源。尼采认为,从巴门尼德和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被牢牢地规定为永恒静止的“存在”,以至于“存在”一词后来与“无限重复的静止”成为同义词。而与之相对,“多”就是变动不居的生成。唯有与赫拉克利特的思想相遇时,尼采才感到“心情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觉温暖和愉快。肯定流逝和毁灭,酒神哲学中的决定性因素,肯定矛盾和战争,生成,以及彻底否定‘存在’概念——我在其中不能不认出迄今为止与我最相像的思想”。借由赫拉克利特,尼采否定“一”而肯定“多”,将“一”置于“赫拉克利特那最能描述经验世界的生成论的对立面”。在此过程中,尼采与赫氏生成论中“游戏的儿童”相遇,并进行了接续性思考。
在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中,世界万物处于永恒无限的运动变化之中,正所谓“万物生一,一生万物”。他用“永恒之火”作为事物全部的象征,揭示世界的本质是生成而非存在。他曾说,“世界(Aeon)是一个游戏的儿童,玩着棋子游戏;主宰是儿童”(亦即是存在者整体的主宰)。在这里,赫拉克利特将世界或者永恒的活火譬作游戏着的儿童,而且用“主宰”来强调游戏着的儿童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在与成年人比较之时更为凸显:“所谓专家经常在思考时过于曲折和复杂,以至于他们见木不见林;相反,儿童在考虑问题时有一种特定的单纯,使他们能够立刻捕捉到一定的真理。”以儿童对语言的理解和领悟为例,赫拉克利特式的、具有浓缩性和丰富内在意蕴的语言,其出色听众的典范正是儿童。因为,“对于年幼者,语言是崭新的——一种快乐和实验的对象,一个新鲜的世界,在其中,真理在他们眼里是显而易见的,而大多数人却大大地错过了这些真理,因为对他们来说,不断的使用已经使语言变得过于稀松平常,不再具有启示性”。儿童较之于成人的优势在此过程中透显出来。
尼采赞成赫氏生成论,显然也被“世界是一个游戏的儿童”激发,对其进行了回应。但值得强调的是,尼采的回应并非只是对赫拉克利特话语的简单重复和解释,而是借由赫拉克利特“游戏着的儿童”继续其“生命审美化”的阐发:“生成和消逝,建设和破坏,对之不可作任何道德评定,它们永远同样无罪,在这世界上仅仅属于艺术家和孩子的游戏。如同孩子和艺术家在游戏一样,永恒的活火也游戏着,建设着和破坏着,毫无罪恶感——万古岁月以这游戏自娱。”在尼采的表述中,世界不仅是永恒活火的游戏和孩子的游戏,同时也是艺术家的游戏。儿童与艺术的并置,而且“仅仅”与艺术并置,使游戏着的儿童与生命的审美维度紧密联结,也使得创作着的艺术家与游戏着的儿童呈现着同质的生命状态。进而,此两种意象均与世界的生成本质相呼应。尼采进一步阐释:“它(火)把自己转化成水和土,就像一个孩子在海边堆积又毁坏沙堆。它不断重新开始这游戏。它暂时满足了,然后需要又重新抓住了它,就像创作的需要驱动着艺术家一样。不是犯罪的诱力,而是不断重新苏醒的游戏冲动,召唤另外的世界进入了生活。孩子一时摔开玩具,但很快又无忧无虑地玩了起来。而只要他在建设,他就按照内在秩序合乎规律地进行编结、连接和塑造。”尼采在强调,儿童和艺术家不是任意玩耍,而是投入且陶醉地创造,在不断地重新开始中内在地生成秩序。不仅“世界是一个游戏的儿童”,而且“世界是一个游戏的艺术家”,因为这二者所呈现的正是充满着酒神精神的生成游戏,亦是充满着酒神精神的审美化生命——作为艺术品的生命。
早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便提及赫拉克利特式的儿童游戏,并将其视为对酒神精神的恰当表现:所谓在悲剧中既想要观看又渴望超越观看的状态,“是一再重新把个体世界的游戏式建造和毁灭揭示为一种原始快感的结果,其方式就类似于晦涩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把创造世界的力量比作一个游戏的孩童,他来来回回地垒石头,把沙堆筑起来又推倒”。既想要观看又渴望超越观看,既想要倾听又渴望超越倾听,既想要严肃地投入游戏又想要超越地静观,“既以静观的态度凌驾于艺术品之上,又能动地置身于艺术品之中”。这其中既包含着注定毁灭的存在者,又充满着不断觉醒的游戏冲动和生生不息的生成。这正是尼采所说的酒神现象,也是其理解中的赫拉克利特式的生成游戏的本质。
(二)儿童——超人的诞生
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始,尼采开启了其哲思的最后一个阶段,即所谓“权力意志”时期,也是一个尤其重视美学与艺术的时期。而恰恰是在这个再次思考美学与艺术问题的时期,“儿童”作为核心意象耀眼地出现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喻示着超人的诞生:“我要向你们指出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狮子如何最后变成小孩。”骆驼身负精神的重担,贬抑自身,是对生命力和自由的否定。骆驼向狮子的变形,意味着虚弱的生命开始恢复猛兽的强壮之力,意味着人生负重的瓦解。但是,狮子只是取得了想要的自由,却不能创造。最后,超人诞生于儿童之中,儿童是人的超然—应然状态。
为何是儿童?尼采自析:“小孩还能做什么连狮子都不能做的事?何以掠夺性的狮子必得变成小孩呢?小孩乃是无辜和遗忘,一个新开端,一种游戏,一个自转的轮子,一种原初的运动,一种神圣的肯定。”由于儿童的无辜和遗忘,他们没有重负和内疚,他们代表着新的力量、原初的运动,自发地运转。儿童的生成游戏在不断的重新开始中肯定着、创生着世界和生活,体现着“自转的轮子”般的“永恒轮回”,这是一种生成性的肯定。这种肯定之所以神圣,尼采进而阐述:“为着创造的游戏,需要有一种神圣的肯定:精神现在意愿它自己的意志,丧失世界者要赢获它自己的世界。”这里的关键是,精神想要有它自己的意志、想要肯定自身。“孩子无辜自在的圆圈式游戏恰是全书思想和体验的顶峰,是权力意志在意愿永恒轮回之后所呈现的境界,真正的超人或当由此诞生。”可以说,尼采晚期哲思中的三个核心——“权力意志”“永恒轮回”和“超人理想”,在“儿童的生成游戏”中得到了统一。
进一步,尼采在其儿童意象中释放出的生成性的肯定之力,使儿童审美化生命的创造性本质更加凸显,“作为艺术品的生命”在“超人”儿童这里得到充分体现。无论是权力意志还是永恒轮回学说,在尼采这里始终具有艺术哲学的旨归。生命的本质是权力意志,是求强力的意志,而作为人类创造性活动的艺术正是这种生命本质的基本实现方式,“艺术乃是强力意志最易透视和最熟悉的形态”,“是对人生此在的肯定、祝福、神化……”而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源于其永恒轮回学说,永恒轮回学说的要旨就在于生命的创造性,内蕴着艺术哲学的求索。“永恒轮回学说中最沉重和最本真的东西就是:永恒在瞬间中存在,瞬间不是稍纵即逝的现在……而是将来与过去的碰撞。在这种碰撞中,瞬间得以达到自身。瞬间决定着一切如何轮回。”在生命的每一个瞬间,做出生存决断的依据都出自每个人自己,将来生成的东西正是一个瞬间要决断的事,“轮回之物——如果它要轮回的话——取决于瞬间,取决于那种力量”。以这种方式存在的生命就是审美化的生命,也就是超人——儿童是超人,儿童的生命成为艺术品。
二、德勒兹美学对“作为艺术品的 儿童生命”的承续
“生命”不仅是尼采思想中一个闪闪发光的概念,也是德勒兹哲思的核心。德勒兹对尼采的追随,反映在其对生命意义之丰富可能性的不断思索。“作为艺术品的生命”系德勒兹谈到福柯的一段著名访谈的标题。这一标题鲜明地显示着他与福柯同样认同的、承续自尼采的理念。同时,德勒兹的思想“带着童年的动机——充满童趣的愿望,重新思考刻板印象和陈词滥调,唤醒尚未思考的空间……”,因此,“作为艺术品的儿童生命”在德勒兹美学中蓬勃生长。
(一)儿童——“生成之在”
作为“创造概念的大师”,德勒兹创生并运用“无器官的身体”“根茎”“解域”“游牧”“平滑空间”等诸多概念来呈现其差异哲学和美学思想。其中,“生成论”是最重要的基石之一,甚至被认为具有后结构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对“生成”的思考,亦成为德勒兹对“作为艺术品的生命”继续诠释的关键理路。
德勒兹将儿童游戏作为激活尼采的重要切入点,发展出自己的生成本体论。他认为,赫拉克利特和尼采意义上的儿童游戏不同于那些“人们既会赌输又会赌赢的糟糕游戏”,正如那个海边孩童的玩沙游戏,“这种游戏不再有预先存在的规则,因为这种游戏已然指向了它自己的规则,因为儿童—游戏者只能赢——每一次都肯定了所有的偶然”。德勒兹通过诠释尼采所述的掷骰子游戏来进一步说明上述的儿童游戏:“肯定不再是约束性的或限制性的,而是与被提出的问题和产生问题的决断同外延:这样一种游戏引起了必然会赢的骰掷之重复,因为它在其自身的回归的系统中不断地囊括所有的组合与所有的可能规则。”德勒兹强调,“尼采把偶然性变成了肯定”。掷骰子的游戏包含着掷出和落回这两个时刻,这一过程发生于大地和天空这两张不同的桌子上。但是,“这两张桌子并非两个世界。他们是同一世界的两段时间,同一世界的两个时刻,是午夜与白昼……”在掷骰子的过程中,“并非大量的投掷次数导致组合的重复,而是有限的组合数目导致骰子的重复。被掷出的骰子是对偶然性的肯定,它们落回时形成的组合却是对必然性的肯定。必然性为偶然性所肯定,恰如存在为生成所肯定,统一性为多样性所肯定”,因此,“知道如何肯定偶然,就知道如何游戏”。骰子落回的时刻是结果显现的时刻,是对必然的肯定,但“它同时又是第一个时刻的回归,是投掷的重复,是偶然本身的再生与再肯定。永恒回归中的命运是对偶然的‘迎接’”。质言之,德勒兹强调尼采永恒轮回说的时空法则就是生成。永恒轮回是“生成之在(the being of becoming),是生成本身的存在,是在生成中被肯定的存在”。在诸如孩子们和艺术家的生成游戏中,是“生成之在在跟自己玩着游戏”。
德勒兹坚称,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隐匿在生成之流背后,“在生成之流之外无物‘存在’。所有的‘存在者’都只是生成—生命之流中相对稳定的时刻”。可以说,在“生成”的意义上,生命表现为一种对既成的抗拒,拒绝一种被概念化了的经验,并于经验的生成之流中,展开生命无与伦比的力量。生命是生产性的,而非再现性的。“生成之在”是充满差异的轮回。人不是再现生命的普遍目的以及遵循先在原则所赋予的生存方式(如文化的、共识的等控制符码),而是应该从局限生命的普遍目的和形式中逃逸出来,并不断实验、创造出新的样态。这样的生命就像艺术品一样,在开放中探索多样性的生成,期待新的组合在实践中被遇见。
德勒兹通过对尼采的诠释,在儿童游戏所呈现的意象中,强调着“生成”的创造性、差异性、多样性、肯定性。生命在“生成”的角度上成为艺术品。然而,德勒兹并没有止步于解释尼采,在其晚期的文本中,他“从对尼采的解释而转向一种借助尼采的试验”。这些思想实验使德勒兹的“生成”越出了永恒轮回的涟漪,从而在蔓延的根茎、无器官的身体、逃逸线、游牧等诸多具有创造性的概念中更深层地回到生命本身。这些概念也揭示了“作为艺术品的生命”与“儿童”之间更为多元且深入的连接。
(二)儿童——“无器官的身体”
“无器官的身体”是德勒兹借鉴自法国先锋戏剧大师安东尼·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概念,是其关于“身体”的核心概念。“无器官的身体”不是与“器官”相对立,而是与被称作“有机体”的“器官的组织”相对立。正如阿尔托发动的对有机体的战争:“身体就是身体。它是单一的。它不需要器官。身体决不是一个有机体。有机体是身体的敌人。”有机体将“器官”之间的划分和各自功能的界定作为固定的、先在的、理想性的本质,而无器官的身体强调的是在本质上尚未编码的身体,这时的身体还未屈从于各器官的限定而成为某种单一的统一体,因此具有非确定性、无限生成和发展的可能性与开放性。无器官的身体“力图把‘器官’放回到身体自身的生成运动中来理解其‘暂时性’和‘器官’彼此之间本身就存在的内在关联”。可见,在德勒兹这里,无器官的身体就像是生物形成个体之前的“胚胎”,是生命自身进行实验和生成的“介质”。他直接用“卵”的特征生动地说明了无器官的身体所凸显的强度性和非确定性。无器官的身体“就是卵”,“卵就是纯粹强度的介质,是非广延的空间,是作为生产的本原的强度0。在科学和神话之间、胚胎学和神话学之间、生物的卵和物理的或宇宙的卵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会通:卵始终指涉此种强度性的实在,后者并非未分化的,但在其中,事物和器官仅仅通过级度、迁移和邻近的区域而彼此区别”。沿着德勒兹的思路,幼儿身心的混沌互渗、未精确分化等特点是无器官的身体的非确定性的表现,而如杜威所述幼儿的“未成熟性”所内蕴的生长力则是纯粹强度的体现。当然,德勒兹并没有止步于解释何为“无器官的身体”,而是更进一步,以“童年”为例揭示无器官的身体作为生命自身进行实验的“内在性平面”所创生的意义。
德勒兹解释说:“无器官的身体是童年的阻断,是生成,是一种童年记忆的对立面。”也就是说,他所揭示的身体“实验”,并非身体试图回到“起点”、回到结构尚未形成前的“卵”或者“混沌”,因为这是消极的“退化”而非积极的“创造”。无器官的身体表现的是一种新的存在向度和意义的创造,而这种“实验”显然是始终与身体并存的,“无器官的身体并非‘先于’有机体;它与有机体相邻,并不断地处于构成自身的过程之中,它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同时性的回卷”,它描绘的是身体积极能动的状态,它不是倒退回“过去”,而是向着未来的“生成”。
“无器官的身体”携带着阿尔托戏剧艺术的基因,且德勒兹将它的解释力彻底地释放在艺术领域,这使得“无器官的身体”成为联结“儿童”与“艺术”、理解“作为艺术品的儿童生命”的重要中介。德勒兹专门著书《感觉的逻辑》,细致深入地分析了英国当代画家培根的画作,阐明了艺术创作中新意义的创生过程。他通过“无器官的身体”强调了感觉的两大特性:开放性和综合性。开放性是指感觉的变化生成、积极能动的状态;综合性是强调异质要素间的全新的关联。这也使感觉突破了作为既定事实的第一种含义,而具有了第二种含义,即作为可能性的感觉。“培根一直在说,感觉,就是从一个‘范畴’到另一个范畴,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东西。”“无器官的身体”的概念为理解“通感”现象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德勒兹看来,培根画作的伟大之处在于穿越了视觉与触觉的界限,达到了一种全新的视觉:触觉般的视觉。“培根的绘画以纯粹的形象取代了具象绘画,从而在抽象与具象之间,找到了第三条道路,拯救了形象在20世纪的命运。……这一探索的本质就是用一种具有触摸能力的视觉,取代纯粹的视觉……”德勒兹提出,“画出感觉”是培根和塞尚的共性,而更早的古埃及艺术也具有同种特性。可以看到,内蕴着儿童生命状态的“无器官的身体”概念,对于培根、塞尚等艺术家的创作具有解释力,同样,对于在幼儿艺术活动中经常出现的通感现象、幼儿的触觉型绘画特征亦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艺术家的创作状态与幼儿的生命真实状态在此角度实现相通,这也是理解“艺术家向儿童学习”的重要视角。正如塞尚曾发出的感叹:要是我们只能用新生儿的眼睛看有多好!他直接用孩子来表述自己的绘画状态:“你就应该用一颗稚子童心去忠实记录大自然。……一旦一管管颜料在侧、一支支画笔在手,我就仅仅是一个画家,最最单纯意义上的画家,一个小孩子。……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画着,画着,画着。”质言之,在德勒兹看来,培根、塞尚之所以是伟大的艺术家,是因为他们创造着“感知物和感受的聚块”,彰显着“无器官的身体”的开放性和综合性。这些特性在儿童的生命状态中闪耀着令成人艺术家羡慕的光辉,儿童生命本身即为真正的艺术品。
(三)儿童——“一种生命”
德勒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仍是围绕“生命”,且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总结性概念——内在性:一种生命(UNE VIE)。在他看来,“一种生命”是纯粹内在性,是内在的内在,即绝对内在:它是满满的潜能和至福。作为内在性平面,德勒兹所定义的“一种生命”与经验性生命相区别,既非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也非心理意义上的生命。它超越了传统哲学对主体和客体的二分,作为先验场域,“显示为一股纯粹的主观意识流,一种前反映的非个性意识,一种无我意识的质的绵延”。德勒兹强调,“一种生命”所呈示的是某种达到了至善状态的“纯人”(Homo tantum),“一种纯粹内在性的生命,没有明显特征、超越善与恶的生命,因为只有在万物中实现了这种内在性的主体才使其变得好或坏。……一个单一的本质,一个生命……”“一种生命”强调生命的“独异性”,这是生命之“一”,即生命体现出一个统一的、超越的指向。可以看出,超越而独异的“内在生命”与德勒兹另一个根本论断密切呼应:哲学是“形成、发明和制造概念的艺术”。在这个命题中,“概念”只是衍生的产物,创造才是真正的本原。同样,“一种生命”作为具有“单一”本质的内在性平面,其“满满的潜能”指向的正是创造的本原。
在德勒兹这里,凸显着创造的本原,同时又超越善恶的“一种生命”,具有了超越传统美学与伦理学之间界限的可能性。因为,在德勒兹看来,或者在德勒兹对尼采的解读中,生命是无辜的,它不能被置于某种外在理念的评判之下,生命本身就是一种肯定:“存在不是肯定的对象,如同存在不是呈现自身,也不是把自身托付给肯定的一个要素……肯定本身就是存在,只有存在才是肯定的全部内涵。”那么,生命自身能否被评判?在这一问题上,德勒兹赞同尼采,认为没有“善恶”,只有“好坏”:善恶判断是规定性判断,是绝对的、外在的(判断和生存实际相分离)、无条件的、无例外的,而好坏则是相对的(视角主义)、内在的(好坏内在于生存实际)、描述性的、有条件且充满例外的。德勒兹认为,尼采意义上的“坏”就是“被耗尽的、退化的生命,它非常可怕并可以扩散”。而与之相反,“好”则是“蓬勃的、进化的生命,它懂得因势利导,根据自身遇到的力量改变自己,并同这些力量一道构成一种更加强大的强力,永远开拓新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以力和力的生成来评判生命。用德勒兹的话来说:“宁可让感受作为内在评判,也不判决超验价值。”可见,作为生成、感受的生命正是指向生命本身的肯定,亦即指向生命的创造本原。通过激活尼采,德勒兹所要强调的是,“肯定是去创造生命的新价值,使生命更轻松和能动的新价值。确切地说,只有当我们尽其所能去发明生命的新形式而不是将生命与其能力分开时,才会有创造”。
在“一种生命”的概念中,德勒兹将美学与伦理学相联结,伦理学被重新定位为生命的伦理学、内在性的伦理学,“这种伦理表征的是一种内在的创造潜能,它根植的论域不再是意识层面上的先验的、神圣的道德律,相反,它关注的是个体身体被影响的能力、力量”。这一重新定位,使“生命得以作为一件艺术品而存在,成为既强大而又幸福的东西”。“一种生命”也因此成为德勒兹生命美学的核心概念。
在德勒兹看来,“一种生命”并不局限于诸如面对死亡等特殊时刻,而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体现出非主体性、非个体性、非个人性,只要我们摆脱了主体、客体以至主客之分这些超越性幻觉,就能达到它。阐述至此,儿童的生命状态成为德勒兹所选择的、最恰切且有力的例证:“非常小的儿童都相像,几乎没有什么个性,但他们都有单一性:一种微笑,一个姿势,一个鬼脸——不是主观属性。”在他看来,通过克服痛苦和柔弱,小孩们展示了一种非主体的与非个人的生命力量,被一种内在性的生命贯注,这是一种纯粹的力量,一种至福。更进一步论,在德勒兹这里,经由“一种生命”的概念,“作为艺术品的生命”通过儿童意象获得了诠释。也可以说,“作为艺术品的儿童生命”至此成为对“一种生命”的直接注解。
三、余论
尼采与德勒兹美学中的儿童意象,开辟了一条省思“儿童生命”,进而继续“发现儿童”、丰富“儿童观”的美学进路。通过这条进路,“作为艺术品的儿童生命”得以确证,儿童生命本质的美学维度得以呈现,进而,儿童教育的美学根性得以彰显。
需要强调的是,美学根性不同于美学属性。所有年龄段的教育在本质上都具有美学属性。通过杜威(John Dewey)、格林(Maxine Greene)、艾斯纳(Elliot W.Eisner)等一批学者的探究,以美学的视野和方法论来对教育发展进行积极探索与主动建构已经成为教育研究的一种重要视角。然而,在教育实践中,教育的美学属性常常被遮蔽,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艺术品的儿童生命”使我们看到,对处于生命早期阶段的儿童来说,仅在一般意义上阐述并强调教育的美学属性并不足够。因为,教育对象的年龄越小,教育的美学属性越具有内在性与本体性,美学属性愈加应该被推进至美学根性的深度予以重视。可以说,“作为艺术品的儿童生命”需要并决定了儿童教育的美学根性。强调儿童教育的美学根性是对儿童的审美化生命的必要呼应,体现为教育对儿童的创造性生命状态的肯定、欣赏与支持,从而使儿童生命得以作为一件艺术品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