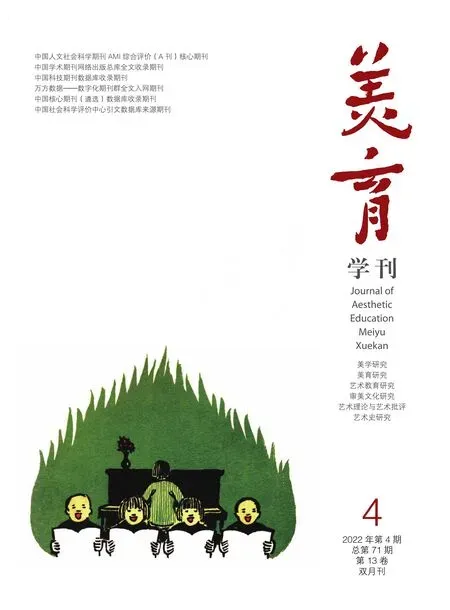审美体验的科学性
——从朱光潜“美本质”问题的逻辑起点出发
周 丰
(上海社会科学院 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020)
21世纪已经走过了五分之一,距克莱夫·贝尔提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已有百年,距黑格尔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也已过了两百多年,距柏拉图提出“美是‘理式’”更是已有两千五百多年。从柏拉图直至朱光潜的两千多年中,关于“美本质”的讨论一直走不出精神与物质的二分、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即便是今天,关于“美本质”仍存在着客观论、主观论和关系论等三大争论,学者们提出了“典型说”“和谐说”“历史积淀说”“主客观统一说”和“主体实践说”等关于“美是什么”的观点。然而,这些讨论却都没有走出二分的局面,这种二分的原因究竟何在?“主观派认为美在意识;客观派认为美在物质;主客观统一派认为要在人的活动当中,尤其是物质生产实践中来寻找美的根源。”然而,将三者放在一起不难发现,三者似有对垒,但整体上却是一种中和。显然,审美中包含了主体与客体。即便是第三种解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主客体的关系问题,但仍不能对前二者的存在作出解释。
一、朱光潜“美本质”问题的 逻辑起点
“美”这个词经常挂在人们口中,似乎不需要解释,但一经提出便成了一个难题。这个问题的存在到底是怎样的?主、客观之争的症结是什么?朱光潜曾在《文艺心理学》中对美的性质问题有过一个很好的讨论。在此,借朱光潜对美的发问做一个引子。
我们说花红、胭脂红、人面红、血红、火红、衣服红、珊瑚红等等,红是这些东西所共有的性质。这个共同性质可以用光学分析出来,说它是光波的一定长度和速度刺激视官所生的色觉。同样地,我们说花美、人美、风景美、声音美、颜色美、图画美、文章美等等,美也应该是所形容的东西所共有的属性。这个共有的属性究竟是什么?美学却没有像光学分析红色那样,把它很清楚地分析出来。
美学何以没有做到光学所做到的呢?美和红有一个重要的分别。红可以说是物的属性,而美很难说完全是物的属性。比如一朵花本来是红的,除开色盲,人人都觉得它是红的。至于说这朵花美,各人的意见就难得一致,尤其是比较新比较难的艺术作品不容易得到一致的赞美。假如你说它美,我说它不美,你用什么精确的客观的标准可以说服我呢?美与红不同,红是一种客观事实,或者说是一种自然现象,而美却不是自然的,多少是人凭着主观所定的价值。……美的审别完全是主观的,个别的,我们也就不把美的性质当成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因为科学目的在于杂多现象中寻求普遍原理,普遍原理都有几分客观性,美既然完全是主观的,没有普遍原理可以统辖它,它自然也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了。但是事实又并非如此,关于美感,纷歧之中又有几分一致,一个东西如果是美的,虽然不能使一切人都觉得美,却有多数人觉得美。所以美的审别究竟还有几分客观性。
朱光潜是西方美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可以说这段关于美的论述是朱光潜对西方美学史的提炼性认识,因此,某种程度上这种关于“美本质”问题的认识基本上代表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对美的认识。在西方美学中,从苏格拉底开始,美作为事物的属性,就已被打上了存疑的标签,而这个问题也与“美本质”问题存疑相始终,试看西方美学史上关于“美本质”问题的论断:
苏格拉底:“同一事物同时既是美的又是丑的。”
柏拉图:“年轻小姐比起神仙,不也像汤罐比起年青小姐吗?比起神,最美的年轻小姐不也就显得丑吗?……黄金在用得恰当时就美,用得不恰当时就丑,其它事物也是如此。”
普洛丁:“同一物体,时而美,时而不美,仿佛物体的实质并不同于美的实质。”
笛卡尔:“所谓美和愉悦所指的都不过是我们的判断和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人们的判断既然彼此悬殊很大,我们就不能说美和愉快能有一种确定的尺度。”
布瓦洛:“实际上只有后代的赞许才可以确定作品的真正价值……有一些作家在许多世纪中都一直获得赞赏,只有少数趣味乖僻的人(这种人总是随时都有的)才瞧不起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如果要对这些作家的价值有所怀疑,那就不仅是冒昧,而且是愚蠢了。如果说你见不出他作品的美,你不能因此就断定它们不美,应该说你瞎了眼睛,没有鉴赏力。”
休谟:“美并不是事物本身里的一种性质。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每一个人心见出一种不同的美。这个人觉得丑,另一个人可能觉得美。每个人应该默认他自己的感觉,也应该不要求支配旁人的感觉。”
狄德罗:“美是一个我们应用于无数存在物的名词。存在物之间纵有差异,若非我们错用了美的名词,便是这些存在物皆有一种性质而美这一名词即其标记……哪一种性质?那只能是它一出现,就使一切存在物美的性质。”
可以看出,每个时代都默认了一点,一件事物可美可不美,美难以确立为事物的某种属性:不同的人在看同一件事物的时候会有美丑的差别;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看待同一件事物,有时是丑的,有时是美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可能有人会说,审美体验活动是人的主观性活动,会随着人的审美心境和经验的改变而改变。这是美在主体论。但显然先贤们在讨论美时,首先是以作为对象的事物而引发的,如苏格拉底的“事物”,柏拉图的“小姐”“神”与“黄金”,普洛丁的“物体”,等等,都是由物出发。最为典型的当属乔德之问:世界上如果没有了人,而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依然如故,那么,“难道会有任何变化发生在这幅画上吗?难道对它的经验会有任何变化吗?……唯一发生的变化只不过是它不再被鉴赏罢了。但难道这会使它自动地变得不再是美的了吗?”这便是美在客体论。然而今天我们所说的“美在主体”“美在客体”“美在主客体的关系”等论说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显然,美的主客体之争并不能仅仅用“鉴赏力”和“感觉”的差异来解释。或许可以从休谟和狄德罗的思路来思考:“美”能不能成为一种性质?这种性质又意味着什么?作为审美体验活动的核心或“产物”,它应该由谁主导?抑或主客体之间不存在谁主导谁,审美体验是在这个场域中自然生发的?对于美学史上由来已久的美的主客体论的问题,朱光潜的理解极为清晰透彻,本文即以朱光潜的论述为起点,对此问题继续展开探究。
朱光潜指出,若是存在美的本质,那么这个本质就应该是“所形容的东西所共有的属性”,然而,美并不像“红”那样作为一种属性而具有普遍性,即若花是红的,除色盲人人都觉得它红,并且“红”是可以进行光学分析的科学问题。而若花是美的,却并非人人都觉得它美。“美的审别完全是主观的,个别的,我们也就不把美的性质当成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但一个事物若是美的,“虽然不能使一切人都觉得美,却有多数人觉得美。所以美的审别究竟还有几分客观性”。显然,这就是关于“美本质”问题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症结所在。朱光潜在论述中持有这样一种态度:美若要成为事物的属性,似乎所有的人都要对某一物件持美的态度,才能说美是该物的属性。在此,我们不妨先梳理一下其中的逻辑:
前提,
a.红,是所形容东西的共有属性;美,也应该是所形容东西的共有属性;
b.若花红,除开色盲人人都觉得花红;但若花美,并非人人都觉得花美。
结论,
c.美不像红一样,即美不是所形容之物的共有属性。
其中存在一个逻辑转折:从“花红”“胭脂红”“人面红”和“花美”“人美”“风景美”转到了“花的红”和“花的美”,由美所形容的事物群体直接转到了单个事物,并意味着只有当这单个事物在人人(群体)看来都会产生这种效果时,才能被看作是美所形容的事物,才可以说具有美的属性。这里的逻辑问题在于,花红、人面红、血红、火红等是基于个体对一个群体共性——“红”的认识,而转向“花的红”和“花的美”时则意味着群体对个体的认识,但这个逻辑中仍提示群体对个体保有一致的认识,即“花”是“红”的,“花”是“美”的。
此外,日常生活中存在一种认识惯性:“红”或是其他感知认识,如色彩、轻重、缓急等,几乎人人都可以有一致的认识。如此一来,人们便会形成一种认识惯性并类比于美的问题。笛卡尔、布瓦洛、休谟等在讨论美作为一种属性的时候,也更多关注它作为一个范畴的群体性特征,这也是一种认识惯性的体现。如果“红”是所有红色事物的共有属性,而“美”对其所形容的事物来说也必然是其共有属性。如果任何个体都将上述所列事物判断为“美的事物”,那么,“美”就是这些事物的共同属性。
如前所述,对于“红”的一致认识要除开色盲,这个“除开”,言外之意就是要人们必须以“红”的判断为前提,对于色盲群体而言,“红”肯定不是他们认知中的事物的属性。因此,对于“美盲”群体而言,“美”也不会成为他们认知中的事物的属性。但问题就在于,并不是人人都会对特定事物产生审美体验,作出美的判断。如果表述得更准确些,便可以说:除开“美盲”,人人都会觉得它是美的。因此,原本的逻辑表述应当是:
前提,
a.红,是所形容东西的共有属性;
b.花红,除开色盲人人都觉得花红;花美,除开“美盲”人人都觉得花美。
结论,
c.美,也是所形容东西的共有属性。
笔者认为,其中微妙的逻辑偏差正是使得“美本质”问题陷入瓶颈的重要原因之一。审美活动首先是一种个体活动,个体之间对某物的态度本就是有差异的。显然,朱光潜对“美本质”问题的讨论绝不是一种个人的认识,而是一种集体性认识。在此,我们需要回到问题的逻辑起点,重新认识“美本质”问题。美作为一种认识态度,绝不是人人对某物都表现出一种一致的欣赏愉悦态度才能继续言说“美本质”问题,只要有审美体验产生,只要我们获得一种审美判断的信号,那么这种体验的发生方式就一定是一致的。所有使人产生审美体验的事物,其中也必然存在着某种一致性。这就是美的本质,只是在此,它“已然不是形而上学实体论意义上的‘本质’,而是把‘本质’视为复杂现象背后统一的属性、原因、特征、规律等”。
在此,还需指出属性与本质的关系。属性,即性质,“事物的性质是多方面的,可分为根本性质和一般性质两类。其中根本性质决定着一切事物之所以是该事物,其他性质则不具有这种决定作用。因此,根本性质也叫决定性的性质。本质就是事物根本性质或根本属性的简称”。可见,事物的本质也是事物的某一性质,而这个性质决定了某物之为某物,美所具有的本质决定了美的存在。“美本质”是美之所以为美的性质,是美的根本性质;而美作为事物的一种属性,是事物的一种性质。这也是问题逻辑偏差的一部分。因此,“美作为事物的一种属性”与“美的本质”之间具有这样一种关系:只有美作为一种属性的确立,或者说这个命题是合法的,我们才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讨论“美本质”问题。而“美作为事物的一种属性”的体现必须从“美的发生”开始,也就是审美体验。
二、审美体验的科学性
欲言说美的本质,必先言说审美体验。换言之,审美体验是“美本质”问题的前提。贝尔也曾指出:“所有美学体系的起点一定是个人对某种独特情感的体验。”然而,如朱光潜所言,对“红”进行科学分析之前,必先是我们产生了“红”这种感知或曰体验,我们的分析是以“红”的体验为起点,“为什么花看起来会是红色的”这种科学分析也正是如此。科学分析的对象是“红”这个色彩吗?显然不是,科学所分析的是“红”得以形成的物理与生理基础,即使是对色盲的研究,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物理与生理的差异。我们在对任何事物进行探究之前都必先给予其一个明确的命名或界定,这个命名也正是由感知而来的。我们的探究也只不过是逆向地回到感知的起点,梳理这种感知得以形成的起因与过程罢了。因此可以说,对事物的感知体验也是我们反思事物本质的前提。体验,是进入事物的唯一通道。
可能有人会问:色盲是可以用科学手段分析出来的,是以一定的物理和生理数据为基础而认定的,那么,“美盲”又当如何界定呢?我们是否可以用一定的物理和生理数据来确定审美体验是否发生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此,笔者将“美盲”视为无审美体验的发生状态,“美盲”并不是由先天的生理缺陷造成的,“美盲”是一种认知的缺失。正常人的大脑或多或少地都能产生审美体验,换言之,我们并不总是会有审美体验的发生,就像对于康定斯基的《哥萨克人》,在有的人看来,可能这就是涂抹乱画,而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这就是艺术,这是基于他们的审美体验。换言之,在面对《哥萨克人》时,有些人会有一种美的认知缺失,即表现出“美盲”状态。
“美盲”就是无审美体验发生的状态,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显然这种“无”的状态是占大多数的。因此,判断“无”的状态正在于确定“有”的状态。我们怎样才是真的发生了审美体验呢?这些曾经被视为主观的、个别的审美体验在今天能否进行科学的分析?显然,通过上述的逻辑演绎我们是可以重新确认,美能够成为其所形容事物的一种属性。只是,这种属性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介入这种属性?为何朱光潜认为这种属性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是科学无法分析的?笔者认为,这种科学性的疑惑,也正是主观与客观之争的起因。科学,意味着客观性、统一性,主观的认知属性意味着不确定性。然而,这些在朱光潜时代所谓的“不科学性”今天又能获得怎样的诠释?主观到底意味着什么?按朱光潜的思路,审美体验作为一种主观认识活动,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几乎无法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说,如果能够解决以上几个问题,就可以确立审美体验的科学性。
进一步说,这个问题可以切换为“主观何以具有客观性”的问题。不止美学,心理学领域也与该问题深度关联。1862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开设了“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课程。同年,冯特在《对感官知觉理论的贡献》中第一次提出了“实验心理学”概念。1879年,冯特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的独立。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心理或意识,在当时来看,意识就是主观的,意识不会成为科学,这违背了科学的客观性。尤其是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对“意识”的研究更是将之神秘化。后来新兴的行为主义者如华生,在《行为主义观点的心理学》(1919)中批评道:心理学不是研究心理的科学,而是研究行为的科学,并极力扭转心理学的科学地位。“从一种极特殊的意义上可以说,行为主义乃是西方心理学追求实现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观念的学术实践的必然产物,是这种实践追求的逻辑的完成形式。”可以说行为主义对意识的否定违背了心理学学科的研究对象。20世纪60年代的人本主义抓住了行为主义本身的缺陷,凭借对行为主义的批评一跃成为当时心理学研究的主流思潮。人本主义强调意识是心理学的立足点,纠正了行为主义的异化,使心理学回归其本身。但人本主义的不足在于它秉承的是人文科学观,这是与“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相悖的。在人本主义兴起的同时,认知心理学也对行为主义发动了革命,认知心理学对行为主义的抨击点也在于行为主义对意识的否定,认知心理学不仅回到了意识,而且沿袭了“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以科学的方法与先进的工具对人类思维、记忆等高级认知过程进行研究。认知心理学“强调认知主体的能动作用,以及认知主体既有的经验、知识在信息加工过程中的作用,这对于研究人的心理活动的本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至此,心理学的发展路径“从精神分析到行为主义,从行为主义到人本主义,再从人本主义走向认知心理学,恰恰体现了对‘意识’研究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历程。而这个历程的原动力正是‘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主观认识活动在认知心理学中获得了客观性。“物理世界与思维的分立以及与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大脑处理感觉信息方式的分立,都是人为的分立”,甚至可以推演,审美活动是心理活动之一种,心理活动又是生理活动的结果,而生理活动又完全基于物理活动。
进入21世纪的今天,审美体验已然成为了科学研究的对象。早在1999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神经生物学教授萨米尔·泽基(Semir Zeki)就已指出:“我们正要开始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探讨艺术的意义。除此之外,我还希望能在美学的神经学(neurology of aesthetics)或者说神经美学(neuro-esthetics)的基础理论的建设上略尽绵薄之力,让人们能够更为深入地认识审美体验的生物学基础。”神经美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融合了神经生物学、脑科学、认知心理学及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此,审美体验不再是一种不确定的、不可分析的谜团,神经美学对审美体验的实证研究为原先美学对美的讨论提供了切实可靠的证据。神经美学以审美的愉悦感作为效果,由此出发,通过近来发展出的脑成像技术来探究相应的审美体验所对应的大脑区域及活跃表现。其中常用的技术有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以及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ET)等。这些技术大多是通过多种示踪剂(一些带有放射性粒子同位素脑组织供给物,如带有碳、氢或氧的短时放射性同位素的葡萄糖)对脑组织灌注、葡萄糖和氧代谢以及多种神经受体的活跃进行跟踪成像。“这些技术背后的逻辑在于,大脑特定区域的神经活跃需要大量的能量与氧的支持,因此就需要大量的血液。如果我们能够追踪到血流明显增加的区域,就能够确定大脑当下活跃的精准区域。而后将这些监测结果与外部事件,如观看一幅画、听一段声音信号、思考、回忆等,就能得到一个外部环境刺激与相关皮层活动之间关系的详细印象。换言之,一种外部事件对应的大脑地图就可以被绘制出来。”总而言之,借用最新的科学手段,神经美学已经能够窥探到审美体验发生时大脑的内在活跃状态,审美体验的发生状态所对应的物理与生理数据已经可以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三、神经美学的发展对审美体验 科学性的贡献
朱光潜曾提出:“假如你说它美,我说它不美,你用什么精确的客观的标准可以说服我呢?”这个问题反映到神经美学中便是:实验者们是如何界定“美”“审美体验”“审美欣赏”或“审美判断”的?在实验心理学看来则是如何给“美”或“审美体验”下一个操作性定义。实验是神经美学的基本途径,神经美学实验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科学地呈现出审美发生及其性质。在实验中,艺术规律可能与视觉系统的规律呈现出同质性,视觉艺术不是概念性或静态的分析。实验的关键是实验中审美体验的现时性和个体性,这也是审美体验的关键特征。
神经美学的实验者对“审美体验”给出什么样的操作定义,决定了实验的方向和结果。从这个操作性定义中,我们能否找到“美的标准”?即实验者或被试如何判断审美体验的发生?审美体验发生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们需要借助一些神经美学具体的实验案例来说明这样一种无可争议的“精确而客观的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我们并不关注神经美学实验的结果,而是关注实验中对“美”和“审美体验”的操作性定义。合理的操作定义更意味着美可以被测量或量化,这就意味着“美的标准”。在此,我们需要理解神经美学实验史上的两个问题:其一,实验者如何定义“美”或“审美体验”?其二,他们的设计和操作能否支持他们的定义?根据这两个问题,神经美学实验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神经美学实验并没有自觉地对“美”或“审美体验”进行界定或研究。主要是对艺术的单个要素进行分析,如只针对视觉的色彩、图形或线条的脑成像研究,该阶段的研究并未脱离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生物学的范畴,只有很少的艺术作品被作为研究材料。这些艺术因素虽然都是公认的美的要素,却并不符合审美体验的现时性与个体性特征。
第二阶段,“美”被定义为“愉悦”(悲伤)或“对称”。在实验中,那些经常使人愉悦或悲伤的事物被用作实验材料,以跟踪其相应的活跃脑区。虽然实验者设计了“心理物理实验”(psychophysical experiments)来测试“美”“丑”,但这些结果可能并不能连接或保证下一步的脑成像实验。还有就是直接研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这里使用的是公认的艺术,但还不能摆脱先前的经验认识。
第三阶段的神经美学实验更为成熟,能够清晰地界定“美”或“审美体验”。这里的“心理物理实验”不仅为下一步的脑成像实验界定了“美”或“审美体验”,而且强调了审美体验的现时性和个体性,它不仅仅是脑成像实验的前提,甚至可以成为独立的、完整的一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阶段的划分并非仅基于线性时间的发展,更侧重于实验者对“美”或“审美体验”的判定标准或者说“操作性定义”的完善。
神经美学发展初期,研究者的实验设计并没有真正定义“审美体验”或“美”,这些早期的实验大多是基于艺术的元素如色彩、线条、饱和度、形状、对称性、面部或一段声音的加工区域及路径进行研究,以便找到相应的活跃脑区,如利文斯通(Livingstone)与休伯(Hubel)对色彩与眼睛、视觉与光强度的分析,索尔索(Solso)对视觉审美的信息加工中所涉及的各个要素、阶段与路径的研究,泽基(Zeki)与马里尼(Marini)的彩色与黑白色彩对照实验,等等。神经美学早期的实验中这种“判断标准”并不明显,或者说这些实验只是大而化之地涉及审美,审美体验的加工必然包含于视觉与脑的加工机制,视觉艺术也必然具有色彩、轮廓或形状等,因此,这些基本实验对审美体验的阐释并不十分精确,但在当时这也确实是一股新异的思想,为“美的规律”的思考注入了新的内涵。
中期的神经美学的特征表现为两点:其一,实验材料多以现有的艺术作品为对象,如名画、雕塑或音乐等;其二,实验的设计变得更加精确,例如“心理物理实验”,在成像实验之前使用李克特(Likert)量表,以确保下一个成像实验的有效性。显然,这些作品得到了大众的公认,一般人在面对这些作品时都能产生一定的愉悦感,即表现出审美体验状态。而实验的目的正是获取被试在观看或聆听这些作品时,其脑区的活跃表现。如川畑(Kawabata)和泽基(Zeki)研究了被试在观看多种类型的视觉艺术时其眶额叶皮层活跃的特点及差异,雅各布森(Jacobsen)等研究了被试在观看视觉艺术或几何图案时前额叶皮层的活跃性,等等。但问题在于被试是否一定会对其所观看的作品产生审美体验或审美判断,这显然是无法确定的。这些实验没有在操作中真正实现审美体验的个体性。有些实验者甚至对美或审美体验没有可操作的定义,就简单地把艺术的观看视为审美体验活动。
比如,在“Neural Correlates of Beauty”(2004)中,川畑和泽基研究了当被试观看各种视觉艺术刺激(肖像、风景、抽象绘画等)时眶额叶皮层活跃的特点和差异。在实验中,被试应首先将所有类型的绘画分为三类:在功能磁共振成像之前的心理物理测试中,根据李克特量表对视觉材料进行美、中性或丑的评级。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即使被试将某件作品评级为美,那么他在脑成像阶段的观看是否一定就是审美体验呢?脑成像实验阶段被试对每幅作品的观看即他所进行的审美体验时间仅仅只有2秒,2秒真的会发生审美体验吗?因此,这里就存在一个风险,实验所得的结果很可能是被试的一种概念选择或者观看而已,并不是审美体验所对应的神经基础。或许他只是在完成一个概念选择,而不是一个审美判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实验的设计并没有给予被试以主动权,他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限制内“被迫地”完成“审美”。因此,我们不得不对实验的效力和可靠性存疑。
此外,有学者如瓦塔尼安(Vartanian)和戈尔(Goel)的研究甚至没有心理物理测试环节,他们直接将被试的绘画观看视为审美体验;而雅克布森的实验则因“对称往往是美的标准”就直接将被试对对称的判断等同于美的判断,显然,雅克布森是将“美”界定为“对称”,因此,这一定义所得的结果也会和其他实验不同;乔治亚(Gerger)和莱德尔(Leder)等人则使用EMG技术对自然的(面孔)和人工(抽象)的刺激在长时间和短时间呈现下检测其吸引力的反应,这里“吸引力”被定义为“审美反应”。
上述实验中对“美”“对称”或“吸引力”的判断仅是基于被试自身的选择,且只有两个或三个选项:是/否,或美/不美/中性。因此,被试的选择就有可能决定实验的结果走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验设计的不足。
此外,还有实验对艺术家的创作活动直接进行脑成像研究。在这个实验中,肖像艺术家汉弗莱·奥切安(Humphrey Ocean)被要求在MRI设备中对一张照片进行肖像临摹。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一定是审美体验吗?第二,实验中的肖像临摹并不一定就是艺术创作,其中艺术件也未必具有审美体验。因此,实验所获得的脑成像并不能说明审美体验的什么内容,而只能说明艺术家在这个作画的过程中脑区活跃的具体表现。不过,索尔索已然认识到这一点,并与普通人的临摹任务所获得的活跃脑区相对照,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
在此阶段,艺术接受者和创作者都不能保证他们在观看或创作的实验过程中发生了审美体验,尽管实验被试在实验中报告了愉悦,愉悦被定义为对“美”或“审美体验”的判断。然而,对愉悦的实验研究是基于现有的艺术作品,如名画、雕塑或音乐。很明显,这些作品已经被大众认可为艺术,所以普通人面对这些作品时可能会有一定的愉悦感(包括悲伤)。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表现出审美体验状态,但也可能没有审美体验的发生,实验最终所获得的结果是被试看或听这些作品时所对应的脑区的活跃状态。
可以看出,前两个阶段的实验并没有明确界定审美体验的发生。他们只是用一种观看来确定相应的活跃脑区。第三阶段实现了审美评价与脑成像实验的有效结合,实验的设计与操作都更为成熟,能够充分实现审美体验的现时性和个体性。
首先,就审美体验的现时性来看,实验中仍然会在fMRI实验之前运用的“心理物理测验”量表,但不同之处在于,此阶段增加了一个测试用于剔除被试所熟悉的实验材料,以确保所有的实验材料都是被试第一次所见。因此,被试便不会根据以往的知识经验对他所面对的材料进行判断,他只会就他的当下体验来下判断。此外,在实验过程中,实验者经常要求被试用李克特量表来选择每件作品的愉悦(美)程度,最后根据外部的审美判断和内部的脑成像来识别审美体验的发生。其次,就审美体验的个体性来看,实验的设计给予了被试充分的时间,让他们做出审美判断。并且被试的实验结果最后还会有一个“评估问卷的个体差异分析”,以保证被试的判断不受其他人的影响。
此阶段的神经美学实验研究已经有很多。我们以维塞尔(Vessel)、罗宾(Rubin)与斯塔尔(Starr)的实验“The Brain on Art: Intense Aesthetic Experience Activates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2012)和石津(Ishizu)与泽基的实验“The Experience of Beauty Derived from Sorrow”(2017)为代表进行分析。
就现时性来看,“The Brain on Art”采取三种策略来消除先前经验的影响。其一,不选用通常复制的图像,以尽量减少再认。其二,在进入fMRI扫描之前,被试会被给予积极和消极情绪影响测量表(PANAS)。PANAS是一种高度稳定且内部一致的情绪测量方法,用于确定实验中被试不受自身情绪的影响。其三,实验后期,被试仍需完成一个关于自己的艺术和艺术史知识的问卷,并标明自己识认的作品,以确保被试对作品的评价不是因为熟悉。
“The Experience of Beauty Derived from Sorrow”也运用了三层策略来保证审美体验的现时性。首先,为消除图片内容的影响,实验者选用了葬礼、孤儿、建筑物和悲伤的面孔,以及风景和日常场景来代替描绘战争场景、武器、暴力的图片,以排除与当前任务无关的大脑自动反应。其次,用情绪等级评价量表来保证他们在观看时所引发的情感是由图像本身而不是由图片里的人物所引发的。最后,在心理物理测验中的一个问题(你先前是否见过这张图),将会确定哪些是被试见过的,熟悉的图片将会被剔除。
除了现时性,审美体验的个体性也被充分考虑。首先,在设计与操作层面,实验者会给予被试充足的时间以做出审美判断,这意味着判断的选择更多的是由被试自己控制,而不是实验设计本身。在“The Brain on Art”中,“每次艺术品呈现时间为6秒,之后为4秒的空白屏幕,在此期间,被试可以按下一个相应键”。被试拥有10秒时间对一件作品做出反应,而不再是曾经的2秒。实验最后,维塞尔等人对脑成像观看阶段被试对作品的4个等级评估和后期的情绪9项评估分别做了皮尔逊相关系数研究:在4个等级评估中,以作品为中心,对每幅作品的评估结果进行两两配对;在情绪9项中,以单个情绪选项为中心再进行两两配对,结果发现被试之间的一致性极低。“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方法学后果:一般来说,一个被试高评价的一图会在另一个被试那里获得较低的评价。”因此,这种高评价与低评价的对比说明相应图片所对应的大脑活跃反映的是审美反应本身的差异,而不是图片自身的特征所引发的差异。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审美体验的个体性。
石津与泽基的实验也运用了类似的方法。“在每次刺激呈现之后,被试都要被要求用右手食指、中指或无名指按三个按钮中的一个,用3项李克特量表对其进行评分。反应时间持续5~7秒,被试可以在这段时间内的任何时间进行评分;结束后有20秒的空白期”。相比于泽基先前的实验“Neural Correlates of Beauty”中每张图只呈现2秒,显然泽基等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艺术欣赏……在实验室的平均时间为20秒”。根据这些年的相关实验来看,只有近年实验中所给予时间的数据接近这个数,只有审美体验被完整呈现了,才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捕捉到审美体验或深度审美体验所对应的脑区。最终,石津和泽基发现:“悲伤感的审美体验和愉悦感的审美体验均有内侧眶额叶(mOFC)的参与……这一脑区在各种刺激下的审美体验活动均是最活跃的……在愉悦感的审美体验中,mOFC与前内侧前额叶皮层(rMPFC)表现出了功能关联的增强;而在悲伤感的审美体验中,却是在辅助运动区(SMA)/中扣带皮层(MCC)与双侧前额叶皮层背外区(dlPFC)之间表现出了功能关联的增强。”
值得肯定的是,神经美学的实验仍在发展,实验者越来越自觉地在努力实现审美体验的科学性。在第三阶段,实验的设计可以充分实现现时性和个体性。它的设计和操作可以支持它的操作定义。由于被试的审美判断和愉悦感是在现实体验中发生的,而不是被试“先入为主”的认知或实验设计本身的影响,从而保证了实验结果的有效性,这些都是审美体验科学性研究的基础。
当然,有学者提出质疑:“审美体验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整体上的热的情绪反应,但实验美学却停留在对部分的冷评价上。”马金(Makin)将审美体验定义为具有强烈情感的“狂喜”,这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马斯洛(Maslow)的“高峰体验”。但审美情感并不等同于“狂喜”。显然,不同的美的操作定义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也有人质疑,神经美学的实验全部是在实验室展开的,头部也是佩戴着相关器材;实验所选用的研究材料,即审美体验的对象几乎都是一些自然景象或艺术作品的照片,并不是真实的自然或艺术作品,而只是一种片段,“这些审美对象已经被符号化、精简化、平面化了,被试并没有真正在现实世界中与他们的审美对象相遇,所有与审美对象相关的背景几乎都被剪除,而只留下一些片面的符号”。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被试依然有审美体验的发生,甚至是深度审美体验的发生,可以观测到审美体验的脑区活跃。换言之,现实生活中审美体验的发生强度至少是等于实验室内的,有很大可能实验室之外的审美体验脑区活跃表现要比实验室内的更为强烈。
综上可以判断,神经美学关于审美体验的实验是有效的。因此,审美体验发生状态的标准在神经美学这里能够得到确认。审美体验作为一种主观体验的科学性便能得到确立。“美本质”问题显然并没有终结,主观性的打破与科学性的确立正是神经美学为“美本质”问题走出瓶颈的贡献所在。
实验的可操作性直接指向了审美体验的物质性。与先前各阶段对艺术与美的讨论相比,神经美学的概念体系不仅包含了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哲学美学的基本问题,还吸纳了神经科学、脑科学、神经生物学等学科的概念与方法,如神经、动作电位、神经电化学信号、视网膜、视皮层、光以及脑成像技术,等等。显然,这些概念不再仅仅是一种生理学或脑科学的概念,更是对主体的认知,是基于物理、生理的事实发生对主体“我”的进一步解剖。主体在此不再停留于心智、身体等概念,心智、身体等概念需要依靠对主体进一步的剖析来完成。心智被落实在了身体的基本构成之中,神经电化学信号、默认模式网络、内侧眶额叶等成为心智构成的一部分,成为审美发生的一部分。并且这不是静态的概念解析,而是一种现时的动态发生,是活生生的心智生成。心智有了来处,有了生成之过程。与先前的鉴赏力、感觉等概念相比,这实在是巨大的进步。神经美学将审美活动发生的起点由作为主体的“我”延伸到了大脑神经元,在这样一个更为完整的审美活动现象中重新讨论审美、审美体验等传统美学概念。
从神经美学20多年来的发展也可以看出,神经美学由起初的审美活动的神经科学研究,逐渐侧重或者说转向了审美的哲学美学研究,当然,这也是神经美学这一概念的落脚点。神经美学的目的是揭示或找到审美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神经美学的方法是实验实证,然而,欲找到审美之基础,必先搞清楚什么是审美,这就需要对哲学美学中的“审美”概念有充分认识。神经美学与传统美学如何衔接?神经美学对传统美学的继承在哪些方面?这些也都是神经美学得以立足与拓展的领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神经美学对审美神经生物学基础的发现也是为了完善对美的认识。实验不是目的,实验是认识活动的一种手段,神经美学实验也是如此,它最终是要实现对“美的规律”的完善,即通过实验完善审美现象,全面呈现审美体验中主客体的关系。这也是我们认识审美现象中主客体关系的一种必然趋势。实验之发展也是神经美学研究方法与传统美学理论相互碰撞的结果。
神经美学以双重事实给出了“精确而客观的美的标准”:外部的量表和内在的神经生理基础。显然,与朱光潜所说的色盲相比,神经美学也能够找到基于物理和生理数据所对应的“美的标准”,审美体验的科学实验研究能够实现与前述色盲论相一致的路径和基础。这有赖于神经美学对审美体验中主客体关系的厘清与把握。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已经能够为我们打开一个朱光潜时代不可见的世界,虽然神经美学兴起不久,但神经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及未来技术手段的突破一定可以更好地解决审美体验的科学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