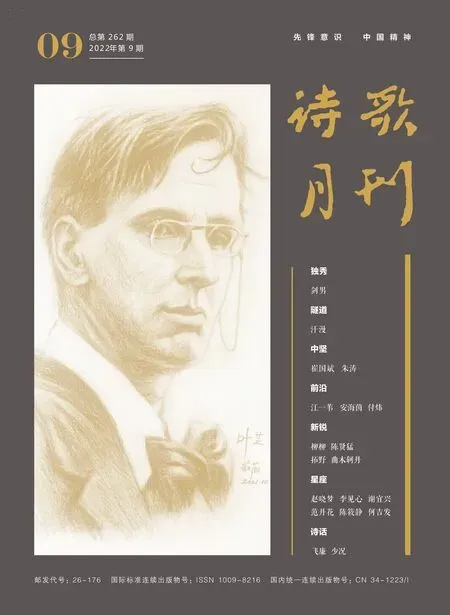诗歌是由各种“偏见”构成的(随笔)
剑男
1.一首诗之所以成为一首诗,更多的在于语言的创造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呈现出来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文学很难超越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而存在。无论我们怎样标榜自己的写作态度,追根究底,态度也是思想情感或价值观念的一种。
2.我很喜欢波德莱尔诗歌中对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形式与内容以及各种艺术之间关系的覆盖,他说:“天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一切,形式,运动,数,颜色,芳香,在精神上如同在自然上,都是有意味的、相互的、交流的、应和的。”(《恶之花》,郭宏安译评,漓江出版社,1991 年)我很喜欢他的神秘象征,使我们能在感性层面感受到理性对世界现象与本体的诠释。虽然现代诗歌的发展并不是永远的象征主义,但诗歌却总是要涵盖这样一些基本的东西,并不断与之发生着联系。
3.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最潇洒的有三种人:一种是先知,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事先就能洞悉人生的全部秘密。一种是精神病患者,他摆脱了外在世界的羁绊,全然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并且他所有的行为都能得到所谓正常人的理解。还有一种是乞丐,他能放下所有的尊严,为自己的一日三餐而坦然伸出自己的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人的痛苦也源于此:既不能洞悉人生,也不能尊崇自己的内心而生活,还必须保持作为人的体面和尊严——诗人介于这三者之间,这可能也是诗人被逐出理想国的又一个原因。
4.庞德在谈到写诗的目标时说:“用抽象术语作一般性的表达是一种懒惰,这种表达是空谈,不是艺术,更不是创作。”胡适说李商隐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不是诗,说:“凡是抽象的材料,格外应该用具体的写法。”就诗歌写作来说,庞德和胡适说的都是有道理的,诗意是语言中溢出来的那一部分,而不是作者介入其中的抽象说理。
5.对任何一个有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的民族来说,它的文明形式都是有传统的,这是语言和思维方式决定的。它在发展流变过程中可能有断裂、有落差,但很难彻底割裂与传统的联系。比如从《诗经》到《楚辞》,这其间有三百年左右没有留下一首诗歌,我们可以看作一次断裂——当然我相信这其间一定是有诗歌的,只是没有留存下来——但两者的传承关系是明显的,《楚辞》的艺术手法就直承《诗经》中的比兴手法。从古乐府的自由到律诗的严苛,我们可以看作诗歌的落差,形制变了,但诗歌的抒情叙事传统仍然在延续。从旧体诗词到新诗,也是如此。当然这个过程中肯定还有其他文学艺术的汇入。在古代诗歌发展过程中,这个汇入更多来自相邻民族的文学艺术形式或观念,近代以来,则更多来自日本文学及欧美文学。但无论什么样的理念或形式的加入,它必然要融入汉语言的传统中,本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一定要映照其中。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交融只能部分改变它的结构,且这种改变一定是一个不断扬弃、不断优化的过程,并不能改变它的本质,这个本质的东西是和一个民族的语言共生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其剥离出来。
6.和荷尔德林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短命的天才诗人——诺瓦利斯曾说过,哲学是一种永远的乡愁。他说不安是人存在的常态,这种不安就是你离开了故乡之后在异乡的不安,所以人总是会不断地往回走,寻找回归故乡的路,每个人都在离开故乡的路上,同时又在返回故乡的途中。我想很多的文学写作也莫不如此。因为一个人对世界的最初认识,包括情感的认知、对事物的认知,都是在童年故乡的时候形成的,童年世界没有功利性东西的侵扰,纯洁、干净,它能让我们借此来打量充满功名利禄的较量的成年世界。
7.诗歌是由各种“偏见”构成的。没有个人可以穷尽的世界,只有各种“偏见”织成的百衲衣——如果诗歌也是一种缝补世相的针线活的话。
8.沃尔科特说:“要改变你的语言,首先要改变你的生活。”这是一个真正诗歌写作者的经验之谈。远离生活、凌空蹈虚的词语不过是语言的僵尸,是生活保证了语言的鲜活性,也是生活在不断拓展着语言的意义空间。
9.诗歌史是依赖具体的诗歌构建起来的,文学和历史不一样,历史主要由事件构成。历史事件非亲历者难以窥见真相,故历史往往留有诸多疑点。诗歌史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无论编者站在何种立场,作品摆在那里,它可以摆脱外在的东西进行自证,或者说不证自明。
10.孤独是一个人的常态,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的。诗歌写作就是个人抵抗孤独的一种方式,很多时候,这种孤独不是人离群状态下的孤独,而是人在人群中不群的孤独。
11.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乃至诗歌,应该有思想。唐代刘晏总结孔子等人的教育思想后说,士先器识,然后文艺。读书人先要有气量、见识和情怀,有对人生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然后才谈得上学习写作和研习六艺。这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仍然有用。为什么有些诗人的作品词藻华丽、技艺娴熟,却总给我们平庸之感,原因就在于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见他本人在什么地方,看不出他的情感、思想和立场在哪里。他的作品就像一尊蜡像,有完美的躯壳,却没有血液和灵魂。
12.于坚有一篇文章,叫《拒绝隐喻》,他在文中说:“几千年来,一直是那两万左右的汉字循环反复地负载着各时代的所指、意义、隐喻、象征。命名在所指的层面上进行,所指生所指,意义生意义,意义又负载着人们的价值观判断,它和世界的关系已不是命名的关系,而是一套隐喻价值观的系统。能指早已被文化所遮蔽,它远离存在。那最初的声音消失了,我们坠入辞不达意的隐喻的黑洞中。”我理解于坚拒绝隐喻的初衷,可能是希望诗歌回到语言本身。但于坚却没有给出一条清晰的路径。隐喻是一个文化知识系统,并不统一呈现在所有人的言语活动中。也不是所有的言语活动都是一种言此及彼的游戏。实际上,所有的写作都有它的言外之意,我们只是应该尽力剔除语言中那种陈腐的、庸俗的意义承载,我们对世界的命名仍然依赖于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语言规范系统,彻底摒弃隐喻是不可能的,诗人要做的是刮骨疗伤,而不能因此取了其性命。
13.诗歌批评可以尖锐,但要建立在具体的文本之上。我们不能将作品中描写的生活和诗人本人的生活等同起来,假批评之名对诗人进行人身攻击。更不能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甚至不惜捏造事实对诗人及其诗歌作品进行歪曲和辱骂。批评也是有伦理的,我们要警惕那种有选择性的道德审判,因为道德审判的背后往往是批评者的非道德。
14.有时候,诗人个人的卓异可以改变大众对诗歌的认知,但有时候则是大众的审美改变着诗歌并使诗歌流俗。
15.诗人是被自己的观察充满着的个人,他的诗歌要展现他作为个体存在的独立性,但与此同时,又没有哪一个诗人能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生活与写作。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区和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个人,他既是个人又是社会中的一员,社会必然要进入他的创作。他可以反对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可以尽力去抵制社会环境的影响,但社会环境对一位诗人的影响永远不会消失。艾略特曾经说过,诗人在创作时,似乎绝然遗世独立,不考虑任何社会影响;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个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都不可能抱有支撑着他创作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诗歌就是诗人个体生命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
16.人生只有一种真正的快活——那就穷快活。穷只有偶得之喜,而无失去之忧——因为没有,就无所谓失去。写诗大概也算穷快活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