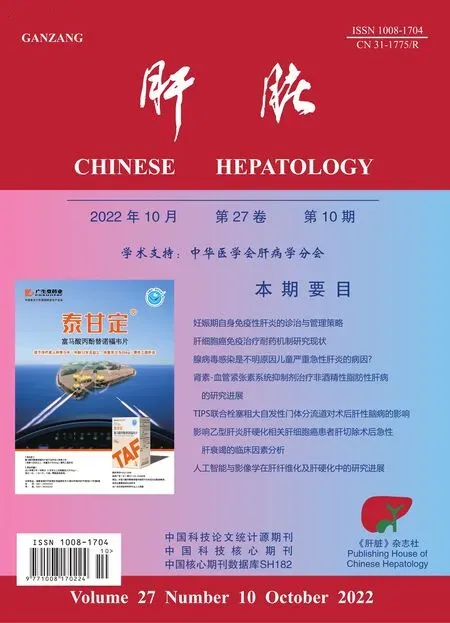一例自身免疫性肝炎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男性患者6年诊治随访
朱亭亭 苟悦 孙鑫 邢枫 刘坤 刘成海 顾宏图
患者,男性,33岁,出生并居住于上海市崇明区。2014年5月18日,我院门诊检查:ALT: 60 U/L,AST: 31 U/L,TBiL: 33.25 μmol/L,腹部超声示肝内脂肪浸润,诊断为“非酒精脂肪肝”,予“复方甘草酸苷”及中药汤剂(柴胡、黄芩、泽泻、荷叶、垂盆草、鸡骨草、枳壳、陈皮、甘草)治疗后指标好转。2014年10月12日,患者出现目黄,我院查血清肝功能:AST: 364 U/L、ALT: 669 U/L、TBil: 208.05 μmol/L,血清IgG:19.5 g/L(表1),余指标未见异常,血清肝炎病毒学标志物及自身免疫性肝病抗体均阴性。既往否认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史,2013年曾行疝气手术,否认输血史,否认药食物过敏史,否认长期服药史,否认饮酒史。查体:BMI: 31 kg/m2,全身皮肤黏膜及巩膜轻度黄染,腹微膨,无压痛、反跳痛及肌紧张,肝脾肋下未触及,无蜘蛛痣及肝掌,双下肢无肿。腹部超声示肝脂肪浸润,诊断为“急性黄疸型肝炎”,予谷胱甘肽、多烯磷脂酰胆碱、天晴甘美保肝降酶,思美泰、苦黄颗粒等对症治疗,肝功能明显改善后出院。2014年11月17日再次出现上述症状,遂再次入院。BMI: 29 kg/m2,全身皮肤黏膜及巩膜轻度黄染。肝功能:AST: 225 U/L、ALT: 735 U/L、TBil: 64.45 μmol/L,血清IgG:21.3 g/L(表1),余正常。自身免疫性肝病抗体:ANA 1:100阳性,余同前无特殊。为明确病因,行肝组织穿刺活检,肝组织病理见图1。结合血清生化和肝组织病理结果,采用AIH综合诊断积分系统(1999年)评分为16分:ALP与正常上限倍数/AST与正常上限倍数<1.5,2分;IgG与正常值之比在1.0~1.5,1分;ANA 1:100阳性,3分;肝炎病毒标志物阴性,3分;药物史阴性,1分;平均乙醇摄入量<25 g/d,2分;肝组织界面性肝炎,3分;主要为淋巴-浆细胞浸润,1分,故该病例明确诊断为AIH。予以泼尼松龙片单药治疗:初始剂量为60 mg/d,ALT复常后逐渐减量至15 mg/d维持,半年后患者症状平稳且复查转氨酶指标仍维持在正常水平,逐渐调整剂量为5mg/d维持,随访至2017年8月,期间肝功能稳定。
治疗4年后,患者于2018年12月3日入院行第2次肝活检以明确是否达到停药指征。入院时患者无明显不适,但实验室结果显示肝功能异常,ALT 209 U/L、AST 76U/L、TBil 16 μmol/L等(表1),自身免疫性肝病抗体均阴性,血清免疫球蛋白:IgG20.1 g/L。腹部超声:脂肪肝浸润。肝脏弹性超声示:肝脏硬度6.3 kPa(F0),脂肪衰减314 dB/m(重度)。查体:BMI 29 kg/m2,查体未见异常。遂再次行肝组织穿刺活检,肝组织病理见图2,符合典型NASH病理特征。再次采用AIH综合诊断积分系统(1999年)评分为13分:ALP与正常上限倍数/AST与正常上限倍数<1.5,2分;IgG与正常值之比在1.0~1.5,1分;肝炎病毒标志物阴性,3分;药物史阴性,1分;平均乙醇摄入量<25 g/d,2分;肝组织界面性肝炎,3分;主要为淋巴细胞浸润,1分;其他改变(脂肪变),-3分;对治疗的反应-复发,3分,故诊断为可能的AIH合并NASH。予阿拓莫兰、天晴甘平保肝抗炎,考虑糖皮质激素可加重NASH,故停用泼尼松龙,改用硫唑嘌呤(azathioprine, AZA)50 mg/d治疗,经治疗后肝功能好转出院,嘱其调整饮食结构,控制体重,随访至今,肝功能未见明显异常。

注:A、B:小叶内肝细胞弥漫疏松化,散在较多点灶状坏死,汇管区中度淋巴细胞浸润,可见少量浆细胞浸润,汇管区轻中度界面炎(A:HE染色,40×;B:HE染色,200×);C:汇管区及窦周轻度纤维化(Masson染色,100×)

注:A、B、C:小叶内肝细胞部分疏松化,散在点灶状坏死,腺泡III区肝细胞明显脂肪变性(大疱性脂肪变为主,约占样量40%),汇管区中度混合炎症细胞浸润(淋巴细胞为主,伴少量浆细胞及嗜酸性粒细胞),部分汇管区轻度界面性炎,未见明确肝细胞花环结构,胆管及血管未见明确损伤(A:HE染色,20×;B:HE染色,100×;C:HE染色,200×);D:汇管区及肝窦内胶原沉积(Masson染色,100×)

表1 患者血清肝功能及IgG变化一览表
讨论本例青年男性患者,体型肥胖,初诊时BMI 31 kg/m2,超声提示有肝内脂肪浸润,但经抗炎利胆保肝治疗后,肝功能仍反复异常,甚至出现ALT等升高幅度近10倍上限,行肝组织穿刺活检发现患者肝内点灶状坏死,肝细胞轻度微泡脂肪变,汇管区轻中度界面炎伴淋巴-浆细胞浸润,NAFLD活动度积分(NAFLD activity score,NAS)为3分(肝细胞脂肪变1分,小叶内炎症2分,肝细胞气球样变0分),不支持NASH的诊断。无明显可疑肝毒性药物服用史,RUCAM评分2分,药物性肝病诊断不成立。AIH综合诊断积分系统(1999年)评分16分,诊断为明确的AIH,使用泼尼松龙治疗,患者生化与免疫应答良好,提示诊断正确。然而,第二次肝活检结果出人意料,不仅肝组织汇管区炎症仍然有明显中度界面炎、小叶内点灶状坏死,且出现腺泡III区大泡性脂肪病变,肝细胞气球样变,窦周纤维化等典型的NASH病理特征,遂修正诊断为AIH合并NASH,改用免疫抑制剂AZA治疗后好转,随访至今,肝功能无明显异常。回顾该患者的诊疗过程,考虑该患者AIH合并NASH的诊断正确,属AIH的一种特殊合并类型。
研究发现,NAFLD或NASH患者可出现血清ANA的阳性,较一般人群阳性率明显上升,并与肝脏组织学损伤明显相关[1-3]。同样,也有报道约10%的AIH患者常规自身抗体检测呈阴性,而且血清IgG水平无异常[4]。然而,AIH与NASH的治疗与预后均不一致,二者需要鉴别。在治疗方面,AIH的常规方案中需要使用糖皮质激素;NASH治疗以抗炎保肝、改善生活方式、控制代谢综合征为主,由于大剂量或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会诱导肝细胞脂肪变性而加重NASH病情[5-6],应慎用糖皮质激素。据报道,近1/4的成年人均有不同程度的NAFLD,其可作为基础疾病合并见于其他许多疾病中[7]。存在AIH与NAFLD的特殊类型,与单纯AIH患者相比,AIH合并NAFLD会因AIH的诊断滞后而延误病情。此外,二者重叠发病,病情易进展至肝硬化,严重影响生存率[8]。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应仔细甄别AIH合并NAFLD的患者。
AIH合并NAFLD的诊断往往需要结合临床、生化、影像学及组织学特征[9],其在性别、年龄、肥胖程度、肝功能、肝纤维化进展程度、初次活检肝硬化检出率等方面与单纯AIH患者相比均有明显差异[10-11]。病理上,AIH急性发病常呈现小叶中央塌陷性坏死或中央静脉周围炎等特点,需注意与NASH区分;慢性损伤则表现为汇管区中重度界面炎,伴不同程度的淋巴-浆细胞浸润以及穿入现象,肝细胞花环形成[12]。NASH多表现为腺泡III区肝细胞大泡性脂肪变性,散在性(主要为小叶性)炎症和凋亡,肝细胞气球样变性,可伴随肝窦周围纤维化,但门管区炎症较轻[13],并且随着NASH进一步进展,会出现肝细胞脂肪变性并不明显,这一现象可能是“脂肪燃烧”后的结果[14]。除了病理上同时存在两者的典型或不典型表现外,AIH合并NAFLD患者的门静脉炎会较单纯AIH患者严重[10]。此外,AIH合并NAFLD的诊断还需结合患者的基础情况,如是否伴有代谢和心血管危险因素及并发症,患者的自身抗体与免疫球蛋白,乃至基于激素的应答反应等做出综合判断。
目前对AIH合并NASH这一特殊类型的系统研究较少,且相关指南中未明确提出,尚缺乏系统的诊疗方案。因此,需重视对此特殊类型AIH的认识。尽管AIH在男性中发病较少见,但该青年男性患者的二次肝活检AIH的诊断基本一致。首次肝活检前患者已有明显代谢综合征,影像学也提示肝内脂肪浸润,但组织学却未发现NASH证据。主要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肝穿刺活检样本误差,二是早期发病以炎症为主,而脂肪变较轻,表现不典型,难以区分。第二次肝活检目的在于评价激素治疗效果,却意外发现明显的NASH表现,主要原因可能是患者本身的糖脂代谢紊乱及激素的副作用。肥胖、脂质代谢紊乱等危险因素会增加循环中游离脂肪酸的水平,促进肝脏葡萄糖转换为脂肪酸,从而导致肝脏脂肪的过度沉积,进而促进NASH的发生[15-16]。糖皮质激素可缓解炎症,但会抑制蛋白质的合成,致高脂血症、葡萄糖耐受异常,加重代谢综合征,引起肝内脂质含量升高,诱发大泡性脂肪性变,也会导致NASH的发生。所以,对于此类AIH合并NAFLD的患者,治疗上应优先选择硫唑嘌呤等免疫抑制剂治疗。此外,该病例也提示我们治疗前后两次肝活检在AIH诊治过程中的价值,对于合并疾病的诊断、判断预后和停药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AIH与NAFLD缺乏特异性诊断标志物,鉴别诊断在临床实践中尤为重要,虽然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有助于明确诊断,但肝活组织检查至今仍是诊断AIH、NAFLD及其重叠症的金标准。早期诊断和个体化治疗是控制疾病进展的关键,结合定期随访,根据病情需要灵活调整治疗方案,延缓疾病进展,争取病情逆转。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