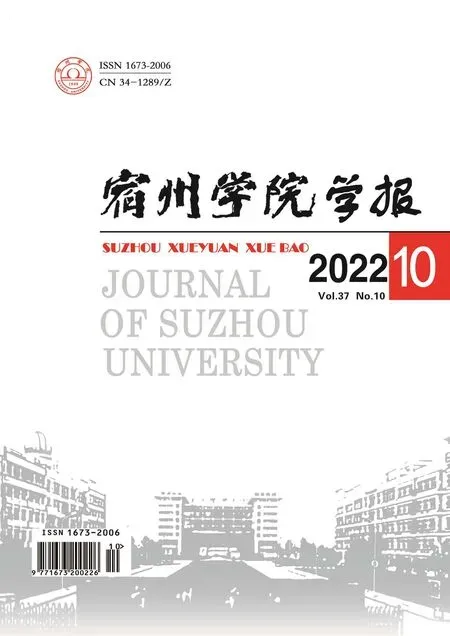强制阐释与理论建构的艺术作品研究
——再论《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梵高的《一双鞋子》
曹学莉,李向伟
1.六安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安徽六安,237158;2.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艺术作品的本源》(DerUrsprungdesKunstwerkes)来源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1935年底和1936年初所做的几次演讲,这几次演讲事后被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描述为“惊动一时的哲学事件”。在这篇论文中,证明了只有借助艺术作品,才能真正揭示“器具即一双农鞋实际上是什么”[1]22,也就是器具的器具性存在。这种存在已经内隐着鞋子物理性存在和艺术性存在的勾连。海德格尔援引了梵高那幅著名艺术作品——《一双鞋子》,这双鞋子日后却成为《艺术作品的本源》被批判的重要原因。而论争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海德格尔对鞋子的阐释是否揭示出其本质特征,甚至这种阐释是否合法。鉴于此,有必要梳理关于梵高的鞋子的几种论争,并厘清批评-阐释与理论建构两种关于艺术作品的阐释方式的区别,进而管窥海德格尔的真实用意。
1 《一双鞋子》若干理论批判的价值解读
1.1 夏皮罗关于《一双鞋子》的批判
对《一双鞋子》的论争,开始于美国艺术史家、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系教授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1968年,夏皮罗为了纪念其同事库尔特·古德斯泰恩(Kurt Goldstein)写了一本有关海德格尔和梵高的札记,名曰《作为个人物品的静物画》(TheStillLifeasaPersonalObject)。在这篇札记中,夏皮罗对海德格尔发起猛烈攻击。夏皮罗针对梵高的画鞋,给出了一个个有着颠覆性含义的提问:梵高画中的这双鞋子,真的是一双农鞋吗?抑或更确切地说,这双鞋子的主人真的是农妇吗(如图1)?

图1 一双鞋子
夏皮罗曾对八种不同版本的画面鞋子加以研究,分析呈现出各自的特征。八幅画中,仅三幅具备了海德格尔所说的“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1]20的特点。他断定,“它们(这三幅画)所描绘的显然是画家自己的鞋,而并非普通农民的鞋”[2]。海德格尔在回复夏皮罗时表示,他所提到的作品正是于1930年3月在阿姆斯特丹展览中所见,这使夏皮罗更加自信。
夏皮罗坚定不移地认为,这双农鞋的主人是梵高而不是农妇。他指出海德格尔的这些处理方式忽视了画家在艺术作品中的独特存在性,“在海德格尔对艺术本质的理解中,他完全忽视了靴子的个体性和面相学特性,也正是由于其个体性以及面相学特性才促使靴子成为对画家们而言这样深刻和诱惑人的主题(更不要说它们与成为油画作品的画作的特定颜色、形状及笔触组成的外表之间的私密联系了)。至于我们可把它们说成是旧鞋子的真实写照”[2]。因此,夏皮罗认为海德格尔连基本事实都混淆的情况下,自然无法解释这双鞋子的本质。
夏皮罗在《作为个人物品的静物画》中造成了一种认知的异化冲击,即哲学不懂艺术的诽谤性效果。海德格尔之所以要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援引这幅画,是为了证明他内心的一种观点:唯有借助艺术作品,才能体现出物之物性,也就是鞋的鞋具存在。在夏皮罗的逻辑中,海德格尔对鞋的阐释带有“精神的纯粹性”[2],是艺术阐释的挪移。在夏皮罗的逻辑中,需要用一双真实的鞋子做支撑,这幅画模仿、复制又再现了它们。但海德格尔所主张的是使存在者的存在进入澄明的无蔽中,而不是把重点放在这幅画所画的鞋究竟属于谁。
夏皮罗认为海德格尔是自欺欺人,把自己建立在“那种对原始性和土地怀有浓重的哀愁情调的社会观基础之上”的想法,投放到了艺术上[2]。简言之,夏皮罗认为海德格尔倾注了太多的主观意识,而忽略了大部分的客观事实。因而《一双鞋子》里自行嵌入的真理得不到绘画本身的支持。夏皮罗在论证鞋子的归属等问题时,完全回避海德格尔的艺术思想,这种方法其实是有问题的。他深陷逻各斯中心主义——为鞋子确定主人,夏皮罗自认为明确了鞋子的主人是梵高而非农妇就能够成功地摧毁海德格尔艺术思想的基础。夏皮罗看似完美无缺的断言——“农妇的世界”只是海德格尔的臆想,但是仅凭鞋子的主人不是农妇就可以认为《艺术作品的本源》的思想体系就扎根于一个错误的思想地基上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1.2 德里达关于《一双鞋子》的批判
在夏皮罗之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介入了这场论争。德里达对海德格尔不是辩解而是认为夏皮罗的关注点非但未能触动海德格尔的真正问题,反而和海德格尔相比,不仅对画中一双鞋子的非双性别概念毫无意识,甚至对鞋子的真正拥有者的性别抑或对鞋子的性别概念也没有反思。
首先,他认为夏皮罗的考证并非无懈可击。皮鞋与农鞋并不是区分鞋子的真正主人是梵高还是农妇的决定性因素,毕竟梵高的书信都曾证明了在其中的一幅以皮鞋为主体的画面场景中所画的就是一双农鞋。而从鞋子的内在特征来看——即“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1]20,再现了艺术阐释论中的解释学谱系,以此来确认鞋子的外部归属同样不合理。其次,德里达认为,即便是夏皮罗证明了鞋子是画家自己的鞋而非农妇的鞋,也无法从根本上推翻《艺术作品的本源》中的核心命题:艺术的本质应该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1]20。在海德格尔看来,真理的本质是自由,而自由的实质就是让存在者存在。这就是说,所谓真理正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1]40。因而他试图反对的是“那个以为艺术是现实的模仿和反映的观点”[1]23卷土重来,他主张“作品绝不是对那种时时现存手边的个别存在者的再现,正好反过来是对物的普遍本质的再现”[1]24。而夏皮罗的艺术观正是这里所批判的“模仿和反映”,所以他自然也就无法领会海德格尔的本意。最后,德里达认为,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梵高,都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这里的鞋子并非“一双”,而是两只左脚鞋。而陷入误区的原因,是因为都有一种“还原”的欲望,即鞋子必然是有所归属。具体到真理这一命题,他们都在试图揭示真理或者说将真理还原,并且陷入了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一个共同的准则或者一个同样的愿望,一种同样的勤勉,总之,一个共同的兴趣又或者一个共同的债务、共享的责任。他们亏欠着艺术上的真谛,艺术的真谛或者是作为真理的艺术,又或者是作为真理的真理”[3]。这种陷入无价值循环的“逻辑怪圈”,是对解构主义的反噬,也是人们必须规避的“阐释陷阱”。
作为解构主义哲学家的德里达用解构思维把《一双鞋子》弄得支离破碎。从松开的鞋带到推断是左脚或右脚的鞋子,他断定不管是农民的鞋子抑或画家自己的鞋子,都极有可能不是一双却是两只,并指出无法提供任何证据来证实梵高画的是同一双鞋子。其实,失去主人的鞋子已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德里达比夏皮罗更为极端,他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更为彻底。他们的批判都没有锚定真正的中心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
1.3 张江关于《一双鞋子》的批判
中国学者张江从艺术作品阐释的角度看待海德格尔的做法。在他的观点中,海德格尔的解释是一种“脱离原文,消除文学的特征,在立场和方式上,根据论者的主观意愿和结论,对文本和文学进行解释”[4]。张江的论点聚焦在文本阐释问题上,体现了论者主观意愿的注入,是很有理论辨识度的。
具体来说,他认为海德格尔的阐释脱离了对象,其阐释的不是鞋子,而是自我思想。如果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则完全无需梵高的鞋子:“我们的疑问是,可否将海德格尔关于那一双鞋子的煽情阐释迁移至其他鞋子,作同样的阐释?如果可以,对梵高的其他作品,譬如静物、女人、自画像,是不是也可以作同样的阐释?很显然,我们完全可以代他做到,任何有西方文艺理论训练者皆可做到”[5]。因此,海德格尔是将自我思想强加于梵高的作品之上,并未顾及鞋子的本意:“把阐释者的思想强制于对象,强制为对象所本来具有或应该具有,乃标准的强制阐释”[5]。这种强制阐释建基于对自我思想投射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思想化和理念化的阐释”,是对一双鞋子的新的艺术解释。
从以上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来看,德里达对于《一双鞋子》的批判,其实隐含的是他对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本源》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是出于解构真理的目的,同样与鞋子本身无关。而夏皮罗遵循的是传统的艺术反映论,认为海德格尔既然没有明确鞋子的归属,那么在此之上的所有阐释都将不成立。张江的强制阐释,实际上也是出于维护作品本意的目的,即认为离开了鞋子本身的阐释是非法的,与夏皮罗可谓殊途同归。
2 批评-阐释与理论建构两种关于艺术作品的阐释目的
2.1 批评-阐释看待艺术作品的阐释方式
无论是夏皮罗还是张江,其实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人们关于艺术作品的阐释是否只能关注它的原有内涵而不能扩展,甚至挪至它用?这一点,德里达已经有所触及,他认为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已经告诉人们,艺术不再是传统的模仿与再现,那么,人们对艺术作品的阐释自然也是自由和敞开的。
德里达在这里所涉及的仍然是艺术作品的批评-阐释维度。在此,以作为艺术作品的文学作品为例,面对一个文学文本,在传统意义上,一方面,人们可以考察作家作品的外在因素,包括作家生活的年代背景、生平、写作风格,作品的产生背景以及与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联系,对文学作品作外部批评。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的、多层次的艺术对象,它是一个自我完善的世界,它是文学活动的源头。因此,它的内在要素包括词义、语境、修辞等,是一种内在的批判。德里达的看法是后结构派,即试图解构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德里达看来,语言符号结构构成了语言主体,它的内在包含所指的观念成份与形式成份是对立多元而多义的,所以基于语言符号之上的语言主体以及由之所“书写”成的整个人类世界也是矛盾多元的。文学是一种人类的语言符号,它的含义也是多种多样和异质性的。
再来看《一双鞋子》。如果从忠实的还原式阐释维度——也就是夏皮罗和张江的观点,的确要考虑到梵高的本意与鞋子的本身。人们要考虑到梵高是在何种情况下创作的这双鞋子,他的创作目的是什么,这是不是“一双”鞋子,真正的归属者是谁等等。接着,在此基础上,人们再去探索鞋子所蕴含的本原意义为何。而假若人们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维度来对其加以批评,那么其实就是德里达对于海德格尔的理解。他认为海德格尔是通过这双鞋子来证明意义的敞开与存在者的无蔽,这样就为人们从不同角度来阐释鞋子的多元意义设置了合法性。因此,尽管海德格尔还是没有摆脱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所谓多元阐释最终是为了揭示“真理”,但这并不是因为鞋子的归属者导致的,也无关乎梵高创作鞋子的本意。
批评-阐释是指一般意义上人们对艺术作品进行评述和解释,而这种评价往往与作者相关。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在《批评的功能》一文中所言,“我此处所说的批判当然是指透过出版物对文学作品所做出的评述和解读。”“一种批评性的言论常常含有对个别作家式作品的‘解释’”[6]。人们并不是武断地认为批评就是阐释,但它俩像孪生姊妹一样内在的关联是骨肉相连密不可分的[7]。强制阐释是批评-阐释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即“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4]。当回望以上关于梵高《一双鞋子》的论争,不难发现,它展示了一种新的话语理论范式和阐释的价值视角。这就需要对强制阐释和批评阐释的关系做重新厘定。强制阐释和批评阐释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即强制阐释重视从文本阐释出发,强调在逻辑中产生解释的循环。这契合了批评阐释视域中文本中心论的解释自足指证,促使批评阐释更加明晰了自身的主观预设。导致强制阐释和批评阐释产生了互为支撑、交叉濡染的关系,产生了价值协同效应,完成了阐释的更新和回归,对中国本土的文论阐释体系构建形成了新的助力和拓展。
无论是德里达、夏皮罗还是张江,其实都是批评-阐释,只不过张江和夏皮罗对海德格尔的批评-阐释脱离了作品和作家本体,是一种强制阐释。而德里达则是将阐释的界限扩大,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角度来证明海德格尔的合理性。
2.2 理论构建看待艺术作品的阐释方式
如果想为海德格尔辩护,以上的批评-阐释维度仅仅是一个方面,还须要回到艺术作品作为“物”(thing)的本质。海德格尔指出,物性的根基是作品最直接的现实。海德格尔的理论建构,其核心就是对艺术本质的探索,其立足点也就是艺术作品的现实性。海德格尔把理论建构集中于这双鞋子的存在论立场,即鞋子与器具的本质探寻上,但是他在陷入无始无终的逻辑循环的同时,也陷入了器具和鞋子无法区分的尴尬。对器具之器具的存在论述,海德格尔从未掩饰,他使用嵌入式叙事来对原有的话语空间进行干扰和破坏,给读者阅读或阐释叙事意义制造障碍。夏皮罗想要证明,这就是梵高的鞋子,而他却停留在只是一件艺术品上,单纯强调了物性。海德格尔批评传统和通常意义上的“物”的观点,认为人们过多地关注物的有用性而忽略了它的普遍性,特别是艺术作品。这种普遍性,实际上成为现代西方原创性理论家们在建构理论时所借鉴之处,也是他们的追求所在。
今天,以文艺理论为例,一方面,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家们往往借用艺术作品的普遍意义,来证明自己理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主张这种学说的人从未满足自己的学说只用来解答本学科的疑点,始终期望自己的学说有着普世的旨意与功能,亦用来解答其他学问甚至是整个人文学科各领域的问题——如弗洛伊德就曾经如此期望。这个时候,他们在理论建构时所采用的例子——往往是艺术作品,也必然具有普遍意义,其本来含义就变得不再重要。
海德格尔的做法也是如此。在海德格尔看来,他根本无须为此与夏皮罗等人争论,也不屑争论。海德格尔并非鉴赏家与批评家,其研究目的并非出于关注《一双鞋子》的本质属性。他不需要用谁的鞋子来证实自己的哲学思想。同样的,并不是只有希腊神庙才能证明艺术作品的世界性,也不是只有锤子,才能证明物只有在实际使用中才能真正成为其本身。他只是将梵高的作品作为阐释其理论思想的例子,重要的不是鞋子,而是如何借助这双鞋子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来看,张江对海德格尔的质疑,若被海德格尔知晓,他可能不以为忤,反而深以为然:“他对梵高鞋子的阐释,他对康德形而上学的疑难,不都是动机在先,确定指向性目标,以动机性推理,制造虚假相关。也就是将对象作为某物筹划和把握,以本己之念强制于对象,有效地阐释自己而非对象吗?”[5]
2.3 批评-阐释与理论建构看待作品方式的区别
再论《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梵高的《一双鞋子》,由于不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农妇的鞋,而是梵高本人的鞋子,自夏皮罗以来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人们对“一双鞋子”(艺术品)的解释,是批评-阐释式的,还是海德格尔的理论建构式的,其实关于艺术作品,一直都存在两种阐释方式:一种是将其作为批评-阐释的对象,一种是以其为例来完善自身的理论话语。人们往往是从第一个层面来理解这双鞋子,而海德格尔本人作为理论家,所采用的则是后一种方式。事实上,海德格尔没有做批评-阐释,是在进行理论建构。强制阐释本身就是对原研究者的强制,即张江认为海德格尔对一双鞋子是强制阐释,那么他对海德格尔又何尝不是?因此,无论是德里达、夏皮罗还是张江,其实都没有理解海德格尔的真正目的。海德格尔是在理论建构,目的根本不是张江所说的“阐释”。
3 结 语
综上所述,发现目前关于《艺术作品的本源》中鞋子的争论,虽然各自的出发点不同,但无论这个鞋子的真实是否会影响其意义阐释,其创建性的解读都是值得尊重的。“创建乃是一种充溢,是一种赠与”[8]。这种创建是对艺术本体的思维补充,也是对文本解释的理论拓展。从扬弃的角度来看,从构建的逻辑场域和话语体系来讲,强制阐释与理论建构的理论触角是在对作品的深度思维投射和价值反思中生成的,总是锚定“艺术与真的关系”[9],这种艺术与真的关系体现出现象学话语中对艺术本体的价值反思。现象学话语的艺术争论从来都是在各自“逻辑域”中完成建构,而又在“意义域”中重塑的,这就是强制阐释与理论建构的魅力所在。但是围绕的核心问题无外乎鞋子的真实是否会影响其意义阐释,进而颠覆海德格尔的理论建构。海德格尔的做法,虽然说从批评-阐释的角度,存在强制阐释的风险,但是,从批评-阐释的维度,海德格尔本身就为人们建立了一个关于艺术作品解读的开放域。仅仅如此还不够,也无法解决关于鞋子的质疑,那么从理论建构的维度来说,海德格尔的做法同样合法、合理,是所有成功的理论大师在建构自己的理论话语时一致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