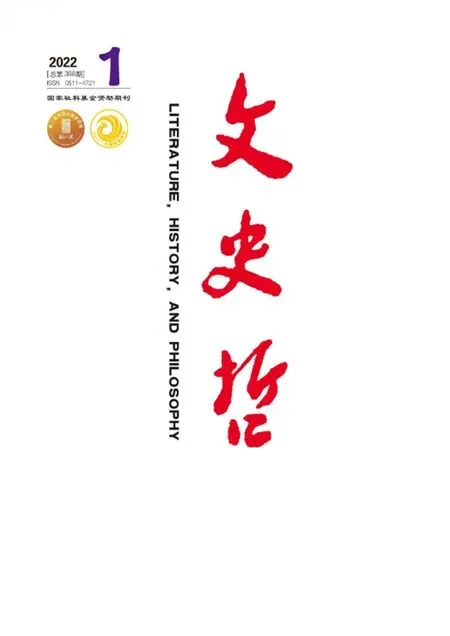《春秋》笔削见义与传统叙事学
——兼论《三国志》《三国志注》之笔削书法
张高评


一、《春秋》笔削与叙事传统
《左传》是经学、史学,《东周列国志》为小说、文学。《三国志》是历史,《三国志演义》属文学。历史之编纂,文学之创作,写作之心路历程虽相似而实不同。就事件本身之表述来说,前者是历史叙事,后者为文学叙事。何谓叙事?有西方学者将之单纯化,说成“讲故事”。虽不周延尽致,却也易懂易知。
(一)《春秋》《左传》《史记》与叙事传统


孔子成《春秋》,子夏之徒所以“不能赞一辞”者,缘“拨乱之志”,孔子“窃取之义”,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故《春秋》往往“推见至隐”。唯藉由或笔或削之对照,或书或不书之映衬,彼此可以互发其蕴,互显其义。笔而书之,与削而不书之间,类似“互文见义”之性质。笔与削、书与不书之互文关系,即赵汸所谓“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四言之教。宋朱熹曾谓《春秋》“多不说破”,“盖有言外之意”,大抵指削而不书之类。于是《礼记·经解》所谓“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乃成解读《春秋》之金锁匙。连属辞文可以显义,排比史事亦足以见义。诠释解读《春秋》,属辞比事,遂成为津梁与法门。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提示《春秋》笔削与中国史学之渊源,笔削见义为叙事传统之要法。其中论说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辩证关系,可作属辞比事《春秋》书法之具体揭示。其言曰: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
章学诚提示: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依违取舍,即是独断别裁、一家之言、历史哲学、历史识见之所由生。史料文献经由“独断于一心”之笔削取舍,于是有书,有不书。笔而书之者,又有“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笔法,以及曲直、显晦、有无、虚实,乃至于忌讳、回护诸写作手法。上引章学诚称:“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事具始末,指比事;文成规矩,指属辞。元赵汸《春秋属辞》论笔削,以笔而书之,削而不书互文见义。明湛若水《春秋正传·序》:“笔,以言乎其所书也。削,以言乎其所去也。”比事与属辞之法,为笔而书之诸法之大纲目。换言之,所笔所书,或以比事显义,或以属辞见义。至于削而不书,则体现为所无、所略、所轻、忌讳、回护之伦。可见,笔削之义,确实不止属辞比事而已。属辞比事之终极追求,在经由“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安排措注,进而考察“独断于一心”之史识、史观,甚或历史哲学。

叙事有主意,如传之有经也。主意定,则先此者为先经,后此者为后经,依此者为依经,错此者为错经。
杜元凯《左传序》云: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辩理,错《经》以合异。余谓:经义用此法操之,便得其要。经者,题也;先之、后之、依之、错之者,文也。

《左传》先经、后经、依经、错经,“随义而发”之解经方式,后世衍变成为一种叙事模式。若此之比,即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所谓“史传”传统。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推崇《三国》书乃文章之最妙者,论及三国故事之起始与终结,参差与错落。《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其先经、后经、依经、错经之叙事传统,显然可以前后辉映,相互发明。其言曰:
三国必有所自始,则始之以汉帝。叙三国不自三国终也,三国必有所自终,则终之以晋国。刘备以帝冑而续统,则有宗室如……以陪之。曹操以强臣而专制,则有废立如……以陪之。孙权以方侯而分鼎,则有僭号如……,称雄如……,割据如……以陪之。刘备、曹操于第一回出名,而孙权则于第七回方出名。曹氏之定许都在第十一回,孙氏之定江东在第十二回,而刘氏之取西川则在六十回后。假令今作稗官,欲平空拟以三国之事,势必劈头便叙三人,三人便各据一国。有能如是之绕乎其前,出乎其后,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者哉?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云:“传或先经为文,以始后经之事;或后经为文,以终前经之义。或依经之言,以辨此经之理;或错经为文,以合此经之异,皆随义所在而为之。”罗贯中《三国志演义》,所以叙事见本末,或宗法《左传》以史传经“先之、后之、依之、错之”之叙事特色。细绎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所称《三国志演义》之起始与终迄,即前文所引杜预《春秋序》所谓“《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乃先之、后之之叙事模式。如三国领袖之登场,刘备、曹操,同时安排在第一回。孙权则推迟到第七回。魏、吴、蜀之定都,分别设计在第十一回、第十二回、第六十回后,参差错落如此。或绕乎其前,或出乎其后。如此安排措注,毛宗岗但见“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之效应而已。笔者以为此亦杜预《春秋序》所云依《经》、错《经》之叙事模式。无论绕乎其前,出乎其后,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要之,多“随义而发”。凡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者,皆归本聚焦于“义”。
桐城派始祖方苞,会通《春秋》《左传》《史记》之经学、史学、古文,而倡说义法。撰《又书货殖传后》一文,界定“言有物”为“义”,“言有序”为“法”,为中国叙事传统提供一学理依据,其言曰: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是篇(《货殖列传》)义与《平准》相表里,而前后措注,又各有所当如此,是之谓“言有序”,所以至赜而不可恶也。
方苞楬橥“义法”之说,推本于《春秋》;盛赞司马迁《史记》阐发其精微,以为后代深于文者多不约而同,有所体现。方氏著有《左传义法举要》《史记评语》。《望溪文集》卷二有《读子史》二十八首,综论诸子、《史记》《汉书》《新五代史》之叙事义法。《又书货殖传后》以“前后措注,各有所当”,凸显“言有序”之“法”。言有物之“义”,形而上。“言有序”之“法”,形而下。盖欲人下学而上达,如前引朱熹所言“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故传统叙事学强调“言有序”之“法”者居多。尤其如先之、后之、依之、错之之伦,“前后措注,各有所当”诸法,即其流亚。
(二)《西厢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与叙事传统
试考察《左传》《史记》《三国志演义》《东周列国志》诸史传、小说之叙事学,乃至于乐府叙事歌行、传奇、变文、话本、戏曲,着重“叙”(序),多于关注“事”,即可见中国传统叙事学特色之一斑。如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列有追本穷源之妙、巧收幻结之妙、以宾衬主之妙,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浪后波纹、雨后霡霂之妙,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来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添丝补锦、移针匀绣之妙,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奇峰对插、锦屏对峙之妙,以及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等等。毛宗岗所提示,一言以蔽之,即前引方苞所说义法,所谓“前后措注,各有所当”,只就“言有序”之“法”言之,大抵侧重“如何书”之表述。至于“何以书”如何体现?似乎非我思存。其法,或排比史事、或连属辞文,是所谓“言有序”。
叙事一词,作“叙”,为初形本义。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叙,次第也。从攴余声。”于是,“叙”字,引申即兼涵位次、主次、调整、安排、设计之意。中国传统叙事学之范畴,“叙”之本字已概括无遗。叙事一词,作“叙”,为本字正字。或作“序”事,则为同音通假字。中国传统叙事学,着眼于“叙”(序),多于关注“事”。换言之,较着眼于位次、主次、安排、设计之“法”。笔者近著如《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属辞比事与〈春秋〉诠释学》,论说《春秋》《左传》《公羊传》《春秋繁露》《史记》《汉书》诸史籍,其“言有物”之“义”,大多推见以至隐;往往藉由“言有序”之“法”以表述之。《左传》《史记》诸史传之著书立说,大抵暗合上引朱熹所提“《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之原则。义,形而上,不可说、不能说、不好说、不便说;由于“法以义起”“法随义变”,故史学论著、小说评点,多以说“法”、示“法”,作为金针度人之津筏。读者自当舍筏登岸,即器以求道。

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叙事学所关注之叙事法,以及比事属辞之叙次,西方叙事学并不在意关切。西方所谓“叙事”,近似说故事,侧重叙事动机、叙事立场、叙事视角、叙事聚焦、叙事盲点,讲究人物形象、情节发展、对话穿插、观点诠释、主题意识等等。就西方叙事学而言,凡所侧重,大抵归于事件之铺陈、指义之凸显,与方苞说义法所谓“义以为经”近似。其所讲究,前三者着重事迹之考察,后二者偏向指义之解读。整体来看,若类比《春秋》书法,大抵关注“义以为经”“比事见义”二端而已。其余,如笔削见义、属辞约文等法度,似皆略无涉及。

二、《春秋》或笔或削与历史叙事学

《三国志注》一书,或同或异,或详或略,或晦或明,或曲笔、或回护、或讳书诸手法,大抵薪传孔子作《春秋》时“笔削”去取之书法,稍做转化与发用。文献取舍与夺之际,多可作史传文学、叙事文学研究之借镜与参考。
(一)《三国志》之历史叙事与笔削书法

《春秋》,由其事、其文、其义三位一体组织而成。孔子“窃取之”之义,可以藉由“其事”“其文”体现出来。衡以《礼记·经解》“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之提示,知比事与属辞,即是《孟子》之其事、其文。排比史事,可以显示指义;连属辞文,亦可以呈现史义。同理可推,陈寿《三国志》之成书,无论尊曹魏,或宗蜀汉,亦皆可持《春秋》之教——以属辞比事之法,辩证《三国志》之史义与文心。


《公羊传》曰:“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书“高贵乡公卒”,其犹有良史之风欤!抽戈犯跸,若直书之,则反得以归狱于成济。今“公卒”之下,详载诏表,则其实自著。而司马氏之罪,益无可逃。所谓微而显,顺而辨也。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发明史家“书法”者不少。如《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一条,揭示由于“所值之时不同”,故《三国志》之讳书、《后汉书》之直书,皆属史法之不得不然。其言曰:“陈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蔚宗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书。固其所值之时不同,然史法究应如是也。”《左传》揭示《春秋》书法,有所谓“《春秋》五例”。成公十四年“君子曰”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尽而不污”,为直书;“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三者,为曲笔,忌讳书写、偏袒回护多用之。无论直书或曲笔,多脉注绮交于“惩恶而劝善”之史义。赵翼《廿二史札记》持曲笔讳书之书法,断定陈寿《三国志》;以据事直书之书法,评判范晔《后汉书》,持时移势异以评断,实有见而云然。
《三国志》之体例,上承《春秋》书法,下开后世国史记载诸多法门。《廿二史札记》于《三国志书法》一条,枚举《三国志》不书之例。从“削而不书”之例,可以推想“笔而书之”之实。由此可见陈寿编纂史书,取舍文献之际,或笔或削之一斑。如:
《魏书》于蜀、吴二主之死与袭,皆不书。……蜀、吴二志,则彼此互书。……《蜀志》,其于魏帝之死与袭,虽亦不书,而于本国之君之即位,必记明魏之年号。……而必系以魏年,更欲以见正统之在魏也。
陈寿《三国志》之史观,以曹魏为正统,在“外文绮交,内义脉注”之引导下,排比史事、连属辞文,而皆以史义为依归。陈寿为蜀人,《三国志》往往寄寓乡邦情结,对于魏帝之死亡与袭位,既以“不书”为史法,于是形成书例。以此类推,《蜀志》于“蜀、吴二主之死与袭,亦不书”。不过,或书,或不书,“必记明魏之年号”,示“正统之在魏”。削而不书,一也;或以见正统,或以别亲疏。陈寿之守经达权,有如此者。
孔子作《春秋》,藉或笔或削,比其事而属其辞,以体现褒贬劝惩之书法。赵翼身为史家,想必娴熟能详。其论陈寿《三国志·魏本纪》,运用回护讳书者颇多。盖本僖公二十八年《春秋》经书“天王狩于河阳”,所揭示曲笔讳书之书法。赵翼云: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特为尊者讳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至高贵乡公之被弒也……司马昭实为弒君之首,乃《魏志》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弒之迹。……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

皇后,为国之母仪。依《春秋》书例,若正常死亡,当书“薨”,如太祖之卞皇后,《三国志·魏书》太和四年,书曰:“五月,后崩。”又如文帝之郭皇后,《三国志·魏书》青龙四年,书曰:“春,后崩于许昌。”然如《魏书》卷二《文帝纪》黄初二年六月,书“丁卯,夫人甄氏卒”。又,卷三《明帝纪》景初元年九月,书“庚辰,皇后毛氏卒”。死生亦大矣,国之皇后死亡,但书“卒”,未书“薨”,书法暗示非正常死亡,所谓“《春秋》推见至隐”。盖甄皇后、毛皇后皆因得罪赐死,故不可得而书“薨”。特书“卒”,示意外亡故之义,而曲笔讳书在其中矣。《汉晋春秋》叙甄皇后“殡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惨状如此,“是甄之不得其死可知也”。故《魏文纪》书“夫人甄氏卒”。其所体现之微言大义,自有“推见至隐”之书法在。

笔削昭义之书法,形之于外,则有或书,或不书;或言,或不言;或称,或不称诸名目。笔而书之,则有详书、重书、大书、特书之伦。从或书、或不书,或笔、或削之互发其蕴,互显其义,而微辞隐义可知,史观、史义可考。赵翼《廿二史札记》论《三国志》多有“不书”之例,如:

史家修史,自博采、辨伪文献,至比事、属辞而成撰述、著作。无论笔而书之,或削去“不书”,必经过层层之商榷,种种之考虑。赵翼发现《三国志·魏纪》之叙事,魏将大破蜀将诸葛亮,“固已大书特书矣”。然而蜀将诸葛亮、陈式、魏延等之斩杀魏将、攻克郡县、大破魏军,却削去不书。乃至于张合被杀、郭淮交战诸事,《魏纪》亦削而“不书”。对待曹魏与蜀汉,或笔或削之叙事不同如此,“讳败夸胜”之史观显然。陈寿《三国志》叙事,曲笔讳书处,《廿二史札记》指为“回护”,盖缘于尊魏为正统之史观使然。《三国志》“讳败夸胜”之叙事,凡所以“内义脉注,外文绮交”者,不过是尊魏为正统之史观、史义发用而已。
《三国志》书成于晋,其史观尊魏为正统。正统在魏,则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故陈寿之尊魏抑蜀,诚有其不得已。大体而言,其所著书,简而不漏,详而不赘,“尊魏而不揜其恶,抑蜀而不没其实,讳晋而不灭其迹。”微而显,曲而直之书法,即藉或书或不书表现之,所谓“隐寓夫褒贬而显示乎惩劝,动有合于《春秋》之书法焉”。可见,称誉陈寿为良史,长于书法是主因。

清人黄恩彤《三国书法》曾探论《三国志》或书或不书、削略弗书等议题,颇具代表性,其言曰:“(裴松之)不知寿书之略,略所当略也。所引书,寿非不知之,特削而弗书耳,非脱漏也。史家之例,有书,有不书,一断以义而已。今裴氏繁征博引,而寡所取义,非惟不知寿,亦不知史也。”黄恩彤批评裴松之“繁征博引,而寡所取义”,则就史家对文献之笔削去取而言之。说《三国志》有简略处、有删削处,实即史家“或书”“或不书”之史例,亦即《春秋》或笔或削、或详或略之书法表现。《三国志》有据事直书者,有曲笔讳书者,或言或不言,或称或不称,或笔或削之际,藉此可见陈寿褒贬劝惩之史义。

(二)笔削见义与《三国志注》诸书之叙事书法


裴松之注《三国志》,鸠集传记,增广异闻,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此犹孔子作《春秋》,以鲁史记为蓝本;司马迁纂修《史记》,以金匮石室之书、天下遗文古事为底本。待《史记》书成,与所本之传记佚闻相较,自然互有异同、详略、重轻、曲直、晦明、损益。吾人对读参照、折中取舍,而文心可以求索,史义呼之欲出,史观昭然若揭。就历史编纂学而言,从文献取舍到成一家言之间,书法将随或笔或削,或因或革,而生发或异或同、或详或略、或重或轻、或晦或明、或曲或直、或损或益之殊异。而假笔削去取以见褒贬、劝惩,实胎源于《春秋》书法。
裴松之《三国志注》,广征博引当时图书文献,作为笔削取舍、因革损益之资材。陈寿时代较早,范晔与裴松之时代相近。范著《后汉书》,裴著《三国志注》时,《三国志》所征引之图书应尚在。赵翼《廿二史札记》称:“寿及松之、蔚宗等,当时已皆阅过。其不取者,必自有说。今转欲据此偶然流传之一二本,以驳寿之书,多见其不知量也。”裴松之编著《三国志注》时,可见之文献在五十种以上。今考索《三国志注》所引书,或取而笔之于书,或削而不取。于是赵翼断定“其不取者,必自有说”,诚然!孔子取资《鲁史春秋》,而成一万六千五百余言之《春秋》,其中自有笔削去取。笔而书之者,固符合“丘窃取之”之义;削而不取者,亦“必自有说”。或笔或削,以至于详略、重轻、异同、忽谨之依违,亦皆有其所以然之故。要而言之,在“义昭乎笔削”之原则下,或尽心于比事见义,或致力于属辞显义而已。
陈寿著《三国志》、裴松之编著《三国志注》,于《春秋》或笔或削之书法,盖驾轻就熟,能运用裕如。同理可证,《三国志演义》镕铸《三国志》,又有所修改,颠覆、转化、创新。彼此之间,犹传之于经之关系。换言之,《三国志演义》镕铸《三国志注》,演义《三国志》,何异《左氏传》以历史叙事解释孔子《春秋》经?其中之有无、虚实、详略、重轻、异同,要皆归本于笔削损益。可见,彼此之间,自是同源共本,心气一元。谓小说祖始史传,以此。






史料之笔削去取,依违与夺之际,自见史家之别识心裁、历史哲学。陈寿著《三国志》,于王沈《魏书》之史料,刻意视而不见,几乎削而不书,弃而不用。以王沈《魏书》之史观,美魏毁蜀,重北轻南。《三国志》削而不载,弃而不取,是所谓“略人之所详,而重人之所轻,异人之所同”,删集裁抑之际,即见笔削针砭之指义。大抵详略见重轻,重轻见笔削,或笔或削,乃见一书之史观。由详略、重轻、异同、笔削之书法,陈寿刻意隐藏在《三国志》中之《春秋》书法,当不难推求之。盖史料之裁汰拣择,攸关笔削显义之大凡。苟将《三国志》与《裴注》引《魏书》之史料对读比勘,然后知“尊蜀抑魏”之隐微笔法,缘于陈寿汉遗民之身份。其中之《春秋》大义,多藉详略、重轻、异同之书法,而曲曲传出。自史料之笔削去取,可以考察史观之指向。学界质疑《三国志》过度“回护魏、晋”,是否属实?但观《三国志》详略、重轻书法之偏向,持《春秋》笔削示义之说考察之,则是非、疑似、忌讳、回护之际,自有助于问题之定夺与判准。由此观之,王文进《裴松之〈三国志注〉新论》一书,企图重建三国历史,所用之方法与策略,与《春秋》笔削见义之学,可谓不谋而合。


从史笔之详、重、偏、美,可知史家叙事之视角、史家之史观指向。由此观之,欲解构三国学,重建三国之历史,其策略运用,可以考察文献之笔削,进而阐发其中之书法与史笔。观照史料取舍之有无、多寡、异同、偏全;探讨史家笔法之晦明、详略、曲直、虚实、抑扬、重轻。或就史事之编比探论,或就史文之修饰商榷,两两比观对读之,而陈寿、裴松之、习凿齿、鱼豢、王沈、虞溥、韦昭、张勃、胡冲,乃至于范晔诸三国史家之史观、史义、历史哲学,乃昭然若揭,呼之欲出。
此一胎源于《春秋》,发明于《左传》,大成于《史记》之传统叙事书法,其后开枝散叶,影响深远。吾人寻根探源,思量重返中华文化之精神家园,固然可据笔削书法以研讨《春秋》《左传》《史记》;更可以持此以考察《汉书》《后汉书》《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乃至于《通鉴纲目》之书法、史观、史义、历史哲学。中国传统叙事学渊源于史传,特重“叙”;西方叙事学渊源于小说,较侧重“事”。东西方叙事学之出入异同,从此可以管窥一二。
要之,从《春秋》笔削示义,到史传比事见义,属辞显义,其流派衍为历史叙事、文学叙事。其要,归于“言有序”之义法发用而已!
三、馀 论
上引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称“《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又谓:“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云云。以上数语,牵涉到笔削、比事、属辞、详略、异同、重轻、忽谨诸《春秋》书法之课题。中国传统叙事学之指涉、元素、纲领、方法,多已具体而微表出。前后史料相形相絜,或书或不书,或取或舍之际,若趋向无、寡、略、轻、同、偏,固可从中考察其史义;反之,文献取舍若呈现有、多、详、重、异、全诸书例,尤可藉此探索其史观、史识,甚至于历史哲学。




因此,若持《东周列国志》历史小说,与《左传》《史记》诸史传对读,则藉由文献史料之取舍删改,可以考察比事属辞之叙事,于是因彼此之有无、异同、详略、重轻、虚实、损益、曲直、显晦,而见笔削、抑扬、劝惩、褒贬之史观、史义。学界不妨以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之霸业为研究课题,外加吴越争霸之原委,作为研究选题,从或笔或削,看《东周列国志》对《左传》之接受,以此见历史与小说之分野,史学与文学之异同。此一选题,值得投入心力耕耘,犹持《三国志演义》文本,与《三国志注》《三国志》对读比较者然。深信对于小说之取资史传,如何自成一家,当有启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