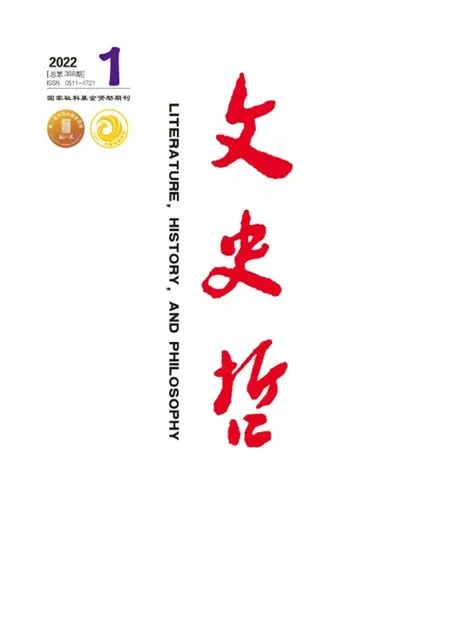古希腊思想中的秩序与无序
——从耶格尔的《教化》谈起
陈斯一
2021年暑期,德国古典学家韦尔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的名著《教化》()的中译本问世,可喜可贺。近年来,国内古希腊研究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学人开始关注古希腊文化之于西方文明的开源性意义;随着广义古典学的兴起,不少研究也不再受限于狭隘的文、史、哲分科,而是能够综合不同性质的文献和材料,对古希腊文化的肌理进行深层次和系统性的考察。正如李猛指出的,“对于现代中国来说,西方早已不再是大地另一端毫无关系的陌生世界,而已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内在构成部分。而西学也不仅是在内外体用的格局中权宜以应世变的工具,反而一度成为我们通达自身传统的要津……西学是重建我们自身文明的世界图景的总体性学术”。现代中国学术要重建“自身文明的世界图景”,就需要尽可能原本地理解西方文化,尤其是其“本源”。在这方面,耶格尔的《教化》能够为我们提供巨大的帮助,因为《教化》一书的任务正在于“对古希腊人的文化和教化进行阐述,描述其独特品质和历史发展”。
数年前,耶格尔的《教化》英译本曾点燃笔者从事古希腊研究的热情,此刻重读中译本导论,一方面感慨良多,另一方面,与笔者学生时代相比,又增添了几分反思和批评。本文希望借《教化》中译本出版这一时机,将《教化》导论对古希腊文化的推崇与西方学界对古希腊思想的批评相比较,并结合赫西俄德、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一系列重点文本,尝试对古希腊思想的独特品质提出一种更加准确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古希腊文化最为耶格尔赞颂之处在于对理念、形式、秩序的追求,但是在阿多诺和列维纳斯看来,这种单方面强调秩序的思想倾向于抹平世间本然的无序、扼杀鲜活的生存经验。相比之下,尼采的观点更加复杂,也更加深刻。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洞察到古希腊文化的精髓在于代表无序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与代表秩序的阿波罗精神的结合,这是一种在深刻体认无序的前提下努力创造秩序的悲剧精神。笔者较为赞同尼采的思路,并且认为,秩序与无序的张力贯穿古希腊思想的始终,不仅存在于悲剧中,也存在于史诗和哲学中,因此,想要更加原本地把握古希腊文化的特性,我们必须研究这种张力的演变。
接下来,笔者将首先对耶格尔对古希腊秩序观的阐述与阿多诺、列维纳斯、尼采的批评进行梳理和比较(第一、二节),然后再沿着尼采的思路,从秩序与无序的张力出发,对古希腊史诗和古典哲学的多个重要文本提出一种思想史的诠释(第三、四节)。
一、耶格尔的《教化》与古希腊秩序观
耶格尔的《教化》全书共三卷,第一卷从荷马的“德性教化”讲到雅典悲喜剧、智者思想的兴起和修昔底德的政治哲学,第二卷重点阐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伦理政治思想和教化理念,第三卷补充介绍柏拉图时代的思想争论,以及后期柏拉图、色诺芬、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梯尼的先后登场,医学、修辞学与哲学对教化权威的争夺。可以说,凡以文本为载体的古希腊思想,其所有重要的领域、阶段、派系和方方面面的问题与争论,都被耶格尔囊括在《教化》的视野之内。更加重要的是,耶格尔在导论中清晰地交代了他对古希腊文化独特品质的总体理解。在他看来,古希腊一切文化成就的根源都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形式感和秩序感,由此产生出以完美的形式秩序为范式塑造人性的教化理想。《教化》德文原版的副标题正是“形塑古希腊人”。


古希腊文化对理念与形式的秩序感的强调(以及德国文化对此的继承)让耶格尔引以为豪,这使得《教化》的导论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然而,在学术史上也不乏对古希腊秩序观及其缔造的哲学传统进行批评的声音。在晚近的学者中,阿多诺和列维纳斯对西方哲学及其古希腊源头的批评是比较典型的,他们的批评实际上延续了早期尼采站在悲剧精神的立场上对古希腊哲学的批评。下面,让我们从耶格尔对古希腊秩序观的推崇,转向阿多诺、列维纳斯、尼采对古希腊秩序观的批判。
二、阿多诺、列维纳斯、尼采对古希腊秩序观的批评


当然,阿多诺和列维纳斯的论述语境与尼采完全不同,阿多诺倡导的“非同一性”和列维纳斯重视的“陌异性”也并不等同于尼采所说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但是从结构上讲,尼采的观点与这两位哲学家的论述框架确实能够呼应。尼采看到,古希腊文化并不缺乏对逃逸概念把握之物的敬畏,也并不缺乏自我和他者的陌异性张力,只不过这种敬畏感和精神的张力存在于悲剧而非哲学之中。对于古希腊哲学,尤其是苏格拉底之后的哲学,尼采的批判同阿多诺和列维纳斯的批评是相通的。尼采提出,苏格拉底是悲剧精神的终结者,他将苏格拉底比作独眼巨人,用乐观理性主义的“独眼”建构出一个完全符合秩序的虚假世界,并且自欺欺人地把这个虚假的世界当作唯一的真实,既驱逐了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迷醉,也败坏了日神阿波罗的梦幻,从而导致深受他影响的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失去了真正的悲剧精神,伟大的悲剧传统就此消亡。柏拉图的理念哲学是耶格尔心目中古希腊秩序思想的巅峰,但在尼采看来,它其实标志着古希腊思想张力失衡的极致与健全生命力的衰败。

本文余下部分将对古希腊秩序观的思想脉络进行简要的梳理和分析,以便挖掘贯穿其中的秩序与无序的张力,力图对从史诗到哲学的古希腊思想提出一种更加全面和准确的分析。受限于篇幅,笔者将忽略尼采业已充分论述过的安提卡悲剧,而将重点放在史诗与哲学这两个脉络的端点。
三、古希腊史诗中的秩序与无序

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思想。在大部分时候,荷马提到的诸神指的都是高度人格化的奥林匹亚诸神,它们之间保持着严明的秩序,宙斯是万神之父和主权者。然而,荷马也保留了另一套更加自然的神系,那就是各种河流之神、海洋之神,以及他们的始祖“长河神”奥克阿诺斯。在主流的神谱中,奥克阿诺斯是天空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之神盖娅的长子,是环绕世界之河、所有河流与海洋的源泉,阿喀琉斯的母亲忒提斯是他的外孙女;但是在另一套或许更加古老的神谱中,奥克阿诺斯是最早的神和宇宙的本原,他被称作“众神的父亲奥克阿诺斯”与“生成一切的奥克阿诺斯”。在《伊利亚特》的剧情中,奥林匹亚诸神常常参加人类的战争,而在阿喀琉斯最终复出的那场宏大战役开始时,宙斯召集众神开会,让他们自由参战,唯独长河神缺席。随后发生的战斗逐渐从人与人转移到人与神之间,阿喀琉斯对战特洛伊的护城河神克珊托斯,这位河神是奥克阿诺斯的儿子,他以流动无形的水体出场,用滚滚巨浪攻击阿喀琉斯,自始至终并未化作人形,这种纯粹自然的神明形象在荷马史诗中是极为罕见的。最终,代表技艺的工匠神赫菲斯托斯用神圣的天火打败了河神克珊托斯,正如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宙斯用霹雳之火征服了混沌。
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无序和有序的对立最初表现为混沌和大地的对立,最终表现为混沌和奥林匹亚诸神的对立;在荷马史诗中,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亚诸神同样代表着最高的神圣秩序,而长河神奥克阿诺斯暗暗挑战这一秩序的权威,争夺众神之父的名号。混沌是黑暗的深渊,奥克阿诺斯是无限循环的洋流,总之,都是混乱无序、流变无形的最原始的自然力量,而奥林匹亚诸神构成了光明的殿堂和文明的秩序。从内容方面来看,史诗作为古希腊文明最早的思想性文本,其实并非耶格尔认为的那样仅仅着眼于建构完美的形式,也并非像尼采说的那样仅仅反映了“朴素的阿波罗原则”,而是强调无序和有序的对立,讲述秩序战胜混沌的斗争。
四、古希腊哲学中的秩序与无序



《理想国》对哲学家王“制礼作乐”的描述和《蒂迈欧篇》对工匠神创世活动的描述如出一辙,这两种创制活动都以“存在”为根据,依照永恒的理念或范式来建立宇宙和城邦的秩序;而正如工匠神的创世活动需要克服混沌的必然性,哲学家王的立法和统治也需要克服人性中混乱无章的欲望和激情。柏拉图思想的复杂性就在于,在强调宇宙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同时,对自然和人性的无序也有着深刻的认知。《蒂迈欧篇》提到的必然性是独立于理智和技艺、无法被彻底革除的自然力量,而《理想国》关于完美政体的哲学论述也需要面对人性之恶的挑战,完美城邦的建立取决于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前提:“除非哲学家在我们的这些城邦里是君主,或者那些现在我们称之为君主或掌权者的人认真地、充分地从事哲学思考,并且这两者,也就是说政治力量和哲学思考,能够相契和重合……否则政治的弊端是不会有一个尽头的,并且,在我看来,人类的命运也是不会有所好转的”。完美城邦的理想和人类政治的现实之间存在一种悲剧性的张力,这才是《理想国》真正想要表达的思想。




他就像黑杨树那样倒在地上的尘土里,
那棵树生长在一块大洼地的凹陷地带,
树干光滑,顶上长出茂盛的枝叶,
造车的工匠用发亮的铁刀把它砍倒,
要把它弄弯来做漂亮战车的轮缘,



五、馀 论
耶格尔在《教化》的导论中盛赞古希腊教化理想背后的秩序观,而阿诺多、列维纳斯则对古希腊秩序观及其缔造的西方哲学传统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虽然以上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但是双方都只看到了古希腊思想强调秩序的一面,相比之下,尼采对古希腊文化特质的理解更为深刻,但他将悲剧和哲学对立起来的观点则有失偏颇。尼采提出的阿波罗精神与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张力,实质上就是秩序和无序的张力,这种张力贯穿从史诗、悲剧到哲学的古希腊思想史。古希腊文化缔造自然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强烈冲动,源自古希腊人对宇宙和人生本然无序的深刻体认。因此,想要更原本地把握古希腊文化的特性,我们必须重视古希腊思想中秩序和无序的悲剧性张力,研究其根源和演变。

然而,单从《教化》的导论,我们很难还原耶格尔对战争的态度。如果西方各民族国家的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子嗣,继承了古希腊文明的“形式和理念”,那么按理说,以欧洲内战为中心的两次世界大战就并未完全违背古希腊文明的精神。毕竟,古希腊文明根源性的形式感是由战争史诗所建立的,而且在古希腊文明最灿烂的时刻,“真正的文化”内部也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不仅是希腊人的历史,而且是大部分异族人世界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动荡”。尽管雅典帝国的伟业失败了,但是古希腊文化最早也最忠实的继承者——罗马,最终征服了当时已知的世界。耶格尔并非没有设想过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未来的某一刻,“真正的文化”再次通过“历史的力量”将全人类统一在一起。这正如阿多诺所言,“伟大的哲学”都具有绝对主义的征服性激情:“伟大的哲学伴有一种不宽容任何他物而又以一切理性的狡猾来追求所有他物的妄想狂似的热忱”。
在尼采看来,古希腊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在深刻领悟了生命的全部苦难之后仍然选择拥抱生命。或许,古希腊人也比其他民族更加清楚地知道,一种从狄奥尼索斯的深渊中艰难创生的阿波罗秩序将永远伴随征服与被征服的残酷斗争。重读《教化》让笔者想到,对于辉煌而短暂的古希腊文明,热爱和平的人们不妨在满怀敬意的同时,也保持一份清醒的警惕。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