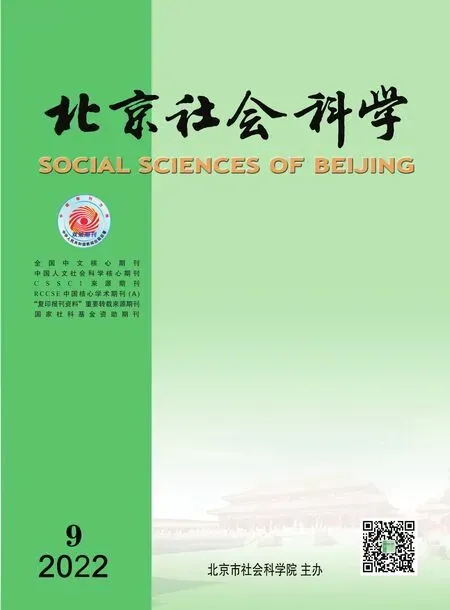新浪潮电影的本土化实践
——以严浩《似水流年》为例
田 泥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香港城市化的发展,香港电影广泛吸收西方新浪潮艺术元素,开始了与域外文化融合的自我革命的本土新浪潮电影运动。严浩作为中国香港的新浪潮代表,于1978年率先执导了被视为香港新浪潮电影开山之作的《茄哩啡》,开始了香港电影思想与艺术革命的探索。其实,1958年兴起于法国的“新浪潮电影不仅是思想和艺术表现形式上的一场革命,同时也是制作领域的一场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电影制作人员的职业观念和职业生活习惯。”这种革命性的浪潮很快席卷欧美。香港中西文化交融会通的地理与文化优势,还有社会环境、产业生态、多元文化冲击力,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严浩等青年导演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在中国文化、香港本土文化、欧美文化等相互交融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因此,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电影语言上均表现出了一定的前卫性,并在两个维度上得到了发展:一是寻求商业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淡化意识形态与政治性;二是寻求艺术性与主题表达的有效结合,强调对人性与生活性的立体展示。应该说,严浩等掀起的香港电影新浪潮运动,不仅促进了电影主流叙事方式的改变,将殖民化的社会历史嵌入生态格局的裂变与重组中,展现了港人由于所处历史时空与母体文化所产生的割裂性,也反映了其对中华母体精神的依存性,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根脉性。香港电影一直以反映市民趣味的类型片为主,严浩等人的新浪潮电影开拓出一片不同于香港主流商业电影的影像空间,也激发了内地、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兴起,并促进了整个中国电影艺术现代化的发展。
严浩最具代表性的新浪潮电影是1984年拍摄的《似水流年》,该片由孔良编剧,斯琴高娃、顾美华主演。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香港人回内地拍摄的第一部文艺片,《似水流年》一举囊括了198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剧本、最佳女演员、最佳新人、最佳美术指导六项大奖。该片以现代性的眼光来审视城乡之间的切换,以纪录片般的写实电影语言,尽可能地展现乡村记忆、道德伦理与生活美学,并对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生活经验进行描绘。电影的叙事、风格、节奏、主题等,既是对西方新浪潮的延续与拓展,又回切到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中,昭示了港人对中华母体的精神皈依性。该片也显示出了个体或群体的主体性在城乡切换的多元建构中的重要性,是新浪潮电影在本土的美学实践。电影揭示出,“城市”作为现代化的先锋符号,对乡村造成了冲击力,但又因自身商业化造成了港人的极度紧张情绪,而乡村成了个体渴望得到释放、获得原乡精神动力的有效空间。从《似水流年》可以看出,严浩一方面扎根中国本土,展示中国故事、世情伦理、道德秩序与情感结构等,另一方面也将目光投向世界,寻求获得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二、新浪潮运动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
严浩深受1958年法国新浪潮的影响,对旧有香港重消费的电影观念与创作模式发起了挑战。法国新浪潮的内核在于,当时安德烈·巴赞主编《电影手册》,聚集了克洛德·夏布罗尔、特吕弗、戈达尔等50余位电影人,他们深受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提出“主观的现实主义”口号,刻意描绘现代都市人的处境、心理、爱情与性关系,充满了主观性与抒情性。随后,这种浪潮逐渐传播到意大利、瑞典、德国、波兰、美国等国家或地区,掀起了新的电影运动。新浪潮的审美特征主要体现在:致力于表现人的内心生活,不纠缠于具体历史事件的讲述;通过长镜头、移动摄影、画外音、内心独白、自然音响,甚至使用违反常规的晃动镜头,来表达人的主观感受和精神状态等;在取景、色彩、自然光、剪接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表达形式与风格。1978年,严浩、余允航与任泰合组公司拍摄的影片《茄哩啡》拉开了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序幕。影片以独特的电影语言与叙述方式,讲述了社会底层何能克失业后,偶然成为一名临时电影演员的故事。随后,1978年8月18日出版的香港电影杂志《大特写》发表了题为《香港电影新浪潮:向传统挑战的革命者》的评论文章,首次用“新浪潮”一词来形容香港电影的新气象。之后,许鞍华的《疯劫》(1979)、《倾城之恋》(1984),徐克的《蝶变》(1979),章国民的《点指兵兵》(1979),方育平的《半边人》(1983)等相继问世,成了“新浪潮”在香港本土电影的一次对接与实践。这些电影所涉题材广泛,其中《疯劫》改编自真实的案件,充满悬念与推理,强调实景拍摄、不加雕饰的写实风格,被称作“香港第一部自觉探讨电影的叙事模式、手法和功能的电影”;《蝶变》把科幻和武侠合二为一,打造成了“未来主义武侠片”;《点指兵兵》是关于警匪故事的影片;《半边人》讲述年轻的卖鱼女阿莹面对单调的生活,在现实与理想、爱情与友情、家庭与工作的冲突中,以积极姿态应对的故事。这些电影显示了香港电影对商业逻辑的遵从,也预示了香港新浪潮并不能推动社会文化内在结构发生变化。如徐克说:“新浪潮的开始,虽然会有导演选择一些比较冷门的题材去拍,但我一直都希望做个商业导演。”许鞍华感叹:“如果我们当时有一个意识形态,或者大家一起合作,将这件事变成一种在经济上与意识形态上可行的东西,即团结性的东西的话,我相信会好很多。因为搞电影并不只是拍东西,搞电影是一种意识形态,需要将这件事系统化及企业化,将经济结构与制作结构的系统弄清楚。我们没有将它变成一套制作的方式,亦没有团结的力量,最多是大家不会互相斗争,但肯定是没有合作。我觉得这是一种可惜。”新浪潮导演当时并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面对都市商业化的兴起,在本土传统与外来文化冲击的夹缝中,展示了香港都市现实生活的紧迫与焦虑。
显然,严浩本土新浪潮电影的实验“不同于徐克的求新多变和许鞍华的沉重探讨,也不同于方育平的写实风格和谭家明的实验影像美学,而在一系列作品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贯穿了执着的主题探讨、自觉的叙事策略和鲜明的影像风格……严浩是新浪潮中‘最中国化的导演’”。魏君子在《香港电影史记》中对严浩导演评价道:“淡而有味,言之有物,不盲目商业化,追寻命运的价值与身份的定位。”严浩也表示:“希望在通俗上下功夫,在娱乐与艺术之间平衡,娱乐是电影的基本,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根基,有了生存才说得上如何生存得更好、更有意义。”曾游学伦敦电影学院的严浩,早在1975-1976年就执导了个人首部电视剧《北斗星》;1977年编导的犯罪剧《国际刑警》获得美国纽约国际电视节铜牌奖。1978年执导了《茄喱啡》首部新浪潮电影之后,严浩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其实“我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生命点上,既不能退后,又无法前进”。严浩声称:“归根结底,我想拍一部表面上是个简单故事,而涉及的命题是多层次的、深沉的,以无中见有,以小中见大。”在《似水流年》拍摄之时,严浩对影片的基本定位是对城乡人生活情态进行描绘,以凸显人物在转型时期的心理变迁与内在情感变化。而如何将新浪潮与本土的文化语境结合,体现新的艺术样式与意义价值,这成为严浩着力要寻找的。
严浩的电影叙述,力求展示港人在20世纪80年代焦躁、恐惧的漂移复杂的文化心理。同时,由聚焦于都市生活景观,转向对原乡生存景观与精神文化的找寻,还有在城乡切换中建构女性形象,并发掘女性的主体性价值所在。因此,严浩在谈论《似水流年》时说:“整部电影既然是一个寻找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情节绝对不能太起伏了。”的确,《似水流年》是单纯的线性叙事,以移动的视角将城乡空间中的个体与群体作为考察对象,讲述了在香港生活的姗姗(顾美华饰)回到阔别20年的潮汕老家,给儿时的玩伴如今已是夫妻的阿珍(斯琴高娃饰)和孝松(谢伟雄饰)的沉闷生活带来了一些小小的冲击和现代气息,还出资与阿珍一起带领乡村的儿童去广州观光等。同时影片还展示了因生活环境变化、城乡文化心理差异、伦理观念冲突导致的阿珍和姗姗之间内心的极大反差。电影还蕴含着深层的象征意义,正如严浩所述,“主人公回到一个怀抱和纯朴的世界里,一个可以接受她的地方,代表的是一部分香港人对祖国的感觉,既亲切又陌生”,这意味着个体向原乡的回归,也是港人向中华母体的靠近。
《似水流年》城乡切换的动力来源于两个互逆的运动:一是乡村走向城市空间的移动,姗姗随父亲进入了充满诱惑的都市香港,但也衍生了诸多对城市生活的“水土不服”;二是城市走向乡村的移动,香港城市中相互倾轧的利益关系,导致姗姗竭力想要逃离,从城市空间回到潮州空间。姗姗在城乡空间中移动,与城市生活做了短暂切割,见证了虽清贫庸常但透着宁静与祥和的原乡,一种近乎桃花源般景象的潮汕乡村,为自己飘忽不定的内心找到了暂时安放的空间。严浩不是简单地把乡村景象与生存历史展示出来,而是靠声音和画面营造历史语境,并与现代社会发生关联。女性在历史中也不是隐匿性的存在,严浩试图以潮汕和香港互为参照,又以广州作为勾连,通过两地女性性别角色的差异,来反映时代浪潮下城乡伦理文化的变迁,勾勒出时间中的情感线索与心理,还原时代浪潮中的乡村记忆。
电影《似水流年》也不仅仅是故事的讲述,还有艺术的提炼与意义的表达。作为精神产品,《似水流年》承载着时代的印记,在记录历史与现实生命实践的同时,也雕刻着城乡切换的景观。更重要的是,如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所表述的,中国传统乡村文化中出现了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电影通过两位女性人物关系的反差,反映出新时期乡村遭遇现代化后被压抑的人性、思想逐渐被激活;同时指出,远离城市喧嚣的偏僻淳朴的原乡,也净化着被城市商业化控制而扭曲的人性。如此,一方面将香港回归前人们的复杂心态展示出来;另一方面也深化了城乡切换主题的表达,即转型期个人或群体的焦虑其实是社会整体精神状态的反映。“一个特定时代和国家的社会焦虑和精神焦虑会在它的艺术中表现出来……艺术必须就它的表面含义和内在含义来加以分析,在它的显而易见的内容中存在着大量潜在的社会和精神信息。”这在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看来,“因为在艺术中心中,思想仅存在于形象的表达之中,而形象既是客观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作为对现实的某种主观认知而存在的,取决于艺术家的主观倾向与世界观”。严浩通过对比香港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的生存空间,使电影带有时代剪影的痕迹,同时也通过对乡村生活图景的展示与人的素朴形态的构造,与现代都市文化形成伦理张力,从而使电影兼具客观真实性与主观写意性。
三、电影的抒情与诗意及乡村景观叙事
电影《似水流年》的叙述张力,来自对潮汕乡村景观—人或事—文化等进行散文式的纪实美学表达。严浩追求真实与电影技术的合一,围绕着姗姗和阿珍、孝松重逢引发的情绪表达构成电影结构,进而完成对整个故事的讲述。电影主要由两条线索构成,主线是对潮汕原乡中姗姗、阿珍和孝松三个人之间欲说还休的情绪表达,副线是与姗姗互动中的长寿双胞胎老人、儿童等人物的故事。电影不仅把人物形象与潮汕景观联结,凸显其地域文化特色与文化性格,也将个人或群体与时代、环境的冲突进行了呈现。具体而言,从个人的生命形态、命运遭际来印证地域环境的影响,也透视出所处时代的动荡与变化,并以此来揭示女性内心世界及情感脉络,凸显潮汕乡村生活的简单素朴与人的价值根本,从而展示了城乡的差异性。
电影透过对港人姗姗进入乡村的视线移动,呈现出潮汕乡村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在姗姗眼里,乡村依然保留着自在的乡村伦理秩序与情感结构。《似水流年》是散发着淡淡乡愁与诗意的电影,带有特殊的时代感。其实,单纯的乡愁在整个20世纪及新世纪最初的十余年是电影的常见叙事母题。严浩记录潮汕乡村,“影像不是现实的摹写,而是艺术家的创造物,是经过文化‘过滤’的符号。影像的组合方式,是具有纯语言的约定性的重新结构的符号系统……为的是增添文化的属性”。电影中,“月光月梭朵,照篱照壁照下槽,照着眠床脚踏板,照着蚊帐绣双鹅”,镜头中的百年老树、暗淡老屋、挂在梁上的竹篮、木屐样式的拖鞋、南方带蚊帐的老式素眠床、瓢泼大雨中的油布伞及诗意化处理的风筝、稻草垛,还有潮汕方言唱的歌谣,构成原乡景观的自然与文化元素。如此,佐证了乡村景观的塑造应“从地方历史与传统、典型民间神话、口述历史、集体记忆中发现故事。文字描述、新的形态转译、情节编排、邀请当地人讲述故事等,是营造景观的必要手段”。《似水流年》将乡村景观纳入叙事中,既有水田、老树、河流、小船等自然景观的展示,也将祭祀仪式、祠堂、太极程式等人文景观纳入叙述,如镜头多次聚焦奶奶的祭奠仪式,灰暗压抑的屋子与鲜亮生机的桔子形成强烈对照,这种内生于乡村社会的礼仪习俗、宗族信仰等,恰是维系乡村根基的文化力量所在。
正如居伊·德波提出的,“景观社会”其实是一种“意象”的社会,作为乡村文化符号的象征,昭示着乡村文明的绵延与承传,具有内在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似水流年》中乡村日常生活以最为自然的方式存在,年老谢世的奶奶、早十年去世的父亲,还有与化肥一起倒在田间的老同学,他们自然生息于大地,也悄然融入了大地。孝松讲给姗姗:“你看,连我们这种年纪都在开始死去了。”忠叔劝慰姗姗:“年纪大了,去了是福气。”活着就意味着付出,乡村老伯的话:“平时怕惯了……儿子小的时候,怕失业,怕没钱,怕了几十年;儿子长大了,我又怕他们嫌我没本事,看不起我;儿子离开身边,又怕他们出事。”这是一种家庭与代际关系的现实。而千年古树旁边那两个练气功的百岁双生老人、大老粗的生产社队长、系着红领巾的小孩及几次出现的年轻老师等,他们的生命显示了从容与安然。这与都市生活中被姗姗自己扼杀的新生命及那对小夫妻无法获得的新生,形成极大的反差。但《似水流年》也折射出乡村生活伦理与都市生存秩序的平行性,尽管乡村生态延续着旧有的模式,但乡村意识形态却是一个闭环的、稳定的生态环境,无法介入、影响都市生活。
严浩以一种超然的叙述方式,在时间的脉络里考察城乡切换中的情感结构变化,同时将本土意识形态与伦理价值融入电影叙事,充盈着浓郁的乡情与时代气息。电影大多采用同框构图展现静态情感张力,将群体的不同情感需求表达得淋漓尽致。《似水流年》与同时期台湾新浪潮导演杨德昌的《海滩的一天》(1983)、《青梅竹马》(1985)一样,都是在讲述传统伦理情感与时代的冲突。不同之处在于,杨德昌局限于都市空间,以万花筒式的结构和精准的镜头调度,展现年轻一代的欲望与恐惧,具有理性与自觉的反思意识;而《似水流年》展示了现实处境中留守港人的各种焦躁、抗拒和恐惧,以及内地乡村的固守与流变,这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在香港、广州与潮汕的移动空间中,严浩试图展现转型时代人的内在心理、情感线索、生命形态及心理变迁,并把这一切表达融入中国风景画般的美学风格中,尽显情感张力与情绪反差。严浩曾说:“乡间的朴素生活、景色,很容易令人联想起中国画、中国诗。戏中主角的‘愁’更是中国诗词的传统主题。所在拍摄时,我给自己添加了很多功课,尽可能在适当的时候,利用画面去渗透诗、画的意境。”电影一方面凸显了香港都市人的紧张与压抑情绪,一方面赋予原乡以神话式的精神想象与情感皈依。电影充满了乡村美学格调,镜头里反复出现水田、白墙黛瓦、河流中的白帆、河边洗衣的少妇、赶鹅的少年、巷子里的大花猪、随风飘动的风筝、缓缓而过的帆船等;一些空镜头也反复出现,加上近景与远景的切换,构成了一幅原乡生态图。影片以轻缓的音乐伴随着行进的车辆,与孩子放风筝的段落构成了慢生活的景象,片尾以超现实的方式展现了姗姗与已故祖母一起的景象,这都为影片带来了灵动与诗意。
显然,电影中的乡村景观成了香港都市人释放的物理空间与精神想象空间,而对香港都市生活场景并没有过多的展示,仅以香港人姗姗的回乡之旅将香港与内地联结起来,并通过姗姗与阿珍的讲述,还有妹妹与姗姗通电话的画面来实现两地的互动。姗姗与妹妹关系的恶化、情感的失败与多次堕胎的经历,使姗姗退守到精神的原乡潮汕,期望回到原乡并渴望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对于自己的‘根’的确认代替了无根的漂泊感,主人公的精神已经回归大陆。”但是,回归充满传统伦理文化的潮汕原乡只是暂时的,最终还是得回到本已厌倦的香港,尽管在那里的家已不复存在。而姗姗所期许的精神治愈、内心宁静及所寻找的精神皈依依然难以完成。阿珍跟姗姗告别:“下一次相逢,恐怕又要十年以后。”电影里这样的对白充满了茫然与无奈。
电影中张姗姗尽管陷入了都市困境,但也在城市中获得了自立的女性意识。如在广州时阿珍陪姗姗住酒店,二人聊起之前在乡下时的情景,姗姗得知当时是阿珍让丈夫孝松来安慰自己,便不无气愤地说道:“你别搞错了,我不是来讨男人安慰的。我不是男人养的!每个铜板都是我自己赚来的!现在不是男人挑我,是我挑男人哪!你生活太淡,把我当盐哪?”她也会发出“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的心声,这种充满女性主义色彩的意味,与乡村女性构成了极大的反差,这也是乡村生活里的阿珍所不具备的。
四、城乡切换中的女性主体建构
严浩将城市与乡村的冲突置放在个体经验之中,并通过艺术的表达来展示这种无法切换的矛盾与复杂性,同时通过影像细节与情绪渲染,还原和记录20世纪80年代的风貌人情,其影像文本不啻是大时代小情境下的一部精心制作。作为新浪潮的推动者,严浩深受小津安二郎、弗朗西斯·科波拉、米克洛什·杨索及布努埃尔四位导演的影响,诸如小津安二郎镜语简单的固定镜头、科波拉复杂的景深、杨索的运动长镜头和布努埃尔的超现实主义,这些捕捉人类普遍性情感的方式,都是严浩积极借鉴的。同时,严浩又颇受中外文化的浸润:“小时候我的阅读很杂,中国古典的、英美的,还有大量的苏俄文学,那些博大的、理想主义的作品对自己有着很大影响。”严浩的艺术体悟来自社会现实、电影、文学经验等,这也使他能够切入人的内心世界,采用视像媒介来表达外在社会的变化。
《似水流年》尽管呈现出一种简约、静默的美学格调,但导演将富有潮汕生活气息的画面,诸如耕田犁地、水牛打滚、河边洗衣、下水捉水蛭、给老人煨茶、送橄榄炭等,以静态的构图与人物的复杂心理形成对照,加之剪影式的与手持摄影机的跟拍方式,使人物在长焦镜头中走向纵深,营造出疏离与不确定的感觉。“如果我在原来的内容上没有做提升,这结果便‘很平’,相反,在一个镜头里内容有变化有层次,这就是有‘电影感’。”如把阿珍与孝松日常化生活场景的展示一直置放在夜的暗色中,对阿珍与姗姗在老宅中生活细节的展示,也只有一盏昏黄台灯的光亮。类似的画面尽显示乡村的宁静单调,当然也包含因乡村物质匮乏所带来的困惑。另一方面,电影也透过展露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姗姗在夜晚向领奖回来的阿珍袒露自己的情感经历,触及到人的心灵深处,显示出多重的深度内涵。
无独有偶,拍摄了《非法移民》(1986)、《秋天的童话》(1987)的香港导演张婉婷,又推出了《似水流年》的姊妹篇《八两金》(1989)。从船舶遍布的沿海到演员人物的出现,这两部电影有诸多雷同之处。编剧罗启锐、张婉婷似乎更中意对政治标语和文化差异的解读。《八两金》讲述了纽约华人回大陆乡下探亲的故事,充满了原乡景致与乡土情怀。《八两金》的格调经历了从欢快到忧伤的转变,《似水流年》则自始至终是沉郁的。《八两金》的结尾以一首萦绕不断的《船歌》表达了身份转变带来的困惑。严浩的内心世界一直蕴藏着中国本土的文化牵动,尤其父亲的离去对他触动很大,找寻文化根脉的归宿成为他的精神动力。他说:“国家民族对我来说是身体情绪的一部分。”《似水流年》没有过多的戏剧冲突,弥漫着诗意的追忆与感伤,蕴藏着对逝去的乡村景象的追怀与乡愁,以及对道德、宗教、人性、女性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思与批判。
其实,以严浩为代表的香港新浪潮运动,也激发、推动了内地20世纪80年代的新文艺思潮运动。张暖忻和李陀认为,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电影“现代化”的进程,是“从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这一方面着眼的”,即“对电影语言进行探索”。作为新浪潮电影实验的样式,内地导演张暖忻的《青春祭》(1985)绝不逊色。电影运用纪实性加抒情的散文叙述,淡化戏剧的手法与传统模式,重视情感表达,采取散文结构形式,一方面对自然流动着的傣族日常生活场景、民俗风情予以展示;另一方面,透过女主人公的眼睛,呈现了傣乡人的生活形态,折射出傣族社会生活场景,侧面展示了傣族人的心理结构,以及追求自然、社会与人和谐共存的生命图式,从而揭示出中华民族的深刻底蕴与思想内涵。可以说,严浩的《似水流年》、张暖昕的《青春祭》等,从中华文化精神谱系中发掘生命力量,注重对时代困境的反思和抗争,极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现代电影语言”,即淡化故事情节,注重时代情绪的渲染,凸显人物内心世界,强调造型艺术美学对电影的意义。
《似水流年》成了严浩艺术创作的转折点,之后他逐渐转战内地,拍摄了一系列与内地文化紧密相关的影片。与之前的《茄喱啡》(1978)、《夜车》(1979)、《公子娇》(1981)等专注于香港空间经验故事表达不同的是,《滚滚红尘》(1992)、《天国逆子》(1994)、《庭院里的女人》(2001)、《太阳有耳》(1996)、《浮城大亨》(2012)等移动到内地、台湾空间,构建出关于多重跨时空的想象,发掘女性存在的自我革命与反抗精神。《滚滚红尘》作为一种反思女性历史的影片,既是关于女性自我拯救与觉醒的故事,同时也蕴含着对女性之于民族、国家以命运关联的思考。电影《太阳有耳》体现了一个弱女子对抗强大男权势力的自觉意识。《天国逆子》中的母亲蒲凤英为追求幸福变成了一个谋杀亲夫的荡妇并受到惩戒的罪人。《浮城大亨》中充满了对母爱的赞美。严浩将对女性群体的审视,放置在整个宏阔的社会、国家、民族层面,来展示其生存命运与情绪的表达,颇具“小人物”与“大历史”的电影叙事与美学格调。但这里的“小人物”显然不是历史的符号,而是体现了所属时代具有普遍性的人的价值。严浩趋向于表现立体的人性与生活性,如他评价《浮城大亨》中深受名利诱惑和身份困扰的布华泉所说的:“这个人毕竟不是历史,也不是政治,他代表人的精神。”无疑,这些影片均展现出了时空的“移动性”“跨地性”,而严浩的这种“跨地性”则“意味着与多个地方的关联,人们通过跨地行为,或想象使不同空间和地方联系起来”。正如倪震所指出的:“无论从两岸三地电影文化交流与合作已经取得的成果,或是从弘扬中华文化这一共同历史责任看,发展三地合流的完整意义上的大中华电影,都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的。”顺着这样的逻辑,对于中华文化根脉性的挖掘与呈现,《似水流年》尤为典型。
进一步说,相较于严浩其他持有女性立场的文本,《似水流年》更具双重的隐喻性。一是有潜在的香港回归背景与相关问题指涉。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返乡或回归的故事,影片成片于中英就香港前途命运展开谈判并发表联合声明的1984年,呈现了当时一些港人由于历史时空与母体文化所产生的割裂性,对回归母体的复杂心情,其不仅有对中华母体文化的精神依存性,还有对内地刻板的认知图式与内心焦虑。影片中自香港返乡的姗姗、小学校长阿珍的内心复杂情绪既是时代情绪的显现,同时也是融入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女性的真实反应,展示了在城乡切换中的女性心理的变化。阿珍一方面本能地拒绝姗姗介入自己的生活,如室内广角镜头两人洗澡后的画面:姗姗强行要给素颜的阿珍化妆,而阿珍却极力躲闪,并对着镜子把口红擦掉。另一方面,阿珍又对经历感情受挫、父亲早逝及同妹妹决裂等人生变故的姗姗充满同情,对“去了香港也不讨好”的姗姗抱有惋惜之情;而丈夫、女儿、学生都接近姗姗,阿珍意识到城市的诱惑开始显现。所以,当阿强的家长表示希望孩子走出乡村、到广州上学时,保守的校长阿珍立刻阻止。这也预示着对城市化所带来的担忧、隐痛已初见端倪。《似水流年》的片尾曲:“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浩瀚烟波里/我怀念怀念往年/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留下只有思念……”恰好印证了电影文本所蕴含的内涵与意义,人在城乡切换中的流变与坚守。
其实,以城乡切换为切入点,将女性置放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解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女性生命形态、生存方式,洞悉女性心理转变与精神追求等,已成为当代艺术的一种潮流。《似水流年》中城乡作为一个移动的场域,所承纳的女性认知图式与生命形态,有资本主义消费意识形态与乡村伦理意识、主流意识形态与女性自我意识的冲突,也有乡村伦理文化与现代女性主体认同的碰撞,更有西方资本消费主义的商业逻辑与女性自我精神追索之间的博弈等。因此,聚焦导演、文本、观众与世界之间的联系,重新审视女性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并揭示在城乡一体化构建中的女性个体作为主体的生命价值与精神价值所在,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深受法国新浪潮电影影响的严浩,虽然在形式上有所创新,但在主题表达上还是难以托起对意义及价值本身的构建。或许这就是新浪潮所谓的“主观的现实主义”的另一弊端,即强调主观性与抒情性的表达,忽略对故事本身、具体历史事件的深度讲述。香港新浪潮电影在20世纪90年代末式微,之后在主流传统叙事的强压之下并未再形成大的声势。
五、结语
新浪潮电影有其生成的土壤,诸如变革的社会环境、宽松的文化氛围,还有启蒙的理性精神,这本身也是一场美学革命。严浩借助西方现代电影语言进行商业与电影内涵、意义表达的艺术探索,开始了思想与艺术的自我革命的实验,开拓出一片不同于香港主流商业电影的影像空间,并与中国内地兴起的当代寻根文化形成合流,融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艺潮流。作为新浪潮电影在本土的美学实践的代表作,《似水流年》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吸纳了新浪潮的艺术表达方式,具有多重美学意蕴与文化指向,其既展现出香港由于所处历史时空与母体文化所产生的割裂性,也反映了港人对中华母体精神缱绻的依存性,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根脉性,同时也反映了城乡切换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改变,还意味着因时间与空间中的移动,人的精神结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伦理价值观等发生了改变,而这恰恰说明了个体或群体的主体性在城乡切换的多元建构中至关重要。对于生存于其中的女性来说,她们承担着多元城乡文化的建构使命,其本身既是城乡切换的载体,又是主体的建构者。可以说,女性作为社会发展变化的标尺,在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中携带有时代的个人主义与群体特质,而女性在城乡空间中的生命形态与心理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图景与镜像,也是女性整体之于现代性的一个表征。
因此,将影视文本中的城乡切换作为一个视角,进入人与自然、本土文化、民间习俗、乡村景观、现代化元素等构成的共置空间,成了观察当代社会发展与个体自我革命的一个有效途径。城乡切换是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发展模式,也是新时代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严浩的《似水流年》如一面镜子照拂到了尘世,让我们看到了生存景观里的城乡切换及女性主体建构的必然性,因此电影不仅具有中华母体文化内涵与精神底蕴,也具有现实意义与审美价值。严浩等人掀起的香港新浪潮运动不仅推动了电影主流叙事方式的改变,也突破了新浪潮本身的形式框定与现代意识形态的规约,激发了内地、台湾新浪潮兴起并促进了整个中国电影艺术现代化的发展,也使中国传统文化、生存经验、中国故事得到世界意义上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