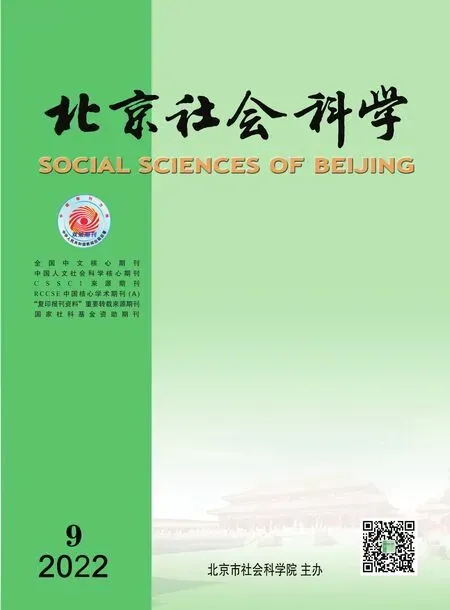从明清家训家规看儒家伦理的日常生活指向
钱国旗 刘 坤
一、引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思想工具。宋明以降,儒学以儒释道合流和世俗化、生活化指向,实现了哲学化的理论发展和大众化的实践转化,由此使儒家思想不仅成为维护统治的正统学说和官方意识形态,而且成为扎根民众日常生活的基本伦理观念和行为准则。
传统家训及家规,是圣贤经典的世俗化、生活化载体。家训家规旨在确保子孙繁荣、家道长远,但其不仅是针对子孙的家教,而且是具有更为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示范,体现了民间上层人士的思想价值取向及其对基层社会的价值引导指向。家训家规以世俗化的形态保存并发展了经典儒家的基本精神,使儒家伦理直接延伸到世俗民间,从而体现了其对民间日常生活发生直接作用的制度性价值。
长期以来,学界对圣贤经典的精英儒家研究较多,而对于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发生实际作用的世俗儒家伦理关注较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哲学史、思想史、社会史学者把目光投向“世俗儒家伦理”“一般思想史”“日常生活史”等研究主题。事实上,圣贤经典中的儒家思想往往代表的是精英思想家的信仰、哲理和官样教义,它们大多缺乏实际应用的可操作性,难以对民间生活发生直接的规范和协调作用。本文拟通过对明清家训家规类文献的梳理,观察这一时期儒家伦理的日常生活指向,以考察其对民间生活的规范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精英儒家和世俗儒家这两种理论形态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建构的。
二、明清家训家规与日常生活
通过对明清家训家规的研究,可以探察存在于经典价值体系中的精英儒家伦理,是如何由圣入凡与世俗社会相妥协,最终化民成俗推动官样教义走进民间生活的。本文从六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孝”的规约化和强制性
“孝”是儒家极力倡导的底线伦理和首善品行,在历代圣贤的价值观体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孝道不仅维系着家庭和睦,而且巩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色。孔子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二程强调:“致知,但知止于至善、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之类。”黄道周认为,孝乃“天地之情”。王夫之也认为:“君子之道大矣,而必以孝弟为万行之原。”他们都将遵从孝道作为治学行世的根本。
在明清家训作品中,孝也是被强调的重点内容。姚舜牧《药言》开篇即云:“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字是八个柱子。有八字始能成宇,有八字始克成人”,孝在成人八柱中居于首位。王士俊《闲家编》强调指出:“父母为吾一身之天,吾一家之君,故孝为百行之首。”
值得注意的是,与思想家的哲理化阐述不同,明清家训家规对孝道的强调,并非以先贤章句为主要内容的原则劝告,更多是包含各种行为准则的规约化条款,其根本内容都是要求子孙对父母祖辈听命顺从。在这些条文中,家族长辈对孝与不孝行为的奖励与惩罚,体现出民间生活的功利取向和约定俗成的社会控制效力。有些家族将子孙能够贯彻孝行视作家族的荣耀,因而对其给予褒奖。《东阳杞国楼氏家规》有《按抚公家规遗训》一条:“孝子悌弟,人道大节,风化所关。如有事亲敬长,行谊纯笃,可方古人者,合族举呈贤有司,以俟旌表。”《泾县新紫山倪氏家规》中对孝与不孝行为的奖惩规定十分明确:“凡族有孝于父母者,奖之励之,纯孝格天者合族请旌。有不孝者告诸族长,于宗祠内申明家规,委曲教诲之,不变则扑之,又不变则告诸官长而罪之,屏诸族外。”
由于家训家规直接面向家族成员日常的衣食住行和为人处世,所以这种对民间生活带有规约性质的文本,往往显示出较为强烈的强制性色彩。如《桐城祝氏家规》第一条《敦孝悌》:“堂堂七尺之躯,谁实生我,泛泛九州之众,孰是同胞。汉诏之首孝弟,良有以也。族中有忤逆不顺者,家规惩治。”而大部分家族则规定将情节严重者送官治罪,《邵阳隆氏宗规、家训》中的《宗规十六条》首条即云:“族中有不孝养父母及凌犯伯叔者,族众拘而重责之。不改,鸣官治罪。”《丹阳厉式宗祠规约二十四条》规定:“子孙有不孝、不弟及嫖赌、行凶者,父兄、分长鸣祠公集察核,于祖宗前杖责,勉其自新。如仍怙过不悛,则送官重处。”清代《龙舒秦氏家训》第一部分《孝顺父母》引用《大清律》规定:“子孙违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者,杖一百;子孙骂祖父母及妻妾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并绞,殴者斩,杀者凌迟处死。”可见,对不孝行为的家法惩戒是极为严厉的。
“孝”的规约化和强制性,使家训家规约定俗成为一种民间规则,这比温和的道德说教和原则要求更有民间教化功能和社会控制效力。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下,家训家规和国家制度相互关联,使得统治者以孝治国的制度要求得以在民间日常生活中贯彻落实。
(二)积极的家族主义
在儒家思想统治下,家族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孝经·开宗明义》指出:“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种光宗耀祖、扬名显亲的观念无疑是家族主义的重要内容。二程以孝悌之道阐述圣人之道:“孝其所当孝,弟其所当弟,自是而推之,则亦圣人而已矣。”明清时期的家训家规通过突出家族制度的正面功能,成为驱策人们努力向上的精神动力,其中所阐述的治家原则及修身立名、传业扬名的思想,体现了世俗儒家伦理积极的家族主义和成就关怀,反映出世俗社会信仰与价值体系的普遍取向。
两宋以降直至明清时期,世家大族式的家族组织趋于瓦解。随着士族制时代的终结,科举制度成为促进社会流动的一个基本动力,一般寒素之家可以凭借科举功名来提升个人和家族的社会地位,以科举功名光宗耀祖成为普遍受人关注的世俗目标。在一个流动的社会结构中,个人与家族的声望和地位有起有落,时升时降,如何维持和提升既得的名声与地位以确保家道长远,是每个家族成员所共同关切的问题。《含山環峰庆氏家规》有《务读书》一条:“千年阀阅之宗,必是家传黄卷;屡代簪缨之胄,无非世守青缃。金张七叶,显贵盈朝。王谢两家,风流满巷。莫不枕经藉史,因而驰誉腾休。”《金坛峙盕何氏家训、宗规》有《勤耕读》一条:“所谓故家大族者,以其读书成名也。故必习经书,明理义,达则可为朝廷梁栋,穷则可谓文墨通儒。”从他们追求功名的功利取向来看,子孙读书考科举是家族保持地位名声的重要保证。《萍邑姜岭陈氏祭规、家规》认为:“荣耀祖宗,显扬父母,全在读书。若家有读书之人,则礼义有人讲究,纲纪有人扶持,忠孝节义从此而生,公卿将相由此而出,读书二字关系如此。”
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秩序,提升家族的声望和地位,确保家门不坠及家道长远,这在家训家规中是一个永恒的训诫主题,其基本精神在世俗民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强调居家之道贵在立本:“一家中男子本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本之本也。本立矣而末犹萎焉,必其立之之根本未固耳。”蔡衍鎤《亦政编》强调,一个有功业的人更要以谦卑的态度去和睦家族:“家有显者,举族之幸也。然必能亲爱和睦使家门之内,肃肃雍雍,方能上慰祖宗之灵,下副一族之望。”
积极的家族主义也体现在“戒争讼”等训诫中。朱柏庐《治家格言》说:“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大荔西野杨氏家训》说:“宗族不可兴讼……骨肉兴讼,未有不家败身亡者也,戒之。”《宜春石里登南桥吴氏家规十则、家训十则》则认为:“人情争必斗,天道讼多凶”,“小忿宜忍耐,大事需消融。身家可长保,何必逞英雄。”在世俗社会的价值理念中,争讼不仅不利于人际交往,过多讼事,还会丧失名节,败坏家产。通过强调“居家戒争讼”,既保留了精英儒家“和为贵”及“必也使无讼乎”的理想价值,又给出了“以和治家”的生活准则,体现了儒家伦理的世俗化、生活化智慧。
为了维系家门不坠,振兴家族的名声与地位,明清时期的家训普遍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梁显祖《梁氏家训》云:“人家门祚昌盛,皆由修德砥行,世代相承,故能久而勿替。若为祖父者,不能积德行以贻其子孙,为子孙者,复不能积德行以继其祖父,未有不立见倾覆者矣。”涂天相《静用堂家训》云:“人家盛衰之故,不关一时之富贵贫贱,而系乎子孙之贤不肖。子孙贤,则虽劳苦饥乏,艰难百状,而势将必盛。子孙不肖,则虽势位富厚,煊赫一时,而势将必衰。”张英《聪训斋语》云:“人生必厚重沉静,而后为载福之器……思尽人子之责、报父祖之恩,致乡里之誉、贻后人之泽,惟有四事:一曰立品,二曰读书,三曰养身,四曰俭用。”每个人只有积德累行造福子孙,才能使家道长远、家门不坠。
在世俗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功利的追求往往高于道德的追求。在家族意识中,通过个人的功利成就来提升家族的声望和地位,无疑是积极的家族主义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的家训家规把功利追求合理化为伦理性准则,从而建构起伦理道德规范与功利成就取向融为一体的价值系统,子孙的道德修养和功利成就则成为保持家门不坠和家道长远的重要保证,显示出了儒家世俗伦理的鲜明特色。
(三)务实的治生之道
在社会分层和职业选择上,精英儒家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在传统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少数手工业者、商人属于被统治阶级,“学而优则仕”是先进分子流动上升至统治阶级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儒家提倡“重农抑商”,于是“士农工商”四民的划分成为中国传统社会通行的职业等级制度。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发展引发了士商合流,打破了传统的四民观念,对财富的关注和依赖成为支配社会关系的重要力量,人们的择业和治生观念也开始变得更加务实。从家训家规所提倡的治生之道来看,虽然倡导耕读传家,强调“士为贵”,但四民职业界限开始变得相对模糊,对职业选择的要求也更加多元。如庞尚鹏劝诫子孙:“士、农、工、商,各居一艺。士为贵,农次之,工商又次之。量力勉图,各审所尚,皆存乎其人耳。予家训首著士行,余多食货农商语,皆就人家日用之常而开示途辙,使各有所持循。”《何氏家规》要求:“男子要以治生为急,于农商工贾之间,务执一业。”大部分家训族规提倡随材就业,子孙聪颖便可力学上进,如果天资愚钝,则可从事其他职业,自食其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有所淡化。清代江苏吴县《金氏家训》提出:“读书原不专为举业,希图出身。子弟中英敏可以上进者,固应使之力学,不宜暴弃。即资性迟钝者,也要教他明白道理,通达古今,庶知利害,学做好人,在商贾中亦自令人起敬。”
治生之道,贵在勤俭,要在各务其本。明清时期的家训家规普遍倡导生活勤俭,反对游手好闲。《任氏家规、家训》云:“勤俭,为治家之良法。勤则贫可致富,俭则富不遽贫。”桐城姜氏家训中有《务勤俭》一条,强调“居家以勤,持身以俭,此治身之要也”。《治家格言》云:“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胜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益阳南峰堂龚氏家规、家训》云:“吾族为士者必以读书为本,为农者必以力田为本,为商者必以贸易为本,为工者必以精艺为本。各务其本,皆不失为资生之务,此皆悠游安乐而无后灾者也。”
在明清家训家规中,“勤”是受到特别重视的一个伦理价值,无论是子孙的学业修炼、职场谋生,还是个人的品德修养、家族的兴旺发达,“勤”都是重要的基础品质和教育重点。姚舜牧在家训中强调“一生之计在于勤”,他在教导子孙勤学以成就完美人格时指出:“要做天下第一等人在品格,要成天下第一品格在学问,要学问成立于世间在勤修。”袁黄《训儿俗说》告诫子女勤学修业:“人须法天,勿使惰慢之气设于身体。昼则淬砺精神,使一日千里;夜则减醒眠睡,使志气常清。”对“勤”的强调,在这一时期的蒙学读物中比比皆是,如张履祥《初学备忘》说:“韩子曰:‘业精于勤荒于嬉’,刘忠宣公曰:‘习勤忘劳,习逸忘惰。’人至嬉游忘惰,亦可哀矣。且思世间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者何物?”李惺《老学究语》劝诫人们:“民分为四,各技其艺,欲善其事,必致其志。只怕不勤,不怕不精。只怕无恒,不怕无成。”“勤”之提倡,最能体现儒家伦理对世俗生活的价值引领。“勤”的要求不仅适用于子孙的学业和职业,在个人修养和家族治理中也是贯穿始终的重要内容,这充分体现出了儒家伦理的日常生活指向。
(四)贵生养生与明哲保身
儒家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当生命与仁义发生矛盾冲突时,应该放弃生命,成全仁义。孔子说得很清楚:“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的态度更为鲜明:“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明清家训家规普遍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其教育子孙的着眼点并不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而是贵生养生、明哲保身,即如何在不害仁义的前提下通过贵生养生与克己不争自处于世。这一点,正体现了精英儒家伦理与世俗生活达成的妥协。
养生重在养心,贵在养德。石成金《传家宝》作为中国古代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和家庭教育读本,兼具善书和家训功能,书中强调:“心为君主,秉一身百骸之令,人欲长寿者,须从此调养,而木根水源也,因以心思为第一”,并提出了仁慈恻隐、少欲安静、戒除思虑、就事安乐的具体要求。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予拟一联,将来悬草堂中:‘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姚舜牧在《药言》中提出了节欲的养生思想:“凡人欲养身,先宜自息欲火。凡人欲保家,先宜自绝妄求。”欲望常常是不能得到满足的,如果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也就无法达到养生的目的。
不少家训非常关注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比如张英认为:“古人以眠、食二者为养生之要务。脏腑肠胃常令宽舒有余地,则真气得以流行而疾病少。”再如石成金《传家宝》对饮食养生提出了具体要求:“食宜早些,不可迟晚;食宜缓些,不可粗速;食宜八九分,不可过饱;食宜和淡,不可厚味;食宜温暖,不可寒冷;食宜软烂,不可坚硬。食毕,再饮茶两三口漱口,令口齿洁净。”又说:“人或有事争斗恼怒,不可就食。盖气上逆,而饮食咽下,气涎裏食,窒塞于胃之贲门,必成噎症。饭食难入,胃哽疼痛,最难医治。”
明哲保身的思想体现了中国文化精于世故的一面,但保身并不意味着苟且偷生,也不是放弃基本的原则与道义,这是一种在不害仁义前提下的明智选择。明清家训家规多从立身处世等方面,阐述明哲保身的思想。如张履祥强调自爱名节来保全自身,认为:“名节不可不自爱,一日失足,孝子慈孙犹将羞之。”关于如何自爱名节,庄元臣《治家条约》有《绝外事》一条专门讲述具体做法,强调:“一味闭门静守,便是吾家贤子孙也。”认为一个人只要洁身自好,不为名利所累,自然能够保持名节,保全自身。
明哲保身的思想更多体现为具体的处世策略。高攀龙《高子家训》曰:“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又说:“言语最要谨慎,交游最要审择”,“人生丧家亡身,言语占了八分”,以此警示子孙慎言慎行。他还教育子孙:“切不可结怨于人。结怨于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发,但有小大迟速不同耳。”王祖嫡《家庭庸言》告诫子孙要时刻铭记“容忍”二字以保全身家:“‘容忍’二字,不但避祸,实进德大助也。”庞尚鹏告诫子孙:“处宗族、乡党、亲友,须言顺而气和……若子弟僮仆与人相忤,皆当反躬自责,宁人负我,无我负人。”这些都是强调克己不争、自守保身的处世策略。
(五)约束与禁戒
儒家注重礼治,强调秩序与克制。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宋明理学家将“礼”作为“理”的外在行为标准,如朱熹提出:“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二程更是将礼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主张通过礼治教化来治国安民,所谓“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礼存则存,礼亡则亡”。他们将礼与国家的治乱兴衰结合起来,将礼作为一切社会行为的总原则。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变化,赌博、狎妓、吸毒、酗酒等各种社会不良问题也随之而来,儒家的伦理价值因此受到重视。这一时期的家训家规,多有针对赌博等不良行为的训诫,注重个人日常行为规范,强调审慎、约束与禁戒,这是儒家礼治思想向民间生活的延伸和转化。
庞尚鹏《庞氏家训》有《严约束》一节,其十六条内容均是对子孙生活伦理的约束劝诫,第一句就提到“子孙各安分循理,不许博弈、斗殴、健讼及看鸭,私贩盐铁,自取覆亡之祸”。《蒋氏家训》对子弟的私欲进行规劝:“少年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刻削元气,必致不寿。甚至恶妓娈童,不择净秽,多致生毒,势必攻毒之剂服之,而此身真气消烁殆尽矣。”
明清家训家规明文禁止子孙沾染赌博等恶习。汪辉祖《双节堂庸训》指出:“赌博之事万不可犯,犯必破家。即一切赌具,亦不可蓄。”河北任邱边氏《一经堂家训》规定:“禁赌钱……赌钱初则甚失钱,钱尽则失物,物尽则破产,及至破产,上不能事父母,下不能畜妻子,名为匪类,甚而卖子质妻,身居下品,此时悔之晚矣,能无惧乎。”南海佛山廖维则堂《家规》对子孙的赌博行为提出劝诫,并附有对触犯者的惩罚措施:“赌为盗源,最坏风俗。如有在乡设局开场聚赌,无论大小窝主者,停胙两年。”对于赌博这种不良行为,长辈以停发祭肉来惩罚,倘若有更为严重的情况,“乡内开设白鸽标厂,及招引外乡人开局诱赌者,停胙不足蔽辜,另行禀官究办。”
除赌博外,明清家训家规还禁止子孙有嫖娼等淫秽行为。浙江《皮氏宗规》规定:“淫为恶首,至祸甚钜。女宜谨守闺门,男当不苟颦笑。”清代《宁乡涧西周氏规训》中有《妨淫乱》一条,通过历史案例规劝族人:“淫者,百恶之首也……淫心一炽,或因宠而弃糟糠,或贪花而败名节,甚者衽席操戈、房帷设阱,种种祸端,皆由此起。戒之戒之!”崇明吴氏《祖训十则》:“色之害人,谓之软剑……戒之在色,先圣良言。百病攻人,皆由于色。”清代四川唐氏家族把吸食鸦片、嫖娼和赌博等行为一起列入“非为”,要求对“迷恋娼赌、酷嗜鸦片、打牌掷骰”等行为,先以情理感服,直至“爰请家法,以重惩责”。
明清时期的家族盛衰无常,家族荣盛的延续取决于子孙的德行功业。尤其是对于通过科举踏入士绅阶层的家族来说,只有子孙贤能,才能保证家族的长久兴盛。在明清士绅的家训家规中,除了有通过读书考取功名的仕宦期许,还包括长辈对子孙优良道德行为的观照。倘若子孙惹出祸端,则家族极有可能重回寒素。约束与禁戒的内容体现出家训家规的功利性与强制性特征,对嫖赌等恶习的禁绝和惩戒是对子孙最起码的道德约束,这也体现了儒家伦理对民间社会正风澄俗的制度性约束。
(六)善恶与因果报应
家训家规往往折射出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其中的伦理准则主要来源于儒家。传统儒家强调“为仁由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仁行善,这是儒家伦理在为人处世方面的道德标准,也是顺应礼治的内在道德自觉,后世儒者也将其看作个人道德修养的根本。在明清时期的家训家规中,为仁行善是与家教门风紧密联系的主流价值观念。
浙江浦江郑氏家训指出:“居家则孝弟,处事则仁恕,凡所以济人者皆是也。”明代仁孝皇后徐氏所作《内训》提出:“吉凶灾祥,匪由天作,善恶之应,各以其类。”明代陈继儒有家训作品《安得长者言》,通篇格言俗语,专攻修身处世之说,对子女后代进行道德教化和训诫,其开篇云:“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以此敦促子孙行善积德。 朱柏庐说:“积德之事何日可为?惟于不富不贵之时,能力行善,此其事为尤难,其功为尤倍也。”可见行善之事,不为外物所影响,也非亲疏贵贱所能隔离。正如陈继儒所言:“人生一日,或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虚生。”
古人于家训中推崇善德,劝人向善行善,首要目的在于强调人要以善修己、以德立身,培育完美的道德人格,以顺应伦理社会的礼治规范。汤斌《常语笔存》认为:“凡人为一善事,则心安而体舒,为一不善事,则心不安而色愧。”在家族的精神传承中,行善去恶被视为优良传统,通过家族的教化世代相传。许多家训家规将端正人心、风化天下作为教育目标和要求,推崇善行之教化,美化社会之风俗。如张履祥《训子语》以祖宗所传之“积善”二字教化子孙。清代名臣于成龙《治家规范》指出:“正惟一家有教,一国观感,相习成风,而仁让兴焉矣。”
儒家的天人感应思想对中国古代君主政治发挥了积极的制约和促进作用。世俗生活中的善恶观念,往往会与因果报应相联系,如此便将行善积德的伦理原则附上了鬼神宿命论的神秘力量,以超自然力推动人们从善去恶。《周易·坤卦》中就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古训。人们普遍相信,每个人今生行为的善恶,影响着自身的来世和后世子孙的福报及家族的盛衰。姚舜牧认为:“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古来人试得多了,不消我复去试得。”善事做得多了,自然会有祥瑞,恶事做得多了,自然会有祸害。袁黄《了凡四训》有《积善之方》一章,通过具体事例为因果报应学说提供事实依据,比如杨荣进士及第、位居三公,后世子孙也多有贤者,正是因为其祖父的善行所致。
从本质上看,善恶因果报应不过是行善积德这种道德行为由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但因其附加了天命论的神秘色彩及后世得报的功利成效,契合了世俗生活和一般百姓的精神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普遍的心灵寄托,从而也使儒家伦理价值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在明清时期的蒙学读物中,善恶与因果报应思想是极为常见的内容,如《名贤集》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积善有善报,积恶有恶报。报应有早晚,祸福自不错”;“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侵人田土骗人钱,荣华富贵不多年。莫道眼前无报应,分明折在子孙边”。《增广贤文》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善必寿考,恶必早亡。”
三、明清家训家规推动官样教义进入民间生活
作为圣贤经典的世俗化、生活化载体,传统家训及家规融合了家族的处世智慧和社会的行为规范,把精英化的道德理想转化为大众化的实践伦理,从而在家族层面建构了适应世俗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通过家族的繁衍生息实现文化的薪火相传。
明清时期,精英儒学的发展呈现教条化、哲理化、意识形态化的特征。“理学化的《四书》学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完成了其思想、学术、教育地位的全面提升,作为国家哲学、意识形态的色彩更为浓厚。”明清家训家规所反映的儒学世俗化、生活化转向,是对精英儒学的调整与纠偏,是把精英化的道德理想转化为大众化的实践伦理的一种有益调适,由此推动儒家伦理从官样教义进入民间生活,实现儒家“化民成俗”的教化功能。那些适合世俗社会、符合人性人情、契合家族利益、有利于社会秩序和谐的思想观念被人们所接受和传承,通过由圣入凡的妥协,最终成为化民成俗的制度性力量。
明清时期出现了较多的宗族家训家规寻求官方认可的情况,受到官府承认的家训家规在宗族层面担当起世俗教化的责任。万历十六年(1588)《陈氏族谱·家训》记载:“长沙县知县骆批,祥观族约,宜家化俗之心,再阅奏疏,崇本重源之念,此乡先生之贤者也。仰户首照依条款,一一举行,如有户丁抗违,许指名具呈,以凭惩究,付照。”这种官方认可的“合法化”进一步提升了家训家规的制度属性和执行效力,经过官方批准后,“大多数的家法族规成了国法的补充,发挥着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作用,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利益和意志。”
同时,在家族认同的基础上,家训所传达的世俗儒家伦理通过一定的节日仪式、行事准则、礼仪规范等方式,形成日用而不知的民风民俗,从而影响和引领人们的价值观念。如《庞氏家训》规定:“每月初十二、十五二日,凡本房尊长卑幼,俱于日入时为会,各述所闻。”在浦江《郑氏规范》中,规定每月旦望令弟子一人诵读家训,其余人皆认真聆听学习。通过这种风俗化的形式,官样教义中的儒家伦理化民成俗于民间的日常生活中。
四、结语
明清时期的家训家规还呈现出大众化、通俗化、社会化以及与童蒙教育合流等特征。较之儒家传统经典,明清家训家规向着语言通俗、道理简明、便于记诵、易于传播的方向发展,但其核心内涵仍以儒家思想为基本精神。有些家训多采用日常化的语言或直接引用俗语对子孙进行说教,如姚舜牧认为:“常言俗语,与圣经贤传相表里,慎毋忽焉而不察”,“俗语有尽可动人者,即骂詈之言,不可不察也。”家训内容中凝结了许多来自日常生活的经验和智慧,与宋明理学倡导的道德理想和道德修养相比,更易在世俗生活中得到实践。以常见之理和通俗之语表达圣贤道义,更有利于发挥对世俗社会的心理约束和行为规范作用,从而使儒家伦理穿透日常生活成为引导人们守正向上的文化动力。
① 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较多,例如:陈来.蒙学与世俗儒家伦理[C]//.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常建华.生活与制度:中国社会史的新探索[J].社会科学文摘,2021(3):25-30;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