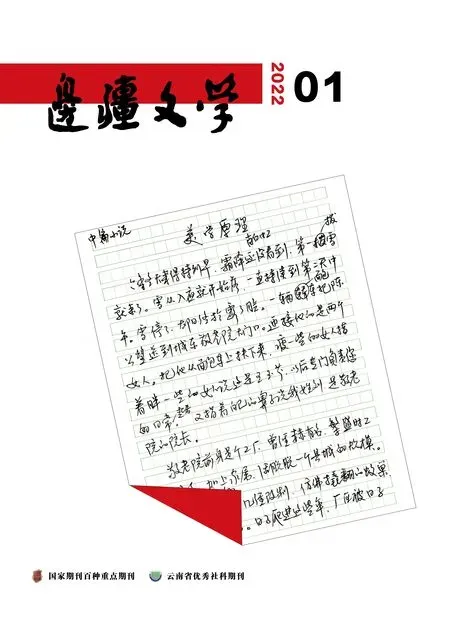天边的若尔盖
杜阳林
若尔盖草长莺飞,流水如碧,天际云朵相接,星辰触手可及。
若尔盖牛羊成群,牧歌飘散,英雄传奇不朽,族群生生不息。
黄河长江流经若尔盖,抚育了万物生灵,衍生了部落文化,汇入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奔涌向前。
都江堰的飞沙堰上方,便是岷江上游。重重大山峰峦叠嶂,山体轮廓渐渐模糊,消失在茫茫白雾之中。沿着山峰相连的曲折道路,便能通向若尔盖草原。
车行若尔盖的旅途,不绝于声的,是河流湍急奔腾的咆哮。白浪翻滚,穿行于深山峡谷,叩敲击撞,声响如雷,宛若大地强健有力的心跳。若尔盖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质运动多番博弈,在这里似乎达成了一种和解,拥有了历史沉思的稳重力量。回首远望,河水的奔流声响渐渐隐没于身后,海拔悄无声息地逐渐升高。若尔盖像是一只巨手托举的宝盆,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度傲然屹立,与流逝的河水更远,与天边的云彩却很近。
翻越查针梁子山时,山口立着一块石碑,这里便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在绵延起伏的草原两侧,流淌着中国著名的两大水系。发源于山南的白河,在若尔盖县唐克乡注入黄河,成为黄河支流;山北的铜锅河水,向南流入大渡河,成为长江支流。在查针梁子翘首东望,林木覆盖峡谷幽深,远处雪峰风起云涌;转而向西,草原辽阔平坦,溪流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在草地间缓缓流淌。水系的分水岭,从此也就成为地形地貌的分界线。
区分和交融,是若尔盖永恒的主题。这里历来是去甘肃和青海的要塞,身为阿坝州的北路重镇,是青藏高原与内地沟通的前缘地带,历史上为兵家必争之地。因地处南下岷江、大渡河或东出嘉陵江通达四川盆地的三角区域,若尔盖的交通和贸易,陆路水道,一应俱全。
若尔盖拥有枢纽一般的位置,也有悠久的历史。在史前时期,若尔盖便是中华民族重要族源“古羌人”繁衍发祥的重要场所,属西戎范围。先秦时,为析支河曲羌戎辖地,南北朝属吐谷浑,唐朝初年为松州羁縻,贞观十二年为吐蕃所据,元朝时于今求吉乡境内设潘州,明代属松潘卫,清朝受松潘厅漳腊营管辖,民国时期属松潘县。1956年7月若尔盖正式建县,隶属于阿坝藏族自治州。
随着太阳西沉,若尔盖的风越来越凉,温度骤降,才知草原气候一日多变,名不虚传。若尔盖位于多环流交汇地带,受东亚季风、印度洋季风、西风急流以及高原季风的影响,冬夏季风分别受控于不同的环流,也同时受控于多种环流的作用,常常表现出不同的冬夏季风组合特点,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又相互嵌套,反映出了复杂的气候系统特点。特殊的大气环流以及地理特征,使它成为中国三大自然区域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的交错地带。
复杂的气候与地形,塑造了不一样的若尔盖。东边的岷山、南面的邛崃山、西边的果洛山、阿尼玛卿山、西倾山以及北面的西秦岭重重环峙。群山轻拥高原盆地,此处年均温仅为0℃至2℃左右,终年低温使得这里的降雨蒸发量较小。若尔盖河曲发育,湖泊众多,高原中部地势低平的地区排水十分不畅,地表经常处于过湿状态。黄河之水,“随身”携裹着来自青藏高原冰川和湖沼的泥沙以及营养物质,在若尔盖开始了第一轮的大规模沉降堆积,滋养着这片独特而宽广的草原,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
若尔盖湿地面积30 万公顷,其中泥炭厚度达30 厘米以上的面积就有28 万公顷。泥炭层一般2至3米,最厚可达10米,泥炭储量22亿吨,占全国泥炭总储量的23%以上,是全国最大的泥炭矿区。
泥炭由植物残体、腐殖质和矿物质组成,是植物残体在无氧的环境下沉积而来。即使盛夏,若尔盖夜晚的气温,常常徘徊在零度左右,几万年来生长又死去的水草,在寒冷湿地腐烂的速度,变得缓慢而郑重,一层一层堆积,让泥一样的黑色物质,成为草地有机物的宝库,积淀了太多时光漫长的秘密。
泥炭的积累和分布,与气候地貌、水文和植被多种因素有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若尔盖是黄河、长江两大河流重要的水源涵养之处,被称为世界上最大最奇特的“固体高原水库”、黄河“蓄水池”“中国水塔”。泥炭沼泽湿地就像一块巨大疏松的海绵,在该收时收,在该舍时舍,雨季积蓄水,干旱时释放水,以最自然和朴实的方式,无怨无悔地调节水量,造福人类。
黄河流经草原,促进泥炭形成,泥炭反哺黄河,又能净化水质,锁住二氧化碳,给黄河上游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它们相辅相生,不可分割,犹如因和果,好似信和念,缘分既生,循环依旧。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古人面对她时,总是充满了瑰丽而浪漫的想象。李白潇洒书写“黄河之水天上来”,王之涣笔下舒展“黄河远上白云间”的意境。滔滔黄河,她到底从哪里来,又流向哪里,在盛唐诗人的奇思妙想中,她是一条打通了天与地、神和人的界限长河,流经之处,绽放了无数令人欣喜的“黄河花朵”。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她的第一道湾,以及这清清黄河之水滋养的丰美草原。
如果我不来若尔盖,见识这“九曲黄河第一湾”,留在我印象中的黄河,还是壶口瀑布雷霆万钧浊浪滔天的景象,抑或抗日歌曲“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中的高亢与豪迈。若尔盖的黄河,颠覆了我过往固有的认知。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她的源头是一股股细微清泉,融汇成河,自西滚滚向东,一路斗折蛇行,到了四川边界,像是轻巧地串了个门子,打个招呼,便又折向西北。在近乎180 度的折返中,在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唐克镇境内,形成了荡气回肠的“黄河九曲第一湾”。如同回眸一笑,黄河“微微一顾”,又转身回到青海,充满了刹那惊喜的仪式感。这是黄河在四川境内唯一的一段,全长174 公里,与黄河5464 公里的长度相比,一百多公里的流域,显得那么短促,但谁也无法忽略“第一湾”的独有魅力。
倘若青海的黄河之源,涓涓细流的稚弱神态就是“豆蔻年华”,到了唐克镇,黄河已有初为新妇之美。唐克镇索格藏寺院的诵经之声朗朗在耳,应和水流韵脚,犹如应和呼吸与心跳,为黄河的到来轻吟浅唱,就在寺院前,黄河与白河两相汇合。登高远眺,白河逶迤直达天际,黄河蜿蜒折北而返,两条河水交融相拥,携手走向西北。
河与河的汇流,水和水的邂逅,像是世间的久别重逢,缘分起落纷呈,是一场浩大的宿命,该遇到的终究会遇到,该牵手的一定会牵手。藏地传说中,若尔盖大草原上流淌的白河,是位美丽姑娘,而黄河是相貌英俊、智勇双全的勇士。他们远远而来,在索格藏寺院庄严的见证下,一见钟情,携手并行,快乐地奔流天涯。
酥油灯的光焰,托起了索格藏寺深情的目光,年复一年注视着白河汇入黄河。黄河在若尔盖如同神龙摆尾,蜿蜒迂回,留下一串大大的“S”形弯道,在地图上恰似《周易》中阴阳太极图的大写意,与藏族本教(卍)和藏传佛教(卐)的“生命轮回”或者“日月轮回”学说,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太极也好,轮回也罢,都是象征着生生不息周而复始,生与死是一个圆满的循环,无所谓从哪里始,也不必在意到哪里终,以苍茫的天地为背景,河水千年不衰不竭。
索格藏寺庙前的黄河,仿佛刚刚褪去了少女的青涩,还未染尘于心,有一点闺阁天真的意趣,迈着不急不缓的步伐,在看似急促的拐弯处,伴随一个轻盈的转身,从容地浮沉进退,河面清澈平缓,不见丝毫欲望和野性,呈现一幅安然恬淡的景象。
河道曲曲折折,河水似乎与前后相隔断,形成了暂时静止的水潭。水中浮游着成百上千只蝌蚪,黑豆般的脑袋,细叶似的小尾,受到人们脚步的惊动,迅速溯游,将水波搅动得碎光片影,翻腾喧嚣。
也许一场夏雨,这一段断道涨水,与前后河段相连,这些蝌蚪会顺着黄河之水,开启生命更深更远的旅程,在散发着水腥气的黑色淤泥中,激情澎湃地演唱日月星辰的赞歌。
生命是黄河永恒歌吟的主题,河床孕育蛙声一片,盛夏就会开启一场场交响乐的晚会。只不过此时此刻,风过芦苇,鸟鸣声声,流水潺潺,仿若温柔的耳语。造物主将这些细碎而绵密的声响吹送进生命的摇篮,也让霞光微暖的温床,接纳散落在悠长河道之中徘徊的万千生灵。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黄河落日,从盛世大唐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在唐克镇山坡的至高处,修筑一座法螺状的观景台,沿着三层高的环形走廊徐徐缓行,都可三百六十度远眺望景。眼前的黄河,如同一条长长的哈达,在碧绿的草地上绵延伸展。
日暮的太阳犹如一个燃烧的火轮高挂天际,山顶的风却已带着凛冽的寒意向人袭来。但同行的没有一个人舍得离去,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缄默不语,以固守的姿态来等待,等待落日余晖,洒向壮阔的草原。
长河落日,比想象中来得更为缓慢,人们隔了许久望向天空,太阳还在原初的位置,不见一丝坠落。但黄河有色彩细微的变化,昭示着时间也如同河水,在一刻不停地平缓流动,并未浪费行经的一分一秒。金红的霞光,慢慢提亮河水的银白,古朴粗拙的光泽,渐渐变成了鲜亮的银色。晚霞像是一双勤劳的手,拂拭轻抹玉带一般的黄河,将它擦得熠熠发亮,光洁如初。
每一次的落日,都像是重复古老的寓言,在太阳即将收走万丈光彩之前,总要拼尽全力去燃烧和绽放。人生往往也是如此,每人都有自己的长路要行走,有自己的责任要承担,到时才恍然醒悟,人的一生还有这么多遗憾,汇成一种自我奋进的信念,骤然爆发难以想象的力道,绽放生命的光彩。
若尔盖的太阳从容大气,它有无数次机会,日复一日地书写晚霞的璀璨,将每一次离去,都上演得惊心动魄,光彩动人。其实每一次的日落,都具有唯一性,因为时间单向流逝,我们无法回头,无法预演,只能睁大眼睛,攥紧拳头把握现在的光景。
悬挂西天的太阳,像是从冗长的沉思中醒了过来,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若尔盖的长河。河水在它的光芒衬托下波光闪烁,霞彩也就来了兴致,决定用更加隆重的仪式,给黄河涂抹上神笔天赋的色彩。太阳是当之无愧的行动派,它毫不犹豫,即刻拿起画笔,一鼓作气,那由金转红的霞彩,从天空的颜料罐中倾倒而下,纷纷扬扬,河床顿时流光溢彩。
银白的长河,就此罩上金红的霞光,如同人间至为贵重的黄金红玉跌进粼粼波纹里,搅荡和融化,生就了一匹华丽锦缎。太阳还在天空原先的位置,就像被一枚巨大的图钉,固定在天幕上,以王者的威严,驱走了遮挡光芒的云层,将人间的黄昏擦得明亮如新。
中外科学家称黄河九曲第一湾为“宇宙中的庄严幻景”。倘若不见落日,就不知天空的庄严,水中的幻影,彼此可交可换,或又互相成就。不料太阳为自己确定了时间,它不再延宕,潇洒地纵身一跃,心甘情愿地扑入河水,像是水下点燃的火柴,河床漾起了烈烈火焰,化作凝重而辉煌的叹息。黄河张开了温暖的怀抱,容纳了它的躁动和光明,热情与壮丽。
若尔盖的晚霞没有愁情别绪,离恨牵念,在尽兴时潇洒放手,在恣意时毅然离去。
红日西落,天幕最后一缕光芒,还在河谷荡漾。大地沉默了,黄河也沉默了。经幡猎猎,山顶的冷风踉跄地扑将过来,撞得人们满怀生凉。人群被落日的决绝所震撼,又像是不解一条长河,如何让王者的太阳也能臣服,心无旁骛地飘落到平缓流淌的河水,化为沧海桑田的青黄变迁。
黄河奔流前行,与她相伴相依的,是勃勃生机的草原。草原用坚实的力量,托举起了青涩而秀丽的黄河,他们在天地之间相拥交缠,共同书写了一曲生命之歌。
久居城市的人,初次见到若尔盖草原,心里会滚过一阵强烈的震撼。数之不尽的草,织成一张绿色的草毯,在目之所及处,尽情地向天边延伸舒展。
世上美好的东西,多半和“醉”有关。若尔盖草原铺天盖地的新绿,让人心生“醉草”之念。柔弱的草,连成了片,织成了无边无际的绿色绸缎。微风拂过,草浪起伏,这一刻令人顿生疑惑,是身在草的大海,还是无垠原野?近处绿草茵茵,远处山峦叠黛,草原以庄严的深沉,担负了辽阔地域生灵繁衍的万钧重担。
没有尽头的草原,让人荡尽心魄俗念。心灵的闸门既开,思维就会四方奔驰,青春热烈也好,豪情万丈也罢,人已尽得自在之妙。仰望天空,蓝天白云如絮如棉,似千军万马奔袭而来;而漫无边际的草原,弥漫着花草香气,清淡悠远。
若尔盖的热尔大草原,纵横数十公里,浩原沃野,广袤无垠。热尔大坝在藏语里意为“神仙居住的地方”,只有亲眼见过她的人,才会懂得这里为何会赢得神仙的青睐。坝里的大海子,俗称“花湖”,水中湖畔生长茂密水草。这些水草夏季开花,一团团、一簇簇,犹如满天繁星,四下散落,草原湿地就是夏季的华丽盛宴。
草原花开,到处都流淌着生命的欢悦。黄花水毛茛密密麻麻连成一片,在沼泽中揽镜自照,倒映倩影流连;溪木贼纤身如细竹,节节蕴藏生机,青翠欲滴;蓝翠雀花颜色深紫,形如伞状,微风摇曳蝴蝶栖停;红花绿绒蒿枝干如箭矢挺立,犹如身着华服的新娘,不胜娇羞低头垂眸;雅江报春淡红浅紫,随心所欲地飘散于湿地沼泽,或缓坡草丛。河谷也好,草地也罢,就是高山雏菊、蒲公英、羊羔花、紫丁杜鹃等各色野花,都能在这片土地绽放自己的光彩。
野花遍地,并非都是名贵品种,也就少了一分骄狂。每一朵花,都是一个怒放的生命,在阳光下昂头挺胸,在月色中抖落轻寒,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凭靠自己的力量,无拘无束地点缀这片草原。
一季荣一季枯,是草更改不了的宿命,无论它多么眷恋这片美丽的湿地,终究逆抗不了时间无情的征伐。它在寒冬的风雪季节,许下郑重的心愿,用自己的牺牲化为成全,滋养后代子孙。
牺牲是悲壮的,却也铭刻着坚强的印迹,让稚嫩的新草,不必害怕草原变化莫测的天气,不必害怕生死的轮回,也不必害怕生而为草的卑微。一株枯草历经风霜,为后来者竖起一个坚强的屏障,一道无言的丰碑。
草原的枯黄和新绿共存,有的化为沼泽泥炭,有的茁壮成长。在这片看不到边际的草原上,到底曾生养过多少生命,又奏响过多少离歌呢?
岁岁年年,枯荣交替,草原却总能返青归来,从不让人失望。
在草原最美的花期来访,花湖给予了我们莫大欣喜。行走于木头栈道,两旁是连绵无尽的草地,有旱地也有沼泽,继续走下去,能看到清澈如碧的海子,云彩与群山的倒映。湖面上游荡的黑颈鹤、野鸭、苍鹭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水鸟,为这片水域增加了生气。天与水相接,与草相连,它们无缝无隙地合成一片,人在其间,自身有多渺小,碧草蓝天就有多开阔。
“踏花归去马蹄香”,牧民打着响鞭而来,一匹马身后跟着一群马,四蹄没入青草,又速疾弹跃而起。行走不如奔跑,奔跑不如跳跃,群马奔过,牧民的歌声和马蹄上的花草,随即散落天涯,成为草原的芬芳。
草原并不总是“岁月静好”,唐人鲍溶曾写“西风应时筋角坚,承露牧马水草冷。可怜黄河九曲尽,毡馆牢落胡无影。”他眼中的茫茫草原,何其苍凉冷硬。壮美的草原,却也拷问着人们的生存意志,隐藏着看不见的危机。
茫茫草原像是命运未知的走向,充满了叵测和随机。夏季的草原一会儿艳阳高照,一会儿乌云密布,一会儿雷雨交加。太阳还来不及躲进云层,闪电已伴随响雷而来,天空成为一张孱弱的纸,被无情撕开,亮光映照天际,闪电成为一柄利剑,切开密云,轰然爆出火球,震人心魄。
草原上的早晚温差,让人体察它极端的热情和冷漠。中午阳光强烈,人畜一身晶莹细汗;清晨和夜晚,草尖结着一层薄薄霜花。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酷暑严寒,草原从来不闻悲鸣呻吟,人们在和自然相处中,雷霆雨露,风和日丽,都将生死悲欢,隐忍成一种恒久生存的力量。
草原的感性之中永远藏着理性,情浓之时也有克制。这里的人们保持内心的宁静淡定,既要敬畏万物,又能战天斗地,使源自人类的本能,符合生活的习惯,形成了若尔盖族群部落的文化。
牧民曾经逐水草而居,迁徙搬家,居无定所,正如藏谚所云:农者木门内居,牧者帐篷里住。雪山顶上白雪皑皑,湖沼河流平如明镜,清凉水中鱼儿畅游,天鹅大雁流连岸畔,只要水草丰茂之地,都是牧民繁衍生息安居乐业的家园。这种生活方式成为人们一种长久的历史实践,有了与之相应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追求。在由人畜和自然构成的生态系统中,牧民驱赶着牛羊适应草荣草枯,水涨水落,又在自然的氛围中,加深了敬畏和自由的生存理念。
行走的牧民将脚印散落在故乡的版图上,将孤独的影子映在清澈溪流中,更让“团结”成为一种可能性。部落是草原上若干单独行事的人,自觉与不自觉地组合而成的温暖集体。风雪突袭,部落族人共抗天险,遭逢强敌,部落男儿挺身杀敌。
部落的形成,是人对自然的适应,也是一种反抗,并非古而有之。在渺无人烟的荒野之地,一些牧民赶着牛羊迢迢而来,聚群而居,互帮互助,逐渐生成了共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草原部落文化从诞生之初,便有着一种深刻的生态内涵和强烈的艺术气质。
德高望重者可以成为部落首领,负责部落的精神和世俗的管理。草原无边无际,牧人可以随意而居,但山川河流,皆可成为部落之间的界限。界限之内部落掌控的草山、草坡、草地都有明确划分,一般数户或数十户牧民聚群而居,组成一个群体,称为“菇廓尔”,其负责人称为“菇本”,负责组织春夏秋冬替换时游牧点的搬迁移动,以及菇廓尔内部婚丧嫁娶。“菇廓尔”和“菇本”的存在,让部落与部落之间有了清晰的定位,这是草原上的温暖集体,集腋成裘,五指握拳。
游牧的若尔盖人倘若不形成部落,他们就如同一粒粒散落在大地之上的微尘,也许一阵风过,便拂之于无形,而如今微尘相拥相裹,汇聚成团,叠加了很多人的力,共筑一道生活的屏障。
草原部落有着明确的名称,他们的信仰和习俗,成为部落的精神象征,在追求生存的基础上,部落子民无师自通地去探求精神之光。考古队曾在若尔盖草原沙化地带出土了陶片、细石器、羊颌骨等遗物,表明远在5000年前,若尔盖的先民已经在沙化地带边缘的斜坡上聚集居住,这些物质的载体,正是先民精神的依傍。这里也曾雷鸣电闪,也曾风雨交加,个人的力量难以与雄阔的大自然抗衡,唯有你帮我助,聚迁一致。这些生活习俗相同的人,以游牧的方式,在草原大地建立一个不再颠沛流离的家园。
如果说“聚合”闪烁着一种物质的烙印,从这种形式与制度下脱胎而来的文化,便天然具有和别处文化相异的特性。它是“游移的相聚”,像天上的云朵,水中的涟漪,每一次的聚合都具有崭新的意义,却又沿循了传统的道路。
若尔盖人常年生活在草原上,牛羊迁徙,牧歌飘荡,以行走丈量着生命的长度,游牧文化便成为部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游牧有着“恣行天涯”的浪漫情怀,更多的是为生存的现实考虑。部落文化深刻影响着这片土地,时光浩浩荡荡,风云聚聚散散,走过了漫长岁月变迁的若尔盖,其地名的由来,充满了传奇和遐想。
若尔盖系“若嘎”的近音,“若”是犏牛之意,“嘎”是指喜爱,传说很久以前,墨曲、热曲之间有一部落擅长饲养牦牛,谓之“若嘎”部落。此部落的牦牛越养越多,肥壮可人,将之分给十二户牧人分别饲养,十二牧人不负所托,牦牛在他们各自的看护照顾下繁衍生息,队伍壮大。物质的丰盛和富裕,壮大了牧民的发展,每一户都若巨树一般,在沃土上抽枝生叶,逐渐成为若尔盖十二部落。“牦牛喜爱的地方”,是若尔盖直白而通俗的解释,牦牛的皮毛,将草原辽阔的版图挂在历史的天空,成为从往昔到现在鲜明的印迹。
若尔盖的得名也许和人名有关,寄托了草原子民对“完美人格”的崇敬与向往。贝多芬曾热情洋溢地说:“在全人类之中,凡是坚强、正直、勇敢、仁慈的人,都是英雄。”第四十代吐蕃王赤祖德赞时期,派大臣噶·益西达吉到多麦地区收取税赋,大臣后裔名叫“若巴·更登”的,深受民众爱戴,他去世后,所在部落将其姓名“若巴·更登”简称“若盖”,汉译为“若尔盖”。这位若巴大人当年到底有何丰功伟绩,惠民之策,如今已不可查证,唯独他能“名垂青史”,让当地百姓世代传颂,他的名字也成就了若尔盖的地方之名。
或许一座寺院,一段叛乱与平乱的史实,一场刀戈铿锵的纷争,一种渴慕和平的热望,也能找寻若尔盖的来历。清朝雍正年间,四川提督岳钟琪因平定青海罗卜藏旦津叛乱,由松潘出黄胜关,招抚草地、班佑等十二部落。同年,清廷分别授予土千户、土百户,其中有“上作尔革”寨。民国时期,境内建有“作尔革寺”,后音译为“若尔盖”。身为基层百姓,最大的幸福,便是“吃上一口安乐茶饭”,叛乱、战争、厮杀,都和血腥气息丝丝相连,和生离死别如影随形,是百姓拒之不迭的噩梦。清兵平乱,部落得以安定,人民得以乐业,从此化为地名,传承后人。
若尔盖名字的来历出处迥异各有不同,但细究下去,都与“部落”和“族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人活着不能缺少空气和水,部落也是如此必要的存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草原游牧族人出于现实的考虑,生存的需要,实行部落制,它既是自治单位又是军事单位。部落看似庞大松散,内里又有一股强大而向心的凝聚力,这种力不仅保障着牧人的生存,也强化了他们人格的认知和灵魂的归宿。
草原牧民一年四季放牧牲畜,部落是必不可少的依傍,他们的生活经验代代相传,与自然的调谐和抗争,融合与适应,诞生了智慧之花,又结出了文化之果,若尔盖的部落文化,距今已传承两千余年。
《管子》曰:“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若尔盖的藏族部落的生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成为浓厚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的一种复合性文化。它是中华文化极具特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诞生那日起,便有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它并非生成以来一成不变,而是在与其他文化相互激荡,吸纳和统一,使之永葆活力,不断发展。
部落文化以柔韧的方式传承着先辈的精神,草原上时常飘荡悠长深情的《格萨尔王传》的歌声。
若尔盖的藏民对草原上的花,都称为格桑花,就像草原上美丽善良的女子,他们都称为卓玛。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或粉或紫的“八瓣波斯菊”,才是正宗的格桑花,原来,扎根草原,不畏恶劣气候,生命力极其顽强的野花,都可以称为格桑花。这样的解释,让我略为懂得了草原人民为何如此钟情传唱《格萨尔王》。人们在传唱古老歌谣时,心中映现的是英雄豪情。这首古曲的代代传唱,演绎了很多版本,具有动态的变化历程。
充满了英雄主义的草原,摔打着人的意志,让接踵而来的磨砺,使人无从退让和逃避。真正的英雄,一定是面对挑战,还能握紧手中的刀枪,立于天地之间,以风云不改的淡定,迎受命运的一次又一次洗礼。
格萨尔王和草原的部落之战,冲突的结果不是一个部落彻底消灭另一个部落,而是将“部落们”的文化叠加在一起,融汇成新的部落文化。文化的包容,象征着草原对待万物的态度,它给予了平等生存的机会,即便不够完美,却从粗粝中优胜劣汰,绽放出自由的花朵。
草原牧民激荡的歌声,源于对草原深切的眷恋和热爱。人们倾注心血和热情来爱这片土地,因为它不仅以丰富物质供养着草原上的子民,还以精神的食粮,养育出了族群独特的文明。这文明是如此宽宏深博,不仅有胜者的长剑,也容下了败者的哀歌。
草原的英雄情结和部落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最具古老传统的地域文化之一,如同长河滔滔,漫展徐行,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连成不可分割的一体。
黄河在若尔盖草原画下的一道道弧线,犹如藏文字的笔画,曲曲折折,潇洒流丽。她把来自青藏高原的冰川和湖沼的丰沛水源,最终纳入自己的怀抱,成为了上自世界屋脊、下至浩瀚汪洋的万里长河。
黄河在四川行经的途径并不长,流域面积占全流域的2.4%,短短一场“遇见”,值得珍惜和回味,它贡献了黄河干流枯水期40% 的水量、丰水期26% 的水量。流经若尔盖的黄河,因无私而博大,因情深而缱绻,她就是一首缠绵悠长的牧歌,在茫茫草原中平仄回荡,环环相连,分割出无数的河洲与小岛,孕育了深厚的黄河文明。
古代记载“四渎唯宗”“百水之首”,说的便是黄河。《汉书·沟洫志》:“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赋予了黄河崇高的地位。千百年来,黄河养育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以奔流到海的执着,见证了华夏民族历史的变迁。深远厚重的黄河历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国人将黄河称为“母亲河”,噙着一腔深情,怀着一片赤心,从古至今,莫不更改。
一滴水能折射太阳,从黄河往昔的蛛丝马迹中,同样能窥见祖先生活的状态。考古学家早在黄河区域发现了斑驳印迹,我们的先民早期主要活动地域就在黄河沿岸。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华夏始祖伏羲帝和炎黄帝的传说也诞生于此,筑就了华夏儿女根深蒂固的根亲观念。黄帝部落被誉为是华夏文明的第一块基石,早期的黄帝部落是一个游牧部落,依河流水草四处漂泊,随着黄帝与其他部落大大小小的战争中获胜,《史记·五帝本纪》中称:“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凡五十二战,天下大服。”黄帝部落由此发展为中国大地上最强大的部落,成为早期中华民族的主体。
黄河护佑了黄帝,黄帝擦亮了黄河的光芒。树高千尺,难忘沃土之中的根脉,黄河便是这坚固无比的树根,顽强地伸展,努力地掘进,直至破土发芽,长出了茂枝密叶,开出了繁花馥郁。无论中国人走到哪里,一句“黄河的子孙”,都让我们找到了历史的认同和依归,找到了血液中遗传或相似的DNA。
黄河让流动的游子不再彷徨和离散,她用自己不竭的流水,繁衍世代子孙,也延续了古老中国的文明史。早在六千多年前,先民在黄河流域尝试种植粟、黍等旱地作物。黄河周边农业的发展和壮大,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为中国往后走向文明社会奠定了初步且必要的基础。
进入文明版图以后,夏商周三代王朝国家,乃至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的国都,几乎都建立在黄河流域,黄河文明成为那些时代的最高文明。这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象征,黄河被历史所簇拥,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演绎着朝代更迭的悲欢,无论风云如何聚散,成王败寇的故事如何流转,黄河始终是聚光灯下抢眼的主角。
中华文明以一颗谦逊之心,传承着黄河文明的精粹,并凝聚融合成大一统的国家。
是聚与散,合与分,包容与征伐,还是接纳和抗争,黄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交汇交融,也是中原文化同草原文化相互交流交锋之地。沿着漫漫河道,这片热土有过争议和干戈,抢夺与复仇,热血和悲情,但从古至今,中华儿女走向统一融合的愿望一直未变。华夏大地出现过多次的分裂和对抗,最终都趋于统一,中华文明也得以绵延不断。
若尔盖的藏语称“河”为“曲”。俗语说:天下黄河九曲十八湾。藏族人民结合黄河上游的地形、景观等,以神来之笔,为上游河段取了许多具有特色的名称。如此多的“曲”融汇交织,也许有的是远道而来,欣喜赴约,有的是针锋相对,但不管是相拥还是相吞,是一场爱恋还是拼斗,终究浩浩汤汤,化零为整,聚为养护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见证了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正是这些热烈的对抗与融合,所有的干戈,终究化为玉帛;曾经的杀伐,换来和平盛世。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论出现多少磨难,始终不改初心和方向。黄河文化的形成,不是孤立避世,容纳吸收了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精髓。它还以其博大胸怀,学习和吸收域外文化,把自己的文明推向世界。
若尔盖草原的九曲黄河第一湾,如玉带光影伸向远方,让人类明白世上所有的弯道,不是为了隔阻和避逃,而是为了向前发展而产生。黄河文化的传递与承续,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它有艰难的开始,有纷争的过程,才能万流归一,汇入浩瀚大海。原来世间的弯道和阻隔并不可怕,怕的是失去远方目标的感召,失去心底那份虔诚的人文情怀。
“万涓成水汇大川,千转百回出险滩;滔滔长流济斯民,力发黄河第一湾”。若尔盖草原上静静流淌的黄河,水流清澈见底,水面澄明如镜,倒映碧空白云朵朵。她所流经的草原,辽阔圣洁,令人愉悦安然。
太阳缓缓滑落地平线,牛马羊群,在草原立成一尊尊雕塑,在河边变作一枚枚深色的剪影。草木摇曳,飞鸟低吟,黄河与草原,共同绘就了一幅幽远的画面。
若尔盖草原延宕河水的浩荡,绵延成黄河长江的滚滚浪花,从历史走到了现在,从原始的部落文化融入到璀璨耀眼的中华文明。这块镶嵌在川西北瑰丽的绿色宝石,代代流传,世世相承,无论何时,人们都能找到心灵的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