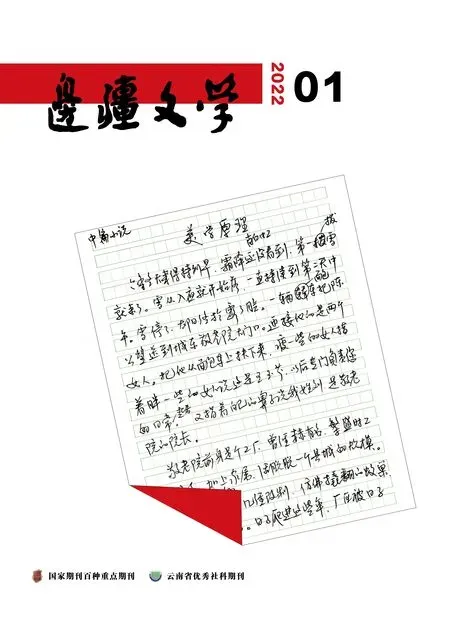异物 短篇小说
八道
每次她看到这面墙就觉得亲切又别扭,而别扭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因为一开始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别扭,谁又会去深究说不明道不清的一闪而过的异样感受呢?对于似曾相识的,总是不知不觉地天然似的令人感到放松和乐于亲近。实际上是有迹可循的。四扇残破的窗框贴挂在灰扑扑的斑驳的墙上随时要飞走的样子,令她想起小时候趴在小石板铺就的窗台上仰着头看《小龙人》的村口那家小店里美味的橘子水和甜蜜的糖果,好像那记忆中的滋味在看到这面墙的时候又回到她的口腔里。还有被大人反复提起的她命大的例子,小时候的记忆是靠不断的重复提及而印象深刻的。每提及一次她就被迫回想一次自己当时唯一的感受——那个滑溜的桃核随着抽泣声一起被喉管吞没,小耳朵里刹那只听得见血液的声音轰隆轰隆地在滚滚奔袭,一个无限延长的时间停留在耳朵里,周遭的一切消失殆尽,老旧的电视机里飞出雪山的白,铺天盖地的白色倏忽温吞而紧密地包裹着她,令她喘不过气来。有时候,危险只在刹那间发生。有时候,危险转眼解除。她还来不及做出挣扎,一个路人发现了她的异样,并救了她。而她,那个小小的女孩,继续踮着脚昂着小脑袋扒着窗台盯着电视里哭泣的小龙人继续陪着抽泣,全然不知自己已经和死神一起待了那么一段时间。很多年后,她妈妈告诉她,那个救她的人死了。她想了很久想不起那救命恩人的脸,或者他别的什么形象,有个模模糊糊的影子,说不清楚,那双强而有力的胳膊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回想起来清楚地记得的只有当时那窒息的白色和血液汹涌的奔袭声,还有胸廓下被瞬间箍紧,然后喉管像打开瓶塞般涌入生硬莽撞的空气引起的轻微撕裂的疼痛,刺激得咳嗽了一小会。这种瞬间解决的危机远不及那会儿小龙人找不着妈妈的悲伤给她的感触深。年幼的她一联想到如果妈妈离开她,捂着脖子跟着小龙人哭得更加厉害。
由别人的事情假想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是最常有不过的事情。小谷说蒋萌没有同情心。蒋萌对新闻不甚关注。对小谷说的那些新闻无感。小谷说自己看不得别人过得惨,特别是孩子。这世上悲惨的事情太多,真同情不过来。蒋萌想。小谷生不出孩子,为此跑遍了省内外各大医院,折腾了各种手段,孩子还是没有生出来,最后落得割掉两侧输卵管,各种激素导致身材臃肿肥胖,身体各种疼痛。医生说她35 岁的身体机能已是六七十岁老人的状态,小谷说自己是隐性残疾人。丈夫的出轨,令她再也不愿坚持自己都看不到光的婚姻生活。离婚。净身出户。短短半个月,身高165 厘米的她体重145 斤瘦至100 斤,憔悴得脱了形。明明七年的生活一直悲惨,却在离婚后以肉眼可见的方式为旁人看见她的痛苦。小谷说自己并不痛苦,她是松了一口气的,身体也漏气娃娃般迅速干瘪下去。小谷的事比新闻真实可感得多。在她看来,小谷是看着别人的悲惨哭自己的痛。小谷说起她的过往轻描淡写,内容却总是惊心动魄。不敢让父母担心,不想麻烦别人,所以,一个人进出医院,那么多次的保胎、流产、大出血。她无法想象小谷经历时的感受。只知道自己生产时疼痛和莫名呕吐的无助,还有牲口一样躺在待产室和手术台时任人宰割的失控感,令人有多么不安。在迎接光明和圣灵的大通铺一样的待产室,一张张病床之间没有一点遮拦。下体裸露在空气中,羞耻令她稍得喘息便不停地拉扯白被盖住下身。而医生却时不时地隔一段时间过来掀开薄被,让她屈膝,将手伸进体内摸索,探察宫口开到几指,并告诉她不要再盖上这条给她唯一安全感的薄被。疼痛和呕吐令她无力维护和探究为什么自己不能为羞耻做一点屏障,只得揪着被角捂住脖子,不知该忍住喉咙里的异物不往外冒还是应该干脆地呕吐,像一条缺氧的鱼开合着沾着污物的嘴巴喘着粗气咽口水。每一次体内的搅动,都让她呕吐得更厉害。她逐渐明白,原来疼痛会引起呕吐。
那一个夜晚加一个白天的时间,蒋萌说不清楚时间是否漫长,那是时空凝滞,感官超敏的空间感,蒋萌的回忆里只有疼痛、呕吐,还有始终模糊着脸的医生红绿灯般的话语:深呼吸……用劲……必须侧切……我说用劲的时候用劲……再生不出来,两个都会有危险——疼痛使思维和行动不能很好地配合。蒋萌没有像隔壁床的女人一样骂天骂地,骂丈夫不心疼她,骂婆婆逼她顺产……那时候她多羡慕这位浑身充满力量的悍妇。执行医生的指令已经令她精疲力竭。蒋萌不是被逼顺产的,她是自愿的。她天然地觉得应该为了孩子的更健康、更聪慧而选择顺产。用拉大便的劲——有时候一句话就像一把钥匙一扇门,打开了另一种局面。在力气快要耗尽,恐惧和慌乱到崩溃边缘的时候,她终于用劲得当,用拉大便的劲生出自己的孩子。医生轻轻地对她说了一句:每个妈妈都很伟大。听到这句,一直没有落泪的蒋萌瞬间决堤,泪水攻陷了她的眼眶。也许是喜极而泣。她有了自己的孩子。看着初生的婴儿,她感觉身上有一层厚茧脱落,内里某种不知名的东西似乎变得更加坚韧。她被自己感动了。
那些清宫时手术刀在阴道内操作的刮凌感,麻醉过后的发冷打颤,人们奔走相告喜讯,因为安全完成生产而显得轻松平常不被关注的失落反差,每次想起生产那条件反射般出现的生理性疼痛,那些无比清晰地在身体和精神上重复播放的痛感、情绪,令她心有余悸,久久不能消除……蒋萌想,这是正常安全生育的普通女人并不特别的经历。软弱得一塌糊涂的情绪被她重新用一层又一层的各种鸡汤理论的厚茧包裹起来,极少碰触。
由此共情,蒋萌心疼小谷。感同身受。
这家咖啡馆是老房子改造的。在一条绿得异色的河流岸旁,一棵棵婆娑招展的杨柳树下,斑驳的墙体老旧、隐蔽,浑融在一条街的尽头。附近一溜明堂敞亮的商店,它属于它们的背景色,和后面老旧的居民区和谐统一,在这条街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了令人视而不见的地步。大芝曾经在距离店门口三米不到的路边来回徘徊着找寻“Miss 花先生咖啡馆”,怎么也找不到。直到蒋萌关掉手机,将脑袋探出窗外招呼她。
在春季,一切充满蓬勃生机,爬虫拼命繁殖,没日没夜地嘶叫。墙上的爬山虎太能爬,爬遍了整幢房子,有向屋顶开进的趋势。过于繁茂并不会令人愉快,适当的修剪是必须的。它被斩断了根,一劳永逸。
招牌有点小,坑坑洼洼外皮破损的门楣上方钉个钉子挂上一块刻有朱砂色字样的原色木板块,和小店的木门融为一体。在冬季已经过去绿意刚刚探头探脑的时候,死去的爬山虎赤裸着暗褐色根茎错综复杂地盘踞在原来白色的现在老旧斑驳的外墙上,爬满了整个门面,随意杂乱。一些字牌随意地贴在外墙上:这家店很棒!咖啡的苦与甜,完全在于喝的人。听会儿音乐吧!发会儿呆吧!今天好吗?你是谁……这些木牌和小店竟然如出一辙,纯天然木板片,周围的树皮也被完好地保留着。每次推开这扇破门,它吱呀作响的动静都令她很不自在地硬了硬喉管艰难地吞咽一下口水以缓解这别扭劲,她不知道自己在别扭什么,她不曾留意过自己这些不易察觉的细微的习惯问题,直到那个人的离开,他说他受不了她的喉管总是这样神经质地上下滑动。原先被他视作神秘迷人的性暗示成为神经质的滑动,令她窘迫得无所适从,她才想到,也许是被那颗桃核堵塞得不能呼吸的潜意识里的害怕的应激行为。
他受不了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蒋萌努力检讨自己,非常认同他指出自己的缺点,想要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什么是更好的自己?她经常迷惑。迷惑的东西太多,她无力探究,只能不去想那么多。珍惜眼前人,珍惜当下。而当下和眼前人是否值得珍惜?蒋萌下意识不去想,唯恐被吞噬掉神志,把生活搞得七零八碎,叫人笑话。可笑话终究以嘲讽的姿态在等着她。那些他一开始觉得的神秘魅惑,了解后的可爱迷人,到厌烦后的视若无睹甚至嫌弃恶心……人的每一个阶段表现出来的情绪行为变化的奥秘是心理学和哲学、社会关系学等太空学科喜欢讨论的命题。她不敢深想。她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他说她做得越讨好,他觉得越窒息。他原以为她会先离开。
她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原来他在逼她先
离开,而她没有离开是在逼他做恶人。终于,她停下追逐“更好的自己”的脚步,开始深深地自省,开始原谅自己。原来,她成了《苦月亮》中的咪咪,无底限地迁就,无自我而不自知。理智告诉她,她应该感谢他的离开,但她抱着孩子感到深深歉疚,她迷惘所有这一切,她痛恨他的不负责任。他是奥斯卡也是乔。
那扇木门,摇摇欲坠,像个残疾干瘪勉强站立的瘦子,轻轻一推,吱呀作响,进出时总有一闪而过的不快,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音乐和咖啡的香味可以瞬间抚平她。进门后咖啡的醇苦和木制装潢的气味令人进入一种幽静慵懒的空间,店里播放着法文歌曲《La vie en rose》(玫瑰人生)。尼采说过,上帝独独只把天使的语言留给了法国人。爱语呢哝,慵懒散调,她不了解法国的任何,却在这类香颂中为之迷醉。蒋萌很后悔去查阅那些歌的意义,一看到歌词释义,就被定义了某些情绪范围。她喜欢听不懂的歌曲,这样同一首曲调在不同的情绪中会有着不同的陪伴效果,而不仅仅限于歌词表达的意义。
Des yeux qui font baisser les miens
Un rire qui se perd sur sa bouche
Voilà le portrait sans retouche
De l'homme auquel j'appartiens
那双眼使我低下双眼
那笑容在嘴边漾开
那就是一幅没有雕琢的画
属于那个我所属于的男人
Quand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
Il me dit des mots d'amour
Des mots de tous les jours
Et ca me fait quelque chose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oe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
C'est lui pour moi
Moi pour lui dans la vie
Il me l'a dit,l'a juré
Pour la vie
当他的眼神捕捉到我
他很低声地说着话
我看见了玫瑰样的人生
他和我说着那些爱的话语
那些每天都会有的话
这对我很是触动
他走进了我的心
那部分的快乐
我知道它的原因
他为我而存
我为他而在,我们的人生中
他告诉我,他发誓
以生命
Et dès que je l'aperCois
Alors je sens en moi
Mon coeur qui bat
Des nuits d'amour plus finir
Un grand bonheur qui prend sa place
Des ennuis,des chagrins s'effacent
Heureux,heureux en mourir
当我一想到这些
我便感觉到
我的心在跳动
夜晚不再结束
一种莫大的快乐占据了它的位置
烦恼、忧伤都消散了
幸福啊,死去也是幸福的
右侧长长的吧台前摆放着四五把高脚椅子对面有个大屏幕,夜以继日不停地播放着理查德·林克莱特著名的《爱在》三部曲,有字幕,却从来不打开声音。这里只播香颂乐曲或者其他一些治愈的轻音乐。她太喜欢那个导演说的:“我要能把我现在的感觉捕捉保留下来就好了,而不是只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它……”“谁也不知道我们怎样在彼此的生命中交织回荡出声响,但她是这回荡声响的灵感……”蒋萌觉得自己发朋友圈的意义与此义契合。现在,人人都在导演着自己在互联网社交上的人生大片。
那天,他突然出现在这间咖啡馆,对她说:我终于找到你了。
她不认识他。
像一阵风将柳条卷起来的不安,底下的水纹荡漾开来。他看起来真诚喜悦又有点慌张。经过一番语无伦次的解释——他是谁——蒋萌才想起来——很久以前(在那时的大概两年前的秋天),在临海紫阳街的一间民宿的花园小院里,涌泉蜜橘、蛋清羊尾、海苔饼,糟羹、黑枣酒……石桌上一股脑铺开,她戴着耳塞就着清寂的月亮下的灯红酒绿,孤单一人,细嚼慢咽。那夜的月冷眼直射,没有半点风花雪月的情绪。她甚至都提不起劲发朋友圈。因为小谷放了她鸽子。在抽烟找不到打火机的档口,一个男人从她后侧点着火弯下腰递过来,靠得有点近,但又不让人觉得冒犯。灰色地带。人与人的关系很奇怪,距离的远近能让感觉生出微妙而莫名的不同情愫。他们互相交换了微信,只是她加了之后随手点了不看他朋友圈的设置。他偶尔有在她发的朋友圈底下点赞,极少。
你怎么找过来的?蒋萌讶异地盯着他。
我关注了你很久。他说了很多,没多久就像熟稔的朋友。
在她不知道的时候,他关注了她很久。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吓她一跳。
蒋萌对信息的隐私从来没有在意过,对互联网的便利,拿来即用。她觉得,诈骗这种事离她太远,骗子也不会骗她这类没钱没色没秘密的普通人。如此这般思绪在她脑海里快速切换闪现,她发现原来自己真的没有任何隐私——开心发个朋友圈,不开心发个朋友圈,聚餐发个朋友圈,一个人看风景发呆也发个朋友圈,连收个快递也发朋友圈,发现个好去处发朋友圈还特地显示位置……这家店她常来,在朋友圈发一些窗外的景色、一瓶水培绿萝,一杯咖啡,一碗意大利面或者五成滤镜的自拍照是常有的事。
蒋萌看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但不可否认,内心有一丝飘荡。阳光从窗外斜落在他们之间,形成一条光道,有飞尘在上面飘游,他站在一侧,脸有些朦胧,半明半暗。静默在此时尤其漫长,他停下来等她反应,蒋萌手指点着脖子不露痕迹地吞咽下一口水,温柔地说:呃,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事不能找你吗?
啊,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她笑了起来。
他在蒋萌对面坐下。窗边飞来一只黑鸟,双眼幽深,支棱着脖子一顿一顿地来回转动,不知道它看出来什么,站了一会就飞走了。飞到岸边的柳树上跳来跳去,它是不安还是雀跃,她看着那只黑鸟忐忑无措。他们交换了手机号码。他说他专门从连都来找她的。他极力营造一种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亲密和宠溺。蒋萌有些羞涩不安但也非常享受这种内心悸动的滋味。一个男人花费心思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她感觉有点恐怖,虚荣却得到满足。她不自觉地不时地缓慢地吞咽着唾液,手指在脖子上来回拨动不存在的异物。
苦难灾祸也可以是人生的财富。熬到别人都死了,你就赢了。瘦下来褪去憔悴恢复灵动的小谷说。
蒋萌喃喃地道:赢不赢的,谁知道呢。
反正我觉得活到老死闭眼的那一刻,才是最划算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嘛,各种景色都应该见见才是。小谷娇嗔道。转头对大芝和于飞说:蒋萌这人故作清冷,实则薄情寡义,别想着哪天她能对我们掏心挖肺的好。
类似的话小谷总说,她很不高兴听到,薄情寡义这词应该还给小谷,她觉得自己对她们已经是掏心挖肺的好,而她却感受不到。调侃多遍,语言是证词。但是应付这些很麻烦,蒋萌索性懒费唇舌。对于自己,她不知道下一刻还是不是这一刻的自己,那么纠缠于别人给她下判词的三言两语,又有什么意义。人们的嘴经常挂在肚脐眼上。没人愿意多费心思去检阅别人的行为和言语背后的缘由。也许有人会说,解释等于诡辩。
轻飘飘吐出的一句言语,有时候,一个人就死了。斯童就是这么死的。老板说:你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要死死远一点。她就去死掉了,偏要死在公司门前,那么高的写字楼跳下来,砸在地上,鸡蛋一样一摊躺在那里。只是蛋心深黑蛋清是暗红色的,令人作呕。人们叹息几句太惨了,继续自己的生活。像农场里的鸡,一阵呆愣过后,继续闲庭信步。
桌子、沙发椅和隔断是一色同材料的船木制成,隔断做成书架顶到一样船木拼接的贴着几张明信片的天花板,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有菜谱、园艺一本通、婚姻幸福秘籍、标着世界名著令人望而生畏的精装书,灰色丝绒沙发紧靠着布满树疙瘩疤痕的书架,泛着诡异却美妙的和谐光感。陈旧、沧桑,适合贮藏故事。她往里走去,经过吧台,朝狭窄逼仄的楼梯走去,墙壁上与外墙一样挂着一些木牌:你是一只爬虫吗?上面很好,你要上来吗?生活是让处女成为女人后才开始的——每次看到这块木牌大芝就给它翻个面,后来,小谷在背面写上:生活是让处男成为男人后才开始糟糕的。于飞大呼:好像怎么说都不对劲。一种是男人的得意,一种是女人的怨愤。大芝赞同于飞,说这是对女人的侮辱。生活随时都在开始。斯童无可奈何,对她说:蒋萌,有没有不偏不倚适用男人和女人的俏皮话呀?大芝一本正经地说:我现在就有一句。然后她夸张地噘着猩红大嘴,双手做喇叭状,轻声又用劲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喊:好——大——啊——一帮女人哄然大笑。天花板上玛丽莲·梦露捂着裙子仰头笑得风情万种。笑声穿着裙子在店里旋转不停,曼妙,娇俏,张扬,招展。
大芝说果然好女怕郎缠,烈女怕闲夫。这人是个老手。你可得留点心,别傻乎乎地把心全交出去。外地人,万一人跑了,你可别哭。虽然现在飞机什么的都很方便,但是成本太高了。于你不利。你的父母、朋友和工作都在这里。
她觉得大芝过虑了。他费这么大心思从连都跑到这里应该是来真的,她一个普通上班族薪水不高,长得又不漂亮,矮小单薄顶多算得上清秀,他图什么骗她?图她的小情小调,图她的按部就班吗?他说看着她就觉得温柔,内心情不自禁地柔软起来,他说她在哪里,哪里就有一束光,她在哪里,哪里便是一处安谧的神境。他说他承认当时是被一支烟给挑逗的好奇心,一个瘦弱文静却会抽烟的女人,有怎样的故事?
蒋萌没有故事,平平淡淡谈过几次恋爱,全部无疾而终。因为她太平淡,宛如一潭死水没有波澜。彼此不合适,是匆匆收场的好说辞。对蒋萌来说,抽烟不过就像吃零食一样的行为而已,为什么人们会赋予它这么多额外的意思?大芝明艳动人,是美剧《欲望都市》里的萨曼莎,对待男女关系是开放的,好聚好散,潇洒自如,对闺蜜们充满保护欲。大芝说:蒋萌,如果哪天你愿意接纳我,也许我们可以成为终身伴侣。我保证比任何男人都让你舒服。她朝她挤眉弄眼,随即哈哈大笑。你别动我。我确定自己喜欢真刀枪。蒋萌淡淡地接道。
他说我很性感。她们翻着白眼。谁也不会在意他一首歌唱给几个人听过。听过了就过了,一定要去听明白,可能就失去了原有的滋味。你好自为之吧。大芝把一句话变了味地调侃着还给蒋萌。蒋萌觉得大芝太不相信爱情了,虽然她也不太相信,但是他带着他的爱情来了,还是宁可信其有吧。蒋萌在心里欢欣鼓舞。
如果克白能这么主动就好了。于飞把散落在鼻尖的及肩黑发捋到耳后夹住,不无遗憾地叹道。她们继续翻着白眼。克白的朋友们都知道克白喜欢于飞,可是克白从来没有私下向于飞表白过,克白在于飞面前是克制温柔的绅士,他表现得好像是于飞已经拒绝了他,可天知道他从来没有表白,何来拒绝。在她们看来,他们两人都一样的别扭,从来都用揶揄的语气谈论在乎的话题,得来的答案模棱两可。明明在意却谁都不愿意先一步明确态度。他们玩味这段关系,各自叹息,又甜蜜又虚幻。
小谷以过来人的身份说:这是最美好的状态。要知道,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可是我想结婚!总不好叫我一个女人主动推倒他吧!于飞不无愤慨地叫道。为什么不能主动推倒他?大芝斜眼吊眉地看着于飞。跟你这荡妇说不清楚!于飞没好气地丢了个白眼给大芝。大芝抓起身后的靠枕扔向于飞,找死!你这个闷骚的小贱人!小谷笑得花枝乱颤地摆手劝架。你俩中和一下就好了。小谷说。
清一色船木板做的原色长方桌子,那坑坑洼洼的孔洞附着了海洋的汹涌和深沉,有些火烧的黑色痕迹,这是为了抵御风浪和岁月侵蚀所付出的危险代价。燃烧需要火候掌控,过猛,烧成灰烬,过于温和做不了防护盾。哪一个节点恰好,谁也说不准。只有不断地尝试,久而久之自会理出一套天成的经验之谈。于飞就是顾虑太多才裹足不前。蒋萌说。外面下着雨,一切清新可人。蒋萌看着她们瞎闹胡打,觉得自己比她们都幸运。
斯童还在的话会更加热闹。蒋萌又说。
笑闹声在空气中凝滞,消散。
于飞叹道: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唇枪舌剑最在行。其实最脆弱。你看她在我们面前一不小心就崩溃痛哭就知道了。我们在外面都是装。你说,谁不在装。
她妈死了,她成了一个孤儿。小谷说。我们总是以为说出来解解闷气就好了。可是问题不是说出来就能解决的。
其实,我们谁不是孤儿呢。大芝说。事情最终不都是靠自己去想办法解决。她撑得太累了,那个节点上来那么一出,也真是……大芝向后瘫倒,丝绒的沙发靠背推着她的腰弹了几下,好像这样能使她松快些。
因为下雨,两扇看起来随时要飞走的窗框被半合上,闭不紧。于飞拽着插销使劲往里拉,它们卡在一个点上,互为犄角,纹丝不动。她站起身来将其中一扇先固定,再扶着另一扇摆弄角度,窗户发出吱呀吱呀的不安之声,仿佛随时它会脱离它应有的位置,落入某人的手中,或者粉身碎骨。
天灾人祸。斯童的父亲死后,母亲也瘫痪在床且患有肺癌。最后的时期,在医院折腾了好几个月。母亲经常戚戚哀哀地看着斯童,又渴求摆脱痛苦又害怕。斯童知道母亲是害怕死后会被别的鬼欺负。她从来胆小懦弱。害怕很多东西,害怕未知,害怕死后的世界……那是个未经风雨的小妇人。父亲死后一直是斯童顶起母亲的天。除了和她们几个吐吐槽,斯童孤立无援,无助又无奈。在母女俩都精疲力竭的时候,她告诉母亲父亲会接来她,才犹疑不定不情不愿地微松了手,不停翕动的眼才终于没有再费力睁开。她没有时间去感受伤心和疲惫。料理完后事就回到公司上班。
真惨。小谷抱着沙发抱枕说,她在医院见缝插针连续熬夜做出来的重要项目被协助的副管顶了。我听她同事说,她找老总理论,说他这样养情妇早晚把公司玩完,说自己要这个项目应得的红利。她妈死了,她欠了一屁股债,红利不给她会死人的,说老总这是在逼死她。于飞忿忿地说:可不就是被逼死的嘛。那个该死的肥猪!大芝无不可地耸耸肩:老总觉得自己已经仁至义尽,不来公司,工资照发,了解进度都找不到她人。我后来帮着处理后事的时候,老总跟我说的。于飞愤愤道:她同事说,当时那死肥猪说斯童跑到他面前这样闹腾起来太有失体统,不知分寸。斯童当时被同事们架着胳膊出来的时候,嘴上还在骂骂咧咧,一副誓不罢休的模样。接着于飞叹道:是的,前台说大家安慰几句陆续都走开了,最后谁也没有留意她什么时候离开的。谁知道没多久大门外“咚”的一声重物砸在地上……
斯童死前在想什么?对这个世界的心力交瘁?也许,她还是放心不下她的母亲。她赶到时,斯童的脑袋被盖上了一件脏兮兮的黑色夹克,血渗透出来,黑得亮着红色的闪光。那么精致干练的一个人,以奇异扭曲跪地投降的姿态向上不雅地瘫展开在干净的水泥地上。不,已经不干净了,上面躺着斯童和从她身上流出的鲜血,她的脑袋上还被盖着一件不属于她的污秽不堪的泛白的黑色夹克。她突发奇想,走过去想帮斯童把腿脚放好,她想,斯童一定不喜欢这个姿势。她痛哭着正要走过去,围观的人群一阵骚动。“警察来了……”不知是谁从后面推挤了一下,她朝着斯童踉跄了几步,脚勾到了夹克。人群中再次骚动起来:啊呀,摔成这样……眼睛睁着的呢……她猛地抬头朝斯童看去,雪白的脸上血迹潦草,双眼圆睁,异常狰狞,凄惨,似怒目,又似望向虚无。她闻到一丝血腥味。她感到喉咙发胀,想要呕吐,眼前有点发黑……瘫软下来时,她想,那时,在干净的水泥地上,坠落,仅有的尘土也许并未高扬。斯童成为人们一时的谈资——一个想不开跳楼的异类。
蒋萌径直穿过狭窄的木梯走上二楼为自己找到专属位置,一个靠窗可以看到斜对面桥的风景的位置。岸边的柳树扭曲着枝干,几点绿粉饰了它的荒芜软弱,使它看来生机勃勃,好像之前落叶的离去使它萧条惆怅的时候不复存在。水泥桥横跨绿意满溢的小河,如果不往下看,只会以为是平坦的道路,哪里有半点桥该有的优美的弧度……人们为了通畅,舍弃了很多,起伏的走势令人费劲,现在谁也不愿费劲。蒋萌就是在这座桥上看到他搂着小谷笑得温柔得流出蜜。她终于在看到那一幕的瞬间明白,爱情永恒不变并没有说得不对。爱情一直在,只是换了人。他搂着小谷流出蜜的温柔笑容直刺入目,闷狠地震击着她的心头,呼吸被长久地遗忘,她动弹不得。脑海里飞速切入关于他和她,她和小谷,他和小谷的曾经的场景、对话和亲密,交织错乱。她想起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起。毫不设防的她和毫不设防的他们;她在楼上,他和小谷在阳光下;被真相击中的她正一个人坐在她们经常小聚的咖啡馆准备约上闺蜜三人,真相中的他们正搂在一起笑得流出蜜来,不知刚知真相的她坐在咖啡馆楼上的窗边正看着他们。各种猜测各种设想层层叠叠向她涌来,阳光落在他们身上,晃眼得疼,她成了暗处的阴影,寒冷、潮湿。她觉得疼。终于拨开云雾解开心头惶惑却被真相淹没的窒息的疼,刮凌感和搅动着的疼也纷至沓来,缺氧的鱼嘴开合着发出艰难断续的呜咽声,她不知道该捂住眼睛,还是嘴巴,还是脖子或者肚子,只得将指甲深深地掐进被海水和烈火熬磨过的斑驳不堪的船木桌。她的眼睛被迫掉在他们身上,她的思绪尾随其后,抬起背叛、欺骗、羞辱的大脚向她的眼珠子践踏了一次又一次。泪是受伤的血,疼痛会引起呕吐。从那以后,蒋萌噩梦连连,反复做着连续剧一样的梦——
左手食指的皮肤下逐渐拱起一个气泡一样绿豆大小的小脓包,她有些奇怪地看着它,因为她并没有感到不适,没有疼痛也没有别的什么感觉,好像在看着另一个人的手指。当她意识到自己没有感觉的那一刻,一丝痒意随着那个气泡的抖动明显起来,好像是意识告诉身体这个时候应该有感觉,所以应有的感觉才配合视觉告诉了她,因为有微微的动静才有了一丝痒意。她疑惑不解,脑袋里闪过一些问题,是被什么咬着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她小心翼翼地用左手食指去挠了挠逐渐变大的小脓包,犹疑着要不要挑破它。一般来说把里面的脓水挤掉就好了,正当她这么想的时候,那个气泡变得凹凸不平,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挣扎,好像要从里面刺破那层薄如蝉翼的包裹着浓浆的透亮的皮,她惊恐地发现旁边出现一模一样的好几个好像马上要爆浆的脓包,它们躁动不已,此起彼伏,而且越来越大,沿着手臂越来越快地向上翻滚,皮肤上的毛孔随着它滚动的到来和离去快速地张开又闭合,她慌乱地想要采取行动,发现双手这时候却动弹不得,只能扭着脑袋歪斜着张得眼白占据了大面积的充满恐怖的眼睛看着它们开始爬上肩膀,越逼越近……恐惧堆积如山压在胸口,她终于在梦中费力地大声喊了出来,好像要用喊声来冲击那些令人恐怖恶心的不知名的东西。
梦醒了。蒋萌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喊出声来,眼睛一睁开,梦境就褪去。只一些可怕的镜头和恐惧的情绪还盘踞心头,蒋萌隐约觉得有许多内容给忘记了。做梦很累人。夜还很长。蒋萌只得继续睡下去,有一片片思绪若隐若现,浮动在迷蒙之中,这个梦隐喻了什么?蒋萌模模糊糊地想着,慢慢地睡意继续笼罩回来。梦境接着继续——
它们开始爬上肩膀,钻进喉咙,喉咙还是涌动不适,她惊恐万状,想要抓着喉咙又害怕,她不知道应该害怕它们破喉咙的皮而出,还是害怕它们从口腔中爬到舌头爬出嘴唇再爬到光天化日之下,清楚地看到它的本来面目。她开始干呕,喉咙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异物,喉管被抓挠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她不停地干呕,脸涨得通红,眼珠子都快被挤出来,眼泪已经被迫溢出眼眶,不停地在脸上划线……很久,随着唾液流出一条细长的蠕动着的有着很多脚的虫子挂在了张开的口腔中间,她崩溃地哭了起来,可是她一哭泣,喉咙起伏一呼一吸。那虫子跟着缩进了嘴里,她干号着,不得不逼自己张着嘴巴继续干呕,而喉管里还更多的虫子在骚动,它们被堵在里面出不来,她知道她必须揪出一半挂在嘴巴里的虫子。她伸手去抓它,它在挣扎,它可能想要出来也可能想要缩回去,它也随时可能出来随时可能就缩回去,她必须当机立断,她伸进食指和大拇指用指腹夹住暴动扭曲的异物,一接触到那异物,它千足虫似的多足部分立即紧紧箍住她的指腹,仿佛马上又要钻进去,她已经惊恐得无以名状,也不敢松开手指,只得快速拽出,并用力甩向脚边,与此同时,喉咙里的异物喷涌而出,像美杜莎满脑袋的蛇长在了她的嘴里,随着她的呕吐不断地掉落在地上。周围一片黑暗,只看到一地密密麻麻蠕动着的异物仿佛又要爬向她,她只剩干号着,是惊恐是无措是软弱,是某种说不清楚的意义的坍塌。
然后梦又醒了。梦境与现实,往复无已。
和往常一样她双手垂在身侧点压柔软的坐垫,坐上去弹了弹她的臀部,然后瘫陷在沙发中发呆。玻璃被死死地嵌在窗框里,窗框的内壁被涂成红色,油漆已经开裂露出了布满荆棘的丛林。黑鸟在玻璃画中的柳树间跳跃并啾啾地叫唤。蒋萌很长时间里一度在保持痛苦,沉浸并品味着痛苦带来的畸恨流转在口中乃至身体的酸苦。蒋萌盯着桥上他们曾经经过的已空无一人的地方,脑子里不由自主地重又闪现——他搂着小谷温柔地笑得流出蜜。那一幕不单坐在这里的时候自动浮现,平常任何的间隙说不定就掠至眼前,越来越频繁地闪现,令蒋萌喉咙发紧,犯呕。有时候她觉得斯童在招呼她,勾引她去与她相陪。蒋萌琢磨着要去看看心理医生。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看见了这一幕,只是回家与他说,自己看见了。现在你可以好好想想是否要离开这个家,若要离开,律师谈吧。
他说自己从来没想过离婚,是误会,没有背叛越轨……
随后的几天,蒋萌觉得自己难堪得比梦中赤裸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还要手足无措。
小谷跟蒋萌道歉,说自己贪恋了一下被宠的感觉,没有做什么,就是平时问问心情好点没有什么的……
大芝说蒋萌,男女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别太较真。想离就离,不离就别抓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不放。也没个捉奸在床的证据,别庸人自扰……
于飞在手机的另一头无语良久,咕哝一句:我一直纠结要怎么跟你说……也许他们真的没什么……
那只黑鸟在叫什么?
笑话……笑话……那只黑鸟在柳树上跳来跳去地叫。蒋萌看到那一幕时才惊觉破绽随处可见,觉得自己洞悉了一切。那一幕好像是一张电影票,打开了整场电影的门。那么,他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小谷在暗处看着她多久?她们在背地里议论了什么?怎样才算背叛越轨?需要做什么才构成有罪?可笑的是她忙着如何更好地做妻子和母亲,心灵鸡汤一碗一碗地麻醉自己。
蒋萌愤恨为什么这种事情当事人被蒙在鼓里最后一个知道?蒋萌问自己,假如早知道又要怎么办?答案蒋萌自然不知道。过去已然发生,假如也没有假如……
蒋萌想再也不见她们。也许可以由大芝在网上代表她全权交涉。始于网络,终于网络。完美的一个剧本。大芝说。做人脸皮要厚。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她可以最后出席自己的离婚仪式,签字,拿证,抱娃走人。
可是,从前车马慢,一辈子只够爱一人。很多时候,人与人的关系修修补补地过一辈子也颇有层次。
窗外阳光依旧明媚,所有的光影一边倒,前面的高楼躺在地上,风吹不去它的灰暗。
蒋萌木愣愣地瘫坐着,等待一杯双份意式浓缩。她没有点单,老板知道她的需要。习惯让他摸透了她在这家店的喜好。对于隐私,她仍然没有设防。她仍然觉得没什么可再失去的。一如那条绿得异色的河,是因为河底看不见的污浊和两岸绿色的映照,只要不发出恶臭,谁也不会太在意。
于飞受到大芝的蛊惑推倒了克白。当她牵引着克白进入她幽闭的私密世界的那一刻起,于飞说,她和克白的天平开始倾斜,开始感觉矮了克白一头,好像她永远应该是更包容、付出和妥协的那一方。说话底气都虚了,好像自己之前的矜持是做作的荡妇在扮演处女。克制矜持和敢爱敢恨到底哪一个更可贵?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她对着窗外的黑鸟又拍了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写着:春夏秋冬,年复一年又一春。咖啡馆。一切如故。她想——一切如故吗?不。并不如故。比如记忆,比如曾经一起在这里的人们,比如一个孩子……阳光明媚,晃得眼睛模糊。咖啡馆里依旧静谧,只是往事太过喧闹。别扭在这时突然强烈起来。她想,她不会再来这里了。
蒋萌正准备起身离开时,老板端上咖啡——双份意式浓缩——没有糖,一杯温水和一份杏仁,他与她之间横有阳光射成的一条光道,里面飞尘浮游。他说:心情好点了吗?
蒋萌突然干呕起来,越呕越厉害,呕得满脸通红,额头青筋暴起,呕得满头大汗,血丝布满双眼,眼泪和口涎直流。紧接着,蒋萌感到自己的喉咙抖动了几下,并发出很奇怪的喉音,蒋萌感到冷,旋即窒息的感觉在她感觉到冷的刹那席卷而来。在黑暗吞没蒋萌的时候,蒋萌脑中回荡着一丝自己迷惘的声音:这是要死了吗?那孩子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