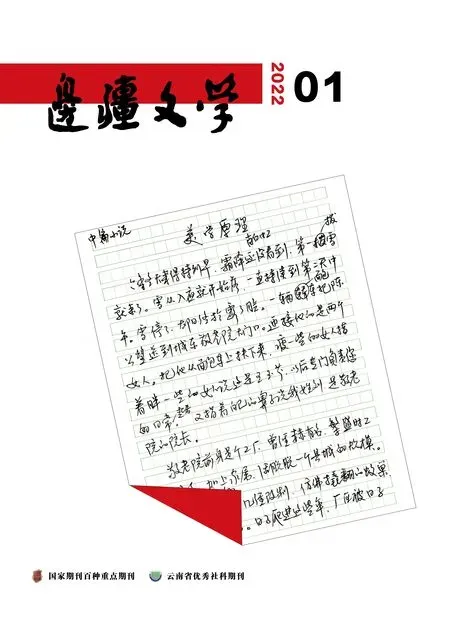稻田里的骑士 短篇小说
肖德林
春龙高考再次落榜,那面目模糊混日子的学校不想去了,在家睡了半年,杨树村人都说他睡傻了。春龙是傻,高考的分数一次比一次低,最后低得不好意思开口告诉人。
初春,他似乎从梦中惊醒,到镇上闲逛了半天,回来对他老子猴子说:我要种高垛的田。
猴子惊掉了下巴。
猴子只是偶尔回家,他的心烦,在脸上挂着。
高垛的田几乎是块废地,春龙撺掇猴子:种水稻。猴子怀疑地看他一眼,村里从来没有在这块地上种过水稻,宁愿它长青草,茂盛的青草,猪子抢着吃。你不是脑子坏了吧?这句话猴子没有舍得说出口。春龙的脑子出生时挤伤了,也把种字、种公式定理的空间挤掉了。猴子对春龙笑了一下,猴子问:你能把这地伺候好?
春龙明白,他老子的意思是你书读不下去,能有耐心伺候土地?更何况那地就是个漏斗,得花多大力气。春龙从他话音里听出来,他已经给这几亩田做了安排。他安排不了春龙的命运,这几亩地的命运,他说了算。他想种山芋,他要养几头猪,猪肉价格,突然坐上了火箭,一飞冲天。他已经预定了山芋苗,那些枝枝蔓蔓碧绿可爱的婴儿巴掌一样的叶子,想想都觉得可爱,何况长着藕节一样红红的山芋,像个秘密似的深藏地下。山芋命贱,根本不要伺候。
春龙不知道的是,他老子内心早就不想种地了,他轻慢着这五亩地。他和人共租了一条船,在长江上跑运输,虽然也辛苦,但是比种田强多了。家里其他的地都租给别人,只有这五亩高地太丑,没有人要,只好烂在手里,猴子从来也没有指望这五亩地,只想小和尚撞钟般地种上山芋。
春龙是那个下午听了种子站歪头的话后,下定了决心。歪头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脖子撑着脑袋,他的脖子撑不住,要用左肩扛着,看人的时候睥睨着眼,半睁半闭,一副权威自得的样子。他有资格的,虽然现在种田是各家的事,但是谁保证稻子麦子不生病,生了病就要到“庄稼医院”去,歪头就是“庄稼医院”的医生。歪头说,他发明了一种稻米,可以增加亩产,而且是无公害,不要打农药,虫子啃稻子,死的是虫子,歪头说,这是生物杀虫。
现在要制种子,一斤算十斤,我们可以签合同。
歪头跟每一个到庄稼医院的人宣传,那些人黝黑油亮的皮肤绽放开来,露出被香烟熏黑的牙齿,友好地笑笑,退后一步,一会就不见了。他们已经上过太多的当,每一次实验,最后受伤的都是他们,他们得躲,除了老实种田,他们告诉自己那些空中飘的好事,别沾,沾了,上当受伤的是自己,在村里还要落个笑话,那些笑话加油添醋,最后,笑话里那个丑陋愚蠢的人根本不是自己,可是向谁去喊冤?
春龙听了歪头的宣传,眯眼不睁的眼睛,透出了光亮,他说我种。
年轻人,不出去打工,在村里种田,不是傻子就是呆子。歪头虚虚看了他一样,又把眼睛闭上,嘴角有个不怀好意的笑纹,这重重伤了春龙的自尊。
春龙感到自己在歪头眼里也是一块废地。他咽咽口水赌气地说:我家有五亩地,种这个正合适。
春龙想,五亩地伺候好了,就是五十亩的收成,这种选择,不做才是傻子。
歪头又看了一眼春龙,很响地清了清嗓子,因为常年吸烟,他的嗓子坏了,总是潜伏着许多脏东西。歪头笑了,好像不怀好意,黑黑的板牙朽木似的:你根本是个屁孩,说话能算数?他们都从土地上逃跑了,只有傻子才会指望那几亩地。歪头激愤地指了指虚无的门外。
春龙隔着庄稼医院的玻璃,他看到自己模糊的身影在上面晃动,他重重地说:你明天到我家去,看地。
春龙回家就到了自家庄稼地里。歪头是个信用不好的人,他宁愿在玻璃柜台后面打瞌睡,他左肩扛着脑袋去春龙家庄稼地已经是半个月以后,这时要插秧了,他说他已经准备好了秧苗。
这半个月,春龙最大的收获是说服了猴子。我为什么没有权力决定家里这五亩废地种啥?我也是家里的一员,你没有权力阻止我热爱水稻!
这是这半月争吵中,春龙说过最多的话。
春龙在河堤上打麻雀,一边等歪头。
河堤上有一些灌木和杂树,不知道是谁栽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们就被会砍了,它们的命运从来没有一个准数,好像和村里哪个人的心情好坏有关,一挥手,它们就倒下了,变成干枯的树枝,等待腐烂。但是现在,它们是麻雀的乐园,春龙必须把它们赶走,它们吃起庄稼来,不吃得饱胀绝不会起身,虽然现在稻子还只是养在歪头嘴上的秧苗,但是春龙不允许它们把这里当乐园,他要改变它们的习惯。他用弹弓,子弹是满地可捡的楝树种子,他不打死麻雀,打树枝、草窠,吓得它们魂飞魄散。
歪头躲在树荫下,已经看了好一会。他对这块土地很满意,虽然土地不是太熟,但没有种过稻子,营养丰富,阳光充足,插上制种的秧苗,必有出人意料的收获。他特别动心的是,这处高地,特立独行,俯视众生,稻子的花粉不易被别的稻子侵染。纯粹,是一个多么好的品质,对于稻子育种,没有比这个更珍贵的了。他对春龙说,种子是一切收获的来源,人人嘴上明白,没几个人知道这背后的辛劳。春龙傻傻地笑了,露出很宽的牙床,不断伸缩着手上的弹弓。他的口袋里已经揣上了三只麻雀,他准备烤麻雀来招待尊贵的客人。
他必须把歪头当贵宾。
牛皮吹了,但春龙对这片荒地如何变成稻田,一筹莫展,他不得不求他老子。猴子知道他要找他,所以躲着他,尽量不和他碰面。猴子在船头忙,他的船即将进入长江,他很希望春龙能够上船帮忙,他对春龙迷恋种稻,心里很着急。他一辈子的梦想,就是永远逃离土地,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儿子,要当个种地的农民,事实上,恰恰相反。他希望儿子在城里安个家,娶个哪怕是郊区的姑娘,他一直为此默默努力,受再多苦,遭再多罪,他都不怕,儿子是他战胜困难的力量。他儿子不太聪明,他付出的努力要比别人多一点,他认命。
猴子不愿意见儿子,其实他很痛苦,儿子再傻是自己生出来的,自己是一切的源头。面对儿子,他不知道说什么,重不得,轻不得。
只有躲着。
他讨厌庄稼医院的歪头,他是儿子发疯的挑唆者。
他远远避开他的背影,其实歪头一进杨树村,他就看到了,他正在生闷气,搬了一袋山芋上船作干粮,又把半舱臭水刮出船舱,他已经决定提前开船,逃离儿子这荒唐的主意。
可是儿子说了,要请歪头喝酒。我已经跟歪头拍了胸膛,男人吐出的唾沫落地成钉。
话是不错,可是,现在还有多少男人守信用呢?猴子想告诉儿子,不守信用已经是男人的流行病。可是说不出口,儿子要做一个守信用的男人,作为老子,他也没有权力干涉。
中午,他不得不面对这个挑唆犯。儿子已经把歪头领到家里来了,此时歪头笑眯眯地扛着头,等待一次不错的饭局。灶上已经飘出了红烧肉和洋葱炒鸡蛋的香味。猴子更不能忍受的是儿子笑眯眯地看着歪头,似乎要把歪头脸上的汗毛一一数清。儿子看歪头的眼睛充满了崇拜,是小时候看自己的目光。不知道这个目光,是什么时候在自己面前消失的。氤氲的香气,在桌上弥漫,猴子感到老婆的菜今天烧得特别香,她越来越贤惠了。他想着,再攒点钱,把那条船独立承包下来,把儿子也带上船,如果她愿意,也带上她。再怎么说女人不易,生了个有点傻的儿子,要面临随时可至的羞辱,更不易。但这个女人,自从嫁给他,几乎不出村子,似乎外面正有巨大的危险在等着她。
猴子决定不给他酒喝,四乡八岭的人都知道,歪头是一个酒鬼。
他不愿意给歪头吃好的,他白了一眼老婆,又看了一眼傻儿子,对歪头勉强挤出半丝笑容,掏出了香烟,自己先点上,然后把烟盒勉强递到歪头面前,掂出一根烟:请,抽根烟。歪头其实眼光早落在烟上了,只是看到猴子自己先叼上,不满意地闭了眼,现在见了香烟,精神一振,伸手捉出一支烟来,点上,舒服地吐了个烟路,这才想起来给猴子挤出笑容,猴子不看他,转身坐上正席,点头招呼歪头入座,喊老婆盛饭。
歪头有点尴尬,按规矩,再差的酒也得上啊,这对“庄稼医院”的农技员是一个起码尊重,农技员怎么说也是个公家人,什么时候,他这公家人的身份,在猴子眼里跌了价,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所有杨树村人眼里都跌了价呢?歪头愈发不安起来。歪头枯坐着,捏着香烟,看着桌上的菜愣神。慢慢拿起筷子,似乎正勠力掐灭泛起的酒虫子。猴子扒饭的声音很响,嘴边油浪浪,连看一眼歪头的时间都不给,歪头吃得犹犹豫豫,他眼睛看着春龙,想从春龙的嘴里跳出“酒”字。春龙对他喝不喝酒并不关心,歪头很失望,甚至有点生气。
歪头负气地飞快搛菜。
这稻子长出来和现在有啥不一样?猴子终于开口,不然这桌上的尴尬气氛会让这几个好菜发馊。
你是信不过我?歪头虽然斜着脑袋,但是并不影响他搛红烧肉的速度,听了猴子的话,重重地顿顿筷子,有点生气地问。
猴子笑了一下,顺了一眼春龙,喃喃地说,就是一斤算百斤又能怎么样呢?稻子还能值几个钱!
歪头放下筷子,不吃了:这你还就别说,我就是要发明一斤顶百斤的超级水稻,可恨自己没有那个水平,都不种大米,难道喝西北风去?
猴子看到歪头变了脸色,也和缓下来,搛块肉压在歪头碗里:吃饭不谈事,谈事不吃饭,这是吃青草的猪杀下的——
你放心,你儿子把这稻子种好了,一样可以娶个俊俏的老婆,这稻子会让他声誉鹊起的——
猴子微笑着凑近歪头,他发现了歪头稀疏的胡子竟然是红的。
一抬头,春龙把一瓶海之蓝酒蹾在桌上,对歪头说,喝酒,喝酒,无酒不成宴,不喝酒不算请客——
歪头看着蓝莹莹的瓶子,两眼放光,很有力道地看了一眼猴子,哈哈大笑。猴子脸一沉,转过身去,打了一个很响的喷嚏。
这场酒喝高了,喝完了猴子家最后一滴酒,猴子和歪头称兄道弟,要不是船上的喇叭声,猴子已经忘记了今天是他出发的日子。
猴子突然发现,歪头的头正过来了,原来他一直歪着头是为等酒喝。歪头说:你不走算了,晚上继续喝?猴子坚定地摇头:不行,我们答应客户的,晚上必须赶到。
歪头很失望,头又歪斜过来,无奈地恢复了原状。猴子眼睛很有力地看了一眼歪头:怎么?我家儿子陪你,儿子大了……他说了算……等秧长硬了,再请你喝酒,这回喝茅台……
歪头眼睛越来越睁不开了,含糊不清地点头。
春龙又到庄稼地里转了三趟,歪头还没有醒来。这个下午,他已经雇好了人,抽水机正在向庄稼地灌水,明天就可以插秧,他的超级水稻要出世了。他听着泥土喝水的声音,心里突然明镜似的,想了不少事,他一时兴奋,掏出手机,不厌其烦地拍着视频,不放过在水面上疯狂逃窜的蛾子、蜢子、蚂蚁,还有躲在草丛中的青蛙,灰的、绿的、青的,在亮亮的水上蹦来蹦去,地下安生的蚯蚓也慌慌忙忙地爬上田埂……
人家说:你爸猴子怎不来请我?
他上了船,正在赶往长江,这五亩地,我说了算,放心,有专家指导,歪头正在我家堂屋里齁猪头呢——
受请的人就笑了,转身去拿工具,春龙开出的价码比村里任何一个人都高。当然春龙是有依托的,他妈妈会给他钱,无条件地给,妈妈虽然不大说话,这事上说了算,猴子急成孙悟空也没有用。他感到很快意,有种甩开膀子大干的豪情。多次争吵以后,他感到猴子突然矮了下去。比如,今天给歪头开酒,他自作主张,拿的是家里最好的酒,他看出猴子的心疼,但是他在心里用一只大皮鞋狠狠碾碎了猴子的心疼,没有比这个更让他愉快的了。
他感觉自己一点都不傻。现在对亮着肚皮打鼾的歪头,他有点犯难了,因为天的颜色像锅灰似的,黑了下来。蚊子、蜢虫纷纷出来觅食,歪头虽然干瘦,毕竟吃的是公家的饭,那血肉特别香,他看到蚊子在他的脸上肚皮上落了一层,像陡然生出的毛刺,歪头偶尔会胡乱地挥挥手,扫开一大片蚊子,它们已经飞不动了,纷纷落地毙命。春龙咧嘴笑笑:活该,这是酒鬼的下场。
他妈看不过去,默默给歪头点上几盘蚊香,打了井水,示意春龙用冰凉的毛巾把子唤醒歪头,但是歪头只是脸上的白皮揪了揪,歪歪嘴巴,又入了酒乡。
他妈把求援的眼光落在春龙身上,妈妈的眼光像一只温柔的猫。春龙垂着脑袋,闻着刺鼻的气味,手上扑打着随时无影而至的蚊子,听着歪头的鼾声,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拍拍他的脸,拽拽他的手臂,歪头只是含糊不清地哼哼一声,头一歪,又沉沉睡去。春龙很后悔,歪头是扶不上墙的烂泥,碰不得酒,酒比他爹亲,随时献了身。
春龙妈比他着急,天已经黑透,一个陌生大男人躺在家里打鼾,而且还要在家过夜,这会影响她的名声。怎么把这个男人赶出家门,看着半傻的儿子,她很焦虑。她把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总觉不妥。开了,蚊子水流一样扑进来;关了,屋里又热气腾腾,酒气熏天,熏得人直想打喷嚏。
春龙不知道他妈的焦虑,他的心挂在5 亩荒田上,它们即将变废为宝,他为此兴奋不已。他妈在村里是一个谜。她操着外地口音,与村里的人格格不入,村里的人都对他妈充满好奇,再傻,春龙也能从别人的眼光和闪烁的言语中感受到,不可否认的是他妈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虽然她几乎没有什么新衣服上身,同样一件衣服别的女人穿着不漂亮,甚至很丑,但是穿在妈妈身上突然就顺眼了,就亮起来了。妈妈身上似乎有一个硬壳,紧紧包裹着自己,她几乎不跟村里人打交道,就像一头老牛一样,默默在河堤上田地里劳作,似乎也没有什么亲戚,春龙觉得挺好,清清爽爽。但别人说,这一切都因为生了他这个傻子,春龙为此很难受。
第二天早上,春龙睡得很死,鸟唤醒了他,睁开眼睛,四周无人,他才想起来,今天对他是一个大日子——插秧了。春龙到田头的时候,五亩地上已经热火朝天,每一个人的劳动都让他激动,他的手机屏幕也因激动颤抖不已。
歪头扛着脑袋在田埂上跳脚,嘴里连续不断地喊着:“父本”“母本”“一行父本,十行母本”,村里人对秧苗还分父亲母亲不是太理解,嘲笑歪头。没有人注意他说的,也没有人分得清手上的秧苗哪根是公的哪根是母的,他们种了一辈子稻子,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这加重了他们对歪头的怀疑,对他的话,东耳进西耳出,不如水面上的轻风。歪头没有办法,举着一根柳条棍,不顾脸上、身上溅上污泥点,扛着脑袋在水田里指指戳戳,间或挥鞭抽水,边抽边说:我这是杂交的种子,一斤抵十斤,谁糊弄我,我跟谁拼命。有一个婶婶,对他很不满意,在他转身时用一把秧砸他,烂泥在他后背盖了枚印章,像四爪乱抓的乌龟。歪头慢慢转过身来,但是他找不到那个砸他的人。
所有的人都狂笑起来。
春龙知道,春龙从镜头里看得一清二楚。他看到秧田里土匪一样的歪头,知道他是真心护着这些秧苗,心里感动:下次还是要请歪头喝酒。
秧插下去不久,漫长的梅雨天来了,他透过雨帘对妈妈说:天漏了。
这时候,他倒期盼那个像风筝一样飘走的父亲猴子回来。但是这次航程似乎特别长,打他手机,也常常断线,声音飘飘忽忽的,似乎船正在长江里劈波斩浪,有水点溅落在屏幕的声音。春龙穿着雨衣绕着田地走。歪头要他放一群鸭子在秧田里,歪头说,鸭子可以帮他吃掉那些害虫。歪头不许他打农药,农药有残留,对种子不利。鸭子长得快,在稻田里为争领地,相互伸长了脖子吵架。春龙隔着雨帘,用手机拍它们,忍不住放到了朋友圈。当然更多的时候,他就在田垄里走,看着秧苗成长,他心才踏实。他多么盼望这些水稻开花,可是开花扬穗,那得有阳光,而阳光几乎已经半个月没有照面,这半个月里,似乎所有的东西都在糜烂,墙上的水渍正长出霉斑。在电话里,歪头也感叹,雨不能再下了,秧苗已经无法呼吸了,它会从根上烂掉,烂成一把黑灰。
大雨像一张巨大的白纸覆盖了整个村庄,河宽了,树矮了,到处白花花的。春龙看了手机里的天气预报,屏幕上全是淡蓝色的雨滴,看了真叫人揪心。他无处诉说他的忧心,只有放到朋友圈里,点击量飙升,不少人表示同情,还有人愿意来田里看看超级水稻。
雨声里,烦躁的春龙,脑子里亮了一下,也只是亮了一下,他想不起来为什么亮,整个上午他都在努力寻找着什么瞬间照亮了他糊涂的脑子。哗哗的雨声,让他无事可做,秧苗上面腾起一层蓝雾,它们正在沉没。妈妈在忙碌着开沟排水,她永远是春龙最坚定的支持者。真正为五亩地忙碌的是妈妈,她毫无怨言,春龙更像一个指挥者。父亲逃避种田是有理由的,种地必须把自己变成一头牛,只能负重、负重,只要不趴下,就不断有沉重的劳碌压向腰背,哪怕它们已经弯向土地,喘不过气来。
歪头曾不屑地对他说:你这是秀才种田,种田的苦你根本还没有尝到。等着,你一定会逃跑的,像你那个父亲,你那个风筝一样的父亲。
在一天的雨声里,春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念父亲。更没有像现在一样感到自己的无能,也许真的,自己不应该种什么超级水稻,应该跟着父亲跑运输。我得走,我得逃离这五亩地。春龙悲哀地想。投降吧,投降,自己根本不是种田的料,沉重的锄把自己根本拿不动。漫吧,漫吧,我不管了;老天,你下吧,看你有眼无珠地下到哪一天!
春龙几乎是看了稻田最后一眼,在哗哗的雨声里,他想自己变成一只不怕水的鸭子多好。歪头也多日不见,他卖出了秧苗,他就对5 亩田漠不关心了,这一定是歪头的一个套路了。春龙愤怒地又拨通了他的电话,歪头连连叹息,天下雨,谁也没有办法。谁知道今年梅雨天会这么长呀,这是暴力梅,你知道吧?在老天面前,谁也没有办法,你找石头,天天砸,砸死它——
春龙说,你这都是废话,稻田里的水排不出去,秧苗都在水上漂,你得想办法。
不,想办法的不是我,是你那个正在长江上跑得欢的老子,他这是浪荡,我如果……哈哈,想办法把浮起来的秧再插下去——
有用吗,有用吗?它们的根断了,它们的血脉就断了——只有他妈妈一声不响地在秧田里用戽子向沟里刮水——这活应该是男人做的。
春龙又给猴子打电话,在雨幕里,屏幕湿了,按键也不听指挥,根本无法拨出去。春龙没有办法,越拨电话,越觉得可气:还看我不顺眼,我看你永远不要回来。他狠狠地甩掉脚上的雨靴,默不作声,沮丧地走到妈妈身边。妈妈一身水一身汗,汗味从雨幕里挤过来,她已经挖出了一条很长的墒沟,看样子,快要完成了。锹柄上有血,磨破了手。春龙夺过妈妈的锹,妈妈瞪大了眼睛,想再夺回去,但是没有成功。春龙使着蛮劲,几乎要把锹柄扳断。他只有蛮劲,他没有挖墒的技巧。
汗水雨水泪水交织迷糊了他的双眼,他感到眼睛热辣辣地疼,泪水越流越多,吸到嘴里,很咸,春龙突然喜欢起这种味道。
妈妈到另一边,开始挖另一条墒沟。
水白花花地排出去,田里的秧苗渐渐露出了尖角,然后是叶子,它们像暂时隐身的战士,抖擞着精神,露出了刚毅的面容。春龙抓了一把烂泥,向天砸去,你下吧,你就再下三天三夜我也不怕你。
妈妈正色说,天下雨是天在哭,它有不顺心的事,你何苦砸它?
老天受不了砸,不久雨停了,那满天的白云,春龙像看到了亲人。
春龙拿出手机,透过茁壮的叶子拍天上棉花般绽放的云朵,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雨后的稻叶子不再温顺,一根根长成出鞘的剑,含着被压抑的愤怒。
漫长的梅雨季,歪头脚印子都没有迈来,现在他看到歪头了。他想明白了,五亩地只与他们母子有关,别人的每一次关心,都是意外,当然包括猴子,包括歪头,这两个看上去应该为五亩稻田负责的人。
歪头不让施化肥。要绿肥,绿肥懂吗?歪头说。稻子的肥力不够,春龙想撒点碳酸氢铵或者尿素,遭到歪头的阻止。
绿肥在哪里?
歪头轻慢地笑一下,歪歪嘴:路边,这些青草。还有,河里,那些河草,捞上来,沤臭它们,就是我们超级水稻的绿肥。
春龙畏难,这草得一根根割,要累断筋骨。他不想,他更愿意撒上化肥。他又想逃跑了,他觉得每一根稻子的生长都饱吸着他的汗水。
春龙花了几个上午和妈妈在稻田里插上稻草人,它们戴着斗笠,平伸着手臂,塑料布发出哗哗的声音,想靠近的麻雀在这巨大的声音里,落荒而逃。
妈妈说,好的,明天我们就开始割草。妈妈扔掉手上的稗草,扶正了一个稻草人。她已经默默在秧行里走了两天,必须把那些长得像稻秆似的稗草拔掉,否则它们会和超级稻子争夺阳光、土壤。
太阳突然毒辣起来,怕春龙晒,妈妈给他准备了芦苇编的帽子,还有一幅白色的纱布,系在身上,防晒也透风透气,还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春龙很喜欢。
这次春龙要招待歪头喝酒,他已经学会了喝酒,他觉得酒真是好东西。做个醉鬼很幸福,只管睡觉,不要劳作,一个下午就轻飘飘地过去了,这是逃离这五亩地的好办法。还有漫天飞舞的蛾子、稻飞虱,疯狂的歪头又不允许打农药。稻子都给害虫吃掉了。妈妈很忧虑。春龙满怀忧愁地端起酒杯,歪头不理他,笑眯眯地眨巴着眼睛,滋巴滋巴地咂嘴。有了上次的教训,春龙很害怕他喝醉,但是喝着喝着,歪头抢过了酒瓶,哗哗地给自己倒酒,他边到边说:今天俺爷俩一醉方休。
歪头说:说说,你为啥种稻,你真是傻子吗?
春龙说:你说说,你为啥不断往我家五亩地里跑?
……
妈妈阻止他们,但是妈妈的阻止是徒劳和无力的。
一醉醒来,春龙不知道他成了网络上的名人,他被网友称为“稻田里的骑士”。网友说,骑士,就是英雄。
他看到他的视频后面的留言,傻傻地笑了。原来照亮他脑海的亮光又出现了,这次,他很清晰地抓住了,他要把每一根稻子都编上号,在网上供人领养,他把稻田命名为“骑士的稻田”。
果然,城里人兴趣盎然,每棵稻子都有人认养,他们要给自己的孩子讲述一粒稻子如何长成。他们在屏幕里嫌不过瘾,正呼朋引伴要到春龙的稻田来,说要亲手摸摸稻叶、稻穗。
这个下午,春龙忧郁地在稻田里捉虫子,这是个寂寞的事情,他没有发现妈妈,妈妈被家里无处不在的琐事无边无际地缠着。他看见歪头蹲在田角,分析完根须,拎着那串秧,很响地吐了口唾沫,说:明天拉花,稻子扬花了,每天早上要拉花。拉花是件小不下来的事,一个小时必须全力拉完。
歪头又不放心,转头又叮嘱一遍,只有花拉得好,五亩地才能抵上五十亩,否则我不认账。
春龙听了有点不开心,当时你根本没有说拉花的事,这是要赖账不成?
在太阳出来之前,露水未干,他们必须两个人对拉一根长长的塑料绳子,在水稻上面一遍又一遍地掠,让雄粉和雌粉很好地融合。太阳是它们的媒人,五亩地是它们的婚床。歪头说到这里,自己笑了,春龙又看到他眼睛里长着锥子,刺人。
春龙戴着芦苇编的帽子,系着白纱布,像一朵云一样在叶尖渐黄的稻田上飘荡,虽然现在脸已经晒得黑红,脸上的皮掉了一层又一层,但是胳膊咕咕地生出力气来——越来越像一个骑士了。太阳出来了,春龙在河岸上直播他那高傲的五亩超级水稻,现在他已经熟悉每一根稻子,在河岸上走着,微风吹来,阵阵稻花香,春龙越来越有骑士的感觉了。
他对着屏幕大声地喊,你们看见过水稻开花嘛?快看,水稻正在开花,花飘起来了,飘成雾了……还有鸭,满田的稻花鱼……看看哪棵稻子是你的……
那年,超级水稻丰收,但迟迟不见歪头来收稻子。春龙看着高高堆起的稻种犯愁。他到庄稼医院去找歪头,歪头说,上面那个大商人说话不算数,他不收了,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是受害者,呸!歪头躲进巨大的玻璃后面,不见了。春龙对着空空玻璃镜喊:你这样不守信用,就不是个男人!请你以后,别往我家跑,我们不需要你,再来……打断你的狗腿!
春龙看到自己在玻璃上的影子很狰狞,巨大芦苇帽子的影子,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沮丧落败的骑士。
歪头从玻璃后面,伸出头来,尖着嗓子说:找你妈去,你妈的老相识多得很,嘁——你等着——
春龙受到了莫大耻辱,举起手机砸向玻璃,玻璃裂出很多条缝,屋子里光怪陆离起来。
猴子突然打来了电话,在电话里显得心不在焉,他只是问歪头最近来了没有。春龙现在听到歪头的名字就生气,没有理猴子的茬,猴子愣一愣,继续说,这趟船要去上海,短时间回不了家。
春龙没好气地说:这家你反正已经不要了。
嗯嗯,这一趟完了,我就回家。长江里风浪大,两边的山都在奔跑呢……我们会有自己的船,一定会有,到时候,你也上船帮忙。
春龙嗯嗯两声,没有表现出热情。
猴子又清了清嗓子,声音迟滞地说:我和你妈早分手了,你懂吧,我和你妈一直过得……不愉快……你忙高考没有告诉你,现在你不考了,不考就不考吧,这没有什么,你一点也不傻。歪头对你好吧,他撺掇你种什么超级稻,根本就是一个阴谋,他没有安好心,他就是一个登徒子。他虽然当上农技员,但是你看他那歪头,多丑。
我敲断他的狗腿!
你妈更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城里的夜场当过陪酒女,她的名声不太好,她把所有的微笑都贡献给了她的客人……这个你应该懂的,她吸的烟、喝的酒,也许伤了你的脑袋……
你们不是说我难产吗?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原因,我想——
住嘴,告诉我这干嘛?我不想听,我只知道我妈一滴酒都不喝!
春龙按灭了电话,把猴子的声音生生切断了,脑子里一片黑暗。春龙准备把超级水稻作为普通的稻子卖掉,但不甘心。这稻他是吃过的,香味异常。屏幕救了他,“骑士的稻田”直播的收益,远远超出他的意料,后来他一点也不担心这些稻谷卖不出去,那些认养超级水稻的人,在屏幕上不断呼叫“稻田骑士”,他们正成群结队而来。天渐凉了,白纱布已经不适用,他妈妈特地买来红绒布,披了一身红。他想,不把这超级稻种卖掉,他绝不解下这件“盔甲”。他已经是一个没有老子可以依靠的人了。
在稻子即将都卖掉的时候,家里来了两个人,很精神,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黑夹子,春龙以为是来买稻子的,但他们是找妈妈的。他们关起门来,谈了很久。后来,春龙听到了妈妈的哭声。春龙冲进房间,要赶他们出去,被妈妈阻止了。妈妈眼睛很红,对春龙说:妈妈对不起你……
拿夹子的年轻人说,我们是警察,好了,你妈妈清白了。20年前,你妈妈打工的美容店发生了杀人案,三个……小姐被杀,只有一个在柜台后面的逃脱(显然,她就是你妈),所有的人都认为她与杀人者里外勾结,但是没有证据,她背负着耻辱生活,不敢再离开村庄一步,这里是她唯一的容身之地。现在网络发达了,案子终于破了,她只是幸运者,不是告密者,我们只是请她补充作证,做个笔录。这么多年,隐姓埋名,你妈不容易,好心人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才找到她。
春龙先是惊恐地睁大眼,然后冷冷一笑,这人是歪头吧。
他妈要抱他,他一下子跳开:你……傻……
春龙明白了,他家里所有的祸根,原因在这里,这根毒刺一直在暗处生长。现在拔掉了。
春龙给猴子打电话。
春龙的手机上,满屏白晶晶的超级大米,细长、白净,像一枚枚雪亮的刀,现在屏幕被泪水淋湿了。
手机屏幕上不断有弹幕打出来:呼叫稻田骑士——呼叫稻田骑士——,你是骑士——你是骑士——
它们一行挨着一行,急急如行军。春龙想,明年这“骑士的稻田”还能办下去,他还得继续当骑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