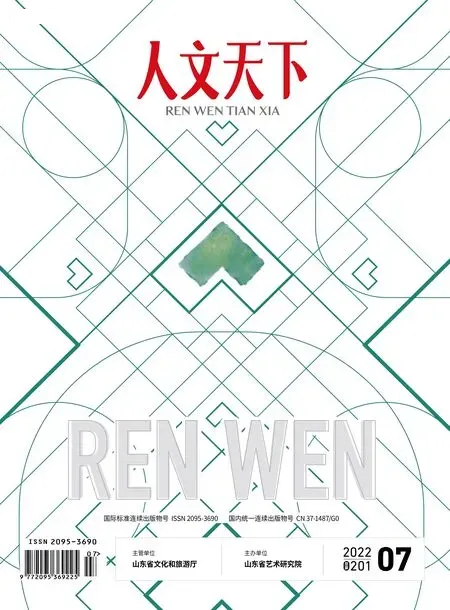“人不知而不愠”的生存论分析
■ 陈春桂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以下所引《论语》一书仅注篇名)这是《论语》开篇的首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后世学者对该句的阐释也层出不穷。本文尝试在生存论视域下对“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作出解释。
儒学的生存论视域是儒学当代阐释的一个新视域,黄玉顺指出:“今日的儒学研究正在开始透露着这样一种消息:对于儒学的‘重建’或者‘现代转换’来说,生存论解释学是一种新的极富前景的致思方向。”当然,与海德格尔生存论分析的全部意图在追问“存在的一般意义”不同,儒家、孔子只关心人的存在本身,即只关心“生存的意义”,用儒家的话语来表达就是:常人如何成为君子乃至圣人,以及这样的超越是如何可能的?这种儒学的生存论视域正是本文解释孔子所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阐释视域。
一、君子:“去是”的生存方式
读《论语》时,我们总会感觉到孔子的形象以及《论语》的语言是鲜活饱满的,洋溢着活泼的气息,我们仿若随着其语言置身于一个个生动的“生活情境”中。张祥龙说:“《论语》中洋溢的那种活泼气息即来自孔子思想和性格的纯构成特性。”只有理解了这种纯构成特性,才能在人生的境域式生存中去理解“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生存样态。
理解孔子思想和性格的纯构成特性,关键在于先理解“构成”。何谓“构成”?张祥龙解释说:“‘现象本身’或‘事情本身’一定是‘构成着’的或‘被构成着’的,与人认识它们的方式,尤其是人在某个具体形势或境域中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换言之,任何‘存在’从根本上都与境域中的‘生成’、‘生活’、‘体验’或‘构成’不可分离。”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对胡塞尔所言“实事在这些体验中并不是像在一个套子里或是像在一个容器里,而是在这些体验中构造起自身”一语的注脚。“现象本身”关乎的从来都不是对象物,而是状态,不是现成的“什么”,而是敞开的“如何”,是境域中的“构成”。可以说,“构成”是“现象”的存在方式。而且如同追问“存在”首先被问及的是“人的存在”一样,“构成”首先也是“人本身”的“构成”。“人”就是在生存活动和生存体验的境域中“构成着”的,这也就是“去是”“去存在”。
君子是孔子所肯定的一种人格,但《论语》对君子并没有一个形式化的定义。因为君子不是现成固定的,而是在人与人相互对待、相互造就的不断“去是”的生存活动和生存体验中构造起来的,或着说“构成着”的。这样来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也一样,“不依赖任何现成存在的‘什么’,而只要求自己与他人的相互构成”。所以,我们从《论语》中看到的只是不同生活情境中,孔子在不停描述君子及其言行,以及如何成为君子,这是一种敞开的“如何”,而非现成的“什么”。君子不是一个“现成在手状态”,不是一个现成的、固化的个体,而是一种“去存在”“去是”“去生存”的可能方式。在这里,“去是”用儒家的话语就可以表达为“去成为君子”。
“人不知而不愠”是儒家所追求的君子的一种生存样态,在这种人与人“不知”与“不愠”的互相对待和互相造就的生存体验活动中“构成”君子。与此同时,“人不知而不愠”这一生存样态也随着君子的“构成”而与君子不断“去是”的生存活动紧密相关。“人不知而不愠”不仅是君子的一种生存样态,而且是一种常态化的样态。君子难于为人知、难于为人理解,“人不知”对于君子而言是很正常的事情,故孔子才会有“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的感叹。就孔子而言,“知我者其天乎”既是他对本真生活的一种生存领悟,也是对“人不知”现状的一种慨叹。因为圣人与非圣人、君子与非君子(如小人)的生存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君子”在《论语》中时常会与“小人”对举。“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
蒙培元说:“‘上达’者上达于天命。”也就是说,君子“上达”而“知天命”。孔子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君子“知天命”而“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反是,小人“下达”且“不知天命”,从而不畏天命,这是一种与君子截然相反的生存方式。
孔子关心“人”,更关心人“生存”的意义,关心常人、小人如何成为君子,其理想状态是“小人”和常人都应当向着君子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不断“去是”,不断“去成为君子”,这也是孔子讲学的目的及意义所在。显然,君子不是一个“现成在手状态”,而是一种“去存在”“去是”的可能方式。所以,君子向来就是有待“去是”的生存方式。
二、“人不知而不愠”:君子的生存样态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指的是,一个人对于“人不知”的这种状态“不愠”,这种人就是孔子所认可的君子。君子是有待“去是”的生存方式,而“人不知而不愠”的生存样态中亦可“构造起”君子,同时“人不知而不愠”也就成了君子的一种生存样态。
(一)“愠”与“不愠”
“愠”与“不愠”都是人在特定生活情境中对当下生存活动体验的一种情感显现,不是现成固化的,而是在相应的生活情境中产生的。同理,“愠”在不同的生存境域、生活情境中会有不同的显现样式,关键要看主体及其所处的境域。《公冶长》中令尹子文之“无愠色”和《卫灵公》中子路之“愠”,给人的感受便不同。其“愠”与“不愠”便是他们在不同境域中对本真生存的不同体会,以及其当下呈现出的不同的生存样态。
“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公冶长》)在这里,“愠”是与“喜”相对的一种情感,朱熹注:“其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无间。”“无愠色”既可理解为他面对人生的起落喜怒不形于色,不在情感上迁怒于别人,所以让别人接收到的信息是“无愠色”,也可理解为他自己内心没有不平之意,所以表现出来的也就是内心的不怨不愠,故而“无愠色”。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处于“绝粮”的生存境域中,面对着“从者病,莫能兴”的本真情景,子路本能的情感反应是“愠”。子路的喜怒都写在脸上,就当时的生活情境与子路的性格综合而言,这个“愠”既含有“怨”义也含有“怒”意,所以子路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情绪。
由此也可看出,“愠”最直接的表现样式无外乎“怨天尤人”,“不愠”也就是“不怨天,不尤人”。孔子和子贡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面对“莫我知”的生存境域,孔子 的态度是“不怨天,不尤人”,即“不得于天而不怨天,不合于人而不尤人”。这种“不怨不尤”既是孔子对生活中“莫我知”境域的一种生存领悟,也是一种生存样态。结合“人不知而不愠”来看,“莫我知”“莫己知”与“人之不己知”都是“人不知”的一种表现,“不怨天,不尤人”也即“不愠”。李景林也说:“所谓‘不怨不尤’,亦即《学而》所谓的‘人不知而不愠’。”所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也意味着君子面对“人不知”的情境“不怨”亦“不尤”。
(二)“人不知”与“知人”
君子为何处于“人不知”的境域却“不愠”呢?尹焞说:“学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所谓“古之学者为己”,说的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最基础的一环——修身,这其实是“大公”,而不是“小私”;而“今之学者为人”,今之学者是为了让人知,这其实是“小私”。君子以“修齐治平”为人生理想,“以修身为本”,其所学在己,而知不知在人,所以何愠之有呢?也就是说,孔子所言“不患人之不己知”是君子“不愠”的一个缘由。
更重要的是,“人不知”不是一个固化的生存状态,而是一种需要打破的状态,是“去知”的可能开显,而且这种“去知”的开显首先面向的就是自己,是自己“去是”“去知”“去知人”“去可知”的可能方式,正是有了人自己“去是”的生存活动,才能“构造起”君子的理想人格。同时,这种生存活动中还隐含着面向他人的开显,“患不知人也”,自己不知人,这是自己之患,所以自己要“去知人”,但他人不知人,这便是他人之患,所以他人也要“去知人”,这是他人的“去是”“去成为君子”的可能开显。所以,君子处于“人不知”的生存境域中,“不患”亦“不愠”: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
“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卫灵公》)
在生存论视域中,“人之不己知”或“莫己知”是“人不知”的一种呈现样式或一种生存境域。面对这一境域,这里有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且均无关于“愠”:一种是因为“患不知人”,所以要去“知人”,这是自己对别人由“不知”到“知”的过程,是“去知人”的生存活动;另一种是因“患其不能”“病无能焉”,即“自己不能”,所以要“求为可知也”,这是让别人对自己从“不知”到“知”的一个新过程,这是“去能”“去可知”的生存活动。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这三句话在本质上想要表达的意义是一致的,都是要让自己有“可知”之实。“能”就是“求为可知也”的“可知”,即“可以见知之实”。自己“不能”,也就是自己没有能被见知之实,所以要“去能”,这是从“不能”到“能”的生存活动,要让自己“能”起来。自己没有能被见知之实,也就说明自己还“不知”或“知”的水平状态还不够,同时还处于“莫己知”的状态,所以要“去求为可知”“去可知”,这本质上就是让自己“能”起来,只有自己“能”起来,有了“可以见知之实”,才能真正实现“求为可知”,也才有可能打破“莫己知”的状态。而且即使达到被人“知”也并不是终点,因为在无穷的生存境域中没有终点。所以,孔子才会有“如或知尔,则何以哉”之问。
“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先进》)平时常言人不知我,“如或知尔,则何以哉”是又开始了以“知”为起点的新一轮“去是”的新征程。因为人始终在生活中,始终在生存境域中,那也就始终处于不断“去生活”“去是”的过程中。所以在孔子看来,君子所患不在“人之不己知”而在自己“不知人”,即“不知人”是君子所患的一种生存状态。前面说过,君子是在人与人相互对待、互相造就的生存活动和体验中“构成着”的,这种人与人的相互对待、互相造就的“生存活动”是双向的:除了人知不知我外,还有我知不知人。而且对于君子而言,我知不知人尤为要紧。尹焞说:“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则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为患也。”由此可见“不知人”之患,难怪孔子十分强调“知人”的问题。所以,君子要“知人”,而且要不断地“去知人”。
事实上,人一直处于“知”与“不知”之间,无论是自己“不知”还是别人“不知”,都要不断地“去知”,去打破“人不知”的状态,所以,人也一直处于从“不知”到“知”的过程中。“知”与“不知”都是一种状态、一种现象,从“不知”到“知”的状态处于一种时间境域中,蕴含着原本的“时间性”,它使人超出固化的“现成在手状态”而进入一种新的可能方式。所以,这种从“不知”到“知”的生存活动,就是对“人不知”的突破和超越,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去是”的过程,正是在这种不断“去是”的生存活动中“构成着”这种“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与此同时,“人不知而不愠”也成了君子的一种生存样态。
三、“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而后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结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这种首尾结构应该不是偶然。君子“知命”“知礼”“知言”,看似是在强调“知什么”的问题。事实上,重要的不是“知什么”或“不知什么”,而是从“不知”到“知”的生存状态,即“如何”的问题。正是在这种从“不知”到“知”的生存活动以及对生存的领悟中,“构造起”君子本身或说“构成着”君子本身。“不知命”便“无以为君子”,“不知礼”便“无以立”,“不知言”便“无以知人”。正是因为“还不知”,所以要不断“去知”,人一辈子都不断处于“去知”的过程中,这是一种介于“已知”和“还不知”之间的生存状态和活动,是“去成为君子”的可能,这也就是儒家关心的常人如何从小人变为君子。
君子作为一种有待“去是”的生存方式,在不同的生存境域中有不同的生存样态,“人不知而不愠”作为生存样态之一,同时也在“人不知”与“不愠”的相互对待中“构造起”君子。也就是说,君子本身就是在“人不知而不愠”的生存样态中“构成着”的。所以,孔子说一个人如果处于“人不知”的境域而“不愠”,便可称之为君子。
在生存论视域下,君子和“人不知而不愠”都不是现成固化的,而且“人不知”这种状态是需要去超越的,超越“不知”才能进入“知”,即进入新一轮“去是”的生存活动中。“人不知而不愠”是君子领会“自己本身”的一种生存样式,君子也正是在这种“人不知”而我“不愠”亦“不患”的人与人的相互对待的生存状态中,开启了“去能”“去知”“去可知”“去知人”等无限可能的新一轮的“去是”,君子正是在这种不断“去是”的生存活动中不断“构成着”的。所以,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绝不是说有一个现成的君子在“人不知”的境域中怎样“不愠”地生存着,而是说在“人不知而不愠”的生存样态中“构成着”君子,使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得以呈现出来。
结语
总之,《论语》讲的从来都不是一种现成在手的状态,而是如何“去立”“去知人”“去成为君子”的生存方式。生存境域中的众多的生存活动和体验,实质上也就是不断“去是”“去成为君子”的生存活动。在儒学的生存论视域下,君子是有待“去是”的生存方式,“人不知而不愠”是君子的一个本真的生存样态,“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说在“人不知而不愠”的生存样态中“构成着”孔子认可和肯定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