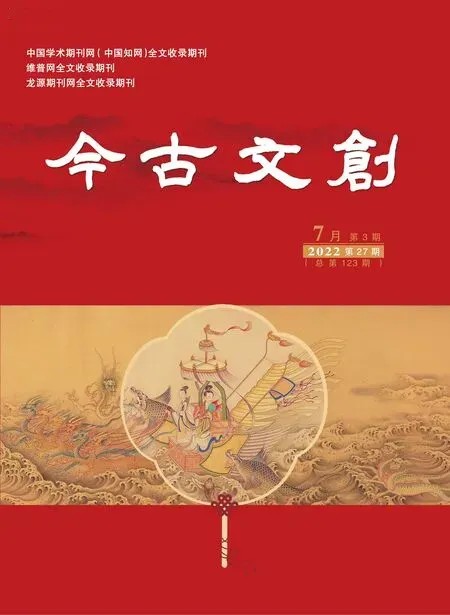试论清朝妖术恐慌
——以乾隆三十三年、光绪二年为例
◎廖 芸
(湘潭大学 湖南 湘潭 411100)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与各王朝并行而存的巫术邪教,因其本身所特有的神秘性质与孤陋寡闻的普通民众一代传一代的迷信思想一拍即合,在基层扎根后甚至蔓延至官僚阶层,统治者自知要明文严禁巫术邪教的传播与发展,否则孳蔓难图恐危及统治与国祚,在一些系列惩禁措施推广后,由于基层管控与法规实行的缺乏使治标的规定流于形式,最终得到“只惩未禁”的结果。自明以来,关于妖术、摄魂的史料记载不计其数,但其多止于纸狐、纸虎等动物形态,至清时积蓄了百年的妖术力量与政府的愚民政策发生强烈碰撞,敲出两次妖术大恐慌——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清剿行动与光绪二年(1876)的剪辫摄魂。
一、乾隆时期妖术盛行的社会大背景
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记述了关于妖术摄魂的基本信息:“在某种条件下,人的魂能够同拥有魂的躯体相分离;一个人若掌握了另一个人的魂,便可以利用它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利;通过向受害者撒出粉状的迷药,可以使他在被剪去发辫时无法抵抗。”开启叫魂案的前四例中国窃贼传奇——德清县的石匠、萧山事件、苏州的乞丐、胥镇口奇事,其中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均来自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叫魂恐惧首先发生在江苏、浙江,然后蔓延到山东和其他省份,权倾天下的乾隆帝却是在山东巡抚富尼汉呈上含各地叫魂案的细枝末节的奏折后知晓,从苏浙等王朝经济中心直逼清廷直隶等天子心腹之地,叫魂案所涉及的地方与案件性质犹如一颗定时炸弹精准地投放在了乾隆龙椅上。恰巧此时,两淮盐政以备办乾隆南巡为由每盐引私自提取3两盐引银之事被揭露出来,作为乾隆朝“三起最重大的贪污案”之一的两淮盐引案涉案官员之广、赃银之多的调查结果犹如给弘历当头一棒,乾隆对江南官场的颓靡之风、官吏擅自封锁消息的不满以及各地官员以跨省调查追捕多有不便为推诿之由的愤怒,终如滚雪球一般堆积成了“政治罪”的官场风暴。距离乾隆上次对官员惰政的敲打已过廿余载,剪辫摄魂之事满足了皇帝进行第二次官场清洗的需求。乾隆时期中国的专制体制已发展到登峰造极,象征专制的皇权至上背后却是一个忌惮、厌恶繁华江南,忧烦老化停滞的钳制官僚运作网的帝国决策者,与皇权至上相悖的剪辫案使乾隆赌上个人尊严与帝国威望誓把苏浙叫魂嫌犯及背后的势力连根拔起而下达了宁错勿放的谕令,“自可得其端绪,正犯不致漏网”,一场史无前例的“无妖捉妖”的清剿行动就此展开。
费正清说:“每个王朝在建立后不出一百年就会开始严重的财政困难。”乾隆三十三年(1768)不仅处于王朝百年时期,也处于乾隆在位的中期,这时乾隆已完成了“十全武功”中的六个,仅观第一次金川之役所造成的帝国财政流失,就可得出盛世下的民众生存不易之结论。根据李鸿彬、白杰的统计:“第一次金川之役从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十一日到十四年(1749)一月二十七日,经历695日,用银7648000余两,平均每日耗银11004余两。因十二年九月三十日清廷拒敌乞降,使战争延长498天,耗银5479992余两。”耗银之巨实乃叫人瞠目结舌,“一全”尚且如此,“六全”何以复加。除此之外,“乾隆六年(1741),全国大小男妇人口1.43亿;二十七年(1762)为2.04亿;五十五年(1790)突破3亿,50年人口翻番1倍半”。乾隆时期的妖术恐慌发生的时候全国人口处于两亿到三亿之间,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土地垦荒及休耕的速度,加之官僚地主阶层对土地贪得无厌地兼并,迫使大量无地、少地百姓破产。乾隆二十年(1755)苏南虫荒,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的米价长到了三十五六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年丰收,价渐复旧,然每升常价也只恢复到十四五文。在乾隆末年回忆道,“50年前其祖、父之时,每升米不过六七钱,每丈布不过三四十钱,如今每升米须三四十钱,每丈布须一二百钱。”美洲低价白银流入中国,客观上造成粮布等基础生活用品价格的上涨,人民生存负担加重。盛世下人口与物价的增长相存的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背景,普通民众无法自行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桎梏,统治者制定的人口对策难以形成生产力发展的新因素,无法开辟吸纳新增人口的新途径。当人口增长突破了社会经济承载力的临界点,失去生存依托的流民队伍势必壮大。
二、光绪时期妖术盛行的政治与经济背景
嘉庆十五年(1810)也曾发生过剪辫妖术,但嘉庆皇帝汲取了乾隆的教训,明确禁止地方官员“株连根究”,结果此事无疾而终。盛世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妖术恐慌发生于“同光中兴”的光绪朝第二年,此时的社会背景较之前截然不同,政治、经济、民生、社会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太平军建立的农民政权崩溃久矣,但两个政权在武力加持下对作为主战场的江南地区的消极影响远没有结束,“以江苏为例,据统计,1851年,江苏人口约为4430万,至乱后十年,即1874年,竟减至2000万不足。”其次,战后人口数量大幅下降,随之而来的是农田土地的疯狂贬值,原来值4万铜钱一亩的良田如今只值1千文(80分)。响应政府号召和被低贱地价吸引而自愿填入苏浙等地的外来移民在为江南经济复兴作贡献的同时也因对生存空间的争夺与当地土著发生了一系列冲突,至此,人多地少的人地矛盾转化成了土客矛盾的社会问题。其次,鸦片贸易合法化作为官方向农民发出的一种指导生产的假讯号,给了农民立足国内市场进行鸦片自产自销是比种粮缫丝更有利可图的错觉,这直接导致种植经济、粮食作物的田亩面积大量减少,出现“米粟贵如珠”的现象。太平天国内乱和外强入侵的内外联动构成了动摇清政府统治的现实基础,“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被光绪朝的“社会脆弱性”所替代,朝廷内部派系林立、各自为政,政府控制力下降、吏治腐败成疾,乾隆的君权时代——即君主对地方官僚的绝对控制在光绪时期一去不返,此即是妖术盛行的政治、经济背景。
三、光绪时期妖术盛行的民生与社会环境
《洪洞县志》载:“春,县南有火自田间出,远望如球,光敷天,东西无定向,时无时现,占者谓旱征”;《元氏县志》记:“荒旱,大饥,人相食,县令请款贩济”;光绪《南乐县志·祥异》有:“五月壬午酷暑,焦大木皮若介,果实如之,是年大旱。”上述皆为发生于光绪初年并持续数年,被称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未见之凄惨,未闻之悲痛”的“丁戊奇荒”相关记载,以直隶、河南为中心的北方相继出现旱情,尔后蔓延至苏北、川北、皖北一带,波及范围之大、蔓延速度之快,前所未见。和旱灾并行的还有蝗灾与疫病,《清史稿·灾异志》载:“夏,昌平、武清、滦州旱蝗。秋,柏乡蝗。”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被蝗虫吃个河落海干,蝗飞蔽天、赤地千里对农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剥树皮,掘草根”成了“人相食”“易子互食”的惨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说:“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但旱灾相对于其他灾害对社会环境的影响是更为巨大的,干旱时间越长,民众对生存的希望更渺茫,焦虑和绝望的情绪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很容易陷入恐慌状态,正如柯文所说:“旱灾持续的时间越长,这样的问题就越急迫:什么时候下雨?干旱什么时候结束?它会结束吗?简言之,水灾形成后,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已发生之事,而旱灾形成后,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尚未发生之事。可以说,旱灾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更大。”民众心理防线在经历了数次为求生而不得不做出的与道德伦理相悖的事件后全面崩塌,在饥饿之苦的生存环境中,抗灾赈灾这些挽救基层民众的常规救助效果不显著的情况下,人们极易将消极情绪转向少数替罪者的身上,如乾隆时期的道士、僧侣,光绪朝的教士,在这种“替罪文化”的影响下,剪辫案被一再放大,百姓对它的敏感程度也愈发激烈。此即是妖术盛行的民生、社会环境。
四、两次妖术恐慌的异同及社会影响
清朝两次妖术恐慌的起始事件均是修桥。1768年,亦是清朝第四位皇帝弘历(乾隆帝)在位之三十三年,东面城墙的水门与城桥坍塌了,亟待重修。中标修缮石桥的吴东明同乡沈士良因私仇将仇人名字写于纸条上交给吴石匠,虽然吴东明拒绝了,但他仍成了第一个无妖术却被冠以“叫魂主角”的无辜民众。据他们说,石匠们需要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这样会给大锤的撞击添加某种精神的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从萧山事件来看,施加诅咒的人需借用奇技淫巧之人的一些谋生手段,并入念力等精神方面客观难以感知的事物就可将受害者的魂从肉体中剥离而出,对技艺人来说这是易如反掌之事;对施咒人而言此乃一本万利的买卖,妖术易施的简单性或许是百姓惧怕的原因。光绪二年的妖术恐慌始于因太平天国战争被毁的长于桥,《申报》记载:
石工起造桥梁,将须合龙之际,俗传石工收人生魂,用以项戴桥梁。其收魂之法像呼人名姓,人一答应,即用小瓶将口塞紧,谓其魂己收入瓶内,俟合龙时,即以此瓶放置桥内,为所收者决无生理云云。
“以魂筑桥”的谣言生存基础极差,但加上剪辫的传闻后基本具备了施法妖术的媒介,也触碰到了百姓敏感的神经。乾隆时期的恐慌始于修桥多半有巧合因子在内,这种只需贴仇人姓名于木桩上撞击即可使活人病痛甚至死去的叫魂方式,是对前朝“折纸成兵”的变相继承,至光绪朝时,石匠有收人魂魄的本事的传闻早在民间根深蒂固,民众虽不知被剪去的辫子有何作用,但天马行空的猜想还是使民间陷入恐慌状态,听闻谣言的百姓已到草木皆兵的地步人为制造恐慌取代了前者的巧合。其次,两次妖术的发源地均是苏浙等江南地区,传播范围沿长江流域扩散,江南自古就有信鬼神的传统,《史记》载:“荆人鬼而越人禨。”《资治通鉴》有:“是以江淮以南无冻饿之民,亦无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由此可以看出信鬼迷神的民风与社会失序的现况交织成了江南妖术恐慌。再者,流民及下层群众是妖术的涉案者或受害者,两次恐慌均未涉及太多贵族阶层。以流民为代表的流动群体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居无定所的他们是传播妖术事件的主要中间人,他们不用刻意伪造妖术事件,只需做好谣言搬运者,将一个地区发生或传闻的妖术传播到另一块土地,借助民众信巫及妖的心理,加上官方对传播妖术的严厉打击等侧面印证,两场妖术恐慌就此蔓延。
从制造妖术的手段出发,相较于乾隆时期剪辫单一模式,光绪朝似乎更“推成出新”,逐渐形成了以剪辫为主、摄魂为辅的妖术运行模式。据《申报》载:
十余年前,苏垣初复,尸积人稀,因有野狼出没噬人,而穿窬者蒙皮效之,人晃而生布被,遂攫取财物。近有纸人剪辫之怪,不意亦有假之以作奸者。
不仅有人为狼患、纸人剪辫,更有遍剪鸡毛、梦魇惊人、变绳为蛇、断势割乳等手段,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打印妖术,《申报》称:
匪党在人身上,不拘何处,连打三笔管圈,难在衣外,而其圈自能透入皮肤,作紫黑色如火烙印,然其人越三日即无疾而死。
随着妖术的升级换代,方式变得繁杂怪诞,为配合匪党的政治行动,打印妖术致死的时间被缩至三日,这反映了妖术的非客观性,若妖术真的存在,则不以近代秘密教会分子的意识为转移。因社会背景不同,乾隆查防重点在于行踪不定的游僧道士,这类人群不仅打破了边缘群体的传统乡土社会的封闭状态,还不受现有经济制度的约束。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研究揭示,在社会动荡不安,引起社会成员恐惧、紧张和危机感的时候,即容易造成传闻盛行。虽然处于盛世,但乾隆觉得僧侣的不定行走会对基层统治造成难以言说的负面影响;而光绪朝因哥老会和民众反洋教的影响,此时期的查防重点在于江南斋教徒、哥老会等会党分子与传教士。
另一个侧面推动妖术恐慌的便是清中期以后才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的士绅集团,在乾隆时期并没有存在双重统治秩序和政治格局,士绅不仅对民间妖术的发展与绝迹无足轻重,对地方其他政治影响也是微乎其微;光绪朝时国家与宗族的力量比重发生变化,以士绅为代表的基层社会实体集团的力量正在逐步增强。尤其在基层上洋教和妖术画上等号后,在地方场域的原有资源被西方宗教势力瓜分后,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捍卫儒术道统,士绅这个群体开始利用自身亦官亦民的双重角色传播洋教施妖、鼓吹民众斗争,这场妖术恐慌持续了半年,在江南地方官府加大查禁妖术谣言的力度后基本绝迹。
五、结语
“传统中国社会的生存经济是农业,这种经济形态所形成的是一种权威式的社会结构,长期在这种社会结构下生活的结果,便模塑成权威性格。”而权威性格中的迷信权力、喜欢用单一的价值评价标准评判人与事物本身、对陌生人不信任且有压抑性的敌意都与妖术恐慌事件普通民众的“权力幻觉”高度契合,在普遍的社会危机中,无权势者才能在混乱中寻求到权力的突破口,从而成了妖术恐慌的无意讹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