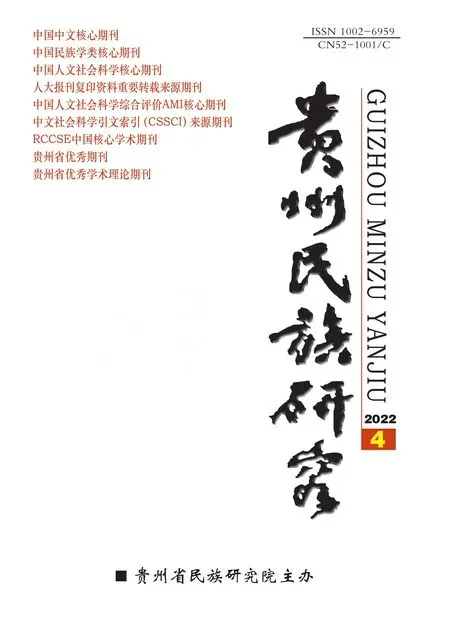清代时调抄刻与民族文化趣尚研究
姬 毓 陈书录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24)
城坊设计作为人为限定的地理空间,在古代社会的城市治理体系中,承载着外部区隔与内部聚合的双重功用,其设计背后往往潜藏着耐人寻味的权力景观。若从较长的历史时间段内还原这种时空场景,可以发现其多呈现出一种偏离初衷的结果,即尽管空间上的畛域分明在特定时间段内实现了多元治理的目的,然而所谓的地理区隔又并非铁板一块,其间亦存着诸多开放性的因子,这就为民族之间的交往埋下伏笔,乃至成为促进民族融合的因素。以清代北京时调抄本为例,因手抄书坊多在京师内城,且内城旗籍民众于清代200余年深受礼乐文化之滋养,故此类时调书坊于抄售之时便不能不对潜在的受众群体有所回应与迎合,并最终在文学的雅俗取舍上透露出某些迥异时俗的特质,擘画出民族文化趣尚不断升降与流动的演进图景。
一、岔曲、马头调的孳乳与清代京师内城唱曲风尚
北京自元明以来历为北方要镇,光绪时人郑观应论北方形势,即以为“京津为往来大道,官商士土,皆荟萃于一途。”可以说,车马交驰、水陆辐辏的区位优势,使得北京自明代起便成为北方时调小曲转输的一大关捩,如“正统十三年戊辰,京师盛唱《妻上夫坟》曲,妇女童幼俱习之”。除市井细民操弦度曲之外,明清京师仕宦人家又多蓄小唱、歌妓。据记载,“京师自宣德顾佐疏后,严禁官妓,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几如西晋太康矣。”另有记载称,康熙年间“京师所聚小唱最多,官府每宴,辄夺其尤者侍酒,以为盛事。”这种唱曲之风至晚清民国依然昌炽,据李家瑞《北平俗曲略》考述,晚清以来北京最为流行的时调曲种即多达30余种。
就现存史料来看,李家瑞所说的这些时调大多以抄刻唱本形式流传下来。蒋寅等人认为“自乾隆年间始,在北京便出现一些专门抄卖各种时兴戏曲、小说和说唱文学唱本的书铺,如百本堂、别埜堂、乐善堂、聚卷堂、耕心堂等”,这种说法与事实大体相符。我们以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俗曲为例,据曾永义等介绍,该馆“论册数有八千余本,论篇题有一万四千八百余目,是目前世界上收藏中国俗文学资料最丰富的地方”。近年来,台北“中研院”又据此编成《俗文学丛刊》,其中明确标志为百本张、聚卷堂、别埜堂等京师书坊所抄录的时调小曲即达80首。有意思的是,尽管李家瑞等人论晚清京师流行曲调时曾详论调名,并极称其种类之丰,然此类手抄唱本中所显示的曲调收录情况却似乎与之相去甚远。以百本张抄本为例,刘半农于民国初年曾于琉璃厂书坊发现百本张抄本俗曲80余包,计有2124种。其中,前6位分别为“昆弋剧本四百六十种,二簧剧本五百七十种,子弟书十四种,马头调二百五十种,岔曲一百二十二种,赶板一百二十五种”。《俗文学丛刊》明确记载为百本张所抄唱本共计68册,其中岔曲35首,马头调22 首,二者叠加起来,几乎也已达到十之八九,至于其他曲调则殊为鲜见。笔者以为,这种文献记载与史料遗存上的反差,实与城市空间下唱本生成模式与民族审美趣尚大有关联。
因清代宗室多由朝廷发放俸禄,故其生活较为优裕,子弟亦通文达艺,多以游冶为能,正所谓“宗室八旗,无贵贱贫富,上下咸以工唱为能事”,而岔曲与马头调即为旗籍民众所熟习之曲。其中,岔曲之产生当在乾隆以前,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其创制云:“文小槎者,外火器营人。曾从征西域及大小金川。奏凯归途,自制马上曲,即今八角鼓中所唱之单弦杂排子及岔曲之祖也。其先本曰‘小槎曲’,减称为‘槎曲’,后讹为‘岔曲’,又曰‘脆唱’,皆相沿之论也。”以为该调乃乾隆年间京师外火器营文小槎所作得胜之曲,因其名中之“槎”与“岔”音近,故以讹传讹为“岔曲”。按,外火器营全名“满洲外火器营”,其前身为康熙三十年(1691) 所设之火器营,营内兵丁均为旗籍子弟。至于火器营之入金川,事又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是年,定边将军温福战死,金川尽没,乾隆帝转授阿桂为定西将军,并“挑派京中健锐营、火器营满兵三千,吉林满兵四千,索伦兵三千,发来以备进剿。”乾隆四十一年(1776),官军“平定金川,逆酋全就俘获”。因此,所谓“文小槎”者,便为此时效命军中之旗籍子弟,而岔曲若由其创制,其时间似应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 至四十一年(1776) 间。
相传岔曲产生之后曾流传于禁中,深受乾隆帝喜爱,《升平署岔曲》记之曰:“高宗喜其腔调,乃命张照等另编曲词,由南府太监歌演。尝于漱芳斋、景琪阁、倦勤斋等处聆之,盖室内均有小戏台,颇便演唱此类杂曲也。”历史上的从征记忆,加之当朝天子的示范效应,故岔曲此后风靡于京师旗籍民众之间。张次溪记晚清京师岔曲“相传嘉、道前,每旗族家庭宴贺,父老多率子弟唱奏,子弟之名,盖本于此”,可见因此调多为旗籍人家所唱述,故此又致有“子弟岔曲”之名。
除岔曲之外,马头调于晚清民国时亦风行于京师之中。马头调之“马头”,实即“码头”,据台湾学者张继光考证,此“码头”泛指水陆码头、旅馆驿站,故马头调特指“流行在交通要冲、旅店馆驿一类场所的曲调”。此调亦于乾隆年间即已出现,李斗《扬州画舫录》记乾隆末叶扬地俗曲,曾言“京舵子、起字调、马头调、南京调之类,传自四方,间亦效之,而鲁斤燕削,迁地不能为良矣”,可知彼时扬州地区即已唱述此调。另据李家瑞《北平俗曲略》考证,马头调向来又分“南马头调”与“北马头调”,嘉庆间人范锴《汉口丛谈》 云:“昔时妓馆竞尚小曲,如满江红、剪剪花、寄生草之类,近日多习燕、齐马头调,兼工弦索”,今《霓裳续谱》《白雪遗音》及傅斯年图书馆所藏马头调当即此种流传在燕、齐等地的马头调。而京师又为马头调于北方传播的要镇之一,道光时人杨懋建《梦华琐簿》云:“京城极重马头调,游侠子弟必习之,硁硁然,龂龂然,几乎与南北曲同其传授。”笔者以为,此类硁硁龂龂、日以自娱的“游侠子弟”大抵多为旗籍民众。马头调于晚清时往往与岔曲、八角鼓等风靡旗籍群体中的时调、曲艺同时搬演。光绪元年(1875) 京师人贾永恩即曾搜集北京时调,汇辑抄成《马头调八角鼓杂曲》,又如晚清公案小说《永庆升平》中亦曾记某外任的京城旗官,也说其“素日所好的是八角鼓儿、琵琶丝弦、马头调”。
二、坊市区隔的边际效应:民族聚合与抄本书坊的策略选择
正如王廷绍《〈霓裳续谱〉序》所言,“京华为四方辐辏之区,凡玩意适观者,皆于是乎聚,曲部其一也”。北京作为明清两代都城,历来为俗曲之渊薮。嘉庆甲戌(1813) 间所刻《都门竹枝词》亦曾盛称京中“到处歌声声不绝,满街齐唱绣荷包”,也足见彼时京师流行之时调小曲极为驳杂,尚还流行绣荷包诸班杂曲。然而,何以在今日所存清代北京手抄唱本中,岔曲、马头调能独得百本张等抄本书坊的青睐?这与彼时北京城市空间内的民族融聚以及不同书坊由此而选择的销售策略关联甚密。
北京城坊自永乐年间建成以来,即分为内外二城,二者分野大体以永乐十八年(1420) 所修内城九门为限,门内为内城,门外为外城。清初,朝廷多于各府、州、县施行分住之策,以便旗人与民人“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而京师“五方杂处,实繁有徒,混迹藏奸较之外省更易,稽查保甲较之外省亦倍难”,故较之他地早得风气之先,于顺治元年(1644) 即在内外城推行分住政策。关于这一时期内城各旗之分布,《皇朝通典》言之甚详:
顺治元年,定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于京师内城分置,以为拱卫。其方位,镶黄、正黄旗居北方,正白、镶白旗居东方,正红、镶红旗居西方,正蓝、镶蓝旗居南方。左翼自北而东,自东而南,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右翼自北而西,自西而南,正黄旗在徳胜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成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以寓制胜之意。
这种井然分住的城坊态势在清初百余年间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均势。康熙间人余缙言及于此,曾云:“皇上轸念民情,即都城内外,自满汉分居以后,军民住址,未尝侵踰尺寸。”尽管此后交往日深,往往有内城民众因各种原因迁至外城,如乾隆十八年(1753),“在外城居住者,已四百余家,奉旨严饬禁止”。然此类外迁之民于当时尚属零星,故时人吴长元在述及京师内城建制时,也仍然认为“内城所编八旗居址,界限甚清”。此后内城人口不断增长,至道光以后,多有因困于生计而变卖祖业移至外城者,乃至朝廷亦“以生齿日繁,移居逾众,遂弛此禁”,然而这种局部的松动却并未在根本上动摇京师城坊中固有的群聚态势,其分城而居的历史惯性得以一直持续至清末民初。
曾大兴先生在论及文学的区域性时,曾以为:“区域内部的文化特征往往是异质的,尤其是那种由于行政或者其他原因而经常变动、很难维持长期稳定的区域,其文化特征的异质性更强。”事实上,这种区域文化的异质性在城市空间上同样适用。以戏园为例,尽管时人盛赞“京师之戏剧甲于天下”,然此类张筵设戏的冶游景象多发生在民人聚居的外城,清代,朝廷唯恐旗籍民众耽于逸乐,于内城开设戏园一事上长期保持着审慎的姿态。康熙十年(1671),清廷即议准“京师内城,不许开设戏馆,永行禁止。城外戏馆,如有恶棍藉端生事,该司坊官察拿治罪”,对北京内外城之唱戏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种悬为厉禁的政策此后时松时紧,乾隆时已偶有戏园出现,然而据震钧《天咫偶闻》载:“京师内城,旧亦有戏园。嘉庆初以言官之请,奉旨停止,今无知者矣。”类似的苗头往往初现踪迹即在持续的高压下趋于消歇。在这种情况下,内城民众虽有听戏之需要,然因朝廷的弹压政策,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找其他消闲形式进行弥补,这种替代品便是各类茶馆。嘉庆时人得硕亭《草珠一串》记云:“内城旗员,于差使完后,便易便服,约朋友茶馆闲谈,此风由来久矣。”此类茶馆中虽缺少戏曲,却转以岔曲、十不闲等各类曲艺杂耍称盛。杨懋建《梦华琐簿》曰:“内城无戏园,但设茶社,名曰杂耍馆,唱清音小曲、打八角鼓、十不闲以为笑乐”,其所谓“八角鼓”者,即以八角鼓为主要伴奏乐器的岔曲等时调曲艺。而除茶馆等固定场所外,当时于内城还出现一种名为“子弟班”的走票形式。据《旧京琐记》记载,“子弟班者,所唱为八角鼓、快书、岔曲、单弦之类”,民国“逆旅过客”所撰《都市丛谈》言及此类票房中之岔曲,也曾说道:
斯曲为八旗土产,向无卖钱之说,演者多系贵胄皇族,故称“子弟”,如欲演唱,必须托人以全帖相邀,至期先在某处聚齐,专候本家儿迎请,应当茶水不扰,唱完各自回家。后因带灯往返不便,始由请者预备晚饭,又兼旗人无所事事,借此可以遣性怡情。不想生计艰难,多有归入生意者。是以汉人学演是艺,不得谓之正宗,虽隔一道城墙,而所唱韵调决不一样,如“南、北板大鼓”、码头调,都有一定准规矩;又如西城有琴腔,而东城至今无此调;至到折活中《开山真逛》《白沟河》,东、西城亦迥乎不同。
由此段可以推知,此类岔曲之流行,起初多是因内城无戏园,民众互相燕集唱和,以作闲居遣兴之助。而据作者所言,岔曲既为旗下“土产”,故外城民众少有能染指此技者,且即便同处内城,因坊市区划所导致的人群区隔,亦使得东西两城在岔曲细目上呈现出泾渭分明的差别。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的北京内城旗籍群体中,岔曲、马头调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内城禁演后的娱乐空白,成为旗籍民众最为喜闻乐见的唱述模式。
在了解这种分城而居的聚合背景后,我们再回看抄本书坊的经营场域,其中的销售逻辑便不难寻绎了。以百本张为例,其本店在西直门内高井胡同,乾隆年间即已营业。据署名“清逸”的《百本张之子弟书》所考,其初代坊主“系汉军正白旗之旗兵,生于乾隆初年……后始售各子弟书抄本,在东西庙及厂甸等处摆摊。”此处之“东西庙”,即京师东西两城隆福寺、护国寺庙会,而隆福寺、护国寺及其本店所在的高井胡同等均位于内城之中。尤其是隆福寺,乾隆十年(1745)时,清廷曾“以朝阳门内隆福寺前官房一所为火器营公署”。而正如上文所言,岔曲之产生本又有来自火器营中兵士一说。因此,对于百本张等抄本书坊来说,其书坊既然居内城之中,且家族亦为旗籍,便不能不在经营策略上就近考虑内城民众在阅读风尚上的特殊性。进一步而言,既然内城少有戏园,且旗籍人家又多以岔曲、马头调为主要娱乐,故其抄售戏曲及岔曲、马头调唱本,一方面以文本形式纾解了内城不便观戏的娱乐窘境,另一方面又对症下药,迎合了内城民众在时调小曲上更为私人化的消费需求。
相较内城百本张等书坊多以抄本作为经营业务,外城书坊所售唱本则多为刻本。这些书坊大都集中于今南柳巷及琉璃厂一带,据张次溪先生介绍,“其在南柳巷者,有聚魁堂、经义堂、四宝斋、起升山房、绿野山房、文盛堂、得月山房、文名堂、文萃堂、松月堂等。其在打磨厂者,有锦文堂、致文堂、宝文堂、泰山堂、宝文堂、老二酉堂等”,其中又以宝文堂、致文堂、泰山堂、松月山房等刻印者居多。然与手抄书坊多面向内城旗籍民众不同,外城书坊所面向的群体则显然是以外城民众为主。今《俗文学丛刊》中所存此类书坊的木刻唱本甚众,然除宝文堂等个别书坊偶有刊印岔曲、马头调外,余皆以牌子曲及靠山调、天津调、叹十声等曲调为主。造成这种仅隔一垣而彼此销售策略截然两端的原因无他,在城坊区隔的地理空间下,清代京师的唱本书坊于经营之初便须对自身潜在的读者群体有一精准的体认,而结合自身的经营场域及周边城坊的聚居特点,内外城书坊便不可避免地以就近方式划定读者范围,以致在唱本曲调内容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导演出了两种面目迥异的消费导向。
三、群体的选择:民族融合视野下的岔曲雅化现象
由城坊区隔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表现于唱本曲调的选择上,在内容书写尤其是雅俗文化的审美选择上亦呈现出明显的特异性。以岔曲为例,满族学者溥叔明称其“大要出入于诗词之间,实近代俗曲之最雅者”。齐如山先生亦认为其“流传禁中,又多制颂圣之曲,逢迎人主之意,体制日趋于雅,风花雪月之词,登山临水之作,蔚然并兴”,在典则俊雅、高情逸态上与一般时调崇尚俗艳的浇薄之气截然不同。
这种差异在傅斯年图书馆藏抄本岔曲上表现得尤为醒目。今傅斯年图书馆藏岔曲极多,种类亦极为丰富,正所谓“春夏秋冬,风花雪月,才子佳人,渔樵耕读,以及市声风俗,琴棋书画,无所不有。”而在该馆所藏岔曲中,又尤以小岔最为隽永,甚与齐如山“日趋于雅”的评价相合。我们以抄本《一阵阵和风》 《秋天到了》《雪》为例:
一阵阵和风,一丝丝细雨蒙蒙,一湾湾绿水流过画桥东,一枝枝翠柳丛中杏花红。一处处酒店留客饮,一行行游春的浪子穿芳径,一声声燕语莺啼动人情。
——抄本《一阵阵和风》
秋天儿到了,秋景儿难熬。光皎皎一轮秋月挂松梢,秋风儿摆动铁马儿摇。秋气儿侵入珠泪双抛,梧桐树上秋秋蝉儿噪,看秋人儿慢闪秋波把秋景儿睄。
——抄本《秋天到了》
梨花成堆,粉映山围,剪碎鹅毛半空飞,乌鸦带粉把朝回。寻食寒雀空中舞,见孟浩然访友归来醺醺醉,又则见小琴童在驴儿后,肩头上横担一枝梅。
——百本张抄本《雪》
就铺陈艺术而论,以上三曲分写春、秋、冬景,彼此手段却又各有侧重。尤其是《雪》,则化用孟浩然踏雪寻梅之典,并以骑驴赏雪、肩头横梅骤然作结,在瞬间美感的营造上甚得严沧浪“透彻玲珑,不可凑泊”之神韵。此类崇雅黜浮的意象体系与审美倾向无疑表明,岔曲无论是在作者还是读者群体上均是极度文人化的,其曲词中典则俊雅的生活况味非但为一般村夫俗子所不及,而且更与彼时落入青楼淫亵一流的时调小曲判若天渊。那么,为何向以控弦驱策为长技的旗籍民众,其所擅之曲竟能如此清丽雅洁?这就涉及了清代的民族融合尤其是京师内城民众在文化趣尚上的升降与流动问题。
事实上,在历朝帝王的右文举措下,清廷于旗籍民众之教育极为重视,积极设立各类官学,并延请儒师教习弓马诗书。如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廷即从国子监祭酒薛所蕴之请,命旗籍子弟入学,“俾文武兼资,以储实用。”雍正年间,又设立宗学,除修习文艺、骑射外,每年还须进行考绩。这一尚武修文的策略在乾隆朝达至顶峰,时人程晋芳便不无自矜道:“我国家承平百四十年,所以教习八旗者,文武并用,盖古法也。”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民族中亦广泛存在,如清初改土归流后,曾于西南贵州等地广泛设置义学、书院,“因义学适应民族地区,从而成为贵州民族地区办学的主要形式”。这种民族教育的铺展,又反哺到民族文学,如清代水族文学之兴起,便与义学、私塾之设立不无关系,有学者即认为:“清代雍正年间,朝廷实行改土归流,农耕文化得到推进,水族地区经济取得相应的发展,由此义学和私塾逐步兴起,汉文化教育推动了水族书面文学的出现。”而随着文化教育上的侧重,原本以弓马娴熟著称的旗籍民众在文化素养上亦得以不断提高。以北京地区为例,嘉庆年间,铁保所编之《熙朝雅颂集》中即已辑有旗籍诗家500余人,同治间人李元度论及于此,更是盛称“八旗士大夫能诗者尤众”,其诗书礼乐之盛可见一斑。
受清廷右文政策及自身相较优渥的物质生活影响,京师内城人家亦多以治文为业,对于子弟教育慎重其事。今傅斯年图书馆藏抄本岔曲中,便有“诗词歌赋,必须要广览多读,五经六易贵如珠,十行锦绣文章要熟”、“折有灰堆,唱曲儿算不了能为,怎似君十年窗下,几度秋闱,方能够名标蕊榜,得中高魁”一类劝学曲词。而某些岔曲中,亦往往隐露出群体性的知识水平,如《水秀山青》等曲:
水秀山青,殿阁楼亭,碧沉沉浮浪清叠管弦声,一处处酒船儿来往恁意行。佳人慢摇花桨橹,一个个行令猜拳吟诗歌诵,吟的是“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百本张抄本《水秀山青》
可叹三春,万鸟投林,桃红柳绿雨纷纷,杏花村牧童遥指唤行人,紫竹苍松芳草深满山坡,奇花异草观不尽,独有一处,茅庐内诸葛先生把诗吟。
——抄本《可叹三春》
以上二曲中,或直接引用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诗,或在曲词与意境上化用前人之作,如“桃红柳绿雨纷纷,杏花村牧童遥指唤行人”之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等,均为诗歌与时调在雅俗嫁接上的一种尝试。至于其师法,又颇有脱胎换骨之妙,而非以驱策典籍、堆砌文字等拙劣手段刻意为之。
此类化用古典诗词之时调于明清以来殊为鲜见。晚明冯梦龙在编辑《山歌》 《挂枝儿》之余,曾照仿山歌体例改编《千家诗》,自拟《夹竹桃顶针千家诗山歌》百余首。冯氏拟山歌中颇有与晚清岔曲声气相通者,如《牧童遥指》 曲词云:“妆台前插柳是清明,二八娇娘去踏青。寻芳拾翠,千人万人,奴归独自,迷却路程。日落西山,不知啰哩是奴家里,牧童遥指杏花村”,便与岔曲《可叹三春》类似。冯梦龙所拟山歌,于后世毁誉参半,如刘大杰即批驳其“终究由于文人的拟作,所以缺少泼剌拙朴的气息”。具体到此类岔曲是否受前人影响,我们自然不得而知,然就彼此在文人拟作意蕴上的契合来看,其欣赏群体也必与冯梦龙所处的晚明接近,为具有一定文艺修养的底层士大夫阶层。这种崇雅祛俗的读者群体的形成,实则正源于清代以来旗籍民众文化素养的结构性攀升,而城坊分住所带来的空间区隔以及抄本书坊因地制宜所作出的选择策略,则使这种审美特异性被选择性放大,表现得尤为彰著。
四、结语
任何载体样式所承担的都是媒介角色,其制造文本的同时,亦是对读者需求正向回馈的过程。从清代北京地区时调抄刻来看,最终,在这种选择与被选择的反复拉锯中,时调文本得以抄本形式流传下来,继而隐现出雅尚斯文的审美趣味,至于其背后因民族融合时代所裹挟而来的交流记忆,亦由此而渐渐浮出水面。
我们通过对京师手抄书坊于特殊曲调抄写偏尚上的考索,在爬梳出彼时某些不为人知的群体心理与坊间书肆的营销款曲之外,亦为今人解读清代京师民族文化趣尚的流动,乃至在文本遮蔽下考量这种民族融合因素在文学史上的投射力度提供了更为细密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