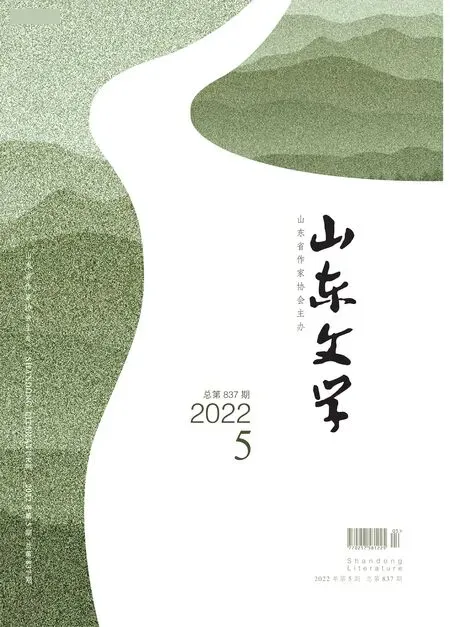和童真岁月说说话
美 桦
与八只眼的灶王爷赛跑
母亲卷着袖子,从热腾腾的豆腐口袋上扬起头来,眼睛里是掩饰不住的欢喜。灶堂里熊熊的火苗,在母亲的脸上煎出了一层淡淡的红晕,让她柔美的笑容如三月里的桃花般灿烂。
又是一年稻谷丰收季。山上的鸣蝉在雨露的滋润下嗓音日渐清亮,它们在稠密的阳光下呼朋引伴,密密匝匝的蝉声卷席而来,纷纷扬扬跌落在山谷里。秋风应和着鸣蝉的吟唱,变得矜持而轻柔,吹蓝了天空,吹清了小河,吹出了一地的金黄。才几天时间,时光老人就用稻穗在原野上铺上金黄的毯子,厚厚的,沉甸甸的,黏黏的暖色调让人心醉。一大早,父亲就带着一拨乡亲到田里去了。开镰割谷,机器轰鸣,脱粒开仓,搬运转送,捆草扎把,不是三两个人就能完成的。寨子里早就有了不成文的规矩,今天你家,明天我家,大家相互帮衬,把田里的金黄的稻谷搬到家里去。两个精壮的汉子,前躬后仰,合力摇动打谷机的把手,咆哮出一地丰收时节的酣畅。
母亲和三婶在家里张罗饭食。母亲忙得脚不沾地,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母亲必须在短暂的时间内,用乡间丰盛的菜肴,在乡亲们面前晾晒一个农家妇女的脸面。不得不说,那锅又白又嫩的豆腐,就是晌午待客最好的佳肴。
此时,那只热气腾腾的豆腐的口袋,犹如一个白白胖胖的玩具,懒洋洋地躺在筲箕上,任由母亲在它身上随意地捏搓,挤压。白白的豆浆,就在氤氲的热气中,汩汩地流在下面的盆子里。有这么好玩的游戏,我们自然是要参与进来的。
我和五岁的弟弟,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昨天晚上落了雨,院子里汪了几摊积水。我们光着脚丫在积水里踩过来,踩过去,试图找到鸭子戏水的感觉。脚下的泥浆伴随着我们的笑声,溅湿了我们的衣裤。几绺个性分明的头发,懒洋洋地搭在我们污浊的脸上,挑衅着母亲的耐心。母亲尖锐的叱骂声,尽管比平时严厉了许多,但震慑作用已经大打折扣。这一天母亲很忙,她没有闲暇用黄荆条来安慰我们的屁股,更没有精力用手扯住我们的耳朵,再笑眯眯地问我们听不听话。
“妈,我来帮你!”
为了证实自己的诚意,我还特意将一双黑乎乎的手,在屁股上狠狠地擦了两下。弟弟没有说话,却飞快地把流到嘴唇上的鼻涕吸了回去,伸出脏兮兮的手随时准备支援。
“滚一边去,我的小祖宗!”母亲凶巴巴地吼了一声,把身子横过来,以防我们过来捣乱。
我们往后退了一步,蹲在盆子边,对筲箕里那只胖胖的娃娃虎视眈眈。
天空早让秋风擦得干干净净,蓝得就像一面深邃的镜子。偶尔有小鸟从上面掠过,那也是悄悄的,生怕惊扰了它的宁静。秋天的太阳很温柔,金色的阳光越过时间的墙垛和门扇,慷慨地筛满了整个院子,渲染着秋色浸润过的富丽和辉煌。
父亲他们回来吃过早饭,踏着日渐温柔的阳光下田去了。院子里很安静。那只名叫二黑的狗,把它吊儿郎当的舌头收敛起来,立着耳朵,专注地看着母亲,似乎从母亲快速翻动的手上,读懂了女主人内心的欢娱。家里那一群鸡,悠闲地在阳光下觅食。那只色彩艳丽的公鸡,用嘴壳在地上虚张声势,咯咯咯地叫声,卖力地向两只小母鸡献着殷勤。
此时以我8岁的心智,确实有很多问题在脑子里萦绕。那白白的豆腐,怎么这个时候全是水呢?
“妈,这豆腐……”
母亲满脸惊愕,停止了手上的活儿,用手指着我,吼道:“不许说出来!”
母亲一脸的嗔怒。
我知道母亲的潜台词。母亲不止一次对我们说过,饭可以乱吃,话不能喳起嘴乱说!关于乡下一些忌口的话,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母亲经常会一本正经地教导我们。比如这个时候,我下半句话就不能说出来。果然,母亲笑了一下,说:“只要你说出来,我不把你嘴撕烂才怪!”
母亲严厉的目光中有几分温柔和无奈,更多的是女性的端庄与妥帖。在我的印象里,老一辈有很多禁忌。比如,做米酒,忌说酸;做豆瓣,忌说馊;腌腊肉,忌说臭……总之,那最糟糕的结果,是不能事先说出来的。
年前,母亲把剩下的高粱、玉米、小麦煮熟,拌上酒曲,用一个盆子盛着,扒开楼上的一堆糠,把盆子放进去等着慢慢发酵。两天以后,屋子里酒香四溢,那特殊的香味儿,从四面八方扑过来,勾引着我们的馋虫。
我和弟弟满嘴的唾液,就像汩汩的河水喷薄而出。弟弟显然比我更着急,已经跑在我的前面,飞快地扒开那堆糠,露出了酒香四溢的盆子。只要父母没在跟前,我就会端出当家长的架式,对弟弟的冒失行为加以管束。可是这个时候是不起作用的。弟弟已经掀开盆子上的饭帕,折了两根小棍儿,拨了一坨在嘴里。弟弟嚼了两口,面带苦色,哇哇往外吐。
“呸,酸的!”
弟弟边吐边说,把手里的棍子丢出老远,背着他那双短粗的手,气呼呼地下楼去了。不仅如此,在母亲回来的时候,弟弟就迫不及待地向母亲报告了这一重大发现。
母亲一下愣住了,俊俏的脸上满是惊骇。
父亲一看这种情形就知道不妙。赶紧过来打圆场:“不要喳起嘴巴乱说!米酒发酵有个过程,时辰一到自然就甜了嘛!”
父亲说这话自然有他的道理。寨子里有一个本家的婶娘,就因为把一锅米酒做坏,找了一根绳子,把自己悬在了梁上。造成这一悲剧,到底有没有人说了忌口的话,我们不知道。只是我们跟着大人去料理后事,吃了丧饭回来,我跟父亲探讨起了这个问题:坏了就做坏了呗,她怎么会想不开呢?
父亲铁青着脸,叹了几口气,说:“你懂个屁!粮食这么金贵,哪个舍得随便抛撒?”
磨豆腐这事儿,多少有些神秘。泡好的黄豆磨成浆,加热,倒进豆腐口袋里挤压、过滤,再把豆汁烧开点上熟石膏水,就变成了鲜嫩的豆花。要是火候或石膏掌握不好,就会变成一锅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老是认为母亲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不就是豆腐嘛,即便是一锅汤,又有啥稀奇的呢?事实上,我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这一天母亲如愿以偿,她的豆腐做得很成功。
母亲做出来的豆腐,确实变不出更多的花样。母亲用嫩嫩的豆花,加香油,辣椒,豆瓣,姜葱,做了一盆红白相间的红油豆花;一盆榨好的老豆腐,配上一个熟油辣椒蘸水,就成了一道人人喜爱的最为实惠的菜肴;用筲箕把豆汁慢慢滤掉,压成豆腐,母亲用它做成了麻辣鲜香的麻婆豆腐。要是时间允许的话,母亲可能还会把豆腐煎黄,再放辣蒜一炒,那扑鼻的浓香就更为解馋。当然,剩下的豆腐再放上几天,就可以做成豆腐干和臭豆腐了。
家里炖了老火腿,用鲜肉做了小炒,用腊肉烀的四季豆做成汤,炒了两个新鲜时蔬,拌了份凉拌菜,再配上这几道豆腐做的菜肴,成就了这一桌丰盛的农家菜。来帮忙的乡亲吃得呼儿嗨哟,他们发自内心的赞誉,让母亲在乐呵呵的自我谴责中,收获了一个农村妇女体面的自尊。
秋天的太阳柔柔地把这一页日历翻过去了。对于这顿豆腐宴,更多的细节我没有放在心上。但是,第二天午后,弟弟说到这个话题,却让我的心悬了起来。
父亲一早去别家帮忙去了。蓝蓝的天幕下,母亲忙进忙出,把稻谷晾晒在门前的晒坝上。沐浴着如酥的阳光,弟弟和我一起笨拙地给母亲打着下手。
弟弟把鼻子里的鼻涕吸了回去,说:“妈妈,乱说话就做不成豆腐了吗?”
“对,是这样的。”
“乱说了,灶王爷要割舌头吗?”
“嗯,那肯定的。”
“灶王爷长了八只眼睛,恶得很咹?”
“那肯定是这样的!”母亲忙着手里的活,嘴里却没有闲着。
“啊,那我哥哥咋办?”
“你哥哥怎么啦?”
“哥哥说……哥哥……说……”我成天用袖子擦鼻涕的弟弟,已经学会了用悬念。他知道把这个秘密说出来的严重后果,他在用眼睛的余光,希望从妈妈的脸上找到破解这道难题的密码。
“说嘛,你哥哥说什么了?”
妈妈停止了手上的活,笑眯眯的目光抚摸着弟弟那头稀疏的黄发。妈妈这一招特别管用,很多时候母亲就是这样麻痹弟弟,轻而易举就从弟弟嘴里拿获我调皮捣蛋的铁证。
弟弟停顿了一下,说:“哥哥说,你的豆腐怎么全是汤,会变馊的!”
弟弟还说:“妈妈,你不是说,做豆腐不许说这样的话吗,怎么没有变馊呢?”
弟弟还没把后面的话说完,我撒腿就跑。午后阳光明媚,我从稠密的阳光中突围出来,猴子般爬上门前那高高的桑树,在上面扮着鬼脸。
就在昨天中午,我干了一件非常冒失的事。我趁着母亲出去晾豆腐口袋的时候,我不仅说了那句让母亲最忌讳的话,还用筷子在那一大盆汤里搅了好几下。
对长了八只眼睛的灶王爷,我是不怕的。我不只一次测算过,从家里跑出来,再爬上这棵树,不过眨眼工夫。年迈的灶王爷,肯定不是我的对手。但我早就领教过妈妈手中黄荆条子的厉害,那东西在妈妈手里是说落下来就会落下来的。
可是,这一次我却错误地预判了事态的严重性。母亲什么也没说,她根本就没有搭理我,用篮子背着弟弟,准备到菜园地里扯菜。弟弟站在篮子里,一手扶着篮筐,笑眯眯地对我说:
“哥哥,你快点下来!”
对于弟弟的天真,我有自己的原则和戒备。天很蓝,太阳依旧灿烂,几只鸟雀吵着叫着在我的头顶撒着欢。稀疏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簌簌筛落下来,鼓瑟吹箫,暗兵涌动。我不能就这么冒冒失失地下来,我趴在树杈上,用我的经验判断事态发展的走向。
见我还没有动静,弟弟不住地向我招手:“妈妈说,八只眼睛的灶王爷睡着了,他啥都没听见……”
在床上午休的狗
弟弟唬着脸让我回去的时候,我的头发一下立了起来。
虽然是隆冬时节,南国的太阳一点也不吝啬。风很张狂,大多数聚集在屋檐上,树梢上,张牙舞爪地抱团吼叫着,撕咬着,抓扯着。只有一小部分,鬼鬼祟祟地在地上闲逛,顺便把我们炸的火炮碎屑和瓜子皮清理得一干二净。
寨子里依稀响起了爆竹的声音。不用说,那是早晨吃了汤圆的孩子,穿上干净的衣服,揣着花生瓜子和为数不多的几颗糖果,用嘻嘻哈哈的笑声作为铺垫的杰作。他们将整挂鞭炮拆散,偶尔才舍得点一个,但营造出来的氛围,已经为乡下的年味儿下足了料。
弟弟已经是第三次来请我了。母亲经常揪着我们的耳朵,对我们说凡事只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母亲虽然不会对我们讲更多的大道理,但如果超越了这个底线,那是会受到惩戒的。家里那根黄荆条子,长短粗细没有多大变化,但依然有威慑作用。弟弟跟我说这话的时候,还特意加重了语气,学着母亲的样子,说如果我再不回去,妈妈就会背黄荆条来请我。5岁的弟弟,已经把母亲的意思表达得很完整,让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我已经多次尝试过那根黄荆条子的厉害,可是这个时候,我确实走不开。我的脸上还残留着几分睡意,正和大我两个月的堂哥,趴在桌上打扑克。我们只用两门牌,仍然打得比大人还要投入。我次次占上风,这让堂哥非常不爽,非要和我一决高下。
伯父在很远的矿上当工人,差不多每年到了年底才回家过春节。每次回来他都会给我们几个小孩,一人3只气球,20个鞭炮,再发上一角两角的压岁钱,让我们在欢天喜地中迎接年的到来。
伯父一回来,远近的亲戚都会聚在他家里,除了家长里短的龙门阵,很多时候他们都用扑克牌,打发夜里清冷的时光。这种时候,小孩子是没有机会上场的。我们手痒痒,心也痒痒,也只能望牌生叹。
对几个小孩拼命地往伯父家跑,母亲老是不屑。各人有自己的家,没事儿,到别家疯什么?无外乎是贪图那三两颗糖果,嗑半把瓜子。母亲老在我们面前唠唠叨叨,小孩子家不知高矮,一个个眼睛饿捞捞的,一上桌抢碗夺筷,让人笑话。对于这一点我有足够的自觉,不像我5岁的弟弟,个头儿才有桌子高,吃饭的时候生怕夹不到,老是往长辈身上窜。要是没有人及时制止,弟弟老是嫌自己的手不够长,一不小心就会爬上桌子去。弟弟的耳朵让母亲揪过好几次,但没有像母亲所期待的那样,迅速长出好记性,下一次说不定好了伤疤忘了痛,不知不觉又会爬到桌子上去。
年初一,更是忌讳到别人家去的。母亲不止一次告诫过我们,老祖宗早就定下了规矩,初一到别家去,会把财带给别人的。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们虽然不敢回嘴,但心里是一万个不服气。想想也是,以自己8岁的身子,两手空空,财在哪儿,又怎么能带得到别家去呢?
这个时候,寨子里的人已经吃过汤圆,穿上过年过节才穿的新衣裳,包里装上瓜子花生,欢欢喜喜集中到生产队的晒场上。
隆冬还没有过去,但南高原的天空,早已让焦躁的风擦洗得干干净净。太阳有些矜持,瑟缩着身子,羞羞答答地从东边的山头露出脸来,慷慨地把阳光铺洒在寨子里。生产队大大的晒场,此时成了乡亲们最为理想的欢乐地。打牌的,嗑瓜子的,摆龙门阵的,纳鞋底的,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用乡下人的狂野,喧嚣着这个传统节日的热闹。
当然也有闲不住的,扳手腕,拧扁担,举石磨,场上的人逼红了脸,看稀奇的人瞪大了眼睛,都屏住呼吸,用时间的厚度来裁决最后的输赢。无论是上场决战的,还是旁边抱膀子的,吆喝的,尖叫的,坏笑的,没有谁是闲人。输赢是次要的,开心最为重要。乡下人有的是憨力,春节期间吃了几天白米饭,在肥猪肉的滋润下,正需要有地方把力气宣泄出来。
青年男女最高兴的是打磨担秋。晒场边的空地上,年前民兵连长就带人竖起一根杆子,杆子上用木屑穿斗着两根长长的秋杆。一边三四个青年男女,呼的飞过去,再呼的飞过来,腾云驾雾一般,好不潇洒。小孩子当然不甘示弱,瞅住空当,从大人的胯缝下钻出来,死死地抱住秋杆,在大人的叱骂和尖叫声中,寻找飞起来的感觉。
可是,这么热闹的地方,我还不能去。
年前母亲就给我做了一身新衣服,此时还好好地躺在床上。我的个头儿明显长高,此时穿在身上的补巴衣服又短又小,裤子下面露出一长截光溜溜的脚杆,看上去非常的寒碜。年初一穿着这身补巴衣服,别人会笑话。别人一笑话,妈妈就会生气。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不怕妈妈用黄荆条子抽我屁股,也不怕妈妈掉眼泪,就怕妈妈不吃饭。妈妈要是生气不吃饭,爸爸就会很焦躁,经常胡子拉碴地转出来转出去。父亲把那几分彪悍小心翼翼地收敛起来,犹如一头被抽掉脊梁的狮子,时时发出无奈的咆哮。家里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随便一颗火星,就会发出让大地震颤的恐怖。要是年初一妈妈生起气来,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早晨天气冷,蛰伏在夜里的风显得很安静。吃过早饭,睡梦中醒过来的风就开始蠢蠢欲动。风很轻,略略带着几分的寒意。这时候的风虽然是试探性的,却隐隐约约裹挟着悦耳的音乐。不用说,这是寨子里有人闲不住,把家里的收音机也抱到晒场上去了。他们备足了干电池,把音量开到最大,让悠扬的音乐尽可能惠及寨子里的每一个角落。要是往常,收音机旁边肯定立着很多耳朵,陶醉在音乐的世界里。可是今天不一样,早有人带来一管竹笛,欢快嘹亮的笛声,招来一群男男女女,手牵手跳起彝家的蹢脚舞来。扭腰、摆臀、拧胯、踢腿、跺脚、击掌、甩手、转身,一气呵成;笑声、叫声、吼声、跺脚声、欢呼声,让寨子里的每一缕阳光都兴奋着,沸腾着。就连蹲在收音机旁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到场子里踏着笛音跳动起来。
不过今天的蹢脚舞,不像平日那样绵长,往往人齐了就会草草收场。晒场上腾起的烟尘,影响大家的心情不说,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晚上通宵达旦有的是时间,哪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上面。
温暖的阳光,翻晒着乡亲们的好心情。一年苦到头,天大的事儿,今天也要放下来,不就是为了寻开心吗。那边拔河比赛的笑声还没有消停下去,这边老公公背儿媳妇的比赛开始了。临近两个生产队,每队出十男十女,由男人把女人背过去再返回来,用时最短的为胜。在嬉笑声呐喊声尖叫声中,赛场上憨态百出,往往男人背着女人在场上飞跑,小孩儿在后面提着裤子,生怕妈妈让人背了去,在震天的笑声中,释放一年辛勤劳作的闲适。当然,还有说书的,唱山歌的,对野调子的,怡然自得,整个寨子里都弥散着喜悦,让乡下的年味儿愈加粘稠。
音乐悠悠扬扬的传过来,撩拨着8岁少年的心事。
堂哥不住地催促我赶紧出牌,我的心思却不在这上面。我得想办法尽快脱身,还得想办法不让母亲生气。
往天,我也来伯父家和堂哥打扑克。但都是午后,因为这个时候伯父要午休,这是一个难得的空当。对于伯父午休这个嗜好,我们脑子里有成百上千个问号,乱麻一样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明明就是睡瞌睡,咋就午休了?明明在家里睡觉,为啥偏偏叫午休?夜里也要睡瞌睡,怎么不叫夜休?最重要的是,瞌睡不是晚上睡的吗,中午躺在床上睡大觉,那不是堕落报应的懒汉吗?
对于这样的疑问,我曾经跟父亲做过探讨。父亲愣了一下,笑呵呵地骂道:“你几个龟儿子!哪里是享这种福的命?”对于什么命,才可以天天午休,我确实没有过多地深究。但这个话题,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了很久。
此时,堂哥和我的战火越演越烈。不仅仅是这样,我们旁边又多了几颗小脑袋,包括我的弟弟。弟弟不知道什么是输赢,但凑热闹是孩子们的天分,显然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只有我,心里忐忑不安。
母亲一再告诫,年初一不能到别人家去。我脑子里飞快地转动着,紧张地做着摆脱眼前困境的各种假设。看着周围那一圈多出来的脑袋,我的脑海里冒出了这样一个念头:
要是有人到我家,把财带回去,母亲肯定高兴!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绝好的主意。
“不打了,我要回去看看!”
“出牌!”堂哥不停地催促着我。
“我要回去。我要去看看我家的狗!”
“你家狗怎么啦?”
“嘿,那死不剩的,学得一身坏脾气……”
我把手上的牌扔在桌上,随口说着回家的理由。
啥——?
周围的几个小脑袋全凑过来,惊奇的眼睛里飞溅出一个个热辣辣的问号。他们确实没有听说过这么日怪的事,都嚷着要跟我回去看看。
大家一哄而散。在小伙伴们的欢呼雀跃中,我的脑海里渐渐清晰出这样一幅场景:几个孩子一进门,首先扫荡了我家桌上的瓜子花生,把桌上那盆糖果不住地往包里塞。而母亲呢,笑眯眯地在旁边站着,要他们慢点儿,不要把东西弄撒了……
每年都是这样,年初一吃过早饭,父亲都会带着狗去给爷爷奶奶的坟头压点纸,然后带我们到生产队的晒场上去。这个时候,只有母亲在家里收拾碗筷。为了保险起见,我懒洋洋地跟在小伙伴们的后面。可是,我恰恰想错了。小伙伴们没有洗劫桌上的花生瓜子,而是直接扑进房间里,把床上的被子枕头掀了个底朝天。年前母亲才给我缝制的新衣服也没有幸免,让他们随手扔在了床角。
这么多小伙伴来我家,母亲果然没有责怪。母亲一直用笑眯眯的表情,保持着一个女主人的宽容与厚道。但孩子们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她大吃一惊。作为一个长辈,她不能容忍孩子这样胡来。
“嗨,你们在找什么呢?”
“你家的狗。”
“狗……怎么会在床上呢?”
“你家的狗,不是要在床上午休吗?骗子——”
“骗子——!”
金黄的阳光透过窗户,簌簌地落在床前,屋子里满是凝重的呼吸。就在小伙伴们脱口骂骗子的时候,不仅我笑了,连母亲也忍不住笑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