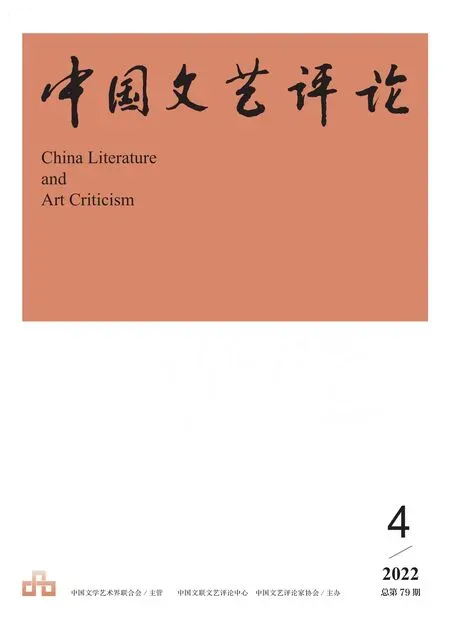“人能弘道”:中国诗教传统与文化特质
■ 董宇宇
一、“道弘人”与“人弘道”:文明比较中的诗教及其历史
中国诗教传统的形成与意义,需要在比较诗学中直观地呈现出来。古代中国、希腊、印度的诗学体系是东西方诗学的三大源头,西方诗学占据了现代理论界的主导地位,然而从古至今的诗教传统可谓中华特色。究其原因,可以从中华文明具有“人能弘道”的特质,而其他文明更多是“道弘人”的理路进行分析。
西方“两希传统”的另一半即希伯来一神教。进入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成为神学基础,其实质是把“理式”偷换为“上帝”,追求更绝对的外在超越。普洛丁、奥古斯丁、阿奎那等认为,世俗是不真实的,世俗文艺只是社会生活的虚构性模仿,用以满足人的好奇心和哀怜癖;只有宗教才能通向永恒,模仿这一永恒才是美善的,但仍然只是模仿。
综上,无论是追求超验的“理式”或“梵”,抑或以绝对的“神”为依据,都可以归为“道弘人”。西方和南亚由于不具备古今一贯的文明形态,难以在更长、更广的视域下建构共同体,也难以产生由上层推动、全社会共享的诗教传统。尤其是基于“社会存在”的分殊状态造成的二分思维,宗教或形而上学对价值观的“设定”破坏了生命情感的本色,诗教也就失去了独立的意义。
这样的历史实践,建构起周全的发展的文明,孕育出“人能弘道”的文化特质:一者,无论是天道的“人为天地心”、“家国天下”秩序的以人为本,还是个体价值的“为仁”“知天”,都是一种天人、物我关系和谐“共在”的主体性,不依赖外在超越,不走向二元分殊,内心也达到情理融合的状态与境界;二者,相比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文明结构,其价值观源于基本的人性与实践,内生着永恒、普适的能量。由此孕育的诗教,即诗之情与教之道相生,既不放任自由与多元、迷失方向,也不设定先验与绝对、强硬灌输,而是在“天人”共同体中,共同以生命情感来自觉提升、获得归宿。
二、儒家“人能弘道”思想与诗教机制
儒家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等论断,彰显了中国主流文化的价值建构方式,也奠定了诗教的原理与品格。
生命自觉是无限的,它一方面与有限的现实条件产生根本冲突,加之不认可“外在超越”,暴露了生命有限、价值无解的困境,这是中国文化呈现的悲剧意识;另一方面提供了“弘道”的永恒动力和指向,人靠自己对生命负责、超越有限性,彻底的悲剧意识反而激发了追求的意志和自由,人不依赖外在和现实进行“弘道”。“弘道”的方式就是,基于生命自觉和历史实践,建立起人类共同“生生”这一根本原则,进而把“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建构为宇宙图式。
由此人与天道自然同在,个人与共同体的生存与价值安顿于天地家园,外在超越处于非必要地位;解答了人为何及如何“活着”的根本问题,生存悲剧性尽管永远存在,却转化为不断弘道的方式。人在天人、物我、情理的圆融状态中体认归宿感、永恒感,具体得失以至生死付与“天”“命”而无待,在审美超越的境界中现象即本体、过程即意义。承认现实、深情追求、知行合一、审美超越等过程,使心灵生成开放而稳定的“结构”,这种悲剧精神是较为合理和积极的。
始于生命自觉、自证天人之道、归至心灵境界,这种开放性源于人性与实践的“人能弘道”,更能保证人类和个人的生存发展,也是“道弘人”文化中被遮蔽的辩证逻辑。“人能弘道”又决定了“人文化成”观念及其实践,诗教正是其中经典的方式。至于新儒家所谓“心性之学”“内在超越”,如果不根除“道弘人”的可能,则未必是中国文化的真正主流。
孔子论《诗经》,涉及“言”(《论语·季氏》)、“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达政”“使于四方能专对”(《论语·子路》)及“思无邪”(《论语·为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温柔敦厚”(《礼记·经解》)等角度,历代儒家对此不断发挥。从中可见,相比诉诸理性、秩序、实践的教化方式,诗教是以精神价值层面的“兴于诗”为基础,涵容了修身、治国等方方面面的综合实践职能。
一是情感审美及语言艺术教育。在审美中培养情感、感知是比价值导向更重要的内容,“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等观点都是如此。中国文化强调“美与善同意”(《说文解字》),情感审美孕育着合理的思维方式、价值建构方式。而以诗教为发端,修身之余进行语言表达、文艺创作,则是以诗“言志”。《诗集传序》所说的“章句”“训诂”“讽咏”“涵濡”则指诗的语言文学教育功能,“涵泳”即体认诗歌内容及形式而获得立体性的启悟。
四是社会礼俗教育及国家治理。诗歌除了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能直接用于明道、说理、劝化、讽谏,诗教也就承载了社会历史实践中相关道理、知识、规则、技能等方面的教化职能,其内核是生成天人、物我相和谐的秩序及形式。这突出体现为诗为礼俗、政教所用,诗、礼、乐一体。统治者还通过诗歌“观风俗、知得失”进而自教、教人,提升政教,由于“美刺”是“观”的重要方面,故而要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毛诗正义》)的气魄。
三、“人能弘道”与中国诗学
由此,诗歌兴于“情”又归于升华的“情”,这种“情”具有“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的主体性。诗歌也不是为艺术或为人生而艺术,而是与社会人生一体,从这一高度保证其本源与品格。故而所谓“诗言志”(《尚书·尧典》)具有丰富深刻的含义,它与“摹仿说”“反映论”和“表现说”的不同正体现了价值取向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