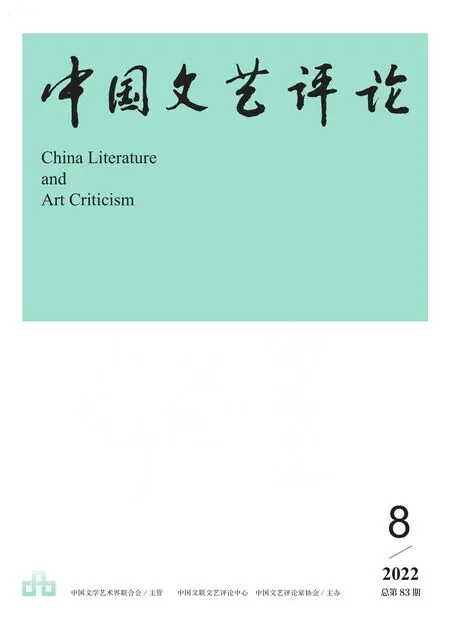分散与重聚:直播场域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
■ 欧阳梦陶
带着这一自觉,再回观直播打赏平台中的传统文化传播,这样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重要:已然确知任何信息都须经由譬如语言、符号、书报、网络等媒介传播,而媒介本身并不是一个纯然、客观、透明的客体,经由它们传播的信息会在其中发生改变。而在移动终端普及之后,以抖音为代表的直播打赏平台带来了一套全新的媒介规则,“人人可赏、处处可播”意味着文化将以一种柔润的、全新的形式在这一“小世界”中流通。这样的流通如何可能发生?在流通过程中,浸透了当代生活养料的传统文化在形式上已然发生了怎样饱含意味的偏转?二者指向的答案,将帮助我们对生活在当下时空的人的文化生活状态有基本的把握,也能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的根源作用、生长能力、精神魅力提供丰富的极具创意的范例。
一、内容分解:视听艺术、场景表演与日常化
直播平台上这种“直接”的表现方式,将传统文化原本整体、厚重、严肃的内容一一分解,以点滴浸润、既有整体格局又有灵动变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使得主播和观众都能同时感受到有滋有味的文化魅力。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主播凭借着自身的热爱和观众的支持,探索着视听表演的边界,将传统文化的呈现风格推向场景化、日常化的一边。
二、圈层重塑:部落化与参与文化
直播这一媒介对传统文化的文化形态的重塑还不仅在于将传统文化内容拆解为元素、表演,融入到当下生活之中,使其内容呈现方式朝着视听化、场景化和日常化方向发展。由以往的产品导向型转向社交导向型是这一基于移动终端、网络软件的媒介平台的又一核心本质。与之相应的,在直播平台内部,不同的传统文化门类、创作者与粉丝之间、粉丝与粉丝之间的全息、立体、交互式的圈层关系正在聚集成形。
在这样的“秘密”圈层内,观众的参与意愿、参与行为也得到了极大的激发和引导。斯图亚特·霍尔将大众媒介的传播视为一个编码解码的过程,受众会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积极的解码。而过去在电视媒介中,无论这种解读倾向处于统治、协商或是对立状态,受众与传播者的影响能力都是不对等的,相较于传播者传播的内容而言,受众的解读只能在小范围内发挥作用。而在直播平台上,“部落化”的受众与解读者之间获得了相对平等的关系,受众的解读影响力与传播者所传播内容的传播范围近乎一致。对于每一个观众来说,他能够同时接收到两者所传递的信息,并随时在受众—传播者、传播者—受众的身份之间跳跃、转换。他们可以和原来的创作者“合谋”参与到这一次的文化传播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也就是亨利·詹金斯所说的与被动型媒体观看行为相对照的参与文化。
三、价值重构:自主定价、元知识与文化认同
而传统文化在这样的价值重构中,也找到了自身在现代生活、现代文化、现代人的精神与情感世界中扎根的形态与可能性。
四、结语
在当下,直播平台带来的传统文化传播形态的改变已是粉丝、学者、圈内圈外人都能共同感知到的一重事实。在直播平台上,传统文化以视听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促使传播者自觉创新传播形式,与当下的媒介形态相适应。一方面,传统文化内部的各个环节都成为了传播的内容,跳脱出了传统传播渠道的限制;另一方面,再小众的传统文化门类,在直播平台上都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使得传统文化在直播平台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传播生态。传统文化不仅可以通过直播间直接触达特定圈层的观众,更能让原本小众的传统文化借助开放式的媒介平台重塑现有的圈层以实现更为广泛的传播。借助直播平台的互动,传统文化的创作者与观众一道,共同成为传统文化的参与者。而传统文化的直播打赏也成为了观众基于认知价值为文化消费自主定价的方式,成为了传播者挖掘传统文化潜在价值的驱动力。在这一文化传播的良性循环中,越来越多的优质人才加入到传统文化的传播队伍中。通过直播打赏,观众所表达的不仅是对创作者个人的认可,更是对传统文化本身的认同与期待。
与此同时,还处在“萌发”阶段的新的传播空间内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其大众性、低门槛的特质,一些打磨不精、质量较粗的传播内容混入其中,给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造成了错误引导;甚至在有的直播间中,有为了争夺流量将不属于本地的异域异民族的文化资源不加分辨地挪用、对传统文化历史进行有意歪曲的不良现象出现。这些问题倘若忽视,将会对方兴未艾的传统文化传播、乃至传统文化本身造成可怖的影响。除了平台方已在技术、知识层面上给出了积极应对方案之外,社会、文化各界也应有所警醒。因噎废食固不可取,在下一阶段,如何发挥新媒介在传统文化传播上的巨大作用,继续探索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可能、可感、可爱的传播形式,同时规范个体行为、预防不正之风、规避不良的社会影响,需要观众、创作者、平台方、任何传统文化的受益者和受影响者共担、共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