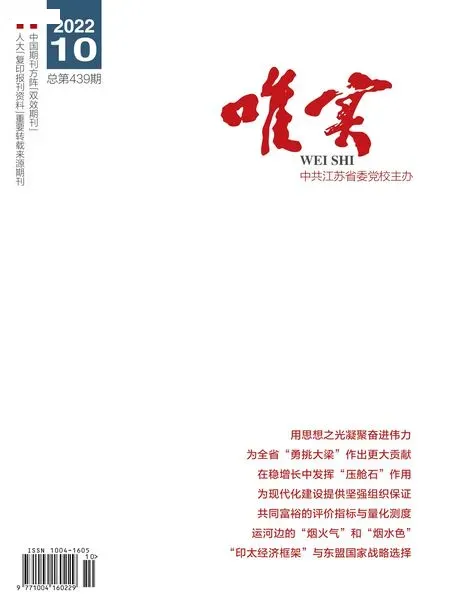运河边的“烟火气”和“烟水色”
——示以汪曾祺小说文学图谱
刘 恋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工程量最大、里程数最长、变迁最复杂、沿用最久远的人工河流,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之一。古往今来,横跨两千年、纵贯六千里的大运河,在岁月无声中积淀了前人的智慧,赓续了通史的文化,承载了家国的记忆,传递了世代的乡愁。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发轫之地和大运河遗产保护的牵头城市,扬州在发掘、保护、传承、弘扬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与价值方面义不容辞、大有可为。2007年9月,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在扬州成立,包括扬州在内的运河沿线8省市35座城市于2014年6月正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扬州不仅是京杭大运河沧桑历史变迁的缩影和注脚,而且是大运河文化精神延续传承的窗口和符号。作为扬州籍代表作家,汪曾祺以各种形式将“我的家乡”(扬州)书写进文学作品,从而让大运河的“本相”在波诡云谲、金戈铁马的政治、经济书写之外,别有一番氤氲着“烟水色”和“烟火气”的文学艺术呈现。
名城扬州记载着大运河凝固的历史
扬州因“运”而生,应“运”而兴,与大运河同生共长,心契神会。作为伟大人工运河的起源,鲁哀公九年(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伐齐,逐鹿中原,筑邗城、开邗沟,沟通江淮,邗沟成为中国境内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早人工运河。作为宏大战略的经营,隋炀帝杨广于大业元年(605年)开邗沟,成就了“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潜运,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的旷世壮举。“开成二年(837年)夏,旱,扬州运河竭”,这是以“运河”指代前朝“漕渠”“官河”的早期明证,并就此成为这一人工水道的专名。自此,扬州城便与大运河声息相通、命运相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丰富历史画卷。”史学家亦早有见识:“瓶水冷而知天寒,扬州一地之兴衰,可以觇国运。”因为动关国计、事关国运的大运河,扬州一地的兴衰辐辏于中华民族的国运起降,在经风雨、历荣辱中同频共振。在2500多年的城市发展史中,扬州曾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发展辉煌。兴盛于汉、鼎盛于唐、繁盛于清的生动史实,叠印于国家统一、疆域广阔、经贸频繁、文化交融的恢弘底色。西汉初年,源于家国一统、政局重建,吴王刘濞开通运盐河,增筑广陵城,即山铸钱,煮海为盐,推动了扬州的初度繁荣;杨隋一朝,源于终结乱世、更起宏图,偃武修文、修渠开河,促进了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政治、经济、文化的融合共兴,催生了唐代扬州“天下之盛,扬州为一而蜀次之”的发展鼎盛;元朝初建,定鼎中原、迁都大都,大运河上至北京,下抵杭州,五大水系一脉贯通,通波千里,奠定了明清以降扬州齐集漕运、盐业、河务三大要政于一身的重镇地位,续写了其盛世华章。作为一个城市的荣光,各种史料史籍和诗词歌赋均有书写且喜闻乐见。而近代以来,扬州城市的落寞则很少被提及。
其实,扬州随着历史变迁而出现的城市兴衰,颇能折射出中华民族国运的一度衰落和式微。作为扬州人,汪曾祺不避此讳。在创作初期,他就以《落魄》为题,精准传神地叙写了扬州人和扬州城在20世纪上半叶的真实境况。《落魄》发表于1947年《文讯》第7卷第5期,后被收入汪曾祺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小说以昆明某校学生的视角,见证了学校附近一个小吃铺子的扬州老板由兴而衰以至于“落魄”的过程。这篇小说恰如一面镜子,照出了“落魄”的扬州城市、扬州人,也照出了作者内心隐藏的故乡情结,扬州人(及城市)的经济地位“落”下了。这个“落魄”的“他”,是脱离了运河交通的扬州文化的一个符号,其智慧与现代世界脱节,“他”的“魄”是附在辕门桥方圆一里的那些饮食休闲文化上的,异地而处便落魄了。一起落魄的,还有讲究的扬州饮食及其做法(精致有特色),扬州文化及其表征(周身那股子斯文劲儿)。

名城扬州延续着大运河涵养的诗意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治水之道。这正是大运河涵养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思想智慧的应有之义。扬州得名的由来,一说源于“州界多水,水扬波也”。运河之于扬州城市,从肌理看,大运河扬州段的生成流变,深刻影响了城市的布局和街巷的形制。伴随着长江岸线的南移和运河水道的变迁,扬州城址自北向南拓展,运河也从蜀冈上下的城外水道一变而为运河绕城、官河纵贯、支河密布的繁复水系。从意境看,扬州对于滨水园林的匠心构建,突出反映了其依水建城的人居哲学。从南朝徐湛之于城北陂泽“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到隋炀帝在扬子津建临江宫、凝晖殿,再到康乾时盐商巨贾沿蜿蜒曲折的瘦西湖临河起园;从南宋贾似道于“郡圃”构“濠(河)想”“剡(溪)兴”二亭,到明代郑侠如的休园以池水“伏行”“溪行”寓“淡泊水乡之趣”,再到清代二分明月楼“旱园水作”的引水入园,前人对城市园林的匠心营造,塑造了扬州城园一体的风貌,糅合了建筑、文学、书画的风骨,更升华了城市清新自然、恬淡冲和的精神旨归,契合了“诗意栖居”的普世追求。
汪曾祺小说中对扬州“诗意栖居”的描述,充分体现在人物的行为举止和品质特性上。戴车匠的门面板壁上写着“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王淡人医生的医室里挂着郑板桥的对联“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千扁豆花”,对他们而言,职业赚钱与否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生境界;大画家季匋民将卖果子的叶三引为知己,只因为认为他“真懂”,只言片语的交流便是高山流水了;鞋匠高大头因历史问题而在“文革”中备受折腾,却能在菊花影中运锉补鞋,自得其乐;清贫、孤僻的教书先生高鹏贴春联不图吉利而求“述怀抱、舒愤懑”。而那些饮食男女更上演了一幕幕浪漫脱俗的爱情悲喜剧:明海宁愿不当沙弥尾也不要当方丈,也要和小英子沉浸于芦花荡(《受戒》);十一子和巧云既打破东西两边人家不相往来的沟壑,更无视世俗所谓对错,深沉而坚定地走到一起(《大淖记事》);甚至“小姨娘章叔芳”的偷情(《小姨娘》)、“小嬢嬢谢淑媛”的乱伦(《小嬢嬢》)都被赋予了一种人道的体谅,被抹上了一层浪漫的色调。
汪曾祺笔下这些人物,被大运河所滋润、涵养,在市井生活之上有诗意的追求,或寄情艺术或化为意境或追求情爱。他们游走于士人雅致与凡人世俗之间而无隙,融士大夫风雅与乡土智慧而无隙。他们和俗同光、俗得很雅,他们雅俗融合,是运河边上扬州城里“诗意栖居”的人。

名城扬州氤氲着大运河迭代的乡愁
对于运河文化的考察,既需要历史的“俯瞰”,也需要当世的“平视”,金戈铁马、归帆征樯、迁客名士的慷慨激越之外,更有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静谧平和,寻常巷陌、饮食男女的岁月悠长。汪曾祺小说中运河市镇高邮氤氲的“烟火气”和“烟水色”,正可以成为乡土地感知运河人文精神别样特质的另一视角。
河之水的“悲歌”。品读汪曾祺的乡土小说,离不开一个“水”字。正如汪曾祺所总结的那样:“少年橐笔奏天涯,赢得人称小说家。怪底篇篇都是水,只因家住在高沙。”这水本是沧桑的:“湖在城那边,而城建立在现在湖的地方。前年旱荒时,湖水露了底,曾有人看见淤泥有街路的痕迹,还有人拾到一个古瓶,说是当年城中一所大寺院的宝塔顶子。”(《猎猎——寄珠湖》)这水曾是恣肆的:“这一年闹大水。运河平了灌。西北风一起,大浪头翻上来,把河堤上丈把长的青石都卷了起来。看来,非破堤不可。很多人家扎了筏子,预备了大澡盆,天天晚上不敢睡,只等堤决水下来时逃命。”(《岁寒三友》)这水也是随和的:“两岸的柳树交拱着,在稀疏的地方漏出蓝天,都一桨一桨落到船后去了。野花的香气烟一样地飘过来飘过去,像烟一样地飞升,又沉入草里,溶进水里,水里有长长的发藻,不时缠住桨叶,轻轻一抖又散开了。”(《河上》)这水终是寂寞的:“左手珠湖笼着轻雾。一条狗追着小轮船跑。船到九道湾了,那座庙的朱门深闭在透迄的黄墙间,黄墙上面是蓝天下的苍翠的柏树。冷冷的是宝塔檐角的铃声在风里摇。”(《小学校的钟声——茱萸小集之一》)河水澌澌流过,但烟水苍茫、杳无边涯,遮断了旅人的眼睛,乡愁的情愫里浸满了于己及人的悲悯。
水边城的“欢歌”。运河终究是流动之河、繁荣之河,虽然“这个城实在小,放一个炮仗全城都可听见”(《最响的炮仗》),却是个“很动人的地方,风景人物皆极有佳胜处,产生故事极多”(《鸡鸭名家》)。到春夏之交赛城隍时,“那真是万人空巷,倾城出观。到那天,凡城隍所经的耍闹之处的店铺就都做好了准备:燃香烛,挂宫灯,在店堂前面和临街的柜台里面放好了长凳,有楼的则把楼窗全部打开,烧好了茶水,等着东家和熟主顾人家的眷属光临”(《故里三陈》)。还有自然形成的商业圈:“承志桥南的旷场周围就来了许多卖吃食的。卖烂藕的,卖煮荸荠的,卖牛肉高粱酒,卖回卤豆腐干,卖豆腐脑的,吆吆喝喝,异常热闹”(《王四海的黄昏》);竺家巷口的两家茶楼“楼上的茶客可以凭窗说话,不用大声,便能听得清清楚楚。如要隔楼敬烟,把烟盒轻轻一丢,对面便能接住……上茶馆是我们那一带人生活里的重要项目,一个月里总要上几次茶馆……我们那个县里茶馆的点心不如扬州富春那样的齐全,但是品目也不少”(《故人往事》);御码头旁的运河小轮船上有“卖牛肉高粱酒的,卖五香茶叶蛋的,卖凉粉的,卖界首茶干的,卖‘洋糖百合’的,卖炒花生的”(《露水》)。汪曾祺将其少年时代对身边世界的好奇凝视,固化为一生对烟火市井的平静守望,以风俗画般的韵致再现了悄然消逝的文化史式的风情。
城中人的“挽歌”。正如汪曾祺被视作“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其小说不可避免地透露着疏离于时代的古旧之气,以及对于那时那人的存问之情。“小城土地肥美,人情淳厚”(《关老爷》),即便外来人如“从里下河一带,兴化、泰州、东台等处来的客户”也都“对人很和气,凡事忍让”(《大淖记事》);小城里的知名人士亦是普通凡人,“既不是缙绅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但“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的公益,从不袖手旁观”;生意人“有的是特制嵌了字号的。比如保全堂,就是由该店拔贡出身的东家拟制的‘保我黎民,全登寿域’;有些大字号比如布店,口气很大,贴的是‘生涯宗子贡,贸易效陶朱’,最常见的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经营小本买卖的则很谦逊地写出‘生意三春草,财源雨后花’”(《异秉(二)》),多是其人见古风、其业有古意。但在时代的裹挟之下,“多少字号要在公会的名单上勾去了。广源,新丰,玉记……只好眼睁睁看着一爿一爿的不声不响的倒”(《除岁》),以至于作者忍不住借小说人物之口慨叹:“一个人监制的一种食品,成了一地方具有代表性的生产,真也不容易。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桥边小说三篇·茶干》)如上,汪曾祺小说看似“不合时宜”的愤懑底色,固然是扬州这座城市近现代以来“落魄”的写照,更是他“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点泱泱的水气,人的性格亦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的深深认同与切切慰藉。
对于一种文化的审视和解读,宏大叙事与工笔白描其实并不相悖。汪曾祺以其独特的心境和笔调,冷静又温情、恰似流水式地凝望记忆里的故乡,在对周遭真人真事的如常记述中,努力攫取其中深植的真、善、美。既发现历史的、前现代的扬州城市个性,或者说是传统运河人文精神所投射与辐照的高邮;又呈示了近代以来随国运衰微一起而急遽沦入庸常甚至“落魄”的扬州(高邮)的缩影。也正基于此,人们才能在对扬州(高邮)水城同生、士商合流、雅俗共赏、南北融汇等运河文化共性特质理解把握之上,静态地、“微距”地探究近现代以来以扬州、高邮为代表的中国城镇现代化进程的急骤曲折,从而从不同层面和视角细细端详运河城市的历史自省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