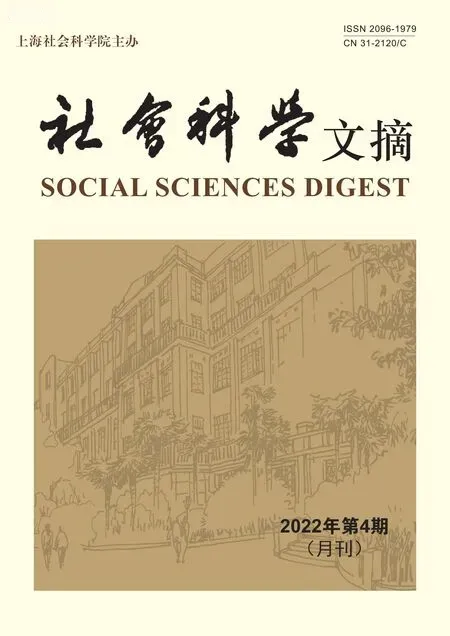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文/文贵良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摘自《学术月刊》2021年第12期)
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文言、古代白话向现代白话的转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离不开文学汉语的现代性,而文学汉语的现代性是以现代白话这一形式呈现的。文学汉语的现代转换如何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笔者所说的文学汉语指的是晚清以来文学作品中的汉语,是“有理”“有情”“有文”三者统一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汉语。“有理”指向汉语的知识体系,包括汉语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发生转化的知识转型;“有情”指向汉语主体的情感维度,包括个人情感和国家意识;“有文”指向汉语的文学维度,包括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以及文学形式的变化。
发生源于实践,发生必在实践中发生。文学的发生源于文学语言的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源于晚清民初文学汉语的实践。文学汉语实践沿着文学汉语的汉语造型、主体意识和文学形式这三个维度展开。汉语造型指向文学汉语的“理”,实践主体指向文学汉语的“情”,文学形式指向文学汉语的“文”。汉语造型在文言与白话、汉语与欧化、标准语与方言之间改变着“理”的结构;实践主体在中国传统价值与西方现代价值以及国家、国民与个体的关系中激荡着“情”的发展;文学形式在西方文类与中国传统文类、旧体诗与新白话诗、文言文与白话文、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晚清白话小说与新白话小说等关系中推动着“文”的演变。当“理”为现代之“理”,“情”为现代之“情”,“文”为现代之“文”,并且三者统一于文学汉语时,则实现了某种文类的新生。当不同类型的文类在同一时代均获得新生时,则可说新的文学在这个时代发生了。
“有理”的文学汉语与汉语造型
文学汉语的“理”指的是文学汉语在语言上的知识结构。文学汉语的“理”包括语音、词语、句法、标点符号以及修辞等因素。
晚清民初,汉语对新名词的吸收,改变着汉语词汇的意义系统,成为汉语造型变化的重要内容。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采用加注释的形式,以此种方式打开一个新词语的意义空间。随着晚清报刊的兴起和出版业的发达,“词语—注释”的节约型结构便成为打开新名词意义空间的主要形式。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因积极提倡采用日译汉词新名词,其翻译和论说多用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构成“叠床架屋”的汉语造型,从语句结构内部爆破文言以单音节词语为组织细胞的语句结构的束缚,从而为文体的现代发生和现代白话文的出现准备了语言造型。同时,汉语词汇的意义图景也在汉语实践中不断刷新。严复“六书乃治群学之秘笈”的语言策略以及语言实践,与其说是对西学的引进,不如说是在西学的视野下重新激活汉语词语意义能量的尝试。这样,新的语言造型,因其组成因子——新名词——的意义空间已经被适度打开,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五四”白话文的语言造型。汉语采用西方标点符号是最为明显的汉语欧化现象,西方标点符号进入汉语后成为汉语造型变化的重要内容。西方标点符号让书面的“五四”白话变成“有声”的语言,变成“鲜活”的语言,在语气上趋近言文一致。西方标点符号可以让“五四”白话变得“深沉”,把作者本意引向深入,从而改变口头白话的浅白。西方标点符号使“五四”白话的语句结构变得“丰满繁复”,变得复杂而繁多。
复杂的修饰语是汉语欧化的特征之一。文言整体上崇尚简洁,中心语前的修饰语不会太复杂。印欧语言可以通过关系词而造出从句,如果直译就会使得汉语的句子延长。复杂的修饰语能让语意指向更为明确,能表达更为丰富的情感以及复杂的思想。
“说理”的文学汉语的第一层意思是运用汉语语法理论解剖文言表达的不当,从而为提倡白话张目。胡适曾运用语法知识批评林纾《论古文之不当废》中“方姚卒不之踣”一句的不通,从而给予古文致命一击。鲁迅批评《学衡》杂志、反对文言文的价值取向也借用了语法武器。“说理”的文学汉语的第二层意思在于汉语因受印欧语言影响而做出合理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讲民初时期“的”“地”“底”的区分以及“他”“她”“伊”的区分。西方语法中形容词词尾和副词词尾的区分,给汉语中一统天下的“的”带来了挑战。名词领格和代名词领格后用“底”,形容词和定语后用“的”,副词和状语后用“地”。这是分化了近代汉语中“的”的功能。在“五四”新文学的表达中,“的”的用法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印欧语言中,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常分阴性和阳性。汉语无阴性和阳性之分,无主格宾格之别,全部都用一个“他”字。翻译汉语如果全部用“他”,就无法与英语中的“he”“she”“him”“her”一一对接,很容易造成歧义。白话文学提倡初期,“她”“伊”都被使用,后来“她”最终成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
“有情”的文学汉语与文学主体
“有情”的文学汉语有两个基本的意义指向。第一,文学视野中的汉语与语言学视野中的汉语不同,后者基于一种普遍原则性的探讨,前者则基于文学汉语使用者的情感。第二,“有情”既然指向文学汉语使用者的情感,就与使用者的主体性捆绑在一起。
晚清民初十位轴心作家都从旧式教育体制中走出来,接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黄遵宪作为“东西南北人”的自我形象,骨子里还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严复只是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他的主体性仍然以中国传统的主体性为支柱。林译小说式古文的“抵制—开放”话语结构恰好应和着林纾生命意识中“畏—狂”的人格结构,从而外发为林纾在晚清到“五四”时期独特的生命形态,即以古文翻译域外小说。梁启超“群学”为基础的人学思想,无法抵达现代独立主体性的深处。章太炎在维护汉语汉字的正当性、汉文文体的合理性、中国国性的独立性等方面四面迎敌,毫不畏惧。但“章的危机意识使得他反复地回归言语文字这一最后的方舟”反而限制主体的开放性生长。王国维接受叔本华的悲剧观所形成的审美现代性以及所进行的旧体诗词创作,已经初步具备现代个体的自主性。吴稚晖的“游戏”观强调的是一种自由精神与主体精神的张扬,这种主体性表现为自嘲人格结构与科学理性精神的结合。只是因为其自嘲人格与“五四”时期所想象的“新青年”的主体性不一致而被放置一边。胡适曾经以“狂”自诩,他的“狂”被自由主义精神以及杜威的实验主义所锻造,形成他主体性的内涵。胡适新文学革命的主张线条为造新文学—造人—重造故国。这样的主张落实到《文学改良刍议》里凸显的是一个以中国式杜威实验主义精神为支柱的自由主体。鲁迅对“个人”的想象一开始就把个人放置在国家/个人以及国民(群)/个人的对立关系中思考。由语言的“诚—谩”二元对立结构而来的语言否定主义,由精神的“真—伪”二元对立而来的个性张扬,两者结合在那个以对抗的方式与现实共生的自我中,从而形成鲁迅独特的怀疑而抵抗的主体。周作人通过对儿童的发现做了“辟人荒”的事业,经过1920年前后对文学汉语实践的调适,把人的解放返归自身时,把它落实在知言型文学汉语的塑造上,于是形成他的智性主体。
晚清民初十位轴心作家的以“情”为核心的主体性内涵各不一样,如果把他们对“国家”(清政府/中华民国)—“国民”(群)—“人”(个体)三者关系的处理稍作梳理,则有一条较为明晰的线索。大体而言,黄遵宪、严复、林纾和王国维的主体处在君臣关系中,可谓传统的君臣性主体;在清末民初王纲解纽的时代里,梁启超、吴稚晖和章太炎处在国家与国民关系中,可谓国民性主体。鲁迅、周作人和胡适三人与前七位轴心作家非常不同,前七位作家对“国家”(清政府/中华民国)—“国民”(群)—“人”(个体)做一种顺向想象,而且到“人”(个体)这个环节往往已经无力施展。而鲁迅、周作人和胡适对“国家”(清政府/中华民国)—“国民”(群)—“人”(个体)做一种逆向实践,切实着手进行“人”(个体)的建设,由“人”(个体)的解放而启蒙“国民”,由“国民”的觉醒而建立现代的“国家”。胡适的自由主体、鲁迅的怀疑而抵抗的主体以及周作人的智性主体,属于“五四”时期的个人性主体。
“有文”的文学汉语与文学形式
文学汉语的“有文”之“文”指的是文学形式。晚清民初,中国传统的文类依旧存在,但西方以及日本的文学形式开始进来,中西文类的碰撞以及融汇孕育了文学形式的生机。
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表现新事物不得不加注,表明传统的旧体诗形式表达新事物的捉襟见肘。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蒋智由等人提倡“诗界革命”,“诗界革命”的创作实践表明旧体诗对“新名词”的吸收非常有限。王国维的旧体诗词并无多少新名词,但是也能表现新意境。胡适对译诗所采用的诗体的考量与琢磨,转化为所创作诗歌诗体的要求。他得出“作诗如作文”的诗歌主张,并把这种诗歌主张返回到诗歌实践中,于是《尝试集》得以问世。
晚清民初,中国传统“文”类的遭遇以及变化呈现多种面貌。如何解构八股文的书写规范成为晚清民初“文”类变化的表征之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梁启超。梁启超对八股文的解构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改变八股文代圣人立言的主题规范;第二,改变八股文结构体式的起承转合和股比特征。章士钊、黄远庸、高一涵、陈独秀等人的政论文,延续了解构八股文的脉络。
晚清民初,“文”的另一重要支脉是桐城派式的古文,其整体倾向是走向衰落。严复和林纾被视为桐城派古文的代表。严复译著对语言新机的压制因而无法突破古文的藩篱。林译小说所用古文的“含蓄”的美学原则无法对接西方小说中大胆直接的抒情方式,古文的语法原则也很难表现西方小说幽默等特质,古文意境说的美学原则不仅很难适应晚清民初那种现代个体表达自我的内在要求。严复和林纾等人的古文,都因无法开放自身而逐步衰落。
晚清民初,“文”的第三支脉是章太炎的古文。章太炎的古文具有强大的“吸新”大法,即新名词、新句法、新学理等无论多新的要素,都被他那牢固而纯正的文类大厦所整合。到“五四”新文学时期,鲁迅、胡适和周作人等人的白话散文展露现代性文学曙光的时候,章太炎古文只能孤独落幕。
晚清民初,“文”的第四支脉是吴稚晖的游戏文。这种文体首先打破了文言与白话的界限,塑造了一种文白融合、以白为主的语体形态;科学理性的严肃表达与闲言碎语的插科打诨相结合,枝叶相扶而主干逻辑清晰;张扬的是一种个体自由的精神。吴稚晖的游戏文出自一种自嘲人格型的主体,而这种主体不可能成为“五四”时期的理想类型,因而吴稚晖的游戏文只能独自游戏了。
周作人在文言翻译、文言创作、白话翻译与白话创作的多重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知言型文学汉语以及独特的美文文类。这种美文的特征在于:语言结构上表现为对各种“言语”的合理裁融;平等趋同的虚拟读者与中庸的叙述机制的结合;植根于人生体验的博识体会;追求“涩”的美学趣味。
小说经过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严复和梁启超等人的大力提倡后,开启了它从中国传统文类的边缘向现代文类中心进入的步履。吴稚晖的《风水先生》以荒村为人物活动场所的环境,风水先生与工人群体的矛盾、文言白话的夸张离奇,显示了人类的某种荒诞性,具有比较鲜明的“准现代”色彩。鲁迅的《狂人日记》完成了他小说创作的飞跃。语言否定性成为创作《狂人日记》的发生机制;狂人白话与书面文言、日常白话之间的包孕与搏杀,显示了狂人、“余”、隐含作者与鲁迅之间复杂纠结的关系,由此发生了对启蒙者启蒙合理性的批判性思考;汉语欧化的创造性运用使得现代主体得以出场。《狂人日记》因而完成了现代小说的诞生。
结语
黄遵宪、严复、梁启超、林纾、章太炎和王国维这六位轴心作家各自的“有理”“有情”“有文”三位一体的文学汉语实践显示,一方面这些轴心作家内部的文学汉语之间相互挤压,一方面遭遇到更为年轻一代的文学汉语的挑战。吴稚晖“自由的胡说”把脏话、雅语、文言、白话、新名词与方言等融为一体,无法成为“五四”时期所想象的“国语”,他那种自嘲人格结构与科学理性精神相结合的主体诚可视为一种现代主体,但不可能成为国民效仿的主体。
通过多样的文学汉语实践,胡适、鲁迅和周作人把握到了语言表达的某种根源性。他们对上述七位轴心作家中某些人的文学汉语曾非常着迷,甚至模仿。他们在各自多种汉语实践中体悟轴心作家们文学汉语的开放与自由、紧闭与压迫,从而萌发寻找新的文学汉语的发展方式。写作是一种悟,乃是一种语言之悟。在胡适身上,“实验性白话”(“理”)塑造的白话韵文(“文”)让胡适的自由主体(“情”)得以出场,于是《尝试集》得以完成,白话新诗得以发生。在鲁迅身上,鲁迅那个怀疑而抵抗的主体(“情”)在语言的否定性场域(“理”)中,以白话小说的方式(“文”)把自己委托给绝望,于是《狂人日记》得以产生,于是新的白话小说得以发生。在周作人身上,知言型文学汉语(“理”)塑造的美文(“文”)得以让周作人那个智性主体(“情”)显露,于是现代美文得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