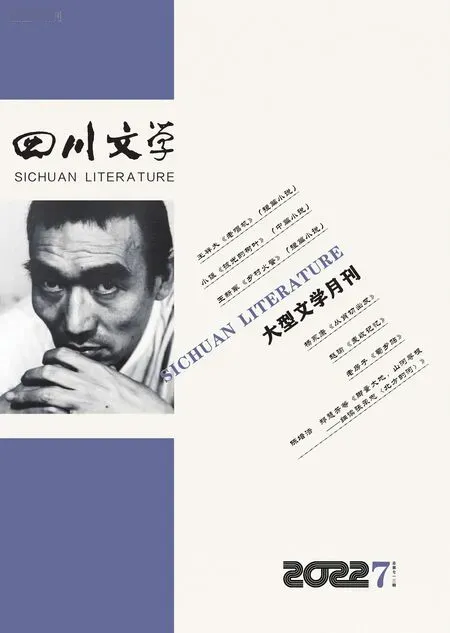大雪有痕
□文/肖辉跃
我踏着鸟的足迹出了门。
“机灵,机灵。”四只白鹡鸰划破了宁静。这些自吹自擂的声音在垅中太普遍,连蛤蟆都要自叹不如。蛤蟆最多只会在夏夜呱呱自夸,秋末开始就不再吭声,现在正躲在雪下的泥土中睡大觉。有一只白鹡鸰落在竹枝上。另一只落在竹枝的那一端,动作没有上一只利索,在竹枝上下滚了三次,最后才歪着身子抠稳枝条。还有两只是幼鸟,围脖尚有三成灰。幼鸟一俯一冲落在冰上,一落脚就摔个大跟斗。冰上除了雪团,还有少量冒出头的青草尖,全都冻成牙签一般。对白鹡鸰来说,“牙签”显然还用不习惯。它们在牙签阵里溜达一圈后,成鸟便机灵着自顾自飞走了,留下幼鸟自力更生。
白鹡鸰的出现如同拴在钓鱼线上的诱饵,垅中立马有了蠢动的痕迹。冰面上闪出一个跳动的红点,一只北红尾鸲从瓜棚下钻出,尾巴抽风似的上下颤抖。它在雪地上刨了几脚,发现完全是徒劳,便跳到瓜棚上。却不料,一只棕背伯劳已抢先登上那个瞭望塔。喳的一声,伯劳朝垅中发出一声警告。北红尾鸲再次打个冷战,又钻回瓜棚下。瓜棚旁边一根木桩兀立雪中,一只翠鸟站在桩上,连打两个无比优雅的大哈欠,就像一个着绿衣的寂寞女郎斜倚在门框上,盼望着某条有心的“鱼”路过。对鸟类来说,下雪天是个严酷的考验,食物不是被埋在雪堆之中,就是躺在冰层之下。不过对于拥有匕首一样锋利尖嘴的翠鸟来说,我的担忧实在自作多情。一年之后细看照片,才发现那个大哈欠实际是翠鸟被鱼卡了喉咙。
前面是一个高田坑,背风,雪堆里冒出一大丛茅草。若干年前,这样的茅草是不可能留着过冬的,都被我们砍了当柴烧。我猫腰穿过茅草,脚底一抖,两只鹌鹑擦着我的裤管飞了,扑啦扑啦,雪泥草屑把我喷成一个大花脸,只留给我一个麻色的背影。如果再有机会,我一定要潜伏在这里,我得看清鹌鹑到底长什么样儿。我正寻思着在哪潜伏,脚边又是一抖,又一个麻色身影擦着我膝盖一闪而过。哼,等着瞧!我要在这里挖一坨泥巴,然后裹着你,糊上一层辣椒粉,再用雪来烧。我是一个大厨,我会做一道湘菜:辣椒雪烧鹌鹑。
我开始去寻鹌鹑。雪地上有了隐约的红光,扭头,太阳在摇旗岭的山头露脸。不等我用雪来烤鹌鹑,太阳已开始烤雪,我加紧向相公塘赶去。
相公塘背靠一片连绵小山,虽说满山尽白,树的形态还是辨得清。落了叶光着身子的是枫树,锋芒毕露的是马尾松,叶片密集而枝丫横生的是香樟,歪着身子瘦骨嶙峋匍倒在路边的是竹子。竹子把山的小路隐了,几只黑脸噪鹛躲在下面开会,它们的声音和它们的个子一样大,依哟依哟依哟,满山的雪仿佛被它们吵醒,开始簌簌抖落。一会儿后,一根树枝接一根树枝在雪花的抖落声中弹起,很快雪花就滴答滴答滴答化成雨滴。一大群小白鹭在塘对岸飞起,不久便没入岸边小山。塘基斜坡上有很多小雪包,鼓成大白馒头一般。几根绿苗从馒头中穿出,是一小撮萝卜缨子,一小群领雀嘴鹎正趴在雪堆上使劲抠。一个穿灰白衣衫的身影在菜地里弓着身子,背对我,纹丝不动,像是给那群鹎鸟站岗放哨。这么冷的天,哨兵的毅力真是让人感动。我走过去,那哨兵立即转头过来,一双眼睛里写满饥饿。
啊呀!稀客!哨兵您可真是个稀客呀!
这是一只苍鹭!
多次听说苍鹭“长脖老等”的功夫,但这一次,在雪地上,不知是我打扰了它,还是雪地上确实无法等到它想要的,它转头就飞。不过,它那个芦苇秆似的细长腿,配上它庞大的身躯,飞起来颇为费力,就像一个胖女郎踩着高跷去赛跑。它缓缓悠悠在塘基上打个飞转,翅膀都没有完全打开,就隐到塘基上的一丛茅草后,长脖子朝前伸成个小弯,一眼看去就是一把倒撑的弯钩大白伞。我猫腰躲到一株樟树后。它站在塘基中间的一片雪泥中,那里的雪开始融化。它望向前方,眼角余光不时扫视我藏身的方向。我希望它把我当成一棵树,一棵积雪已完全融掉的树,而积雪已在我头上嘀嘀嗒嗒。樟树的绿叶也开始显露,竹子的腰基本伸直。我的表演多半成功了,它果真把我当成了一棵树,它并不在乎,上一刻这里其实是没有我这棵树的。但是,它知道,树是一定不会移动的。于是我站在那,任雪水在我头上脸上流出条条小溪。它放心了,眼睛不再瞟过来,继续望着塘面出神。我立马蹲着身子移到一棵桑树下,它又瞟过来,细脚杆踮了一下,身子往前扑了扑。我捂着嘴吁了口气。它又瞄过来一眼,接着双翅完全打开,细脚杆用力一蹬,脖子一缩,往塘里飞了。
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要长成塘边的一棵树,不期望长得樟树那样高大茂盛,就长成一棵桑树也好,一半伸入水面,一半扎根到塘基。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与苍鹭做伴。夜幕降临时,它会站到我的枝上歇息。它可能还会携来一个爱侣,将它们的巢搭在我头上。相公塘里有吃不完的鱼虾,我会结满一树的桑葚,它们一家从此便在这里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我做着来生梦时,苍鹭已在塘面盘了一圈,最后落在一个小洲上。看那显露在水面盘根错节的树根,小洲以前定是树木茂盛的。而自我记事起,小洲上便只有几丘田和成串成串的蚂蟥。苍鹭站在禾兜旁,它的脚下,满塘湛蓝的水。大雪可以冻住小塘小坝,但冻不住水面近百亩的相公塘。它在那守着,像老钓翁在等上钩的鱼。
不再打扰它觅食了,我抽身往垅里退。回头再看山,满眼的白里闪出一块块绿意。这就是南方,雪来得快,消得也快。一个灰色身影出现在山顶,翅膀极速鼓张几下,然后便直升机般朝我俯冲。我以为是只斑鸠,直到它在我头上盘旋,在雪后如洗的蓝天下,那展开的巨大双翅,却是在明明白白告诉我,它绝不是斑鸠。它的胸腹部密布灰色横条纹,细密而工整。它的六根翼指全都叉开,而那长长的尾羽上,同样织了四条粗横纹。
鹰!一只雌性雀鹰!
我曾在辽宁老铁山和北海冠头岭见过气势磅礴的鹰河,各种各样的鹰在我头顶阅兵方阵般流过,但在家乡的土地上,这是第一次见。我等会儿要回去向父亲请罪,我冤枉了他几十年。我一直认为儿时他给我讲的“麻鹰叼鸡”故事是骗人的。那雀鹰此刻正俯视我,端详了我好一会儿,可能发现我不大适合做它的中餐,便拉转机头,往垅中继续巡视。而此时的垅中如此安静,小鸟们不知躲哪去了,连田鼠细小的足迹都没有,更不要说野兔了。山边倒是有几行鸡爪印,如果是野鸡的足迹就好了,但显然这是家鸡留下的。虽说麻鹰叼鸡的历史悠远,不过为了长久之计,雀鹰还是没有去犯这个忌。父亲说过,麻鹰虽说叼鸡,其实还是很有职业道德。所谓“鹞子也要结三家邻居”,就是说鹞子、鹰这类猛禽,绝对不吃它们安家区域的家禽。雀鹰转了一圈便往回飞,接着腰身一闪,钻到山头那片马尾松的幽暗里。
雀鹰白眉紧锁,黄脚爪抠着马尾松的松针,没有再升空。在柔绿的松针上,站成一座灰色的雕像。
阳光一步一步洒过来,积雪一节一节往后退。我的头顶传来一阵颤音,微风扫过银铃一般的细微颤音,来自电线之上。电线有四根,上面的雪已全部消融,密布着抖动的音符。这是一群来靳江越冬的燕雀。抬眼所见,视线范围之内的电线全被燕雀站成乐谱。而电线下的田野同样是一页页翻开的燕雀乐章,海浪一般在田野与电线之间来回翻滚,整个大地似乎在抖动。
天空闪过一道阴影,雀鹰杀了个回马枪,将欢腾的乐章画上了休止符。
眼看一只燕雀就要成为牺牲品,“啊呀呀,”正站在河边枫杨树上聊家常的六只喜鹊一看,噫呀,也不打声招呼,这可是我喜鹊的地盘!一只喜鹊尾巴一翘,箭一般射向雀鹰。另一只张开翅膀挡在前面。其余四只就飞到电线上跺着双脚放声喊打。“强龙敌不过地头蛇”,雀鹰围着电线杆缠了十几个回合,翅膀一拉,歪着脖子往西面的大屯营镇上空而去。
雀鹰前脚刚走,燕雀的乐章又在田野里升起。
某种隐约的预感,我觉得雀鹰一定还会再回来。
晚上听到树叶沙沙响不停,第二日一早醒来,外面又是一片银白。
大雪正漫天飞舞,河边所有树木都弯下腰身。停靠在河边的一艘小木船已装满一船雪,河水不再流动。一只乌鸫站在杉树尖上,兴致勃勃地唱起了雪之歌。很快,它就发现它的歌颂并不合时宜。大雪不仅淹没了它的歌声,还淹没了它表演的舞台,它的身影已成一团黑影在空中乱飘。最后,这团黑影飘到我家的空调架上,贴着空调不再移动,就像上面粘了个黑标签。珠颈斑鸠算是见过世面的,它们集成一个小分队向雪中冲锋。才扑出去,大雪又将它们滴溜溜打回原地。在靳江两岸,真正的雪中高手还是要算丝光椋鸟。大雪激起它们前所未有的激情,它们结成团队一边飞舞,一边随意变换队形。中途又有无数的小团队高喊,快去!快去!直到集成数千只的大群。它们一边抖着翅膀,一边亮开嗓门从雪中划过。整个垅中,除了这几种鸟还在活动外,其他就没一个鸟影了。
我在楼顶上铲出一条通道,将铲出来的雪就地堆成一个雪人,然后抱了几十只橘子、一斤南瓜子、两斤小籽花生,还有几个柿子摆到雪人脚边。一小时过去,雪地上没一只鸟爪印,看来没有一只鸟领我的情。
下午终于雪停。一只白头翁(学名白头鹎)飞到樟树尖上。它在枝头喊了一小会,喊来了五六个同伴。它们在樟树上商量了一会,大概是哪只鸟在哪发现了食物,大伙儿立即高唱着往河边的林子里去了,望都不望我放的食物一眼。真是瞎了它们的鸟眼。
你道它们找着了什么好果子吗?原来是看中林子边那几棵苦楝树。冬天为这些苦得要命的黄果子镶了一圈银白花边,这是大自然特意留给白头翁的冰糖葫芦。一群黑尾蜡嘴雀被白头翁的喧闹声吸引过来,以为有什么好吃的,结果,吧嗒,吧嗒,苦楝籽在嘴边溜来溜去,既吞不下又啄不动。对它们那个核桃夹子嘴来说,对付一颗核桃远比一颗玻璃珠似的苦楝籽轻松。白头翁一看就是老手了,它们一边倒吊身子,一边品尝苦果,一边还不忘唱几句赞歌。对付这些苦果子,它们有一道特别的窍门:像挑食的小孩吃饺子,先把饺子皮揭开,专挑里面的馅吃,再将那层皮揪起来当“手帕”玩。一个冬天过去,苦楝树上到处挂着白头翁抛弃的黄手帕。
光看别人吃可不是蜡嘴雀的性格,领头的厚嘴壳抽动几下,一声召唤,全往林中扑去。
林子里是另一方天地。大香樟、大马尾松、大茶籽树,还有大杜英将天空遮得一片昏暗。哟嗬嗬,茶籽树下传来棕颈钩嘴鹛的口哨声。然而,茶籽树上并没有找到食物。它又跳到大香樟上。很快,它就从樟树皮下挑出一粒绿纽扣似的东西,像虫子又像某种食物的果子。无论是虫子,还是绿色的果实,都不是这个季节会出现的。它也不是一只有谋划的鸟,会在夏季就将食物贮存到樟树皮下。如果是虫子,倒有点像某种越冬虫蛹的肉身,钩嘴鹛可能剥了它的外套。到底是什么食物,也许只有大香樟自己才搞得清。
快点!快点!画眉在后面不远处催促。能在冬季听到画眉的声音就像南方的冬天下雪一样稀罕。当然,三十多年前,两者都很平常。就像夏天会打雷,秋天会下霜,最自然不过的事。好的喽!钩嘴鹛抱着根小树枝侧耳听了会,向画眉发出信号。快点哟!画眉立即给了回音。钩嘴鹛举着翅膀朝画眉奔去。
林子上空此时也有了动静,珠颈斑鸠和乌鸫在树尖上跳来跳去,一落脚,甚至只是翅膀拍一拍,就会有一根树枝直起腰,大团的积雪扑通扑通掉落。很快,马尾松的枝条上有了极细微的笃笃声,一小撮积雪飘洒,一大群黄腹山雀在敲打松树皮。相对啄木鸟那样敲得震天响的专业森林医生来说,它们更像体贴温柔的黄衣小护士。那树皮上有什么虫子吗?透过望远镜,我可以看到黄腹山雀的红舌头在抖动,还可以数清它们眼睛上的睫毛,唯独不见吃的虫子。当然,这大冬天的,也没有哪只虫子有那本事还贴到树皮上。我也相信,黄腹山雀敲打树皮,可不只是特意要来闻一闻松树皮气味的。诚然,松树皮有一股讨人喜欢的清香。不过,在欣赏美景与填饱肚皮之间,它们肯定是选择后者。黄腹山雀的眼睛是自带显微镜、扫描仪、探照灯,任何躲在树皮深处的昆虫都无法躲过它们的双眼。每只鸟都在各自的树枝上翻跟斗、劈叉,嘴里发出唧唧声,彼此之间时刻保持联络,一派友好和谐。当它们的头领吹响再次出发的口哨时,几十个手下立即丢下手头的树皮起飞。像赶集似的,一路上,远东山雀、斑姬啄木鸟、黄腰柳莺、黄眉柳莺,甚至还有一群棕脸鶲莺纷纷抛下脚头的活计,跟着大部队飞跑。而在黄腹山雀敲打过的树皮上,留下一片斑杂的白色牙齿印。有多少虫子煞费苦心藏在树皮底下的卵,有多少虫子在树皮底下做着温暖的冬日梦,所有这一切,被无情粉碎。
快点哟!画眉还在一个劲地催,真是只热心肠的鸟。它发现了一大丛未被积雪覆盖的五倍子(学名盐肤木),马上就将这个好消息向林中广播。钩嘴鹛是第一个响应号召来的。它兴冲冲跑过来一看,傻了眼,那成串成串的五倍子,对它的小弯嘴可是个大考验。这就等于拿把小刀去杀牛。但为了不辜负画眉的好意,它围着树干溜一圈,在一串五倍子里捅了几嘴,什么也没捞着便走了。画眉的热情还喊来了一只红肋蓝尾鸲的雌鸟。这是个极谨慎的姑娘,在来的路上它就左思右想,考虑半天才跳上灌木丛。它还在歪头思考,一只乌灰鸫的雄鸟跳上来,嘴巴一张就摞了一串果子。
一个善于厨艺的老板娘,客人来得越多,吃得越欢,它越是高兴。画眉当这些五倍子是自家餐厅的了,况且这个由大马尾松、大山杉与大香樟做风景林的餐厅坐北朝南,层层叠叠的树枝装饰着雪的花环,形成一个防风帐篷,再加上四周密布的荆棘当屏风,对鸟类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既安全又豪华的宴会厅。它一边摘果子,一边朝林中再次呼喊。
一个巨大的身影掠过,这次来了只大鸟:红嘴蓝鹊。
红嘴蓝鹊一落枝,红肋蓝尾鸲和乌灰鸫就同穿了隐身衣似的,一晃没了影。它在枝头颠了颠长尾巴,发现这丛五倍子杂乱无章,时不时硌着它的大脚,有点路边摊的感觉。这样的就餐环境不是它这种有身份的大鸟应该光顾的。它打了几个哈哈,顺手挑了一颗果子走了。临走还拉了一泡大屎,算是回应了画眉的好意。
五倍子丛里安静了一会儿,画眉从杉树下跳出,又开始招揽生意。
这一次喊来了一大群领雀嘴鹎,十五只。领雀嘴鹎是最不讲客气的,上来就一顿猛啄。每摘三颗果子就要从嘴巴里掉下两颗。喜得原先逃走的红肋蓝尾鸲雌鸟又转回来,专门蹲在它们脚下捡现成的吃。不止如此,它还喊了它老公一起,两口子一边捡,一边乐得合不拢嘴。
林子里好像就没有白头翁吃不下的东西,那边吃够了苦果,它们又一窝蜂奔过来。现在,这丛五倍子已招待了七拨、一百多个客户。照这个节奏,只怕五倍子变成十倍子、百倍子都不够吃。
而我那可怜的雪人,在楼顶的雪地里做了半个月模特,直到化成一堆雪水,依然没有一个食客领它的情。到最后,只有一只远东山雀对其中一粒花生表示了兴趣。它拖了那粒花生到树上,疑神疑鬼研究了好半天才捣碎吃了。看来,即便冬天对它们是残酷的考验,我们也无须可怜它们。
适者生存,这是大自然亘古不变的法则。
当我还在为自己的自作多情反省时,我挂在楼顶上的风吹腊肉,一共十块,肉被鸟啄得干干净净,只剩花一块白一块的肉皮。肉皮在寒风中摆荡,就像旧时剃头匠手中传承了一百年的剃刀布。
时至今日,我仍不知道这些剃刀布的制造者,究竟何方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