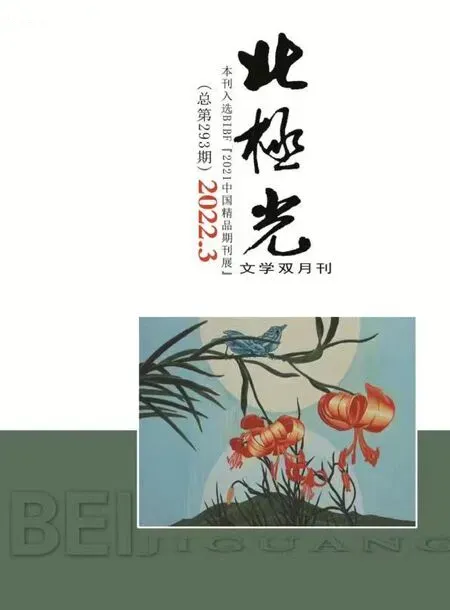听 声(组诗)
□左 右
少年游
以策马天涯、收割闪电的方式
进入一条崭新的长河。时针
在日暮下滞停
余晖在有灞桥垂柳的山岗上
与长安的灯火 告别
起风了。我被眼前盛大的景象
——满眼皆是西征的沙漠臣服
就像他乡的蓝天
挤出一道久违的霞光
和铜黄的月亮安慰我
与闪电一样执着的归心
佛的故乡早已百毒不侵
足以抗衡少年脸上
整颗整颗硕大的泪水
和 声
和上一阵轻轻的佛音,一午暖阳
和上石龟背上断裂的古壳,
老和尚关门的隙缝
和上秋天脱骨的掌纹,
大殿外轻捻轻挑的灰烬
和上风,和上你夕阳下眯着的眼睛
和上蚂蚁的经文,和上塔尖舍利的年轮
和上高山流水,和上默不作声
和上你走后不断回望的头
和上你在我耳畔轻轻说话的回声
听 见
不止如此,数不清耳朵醒来了多少次
在月光的霜冷里
从蛐蛐受伤的身体里
村庄的石板屋檐上,青苔召唤
半夜雨鸣,落花的声音变奏为凌晨绝唱
次次虚醒,枕边留下两行湿漉漉的信物
惊喜之余发现她刚离开不远
我不清楚是哪一个方向发出的余音
但我知道
我的身体里有一个人一直在等我
打开声门
听 声
有一个声音
我一直在倾听
它遗失在一封封邮至远方的信中
或在一本本从未打开的书里
春风也做出一副倾听的姿态
每一捻灰烬的形状,都是我自卑的形状
每一片闪烁的火焰,都是我执着的火焰
列车呼啸而过,站台很静。
铁轨是火车的读者
它敞开手掌,迎接火车幸福的蹂躏
一阵阵剧痛
辗压着我和一株野菊痉挛的耳朵
童年的木耳
正如我想象的那样
木头上长满了银黑的耳朵
正如我的童年
儿时,我在柞水
这块神秘的地方,丢了两只耳
妈妈指着院子后山
密密麻麻的木头架说
“你的耳朵就在树上
它们在和你玩捉迷藏
去找找吧“
我信以为真——
我在这里找了很多年
元宵节
年,从红灯的头顶一晃而过
岁月还在夜空拼命掏一些东西
拼命向世间展示它的爱意
掏出一些陈旧的东西。比如烟花
在夜空中画出你的心跳 比如字谜
在红灯与笺纸之间猜出你的来世
比如我 我老了之后
在你的额头上埋下秦岭云烟、丹江灰鹤
展示一些最后的爱意。比如渭河平原上
稍纵即逝的麻雀、雪、腊梅
以及 雪地上
你用春天笨拙的手笔
写下我小时候遗忘的名字
去汉中
从长安出发,去一座尚未去过的城市行走
一座被花海与森林覆盖的名城。车窗在倒退
恍惚之间,油菜花,朱鹮,大熊猫,山野,
河流
都找到了自相匹配的词根。
在汉江与丹江之间
我也寻见了草丛中
童年时爱过的蓖麻
车过洋县。路上流水淙淙,溪下茶树落花。
这是一个适宜赏花的好时节。一路向西
白雾缭绕。落日如血,若隐若现
仿佛天都的一只惊慌失措的眼睛
一只巨大的灰鹤在盘松下与我不期而遇
好运气总是不胫而走。它告诉所有
异乡来客:在汉中,每一条弯曲的小路
绿皮火车
延安回西安的途中
我看见了整个北方
——贫瘠的冬景
它们像我 像我手里翻飞的书。
一页页 在铁轨上肆意铺写
沟壑起伏的黄土高坡过去了
古老的窑洞、转眼即化的雪野过去了
一马平川的黄土地过去了
白桦林、麦田过去了
结了冰的湖、破败不堪的月台
麻雀的掠影 一直停在我眼中
暖阳像机枪。扫射车窗
正中我目力所及的靶心
恍惚间 火车爬进隧道
将我拉回 斑驳 陆离的童年
在天竺山
时常惊叹:身体会像松针一样疾驰
从涓涓山涧落下来。仙都飘渺的雾
包围着另外一个自己
坐立不安的石阶,不知何年何月
已经滋长 树木的年轮
青苔和野菊伴着流水的声响
微微颤颤地对话。木耳的眼睛紧张地
偷听了几句
风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掠走诗客们心中
酝酿已久的玩具。赞美和遗憾
时不时从石缝里蹦出来,丢给碧空万里
在天竺山顶
深呼吸。在天竺山顶,每一丝仙气
都紧贴着大地 山高水长的喉咙
不急于攀登。每走一处,呼吸和汗水
都是随草木一应而变的龙种
蕨类植物的叶子,此时更像我自然的心情
从山腰到山顶,我一直将心室的眼睛
睁得更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