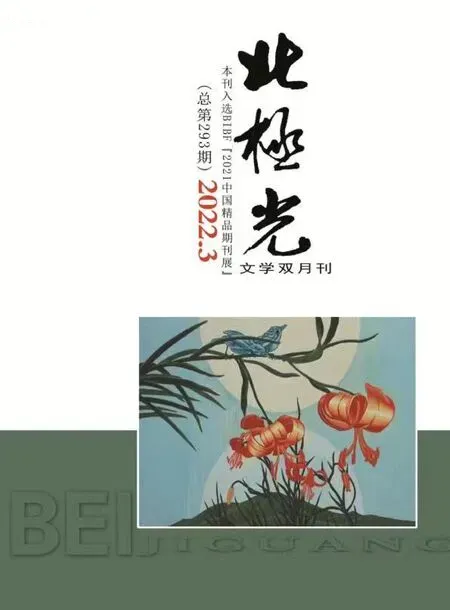其 境(组诗)
□林建勋
女人在河边洗衣。触及水草、石板
和倒影。与波纹隔开一段距离
垂钓者自如收放着
饵线深处的恬然。用一个意境构建一首诗
是远远不够的。卵石的寂静
勾画了这个纯洁的午后
在仰望的目光中,羊群变幻着
云的身姿。作为回应,蚂蚁的搬运
忙碌而曲折。似在印证
物与物间的隐秘关联
这儿是五月,声线细软——
天灾之祸尚远。仿佛只有一念可及的
浮云、流水和望眼
向 上
清晨散步我看见,街心公园树下的少女
踮脚去摘枝上的山丁子
绷直的身子,像一柄刚出鞘的剑
五指并拢,努力地向上
近了,近了:青涩与青涩的对碰——
十公分,六公分,三公分……
直到再也不能向前
阳光透过枝叶洒在她脸上
像斑驳的谜团——
跳起来啊,跳起来
我暗自较劲。就像站在树下的是我
整个上午,这美丽的画面
在我的心里反复放映
让我重生向远之心
和思而不得的奇妙
放 牧
一群羊在放牧我。在街面
零星的草与水泥路面,是牧笛
与牧鞭的关系。一顿饭。一个干瘪的下午
胸中的郁结,要用风来润滑
牧笛来自于店铺——
悠扬的饵料。车子习惯性吐出尾气
牧鞭悬在每个人的头顶
如虚无不可触摸,又随时可能落下
城市就像一个茶杯。叶子与水
不停搅拌。以榨去内部的色彩和滋味
入夜。街灯模拟繁复的星空
栅栏外面,一群羊像反背双手
徘徊的猎人。蓬草上
我一个人侧卧,暂且压住
老寒腿和神经痛,一边倒嚼一边修行
舞 台
幕布拉开。舞者像云影时聚
时散。“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
音乐的构想,发乎想象
止于笔墨。灵魂从沉默中爆发
但无须使用翅膀
风之所以吹,是因为
民俗体内残余的冰。喧响的掌声
源自树干牵动了暗处的枝叶
而篝火,是木的本体在闪光——
舞台高高在上,作为旁观者,我有
自己的戏码。比如在节奏中
迷路,看星空零而不散的鸟群
比如像羽毛一样落下来
牵紧你的手,听你附耳说:我
我轻轻应答:我们
清 晨
第一缕光穿过窗帘。我还在
为写不出一首诗而苦恼。坐上餐桌
仍然没有头绪。四十岁
已经过去。五十岁无限接近
窗外麻雀的鸣叫
像是寂静与寂静的摩擦
而彼岸这个词,始终存在于潜意识
未曾抵达。流水频繁刷洗的卵石
让我对意境的构想
缺少棱角。因而我总是
为我占用诗人这个称谓而羞愧
流水的顺与逆,就像
哲学的双面论,无论怎样
我都走不出一小段漩涡
仿佛一只水鸟,猛地俯向水面
又疾速远去。涟漪退去
好像什么都未出现过
失 神
六月,我被强迫写一首诗
蜿蜒的土路,把记忆从整体,截成
长短句并将平坦的部分
犁得崎岖陡峭——
高处是台,矮处是沟
对文字的布局,就是满足麦米所有的
七情六欲。并剔除
杂草虫蚁的不确定因素
依照这样的逻辑,犹如搭建
一幢高楼:一再压低重心
略去天灾人命,以撑起麦浪起伏
打牢村庄的根骨
村庄之上是炊烟。再往上
是踮脚也触摸不到的浮云——
啊,我的白银纳村
时光的恍惚、易碎和雷同
是机械的永恒,而不是因为我凝眸时
惯性的失神
雪 地
在雪地上行走 我感觉
有什么东西在离我而去
这段时间教孩子们
古诗里蕴含的韵律和光
教室镶嵌在天空,像一个木楔
清脆的诵读声使它微微起伏
白银纳的冬天很冷,泪腺时常有雪落下
这古典的月光扬洒
就像两种水果的嫁接融合
晶体下垂的过程不只是
覆盖和吞噬,而是要让
想象带着本体飞
雪为最纯洁的水,脚步是趟过
梦境的河。风携针与碎布
针线:意境的圆满
仿佛那些离我而去的
又重新回到体内
爱 恋
背靠窗子
想到相邻的两棵树
水龙头下的水,积攒却不落下
想到:花瓣和蜜,欲与节制——
爱有时要站在原地
不需要移动、苦痛和纠缠
几米的距离刚好
枝叶的手无限伸向对方
刚好,青春期的根
彼此交叉,却互不藤蔓缠绕
风吹松针为相思之弦
雨打青蛙吟肺腑之声
大地以短暂的凹陷,成全
音律与倾城之美。缘份如舞蹈
一上一下,一左一右
不远也不近。像因果不离不弃
涡轮转动,天涯与咫尺
像游子与乡村的无声对望
蛙 鼓
它有随时飘逝的倾向,又稳定地
聚拢。就像我正构思的新诗。因为
节奏的不规则而有力
田野是一个整体,而余下的
都是零件——拆散重组
我身体的鼓面
隔着黑夜与青蛙形成对峙
不依附于他物。思绪
自然地凹陷或弹起
看似温软的东西实则
玄机密布。不间断地敲
一波紧似一波,像冲锋号
没有尽头。命运和麦浪起伏。灯火弯曲
仿佛鼓槌是普遍的引信
我是孤单的炸药
飞 翔
风不是吹,而是在飞
我看见了什么?朝阳与剑气
天使和鬼面。午后井边
我在研究蜗牛的螺旋,用软肉
支撑身体爬。女人把扁担放在肩上
扭动宽阔的臀部,以显露
水桶的摇晃和阳光的平衡之美
相比于远山的静,花瓣
脱离花蕊——自制的漩涡
像一个尽职的舞者
飞翔无处不在,让我无法否认想象
对意境的构建力。风在飞
带着整片春天。我看见了什么——
龙飞凤舞的墨迹
带着一张白纸在飞
———《“意境”如何实现———恽寿平意境观念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