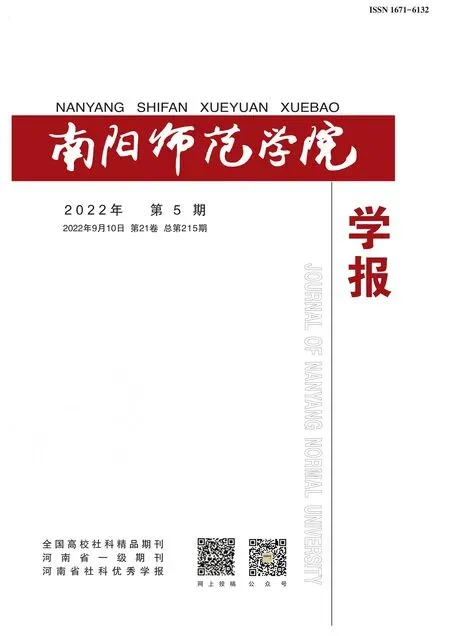郑文焯与邓濂词学交游考
贾光奔, 杜庆英
(扬州大学 中文系,江苏 扬州 225009)
郑文焯为“清季四词人”之一,于词颇注心力。自《瘦碧词》始,郑词便有“家家争唱”之势。沈瑞琳言:“自《瘦碧词》行世,而海内以声应者无虑数十百家。”[1]440谭献亦在日记中写道:“汉军文焯叔问《瘦碧词》持论甚高,摛藻绮密,由梦窗以跂清真,近时作手颇难其匹。”[2]186这固然得益于郑文焯之学识,然独学无友,则易孤陋寡闻。郑文焯“落南三十余年,深获知旧切磋之益”[1]255。郑文焯的词学成就,得友朋之助甚多。郑文焯与邓濂便曾有极为紧密的词学交游互动,但遍检学界之研究,未见相关论述。邓濂在致谭献的书信中提到曾为郑文焯《冷红词》作序,此序文在行世的郑氏词集中均未保留,笔者新见稿本《大鹤山人词稿》中收录了邓濂之序。结合郑、邓二人留存于各自词集中的唱和词以及时人的诗、词、信札,可证二人确有密切的词学交游活动。考察郑文焯与邓濂的词学交游事迹,对了解郑文焯学词历程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也可为郑文焯词学研究作一重要补充。
一、交于仕宦
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号小坡,又号叔问,别号甚多,如瘦碧、大鹤山人等,奉天铁岭(今辽宁铁岭)人。郑文焯生于官宦之家,可谓“世代簪缨”,但其父瑛棨于同治元年(1862)因剿匪不力而被撤职以后,家道渐衰。迫于生计,郑文焯于光绪六年(1880)应吴元炳之邀赴苏入幕,开启了接近四十余年的幕宾生涯,“先后巡抚十九人,均慕其才名,延赞幕府”[1]511,但“贫贱依人自古难”,他一生仕途偃蹇,多遭世变,在穷愁潦倒之中郁郁而终。郑文焯有《瘦碧词》《冷红词》《比竹余音》《苕雅余集》《樵风乐府》及部分词稿传世,于词学之外又精于金石、治印、医道、书画,具有多重艺术身份。
邓濂(1855—1899),字广文、似周,号石瞿、巽庵,江苏金匮(今属无锡)人,为“梁溪七子”之一。邓濂“性敦厚,沉默寡言”[3]1。他为生计奔波于吴楚之间,其母曾言:“全家赖汝一人活,汝一阁笔,则皆饿死矣。”[3]284他先入苏州从事书局,后曾于张之洞处“司主笔札”[3]2,一生辗转,积劳成疾,最终“郁郁病卒于里邸,年仅四十有五”[3]2。他虽英年早逝,但颇有文名。谭献称其文“藻辞斐亹,写情伊郁,有六朝体格”[2]326,评其《悼亡》诗“亦在义山、微之,近人中差近仲则”[2]326。邓氏在词学方面亦颇有成就,有《瑶情词》稿本及《巽庵集》传世。王蕴章评曰:“邓似周先生濂,工词章之学。传食东诸侯,屡为上客。”[4]
郑文焯与邓濂相识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二人同宦寓苏,应该正是二人相交的机缘所在。郑文焯于光绪六年入吴为幕,而邓濂“服阙,赴苏州从事书局”[3]1。关于郑、邓二人交往的记录,曾出现在邓濂姊婿诸可宝的记载之中。诸可宝《璞斋集诗》多次提到与郑文焯、黄彭年的饮宴,其中包括两次寿苏生日会。光绪十五年(1889)诸可宝于寿苏会中有诗作云:“南北东西联主客(谓在座小坡属长白……),八百五十纪春秋……丰年有兆宜春帖,独客无缘归去讴(金匮邓训导,返里未赴约)。试院煎茶曾白下(坐中小坡外四人者,皆侍公江南璅园),头衔从事署青州。”[5]其中“邓训导”即邓濂。虽然邓濂因故而未赴约,但可知此时郑文焯与邓濂曾有寿苏之约。郑文焯与邓濂均有记叙与黄彭年一同参与寿苏会的诗作传世。郑文焯诗题为《戊子冬于咏雪楼作东坡生日会,赋呈黄使子寿年文》《再赋寿苏诗示同社》;邓濂诗题为《东坡生日追忆咏雪楼寿苏故事,感叹而作,仍用聚星堂韵》。据这些材料可知,二人此时应已相识。郑文焯早期的《瘦碧诗词稿》以及《瘦碧词》中,并无邓濂的相关信息。据此可知当时郑文焯与邓濂、诸可宝等人应因宦游而初识,尚无词学上的深刻交流。
二、词学相从
在《冷红词》创作阶段,郑、邓二人的词学互动渐趋密切。郑文焯寓居苏地,“喜吴中湖山风月之胜”,“日与二三名俊,云唱雪和,陶写性灵”[1]437。他与邓濂曾往来山水之间,酬唱应和。邓濂为郑文焯《冷红词》撰写序言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一)灵岩览古
郑文焯曾言:“灵岩绝顶,吴故宫在焉,正堪凭吊,发思古之幽情。”[1]243郑文焯《冷红词》卷四中曾记载其与邓濂灵岩览古唱和之词,分别为《八六子·琴台》(步幽遐)、《西江月·采香泾》(怊怅故宫花草)和《西江月·浣花池》(寒绿一方秋净)。三词均咏写灵岩古迹,兹录析《八六子》一词:
八六子
琴台在灵岩最高顶,秋晚登望怀古,有辞舟客,邓子石瞿扣舷而和之。
步幽遐、屟廊黄叶,西风响出樵车。叹断壁仓皇残霸,好山分付名娃,月明自斜。秋容相对苍华,眉黛依稀岫萼,髻鬟散作云花。
问鹿迹、荒台何年枯藓,马蹄片石,谁家芳草。空余歌舞销尘故国,登临费泪天涯。黯流霞,飘零满溪旧纱。[6]417
此词起句为“步幽遐”,“幽遐”意指幽僻之处,《晋书·礼志》载有:“故虽幽遐侧微,心无壅隔。”[7]可知当时境凄情雅。“屟廊”句,则用典故,范成大《吴郡志·古迹》载:“响屟廊,在灵岩山寺。相传吴王令西施辈步屟,廊虚而响,故名。”[8]该词借古今之比,道出物是人非的凄凉。但此词作于《冷红词》后期,清朝国势已近衰颓,故郑文焯亦应有感于国势之变。“仓皇”二字极精洽,本指匆忙急迫之感。“断壁”怎能“仓皇”?更多的是观者内心的惋惜与悲痛罢了。
“秋容”句写佳人西施去后,容颜化为今景,“秋容”对“苍华”,“眉黛”成“岫萼”,“髻鬟”作“云花”。该词句以美人作喻,道尽悲凉!作者内心感喟万千,又以“问”字起首,古今对比之中,写出旧台今荒之状。虽空有当时“歌舞”,但故国已成残垣断瓦。登临此地,睹物伤情,郑文焯与邓濂难免“费泪天涯”。最后由情及景,虚实交错,交汇而出:流霞黯淡,照映在水溪之上,溪面亦被侵染上色,如同当时佳人的衣纱。景色固美,但“黯”与“飘零”道出二人心伤之感。
翻检邓濂《巽庵集》,其“补遗”中有《八六子》一词。词虽无序,但应为与郑文焯唱和之词,兹录如下:
恁荒遐、白云飞尽,幽禽唤客停车。怅霸业空残越艳,遗宫谁吊吴娃,屟廊半斜。当年何限繁华,夜夜青筝喝月,朝朝紫曲分花。
试问者、青山为谁憔悴,秋波怨黛,总随流水。空余病叶红迷谷口,秋波绿遍溪涯。映朝霞,临流有人浣纱。[3]143-144
二词同用一调且用词颇多相似之处。首先,符合唱和之词的形式标准,如:“幽遐”对“荒遐”,“樵车”对“停车”,“名娃”对“吴娃”,“自斜”对“半斜”,“云花”对“分花”,“问”对“试问”,“空余”对“空余”,“天涯”对“溪涯”,“黯流霞”对“映朝霞”,“旧纱”对“浣纱”。其次,两词描写的地点、运用的典故、描写的对象都是一致的,并且相对应的词句,境地、情感互有呼应。因此不难发现,邓濂这首《八六子》是与郑文焯的唱和之作。两首《西江月》唱和词,并未在邓濂集中找到。刘炳照的《梦痕词》中,有两首词可证郑文焯与邓濂确有览古唱和活动,其《八声甘州》序言曰:“九月既望,同人约游灵岩,月夜泛舟,石瞿用瘦碧词韵索和。”[9]138其《鹧鸪天》序言曰:“石瞿、瘦碧更唱叠和,逸兴遄飞,余因病废吟,填此志慨。”[9]138郑文焯词序中的记载与刘炳照词序亦能对应。据此可知,这次览古唱和活动刘炳照亦曾参与其中。刘炳照在其致缪荃孙的书信中,附《忆旧游》(记香残桂屿)词序:
瘦碧以《石壁纪游诗》索和,忽忆昔年泛舟西崦,遍揽灵岩、玄墓、天平诸胜,绘图联吟,宛然在目。今石瞿物化,予亦久客初归,坠欢莫续,借韵志感,石翁为作《虎山诗梦图》即题于后。[10]1022
由此可知,邓濂与郑文焯一起参与了灵岩览古活动。邓濂在致谭献的书信中亦曾提及与郑文焯的唱和活动:
复堂先生有道,鄂渚为别,屡易暄凄,翘首玄亭,靡时不眷前者……秋初当可锦旋,屈时能迂道吴门,为平原十日之饮否?盼甚盼甚……前年平原师督储来吴,招之入幕。师弟之谊,未容固辞,傭值十金,藉资赁庑,近历落莫,不堪为先生道也。瘦碧、语石,时过从谭宴之余,辄不禁神往左右……[3]276-277
这里邓濂虽未直言,但借信中暗含的几个时间点,仍可推知信中所提及的就包括“灵岩览古”。邓濂与谭献均曾应张之洞之邀,赴鄂入职。邓濂有两首《辛卯五月应南皮尚书之聘将之武昌,璞斋以诗赠行并贻画扇,赋此报谢即以留别》存世,因知邓濂实于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入鄂。但观其致谭献之书信,可知是时邓濂已由鄂返吴。谭献在鄂的时间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终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而信中“秋初当可锦旋”与谭献返里的时间正好吻合,可初步推知此信应作于光绪二十三年。信中提及的“平原师”,亦可佐证此时间。邓濂信中提到与“平原师”为“师弟之谊”。邓濂《呈陆春江师(元鼎)即次其江宁留别诗韵》组诗,其二有:“吾师治行古循良,袖有清风鬓有霜。”[3]77其四有:“元亭一笑尚依然,师弟情深总宿缘。”[3]77首先可知邓濂与诗中提到的“陆春江”为“师弟之谊”。“陆春江”即是陆元鼎,他确曾入苏为官。按信中时间“前年平原师督储来吴”,以光绪二十三年来推算,可知“前年”应指光绪二十一年(1895)。而据《申报》1895年9月4日报刊上的信息“奉上谕陆元鼎著调补江苏粮储道”[11],这与信中提到的“平原师”入苏时间相吻合。据此不仅可以反证邓濂致谭献书信的时间,而且还可知 “平原师”入吴之时,邓濂与郑文焯、刘炳照交往颇深。通过刘炳照《复丁老人诗记》中的记载,可以明确此次览古唱和的具体时间:
丙申之秋,予偕邓石瞿、郑叔问作灵岩之游,舟泊虎山桥。予因病废吟,二子倡酬达旦,有《虎山诗梦图》纪事。[12]
“丙申”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这正处陆元鼎入苏之后。据此可知邓濂致谭献信中所提及,与郑文焯、刘炳照所指应为一事。
(二)次韵清真
郑文焯在《瘦碧词》《冷红词》创作时期,主要以姜夔为学习对象,而到了《比竹余音》时期,便开始“发明清真”。在《冷红词》中,郑文焯和清真之词仅有三首,但是在《比竹余音》中出现了八首,可见其态度的变化。郑文焯颇喜与友朋切磋,在刘炳照《梦痕词》卷下《兰陵王·画桥直》一词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
叔问、石瞿以和清真词索予继声,屡思不属,病起走笔,伤今感旧,情见乎辞。[9]140
此词前明确标有时间的词相继为《买陂塘·戊戌仲春》《大圣乐·春意阑珊》,本词之后紧接着一词《莺啼序》中有句为“长夏初临”[9]141,故刘炳照该词应为戊戌(1898)春夏之交所作。结合刘炳照词及创作时间,翻检《比竹余音》中次韵清真之作,可知应为卷一中的《兰陵王·江上逢北使寄书和清真》。冒广生亦参加了此次唱和,其词集中该唱和词后附有郑文焯原词,正是《兰陵王·江上逢北使寄书和清真》。但是邓濂《巽庵集》却未曾发现其唱和词。通过郑文焯致冒广生的书信,可证邓濂参与了此次唱和活动:
损书得闻绪余,足征同道之深契。辱和《兰陵王》词,深美宏约,得《小雅》之遗音,心折无已。近作数令曲,多为语石藏弃[弆],俟新凉当录进,索紫霞定拍也。石瞿归甫一日,又之白门,渠惯为邻铺假手,恐亦温八叉一流,呵呵。[13]
信中提及邓濂,可见其为生计奔波于江湖,亦可见郑文焯与邓濂之间深厚的情谊。郑文焯曾调侃邓濂说:“渠惯为邻铺假手,恐亦温八叉一流。” 据《北梦琐言》记云:“(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14]此处或可理解为邓濂虽然忙于生计,但才思敏捷,唱和之词得之亦快。谭献评濂姊邓瑜《蕉窗词》:“有生气,有真气,一洗绮罗粉泽之态。以石瞿之慧,兄璞斋之婉俪,门内唱和之盛。”[15]由谭献之语,可知邓濂颇为聪慧,应可证此。
结合郑文焯、刘炳照、冒广生的词及书札,可知邓濂应参与了此次唱和活动。这便牵扯到一个关键问题:为何不见邓濂与郑文焯的部分唱和词?在刘炳照致缪荃孙书信之中或已给出答案:
石瞿一病不起,遗稿待刊。有子三人,年逾弱冠,均不能读父书,良可慨也。[10]1014
石瞿性懒,不自收拾,其子三人糊口四方,无暇及此,搜刻之任微迟,鞠其谁与归。[16]
邓濂曾言:“吾自少无壮怀,故势位富厚不吾及,非吾忧。吾特忧所著诗文不传,姓名与生命同尽耳。”[3]7郑文焯与邓濂同病相怜,二人因经济原因,部分作品未曾刊刻,因而散佚。邓濂《巽庵集》经后人整理才得以刊刻,但因时间跨度较大,词作散佚,亦在情理之中。
(三)邓濂《冷红词序》
在邓濂致谭献的书信中曾自言:“瘦碧续刊乐府竟地益高,不佞曾为作序,借彼杯酒,浇我块垒,可一笑也。”[3]277但翻检现存所有《冷红词》刊本,均未发现邓濂之序。在邓濂《巽庵集》以及今人整理的《清词序跋汇编》之中,亦未收录此序。笔者于近年的拍卖会活动资料中所见《大鹤山人词稿》抄本,其中收录有邓濂《冷红词·序》(1)此稿本见于2020西泠印社秋季拍卖会,拍品名称《大鹤山人词稿》,http://www.xlysauc.com/auction5_det.php?ccid=1197&id=189887&n=376 2021.08.,多处汰除残缺,抄录于下:
郑子叔问以北海之彦侨居吴中,辞荣就始,乐道媅艺,兰晖玉振,旷代才也。而光耀沈落,幽忧憔悴,独以歌曲著声于时。初刻《瘦碧词》二卷志变金石,律谐琯箫,汉寿易实父序之,传唱东南,行十年矣。近者世变益亟,时事益艰,遘选亦益悴,郁拂既久不能无言,遂又成《冷红词》四卷,丰情绵态,曼视远旨,较昔所著,境又进焉。言其格则“翠翘金缕”,无其艳也;“玉钩罗幕”,无其清也;“晓风残月”,无其悲也;“斜阳烟柳”,无其怨也。所造至此,岂非古诗人之遗,楚骚之苗裔欤?然吾闻叔问之于词也,尝喜称南渡,岂不以尧章、邦卿骋金羁于前,君特、叔夏驰玉轪于后,琴笙迭奏,兰翠相鲜,固词家极盛之世乎。然而莺花社稷,蜗角山河,国运之衰不可复矣。士君子生当其世,上不能张国雪耻,立甘陈之功;下不屑低眉摧颜,狎彝狄之俗。于是俯仰身世,徘徊古今,佩楚泽之芳蘅,泪周京之离黍。读其词者,可以悲其志也。今海内纷纷亦多故矣,小雅□□,四彝交侵,拉丁之文,尊于沮颉,兜离之音,重于韶濩。如叔问者,不使之排兰闼、步玉岑、庚咸茎、奏雅颂,而乃韬鳞掩藻,陆沈其间,悼彼美之不作,痛斯文之将坠,情不能已,徒托之绮罗香泽,写厥牢愁。抗音而金雁皆瘖,按拍而玉龙俱怨。其忠爱怨悱,亦犹南渡诸君子意欤?人第见其寻钿紫陌,不改风华;乞食红楼,益增跌宕。遂谓此东泽之绮语,西昆之曼词耳。夫岂知金迷纸醉,皆空漆室之忧;唾碧啼红,即是新亭之泪哉?叔问闻之乃起而呓曰:燕市之筑惟荆卿和之,雍门之琴惟田尝听之,落落今世,茫茫古愁,非我佳人,亦莫之能解矣!遂书之以弁其简端。金匮邓濂石瞿撰于吴门寓庐。
起首点明郑文焯为“北海之彦”,“侨居吴中”,“乐道媅艺”。“辞荣”为辞官退隐,不慕富贵,如陶潜在《感士不遇赋》中云:“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17]“光耀沈落,幽忧憔悴”指郑文焯之处境与心境,“旷代才人”却“独以歌曲著声于时”,不遇之感油然而生。《说苑·修文》云:“其志变,其声亦变。其志诚,通乎金石,而况人乎?”[18]邓濂赞《瘦碧词》云:“志变金石,律协琯箫。”这诚然是对郑文焯其人、其志、其词的肯定。邓濂提到易顺鼎之序,可知邓濂应细读过郑文焯的《瘦碧词》,或与易顺鼎相识。
“声音之道与政事通。”[1]58郑文焯面对世变,怎能无言?诚如邓濂所言:“郁拂既久不能无言,遂又成《冷红词》四卷。”在邓濂看来,《冷红词》比《瘦碧词》“境又进焉”,这具体呈现在“丰情绵态,曼视远旨”,在词格上则表现为“艳”“清”“悲”“怨”。“翠翘金缕”出于温庭筠:“翠翘金缕双,水纹细起春池碧。”[19]“玉钩罗幕”出于李煜:“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20]“晓风残月”出于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21]21“斜阳烟柳”出于辛弃疾:“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21]1867邓濂将郑文焯与温庭筠、李煜、柳永、辛弃疾相比,且认为郑文焯皆有长于前人之处,直为“古诗人之遗,楚骚之苗裔”,紧接着又将郑文焯与尧章(姜夔)、邦卿(史达祖)、君特(吴文英)、叔夏(张炎)并举,均可见其对郑文焯的推重。
“莺花社稷,蜗角山河”,指国势衰颓,且“不可复也”。郑文焯客居他乡,壮志未酬,“上不能张国雪耻,立甘陈之功;下不屑低眉摧颜,狎彝狄之俗”。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下,郑文焯悲痛却又无可奈何,所以“读其词者,可以悲其志也”。“小雅”二字后虽残缺二字,但结合前后之文,便可推知句意。顾炎武曾录有:“夫《小雅》未废,而四夷不敢交侵;《小雅》尽废,而后四夷交侵。”[22]此处指晚清在外来势力的冲击下,风雨飘摇之状。“兜离”指难懂且不雅的音乐。“沮颉”为沮颂和仓颉,均是我国传说中语言文字的创造者和记录者。“韶濩”指为雅正的音乐。宋陈普《孟子·今乐古乐》云:“韶濩无声郑卫淫,纪纲条例杳难寻。”[23]清末倾颓,西学新知涌入,传统则遭质疑,乃至“拉丁之文,尊于沮颉,兜离之音,重于韶濩”。在邓濂看来,郑文焯为“古诗人之遗,楚骚之苗裔”,必须“排兰闼、步玉岑、庚咸茎、奏雅颂,而乃韬鳞掩藻,陆沈其间”。此处意即郑文焯不慕荣利,隐于吴地而重振国学,继雅乐于乱世。葛洪《抱朴子》云:“若不能结踪山客,离群独往,则当掩景渊洿,韬鳞括囊。”[24]“韬鳞”指隐退,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陆沈”亦为隐退。《庄子·则阳》有句云:“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沈者也。”[25]郑文焯“悼彼美之不作,痛斯文之将坠,情不能已”,唯以词“写厥牢愁”。诚如郑文焯自言:“文献存佚,有关世运,更十年后,又不知国粹之销湛,时变之迁流曷极已。触绪悲来,率成俚曲。”[1]268亦如邓濂所言:“其忠爱怨悱,亦犹南渡诸君子意欤?”
针对时人中诋毁郑文焯词者,邓濂亦为其辩曰:“夫岂知金迷纸醉,皆空漆室之忧;唾碧啼红,即是新亭之泪哉?”表面上的纸醉金迷是假,内心的忧愁、对时事的担忧是真。如若不关心时政,郑文焯哪来“落落今世,茫茫古愁”的感叹?!邓濂与郑文焯相似的经历,让他更能够理解郑文焯的心声。此序言未曾刊刻于《冷红词》刊本中,但是二人“次韵清真”活动,已过《冷红词》刊刻之时,因此序言未刊刻乃二人共同知悉,但这并没有影响二人友谊,在《比竹余音》中的唱和便是明证。
三、词心相契
郑文焯与邓濂识于仕宦,却以词而交深,这不仅因境遇,更与二人文学趣尚紧密相关。通过分析二人交游活动,则可以更好地理解郑文焯学词进程中独特的艺术生态。
(一)宦海浮沉,感于身世
郑文焯曾自言:“所依恃者,惟良师益友。”[1]230他始从李复天习琴律,又与潘钟瑞比邻而居。再入吴社,遍和白石词,得《瘦碧词》行世,继与刘炳照等人举鸥隐于艺圃,取径渐广,词艺渐精。伴随着社员夏孙桐离去,词社消歇,郑文焯于时便与邓濂相契颇深,灵岩览古之词便存于《冷红词》。而后郑文焯又与邓濂次韵清真,存词见于《比竹余音》。
粗以分之,郑文焯词友可分三类:一类为同年之谊,以易顺鼎、张仲炘为代表,此类词友多志同道合、趣尚近同;一类为亦师亦友,以潘钟瑞、王鹏运为代表,此类词友多文坛耆旧、学富五车;一类则以仕宦而交,以陈启泰、邓濂为代表,多文学知己、宦游凄异。郑文焯与邓濂虽以仕宦交,但邓濂较为特殊。陈启泰曾为郑文焯府主,对郑有知遇之恩。邓濂则与郑文焯处于同一落寞境遇,甚至更为凄惨。二人经历几近相同,所以邓濂作为词友对郑文焯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透过二人的词学交游活动则能显示出,郑文焯学词进程中一种交于仕宦、感于身世、同于稽古、酬以绮罗的特殊形态。
遍观郑文焯词中涉官场之作,绝无阿谀奉承之嫌,多出之感伤离别,例如《踏莎行·重别次湘,和白石道人江上感梦之作》《踏莎行·送子苾入陕,时以庶常改官为怀远令》。抑或是诗酒饮宴,例如《声声慢·臞庵抚部晚秋宴席》。郑文焯交友不以对方势位为标准,他更侧重文学趣尚以及身世之感。而同样是交于仕宦的邓濂,郑文焯与其唱和之作,则与同类型的作品在取材、情感上有着明显的差异。郑、邓二人唱和词,多览古伤今、感叹身世,尤其多客居之感,这与二人相似的经历相关。郑文焯自寓苏以后,“客居三十余年,历为抚吴使者上客,事必咨而后行”[1]499。作为入苏之后赖以生存的职业,幕宾身份给郑文焯的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让他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客居之感。桥川时雄曾言:“‘落南’二字,先生常用之语。”[1]511而郑文焯词友之中,邓濂于此最为同病相怜。二人有太多的共同点,如年纪相仿、壮志难酬、家道中落、至亲早逝、兄弟四散、客居于吴、乞食四方等,并且这些还仅是从二人身世境遇上所得。
邓濂敏锐地捕捉到了郑文焯内心的客感,这表现在邓濂以温庭筠、李煜、周邦彦、辛弃疾等人比之于郑文焯,用以彰显郑文焯的身世之感。再者世人论柳永往往以艳俗称之,但柳词中亦多宦游凄异之慨,其《定风波》云:“奈泛泛旅迹,厌厌并绪,迩来谙尽,宦游滋味。”[21]21邓濂深熟郑文焯旨趣,故而能够一语中的。郑、邓二人的词体唱和及词学交游,使得郑文焯的词风趋于成熟,同样也让客居的他得到慰藉。面对着强烈的凄苦之感,郑文焯往往借助山水名胜来排解,如邓尉、灵岩、琴台、虎山桥、皋桥、天平山、壶园、西园等。而论及山水之游,郑文焯曾言:“佳侣难得,清独尤宜。”[26]郑文焯与邓濂“倡酬达旦”,更为难得。相近的境遇让二人均擅于凄独词风。以《秋霁》二词为例:
秋霁 郑文焯
城西艺圃,为明贤姜如农别墅。咸丰庚申之变,邻女殉池中以数百计。池莲纯白多异种,花时极游赏之盛。乙未秋期,举词社于此,因和梅溪韵,赋成是解。
残雨空园,剩水佩风裳,暗写愁色。未了琴尊,已凉亭馆,病余感秋无力。坠红信息。废池何恨成凝碧。怅故国。千里、暮云江上倦游客。
还念旧社,醉墨题襟,十年飘零,清事都寂。晚香丛、鸥边梦续,疏狂花也笑头白。一语问花应解得。又断魂处,待赋卅六芳陂,载秋单舸,冷枫江驿。[6]412
秋霁 邓濂

还念白社,石老云荒,夕阳无言,人影俱寂。更休提、秋歌梦舞,兰成年少已头白。几度思归归未得。正断肠处,又是一片猿声,背人啼遍,冷枫山驿。[3]143
二人起首都强调了一个“愁”,郑文焯是“未了琴尊,已凉亭馆”的新旧变幻之感;邓濂则是“瘦策行吟,征衫残泪”的身世浮沉之感。但二人内心极度凄苦,故而在“病余”时,“感秋”“倚阑”均无力。郑文焯用“坠红”,透露出在残局中对美好易逝、时局动荡的感叹与惋惜;邓濂则用“断鸿”,表达羁旅行役、身世浮沉的愁苦。二人侧重不同,故而一为“怅”,一为“渺”,但却都是世间“倦游客”。“倦”字,可观二人苦闷之心绪;“游”字,可见二人游离之状态;“客”字,道出了二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凄独之感。
在词的下阕,二人均开始了回忆,郑文焯追忆往日酬唱,“醉墨题襟”好不快活,但“十年飘零,清事都寂”。邓濂一生亦飘零,命途多舛,故而求于平淡隐逸。“白社”指隐逸之所,所以“夕阳无言,人影俱寂”,更休提“秋歌梦舞”。二人年纪相近,可知二人作词时,均生白发,故而一个“笑头白”,一个“已头白”;一个“待赋卅六芳陂,载秋单舸,冷枫江驿”,一个“又是一片猿声,背人啼遍,冷枫山驿”。此二词虽为分作,却有深层次上的感同身受,均含凄独客感之意味。郑文焯在哀情中透露出一丝洒脱与豪迈,邓濂则更多了些许愁苦。这样的差异,同样可以解释为何邓濂自言:“借彼杯酒,浇我块垒。”[3]277
(二)同于稽古,酬以绮罗
相同的凄独客感,让郑文焯与邓濂词格有近似之处,但深层次的词学交往,则根植于二人相近的词学旨趣。二人相通的观念与趣尚才是决定性因素。郑文焯“尚志耆古”,但不泥古,他推重白石,亦因“白石以沉忧善歌之士,意在复古”[1]218。邓濂亦好古,其《瑶情词》稿本甲卷卷尾有丁绍仪评语,借此可管窥邓濂词学尚古之旨趣:
近世词家多宗姜张,否则草窗、梦窗。学秦晏者已少,取法唐及五代者竟不易观,作者溯源温韦,力追上乘,故即眼前典、口边语,亦能运以妙笔,无语不艳,无字不香。[27]
该评语亦合于郑文焯之学词历程,他虽始于白石,但未止步于此,由《瘦碧词》时期以学习姜夔为主,到《冷红词》《比竹余音》时期,则取于诸家,尤重《花间》、清真。郑文焯曾言:
为词实自丙戌岁始,入手即爱白石骚雅,勤学十年,乃悟清真之高妙,进求《花间》,据宋刻制令曲,往往似张舍人,其哀艳不数小晏风流也。[1]221
丙戌为光绪十二年(1886),而“勤学十年”,或为虚指,但也应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左右。此时郑文焯“悟清真之高妙,进求花间”,这正与邓濂进行词学交游的时间相重合。邓濂“溯源温韦,力追上乘”,“取法唐及五代”等词学宗尚均合于郑文焯,如郑文焯所言:“近悟词家比兴之作,唐、五代为最上。”[1]278取法乎上,郑文焯与邓濂都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郑文焯“悟清真高妙”时,邓濂亦参与了郑文焯《兰陵王》次韵清真唱和活动。二人的词学交游活动随邓濂的离世而终止,但在仅有的记录中,却可见二人词学观念上的契合。值得注意的是,郑文焯与邓濂交往之时,处于鸥隐词社活动之后期,郑文焯此时与邓濂、刘炳照共有着紧密的词学交游活动。除邓濂外,郑与刘有同社之谊,因此郑与邓的交往更可以看出二人趣尚之接近,以及郑文焯游离于词社之外的学词进程。以往论者更重视通过郑文焯结社情况去分析其词学,却忽略了其词社之外的词学交游活动对其词艺的影响。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郑文焯反对侧艳之词。虽然丁绍仪评邓濂:“无语不艳,无字不香。”但邓濂一生辗转,生活窘困。其词虽取法温、韦,自然有温、韦之形,但却不取绮丽柔靡一面,内蕴更多的还是身世之感。与郑文焯相近,邓濂后期词作比之于年少之词,凄恻之情充溢其间,绝不是单以侧艳出之。除去与郑氏唱和词,其自作词中亦可见一二。邓濂《贺新郎》有句云:“春风不惜秋蓬命。怅年来,飘零吴楚,飞栖无定。”[3]136《贺新凉》云:“乞食黄尘里,天地酷,有如此。”[3]138凄独之风,可见一斑。而透过他为郑文焯所撰写的序言,更可见二人共同关注世变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感内核。
郑文焯曾草拟“石芝西堪宋十二家”之名目,小令五家,即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秦观;慢曲七家,即柳永、周邦彦、苏轼、辛弃疾、吴文英、姜夔、贺铸。这与邓濂序言中所列举之人几近吻合,但这并不是巧合,而是显示出邓濂熟稔郑文焯之词学家世以及作词、评词的部分标准。郑曾言:“周、柳、姜、吴为两宋词坛巨子,来哲之楷素,乐祖之渊源。”[1]34郑文焯论词重音律,其中似柳永、周邦彦、姜夔、张炎等人均擅于音律。另一方面,郑文焯论词又重“清空骨气”,他评温庭筠《杨柳枝》:“唐人以余力为词,而骨气奇高,文藻温丽。”[1]1评柳永:“其骨气高健,神均疏宕,实惟清真能与颉颃。”[1]17评周邦彦词:“清真长调骨力奇高。”[1]56且郑文焯曾言:“学者能见柳之骨,始能通周之神,不徒高健可以气取,淡苦可以言工,深华可以意胜,哀艳可以情切也。”[1]18郑文焯取博而用精,兼得友朋之助,故能自著伟辞。邓濂不仅谙熟郑文焯的词学旨趣,且郑文焯词学发展精进之时,邓濂不仅是见证者,更是其中的应和者。二人旨趣近似之处,又并不局限于词学。二人作文都推重六朝,邓濂曾自言:“骈文应以六朝为宗。”[3]291而郑文焯亦自言:“余少日最不喜为帖括,为文专拟六朝。”[1]221据此亦可见二人趣尚之近。郑文焯与邓濂于词推重唐及五代,同于稽古,而又屡屡唱和,酬以绮罗,可见二人词谊之深、词心之相契。郑文焯词友较多,但同推柳永之人,则屈指可数。邓濂直将郑文焯比之于柳永,亦可见二人于词学上的深入交流。
四、结语
郑文焯与邓濂曾有密切的词学交游活动,在郑文焯较为重要的词学观念转变过程中,邓濂皆是其见证者及应和者,对其词学主张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邓濂因病而逝,二人词学交游便戛然而止。邓濂于《瘦碧词》阶段便关注郑文焯,而后又与郑文焯唱和于《冷红词》阶段,最终结于《比竹余音》之初期。虽然二人词学交游相对短暂,但可见二人词学观念的高度契合。二人同客苏幕,身世相近、旨趣相通,故而能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鸥隐词社活动渐歇之后,郑文焯仍与邓濂、刘炳照、缪荃孙、冒广生等人进行词学上的交游互动。邓濂虽未入鸥隐词社,但无名有实,与社员结下了深厚的词学情谊,其姓名屡见于鸥隐社员书信之中。寒碧词社建立以后,虽然邓濂已逝,但刘炳照致缪荃孙书信之中仍然忆及郑文焯与邓濂:“寒碧词社每期交卷不过四五人,屺怀家事困衡,叔问境遇拂逆,不暇复唱,渭城、复堂老病,磵盟、石瞿、蒙叔相继下世,同好零落。”[16]读此令人不胜唏嘘,亦如郑文焯所言:“总之文人固分漂零也。”[1]262
——评《民国时期词学理论批评衍化与展开研究》
——从《词学》看施蜇存的办刊精神
——评陈水云教授新著《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