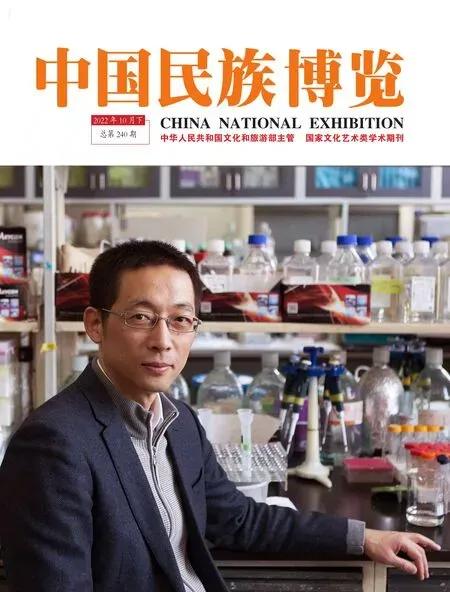道家审美视角下的老君岩造像美学意蕴研究
刘琴姐
(厦门工学院博雅教育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清源山位于泉州北郊,素有“道教圣地”之称。据《泉州府志》载,清源山开发于秦,鼎盛于宋元。现存宋元石造像、摩崖石刻600 多处,雕凿于北宋的老君岩,是我国体量最大、最具艺术价值的道教石雕。
为何在宋代的泉州会出现如此大体量的道教造像?为何这尊雕像具有浑然天成的艺术感染力?其审美特征为雕刻艺术提供怎样的艺术参照?本文将从四个角度来探讨。
一、老君岩产生的“精神气候”与“经济气候”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到,一种艺术形式的出现,依赖于“精神气候”[1]的形成。“经济气候”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也是精神文明体系的基础,因此,“精神气候”与“经济气候”相互关联,共生互动,一起促成特定艺术形式的产生。老君岩诞生于宋代的泉州,便有赖于其特定的“精神气候”与“经济气候”。
道家思想来源于《周易》《道德经》,学术界认为,道教创始于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和五斗米教。自此,老子被奉为“太上老君”,《道德经》《正一经》被奉为经典。古代闽南先民崇拜自然山川,盛行巫卜鬼神之风。晋朝衣冠南渡,道教随中原宗教文化传入,结合当地鬼神崇拜,促成闽南宗教文化的多元态势。泉州府建立的第一座道观称白云庙 (玄妙观的前身),建于西晋太康三年,成为泉州道教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宋朝官方在承袭儒释道兼容的基础上扶持道教。由于宋徽宗笃信道教,大量道观建于宋代。为此风气所传,泉州也兴起建造道观的风潮。诸多著名道观,始建于宋代。位于泉州涂门街的通淮关岳庙,就是始建于宋代[2],至今仍香火鼎盛。东凤山东岳行宫、万岁山真武庙,泉州城内的天后宫、龙宫庙、净真观,以及惠安崇真观、安溪通元观等,这些散布极广的道观,说明泉州历史上道教的兴盛。宋代泉州官吏时常亲自主持祈风、祭海等活动,利用宗教活动来推动泉州港的兴盛。泉州清源山老君岩造像,就是在宋朝政府重道的“精神气候”下产生的。它是泉州现存最著名的道教遗迹,见证了一个时代道教的繁荣。最初,老君岩造像周边有真君殿、北斗殿等道观,年久倾废,仅剩老君岩端坐天地间,与大自然和谐相融。
宋代的泉州港成为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口,在对外文化交流当中,儒家、道家作为华夏传统文化代表,在多元文化荟萃的泉州成为主流。随着海上交通的发达,道教文化也随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国外。商贸鼎盛,民间资本雄厚,在“重道”的氛围中,必然会雇用能工巧匠来修建道教殿宇及造像,这便是老君岩造像所依赖的“经济气候”。可以说,老君岩造像标志着宋代泉州道教艺术的兴盛,也见证了“海丝”文化的活跃。
二、雕刻技法蕴含“道法自然”的审美追求
闽南石雕经历了晋代、南北朝、隋唐的发展,到了宋代,造像技术日臻成熟,雕刻语言和技法也日渐丰富。最初,闽南石雕主要服务于宗教,一方面体现在宫庙的建筑架构以及寺内亭台楼阁的建造雕刻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神佛造像及传统墓葬石像生的雕刻上。建于宋代的泉州东西塔,以其精美的佛道人物、祥禽瑞兽雕刻,不仅反映当时闽南石雕技艺的精湛水平,也体现宋代人崇尚精巧细腻的审美取向。
老君岩石像同样建于北宋,却并没有刻意呈现精巧细腻的时代审美,而是由整块天然岩石来略加修饰雕凿而成,其衣纹简洁,略作阴刻处理,并无较大起伏,凸显朴素天真的审美趣味。清代《泉州府志》记载:“石像天成,好事者略施雕琢。”[3]为何在崇尚精妙细腻之美的时代,会出现这样一种“略施雕琢”的写意手法?这值得我们探讨。
近观之,石像做跨鹤坐姿,左手扶膝,右手靠着小矮几,双目深邃旷远,两耳垂肩,须眉皓然。老君岩造像衣褶简洁分明,刀法柔而有力,须发雕刻细腻精到,层次分明。其朴素而神态毕现的韵味,疏密有致的雕刻线条,质朴混沌的,天人合一的意境,使之充盈着艺术的生命力。最妙在于眼部雕刻“有眼无珠”,没了瞳孔的聚焦,眼神显得极为空远,如此巧妙的处理手法,凸显“空纳万物”语义(语出苏东坡“空固纳万物”),“空”代表着含容与接纳的状态,因此可以承受万物。这种空远眼神,亦恰到好处地契合《道德经》的“大方无隅”。远观,整座雕像峨然而坐,似乎从天地间生长出来一般,极为和谐。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正是对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的阐释。老君岩造像从整体到细部,与《道德经》文本深度契合,说明了两个问题:1.文化传播往往诉诸符号,当时浓郁的道教文化氛围,影响了老君岩的雕造者,他在对老子思想深刻把握的基础上,以其特殊的雕塑符号,将道家经典文本思想外化为艺术形象。2.老君岩雕造者绝非普通小工匠,无论从其对道家文本的把握还是对艺术手法的选择,都体现出其高超的领悟力和艺术表现能力。
类似的形象塑造,我们可以在北宋李公麟《维摩演教图》中看到,图中维摩诘也是跨鹤坐,一手扶膝,一手倚几,神情泰然,作论述状。整幅作品用墨线勾描,人物造型严谨,笔法精妙。遒劲圆转的游丝描和铁线描相辅相成,既巧妙刻画了人物神态,又演绎了佛教教义。佛像画自晚唐兴起崇尚华丽之风,后世相沿成习,后来宗教意识式微,壁画形式减少,立轼形式渐多,于是更趋于细致精工。《维摩演教图》人物造型及细部装饰显然受此影响。绘画佛像,除了法相和手印外,还有相对严谨的度量。人物神态,要表现佛的智慧与功能“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无缺”。因此维摩诘居士面容饱满,嘴角眉宇间透露出庄严、慈悲与静穆。对比同时期两件作品,可以看出,道教与佛教审美追求的异同。老子所谓“道法自然”,庄子所谓“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4],皆推崇不事雕琢、朴素天真的自然之美。道家美学追求,正是自然朴拙之美,是不纹饰之美,是意在象外之美,这种审美趣味在老君岩造像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给我们的启示是:艺术佳品应循自然之势,一气呵成,不事纹饰,而达到气韵生动的境界。
三、朴素审美成就道教造像的特殊气质
道家作为传统文化重要部分,与儒家审美理念有显著差异,儒家强调“仁”与“善”的追求,表现在艺术创作中,强调艺术“美”与伦理“善”的统一。相对儒家审美的“守秩序”,道家审美为世人营造宽广无碍的自由意境,主张不拘泥世俗之美,追求一种超越,去掉人为造作,恪守自身质朴本性,追求自然的大美。这种朴素的审美理想,在历代道教造像中,得以充分体现。据史料,道教最初仅供奉神位而不供奉神像,由于印度佛教的传入,佛教造像的兴起,刺激了中国传统雕刻艺术,因此道教也有了造像活动。纵观艺术史,道教造像相对较少,现存较有影响力的有西魏大统老子碑,开凿于宋代的四川石门山摩崖造像,开凿于元代的山西太原龙山石窟、四川青城山的三皇造像以及本文主要关注的泉州清源山老君岩。
道教的造像技术和风格,随着道教文化的发展和时代审美的变化,在不同的朝代和地区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但总体而言,道教的造像相对佛教造像更为朴素和简洁,人物造型及表现手法都相对简单,从这一侧面,似乎可反映出道家追求“自然”“朴拙”的审美意趣。
传统道教形象通过“以形传神”来体现内在思想。早期道教人物造像皆是清骨秀像,着宽大道袍,衣纹线条匀称,通常采用深直平梯式,以浮雕技法,细密而凸起。始凿于北魏末年盛于隋唐的四川鹤鸣山道教石窟造像,便是道教早期至隋唐造像的代表。1 号窟乃圆雕立体道教造像,现存于露天。造像面颐丰满,身着宽领道袍,右手下垂,左手五指并拢,掌心向外往上举,手势显然受佛教造像的影响,但整体形象古朴,与佛造像之华丽迥异,给人以严肃庄重之感。早期“五斗米教”人物造像大都集中在四川地区,鹤鸣山的“五斗星纹图”,极具代表性地将“五行”学说和“五斗经”“五斗米”内涵集中呈现,以其独特的艺术符号,建立早期道教造像的艺术语言体系。
隋唐时期,道教造像在统治者的扶持下蓬勃发展。在道家审美的统摄之下,道教造像的雕刻语言和表现形式,一直有其独特的风格倾向,即表情淡然、仙道风骨、衣纹简洁、手法朴素。开凿于北宋绍圣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间的四川重庆石门山石刻,是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的佛、道二教结合的石刻群,尤以道教造像最具特色,被誉为“宋代道教艺术绝巅”。[5]
石门山道教造像造,雕刻手法粗犷而生动,将神之威严与人活泼巧妙结合。如2 号窟的千里眼雕像,眼若铜铃,肌肉丰健,简洁粗犷而富有张力。10 号窟道教文官造像,儒雅清秀,衣纹舒展,以朴素的造型呈现仙道风骨。石门山道教造像的清秀、传神,在道教石刻造像史上堪称经典,这得益于宋代精致细腻的审美取向,但与同时期的佛教造像相比,道教造像仍显得衣着朴实、头饰简单、纹饰舒展。这里蕴含着道教一以贯之的“见朴抱素”审美取向。相比同样雕凿于北宋的清源山老君岩,以其“精美传神、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从更深层面蕴含着道家的审美意趣,以形布道,将道家“清静无为”“大巧若拙”的思想展现无遗,可谓体现了道家审美的精髓。
山西太原龙山石窟,主窟开凿于元代太宗年间,共8 窟,有道教石雕像66 尊,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元代道教石窟群[6]。经过历代发展,元代道教造像已相当成熟,此时风格仍是凝练、庄重,渗透道家审美趣味,雕像衣饰简练、褶皱分明,无太多装饰,与佛教石窟雕像风格相左。道家文化和审美意趣,对于道教造像的影响极为深远。从道教文化的角度去探究道教雕塑的审美造型和艺术表现,[7]以及这种表现形式和审美产生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一项课题。
四、道家审美对其他石雕的影响
历来无数学者对“道家文化”做了大量研究和探索。道家学说以老子提出的“道”为基点建立理论体系,把“道”作为宇宙本体,万物规律,认为“道”是超越时空的神秘存在;老子、庄子提出的“清净无为,抱朴见素,大道至简、守一、坐忘”等思想,被后世推崇发扬,[8]虽然作为世俗宗教的道教与道家学说不可同日而语,但也颇受其影响,而道家审美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趣味,形成一套独立于西方审美之外的东方美学体系。
在艺术界一直存在写实和写意两个范畴,写实是对客观事物的描摹,忠于自然,如镜子照物,强调“像”。写意强调“神似”,把事物作为寄情对象,从而摆脱时空观念和自然属性的约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语出《庄子·齐物论》),在这种道家观念指导下,天地造物随其剪裁,从宏观上把握物象,追求艺术表达的自由[9]。可以说,“写意”是探索其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精神世界,这是读懂作品精神内核的钥匙。“写意”对中国艺术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历代艺人在绘画、书法、雕塑、建筑、民间工艺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多种探索,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面貌。
这种探索,我们在汉代石雕作品可窥见端倪,并似乎可将之视为该类探索的开端。在陕西霍去病墓石雕中,一组以“马踏匈奴”为主体雕塑的石刻作品屡屡被人们提起,成为美术史上的经典佳作,甚至成为一个时代风貌的代言。一组石雕作品能有这么大的威力,这与其背后潜藏的审美方式和时代精神有着深层的联系。马踏匈奴石雕战马外形简练有力,整体追求躯体彪悍的风格,马蹄下的人模糊不清,与马交织,细节若隐若现,远观则呈现一种庞然之气。而伏虎、跃马、卧象等石雕则按照石材原有的形状,在关键部位精雕细刻,其他部位略加雕琢,以浪漫写意的手法、丰富的表现力和高度的概括性来彰显对象的神情和动感,风格朴拙、气势豪放,暗合“道法自然、大道至简”的道家审美,也让我们联想到庄子的“得意而忘言”,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王弼的“得意忘象”。
将霍去病墓石雕与道家思想联系起来,并非无厘头的牵强附会。一种艺术形式的出现,往往有某种思想学说在引领,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思想气候”。恰恰在东汉,道教作为一种新的宗教形式产生了,他们推崇道家思想,并影响了中国文化数千年之久。从上文我们探寻的历代道教造像的朴素审美可得知,道家审美取向在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们也可做大胆假设,在宋代泉州,老君岩雕造者在构思老子造像表现手法时,从历朝各种艺术手法中选择了最契合老子文本解读的表现形式,从而溯源到“马踏匈奴”的写意精神。对于一位领悟力极高的巧匠来说,通常是见多识广并对各种风格技艺了然于胸,在面对不同雕凿对象时,可灵活运用或精微或雄浑或朴拙的不同风格,以达到“传神”的艺术高度。此位巧匠在对老子文本深刻把握的基础上,以“大巧若拙”的写意手段,展现了对道家精神境界精微的体认观照,对宇宙物象体贴入微的辨察。
虽然纵观我国数千年石窟历史,类似于霍去病墓石雕这种气势磅礴的大写意表现手法并没有在佛教造像上得到大力弘扬。例如,始凿于北魏的云冈石窟,早期“昙曜五窟”,呈现朴素和伟岸的风格,与道家朴素大气审美尚有一些联系,可到了中期,云冈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展现了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10]到了晚期,窟室规模变小,人物形象趋于清瘦俊美,开启了“瘦骨清像”的佛造像风格。这一发展轨迹与“朴实凝练、天然浑厚”的道家审美越走越远。随着道教的逐渐式微和佛教的几度兴衰,到了清代,佛教造像石刻较少,多为泥胎、铜塑,工艺登峰造极,身材、五官、衣纹、配饰等追求“精致”,与道家审美迥异。由于统治阶级的关注较少,此时道教只是作为一种传统宗教在民间流行,塑像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所欠缺,且保存不多。道教造像虽式微了,但其审美意趣仍深刻影响一代代雕塑创作者。
在泉州惠安崇武古城海边的“鱼龙窟”群雕中,我们猛然瞥见那“混沌之气”“天然雕饰”的道家审美的身影。这组“大地岩雕”和浙江大鹿岛岩雕,都是中国美院教授洪世清在20世纪90 年代,历经数载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洪世清融合浮雕、圆雕和线雕等多种技法,以夸张变形的大写意手法,因石赋形,依海而凿,尽显自然美、残缺美的魅力。其作品粗犷浑厚、苍莽奇崛,成为中国当代岩雕代表之作。这是对秦汉雄浑大气艺术风格的承继,是对宋代老君岩“以石赋形”艺术手法的呼应,是对“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审美趣味的完美诠释, 也体现中国传统艺术对“意”的表达。
在雕塑家吴为山的《孔子》《老子》《鲁迅》等作品中,我们同样看到那种“混沌之气”,那种“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理论。他的写意人物,主要特点是展现形态的夸张意象、凸显人物的隐性特征、将自然意象山水流韵融入雕塑,构建人物雕塑的独特意境。其中《老子》以18 米的超大体量和混沌沧桑,给人以巨大的审美冲击。其朴拙、厚实、深邃的审美特质,如同老子的思想一样,简洁而丰富、深刻而博大,其弓背敞怀的形态,凸显虚怀若谷、玄妙之门的意象,使老子的形象与思想同样巍然耸立。此类作品是雕塑家受道家“道法自然”审美追求影响的有利佐证,其写意形态,呈现“见素抱朴”的自然之美,也阐释了艺术佳作所蕴含的“气韵生动、本乎自然”气质。而这也正是对道家审美的发扬,是研究道家审美风格脉络的珍贵资料。可见,道家审美文化中“道法自然”“见素抱朴”等经典命题,很大程度影响着中国造像艺术写意风格的形成和发展。
五、结语
综上,本文以泉州老君岩为切入点,梳理道教石造像的朴素审美的大体脉络。从道教文化的角度去探究道教雕塑的审美造型和艺术表现及其影响,是值得深思的一项课题,为当代雕塑家提供摹古与创新的参考依据。笔者认为,以老庄为代表的的道家审美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在当下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道家“道法自然”“混沌之气”的美学意趣,成为东方审美的特质,植根于中国传统诸多石雕像领域,以其特有的自然旨趣、直觉观照,丰富了中国当代雕塑美学的思想创构及精神意蕴。
——泉州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