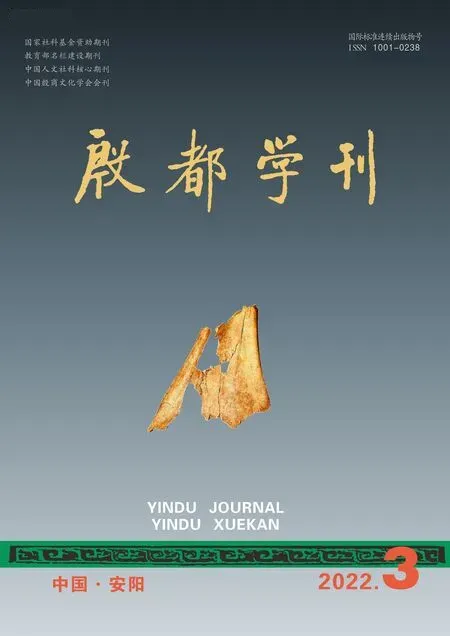李学勤先生与甲骨学研究
任会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100101)
2019年2月24日,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病逝,享年86岁。李学勤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于中国先秦秦汉史、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等领域,均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研究范围涉及上古史、甲骨学、青铜器、金文、战国文字和简帛学、学术史等诸多方面。李先生一生刻苦,不倦于学术,共留下四十多部著作,千余篇论文,被誉为当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李学勤先生学术兴趣广泛,而其中甲骨学是李先生极为重视和关注的领域之一,甲骨学虽不是李先生研究的最核心,但是李先生以渊博的学养、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开阔的视野,做了很多深入研究,承前启后、高屋建瓴、新见层出、影响深远,极大推动了甲骨学科发展,堪称是新时期甲骨学研究的代表人物。
一
李先生最早走上学术道路就是在甲骨研究方面。因自幼对“符号”知识感兴趣,李先生于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进行数理逻辑方面的学习。而早在中学时期,李先生就已熟读过一些甲骨文专业书籍,他曾在访谈中提及:“1950年,也就是考入清华的前一年,甲骨文引发了我的浓厚的兴趣。在我看来,甲骨文是另一类符号,也像逻辑符号一样,非常难懂,令我着迷。”(1)陈颖飞:《从追寻符号的魅力到探索中国古代文明——李学勤访谈录》,《邯郸学院学报》2013年(S1期)增刊。而李先生学习甲骨,完全是自学,当时所仰赖的只有北京图书馆,就这段学习经历,李先生曾回忆到:“我仔细读了《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也看了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和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的《殷虚文字甲、乙编》的序。我还看了陈梦家先生的文章,他的《甲骨断代学》正在《燕京学报》等刊物上陆续发表。我发现他关于甲骨断代,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甲骨分期的看法与董先生有些不同。后来,我又看到日本贝塚茂树、伊藤道治两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法之再检讨》。”(2)李学勤、邹兆辰:《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学科多领域探索——访李学勤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4期。同时,这段时间,李先生也阅读了大量其他文字学、音韵学方面的专业书籍。
抗战胜利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历次殷墟发掘的成果名为《中国考古报告集·小屯》陆续整理出版。就甲骨材料而言,一至九次发掘为《殷虚文字甲编》,十三、十四、十五次发掘为《殷虚文字乙编》。董作宾先生于《乙编》序中提出殷墟第十三次发掘所见的YH127坑甲骨中部分是“文武丁卜辞”,并以此将甲骨分为新旧两派,“文武丁卜辞”争论由此开端。李先生当时对此问题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集中著录此批材料的《殷虚文字乙编》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其中尝试作了很多的缀合工作。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哲学系归入北大,不过由于陈梦家先生的推荐,李先生并未继续北大的学习,而是来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曾毅公先生一道进行郭若愚《殷虚文字甲编》及《乙编》缀合文稿的补充和修订。这一工作从1952年持续至1953年末,1955年,修订成果《殷虚文字缀合》(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缀集:《殷虚文字缀合》,科学出版社,1955年。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亦成为李先生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本书第二部分共158版甲骨即为李先生和曾毅公先生所缀。《乙编》下辑至1953年才于台湾出版,因此当时所见仅有上、中辑,故而材料有所缺失,但本书从内容而言,尤其是在《乙编》下辑和《殷虚文字丙编》传至大陆前,还是具有非常大的价值的,如郑振铎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说:“(此书)为研究甲骨刻辞的学者们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资料。”
1954年春,缀合工作结束不久,21岁的李先生便在侯外庐先生的引荐下到中国科学院刚筹建不久的历史研究所上班,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1954年夏,他进入侯先生领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组工作。因此,从此时到1965年这段时间,李先生围绕思想史做了不少工作,但他对甲骨文尤其是当时学界围绕甲骨分期展开的讨论依然非常关注,相继写出《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等重要文章。
在《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一文中,李先生针对甲骨分期提出了新的观点,明确了“分类”和“断代”的区别,指出“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我们应该先根据字体、字形等特征分卜辞若干类,然后分别判定各类所属时代。同一王世不见得只有一类卜辞,同一类卜辞也不见得属于一个王世。”(4)李学勤:《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又《李学勤早期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2页。这一观点以考古学理论为前提,是对当时传统观点的重大突破。当然,随着材料的充实,文章中的个别看法和细节在日后做了进一步的修正,但此文可以说为后来新甲骨分期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晚年,李先生于清华大学讲授甲骨文时曾经这样说过:“一门科学的产生,每每就是一个思想,比如说分期,我有什么贡献……,就是我所提出的一个观点:一个时代,一个王世,不只有一种卜辞,一种卜辞也不只存在于一个王世。”(5)根据2006年李学勤先生于清华大学所讲授甲骨文课课堂录音整理。

非王卜辞对于商代家族形态、社会等级制度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非常重要。李先生晚年对花园庄东地甲骨,尤其是围绕“子”“丁”等进行了专门研究,在《花园庄东地卜辞的“子”》(8)李学勤:《花园庄东地卜辞的“子”》,《河南博物院落成暨河南省博物馆建馆70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又《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李学勤卷》,北方联合出版传媒,2010年,第126-130页。一文中指出花东H3卜辞“子”内涵较爵称之“子”要广泛,可推定为朝中大臣。而花东卜辞常见人物“丁”与干支之“丁”形同但音义不同,是“璧”字初文,读作“辟”,为王之称谓。(9)李学勤:《关于花园庄东地卜辞所谓“丁”的一点看法》,《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又《李学勤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48-151页。
李先生这一时期另一项重要工作即在《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10)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又《李学勤早期文集》,第33-37页。一文中,首次确定了西周有字甲骨的存在。1954年,山西洪洞县坊堆村一灰坑内发现一版完整带字胛骨,辞见:“化宫□三止又疾贞。”李先生从其辞例,结合“止”“疾”“贞”等文字特征,指出卜辞明显晚于殷代,系西周时无疑。文章同时指出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上发现的有字甲骨,“记数的辞和殷代卜辞显然不同,而使我们联想到《周易》的‘九’‘六’。这块卜骨出土于‘周代灰层’,应当是西周时代的东西。”“它们不但进一步证实了在殷虚(安阳小屯)以外有有字甲骨存在,而且证明了周代也有有字的卜骨。”并于结尾处断言“我们相信,在将来必能发现更多的非殷代有字甲骨。”众所周知,之后无论是在周人发祥的周原地区,还是在西周边裔诸侯国,都陆续有数量丰富的西周甲骨出土。伴随材料的不断公布,以往凡甲骨必殷商的传统看法被打破,西周甲骨——这一全新的甲骨学研究分支诞生并日益壮大。可以说,李学勤先生对这一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对之后不断发现的西周甲骨,李先生也围绕相关材料的特征、释读、性质、族属等问题,一直有持续的研究,著述丰硕。(11)主要的研究专文有:《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文物》1981年第9期;《续论西周甲骨》,《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周文王时期卜甲与商周文化关系》,《人文杂志》1988年第2期;《再谈洪洞坊堆村有字卜骨》,《文物季刊》1990年第1期;《邢台新发现的西周甲骨文》,《中国文物报》1993年3月7日;《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周易研究》2003年第5期;《周公庙卜甲四片试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周公庙遗址祝家巷卜甲试释》,《古代文明(辑刊)》,2006年;《论周公庙“薄姑”腹甲卜辞》,《文博》2017年第2期等。
1959年,李学勤先生《殷代地理简论》(12)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又《李学勤早期文集》,第157-277页。一书出版,此书成稿于1954年,即李先生21岁时。此书采用地理排谱的方法,以详实的研究纲要形式,借助于卜辞材料,对商王朝的疆域、主要城市位置、山川名称、方国及关系、对外战争等诸多问题作了系统论述。书中指出殷商田猎区主要是“商西猎区”,范围“是东起今河南辉县,西至山西西南隅及其以西,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而“商王狩猎是有一定日期的”,“文丁以前,商王猎日以乙戊辛壬为常,丁日为变;帝乙、帝辛时略予放宽,以乙丁戊辛壬为常,庚日为变”。同时,通过排比相关卜辞,将田猎地,按同版同辞关系分为凡、敦、盂、邵四小区,并对每小区可系联的主要田猎地名进行了论说。文中还对称“商”地名与地望,及土方、鬼方、危方、羌方等重要方国进行了考辨。此外,“商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一节,明确将“政治地理”概念纳入以卜辞材料为主的商后期地理研究中,从一个更高的学术层面,揭开了甲骨文商史新课题研究的序幕,展示了一个很有气魄的商后期政治地理研究框架。(13)朱凤瀚:《永远的学术导师——纪念李学勤先生》,《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虽然书中个别观点在后来有所修正和调整,但诸多论述,创见颇多。本书为首部专门的殷商地理研究专著,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后来的商代地理研究。
事实上,殷商地理研究非常重要,但也是颇为不易,在方法和材料上都有很多困难。关于利用卜辞研究殷商地理,李先生多年来也一直有所涉及,如于《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中对战争和田猎卜辞中的方国、地名进行了讨论(14)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33-385页。;《有逢伯陵与齐国》(15)李学勤:《有逢伯陵与齐国》,《管子学刊》编辑部编:《齐文化纵论》,华龄出版社,1993年,又《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李学勤卷》,第433-439页。一文利用卜辞等材料结合文献,对“逢”国商周时期的地望、迁徙及相关联之“寻”地进行了考证;又如《释郊》(16)李学勤:《释郊》,《文史》第36辑,又《李学勤文集》,第162-166页。一文,据《屯南》59卜辞等材料,将旧所谓“亳”字改释为“蒿(郊)”,为解决“亳”地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此外,《甲骨百年话沧桑》一书中《商朝的地理结构》(17)李学勤:《甲骨百年话沧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9-53页。一节及《夏商周与山东》(18)李学勤:《夏商周与山东》,《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又《李学勤文集》,第107-119页。等专文都涉及了卜辞中的殷商地理,而“夷方问题”,李先生多年来更是一直给予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有多篇文章。
另外,发表于1957年的《论殷代亲族制度》(19)李学勤:《论殷代亲族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1期,又《李学勤早期文集》,第71-85页。一文,结合甲骨材料对商亲属称谓中的“亲称”“日名”做了考察,探讨了当时的继承法和亲族制,文中商日名为死后选择的观点,在学界影响广泛,就此问题,李先生后期又有所补充(20)李学勤:《日名的卜选》,见李学勤:《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6、77页。。文中还对《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985、1106两版进行了缀合。
二
文革后,李先生将较多的精力投入到对青铜器、金文及新出简帛等的研究,但对甲骨的关注一直没有中断,尤其围绕分期断代,李先生作了大量工作,对新时期甲骨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直至1976年,李先生以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契机,开始对传统的五期法重新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梳理。他首先在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召开的妇好墓座谈会的发言中,提出了“历组卜辞”的概念——“有卜人历的卜辞,可试称为‘历组卜辞’”,并据“历组卜骨的许多人名、称谓同于武丁以至祖庚卜辞”等,指出“历组卜辞很有可能是武丁晚期到祖庚时期的东西”(26)《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考古》1977年第5期。。后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27)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第11期,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63-277页。这一重要文章,对历组卜辞的年代做了进一步的论证。文章指出:“按照旧的五期分法,历组卜辞被认为属于武乙、文丁时的第四期。新出土的各墓青铜器及玉石器上的文字,其字体更接近于历组卜辞。但是,如果把墓的时代后移到武乙、文丁,又是和所出的陶器、青铜器的早期特征无法兼容的。”文章从“字体演变”“卜辞文例”“历组卜辞人名”“历组卜辞事项”“历组卜辞称谓”等五方面,证明“历组卜辞其实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卜辞,历组和宾组的妇好,实际是同一个人”。
“历组卜辞问题”由此正式提出,此后学界围绕“历组卜辞”展开了深入且长期的讨论。裘锡圭、彭裕商、林沄等学者相继发表专文专著(28)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彭裕商:《也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四川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1983年1期;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给新说以有力的补充。而李先生对此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化,如在《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29)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第5期,又《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李学勤卷》,第75-88页。一文中,李先生指出小屯南地甲骨《屯南》2342与出组《萃编》250为一时所卜,辞中“祖乙、丁”与“小乙、父丁”为同指,“丁”“显然是武丁”。另《屯南》2384则是历组、出组同版,“是出组、历组同时并存的例证”。后又在《论小屯南地出土的一版特殊胛骨》(30)李学勤:《论小屯南地出土的一版特殊胛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期,1981年。一文中,结合《屯南》2384,对所谓“同版不同期”说进行了讨论,从内容、辞例、钻凿、字体等进一步确定其为“历、出同版”无疑。
就卜辞同版异组,当是历组断代的一个重要信息,李先生后来也有持续考证,如《甲骨文中的同版异组现象》(31)李学勤:《甲骨文中的同版异组现象》,《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50-153页,又《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5-78页。一文,将十例材料分为“卜辞同版”“署辞、卜辞同版”“卜辞、干支同版”三类,指出:“凡与历组无关的,都有明证是同一时期的。由此推知,与历组有关的几例,也是同一时期的。”其后,又于《〈合集〉32921和甲骨分期》(32)李学勤:《〈合集〉32921和甲骨分期》,《殷都学刊》1999年第1期,又《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第184-188页。一文,指出《合集》32921甲骨为出组二类署辞与历组卜辞同见,“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显示出历组卜辞实际的年代”。就卜辞“同版不同期”现象,在《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中,亦有集中论述。(33)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第224-240页。

“历组卜辞”问题的提出与和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卜辞分期与断代研究理论水平的提高,而其“不仅涉及甲骨分期全局,对殷墟文化的分期也有一定影响。”李先生继而利用新材料,结合新的“分组”体系,形成了甲骨分期“两系说”这一全新理论。


“甲骨卜辞发展的‘两系说’,历组卜辞时代提前等新见解是建立在对卜辞内涵深入分析基础之上的”(43)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他们科学客观地总结了殷墟各类卜辞的主要特点,对其前后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可以说,“两系说”的提出和探索,标志着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上新突破,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极大地推进了新时期的甲骨分期研究工作,其起例发凡,意义重大,非同一般。
解放后的甲骨学领域的主要成就,简言之可集中于材料著录和分期研究两大方面,而分期研究一直是甲骨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围绕甲骨分期,李先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也作出了非凡的贡献。李先生曾如此说到:“我在殷墟甲骨分期研究这个课题上,工作前后有四十多年,道路的曲折,前进的艰难,迥非我起初所能想见。不过分期工作是考古遗存研究的基础,我觉得这份艰辛是值得的。”(44)李学勤:《我和殷墟甲骨分期》,《李学勤文集》,第133页。
此外,《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一文也是李先生近五十年来所长期关注的“夷方”问题的一次总结。李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于《殷代地理简论》中就将田猎卜辞与征人方卜辞相联系,排出从“十祀九月甲午”至次年“四月癸酉”,历二十二旬七个月的征人方历谱与路线。就此问题,李先生一直探索不辍,后在《重论夷方》(45)李学勤:《重论夷方》,《民大史学》,1996年第1期,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第90-96页。一文中就征夷方途中所经“杞”“索”两地进行了考证,指出:“索”据兖州李宫村所出铜器当在山东兖州,而“杞”,由杞妇卣铭等材料,可知“(杞妇卣)器主系亚醜族氏之女而嫁于杞者。亚醜青铜器集中出于山东益都苏埠屯,杞当距之不远,新泰在位置上是适宜的。”(46)就“杞”地望之问题,李学勤先生曾有详细论证,具体可参阅《海外访古续记·杞妇卣》(《文物天地》1994年第1期)。李先生还以作册般甗、小臣艅犀尊等相关铜器铭文,证明夷方就在山东东夷之地,“商末的尸方还是应该读作夷方,与东夷为一事。”对《殷代地理简论》中人方于西部的观点作了调整。2002年,李先生又在《夏商周与山东》(47)李学勤:《夏商周与山东》,《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又《李学勤文集》,第113、115页。中指出:征夷方卜辞中的“淮”可能是“潍”,“也就是现在的潍坊”,“商人征夷方的地点大多在山东。”而发表于2005年的《论新出现的一片征夷方卜辞》(48)李学勤:《论新出现的一片征夷方卜辞》,《殷都学刊》2005年第1期,又《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34-138页。一文对后见于《殷墟甲骨辑佚》689片的一版黄组“征夷方”卜辞进行了讨论,指出“夷方居于商朝的东方,在这里得到了终极的证明”,且征伐的起因、准备、征战、得胜各环节已基本可以完整串联。《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49)李学勤:《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又《文物中的古文明》,第186-194页。一文则通过《屯南》数版无名组晚期伐夷方卜辞,明确“黄组卜辞该方国名号只能是‘尸(夷)方’,不能读为人方。”其地望在今山东中东部,都邑为淄、潍之间的鲁北地区。及《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一文,则确认《屯南》无名组征夷方卜辞与《合集》黄组征夷方卜辞为同一王世之事,这样帝辛征夷方的整个过程,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起因、准备、过程、战况等,都得以明确,相关史事可排出一帝辛九至十一祀征夷方的完整祀谱。可以说,《扩大》一文不仅反映了李先生甲骨分期研究上的新突破,也极大地促进了殷代地理和年代学的研究。此外,从以上可以看到,李先生对“夷方”方位的认知,前后是有很大变化的,这对今人准确复原晚商政治地理框架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也充分体现了李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的求真精神。(50)陈絜:《李学勤先生殷代地理研究成就浅述》,《出土文献》2020年第1期。
三
事实上,李学勤先生于甲骨学上的研究成果,所涉广泛,如对世系王年、天象气候、计时历法、字词考释、卜法文例、特殊刻辞、相关学术史等等都有深入考证。李先生对结合卜辞研究商代礼制也做了很多工作,他强调殷商礼制的研究须从周代礼制入手,要把商周礼制结合起来考察。李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还多次前往海外访问讲学,期间搜集整理了包括甲骨在内的诸多流散文物,编著了《英国所藏甲骨集》(51)李学勤、齐文心、艾兰编:《英国所藏甲骨集》,中华书局,1985年、199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52)李学勤、齐文心、艾兰编:《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所藏甲骨集》,中华书局,1999年。等甲骨著录专著。尤其是《英国所藏甲骨集》首次公开发表了散见于英国六城市十一个单位的全部甲骨2700余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之前未经著录过的,为学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另外,李先生对美国飞尔德博物院所藏甲骨、美国顾立雅教授旧藏甲骨、美国匹茨堡卡内基博物院藏肋骨刻辞等境外公、私所藏甲骨也进行了关注和研究,相关研究专文发表后集中于《四海寻珍》一书部分章节。(53)李学勤:《四海寻珍》,第217-244页。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说到:“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甲骨文的发现,意义重大,不仅“展现出商代丰富光辉的文化面貌,已经载入世界考古学的史册。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一重大发现以不容辩驳的证据填补了古史的空白。”(54)李学勤:《甲骨学一百年的回顾与前瞻》,《文物》1998年第1期。时至今日,甲骨学研究早已发展成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纵观李学勤先生的学术历程,可以说甲骨学从未离开过他的研究视野,是李学勤先生一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甲骨学的重点领域都颇有建树,著述宏富,成就巨大。李先生的甲骨研究虽亦是从材料入手,却不限于材料,注重考释,但不拘于考释,强调要“把甲骨作为一种考古遗物,加以全面研究”,往往以小见大,提出富有预见性、创新性并可极大推动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创新观点。这自然与李先生博通甲骨材料,又具有极其扎实的文献和小学基础密不可分,但更为重要的是李先生视角敏锐、融会贯通、眼界宏大,善于利用材料深化认识,可以说“既有史学家所必须的微观上的谨慎,又有哲学家在思路上的开阔。”(55)徐葆耕:《四海寻珍·序》,李学勤:《四海寻珍》,第2页。同时,李先生治学著文唯真求实、积极创新,有他人难以企及的问题意识,如先生自己所言“发表文章,不管长短,一定要有新见解。”(56)康香阁:《再访史学大师李学勤先生——治学经历(1955-1976)》,《邯郸学院学报》2013年(S1期)增刊。因此,可以常“开拓学术之区宇”,起到引领风气,凿破鸿蒙之功。
百年甲骨,薪火相传,大师辈出,李先生虽离我们而去,但学问不朽、真理不朽,其为人、为学、为师之风范、思想、成就、智慧,宛如学术星空一颗璀璨的星斗,指引着一代代的后学阔步前进,推动甲骨学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