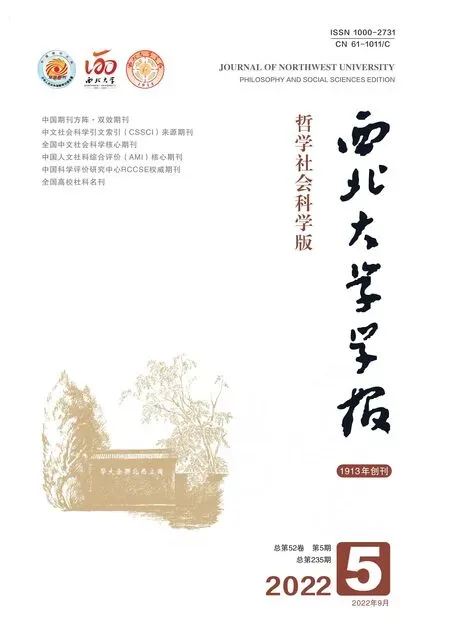先秦“不封不树”葬仪的考古学辨析
钱耀鹏,李 娜
(西北大学 中国-中亚人类与环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关于先秦墓葬“不封不树”的史籍记载,始终缺乏较为合理的解释,但仍与孔子所言“古也墓而不坟”相互佐证,造成了黄河流域坟丘起源问题的认知分歧。在甘肃临潭磨沟墓地的发掘过程中,基于第三次发掘而确认的齐家文化末期墓葬坟丘(见图1)[1],促使笔者回想起2008年首次发掘时也曾遇到过花土堆积而成的坟丘,却囿于史前墓葬无坟丘的固有观念而未能及时识别。进而,墓穴解剖所获埋藏堆积证据显示,磨沟墓地的单人墓时常也不具备即葬即埋的丧葬特点[2-3]。一系列考古埋藏证据的新发现,无不凸显出重新思考“不封不树”和“墓而不坟”本义的必要性。孔子合葬父母时所言“古也墓而不坟”,既有违先秦礼制,也不符合春秋现实,所以前置“古也”一词,目的就在于以“历史”依据淡化其长期不知父墓背后的家庭变故。那么,《礼记·王制》中无法归于“古也”的“不封不树”,所指究竟为何,可否归之于丧葬礼仪范畴,本文就此展开讨论。
一、“不封不树”的诸多疑惑
《礼记》有载:“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丧不贰事,自天子达于庶人。”[4]2888-2889引文句读依郑玄所注。其中,“天子七日而殡”至“三月而葬”因殡葬时限不同而分述之,末句“丧不贰事”因无等级差异而言“自天子达于庶人”,唯“三年之丧”至“不封不树”句读有些莫名。即“自天子达”语义不详,明显缺乏所至内容。再说,“丧不贰事”(丧期不涉他事)的规制不论等级,作为前提时限的三年丧期更当如此。如《礼记·中庸》所云:“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4]3534亦即不论等级贵贱,父母之丧同样都是以三年丧期为限。又如《礼记·丧服四制》所云:三年之丧,“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4]3682。尤其《论语·阳货》直言“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4]5488;《孟子·滕文公上》亦云:“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4]5875显然,此句当为“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郑玄句读之误,或因其释“县封”为县窆即悬下棺,似乎只有“庶人县封”方可化解天子“葬用隧”的矛盾现象。
类似于“不封不树”的“墓而不坟”, 仅为孔子合葬其父母时所言。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 ‘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 今丘也, 东西南北之人也, 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 崇四尺。 孔子先反。 门人后, 雨甚。 至, 孔子问焉,曰: ‘尔来何迟也?’曰: ‘防墓崩。’孔子不应,三。 孔子泫然流涕曰: ‘吾闻之,古不修墓。’”[4]2761虽然“古也”一词已经表明“墓而不坟”与“不封不树”的时代差异, 但这段记载依然揭示出“葬不为雨止, 不封不树”并不限于庶人。 因为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至少拥有士爵, 合葬时并未因雨而止。
据上所述,无论“县封”的本义如何,“不封不树”似乎都应是先秦时期通用的丧葬礼仪,甚至还可追溯到更加遥远的史前时期。如《周易·系辞下》所载:“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孔颖达疏曰:“若极远者则云‘上古’,其次远者直云‘古’。则‘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犹在穴居结绳之后,故直云‘古’也。”[4]181孔疏甚是,因为若是夏商周乃至尧舜时期,孔子一般不言“古也”,即如“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4]5955其中“唐虞”即指唐尧(陶唐氏)和虞舜(有虞氏),禅即禅让。进而,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及研究结果来看,孔疏所谓“穴居结绳之后”,大致相当于人工聚落及埋葬现象日渐普遍的新石器时代。
然而,历史的事实似乎并不完全如此,因为《礼记》等史籍记载中也不乏与之相悖者。即如《礼记·月令》所云:“孟冬之月,……饬丧纪,辨衣裳,审棺椁之薄厚,茔丘垄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4]2989,2991显然,如果墓上无封,则丘垄之大小便无从谈起。另据《礼记·曲礼上》所谓“适墓不登垄,……适墓不歌”[4]2704,可知言“墓”未必不含丘垄。亦即“墓”字原本兼具统言(广义)和析言(狭义)两种属性,并非专指地下墓穴的析言。据此推断,先秦时期即便独立使用的“墓”字,也未必能够作为坟丘尚未出现的确切依据。
《周礼·春官》亦载:“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4]1697其中“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明显有悖于“不封不树”。又《周礼·地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媺宫室,二曰族坟墓……”郑玄注曰:“本,犹旧也。”[4]1521-1522亦即大司徒的职责包括以“族坟墓”等六种旧俗安抚万民,说明“坟墓”一词理应出现于西周甚或更早。况且,“族坟墓”也未必皆“以爵等为丘封之度”。因为《管子·九变》还将“亲戚坟墓之所在”视为“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对上不以功德自居)的首要原因之一[5]165。姑且不论“亲戚坟墓”与“族坟墓”的相似性,守战之民也应涵盖普通士兵,而商鞅变法(前356)以前的普通士兵通常由庶民充任。也就是说,即便是庶民阶层,似乎也难言“不封”。
《左传》等史籍的相关记载不仅提升了“与其树数”的可信度,也增强了“不封不树”的疑惑性。如僖公三十二年(前628)冬,秦晋崤之战发生之前,秦军誓师伐郑,“蹇叔哭之曰:‘孟子(孟明),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杜预注:“合手曰拱,言其过老悖,不可用。”[4]3977亦即“拱”谓墓树已可合手而如碗口粗细,意同《公羊传》所言:“秦伯怒曰:‘若尔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尔曷知!’”宰,冢也(何休注)[4]4915。又《左传》哀公十一年(前484):“(伍子胥)将死,曰:‘树吾墓槚,槚可材也,吴其亡乎!’”[4]4706意即待其墓上槚树长成有用之材时,吴国便要灭亡了。另据《战国策》记载:“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6]315柳下季即柳下惠(前720—前621),其丘垄周围五十步还应有禁止樵采的墓树。《新序·杂事》亦云:“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徐君观剑,不言而色欲之。……于是季子以剑带徐君墓树而去。”[7]235显然,即便不言名称及具体数目,墓木或墓树也足以验证《周礼》所载内容,何以“不封不树”?
至于考古发现所引发的疑惑,磨沟墓地以外的其他例证学界多有论及,如杨鸿勋《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蔡培桂《“墓而不坟”质疑》(《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董坤玉《中国古代坟丘墓起源新探》(《考古》2017年第3期)等,无需赘述。
二、墓葬坟丘与丘封之度
基于“墓而不坟”的影响, 以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坟丘起源问题。 客观而言, 作为墓葬结构的一部分, 墓上设施更易遭受破坏, 保存完好者鲜有发现。 因而对墓上设施的了解程度远远不及墓穴及棺椁制度等地下设施。 不过,在等级制日益发达的社会背景下, 无论如何也不宜将墓上设施排除在丧葬礼仪之外。
《周礼》所谓“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固然无涉具体规格或数量,但也应是营建墓上设施的礼制依据。故而郑玄注曰:“别尊卑也,王公曰丘,诸臣曰封。《汉律》‘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贾公彦疏又引《春秋纬》:“天子坟高三刃(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贾疏引文不仅与《白虎通义》所引《春秋含文嘉》内容完全一致[8]73,也与许慎对“栾”字的解释甚为相近,即所谓《礼》:“天子树松,诸侯柏,大夫栾,士杨。”[9]112差异仅在于“士槐”还是“士杨”。《封氏闻见记》亦载:“按《礼经》云:‘天子坟高三雉,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树松,诸侯树柏,大夫树杨,士树榆。’”[10]446《礼》或《礼经》通常合指“三礼”,但今存“三礼”各本不见许、封二人所引。
值得肯定的是,无论典出何处,士爵当以高度四尺为丘封之度。而且,这一墓葬规制还有实例为证。据《左传》记载分析,叔梁纥当为士爵,故孔子合葬父母时即以四尺为丘封之度。及至孔子葬于鲁城北泗水上,弟子遵其遗命,“藏入地不及泉,而封为偃斧之形,高四尺,树松柏为志焉”[11]90,也是以士爵为度。又《礼记·檀弓下》记载:“(吴)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返)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郑玄注曰:“隐,据也;封可手据,谓高四尺。”[4]2843-2844延陵季子为吴公子,其长子当可承袭爵位,依礼可为四尺丘封,墓穴之“坎深不至于泉”也类似于孔子“藏入地不及泉”。另据《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记载,齐景公宠臣梁丘据死,乃召告晏子:“据忠且爱我,我欲丰厚其葬,高大其垄。”[12]113意如《礼记·礼器》所云:“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为贵也。”[4]3103齐景公虽因晏子谏言反对而作罢,仍可说明爵等与“丘封之度”的规格直接相关。
依前所述,“丘封之度”似乎就是坟丘之度,包括“天子坟高”“列侯坟高”等,但事实并非如此。据子夏所言:“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从若斧者焉,马鬣封之谓也。”(《礼记·檀弓下》)郑玄注云:“堂形四方而高”“坊形旁杀平上而长”“夏屋,今之门庑也,其形旁广而卑”“斧形,旁杀刃上而长。”[4]2798“旁杀”即周围向上内收。其中若斧者,马鬣封即《孔子家语》所谓“偃斧之形”(偃,仰也[13]444)。显然,孔子生前所见仅“若斧者”可谓坟丘,其余均属墓上屋宇类建筑。无论斧刃状坟丘是否限于士爵,也应属于低等爵位的“丘封之度”。同时,孔子又将“封之”作为统一的前置定语,似乎郑玄所谓“王公曰丘,诸臣曰封”的解释未必十分准确。由此来看,言“封”未必仅指地表坟丘,也可涵盖墓穴之上不同形式的屋宇建筑。
战国中山王陵M1椁室发现的铜版兆域图,不仅证实了《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的记载,也为理解孔子所见不同形式的“丘封之度”提供了实物依据(见图2)。该王陵区仅见两座坐北朝南的大型墓葬,其中M1的发掘结果表明墓主当为中山王厝[14],而其东侧的M2 应为兆域图中先于厝而亡的哀后堂,王陵区未及完成预先规划[15]。据兆域图可知,即便同为内宫垣所环绕的封之若堂者,其间也存在规格差别,王堂与后堂均二百尺见方,而夫人堂等则为一百五十尺见方。不仅如此,在内宫后侧的中宫垣环绕区域,紧贴内宫垣还规划有四座“宫”,平面规划百尺见方,有别于“旁杀平上而长”的坊形,似为孔子生前所未见。虽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僭越现象甚为普遍,但通常都是以周礼为基础的越级行为,类似诸侯国君僭越而如周天子称王的现象。也就是说,《周礼》中的“丘封之度”至少包括若堂、若宫、若坊、若覆夏屋、若斧等形式。
再依简报所述,M1封土平面合于兆域图规划而呈方形。封土“由下至上构成三级台阶,现高15米”。如若计算顶层平面,也可以说是四级台阶。无论从堂到覆夏屋的梯级基础是否存在三、二、一或四、三、二、一的等级差数,都可说明墓上的屋宇建筑实际也包括夯筑基础。至于若堂之建筑形式,可参考杨鸿勋的复原研究结果。据此来看,即便是墓上屋宇类建筑,夯筑而成的建筑基础亦如丘垄,《周礼》抑或因此而统称为“丘封之度”。
另据《礼记》和《孔子家语》子夏所言,孔子之丧乃“一日三斩板而以封”[11]90。郑玄注:“板盖广二尺、长六尺。斩板谓断其缩(缚板绳索)也,三断止之。傍杀(倾斜向上),盖高四尺,其广袤未闻也。”[4]2798亦即士爵“马鬣封”不仅状如斧刃,为高四尺,且系版筑而成。据此,《春秋纬》所谓“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或是指其状不若斧刃,高不及四尺,且不以版筑而为“坟丘”者。否则,即便郑玄所引《汉律》“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可归结为先秦两汉时期的丧葬制度变化,也难以解释磨沟墓地所见夏商时期的普通墓葬坟丘。
据上所述,墓葬坟丘与“丘封之度”属于不同层级的概念范畴,犹如白马与马的概念差异。亦即“丘封之度”可以涵盖墓葬坟丘,但墓葬坟丘却无法等同于丘封之度。如陕西商洛东龙山遗址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墓葬M41、M43及M83等,虽无地表坟丘存在的任何线索,但在墓穴四角外侧发现有对称分布的四个柱洞,柱洞底部还垫有数量不等的石块,加之未见墙基及居住面痕迹残存,因而被视为墓上建筑,有别于同期的其他墓葬[16]82-83,89-91。辽宁建昌东大杖子东周燕人墓地的M40、M47,墓穴口部也发现有地上建筑的柱洞遗迹(见图3)[17-18]。无论这些梁柱结构的建筑形式如何,也都属于坟丘之外的墓上设施。另外,除了社会等级分化,时间和地域等因素也可导致墓上标志的多样性特征。最为特别的考古实例就是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一般是在木棺前竖置不同形制的立木[19]。
三、不封不树与三年之丧
孔子因合葬父母而言“墓而不坟”,但却以“古也”而非“礼也”或“今也”为前置定语,寓意颇显蹊跷。结合《礼记·檀弓上》另一则涉及孔子合葬父母的记载,即“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郰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似乎孔子不知父墓的原因就在于“墓而不坟”。然而,前述“不封不树”的疑惑又令这一解释显得过于勉强。再依《管子·禁藏》所载:“宫室足以避燥湿,……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坟墓足以道记。”房玄龄注云:“道识其处,各有记也。”[5]188-189姑且不论管子的生活年代早于孔子,“坟墓”一词也散见于“三礼”所载。因此,孔子不知父墓的原因,似乎很难完全归结于“墓而不坟”。事实上,孔子不知父墓的根本原因,可能还在于幼年丧父及其引发的家庭变故致使孔子不曾服丧。不过,孔子“问于郰曼父之母”,又以“不可以弗识也”为由而建坟丘,也说明其父之墓确无坟丘。
既然考古发现与其他史籍反复证实了《周礼》所载“丘封之度与其树数”,那么《礼记》缘何又云“不封不树”呢?就《礼记》记载而言,最接近“墓而不坟”者似乎并非“不封不树”,而是“坟墓不培”。即《礼记·丧服四制》所谓“丧不过三年,苴衰(缞)不补,坟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终也,以节制者也。”孔颖达疏曰:“苴衰不补者,言苴麻之衰,虽破不补。坟墓不培者,培,益也;一成丘陵之后不培益其土。”[4]3681若按孔疏所谓“一成丘陵”,则“不封不树”和“墓而不坟”之说似乎就无法成立。
实际上,史籍记载也已表明,“坟墓不培”和“不封不树”皆以丧期为前提,所谓“丧不过三年”或“三年之丧”。《周易·系辞下》虽无三年丧期限定,却以“丧期无数”作为“不封不树”之后缀。就考古发现的史前墓葬来看,所谓“古之葬者,……丧期无数”的说法或非虚言。尤其仰韶文化较为常见的合葬墓,即有死亡时间差可达200年左右的多人二次合葬墓,如河南邓州八里岗M13[20],又如陕西华阴横阵仰韶文化早期数座合葬墓共用同一大型坑穴[21],且随葬陶器显示其埋葬时间并不一致者[22]。另外,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虽无大坑套小坑的埋葬现象,但合葬墓的埋葬特征类似于横阵墓地。据人骨埋藏特征分析,即便同一座墓葬的不同个体,也可能是先后而非同时葬入的[23]。显然,对于“丧期无数”的合葬墓,“不封不树”似乎在所难免。当然,“不封”不等于不做封闭处理。
至于先秦墓葬,丧期“不封不树”的葬仪也不是踪迹全无。《礼记·檀弓上》有载:“孔子之丧,有自燕来观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圣人之葬人与?人之葬圣人也。子何观焉?……今一日而三斩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同样的内容也见于《孔子家语·终记解》:“既葬,有自燕来观者,舍于子夏氏。子夏谓之曰:‘吾亦人之葬圣人,非圣人之葬人,子奚观焉?……今徒一日三斩板而以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观乎哉?’”一两则文字略有出入,但意思基本一致,核心是说孔子葬礼并无值得一观的特别之处。即便“三斩板而以封”的马鬣封,也不过是“今徒一日”而成,不足为奇。但言外之意却是通常情况下并非一日而成坟丘。况且,若堂、若宫、若坊类墓上设施通常也很难一日而成。如此则“坟墓不培”便可等同于“不封不树”之不封。
另据《礼记·问丧》所载,孝子送葬时,“其送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返)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入门而弗见也,上堂又弗见也,入室又弗见也。亡矣,丧矣,不可复见已矣!……祭之宗庙,以鬼飨之,侥幸复反(返)也。”姑且不论丧亲之痛的种种表现,即便既葬而返的宗庙虞祭,仍以侥幸之心祈愿亡亲能够得以复返。于是便“成圹而归,不敢入处室。居于倚庐,哀亲之在外也;寝苫枕块,哀亲之在土也。故哭泣无时,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4]3594-3595。其中“成圹而归”明显有别于“今徒一日三斩板而以封”,并居于倚庐、寝苫枕块、哭泣无时,故服勤期间理应不培坟墓。又“孝子亲死,悲哀志懑(闷),故匍匐而哭之,若将复生然,安可得夺而敛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敛者,以俟(待)其生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是故圣人为之断决,以三日为之礼制也”[4]3595。以此类推,服丧三年而待思慕之心“益衰”之后再起丘封,似也合乎情理。因此,“成圹而归”“坟墓不培”“不封不树”可能仅是同一葬仪的不同说法而已,而丧期过后则可“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亦即“不封不树”与“丘封之度”原本并无矛盾。
当然,丧葬礼仪也不能一概而论。除了孔子合葬父母、孔子之丧皆一日成坟外,还有前文所引延陵季子异乡葬子也是如此。这说明基于死者生前意愿或在特殊情况下,士大夫也可即日成坟,未必丧期之内“不封不树”“坟墓不培”。另据《礼记·檀弓下》记载:“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郑玄注:“还,犹疾也,谓不及其日月。”孔颖达疏:“敛手足形者,亲亡,但以衣棺敛其头首及足,形体不露,还速葬而无椁材……。”[4]2836显然,若是家境不济,也不必拘泥于“不封不树”等丧葬礼仪,只要尽心尽力即可。
虽说如此,以“至痛”而有“至孝”之名的社会赞誉,难免令居丧思亲之情趋向极端化。诚如墨子所言:“处丧之法,……曰‘哭泣不秩、声翁,缞绖垂涕,处倚庐,寝苫枕块。’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陬(皱),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是故百姓冬不仞(忍)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24]107,109即便是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也认为如此“相高以毁瘠,是奸人之道也,非礼义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25]239。相,视也[26]8,相高即觊望至孝声名之意;毁瘠即因居丧过哀而极度羸弱。显然,极端化的丧葬礼仪有失人道本义,几乎成了摧残生者乃至影响正常社会生活的消极因素。
这种旨在彰显至孝之名并延及后世的极端化居丧行为,也可一定程度地验证“不封不树”的本义。如东汉早期韦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27]917;东汉末年桓典“会国相王吉以罪被诛,故人亲戚莫敢至者。典独弃官收敛归葬,服丧三年,负土成坟,为立祠堂,尽礼而去”[27]1258;魏晋名士山涛“会遭母丧,归乡里。涛年逾耳顺,居丧过礼,负土成坟,手植松柏”[28]1225等。后两者皆自行“负土成坟”,且行文于为丧或居丧之后,前者“不出庐寝”乃至“服竟”病倒,或久未负土成坟。尤其《隋书·孝义列传》所载:“徐孝肃,汲郡人也,……孝肃早孤,不识父,及长,问其母父状……母终,孝肃茹蔬饮水,盛冬单缞,毁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负土成坟,庐于墓所四十余载,被发徒跣,遂以身终。”[29]1671其祖父母和父亲之墓明显久未成坟,母丧期间“毁瘠骨立”,亦似不宜为坟,“皆负土成坟”当在母丧之后。
反证则有东汉晚期的太常赵岐,临终前“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为床,布簟白衣,散发其上,覆以单被,即日便下,下讫便掩’”[27]2124;又南朝陈的司徒左长史袁泌,临终前亦“戒其子蔓华曰:‘吾于朝廷素无功绩,瞑目之后,敛手足旋葬,无得辄受赠谥’”[30]245。此二人所以遗命子嗣“下讫便掩”或“敛手足旋葬”,当是基于久葬不掩或久肂(假葬)不葬的种种极端现象。据此来看,无论史籍中哀毁、居丧、庐墓和“负土成坟、手植松柏”的记载语序是否完全一致,似乎都难以否定“负土成坟、手植松柏”于三年丧期之后的事实。
四、墓葬县封与埋葬过程
前文有述,郑玄把三年之丧的后续内容句读为“庶人县封”,并释“县封”为“县窆”,以示庶人与天子之丧的区别。然而,“县窆”即悬下棺而葬者并不限于庶人,也包括诸侯、大夫、士。即如贾谊所言:“古者周礼,天子葬用隧,诸侯县下。周襄王出逃伯斗,晋文公率师诛贼,定周国之乱,复襄王之位。于是襄王赏以南阳之地,文公辞南阳,请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听,曰:‘周国虽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为少,余请益之。’文公乃退。”[31]401而晋文公“请隧”一事也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4]3952及《国语·周语中》[32]18-19所载,并非贾谊杜撰。天子用隧,庶人县窆,诸侯、大夫、士又当如何呢!
汉唐学者所以释“县封”为“县窆”,或因《周礼》《仪礼》所载丧葬礼仪常用“窆”字。从使用情况来看,窆字与葬、封诸字时常并用,但具体所指有所不同。如“冢人掌公墓之地,……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大丧,既有日,请度甫竁,遂为之尸。及竁,以度为丘隧,共丧之窆器。及葬,言鸾车、象人。及窆,执斧以莅。遂人藏凶器,正墓位,跸墓域,守墓禁”。又《地官司徒》“乡师之职,……及葬,执纛以与匠师、御柩而治役。及窆,执斧以莅匠师”;“遂人掌邦之野,……及葬,帅而属六綍,及窆,陈役”;“遂师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大丧,使帅其属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笼及蜃车之役。”[4]1537-1538,1595,1597-1598,1697-1698“丘封”无需赘言,所谓“及葬”当指葬日尤其送葬过程,而“及窆”则包括“遂人藏凶器(明器)”“丘笼及蜃车之役”等,远不止于悬下棺。
相对而言,《仪礼·既夕礼》的记载更加明晰。所谓“至于圹,陈器于道东西,……乃窆。……袭,赠用制币,玄纟熏束,……藏器于旁,加见(见即棺饰)。藏苞筲于旁。加折却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实土三”[4]2506-2507。姑且不论“及窆”当在送葬“至于圹”以后,后文的“加折却之”至“实土三”又当与掩埋过程有关。尤其《既夕礼·记》中所谓“柩至于圹,敛服载之。卒窆而归,不驱”,其中“卒窆”明显不可能仅指悬下棺。否则,何以使“上毋通臭”或“气无发泄于上”[24]112,117。联系起来,则“卒窆而归”至少应在“实土三”以后。可以肯定,《周礼》《仪礼》中的“窆”字绝不止于悬下棺,也可涵盖掩埋过程。
无可否认, “封”字的含义较为复杂。 在《礼记·丧大记》中, 悬下棺的确可以言之为“封”。 所谓“君葬用车盾, 四纟孛二碑, 御棺用羽葆。 大夫葬……御棺用茅。 士葬……御棺用功布。 凡封, 用纟孛去碑负引, 君封以衡, 大夫士以咸”[4]3437-3438。 其中“用纟孛去碑负引”即葬下棺时用纟孛背对木碑负引而退行, 诸侯棺上置横木以系纟孛, 大夫士则直接系纟孛于棺束(咸或缄)。 悬下棺既可言封, 也可直言“县棺”, 唯独不言“县封”。 如《礼记·檀弓上》: “子游问丧具, ……夫子曰: ‘有, 毋过礼。 苟亡(无)矣, 敛首足形, 还(旋)葬, 县棺而封, 人岂有非之者哉?’”[4]2797如若释“封”为“窆”, 则“县棺而封”当可训为悬棺而悬下棺, 岂不怪哉!
另据前引延陵季子之子“葬于嬴、 博之间, ……其坎深不至于泉, 其敛以时服。 既葬而封, 广轮掩坎, 其高可隐也。 既封, 左袒, 右还(环)其封,且号者三”, 其中“其高可隐”当缘于“既葬而封, 广轮掩坎”,后文的“既封”又是“既葬而封”的终结, 尔后延陵季子“左袒, 右还其封”(袒露左臂而顺时针环绕丘封)。 如此看来, 悬下棺理应寓于“葬”字而非“封”字之中。 也就是说, 在丧葬礼仪的相关记载中,葬字的意涵明显大于“窆”字, 而“窆”字的意涵又大于“封”字。 换言之, 葬字可以涵盖或替代窆字, 窆字也可涵盖或替代封字, 但封字却不能等同于窆或葬字。 这就是说, 把“县封”释为“县窆”, 当与事实不符。
那么,“县封”的本义又是如何,能否理解为“悬空而封”呢?
有关于此, 《周礼》冢人职责中的“大丧, 既有日, 请度甫竁, ……及竁, 以度为丘隧”, 似乎值得关注。 其中“甫竁”, 郑玄详注于《周礼·春官》小宗伯“卜葬兆, 甫竁, 亦如之”之下, 所谓“甫, 始也。郑大夫读‘竁’皆为‘穿’……皆谓葬穿圹也”[4]1657。至于“丘隧”, 郑玄注云: “隧, 羡道也。 度丘与羡道广袤所至。”然而, 贾公彦又依《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请隧”之事而疏曰: “天子有隧, 诸侯已下有羡道。 隧与羡异者, 隧道则上有负土, 谓若郑庄公与母掘地隧而相见者也; 羡道上无负土。”
至于何以掘地为隧,或可参考《墨子·备穴》。所谓“亻鼠穴高七尺五寸,广柱间也(七)尺,二尺一柱,柱下傅舄,二柱共一员十一。两柱同质,横员土。柱大二围半,必固亓(其)员土,无柱与柱交者”。据清代学者孙诒让考证:“‘员十一’,义不可通,下文两言‘员土’,疑‘十一’即‘土’字,传写误分之。然‘员土’亦无义,盖当为‘负土’。《周礼·冢人》贾疏云‘隧道上有负土’,此为穴,亦为隧道,故有负土。盖以板横载而两柱直榰之,故云‘两柱共一负土’。”[24]331由此来看,墓葬隧道或系立柱上横置木板负土而成,或者利用二层台结构横置木板。再依郑玄所注:“大丧,王、后、世子也。小丧,夫人以下。”[4]1412则及竁而“度为丘隧”者似乎并不限于周天子。
另据《仪礼》所载,“丘隧”抑或不限于“大丧”墓道。如《既夕礼》记载,出殡祭奠时,“陈明器于乘车之西。折,横覆之。抗木,横三缩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缁剪,有幅,亦缩二横三”[4]2488-2489;送葬时,“至于圹,陈器于道东西,北上。茵先入,属引……乃窆。……加折,却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实土三。主人拜乡人”。依郑玄所注:“折,犹庪也。方凿连木为之,盖如床,而缩者三,横者五,无箦(床席)。窆事毕,加之圹上,以承抗席。”“抗,御也,所以御止土者,其横与缩各足掩圹。”亦即榫卯结构的床架式“折”,明显不同于椁室棚木为盖的构造方式。参考“卒窆而归”之语,则“加折却之”及“实土三”只能说是“窆事末”而非“窆事毕”。再结合送葬“至于圹”而终,则加折于圹上者当指墓圹之上,最后再“实土三”以掩盖之。如果说贾疏“至实土三遍,主人拜谢之”的意涵仍显模糊,还可参考《礼记·杂记下》“乡人五十者从反(返)哭,四十者待盈坎”[4]3389。即乡人五十岁以上者随主人“返哭”而归,四十岁以下则“待盈坎”而返。其中,“盈坎”类似于“卒窆”或“成圹而归”,尤其墨子所谓“满坎无封”[24]112,却有别于“丘封之度”。如此则“加折却之”尔后掩土盈坎,可能就是指棚架封闭墓口,“县封”的本义当在于此。故而史籍罕见葬日“成坟”或“成封而归”者,“坟墓不培”的丧期规制也显得顺理成章。

从表达哀思之情的角度来说,“县封”与“不封不树”可谓殊途同归,即逐渐增大生死之隔也应是表现思慕之心“益衰”的重要形式。唐代皮日休《鄙孝议下》可给予反向验证:“故合葬于防,孔子先反者,尚修虞事也。今之愚民,既葬不掩,谓乎不忍也;既掩不虞,谓乎庐墓也。伤者必过毁,甚者必越礼,……自汉魏以降,厥风逾甚。”[33]208合葬尚且如此,单人墓葬可想而知。如陕西旬邑百子村东汉壁画墓前后室,甬道两壁守门力士的外侧分别朱书题记“诸观者皆解履乃得入”“诸欲观者皆当解履乃得入观此”[34],说明墓道一度不曾掩埋封闭,墓穴尤其前室应呈开放状态。当然,若似东汉赵岐“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死后又遵其遗命“即日便下,下讫便掩”,充其量不过是开放寿藏。但赵岐此举当属逆俗而为的特例,实际也不乏与之相反的事例,诸如“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墓道),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27]2124,2159-2160。至于赵宣欺世盗名之罪,并非源于“葬亲而不闭埏隧”,主要还在于其服丧期间违背禁欲规制而育有五子。换言之,在以“举孝廉”为选官制度的社会背景下,“葬亲而不闭埏隧”的守丧现象理应相当普遍。否则,便很难准确理解“埏门只复闭,白蚁相将来”[35]591的挽歌诗句。
考古发现中之所以罕见或不易确认“县封”遗迹,原因可能在于丧期之后一般需要撤去“县封”设施而为丘封之度,构筑丘封难免又会弱化墓口部分的“县封”痕迹。正因为如此,所以磨沟墓地的墓葬口部不曾确认有棚架痕迹,而棚架结构或设施普遍发现于墓穴内部。但从逻辑上来说,基于防雨防水等方面的需要,墓葬口部通常也应加以棚架封闭为妥。对此,环境干燥而有利于有机物保存且与河西走廊文化关系密切的新疆哈密、吐鲁番地区,考古发现的墓葬实例当具参考意义。尤其吐鲁番胜金店墓地,无论竖穴二层台墓、竖穴土坑墓还是竖穴偏室墓,墓口多见木梁棚架的黑果枸杞、芦苇等覆盖物,包括M9、M13距墓口较深的二层台上也搭有棚木者(见图4)[36-37]。另外,如同中山王陵未按“兆域图”规划完成那样,也不能排除特殊情况下墓葬的埋葬过程未按丧葬礼仪完成的偶然现象,亦即黄河中下游地区先秦墓葬“县封”遗存的考古发现可期可待。
总之,古代丧葬过程甚为复杂,理应包含若干思慕之情“益衰”、生死之隔逐步增大的阶段性葬仪。所谓“不封不树”或“坟墓不培”,通常应是以礼制规定的三年丧期为限;即便存在“居丧过礼”行为,一般也不涉及最终的埋葬过程。而所谓“丘封之度与其树数”,通常完成于三年丧期之后,与前者并不矛盾。惟“丘封之度”还应包括堂、宫、坊、覆夏屋等屋宇类墓上建筑,不宜笼统地理解为普通坟丘。因为规格最低且无屋宇类建筑的若斧者“马鬣封”,也是以版筑方式构筑而成的。尤其史籍所谓“县封”,似乎并不限于庶人,也不宜释为“悬下棺”,很可能是指丧期之内棚架封闭墓穴的现象,并以此表示思慕之心和不忍之情。当然,丧葬礼仪的意义并不限于孝悌之心、思慕之情的直接表达,更是维系和推行宗法制度、强化社会秩序的重要举措。如此一来,多人多次合葬、局部人骨位移或缺失、先后放置随葬品等诸多特殊埋藏现象,均可获得较为合理的考古学解释。进而,通过解剖发掘坟丘尤其地下墓穴部分,以获取有关埋葬过程的埋藏堆积证据便显得十分必要。
———《中原北方地区宋金墓葬艺术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