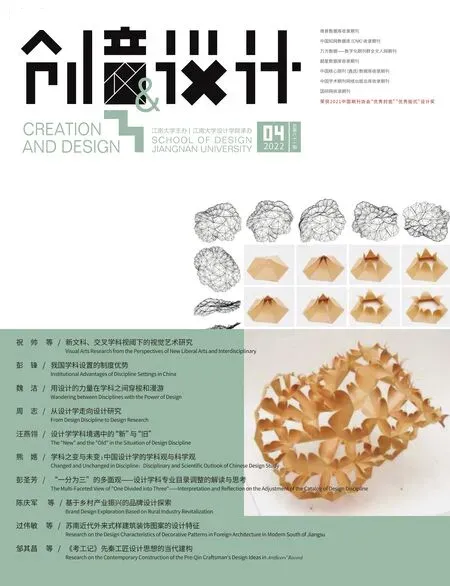中晚明仪式化器物载录中的工艺技术与物质空间
——以《天水冰山录》为例
文/谢 玮(扬州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
中晚明时期的工艺技术与物质空间,潜藏在品貌各异的呈现器物背后,这是一条造物与设计行为演进共生的线索。纵观《天水冰山录》的文字材料,将其物质空间视为社会变化的表征,发掘占有者与设计受体(物)的物用观、制造者与设计受体(物)的自然观、人与人之间的人际观等多元贯连,借助其条目间的相互训释,并充分剖析文本的多重指向,渐次深入到彼时社会的工艺技术、物质用度、消费流转等场域中。窥视静态存续的“物”背后所体现出联结社会生产生活与消费的动态过程。
一、籍官薄《天水冰山录》概述
《天水冰山录》(知不足斋本——下同)字面寄意“太阳一出冰山颓”(见图1),其被认为是嘉靖时期过录籍没权相严嵩财产的册据明细。此财产籍没册于严嵩垮台时由明代官府所定,采用平淡的官方用语,对严嵩所拥有的无法穷尽的财富进行理智罗列。此籍没册囊括两大类别,第一类被朝廷没入国库,第二类则被变卖折合成现钱。《天水冰山录》载录严氏一族衣、食、住、行、用全方位占有、收藏的明细,涉猎广泛[1]。具体涉及金银器物、奇玩、织物、家具、古铜器、钱钞、图籍、石刻法帖墨迹、古今名画手卷册页明细,第宅、店房、基地、田地及山塘登录册录、法书、名画等。据相关研究统计,“其 中 有 金13 171.65两,净 银2 013 478.9两,各式金银器皿、玉器、首饰、家具和珍贵字画、珍贵书籍数千件,房屋宅基地57所,田地山塘27 161.819亩等”。《天水冰山录》文本描述了相应器物品名、重量(即“估银”)、尺寸、数目、造型、材料、成色、装饰,以及时、地等综合信息,以冷静修辞的姿态阐述相应之物的特征。循此,实物集中且系统地呈现出深层次、复杂化的社会构架,反映出明代社会器物规则用度、造物组合构造及其文化表征,以备我们掌握多维度、全局性的瞻明见解。

图1 《天水冰山录》第1册
《天水冰山录》采用账目化明细形式进行书写,其秉承金石、谱录、档案等文本脉络,墨守品类、套系进行齐整登载,这一规范化形式勾勒出当时官方经典话语阐释和惯例习俗的轮廓模式。提要文本依循集成仪式性的科学分类规则,并呈现出抽象的模块化规律。从文本内容看,《天水冰山录》不仅呈现出权贵阶层“过度丰裕”的物质生活状态,还牵涉其时显贵、门阀的其他一些线索,即在社会商业化推进以及随即带来的制度性变革中,人们表层化对“礼”的误读,继而沦为对物质畸形崇尚的源泉,其足可谓明中期社会政治、经济与物质消费、流通最佳的微观注疏,为研究彼时历史极紧要且无法规避的珍贵材料[2]。
二、《天水冰山录》与中晚明时期的成熟工艺与物质用度
一个时代的工艺、设计风貌,完全取决于该时代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特征。嘉靖时期是明时经济发展、商品化有序推进的重要时期,尤其自嘉靖中期始,生产力水平不断稳健攀升,商业化和商品化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特征,手工业中出现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式,工业、农业亦推进发展,资本积累、商业繁盛、贸易流通等均促使商品经济有较大提升。正应如此,成就了明后期近百年间封建社会的商业繁荣,并促使工艺、设计的勃兴[3]。“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社会群体自上而下借助资本累积、财富增加、运作流通等经济规则对“物”进行深入解读,这导致封建统治集团的审美好恶带动该时代“物”的品类、工艺技术、设计风格的趋势,这种审美趋向是一种复杂、综合的艺术旨趣,且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人们对物的喜好推进并拓展了收藏文化。通过《天水冰山录》这一特定事件下的文本解读,我们窥视该时期工艺特性及人们对物的使用规律和范围影响。
2.1 中晚明时期丝织物的工艺、奢侈与消费
中晚明消费社会形成,更加促进其工艺造作的繁盛。嘉靖时期是个分水岭,各项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走向巅峰。最能体现产品差异的物类之一——织物,其不仅是极为重要的奢侈物,且是当时高度商业化的行业产物。
《天水冰山录》记载从严府抄出织绣锦缎等物1 304件[4],其无论是材质品类、机杼工艺、构造肌理、色泽纹饰等均映射出该时期织物的较高水准。
其查抄“缎”30余种品类几乎囊括了“缎”织物的所有形态,这些“缎”的命名,包含了许多需要更进一步揭示的信息。其涉及30余类色相,通过文本可知有红、红闪色、青闪红、蓝闪红、大红、水红、桃红、黄、黄闪色、柳黄、青、青金、天青、墨青、绿、绿闪色、柳绿、黑绿、墨绿、油绿、沙绿、蓝、蓝闪色、蓝闪红、沉香、玉色、紫色、藕色、白、葱白等[5]。关涉文本色相描释的辞藻到底是什么形态?是否与今人理解的色相相契合?亦或者不同人对其色相的解读亦不相同,这一切依据条目式罗列的展示的确并非易于解答[6]。其中采用提花工艺的“妆花缎”是古代织造工艺的至高呈现, 《天水冰山录》所载9 151匹“缎”中,仅明确记载为妆花缎的数量就有2 659匹,可见其比例之大。“妆花”亦称“装花”,其工艺精湛,能自由呈现多种风格主题,在嘉靖时期流行甚广[7]。不仅正红与青色作为妆花缎中色相主体,而且为凸显面料的肌理色泽,其多兼施“织金”工艺。如大红织金妆花蟒龙缎、大红织金妆花过肩麒麟缎等,都达到极高的制作水平和规格等级。(见图2)

图2 《天水冰山录》第3册“段”
其查抄“纱”品类约1 147匹,有素纱、云纱、绉纱、闪色纱、织金纱、遍地金纱、妆花纱、织金妆花纱等10余品类;“绸”品类814匹,有云绸、妆花绸、潞绸、潮绸、素绸、织金绸、织金妆花绸、锦绸等10余品类[8],均用于裙、衫等服饰制作。产地山西潞安的“潞绸”可谓明时绸料之冠,其织造技艺卓越,乾隆《潞安府志》卷九《田赋》载:“明季长治、高平、潞卫3处,共有绸机13 000余张。”潞绸“士庶皆得为衣”“潞城机杼斗巧,织作纯丽,衣天下”,《潞安府志》卷一《地理》载“潞绸遍宇内”[9]。定陵曾出土孝靖皇后大回纹潞绸女衣,可知潞绸不单使用范围广、更是皇家贵胄御用之选。除此之外,查抄亦有改机绒褐、锦214等多种品类。
由文本可见,明时各类织物使用范围之广、需求数量之大、涉及品类之多,无论是横向对不同材质的探究,还是纵向对同一品类的各样纹饰、织造方式的展现,均做到极致。丝织物中尤以纻丝为盛,纻丝在明时是国家织造生产中最主要的一类织物,作为高档丝绸面料中的一类,其在许多场合中,被委以祭祀、封赏等重要功能,赋予了通达神灵、封赠臣僚的政治功效,其在这一社会活动中具备不可替代的属性。首先,作为面料基础的使用功能,纻丝首列于皇帝纳妃的各色礼单中,从王公贵族的冠服,囊括核心权贵的公服、常服等,皆为纻丝。朱明内官服用,按祖制“自十月初四日至次年三月初三日穿纻丝,自三月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穿罗……”“凡婚庆吉典,则虽遇夏、秋,亦必穿纻丝供事”[10]。其次,大量的纻丝以赏赐群臣的模式构建其使命,这种模式既有段匹、亦有成衣,嘉靖皇帝的赏赐名录多样、频次亦勤,从《天水冰山录》记载在册的纻丝有144个条目,计9 151匹,占在册总录织物的过半之上。文本印证了权臣之家纻丝聚敛累积的现状,数字之巨大占到整个国家每年缴纳段匹数量的1/4[7]。
纻丝作为仅次于锦的昂贵织物,其织造工艺繁杂,故而其价格高昂。从明初至明中期,根据律法中的量刑需求而衍生出对应织物的估价法例,尤其在洪武、弘治及嘉靖年间,纻丝价格稳定,3两多银子可购得一匹。嘉靖之后,纻丝估价陡然降至150贯一匹,甚至低于罗、改机的价格,如此差异的价格动荡说明明中期始,纻丝扩大生产、量产稳增、流通便捷,必然导致其价格起伏[7]。
其实,此时期纻丝已然成为民间市井狂热追求的奢侈消费物,尽管皇家禁断犹在,但同时“赐赉屡加,全与诏旨矛盾。”(见明代沈德符《砺野获篇·莽衣》)禁断松动,法典形同具文,这依然难挡其生产、流通、占有的社会需求,最后便是屡禁不绝。如此背离的属性,不仅论证了权贵阶层对此类奢侈物的大量使用需求,更深层次且合理的解释应当是将占有、消费此类织物与身份地位的征象相契合,故而致使明中晚期织造、穿着僭越之风日盛,士、商阶层踊跃地成为皇室之外义无反顾的主体消费群。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情形既是对等级制度的向往、模仿,亦是对等级制度的嘲讽。这个环境下,某种“姿态”要想变得适于“兜售”,必然会导致蓬勃的需求与消费推动纻丝织造技术不断改进、完善,呈现出纻丝品类、纹饰、色泽等愈来愈多样化,以适应某类早已被固化的角色所期待的姿态。明乎此,《天水冰山录》在“还原”与“审视”之间弥补了后世对嘉靖时期高档织物的全部遐想空间。
2.2 中晚明时期高级家具的工艺、奢侈与消费
自上而下的奢侈消费之风在中晚明时期盛行,社会城市化与士绅城居化改变了民众的生活方式,亦带动了一批潜力雄厚的消费群体。高官、缙绅、商甲相继在城市营建宅第、园林,这一行为亦带动室内家具的奢行,高官、缙绅、商甲多喜好材质稀有珍贵、结构精巧、工艺精湛、装饰华贵精美的家具,甚至将家具提升到“古董”收藏的层次。如采用螺钿、玉石镶嵌,雕镂彩绘、描金、泥金等工艺[11]。文人士大夫阶层则构建出与以上人群相异的家具审美及品味,其强化家具实用性与审美雅致特征,文人强调物化在家具中的雅、俗区隔。重视材质的自然属性,厌弃繁复雕琢的装饰;主张形制上遵循古制,不以材质贵贱作为衡量家具的标准;同时,家具亦参与文人社交活动,书房作为家具物品特殊化的有效表现空间,将文人审美品味及社交与家具使用性有效组织在一起,如在书房家具上进行字词铭刻[12]。
2.2.1 高官富甲的家具消费形态 从《天水冰山录》文本可知籍没的家具中,第1类被没入国库的包含“屏风围屏”108座架、“大理石螺钿等床”17张(见图3)。第2类被变卖折合成现钱的包含“变价螺钿彩漆等床”640张,通共估银2 127.85两;“变价桌椅橱柜等项”7 444件,共估价银1 415.56两[11]。其中第1类与第2类部分估价超过1两以上的家具,均为材质稀有特殊、装饰繁复的精品,其强调材质与装饰,如依托贵重石材制作的大理石大中小屏风、灵璧石屏风、白石素漆屏风、祁阳石屏风;依托羊皮材质制作的羊皮颜色大围屏、羊皮中围屏与羊皮小围屏 (见 图4); 亦 有 采 用 漆 工 艺 技术——“螺钿镶嵌”制作家具,如彩漆围屏、描金山水围屏、黑漆贴金围屏、泥金松竹梅围屏、泥金山水围屏等[12]。而第1类“大理石螺钿等床”细分为大理石材质制作与螺钿镶嵌装饰制作两种,此类床在价值上高于第2类“变价螺钿彩漆等床”,从名录中可辩二者虽皆为床,且均关注材质、装饰,但后者材质略逊于前者,多以彩漆雕为主,故而后者直接解赴户部。此外,还有一些品类为“凉床”,其形制展现少数财力雄厚的高级官员消费贵重家具的情形,与主流奢侈物制作、消费、流通皆以工艺、时间等外在因素品论高下的价值取向彼摄相因,其正契合彼时奢侈消费的描述。

图3 《天水冰山录》第4册:屏风围屏108座和床17张

图4 《天水冰山录》第4册:石类屏风、羊皮类屏风和倭金屏风围屏
此外,高官富甲对舶来珍物的关注、追捧使得外来物品渗透在本土的生活方式中。文本中记载的倭国屏风、围屏:倭金彩画大、小屏风、倭金银片大、小围屏、倭金描蝴蝶、描花草围屏等(见图4),均是来源于日本的舶来物。自从来华耶稣会士将钟表、棱镜等西方奇器携入中国,并为高层官员和朝廷所接纳[11]。这并非是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崇尚,物的设计制作要突破单向、封闭、孤立来看,更合理的解释是舶来珍物只是从不同角度透出人们对周边相类似商品类型的多样化需求[13]。
2.2.2 文士阶层的家具消费形态 《天水冰山录》变卖的家具清册中亦附有变卖的价格,从文本中解读可鉴,如若将被朝廷没入国库的家具一同并置比较可得出:屏风与围屏的价格高于床;床的价格均在1两之上而高于其它家什。床价格浮动首先源于其螺钿镶嵌、彩漆、雕漆工艺的精良装饰,其次亦或许是其材质的择选,依次为大理石、椐木、花梨木等。但如此序列似乎与前述提及的材质价值略有出入。究其原因,与此时期文人品味的特殊化影响有关。
奢风渐盛的明中叶,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不同社会阶层对家具的需求亦然各异,文士阶层将书房作为支撑其文化支配权的重要空间进行独立塑造,从书房的整体布局设置、家具摆件等均强化身份认同,且拒绝落入“商品化”的窠臼。用物(家具)的特殊化重新归置其原本所处的各种关联,以此来抵制物(家具)的商品化,这是一种通过文化力量进行的抗衡,借助思想意识的嵌入性实践,如此便得到完全异于高官富甲的品味。家具通过文人群体的特殊化知识生成,使其约束在一定范围的交换流通领域中,自然这类家具便成为该群体共识的标识,使得其他社会群体趋之若鹜。循此,文士阶层尝试在书房家具上进行铭刻,将其赋予文化神圣性与学问、道德、政事相联,这一实践模式是拒绝商业化和商品化的手段。但“物”如何出现,“事”便会怎样兴起,文士阶层致力于家具特殊化以便对自身身份进行区隔,事实上“洛阳纸贵”,更强化了文士参与实践后的铭刻家具的商品化属性。这也解答了《天水冰山录》中材质价值略有出入的原因。
《天水冰山录》映射了高官富甲的家具消费特征、消费形态,窥见当时奢侈消费观念的传播。同时,亦显示出文士阶层作为明家具的另一个消费指向,在早期商品化发达的社会变迁下,对身份的敏感性已然根植于民众的生活中,而士人与文人所建立的特殊品味,试图将其强化。商业化程度提高,社会流动性增强,本质上围绕消费文化将这一形式实现其自身意义,导致这种行为就更为常见。
三、中晚明时期的礼制文化与物质空间的区隔与差异
中晚明,大多数普通民众最关切的依然是最基础的生活必需品,所关注大多停留在生存话题,基本不涉及消费选择。但少数衣食无忧的士绅权贵却是推进业已极度繁杂的社会分层与通往权力之途的主要人群。依托对物的占有与选择的各种差别,就“物应该如何”而达成共识,这种阶层与权力途径之异已然昭然若揭,无论就确切的还是比喻的涵义而言均是如此。该阶层通过对各类物的占有,凸显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积累,并通过区别物的材料或装饰,亦或将两者均纳入考量因素中而存续,并以更费心力的方式给社会群体灌输这些规范,对于物之区别的反复强调不过是对于人与人之间作为物的消费者之差异的陈说。
3.1 权贵阶层对“物”占有产生的区隔与差异
《天水冰山录》条目陈词的背后并非是对物本身的关切,而更多是通过一系列的物,窥视彼时社会陈述,其关注物与物之间的差异,在这副呈现出的关于社会图像背后,向人们展示社会的界限和区别,其突破语言、隐喻或象征的模式,以知晓不同物类的范畴。
中晚明时期,具有显著地位的物质文化和消费行为反映出对“物”在高度压抑且森严等级的社会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的普遍感知,呈现出掌握权力的社会阶层与“物”所认同的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通过相互影响的社交互动而实现,从《天水冰山录》中的器物、服饰折射出彼时严氏一族的从着装到礼物馈赠以及生活日用器物等,这是权力阶层特别关注的问题。其条目下的“物”并非单纯对于“物”在行为上的旁观载录,“物”影响了阶序结构下的个体如何在实现等级特权与等级实践之间进行判断和均衡的问题。
遗存下来的往昔之物是如何被用来赋予延续感以具体的社会形式?我们从这些物的社会内涵层面出发,并引向明代器物必得介入其中的社会交往形式。作为生产、流通重要群体的权贵阶层不仅对彼时精湛工艺物品表现出喜好,且对“古物”亦表现出浓厚的占有情结。“古物”诉诸事物的自然本质与物质属性,其复古式的审美必然建立在实现对社会资源占有、生产、消耗、控制上,彼时社会必然受生产导向的商品体系所支配,以此为基础渗透至生活点滴中,例如其所谓的阶层地位与消费自由度投射出对物的享用,这一表述关系似乎使“物”变得相当合情合理且自然而然,甚至是不言而喻的,这正是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
通过对品类繁多“物”的类属高下评定,以及对其感知褒贬的不安情绪,“物”成为士人智识上聚焦的话题,并在中国文化中扮演了往昔所不曾享有的重要角色。有证据表明,古物的“收藏品”往往非常少,然严嵩财产籍没册上单“古铜器”有1 127件,三足深腹的青铜鼎彝在籍没册中排在首位(见图5)。可见,这类器物数量之大颇不寻常,彼时只有少数人可以竞相豪奢地支配享乐之物。深层次看,对古物的占有既满足了拥有者对财富、身份的诉求,也同时拥有其所包含的象征价值[14]。这种对器物的 “功能层次”配置既包含“技术经济”的层面,亦存在“社会技术”的涵义,对古物的占有作为一种潜在的特权文化活动,反映了一个阶层流动的社会中审美趣味的多变,这种多变通过“物”作为载体来实现,“物”被当成是社会标识,已然渐次转变成一种维系身份的重要消费行为,继而人群审美品味随即而变,如此才能让那些对此起到至关重要的机制发挥相应作用。

图5 《天水冰山录》第4册:古铜器
另外,《天水冰山录》中对于石刻法帖墨迹、法书名画的籍录可探析又一情形。此类事物初被文人所喜,相较于金银、珠玉、华服类器物而言,其社会性往往超越实体价值。金银、珠玉、华服的关注点多在材料、工艺等技术属性上。如此,便于追索筹计、纳库充公的量化处理,而书画类事物从文人流转至贵族府邸和上层僚属间,作为一种特殊的资产,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表层的货币属性以及深层的文化推崇,书画的流动涉及时间与空间,其两者历经的流动是并行的,加之社会性赋予的附加价值。继而可知,其拥有者因此可以获得对于阶层流动而言极为至关重要的社交关系保障,亦导致了市场上买卖真迹、变造赝品的频生乱象[6]。
3.2 逾礼越制与潜奢之风下的物质空间
等级制度是相应历史阶段产生的法令及礼俗约定,用于规范相应群体中民众的生产生活。等级制度要渗透在社会组织与思想观念中,需要社会群体共同遵守,其具备普适性与延续性,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开展必然建立在群体思想观念稳定的基础上,借助代际传承中群体的共同思想意识发挥社会功用。
明时用物规制在初期与中晚期发生明显变化。初期造物敦朴、用物规范;中晚明时期商业高度发展,物品极度丰盛,呈现出造物奢华、用物僭礼越制的特征。从敦朴转而奢华的物质导向,与明时工艺技术及文化背景密切关联。初期礼法制度以望而知之为目标,严苛的制度规范着不同社会等级的民众的一切生活用器,起到明尊卑别上下的文化诉求;经过近百年物质财富的累积、工艺的成熟,加之中晚期政治逐渐松弛,礼法约束被打破,在造物及用度各领域形成僭奢之风,此时更强调人作为主体的生命意识,求美求奢成为各个阶层的普遍追求,僭礼越制理所当然地成为彼时期社会的普遍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追求甚至能够超越那些限制他们生活等级制度的手段,这一现象符合历史习俗风尚的演化规律。
《天水冰山录》是强制曝光族产的历史证据,通过列举的物的具体数据,可知其仍囿于中国古代礼教约束的框架中。通过对“物”的冷静胪举,满足了下层民众对社会上层权贵建诸礼法之上的日常与精神垄断霸权的渐进式认同,亦或叛逆式发泄。古代民众的公、私生存均受制于高度执着的“礼法关系”,以及尝试突破这种关系的抗争中。文本中不单单是表层呈现出的相权挑战皇权,依循传统礼法的延续脉络,是权利之争的胜者对严氏曾经拥有之物赤裸裸的查抄、记录、展列,内中映衬出针对“非礼”的压制,本质亦在对所谓“合礼”的回归。明乎此,我们承认“消费文化”的确引起宽泛层面的礼法构筑,但其行为深层次的意义存在于礼法规约的社会模式内,尊卑、上下在物质用度里依旧通过其间的斤两算计明确反映出来,这种突破消费及流通的局部、隐匿式特征较之政经之兴衰愈加复杂且纠缠。商业繁盛、贸易流通一定意义上深化了礼法对人心的渗透,继而建构出与彼时“物”对应的约束形态,至于“物”于此扮演何种角色,并非能以简单且全盘否定的思维模式看待,“物”还是“物”,通过对其支配流转映射出权力、身份地位的新旧辨识与消解。
总的说来,“物”在身份分化和市场区隔的作用,也反映了他们特有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用“物”来表达社会区隔,在不同层次的权贵、士绅精英中最为严重,因为他们强调要与可能最相近的威胁保持距离的需求最为迫切。每一种“物”的形式都将自身特殊的感官感觉传递进生命的流转中,礼制随时代推进,具备自身完备的演进逻辑,且与社会制度及形式选择联接,其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影响人们的行为,这种维系一定时期稳态状况的模式将人控制、制约。这亦导致其内部出现抗衡的反向干预力,它们在各个特定时期,在特殊的情形下被有效配置,隐藏着人对控制权的斗争,使得社会生活内部秩序和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具备一种强大张力韧性。
四、结 语
综上,《天水冰山录》作为中国物质文化史缩影的一角,其揭示明代物质空间与彼时社会组织、集体心态。通过刻画这一时期物质形态、材质择选、工艺技术等内在因素,并找寻其相关历史文化背景、发展演进动因等外部因素,在两者博弈中切入明代政经情势、剖析文化制史,透过材料铺陈诠释历史可能的情态,为设计学分析提供有益的积累。该文本拓宽了历史探究的维度,不仅条分缕析地记录了彼时权贵对房地、建筑的特殊占有,而且使我们明确了当时建筑造园的设计特征与宏观规制,兼及其流转等可能信息,其不仅是对奢侈物的占有,而且是占有他们的方式。这恰巧是以往资料包括断代史、经济史等所轻忽的占有流通的细节内容。同理,《天水冰山录》中对石刻、法帖等的登载,是严氏所处时代文化与精神表征的最好证据。对其全方位的解读,不仅期待今人透析材料时突破二元的思维定势,亦期待发掘“物”之后的文化与社会秩序,以及隐匿在涨落不停的现象之后的心理动机,并最终回归到造物与日用社群的检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