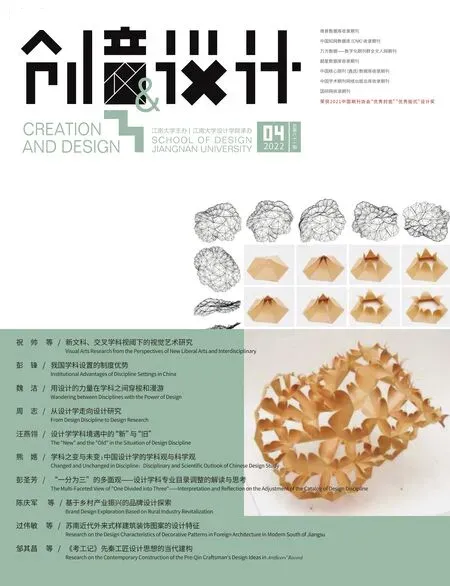如何策展人类世的乡村景观
文/莫军华(苏州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
“人类世”(Anthropocene)首先是一个地质学概念:人类出现于新生代第四纪的“全新世”(始于11 700年前),诺贝尔奖得主、生态学家保罗·克鲁岑在2000年所撰的《我们已进入“人类世”?》一文中,宣布地球已经进入了“人类世”。美国地质学家简·扎拉斯维奇(Jan Zalasiewicz)认为1945年是“全新世”的结束、“人类世”的开端,这是因为美国分别于1945年8月6日、9日在广岛和长崎引爆了两颗原子弹,法国哲学家米歇尔·舍赫(Michel Serres)将这一事件视为“人类世”的起点,这意味着人类的技术活动已经明显影响到了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此外,欧洲诸多当代哲学家也对“人类世”展开了讨论,如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看到了“人类世”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结果,并将18世纪的工业革命视作其中的一个源头[1]。而孙周兴先生比较同意舍赫的观点,认为人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了“人类世”,而且进入了加速状态。这意味着技术乐观主义占了上风,生活世界日益被科幻化[2]。换言之,人类已经进入了技术统治的时代。
相较于平台化的现代城市而言,自然乡村成为人类抵抗技术统治的最后领地,而在“全球变暖对我们的威胁、人工地球成为人类环境”的境遇中[3],乡村社会能独善其身、抽离于“人类世”之外吗?自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从未中断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和改造。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救济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认定晚清以来的百年史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无论是自清同光至欧洲大战时期跟风近代都市文明,或是欧洲大战之后的反近代都市文明,都在破坏中国乡村。梁先生认识到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被“世界大交通、西洋人东进”这一新环境包围[4],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遭受到了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冲击。费孝通先生也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注中国农民的生活,并对长江流域的农村生活进行了实地调查,撰写了《江村经济》博士论文,被其导师布·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费先生在“江村”(吴江开弦弓村的学名)看到了合作社对中国乡村经济的价值,认定中国社会是具有“乡土性”的,乡土社会的生活是一种自给自足、半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生活,村民是在那种“面对面亲密接触中”[5]生产劳动的。但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与空间原本的“不流动”社会格局被打破,乡村社会逐渐变成了陌生化的社会形态,乡村的本地性价值被重新审视和放大。
我们注意到,中国的乡村在近100年经历了“乡建运动”“新农村运动”“美丽乡村”等实践活动,特别是在“艺术下乡”持续地堆叠、发酵之后形成了新的乡村景观:原本在单纯的自然中的乡村被人为地改造为“艺术实验室”,在本地性/生态性被抽离的艺术与乡村、艺术家与村民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问题是,我们是否清楚自己在乡村遭遇(是一种知觉、凝视、体验时产生的不知所措、无所依傍的状态)的到底是什么景观?
一、何谓乡村景观
法国思想家、情境主义国际创始人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指的“景观”(spectacle)一 词 出 自 于 拉 丁 文“spectae”和“specere”等词语,指观看、被看。在希伯莱文本的 《圣经》(the Book Psalms)中,是用于对耶鲁撒冷总体美景(包括所罗门寺庙、城堡、宫殿在内)的描述。在《牛津词典》中,常译为“壮观的景象”。在汉语中并没有与之对应的词,“景”和“观”二字原义分别是:“景”字始见于战国文字,本义指日光;上部是“日”字,作形旁,表义,表示与太阳有关[6];下部是“京”字,其古字形像高大的建筑物。《尔雅》《毛诗》皆曰:“景,大也”;“观”字初文见于商代至西周时期[6],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凝视、审视。《小雅·采绿传》曰:观,多也。物多而后可观,故曰观,多也。顾名思义,“景观”就是对澄明的、大而多的物的凝视。中文语境的“景观”阐释的更为具体,主、客体的关系明确。
不难发现,“景观”的词性是复杂的,既可做动词,也做名词,还有形容词的属性。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物之经验影响了人类对于“景观”概念?西方哲学对于事物理解分为“自在之物”“为我之物”“关联之物”3个阶段,我们从物在不同阶段的概念入手,把“乡村景观”放在人类世的背景之下进行讨论,对照美国哲学家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黑格尔(G.W.F.Hegel)等人那里发展而来的“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思想以及斯蒂格勒的“第三持存”,我们把在乡村遭遇到的“景观”规定为3种,发展了德波的“景观社会”中的“景观”意蕴。
1.1 作为自然景观的乡村“原生景观”
丹尼斯·科斯格拉夫在《社会变迁与景观象征》中,是把“景观”一词当成“自然”的附属概念提出的,他认为“景观”是特定的认识方式,与16世纪以来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同步。在《牛津词典》中,“landscape”被译作陆上的、尤指乡村的风景、景色或乡村风景画。这与我们脑海闪现“景观”一词时,通常会想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大地、河流、树木、天空、田野和牲畜[7]所说的“景观”是同一种所指。哲学界将这种未经人类改造过的自然称为“第一自然”,是城市居民到乡村去享受的由诸多“自在之物”(Ding an sich)构成的原生性自然环境,但他们往往把观看的对象搞错了,如同欣赏那些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去人化”的风景画。这种把劳动者从风景中剥离的、图像化的城乡景观,被科斯格拉夫称为阶层特有的“观看之道”。这种观看显然无法看到汉语“景观”所蕴含的“总体美景”的自然景观,因为“原生景观”被赋予了“乡村总体美景”之义。
在乡村,我们遭遇的这些纯然的自然物应该如何去看?“景观”一词既是对自然物和人工物的“凝视审视”,这里的“原生景观”具有“生态—生存”的本真性,与科斯格拉夫的“自然化”景观视图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不主张那种特定的“认识方式”,反对“去自然化”的景观,提倡把劳动者重新拉回单纯的自然环境,还原人与物的亲密接触(农民与自然物的劳作)场景,共同构建一个广大户外的真实景色。
1.2 作为文化记忆景观的乡村“第二景观”
哲学上把人类改造过的自然称为“第二自然”,是一种人为实践活动创造的人工自然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第二自然”是指人类的后天习得的能力,区别于先天的自然能力;黑格尔主张的“第二自然”,是成为人类性格中的习惯的某种行为方式;而麦克道尔指出:“伦理品格包括实践理智的倾向,而当品格形成之时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部分就是,这种实践理智获得了一种确定的形态,因而对于其拥有者来说,实践智慧就是第二自然。”[8]同理,乡村“第二景观”是对单纯的自然景观人为改造后的景观,是“原生景观”的异化产物,但不是奥古斯丁所说的那种“堕落”,因为“第二景观”具有教化功能。伽达默尔认为,教化不仅仅指修养,即能力或天赋的培养,因为对天赋的自然素质的训练与培养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单纯手段,教化更为重要的是对某种普遍性的追求,使人通过教化而变成其所是的东西[8]。
教化是在共同的一个文化系统中实现的,而在文化范畴内,最先值得留意的是景观意识[9]。这里涉及到“文化记忆”和“记忆景观”两个基本概念:“文化记忆”是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20世纪90年代最早提出:一个区域的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过去,需要文字、仪式、纪念碑等文化形式作为主要媒体,并通过背诵、实践、庆典等机构化的交流进行维持;美国地理学家索尔(Carl Sauer)认为人惯常“把自然景观……转变为文化景观”[7]。2013年,我们在《文化记忆景观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中提出“文化记忆景观”的概念[10],是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需求展开的。村民的身份与生活世界的空间发生了改变,“第二景观”的形成是建立在村民的集体记忆场所之上的,而景观由若干包含物质形态和故事的记忆场所构成[11]。在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这种记忆场所范式正在形成新的乡村景观,且具有自然和文化记忆的双重属性,这也是“第二景观”特有的属性。这种记忆场所离不开物,物的存在在于它如何与人发生关联,即“关联之物”[12]。区别于名词的纯自然景物,“landscape”在做动词时有人为“美化”的涵义,这也体现在现代设计观念的下乡,各种设计物构建了新时代乡村的第二景观:村口标识(标示村名的精神壁垒、主题雕塑等)、导视牌、景观小品、展示馆等,其目的是教化村民接受集体认同,便于持续性的叙事与传播共同体的价值观。这种物的关联性体现在村民被这些景观设计物聚拢在一起,人和人还是有面对面接触的场所,其本质是一种在场的真实世界。
1.3 在全球景观社会中的乡村“第三景观”
德波在《景观社会》第一章的开篇,援引了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一段话,深刻揭示了景观的颠倒性:“偏爱图像而不信实物,偏爱复制本而忽视原稿,偏爱表现而不顾现实,喜欢表象甚于存在”[13]。这里的“景观”是德波关于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词,原意为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景象,也意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作秀[14]。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景观是一种非本真的存在。在德波看来,景观支配中最坏的东西,就是无处不在的图片和电影中迷人的影像再现。在景观表象中,人们会忘记景观在则存在不在场,景观是离开了人的在场的表象存在,而当人迷入景观建构的伪境时已经是存在本身的场境异化,这也是德波自己拒绝在一切景观中出场的原因[15]。
意大利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对德波的《景观社会》做了哲学引申,他是为了证明:在景观社会里,资本成为图像,语言成为商品,词语和图像循环于媒体,人的语言能力则被放到一个隔离区,单独成为大众媒体,在那里自我运行,人因此成为失去了语言的动物[16]。我们把这种处于全球景观社会中的乡村景观称之为“第三景观”,是一种“语言的景观、商品的景观和资本的景观”,原生景观沦为消费的符号。这种符号化的物是“为我之物”,物变成了对我而言的对象,成为我的表象的对象。物的存在等于“被表象性”(Vorgestelltheit),这恰恰是景观社会的典型特征:人们通过网络、电梯、公共场所看到的乡村旅游广告的主要内容,无外乎是展示自然景观的秀美、民宿环境的优美、民俗表演的艳美。这是特别要当心的,人们容易陷入德波所指的“伪交往”“伪使用”“伪享受”“伪权力”的表象世界,我们一方面要对这种颠倒的、虚幻的、数字化的影像资本主义景观进行批判,一方面要讨论如何克服这种令人迷入幻境的景观鸦片。
二、原生景观:“生态—生存”的本真性
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认为在21世纪“人们一定会更加关注自然,更深刻地理解自然。”[17]作为原生景观(自然景观)中的“自然”是什么?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曾说:“创造自然的自然才是真自然”,人文地理学家诺埃尔·卡斯特利(Noel Castree)认为地理学中存在“两个自然”:“第一自然”(环境),其作用施加于“人类自然(本性)”(身体和心理),并因人不同,为他带来或多或少的限制[7]。气候变化对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全球变暖对自然的作用越发严重,人类不得不面对极端气候频发的压迫……这就验证了帕帕奈克的观点,“原生景观”的产生就是人类对“自然”的领会,而“自然”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受的东西。
在人类世,我们把自己抛入乡村,直接遭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困境。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首先肯定了自然界优先于人类而存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8],他认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是不存在的。自然界与人类息息相关,必须消除人与自然的两离,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有的地理学者推行“系统理论”,如乔利(Chorley)和肯尼迪(Kennedy)所列:系统包括组成要素、不同要素的相互关系(简单的或者复杂的)、以及输入和输出(如能量和物质等)……就人与环境的关系来说,人可以被视为复杂系统(often-complex systems)中的一个要素。在这一系统中,人与自然要素按照模式化(patterned)的方式相互作用,并产生可供辨识的后果[7]。
在我们看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人类主动隐退到自然的背景中成为背景的一个元素。但讽刺的是,一些乡村正在遭受毁灭性的“艺术涂鸦”:原本被画成风景画的乡村正在被投射到自身的墙壁上(见图1),墙面成了空白的画布,成为被涂鸦的媒介。艺术家进入乡村,在墙上摹仿那些原本在村中天天“照面”的物:古树、铺首、大公鸡(见图2)、花卉等。村民从涂鸦艺术家那里得知“这是艺术”,因此认为“它是美的”。村民难道说是主动放弃了对自然(生态)的审美判断吗?康德对趣味判断主要是对自然美的判断[19]:当你说,看着夕阳,“它是美的”时,你表达了一种个人情感,你认为它的美应该是客观的,所以和你一起在欣赏“原生景观”的同伴也应该觉得“它是美的”。因此,你把一种共通感归于全人类,……这种共通感正是做出审美判断的能力[20]。而自然美的意义在于“一直连续不断地为艺术提供着有意义的冲动”[21],随着涂鸦活动的结束,这种“冲动”被涂鸦者从自然界中掠夺走了。他们把“原生景观”通过绘画复制到人工物上成为图像化的“第三景观”,村落的自然环境被人为破坏,并没有成为抵抗景观社会的那种创造性的艺术。

图1 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涂鸦

图2 村民在与涂鸦的“大公鸡”对话
自然美的冲动感应是“生态—生存”的合力产生的,是人对自身所处的生命场的直接感动。当我们直观一些神秘的自然物时,自然生发出一种崇高的审美意向。犹如我们在明月湾村口谛视的那棵千年古樟,相传为唐代著名诗人刘长卿到明月湾访友时所植,树龄至今约1 200多年。古樟曾遭火焚雷劈不死,主干东北一侧虽成为枯木,却枯而不朽,最让人惊叹的是“后发枝干倚背而生”,坊间戏称“爷爷背孙子”,令游客感受到“生生不息”的冲力,并时有敬香之举。被人们视作“具有神灵、祖先、福禄、故乡等多重的文化隐喻及寄寓敬畏与崇拜、亲切与熟悉、记忆与乡愁等复杂情感的重要象征物。”[22]人类社会抽象的理念被投射到了这棵树,它被艺术地动用了生态术,被施了魔法,成了自我出土的“原生景观”。人与人围树而坐,人与物“去—远”地在场照面(海德格尔),构成了一个生态的真情境。看似是古典的“自在之物”发生了变异,人们被古樟吸引而崇拜,是自然物的神秘性被赋义,从而产生诸如转树、拜树、围树等一系列为了自身生存的行为,如同原始人打猎/劳作之前的集体舞蹈一般,这种类“原始巫术”其本质就是一种艺术家式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求生存的生态术:自我繁衍、自我接生。
“原生景观”的本真性是“生态—生存”,在人类世,我们要从传统美学风格的笼子里解放出来,放弃涂鸦,任物为物。在乡村,我们只要心无旁骛地仰望星空,把因全球变暖减少的睡眠时间补回来,这就是我们应该领会到的“乡村总体美景”:澄明的天空、幽暗的大地、弯弯的河流、林中的小路、广袤的田野和成群的牲畜……人与人、人与物能够亲密接触的自然景观。
三、第二景观:“生态—艺术”的情境性
林毅夫先生倡导的“新农村运动”清楚认识到新农村建设应该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不能要求农村居民统一建新房,从理论上提出了防范措施,但很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仍然与之相反。温铁军教授是梁漱溟先生所推行的“新乡村建设”的接棒者,他认为,我国只能以“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为前提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安顿农村大量的过剩人口。周祖翼先生强调“合理的城镇化离不开农村的合理发展,合理的城镇化布局应当是城市更像城市,农村更像农村,城市和农村互相促进,城镇化也要传承文化。”[23]然而,从近几年来看,许多被设计过、被“艺术赋能”过的农村已经不像农村了,原本的土制炉灶被改成了科技灶台,炉灶从手工物变成了技术物,这种技术物对手工物的驱离造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无家状态”。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如何处置“人类的返乡冲动和无家状态的遭遇”?[24]
3.1 艺术地改变作品的物性,构造乡村新情境
这是艺术家李牧在2011年历时一年的策展活动,他将荷兰Van Abbe美术馆的收藏品空降到了自己的家乡—江苏仇庄。确切来说,在仇庄展示的只是策展人利用当地的材料来复制美术馆的藏品。为了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他将一些村民拉入了伙。在村庄的主干道两侧,村里的画师绘制了美国艺术家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的两幅墙画、用树枝复制了英国著名艺术家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的《木圈》。这种行为是:我们必须给旧东西找到新的用途,就像孩子们在被劳动分工和心理压制之前所做的那样。用新的用途去顶替旧的用途……这是一种创造性的糟蹋的能力,一种沉湎中的不依不饶的追寻[16]。索尔·勒维特的另一个作品《无题(墙面结构)》被木工用旧木头复制出来后散发给了村民,他们使用得非常上手:做隔断、摆花盆、吊鸟笼(见图3,4)。村民有选择性地把艺术家的作品当作实验用具,斯蒂格勒认为这种选择过程就是“艺术”。斯蒂格勒认为,新的技术装置使我们的身体产生出新的人工器官、新的身体幻觉。而选择哪些新器官、新幻觉留下,将哪些去掉的这个过程也是艺术[3]。

图3 “仇庄项目”:《无题(墙面结构)》被改造为鸟笼架
“仇庄项目”的策展模式:看似是农民被策展人设计了、村庄的日常生活被“艺术化”了,实际上是农民领会了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他们把这些艺术作品当作一种实用器物加以改造、利用,重新对物赋义,他们比策展人还理解这些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村民们的创造行为都是围绕那象征“家”的中心的炉灶展开的,村民与这些改变了物性的作品照面,他们发明的这种“第二景观”是真情境(见图5)。

图4 “仇庄项目”:《无题(墙面结构)》被村民改造为展示架

图5 “仇庄项目”村民集体改造后的策展模式
3.2 降临:发明风景,制作大地
策展人陆兴华认为,该展览假设了一个当代艺术观众突然降临崇明岛最边疆的前哨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生态剧场,是主人公了,须接手后往下演了……这同时也让我们开启新一轮的反思与思考,如何从一个村庄出发去做生态?在艺术家和作品“降临”的那一瞬间,村庄临时成为美术馆:工业生产的存留物、自然物被设计成当代艺术品和展示艺术品的处所,是人类世的“艺术—生态”行动(见图6)。

图6 “降临:发明风景,制作大地”艺术家的作品“降临”在前哨村现场
如图7所示,策展人把作品抛入村庄,虽然与“炉灶之家”分离,但并未远离炉灶,而是与村庄本地的植被、气候进行哈勃森式的“地学拼图”,这种拼图的每一块都具有“构造、气候和植被的组合”。英国人文地理学家诺埃尔·卡斯特利(Noel Castree)把这种看法理解为:地理学的作用并非对人类和环境之间普遍存在的关系开展研究,而是展现特定的区域综合体[30]。在人类世,我们要把尽量多的物种和无机物拉到这个“区域综合体”的帐篷底下,像对待艺术品那样对待它们。法国哲学家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煽动人类从目前的这个自然世界中自我出土,在自我出土后,再回头看去,我们才能直面那个我们要的真正的生态。法国另外一位学者拉怀勒(Marlene Laruelle)则认为,我们这个意淫的生态之前的那一个生态,才是真正的生态。在他看来,这个第一生态,就是将人身上的动物性和植物性考虑在内的生态(人、动物、植物和人身上的动物和植物被平等地考虑之后的生态),这与卡斯特利的“两个自然”观类似。我们回头再去看乡村:既是遮蔽的,也是敞开的,亦可把“林中空地”(海德格尔)让出来任你去策展—筹划。充分发挥残留的现成品的物性,通过艺术—生态之术,将其改造为村民集体的文化记忆景观,即“第二景观”。

图7 “降临:发明风景,制作大地”的策展模式
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艺术展览要把艺术家的个人知识像衣服那样晾到公共空间,成为观众现场生产出自己的知识的道具。在人类世—气候危机里,“地球成了实验室,也成了美术馆”[25]。在乡村这个实验室里,光靠涂鸦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要面对真的生态,就要从乡村的外部进入内部去做生态—艺术实验。当代艺术展览在今天应该达到的生态性,通过展示乡村本地的各种生态物,帮助观众与展览之间发生化学反应,不让人呆在原来固守的美学风格里[26]。我们要认识到现当代的物经验即是“关联之物”,事物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意义,事物的意义在于关联性。在这样的关联性思维影响下的艺术创造活动可以表述为:艺术即表现(expression)、表现即赋义(give meaning)、赋义即创造(create)[12]。第二景观的本质在于人类对“关联之物”的重新赋义,让物与人关联。
四、第三景观:幽灵策展的双重“颠倒性”
斯蒂格勒将技术持存(technical retentions)的中介物—记忆存储器(mnemotechnics)称 之 为 第 三 持 存(tertiary retentions),而电脑和数字化网络则是数字确证性第三持存(digital orthothetic tertiary retentions)。在人类世的网络时代,人们主要是通过数字第三持存(digital retentions)进行高性能数据处理。究其本质,“第三持存”是人类记忆的外化,外化过程被马克思描述为编程化(grammatization),即一种分析的形式化、离散化、再生产和自动化的过程[27]。简言之,斯蒂格勒认为这种外化带来的“废人化”具有“毒性”。这一点与德波眼中的景观社会颇为相似,景观汇合着离散物,像鸦片一样让“多数人”在被资本家给予的数字化影像中尽情的去“伪享受”,由此我们断定颠倒现实世界的“第三景观”是具有“毒性”的。
4.1 表演化的伪情境
人本主义地理学者对真实世界的研究,通常关注个体或者小群体如何对特定的地方及特定的地理环境形成依恋[7]。在卡斯特利看来,这种方法是在强调人类存在的主观维度高于建成景观和自然景观的非人的客观性。我们为何“依恋”一个村庄?我们又如何“依恋”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乡村?“什么都没有”在这里被视为除了原生景观之外别无他物。于是,在资本—商业合流地推动下,村庄就被摆置进了各种艺术物:雕塑、装置、彩绘等,出发点是试图把村庄整体改造成一个装扮成“美术馆”的大商场。稻田、水塘、民居都成为艺术创作的载体,植入了音乐、诗歌元素,制作了一件“大地艺术”。拉开田园艺术季大幕的“稻田宴”,把城市人强行拉入到铺上地毯的稻田里表演饕餮,目的是让游客(城市人)切身感受稻米的芳香(见图8)。装有“蜻蜓之眼”的无人机像幽灵一般盘旋在村庄的上空,与稻田里的长臂摄像机同时向外转播这种没有主演的群体性表演活动(见图9)。随着这些视频、影像在网络上的直播/传播,世界图像的专业化已经完成,表演化的村庄伪情境进入一个自主化的图像世界,在那里,虚假物已经在自欺欺人[13]。这些景观生产是发生在中国传统乡村的劳动异化,村民的劳动异化为商品,这还是我们理解的那个自然的乡村“原生景观”吗?

图8 “稻田宴”现场

图9 大型农耕仪典——“丰谷颂”现场
其实,“田园艺术季”在神州大地上偷偷地虚构了一个 “伪乡村”(pseudo-campagne),德波认为在这个虚假乡村中失去了古老乡村的自然关系[13],“原生景观”的真实场境被颠倒了。总面积近1.5万m2的《蒙娜丽莎巨幅彩色稻田画》、摹仿日本“金阁寺”作为“高品位的茶空间”、玻璃钢群塑《梵高先生来写生》、钢板制作的18世纪法国巴比松画派名作《拾穗者》(图10)、摹仿外国名作的大型艺术壁画等等,在全球商品化洪流的席卷下,策展人认为这些“国际化”的符号似乎更有吸睛的价值。这些“第三景观”是以商业为目的,策展人高举“生态—艺术”的幌子来颠倒游客对“原生景观”真实的需求。

图10 “铜陵田园艺术季”的《拾穗者》装置
旅游业被德波视作商品流通的副产品,人类的流动被看作一种消费,流动到乡村就是乡村旅游。问题是,广告里展示的是一种颠倒现实的景观表象,我们看到的是一场自己即在场又不在场的虚假表演。德波所说的表演者是“少数者”、观众是“多数者”在农田中的表演、作秀中出现反转,在场的村民作为看客/观众成为“少数者”,而表演者却是“多数者”。这种景观的倒错,表演者侵占了村民暂时闲置的土地表演给村民看,村民与游客被商品中介物或者手机屏幕“隔离”了,人与人只能成为一种“伪交往”。游客将自己隔离在稻田里住上一夜,在观看美景的同时也成为了展示物,获得的也只是一种“伪享受”(见图11)。

图11 “铜陵田园艺术季”透明民宿
康德把近代物的概念说成是“为我之物”,也就是说,一个“自我”的时代开始了,“我”的时代开始了[12]。孙红雷主演的《决战刹马镇》是这般搞活旅游的:表面上看是刹马镇的村民把西红柿当成了“颜料”,把游客当成画布进行人体彩绘,其本质就是一出前文所述的“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作秀”,“我”乐在其中。此时,西红柿作为自然物的属性被异化为商品符号了,“自在之物”异化为“为我之物”,是否可以认定这是历史到倒退?因为人与物的关系异化目的在于刺激消费,恰恰是中了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毒,异化了物的“自在之物”的源初涵义。
4.2 通过幽灵策展,颠倒被颠倒的景观世界
“幽灵策展”脱胎于德里达的“幽灵写作”:你身上到底是什么在写?肯定不是你的手或心!也许是你之外的某个装置在你身上写。写好后,文本马上就被没收、充公,被集体化,作者不是死掉的,而是这样先被剥夺掉的。作者怎么重新依附到他们原来写出的文本上?通过策展,也就是说祭它,重新像局外人那样去使用它。……每一个写作者身上都潜伏着这样一个内在策展人或幽灵策展人,在对自己和别人的文本策展、展示和回炉[28]。列斐伏尔说,我们对城市的权利,是在城市空间中追求同时性和偶遇的权利,是对得到交换价值、商业和利润之外的(精神)空间的权利[29]。那么,什么是我们对乡村的权利?我们这样想就景观化了:除了农民的“一亩三分地”的土地使用拥有权利,人们还有仰望星空的权利,在水库、鱼塘、河沟游泳的权利,漫山遍野放牛的权利,在田间地头割猪草的权利……但这些在景观社会中变成了施加于生活经历的“伪权力”。现在,我们要得到新的权利,通过幽灵策展,把村庄整体改造成村民共有的剧场、美术馆。
随着自动化的到来,商品世界必须克服如下矛盾:技术工具化客观上在取消劳动的同时,必须将劳动作为商品、作为商品诞生的唯一场所保留[13]。这种自动化导致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往第三产业(服务业)溢出,在城市从事技术生产的农民工不得不返乡“劳动”。而农村同样不需要这些剩余劳动力,这样一来,表演性劳动成为必要的生产方式,这是“第三景观”的“伪使用”价值。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30]。“种地”这种劳动形式可以成为被策展的对象:在展览期间,菜地、农田、乡道、古树就成为他们自己贴了“封条”(策划展览自己的文本?也就是:在它上面贴上封条,宣布它这两天有病,需要看护几天,这段时间里需被特殊对待,这就是展览。策展是:你只能在你宣布的那一段时间里成为它的作者了,哪怕它本来是你的作品,过后,它即是俗物(profane),是用过的制品了[28])的景观,他们也成了“幽灵策展人”,符号化地每天去田间地头当真地劳作,让游客兴奋地抓拍发朋友圈或发抖音。按照瓦格纳的“总体艺术”来看,这种行动也是被策展的当代艺术。在“第三景观”中,村民不是艺术家,村民变成了商品,为了抵抗这种乡村的商品化,我们是否应当策展“尘世慰藉的艺术”?[31]尼采认为,只有摆脱具有宗教意味的“一切形而上学的慰藉”,彻底抛弃那种把“形而上慰藉的艺术”当作全新艺术的浪漫病,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提升心灵。在传统意义乡村,村民的在场主体性不能被资本主义的景观世界符号化,这是幽灵策展的前提。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在乡村往往遭遇到三种物之概念和三种不同类型的景观:在乡村照面(偶遇)的夕阳、花朵、树木、农作物、牲畜等自然物是“自在之物”的“原生景观”,是那种“生态—生存”的本真世界。问题是,我们在这种真实面前显得不知所措了,因为在“资本—商业”的操弄下,我们从“关联之物”的“第二景观”之文化记忆中滑向了全球景观社会的“为我之物”的“第三景观”。在人类世,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向乡村?康德硬要做个老好人,故作姿态,示范给我们看:一面抬头仰望“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面俯首反思“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那么,在手机屏幕上如何使用理性呢?我们不再切身直观乡村的“总体美景”,只是纷纷用手机拍照、取景,拍下那些被认为“它是美的”对象,同时也把自己抛入景观中,自拍、或者请他者拍摄。商品化的“第三景观”鲸吞了前面两种景观,也就是商业的怪兽鼓动人们把自然和文化一起消费了。
在人类世,乡村正被“资本—商业”修剪成“精致”的盆景,沦为都市人回望—凝视的地方。村民不妨把自己的命运编写到剧本之中:村民是主演,把他者当成配角和群众演员,一起演一场瓦格纳想要的“宇宙共同歌剧”。我们可以在“幽灵策展”的过程中示范给村民看,当村民的身份转变成策展人的时候,“第三景观”才能不断写入新的内容,乡村才能活。策展乡村景观是要回溯到艺术的本源,警惕“第二景观”沦为文化记忆的残留,防止中了“第三景观”的毒,我们要动用生态术,以“生态—艺术”作为手术刀,将乡村景观带回到“生态—生存”的“原生景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