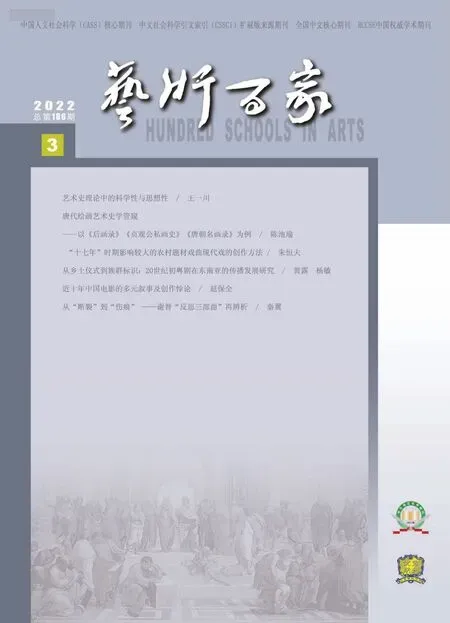强劲的想象造就了真实*
——评《爱情神话》的多元主题
于浩洋
(哈尔滨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爱情神话》于2021年圣诞节前夕上映,在整个上映周期内,共获得2.6亿的票房收入,在如今五百亿总票房的中国电影市场中,这样的成绩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与“50亿+”的《长津湖》《你好,李焕英》相比,更是相形见绌。但它却似一股清流,成为一部现象级作品,引发了广泛的讨论。90后导演邵艺辉在评价自己的这部处女作时说:“强劲的想象造就了真实。”这句话出自16世纪法国思想家蒙田的《论想象的力量》。在蒙田的思想中,想象力可以改变现实,也可以创造现实。无独有偶,2007年《太阳照常升起》上映时,导演姜文在接受采访过程中也曾引用这句话。邵艺辉和姜文相比,只是初出茅庐的新人导演,还远不能总结个人的艺术风格,《爱情神话》也不像《太阳照常升起》那样,有着强烈的前卫实验性质和魔幻现实主义属性,形成了两极分化的口碑。《爱情神话》凭借着独特的叙事风格,散发着想象力的独特韵味。这种想象并不是天马行空,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对现实生活的个性化观照,以及散文化讲述。导演用她的想象力撷取了她所认知的上海市井生活片段和在这都市景观中的众生男女,以及在他们身上的情感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实成就了导演的想象,而想象让影片讲述了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现实生活。
《爱情神话》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文化现象,除了它非常规化的叙事,用一种弱情节、去冲突的手段打破了爱情类型片的藩篱之外,更在于导演用镜头语言描绘了当下市井百姓的人生观、价值观。就像周斌所言:“(影片)从一个侧面反映上海‘魔都’开放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追求,展现了时代浪潮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痕,让观众品尝和回味都市生活的文化内涵”[1]4。正如片名一样,《爱情神话》应该讲的是爱情的故事,但看完影片会发现,爱情只是该片众多主题中的一个,甚至是最为表面的那个。在爱情主题之外,对女性凝视的思考,以及对生活切片的观照,可能是导演邵艺辉最想表达的主旨内核。
一、中年人的爱情观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最浪漫的情感,自然也成为电影最喜欢讲述和表达的主题。近年来,爱情题材的国产电影大放异彩,有着绝对数量的观众人群和票房保障,在视听语言、叙事风格、文化母题等方面也在不断探索。但爱情片依然陷入了创作的瓶颈期,朝着单一化、类型化和空洞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受前些年开启的校园青春风气影响,爱情片似乎陷入了怪圈,“时代怀旧+残酷青春+流量明星”成为创作者惯用的手法和追逐商业利益的不二法门,导致“当下国产爱情电影将爱情叙事过度脱离社会情境和社会现实,爱情表达显得苍白无力、虚假矫情,难以引起观众的认同,更难以经历时间的考验”[2]58。回顾近十年的国产爱情片,也只有《我的少女时代》《少年的你》等为数不多的作品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怎样在更加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表现爱情主题,尤其是打破近乎僵化的叙事模板,成为电影创作者不得不思考的命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爱情神话》脱颖而出。
与大多数国产爱情电影不同,《爱情神话》没有将视角聚焦在青春爱情故事,而是表达了中年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影片是以老白(徐峥饰)的爱情故事为叙事主线,讲述了他与李小姐(马伊琍饰)、格洛瑞亚(倪虹洁饰)、蓓蓓(吴越饰)三个女人的情感纠葛,电影的情节发展都是由这条主线所驱动。这既是影片的主线,也是明线。老乌(周野芒饰)与索菲亚·罗兰的故事亦真亦假,给观众营造了想象的空间,这是影片的暗线。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共同组成了该片的叙事结构,也共同指向了影片的主题。
《爱情神话》中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激烈矛盾,有的只是一种口语化的平铺直叙,甚至是有些寡淡。作为男主,徐峥饰演的老白性格温和,懂艺术并烧得一手好菜,是典型的上海好男人。老白所向往的爱情是传统与纯粹的,他无法原谅妻子的出轨而选择了离异,面对李小姐的主动显得慌张和欣喜,而李小姐后续的躲避与冷淡又让他无所适从。醉酒后与学生格洛瑞亚发生关系,他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不知所措。自始至终,老白对待爱情都是认真的,他渴望爱情,但是他在追逐爱情的过程中,缺少了敢爱敢恨的气魄。影片想要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中年人的爱情观。人到中年,已经褪去了年少无知和热情冲动,在他们的世界中有的只是克制与冷静。这样的爱情观在李小姐身上体现得更为鲜明。
影片一开场,被话剧感动的李小姐主动的“投怀送抱”,表现出她对情感的渴望。而第二天醒来的落荒而逃,又表现出她内心的胆怯,以及对爱情的抗拒。失败的跨国婚姻让她对异性的信任产生动摇,天生心高气傲的她对于爱情和人生的选择时刻保持理智。她给女儿听写的单词是“冷静,距离,保持距离,后悔,后悔做一件事”,这其实就是她内心的真实写照。她在说给自己听,也在说给老白听。老白给她画了肖像,她却说道:“我年轻的时候很吃这一套。”而人到中年,她对待爱情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渴望爱情但是又害怕拥有。影片几次出现她在窗边抽烟的镜头,表现出她内心的挣扎。可以说,老白和李小姐在对待爱情方面其实是一类人,他们已经不再年少,在经历过浪漫与激情后,想要的是一种平静和安稳,但又不断地彷徨与犹豫。影片最后,白、李二人的对话暗含玄机,表面是在说电影,其实是在表达自己对爱情的态度。李小姐把老白比喻成电影,说出了她的顾虑,似乎也下定了接受老白的决心,但电影的结局是开放的,至于最后二人的故事如何发展,就像李小姐的台词,“其实结尾不重要”。
如果说老白和李小姐在对待爱情的态度方面可以划归为同一类人,那么格洛瑞亚和蓓蓓就属于另一类人。格洛瑞亚妩媚风情,有钱、有闲,对于老公的失踪持无所谓的态度。她似乎早就看透了一切,爱情、婚姻都是虚假的,她只在乎洒脱与自由。但其实在她与老白的对手戏中,观众可以窥探到在“放荡不羁”的面具之下,格洛瑞亚有着典型的人格矛盾,也就是所谓的“双重人格”。“双重人格”是文学艺术中的经典母题,霍夫曼、埃德加·艾伦·坡以及史蒂文森都有相关作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3]78。格洛瑞亚整日沉迷于娱乐场所,似乎过得潇洒快活,但她在夜店里那一抹失落的神色就表明了她内心的空虚。这个镜头仅仅几秒钟,但或许那才是格洛瑞亚真正的内心世界。她是欣赏老白的,但她也知道她和老白不是同一类人。在她的世界中,爱情已然不再重要,因为相比于将自己寄托于一个异性,活出自我更加重要。
老白的前妻蓓蓓出场时身着朴素,给人一种温柔贤惠、贤妻良母的感觉,可她却是破坏婚姻的一方,并且她认为自己“只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她说:“我是个讲原则的人,我外面再玩,家里我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你是给我做饭了,给我做饭你也是开心的呀,你有什么好骂我的。”在她的观念里,爱情是重要的,但不是生命的全部,更不是束缚自我的牢笼。她内心想和老白和好,但又不想违背自己秉持的原则。同格洛瑞亚一样,她们都是传统爱情观念的悖逆者,她们践行着自己的爱情观。
相比于上述几人,老乌在《爱情神话》中是一个画龙点睛的人物,他的存在让整部影片在爱情精神层面得到了升华。老乌之所以叫老乌,是因为他讲述了一个乌托邦的故事。或许我们再去追问他与索菲亚·罗兰的相遇是否真实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他用一生维护这个空灵、美好、虚幻的爱情。就像神话一样,不能因为其虚假的本质就否定其存在的意义。正如比较神话学者约瑟夫·坎贝尔所说,“神话是公开的梦,梦是私人的神话”[4]9。老乌的一生是潇洒、轰轰烈烈的,爱情对他来说,既是他的梦也是他个人的神话。
《爱情神话》就是在这简单的几个人物、几组关系中完成了不同于其他影片的爱情表达方式。90后导演邵艺辉用错位的视角表达出了不属于她年龄段的爱情体验。或许正是因为年龄的错位,观众才有了一种新鲜的体验,影片叙事才有了一种介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意味。
二、女性凝视下的世界
在评论《爱情神话》时,避不开的一个主题就是女性主义。这或许是因为导演邵艺辉是女性的缘故,也是因为整部影片女性角色的比重和作用都要远远大于男性。但该片也不是“传统意义的女性主义电影,因为它并不触及两性平等女性权力等社会议题,也不着眼于对父权的批判,而是更多地聚焦于两性情感关系的探讨,特别是女性情感的选择,所表达的观念和倾向其实带有后女性主义的腔调”[5]32。“后女性主义”是后现代性的表现之一,它消解了传统的性别差异,解构了男性中心论,并通过中心化的方式,替代了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在影视艺术中的表现就是一种超越了劳拉·穆尔维将女性与权力结合起来的主张,它不再将凝视视为一种“性别权力关系的运作”[6]99,而是“通过自己的作品以女性独具的视角对女性世界进行深入挖掘及对女性心理的敏锐观察,从而准确地找到女性的生存状况及精神意识,借助影视手法将现实女性的内心诉求、心理状况呈现出来,将大多数现实女性面临的情感危机、生存状况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呈现出来”[7]143。《爱情神话》的后女性主义体现在影片没有强调男女对立,也没有展现对男权的批判,而是在确证女性自我身份的同时,保留对男性的尊重,因此在影片中,男女的相处模式是融洽的。其实这样的一种立场,不只是《爱情神话》所独有的,而是符合21世纪以来中国女性电影的整体趋势。作为90后的女性导演,邵艺辉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决定了她不会去极端表达两性的对立和对性别权力的批判,而是在一种舒缓的节奏中展现了女性凝视下的世界。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李小姐、格洛瑞亚、蓓蓓是当代都市女性的代表,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人生境遇。但是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从自身出发建构了对世界的认知。影片中最为观众津津乐道的一个场景便是三个女人在老白家的不期而遇。按照以往套路化的处理,这时导演会设置激烈的矛盾冲突,以追求故事的戏剧性。但《爱情神话》没有迎合观众的观影经验,蓓蓓说出十分挑衅的语言,就当观众以为女人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时,影片实现了一个大的转折,避免了矛盾的发生。虽然影片回避了情节的冲突,但导演通过演员的台词和微妙的人物关系依然营造了极强的戏剧张力,将这一场景推向了影片的高潮。而这一场景戏剧张力的最本质内核就是三位女性对自我身份的凝视和建构。
蓓蓓将老白比喻为“剩菜”,表面是她对老白的讥讽,以及对李小姐和格洛瑞亚的嫉妒和轻蔑,但实质是一种她对自己在两性关系中主体地位的宣示。在她的观念里对爱情不忠从来不是男人的特权,女性没有义务按照男性设定的规则生活。“野猫”是格洛瑞亚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并为其正名,在她的观念里,女性为什么一定要为某个人、某种关系负责,她对待婚姻不忠,对待感情如同儿戏,对待人生放纵,但在她看来却是“最好的状态,想做什么做什么,无忧无虑”。就像前文总结影片人物的爱情观时一样,蓓蓓和格洛瑞亚是一类人,她们在影片中作为解放者的形象而存在。她们没有活在艾德琳·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说的男性的眼睛和思想中,而是选择打破束缚自身的“监狱”和牢笼。连续的“一个女人一辈子……是不完整的”的台词是她们的解放宣言,在她们挑战传统观念对女性的规训与束缚时,老白最后所说的“一个女人这辈子没造过反是不完整的”显得无力苍白。就像整部影片中他的角色一样,似乎是中心人物,但在整个故事的开展过程中,他总像是一个配角,或者说串联者,仅仅起到连接影片人物脉络的作用。不只是老白,这部电影中的男性角色其实都被弱化了,这也是该片女性视角的第二个特点:男性的缺席。
在影片三个主要的女性人物的世界中,男性都是缺席的。李小姐经历了一场失败的跨国恋,格洛瑞亚的台湾老公也不知所踪,在蓓蓓的世界中也没有丈夫的存在。不仅如此,李小姐和白先生也只有母亲在世,丈夫的缺席成为该片女性自由生活的象征。在萨特的理论中,他者是自我的先决条件,只有处在被人凝视的状态下,才会体验到自我的存在。穆尔维反对的就是这种男性凝视下的女性建构。《爱情神话》并不是简单地反对男性的凝视,而是通过弱化男性角色的存在,消解了作为他者的男性的主体地位。
男性缺席的另一个象征是性别的错位。影片中的女性都要比男性更为强势,这并不是为了表现男性的绅士,而是导演的特别设计。“这是一个性别错位的视角,将李小姐、蓓蓓、格洛瑞亚放到了更男性的身份中去,老白和老乌反而更偏向女性处境,一旦性别进行置换之后再去观察这样的戏剧冲突,就会变得非常有趣。”[8]这样的错位还表现在对白鸽的塑造上。老白和白鸽作为父子,在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上却有着巨大差异。白鸽喜欢化妆,行为举止略带中性,并且有着妈宝男的倾向。这样的人物设置,不仅表达了影片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性别的倒置。
《爱情神话》充分演绎了女性凝视下的世界,也为女性群体构建了一个在都市景观中的文化空间和生存方式,从而“呼应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理论与大众叙事的和解,以及一种‘大众女性主义’的新策略”[9]193。
三、对生活切片的观照
虽然《爱情神话》取得了很好的口碑,但依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对电影的批评主要是对电影深度的不满。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该片主要展现的是一个折叠的上海,浪漫、唯美,里面的人物也似乎从来不为物质所困:主人公不用工作,房客不用交房租,就连路边的修鞋匠也有自己的咖啡时间,并且像一个思想家一样对人生哲学滔滔不绝。有人评价,《爱情神话》是一种“去阶级化”的电影,回避了现实世界中的矛盾,留下的只是导演臆想中的都市生活。虽然有很多痕迹都表明导演在追求伍迪·艾伦的风格,但只是表面模仿艾伦电影的轻量化叙事,而缺少了艾伦电影中的批判性和诉说现实的力量。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评价,一是因为《爱情神话》的确用轻盈、灵动的语调,营造了一个美好的上海弄堂里的市井生活,与人们真实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相距较远。二是多年的观影体验让人们认为文艺片天生应该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或是剖析社会的矛盾,或是揭露人们心灵的挣扎,这已经成了既定的逻辑与规则。但《爱情神话》的定位并不是如此。用导演的话说,她没有义务去展示一个真实的上海,而只是展示一个她熟悉的和她眼中的上海,更不必去承担描绘底层的责任。[10]从本质上讲,《爱情神话》只是一部爱情小品,观照的也只是都市中年饮食男女的生活切片,故事性是它的第一追求。影片避免了沉重的话题和深刻的能指,没有批判,没有说教,没有美化,也没有强行的冲突和圆满,这样的特质反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
就像徐峥所说,“电影创作需要以生活为基础,尊重生活是电影具有本土化灵性与文化自信的前提”[11]22。而生活是多元的,尊重生活的多样性也是电影的责任与义务。并且,《爱情神话》也并非只是空中楼阁,它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就是它成功切中了某种社会情绪[11]23。从这个意义上讲,《爱情神话》也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精神,只是这种现实主义,是一种“轻量化”“唯美化”的现实主义。对于现实主义电影的讨论也是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虽然对现实主义的定义有不同意见,但可以明确的是,现实主义不是只有一种面貌。饶曙光等人就认为:现实主义除了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有“温暖现实主义”“积极的现实主义”“建设性的现实主义”等。现实主义有多元性,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我们要避免对现实主义的片面解读、过度解读,以至于使现实题材电影的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窄。[12]15从这个角度出发,并不能否定《爱情神话》的现实主义身份。比如影片所展现的精致悠闲的生活,比如老乌散发着精致讲究的上海味道,老鞋匠定时喝咖啡、吃点心,都是一种上海独有的真实,它确实没有表现什么真实的全景,但它真实表现了某种截面。影片的现实主义还在于它没有像其他爱情片一样设置一些浪漫或狗血的情节,而只是真实展现人物内心的矛盾与复杂,遵从了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和真实感受。它没有刻意设置完美的男女爱情,当然也没有太沉重、太复杂、太悲苦的东西,它真正深入女性心灵世界,站在女性视角去讨论爱情和生活的故事。
邵艺辉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影片所展现的就是她所观察和理解的上海市民生活的状态。她说:“虽然我不是上海人,但是写这个故事却是我的优势,可以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去看这座城市,会相对客观,就是更有距离地去感知。”[13]20即作为一个亲历者,又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许这就是《爱情神话》能够拥有独特生活韵味的秘密。
四、余论
《爱情神话》讲述的是上海的故事,展现的是一群70后的中年人的生活状态。全程上海话的使用,虚实结合的街拍实景,再加上主要演员都是上海人,成为该片的一大特色,也成了其最鲜明的身份标识——海派电影。海派电影最重要的两个立足点是地域性和美学风格[14]31,地域性是指电影不能脱离上海的地域内容,美学风格可以概括为开拓性、务实性、随俗性。[15]108《爱情神话》完美地符合了这两个基本要求,因此被评价为续接和发扬了海派电影的传统,传递了海派文化个性、多元、包容的精神品格。影片的成功也给了海派电影以及中国电影的创作一些启示:第一,电影的创作要立足于本土文化。本土文化是电影创作的精神依托,只有坚持本土化的创作策略,坚守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才更能引起观众的共情和认可,也才能够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电影作品。第二,电影要进行多元化的创作实践。如今,电影从产业链到电影美学再到观众的审美趣味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电影的创作不能拘泥于固定的模式和套路,而是要在题材、类型、风格、样式等方面进行多样化的创作,打造多样化、多品种、多类型的创作格局。第三,电影的创作既要继承传统也要开拓创新。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我国电影创作诞生了许多经典作品,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美学传统和话语体系,当下的电影创作要充分继承利用这些精神遗产,并在此基础上跟随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