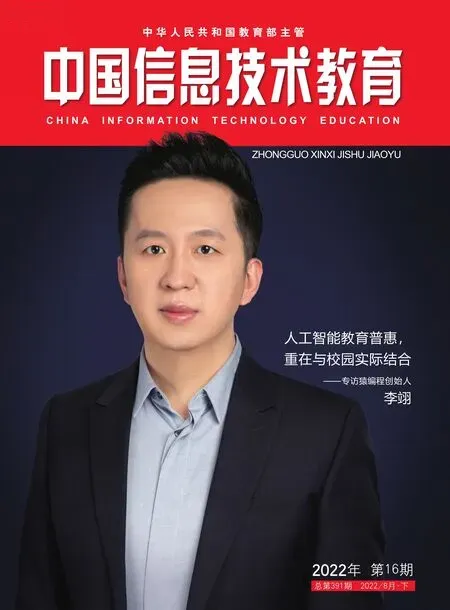君子不器:论基础教育人工智能课程的价值旨归
苏航 宁夏大学
● 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顶层设计演进与学科发展道路
2017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应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2019年以来,教育部把“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相关工作列入历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重点推进;2021年,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开发标准(试行)》,同年,中央电化教育馆印发《中小学人工智能技术与工程素养框架》。一系列文件的出台,昭示人工智能课程的顶层设计正由粗放演进走向逐级细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该课程国家层面的示范引领问题。
目前,各地中小学主要通过人工智能元素同STEAM课程、创客课程、机器人课程相结合,实现基础教育人工智能课程的“从0到1”,开展形式主要以校本课、社团课、“双减”政策落地后的课后服务为主。囿于人工智能学科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还存在定位模糊、课程体系不完善、资源建设良莠纷杂、教学内容脱离人工智能核心知识等问题。
和传统学科相比,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托“以赛促学”——通过相关竞赛活动的开展达到普及人工智能知识的目的。同时,教育服务供给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在人工智能教育推广之初,走的是“企业-社会”“企业-学校”单点多向的辐射道路。企业作为突破人工智能蒙昧状态的先行军,还需在人工智能教育落地过程中不断探索定位、通过建立多方协同机制以观后效;学校教育作为学生接受系统教育的主阵地应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人工智能教育的相关政策研制与课程校本化探索间双向同步进行,不失为当前情境下较为积极稳妥的应对之策。
● 学科定位:“君子不器”与人才贯通培养
目前,国际赛道上高新科技产业与人才储备角逐呈现白热化态势,我国人工智能战略布局形态初显,人工智能的人才贯通培养势在必行。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学习领域有所分化,但基本遵循宽口径、重基础的培养思路,基础教育阶段作为素养培育的关键期,在建设由通识到精专的多层次人才储备梯队中的作用应受到重视。
知识的爆炸式增长、世界的精细分工、技术的迭代更新,无一不冲击着现有的教育体系。对学生而言,学习、接纳新事物的能力比停留在具体的技术应用更重要——多年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基本着力于知识应用到素养培育的转型,充分说明指向知识的浅层次识记应用已无法满足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要,“思维”“能力”的培育更能适应智能时代的生产模式,契合学生作为“人”的整体有机生长。
对于人工智能这门新型学科,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定位应落在科学素养的培育上。以良好的学习体验和高阶思维的有效训练为锚点,通过基本知识技能方法的习得,挖掘并激发学生学科领域内的最大潜能——君子不器,无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艺,则器也。当前,人工智能课程的教学痛点在于过分强调“器”的精通。在基础教育阶段,人工智能课程的实践性较为鲜明,无论是学校教学还是校外培训服务,开展相关教育通常以图形化编程软件为抓手,支持一定类型与数量的硬件拓展,基本涉及图形识别、语音交互、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要素,依托于具体的硬件设备进行一系列的体验实操活动。从学习资源的角度看,目前的资源形式多为相应硬件产品的文档介绍、功能模块的使用步骤与示例程序,性质多趋向“产品操作手册”,既缺乏人工智能相关原理知识的提炼整合,也缺乏情境导入、寓教于乐的教育性元素。
一味停留在浅层次的具体器材使用上,无形之中会弱化对思维的培养与迁移,培养目标很容易从“具有创新思维的设计者”沦为“勤于动手的工匠”——“君子以道为本,故不入于形。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通其变者也”。在学习初期,“入与形”使知识的应用学习真实可感;一味“困于形”,则不利于学生追求更高阶的思维素养之道。
● 关于人工智能课程的核心内容与实施阻力
余胜泉等学者将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的核心领域划分为智能体的“感知”“推理”“学习”“决策”“交互”“道德”六部分,基本兼顾了人与机器间伦理关系的辩证思考,以及智能体采集分析数据、知识的表征与逻辑推理、机器学习与用户交互等完整工作流程呈现,再辅以需求分析、工程搭建、编程实现、方案优化迭代等学习活动,基本涵盖了人工智能的学科概念、核心知识与关键能力。
另一个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是:编程教育在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图形化编程平台内经过降维处理后的人工智能封装模块对学生较为友好,在目标定位为“体验”的初级学习活动中表现优异。但如果基于体现学科特点与知识完整逻辑的考虑,单纯“图形化编程—人工智能应用体验”的二元授课模式在体现原理知识衔接性与进阶性的深层次教学活动中稍显无力。因此,将图形化编程作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入门基础课是合适的,但在人工智能课程的中后期,学习重点应从传感器识记、交互功能体验的黑匣探索模式逐渐转向能体现人工智能原理技术的典型算法学习,Python很适合作为该过渡时期的计算机语言工具。
校际人工智能教学设备配置情况的各不相同,为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开发后的标准化、模式化推广造成一定阻力。从教学硬件产品的角度看,所选用的科创教育产品在品牌内的服务齐全,生态完整,但品牌间的平台、零件、接口各有标准,难以兼容。人工智能的体验学习依赖于一定的平台与硬件,符合教学要求与技术标准的产品又难以统一,两难窘境下就需要各地各校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开发实施课程,需要一线教师投入实践摸索出更多切实可行的教学模式。
此外,开设人工智能专业的高校比例逐年攀升,而人工智能师资培育的专业尚未发展,能够胜任人工智能课程教学任务的一线教师稀缺,部分学校存在购买科创教育机构的服务,以校外培训人员包办代替本校教师梯队建设的现象。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培育具有教学胜任力的中小学人工智能职前教师与在职教师,都是今后亟须解决的问题。
● 小结
目前,中小学人工智能的学科定位应着眼于“君子不器”的科学素养的培养,避免流于科创教育产品的具体使用的浅层次学习目标。在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深受科创教育企业影响的背景下,学校教育应努力适应变革,积极投身人工智能课程开发的校本化探索,重点解决教学内容脱离人工智能核心知识与中小学人工智能师资队伍建设两大问题,借助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共同促进学科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