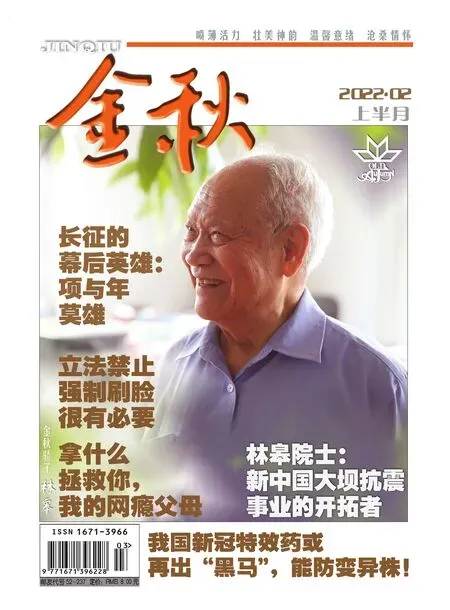挂坡
※文/卫建平

“文革”时期,父亲被关了“牛棚”,每月只给一点生活费。母亲当时没有工作,一家六口全指这点生活费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吃了上顿愁下顿,耳畔常能听到母亲沉重的叹息!我是家里的老大,虽然只有十四五岁,但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为父母分忧、为家里减轻负担了。
有一天,我小学一位姓闫的同学(因为他很早就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颇有些“老夫子”风度,同学们都称他“老闫”)提溜着一条带钩的绳子找到我,约我去“挂坡”。我一听正中下怀,立即在家里东翻西找,终于也找出了一条绳子。按老闫的指点,找来一截铁丝,用稚嫩的小手笨拙地握着钳子弯了一个钩,绑在绳子上,便兴冲冲、却又有些忐忑不安地跟着老闫出发了。
所谓挂坡的“专业技术”,简单点说,就是给负重的两轮架子车搭个帮手而已。我们挂坡的地方选在南沙坡,一听地名就能想到那是一个较大的坡道,从南向北大约有一里多长。主要的“货源”是劳改窑(又叫青砖二厂)出来的拉砖车,都够重的,靠一个人的力量拉一车砖到坡顶确实吃力,而挂坡到坡顶的“行情”是能挣到五分钱。
有一点值得骄傲的是:初去时,因为我人长得瘦小,很难揽到活,所以一旦揽到了我就特别卖力,肩膀磨破了,血刺拉糊的,我垫上一块毛巾,照样把绳子绷得紧紧的。日子久了,拉架子车的大爷、大婶们知道我不会偷懒,所以一出了砖厂大门便会指名叫我挂,惹的带我“出道”的老闫都有些气不忿了!
记得我第一次将挂坡挣到的浸满了汗水湿漉漉的两毛五分钱一分不少交到妈妈手上的时候,妈妈哭了,一边哭一边用稀释的高锰酸钾水清洗我肩上的伤口……
后来因为那次中暑,妈妈说什么也不让我再去挂坡了。
那天已过中午时分,我已经挂了五趟,挣到了两毛五分钱,完成了当天的“指标”,正饥肠辘辘、气喘吁吁地站在坡顶等老闫,准备打道回府了。这时,一位拉着满满一车砖的精瘦大爷问我去不去西大街?说挂到西大街给我两毛钱。我一听来了劲,两毛钱啊!加上我已经挣到的两毛五就是四毛五了呀!而且,西大街离我家又比较近,拿了钱正好可以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于是我也顾不上等老闫了,二话不说,绳钩往架子车辕把旁的铁环上一挂便上了路。
从南沙坡到西大街应该有十多里地吧,又是大夏天!一路上的劳累、饥饿和干渴就不必细说了。总之,刚进了和平门,我就感到头晕、恶心,可为了两毛钱还是咬牙硬挺着;过了钟楼,我的眼前开始一阵阵发黑,还有一些星星在“黑影里”闪烁,路上嘈杂的人声、车声我听着好像特别遥远,意识也开始一阵阵模糊,可我还在挺着。一直到了桥梓口附近的一个什么单位,刚听到拉架子车的大爷说:到了!我便一头栽倒在地上,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大爷把我抱到了树荫下,身子底下垫着他随车带的草席,又给我喂了几口水,我才悠悠醒来。看到大爷的眼睛里好像有泪光在闪,我心里一阵内疚,硬撑着要爬起来,被大爷摁住了。大爷说:你先躺着,等卸完了砖,我送你回家!
砖卸完了,大爷扶我躺在卸空的架子车上,把草席搭在车帮上遮着太阳,一直把我送回了家。路上,我知道了这位大爷姓杨,住北关自强路,家里有七个孩子要养活,孩子他妈身体又不好,家庭情况很困难……
到家以后,大爷没顾上喝一口我妈倒给他的茶,便急匆匆地走了。我知道,他还要再去拉一车砖呢!
从这天以后,母亲死活也不让我去挂坡了,我再也没见过这位杨大爷,心里总感觉愧愧的。那天,大爷走了以后我才发现,我的衣兜里多了一毛钱,那一定是大爷多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