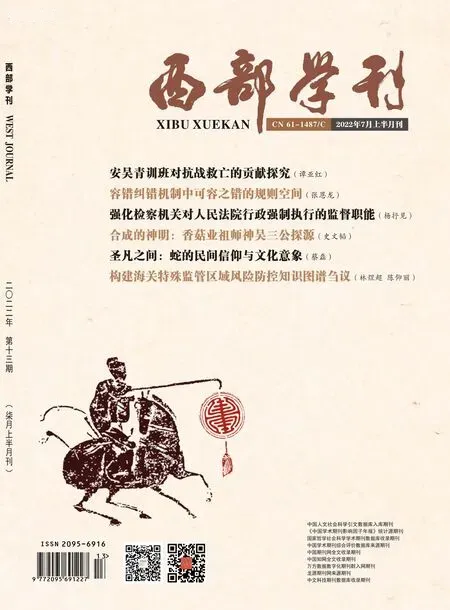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限缩解释
——以性剥削理论为根据
季昊雨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案件频发,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刑法增设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修正案》)公布后,围绕其是否提高了未成年女性的性同意年龄,刑法学界出现了“有限提高说”与“不变说”两种对立观点,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性同意年龄没有提高。“有限提高说”主张,不问未成年女性同意与否,都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加强对未成年女性身心健康的保护[1]。主张“不变说”的学者认为,“有限提高说”会压缩未成年女性的性自主权的支配空间,造成本罪法益内容笼统含糊,也与《修正案》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存在矛盾[2]。不过,这两种观点都是以性同意年龄为核心来解释本罪保护的法益,也都没有深入挖掘制定本罪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分析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本质,指出性同意理论在解释本罪时难以突破的瓶颈,倡导将“性剥削”理论作为性同意年龄的有效补充。
二、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成立标准:从是否提升性同意年龄到是否存在性剥削
(一)性同意年龄及其法律根据
《元照英美法词典》将性同意年龄解释为:“男女方均可不经父母同意而结婚的年龄,或指女方可作同意与他人性交的意思表示的法定年龄,因此,男子若与未达此年龄的女子性交,则构成法定强奸罪”。一般认为,未成年人对世界的认知能力与成年人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只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持续的社会交往与实践中逐步获取社会生活的基本经验,他们才能获取处分自己权益的能力或者准确理解自己行为性质的能力。例如,《民法典》明确规定了不同年龄主体的行为能力,以确定其行为的民事法律效力。《刑法典》明确规定了不同年龄主体的刑事责任能力,以确定其是否应当承担或者承担何种刑事责任。具体到对性行为的认识与理解,更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知识之上。世界性学会发表的《性权宣言》将性权利认定为基本人权之一,但是未规定儿童具有性权利。同样的,联合国大会制定的《儿童权利公约》只规定了儿童具有免受性剥削、性虐待等消极性权利,并未规定儿童具有依真实意愿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的积极性权利。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未成年人的消极性权利,同样没有对儿童的积极性权利做出规定。
(二)性同意年龄存在的问题
围绕本罪其是否提高未成年女性的性同意年龄,刑法学界出现了“有限提高说”与性同意年龄“不变说”两种对立观点。有限提高说主张上述特殊职责人员与14周岁至16周岁女性发生性关系的,不论她是否同意,都应追究刑事责任,实际上部分提高了性同意年龄[1]。原因如下:(1)从近两年的司法实践看,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约一千二百件性侵未成年人案中,教师性侵未成年学生约为一千件,占比很大。(2)本罪并未规定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即不问是否使用暴力手段,也不问未成年女性同意与否,只要负有特殊职责人员与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行为人均构成本罪,体现了对未成年女性身心健康的严格保护。但有限提高说是值得质疑的。首先,有限提高说可能侵害未成年女性的性自主权。通常认为,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可以自主决定何时、何地、和谁发生性关系。若认为本罪将性同意年龄有限提升到16周岁,那么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女性在与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发生性行为时,即使是在双方自愿发生且行为的结果不会对未成年女性造成任何伤害的情况下,也会因未成年女性无性自主权,进而使行为人受到刑法处罚。这样的做法等于是将低龄未成年女性不区分情形地被害化、客体化,副作用显而易见[2]。其次,有限提高说认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在面对负有特殊职责人员时并没有同意的权利,因此本罪保护的法益是未成年女性的身心健康权,但身心健康是否可以作为本罪保护法益有待商榷。第一,身心健康内容过于宽泛且损害程度会因被害人的性格、罪行严重程度的不同而不同。第二,在奸淫幼女型强奸中,为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否定其性同意权。同时,未满14周岁的幼女在面对性侵害时,因其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相比于成年女性,幼女在受到性侵害后更不易恢复,更难从侵害中走出来。但有批评意见指出,故意杀人、抢劫等犯罪也对受害者身心健康造成了损害,那么在性犯罪中对幼女的身心健康给予特殊保护的理由是什么[3]?在本罪中这样的批评更为尖锐,因为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的幼女无性同意权,根据反对解释可知,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女性有权做出同意发生性行为的表示,因为其有性自主权。因此,很难理解为什么未成年女性在面对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时,即使是真心同意,也会受到损害。
保持不变说认为性同意年龄并未提升,理由如下:(1)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在面对特殊职责人员时,不对等的关系会形成看不见的强制,从而压制未成年女性真实意愿的表达[4]。(2)本罪法定刑的设置轻于强奸罪,若本罪侵犯的对象没有性同意权,应当同奸淫幼女型强奸一样认定为强奸罪,而不是增设轻罪予以处罚。该说在稳定性同意年龄方面值得肯定,但保持不变说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不对等的关系不一定会形成隐性强制,不是所有具有实力差距的关系都会形成压制。其次,会混淆本罪与强奸罪。该说认为未成年女性的性同意权之所以时有时无,是因为产生了隐性压制,存在心口不一的情况。但这样的同意并非真实的同意,在未成年女性并未同意发生性关系的场合下应当适用强奸罪,而不是法定刑设置较轻的本罪。
两种学说的支持者就《修正案》对于年龄的规定是否存在矛盾进行了讨论。有限提高说认为,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降与性同意年龄的上升并无冲突,在通常情况下,家长从小就教会自己的孩子不要伤害他人,学校也会对学生进行生命健康教育,可对于儿童的性教育,家长往往不会主动对孩子提起,学校也并未对学生进行教育。因此,存在孩子理解杀人行为,却不理解性行为的情况。保持不变说反驳道:第一,“剥夺他人的生命法益”与“处分自己的性权利”哪个更复杂、更难让孩子认识[2]?他可能知道不能伤害他人,但是否真正理解“生死”的意义,是存在疑问的。第二,二者究其本质都是考察主体对于某件事实的认识能力。一面认为已满12周岁的未成年应对杀人行为负责,一面又认为已满15周岁的未成年女性无法理解性行为的观点存在矛盾[5]。
两种学说对“认识”进行的讨论更加突出了认识的困难度。未成年女性同意的前提是准确的认识,那么双方到底是真的恋爱关系,还是一方给自己洗脑而虚构出的亲密关系,例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PUA等,名为恋爱,实为一方对另一方的精神控制。即使是成年女性也会有对亲密关系做出错误的判断的时候,对人际关系处理更显稚嫩的未成年女性来说,更有可能被别人“洗脑”或者催眠自己从而表现出恋爱状态。也就是说,存在未成年女性自认为二人处于恋爱关系并做出了自认为“心口合一”的同意,可事实上处于被利用、被剥削的情况。“有限提高说”否定了未成年女性对于性行为的认识能力,但会侵害其性自主权;“不变说”肯定了未成年女性具有认识的能力,但是却不能周延地保护未成年女性。同意不过是动动嘴皮,因为表达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认识并非易事。因此,倡导将性剥削理论作为性同意年龄的有效补充,转变判断的位置,从被害人的认知转变为行为人的行为,判断标准会更客观,更具统一性。因为性剥削理论的重点是剥削者如何利用弱势一方获取利益,而不是弱势一方的认知能力。
三、性剥削理论的优势
从文义来看,剥削是指以不公、残忍的方式利用某人或某物。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剥削是指占有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人(那个阶级)对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人(那个阶级)的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6]。艾伦·维特海默在《剥削》中指出,剥削是指一个主体A从另一主体B身上获得了不公平的好处[7]。那么,什么是性剥削?约翰·盖格农在《性社会学——人类性行为》一书中列举了几种男性对女性的性剥削:有几种性关系本身并不违法,但当性犯罪发生时,会使罪名加重,或成为禁止当事人从事某种职业的依据,例如发生于医生与病人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律师与客户之间、法官与被告之间、军官与士兵之间、经理与秘书之间及一切发生于地位优越与处于服从地位的人们之间的性行为,这类关系中常有男性对女性的性剥削[8]。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得到应得的奖励是很正常的事,但不公平地利用他人作为工具去获取好处则是令人不齿的。因为对“不公”的理解不同,所以剥削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所有剥削始终包含了“利用”与“剥削者受益”两个核心要素[9]。性剥削中的利用是指剥削者将受剥削者的某些特性或受剥削者的所处环境转化为对自己的优势,从中获利[10]。受益是指得到好处,但是不限于物质方面,精神或身体得到了满足也应当属于受益。
(一)性剥削理论揭示了行为人行为对未成年女性的侵害性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滥用信赖和优势地位实施犯罪,会对未成年女性造成以下伤害。第一,性侵害的受害者可能有下贱感和背叛感等不健康心理状态。其中,下贱感是指被害人会不断自责,认为被性侵是自己的错,从而厌恶自身,容易因为事情的二次发酵导致自伤或自杀的情况[11]。背叛感是指被害者因为有被信任之人伤害的经验,导致其无法发展正常的人际关系[11]。本罪中,未成年女性通常处于在校学习阶段,如果行为人是教师,事情很容易二次发酵,被害人所感受到的下贱感会更强烈。同时,行为人作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肯定与被害人相互认识,与陌生人相比,被害者更会因为背叛感而受到更重的伤害。也有的被害人会因为被人背叛而感到愤怒,从而出现反社会行为[11]。第二,树木受伤后,会在伤处长出更厚的树皮,但遭受性侵害的人却更容易再次陷入危险的心理状态中。经历过性侵害的人比一般人更容易触发心理防御机制。例如,斯德哥摩尔综合征,它是指受害一方对加害一方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一方的心理情结[12]。斯德哥摩尔综合征并不少见,发生的概率极大,对曾经遭受性侵的女性来说,与伤害自己的人建立爱情关系,反而会让她们感到安全[12]。被害人以为自己出于真心的同意,其实是为了活下去而做出的行为。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存在,才需要性剥削理论在未成年女性“不自知”的情况下保护其合法权利。
(二)性剥削理论揭示了未成年女性有效同意的实质根据
负有照护职责的人员之所以可以对未成年女性进行剥削,根本原因是双方地位、能力的不对等。同时,未成年女性与特殊职责人员间的年龄差距是不对等关系最明显的外在表征,也是不对等产生的重要原因[10]。
年龄包含了生物年龄和社会年龄,后者赋予了前者大量的社会、文化等信息,二者紧密交织在一起。年龄不是对生命简单地度量,它是流动的、丰富的,具有很多意义:第一,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用年龄区分长幼,也会用年龄去定义一代人,比如千禧一代、零零后等。第二,年龄也具有法律意义。比如,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要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等。第三,在心理学上,年龄也被用来判断一个主体是否拥有或者多大程度拥有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因为年龄的增长与社会实践经验的增长成正比。在生活中,我们被教导,遇到危险时,儿童优先逃生。不光是因为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也因为儿童的逃生能力比成年人低。在法律方面,国家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无论从哪个意义讲,未成年人因为年龄小,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10]。年龄的差距越大,双方的实力差距就越明显,也即未成年女性与负有特殊职责人员之间的年龄差距大小可以调节性剥削的强弱程度[10]。因此,当未成年女性同与自身年龄相差不大的特殊职责人员发生性行为时,可以认为不具有性剥削的性质。有德国学者认为,未成年人与他人年龄相差5岁以上就存在实力的差距,但建议将年龄差距规定为4岁,理由如下:考虑到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人员的年龄,如果规定为2岁或3岁,会导致部分特殊职责人员无法适用性剥削理论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