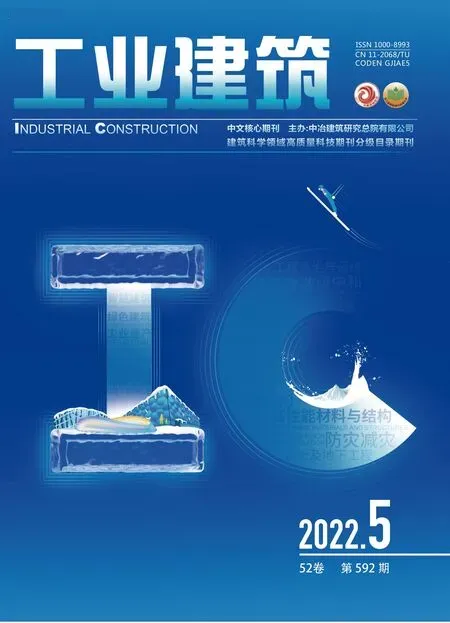“三生”功能视角下乡村景观时空演变及影响机制研究*
——以顺德杏坛北七乡为例
范建红 梁肇宏 罗斯瑶
(1.自然资源部城市国土资源监测与仿真重点实验室, 广东深圳 518034; 2.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广州 510090; 3.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广州 510060)
乡村景观是指乡村地域范围内具有特定景观行为、形态和内涵的人地互动产物,是乡村社会人文、经济和自然环境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的空间性表征,具有人文与自然的复合特征[1-2]。二战后在全球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席卷浪潮下,乡村地域人口、产业、社会结构及生态格局发生深刻的重塑。在欧洲共同农业政策实施下,西方乡村地区普遍经历了从农业集约化、农业规模扩大化到边缘农业废弃化的发展过程,乡村景观实现了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从生产空间到消费空间、从田园景观到后田园景观”的转变[3]。综合多学科范畴的多功能主义和可持续发展观的乡村景观演变呈现区域化和多元化的特征,乡村土地功能转换驱动着乡村景观结构、类型和功能的演变过程。在多元价值主导下农业功能不再是构成乡村经济基础的主要形式,乡村景观多功能转型演变轨迹充满动态性、复杂性与异质性[4-5],关注乡村社区和社会公平[6-7],兼顾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精神文化等综合价值[8],推动着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乡村可持续发展探索。我国乡村景观研究范式与国外具有相似性,在乡村振兴战略导向下,重点围绕乡村人居环境优化提升、农业现代化转型、乡村旅游、脱贫攻坚等方面,对乡村景观格局及其空间特征[9-10]、乡村景观空间演变与优化重构[11-12]、乡村景观保护[13]、乡村景观评价[14]、乡村景观营造与规划[1,15]、传统地域文化景观[16]、乡村社区公共参与机制[17]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乡-城”要素流动差异而导致的乡村人地关系与景观风貌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引发了诸如乡村生态环境“破碎化”、人居风貌“同质化”和乡村地区“空心化”等问题。十九大后,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三区三线”管制和“三生空间”划定作为推动人地关系和谐发展和实现国土全域空间管制的重要举措,对于保护乡村绿水青山的自然地域风貌和维系乡愁的地方情感依托具有重要意义。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乡村空间科学布局及乡村景观多功能融合发展亟需结合“三生”功能协调的视角开展乡村景观的相关探讨。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三生”功能的协调发展并推动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空间优化成为乡村振兴目标的重大挑战。本文选取顺德杏坛“北七乡”为研究区域,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法,以不同时期乡村土地利用类型转变为研究对象,研究“三生”功能空间实践过程下的乡村景观时空演变历程及其影响机制,以期对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背景下构建乡村景观优化重塑和转型发展路径及其土地利用与复合存量资源利用再配置的优化方式、以及为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城乡建设绿色发展以及历史文脉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提供参考。
1 乡村地域“三生”功能理论内涵及其与乡村景观演变的关系
1.1 乡村地域“三生”功能理论内涵解析
多功能的概念起源于欧洲20世纪末农业多功能性研究,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化,多功能内涵逐渐整合农业生产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视角,延伸至关注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乡村社会人文环境等以地域性为特征的多功能性研究。乡村地域多功能是指在农业文明时期、工业化时期到后工业化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乡村自身社会生态系统、城乡区域功能单元作为主体,结合地域资源维持系统内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特性,并对外发挥区域协作功能的综合属性[18]。根据其对自然地理环境和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的基础性服务,乡村地域多功能直接或间接关联以“生态、生活、生产”为核心的“三生”功能。乡村地域生态功能在其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过程中,为乡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可持续运转和乡村聚落的发展提供充足且必备的资源要素,实现地域系统自我调节、恢复并构成区域生态屏障,维持人与自然稳定发展;生活功能为居民提供的物质空间承载、文化精神和情感依托,在人地关系演化下稳固乡村社会结构,形成稳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保障;生产功能则通过组织土地等乡村地域资源要素进行社会生产、原料加工转换从而获取农业产品及其服务[19]。因此“三生”功能更关注于多元的人本需求,并体现于不同时期下对生态性、经济性、社会性和人文性功能导向的发展侧重,促使乡村土地利用结构与利用方式发生改变。
1.2 “三生”功能与乡村景观演变的关系
“三生”功能基于宏观尺度能合理地认识国土空间的属性[20],承载功能的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和景观结构等地理实体则是其微观尺度的体现,且功能与承载实体间并非严格对应。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诠释了土地系统内部功能的复杂关系,乡村景观多样性的形成过程则反映了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的组织关系及其结构的映射[21]。“三生空间”基于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按其主导功能属性划分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三种类型,在不同尺度的区域空间下,“三生空间”功能随时空演变具有复合且动态的特征[22]。乡村景观结构的复杂性记录着不同历史阶段政策实施、社会经济实践、文化塑造等众多活动轨迹,是乡村地域时空演变下可体验、可感知的物质空间和非物质历史文化积淀。
乡村景观的时空演变动态嵌入在乡村发展的空间实践过程,并与乡村土地利用类型转化规律、“三生空间”功能转换共同构成相互作用的动态反馈机制(图1)。在农耕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变过程中,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和现代化等大环境对乡村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城乡区域社会经济形态、乡村内部环境的变化驱动着乡村土地利用方式和乡村“三生空间”功能发生动态转换,乡村景观内涵不断扩充,以改造和适应自然、传统农业耕作、民俗民风承载为主要功能特征的乡村景观不断演变,人对自然的干扰程度减小,乡村景观自然和半自然的属性逐渐削弱[16]。景观功能的演变重构着乡村地域多元要素的兼容整合方式,并直观呈现为多样化的乡村景观结构形式。与此同时,乡村景观多功能性维系于乡村地域人地共同体的环境伦理之中,景观变迁在反映系统内部景观结构、要素重组的同时,伴随着其他部分功能的转变,引发地域空间重构和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进而促使乡村社会经济整体环境发生转变[23]。

图1 “三生”功能与乡村景观演变的关系Fig.1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fun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rural landscape
2 研究区域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顺德杏坛镇传统岭南水乡片区“北七乡”是指位于杏坛镇北部由逢简村、桑麻村、龙潭村、北水村、吉祐村、南朗村和古朗村七个乡村组成的乡村聚落综合体,总面积约30.49 km2,区域范围内历史人文资源丰厚,拥有连片质量较高且保存较好的桑基鱼塘农业生态景观资源。在漫长的农业文明和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形塑下,“北七乡”形成具有显著地域性的乡村自然生态风貌、与自然及社会环境相适应的乡村生产体系以及蕴含丰富地域人文特征的乡村生活场景,是重塑岭南水乡特色空间和社会载体的重要区域(图2)。

图2 研究范围示意Fig.2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search area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包括:1)时间跨度为30年(1988、1993、1998、2003、2008、2013、2018年)共7组Landsat TM、ETM/OLI遥感影像和Google地图高清影像数据;2)问卷调查、部门和村民访谈等数据材料。
2.3 研究方法
2.3.1 乡村土地利用类型划分
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北七乡”遥感影像进行处理和分析[24],参照广东省自然资源厅2019年5月颁布的《广东省村庄规划基本技术指南(试行)》,结合当地土地利用的实际情况,将“北七乡”土地利用类型主要划分为村庄建设用地、对外交通用地、工业用地、坑塘水面、草地和水域六大类,获得1988—2018年间7组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分类图。
2.3.2 乡村土地利用演变模型
1)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用于研究土地利用状态及各类土地利用类型状态相互转移,能较好地刻画特定时空下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间的演变方向及土地利用特征[25]。
(1)
式中:S为土地利用面积;n为土地转移前后土地利用类型数目;i、j分别为特定研究时段内初期和末期的土地利用类型;Sij为研究期初i土地利用类型向研究期末j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的面积。
2)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关注特定研究时段内土地利用各类型的面积变化结果,反映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幅度和速度,有利于探寻土地利用演变规律及其后的驱动因素[26]。
(2)
式中:KT为研究时段内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率;T为研究时段;Ua、Ub分别为研究期初和研究期末该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3 乡村景观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结合“北七乡”用地时空演变形成的功能空间结构,基于“三生”功能空间分类(图3),按照功能空间主导属性获得1988—2018年间“北七乡”不同发展时期的“三生”功能空间与景观的时空演变关系,其中乡村生态景观指区域范围内顺德支流与甘竹溪为主的江河水域景观;乡村生活景观主要是以乡村聚落为载体形成的传统聚落景观、民俗文化景观;乡村生产景观主要指面积广阔的生态基塘景观,以及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推进下区域范围内逐渐蔓延的镇办或村办工业景观。

生活空间;农业生产空间;工业生产空间;生态空间;对外交通道路;行政村边界。图3 “北七乡”1988—2018年“三生”功能空间分类Fig.3 Space classification of the North Seven Rural Area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function from 1988 to 2018
3.1 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分析
在改革开放初期“顺德模式”快速推动了乡镇工业的大量兴起,城市蔓延与工业化快速发展是驱动顺德乡村土地利用模式改变的主要原因。从土地利用总体变化特征结果显示,在1988—2018年间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根据土地转移面积及其区域占比,可将研究时间段分为缓慢变化期(1988—2003年)、急剧变化期(2003—2013年)和平缓变化期(2013—2018年)(图4)。2003—2008年、2008—2013年为土地转移变化量较大的两个时期,其中2003—2008年间土地转移量为521.79 hm2,区域总面积占比为16.75%,2008—2013年间土地转移量为454.50 hm2,区域总面积占比为14.43%。根据两个时期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特征分析可知(表1、表2),研究期间工业用地变化量最大,2003—2008年间土地转入量达到187.10 hm2,坑塘水面为主要的转出土地利用类型,两个时期土地转出量均超过250.00 hm2。结合“北七乡”土地利用转移变化和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变化趋势可知(表3),城镇空间扩张及乡镇工业的快速发展促使乡村农业用地与生态空间不断减少,乡村聚落通过空间整合与调整,为广大乡村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用地条件,并伴随乡镇工业的兴办,以道路为主的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快速兴建,进一步加速了乡村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其中在2003—2008年间工业用地的变化率最高达到326.53%,而对外交通道路用地时段变化率则在2008—2013年间达到最大值为250.24%,由此逐渐形成工业片区沿主要交通干线集聚分布的空间格局。近年来,城镇蔓延的趋势得到减缓,乡村土地利用更注重人与自然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方式。

土地转移总面积; — 土地转移量区域占比。图4 “北七乡”1988—2018年土地转移变化Fig.4 Changes in land transition from 1988 to 2018 of the North Seven Rural Area

表1 “北七乡”2003—2008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Table 1 Land-use transition matrix of the North Seven Rural Area from 2003 to 2008 hm2

表2 “北七乡”2008—2013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Table 2 Land-use transition matrix of the North Seven Rural Area from 2008 to 2013 hm2

表3 “北七乡”1988—2018年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Table 3 Dynamic degrees of land use types of the North Seven Rural Area from 1988 to 2018 %
3.2 乡村“三生”景观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基于景观结构与功能原理,景观是区域尺度上的空间单元,斑块、廊道和基质作为土地镶嵌体共同组成景观结构,是景观功能流的决定因素,在时空变化下景观功能流也影响着景观形态、格局与结构的演进[27]。“北七乡”较好、较完整地保留了传统岭南水乡的整体空间格局。自农耕文明时期开始,农业耕作功能主导着“北七乡”区域尺度空间单元景观要素的组成,形成以“乡村聚落斑块—江河水道通廊—基塘基质”为特征的岭南水乡传统地域景观结构,相对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土地利用方式,从而维持乡村三生空间的平稳转化和乡村景观结构的自然演进,形成自由延展的河道生态景观,依水聚居的团状式、线状式、梳状式和环状式生活景观和自然有机的农业生产景观。伴随后工业文明转型期的到来,以机械化大生产为标志的生产方式转变快速改变了传统乡村土地利用方式,工业所带来的财政收入远大于相同时期的农业生产水平,在倡导工业优先发展等政策扶持下,乡镇工业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聚落扩张和工业空间蔓延深刻改变了乡村地域景观的结构形式。外部生态驳岸景观出现破碎化迹象,内部河道景观形态因机械化、规模化生产以及道路等市政基础设施的兴建而变得更加规整和统一,工业生产景观也从粗放式的散乱布局逐步发展为集聚集约式的工业园,但基塘空间的整体性仍较好得以维持,区域景观功能流的变化促使“乡村聚落和工业区斑块-江河水道和道路通廊-基塘基质”混杂式城乡景观结构的形成(图5)。

图5 乡村“三生”景观时空演变特征Fig.5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landscape
4 乡村景观时空演变影响机制分析
乡村景观时空演变是多种复合要素共同影响下的动态连续的转变过程,需要结合自然、政策、经济、社会人文等多维因素及其时空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图6)。

图6 乡村景观时空演变影响机制Fig.6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landscape
4.1 自然因素影响机制分析
自然条件是赋予乡村景观地域性与独特性的核心因素,乡村地域生态本底、自然资源要素等在漫长的时空形塑下形成结构稳定的传统“三生”乡村景观。1998年以前“北七乡”乡村景观仍较完整地保留着这种自然造化的痕迹,并由此形成岭南水乡的传统风貌。在气候、地质、水文等独特条件下,勾勒出蜿蜒的河道、星罗棋布的基塘等极具岭南特色的乡村美学图式。河道网络与基塘空间对于乡村聚居形态的发展具有限制作用,而在因地制宜等生态智慧的营建机制下,乡民为满足生产和生活需求也循序渐进地改变着自然条件,绕宗族聚居的团状式、依水而居的线状式和环绕式乡村生活景观由此形成。与此同时,从适应自然到寻求创新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开创性地创造出“桑基鱼塘”的农业循环经济生态模式,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并构筑了独具岭南地域文化内涵的乡村农业生产景观。
4.2 政策因素影响机制分析
权力决策下的政策目标决定着乡村空间实体与价值转化,乡村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态功能的快速变化是“北七乡”乡村景观在政策影响下表征及其内涵的演变过程。在2003—2013年土地利用急剧变化的阶段,“工业立县”战略的强大动力鼓励大办乡镇工业,从而为顺德民营经济的快速转型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一方面在工业化发展政策扶持下顺德快速创造了可观的经济增长,民营企业大量出现也为乡镇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职岗位,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另一方面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为乡村带来许多负面效应,造成乡村资源急剧消耗和环境污染。土地财政作为谋求经济短期内的迅速增长的有效手段促使了低成本的城市扩张,致使近郊乡村土地利用结构快速改变,其脱离地租规律和市场机制的土地供给严重制约了乡村地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了解决农村集体土地利用低效、权属分割与局限性等问题,顺德农村土地利用制度改革不断探索土地利用创新模式,如土地股份合作制推动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的资本化进程,实现了土地用途和功能转换并增加了集体经济效益和村民财富积累[28]。然而“以地生财”、“出租经济”的发展模式缺乏土地经营统一管理,对乡村土地资产的可持续利用、乡村社会潜在矛盾激化等均造成巨大影响,过快出台的多项关于集体土地流转的政策导致乡镇工业在乡村地区粗放式发展,其无序蔓延的态势加剧了农业和生态空间格局的破碎化和功能的退化[29]。除此以外,农业现代化转型发展的政策也深刻改变了乡村农业景观风貌,如1998年“青山碧水蓝天”基田改造工程,以发展集约化、规模化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转型促使了“北七乡”传统基塘景观的转型(图7),虽然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方式的升级对提高效率与粮食增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改变了农业景观自然有机的空间形态、生态环境及其生产作物(图8),引起农业生态系统的水循环、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服务功能一定程度的退化[30]。

a—2003年; b—2018年。图7 “北七乡”基塘整改进度Fig.7 Improvement schedule of dike-pond of the North Seven Rural Area

a—2003年自然有机式; b—2018年现代集约式。图8 基塘景观Fig.8 Dike-pond landscape
4.3 经济因素影响机制分析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主导的经济模式驱动着乡村景观的变迁,“北七乡”经历了从传统农业商贸模式、工业制造业进出口模式到产业转型和联动模式等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外界资本对乡村“三生”景观的形塑体现在产业经济的开拓、转型与联动。传统农业商贸经济模式的繁盛是促使“北七乡”形成广阔的桑基鱼塘农业景观的主要原因,凭借水陆交通区位优势并受益于大面积的农业养殖区域,“北七乡”成为支撑农商贸易发展的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与此同时乡村生活空间中商业集市等活动空间逐渐增多,此阶段产业经济对乡村景观的形塑主要体现为形成与拓展。改革开放后,工业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成为顺德经济增长的主要方面,凭借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与港口贸易的兴盛,乡村产业结构在工业化的驱动下发生改变,从传统耕作到工业制造的产业转型过程中,粗放型产业转型打破了“北七乡”传统乡村农业景观系统结构,工业的无序蔓延与低效扩张也对乡村区域生态景观及生活景观的完整性构成极大的威胁。新型城镇化时期,区域产业的发展模式将逐渐从独立互斥转变为共融互惠,产业转型升级与联动发展成为“北七乡”乡村景观实现传统乡村景观修复与转型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也是统筹乡村生态、生活、生产等多元景观联动发展有益途径,促使“北七乡”乡村景观呈现出从单一景观快速增长到多元景观融合发展的趋势。
4.4 社会人文因素影响机制分析
社会传统民俗和乡村社会资本结构等内容是构成乡村社会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的精髓,其中传统民俗文化的形成根植于乡村地域生态环境特征及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乡村社会资本主要为乡村社会的网络结构和共识理念,是构成乡村地域共同体的核心要素,两者对乡村景观的影响是循序渐进且持久的。长期稳定的传统农耕文明造就了风貌突出的传统岭南水乡文化景观,地方传统民俗与丰富的技艺反映了乡村景观营造中的敬畏自然与人地和谐发展的生态智慧。工业文明的更替对乡村的影响是深层次的,除了乡村物质景观的剧烈重塑以外,反映在社会人文层面的乡村非物质文化景观衰退表现为乡村人口外流、乡村人口结构复杂化、乡村社区依恋程度、社区认同感和地方依赖的减弱等方面,其不稳定性逐渐增强,并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具有独特地域风貌的乡村景观不断被侵蚀而消失。城镇蔓延下偏重物质空间而非地域文化提炼的乡村更新改造引起了“建设性破坏”,其脱离对微观主体“绣花式”人文关怀的空间“宏观叙事”权利博弈,造成了乡村社会空间的治理乱象。Lefebvre指出“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31],面对全球化与时空压缩下城乡区域空间差异化、非均衡发展和非正义“社会—空间”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现象,以“人”为本的社区营造是重构乡村社会资本,促进乡村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同时也是体现人文关怀价值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地域文化景观营造的重要路径[32]。
5 乡村景观转型发展优化策略
结合当前我国城乡转型发展的特点,为实现乡村地区地域风貌的现代化重塑,应根据城市与乡村空间尺度的差异性、乡村资源要素自然与人文复合多样性等显著特征,统筹城乡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基于城乡区域时空全过程、景观全要素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多维性等方面,协同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进程。
5.1 立足城乡区域时空全过程的景观协同发展
在长期区域不平衡、不均衡发展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的极化效应和虹吸作用使乡村资源和劳动力逐渐流失,众多侧重于城乡社会经济效应提高的乡村整治和规划建设忽略了地域特色的独特性、不可复制性以及建设性破坏的不可逆性,加剧了同质化城乡景观风貌的形成。立足于城乡区域一体化的视角,因地制宜地保护与修复具有本土特色的生态环境并营造地域风貌突出与功能协调的乡村生产和生活景观,维系乡村人地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要坚持时空全过程的整体性保护方式,秉承以人为本、古为今用的发展理念,结合时代的特征营造多元化和韧性强的乡村景观风貌,在夯实并均衡配置公共服务和基础服务设施等物质基础的同时,加快开展特色乡村社区营造,推动农业与文化触媒、全民旅游等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美好人居环境建设并实现多产联动的产业振兴,以此提升乡村居民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凝聚乡村社区多元社会资本、调动公众参与的自主治理意识和积极性,在多元主体互惠合作下推动乡村物质环境和精神文化的全面复兴。
5.2 统筹景观过程全要素的整合与再开发方式
乡村景观时空演变是以地域性为前提下景观元素异质性和时空维度在特定生态过程、政治过程、经济过程和社会人文过程等景观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统筹景观单要素结构特征、不同类型要素结构特征和景观全要素结构特征进行特定描述,根据其演变规律对复杂的景观过程进行模拟和预测。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减少城乡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效应。首先应整合宏观层面景观结构与微观层面景观要素,维护乡村景观系统、景观因子和景观内涵意蕴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形成区域连通的城乡生态屏障、城乡人文景观风貌与功能协作的产业体系,在区域整体层面上提高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逐步构筑成为和谐稳定的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另外伴随近年来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应以生态、经济与人文效益兼具的再开发方式为根本,释放景观重塑过程全要素潜在动能和价值,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乡村景观。
5.3 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下的景观理念建构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新时期乡村景观理念建构首先应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出发点,综合利用地域资源禀赋的生态服务价值、循环经济效益和地缘优势,创新式地发展可持续的绿色生态经济,带动绿色、低碳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发展;第二,应坚持环境治理与生态系统保护并行,乡村人居环境孕育着地域性自然生态、社会人文等特色优势,是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保护屏障和动力源,为此乡村景观其内涵也必须相应进行系统性、关联性和时代性的拓展;第三,坚持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为引领,强化政策制度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刚性约束与弹性控制,完善生态修复与保护制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机制,乡村景观其实际则更注重于规划实践的实用性。因此,关注乡村生态网络结构、社会环境结构和经济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按照乡村生态、生活、生产发展实际需求和问题导向实施精准的规划决策,由此促进乡村景观的理念与实践的相互深化过程。
6 结束语
乡村景观的时空演变反映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下乡村人地关系的变化轨迹,是综合自然、政策、经济与社会人文等多维因素共同塑造的人文结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生态智慧的生态本底、生产和生活方式、产业结构及乡村社会资本结构,共同组成彰显地域特色的乡村生态、生产和生活人文风貌。通过对“北七乡”乡村土地利用类型转换与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转换的特征分析,研究区域在1988—2018年间乡村景观时空演变进程经历了从缓慢变化期(1988—2003年)、急剧变化期(2003—2013年)到平缓变化期(2013—2018年)三个阶段。伴随着农业现代化转型发展,围绕“桑基鱼塘”可循环经济生态模式为核心形成的乡村景观结构呈现出从“乡村聚落斑块-江河水道通廊-基塘基质”转变为“乡村聚落和工业区斑块-江河水道和道路通廊-基塘基质”的演变特征。与此同时,文明演替与多元文化因素对乡村人文景观产生了循序渐进且持久的时空形塑,乡村景观也由此承载着更丰厚的历史和时代的内涵。
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推动了乡村生产景观、生活景观和生态景观的优化发展。在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发展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寻求城乡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驱动着乡村地域空间功能的多元演化。在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潮流下,资本下乡、多元主体权利关系重组、城乡空间体系重构等因素深刻的影响着乡村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功能结构与乡村社会网络的建构。乡村景观重塑过程透视着新时期城乡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多元效应。关注乡村景观重塑发展的问题,其实质要义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探索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实施路径。中华文明根植于乡村,乡村景观记录着乡村文明的兴起与演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更替、人居风貌的形成与融汇创新的过程。新时期乡村景观建设应坚持以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为导向,推进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步进行,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人居环境。与此同时应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系统性、完整性及其活化利用方式,加强历史文脉的保护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