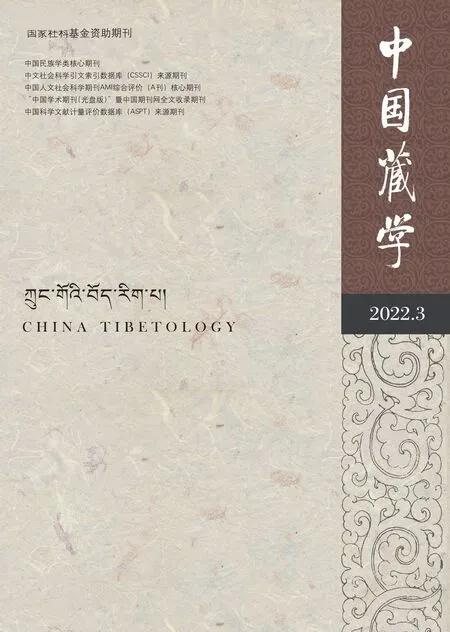大慧法王与明代五台山汉藏佛教交融①
——以碑刻资料为核心
朱丽霞
五台山是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核心区域之一。关于明代五台山藏传佛教传播情况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崔正森《五台山佛教史》的相关章节、赵改萍《简论明代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①赵改萍:《简论明代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西藏研究》2005年第4期。、陈楠《释迦也失在南京、五台山及其与明成祖关系史实考述》②陈楠:《释迦也失在南京、五台山及其与明成祖关系史实考述》,《西藏研究》2004年第3期。等。这些成果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其一,以大宝法王、大慈法王为代表的西藏高层僧侣在五台山的活动;其二,明代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寺庙创建及修复情况;其三,明代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特征。通过五台山的碑刻资料,可以发现明朝在五台山还册封了一位大慧法王,这应是明代五台山藏传佛教乃至整个藏传佛教发展中值得关注的事件,但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除了杜常顺的《明朝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明代藏僧驻京的三大寺院考述——兼论教派色彩与法脉传承》③杜常顺:《明朝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21页;杜常顺:《明代藏僧驻京的三大寺院考述——兼论教派色彩与法脉传承》,《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但杜常顺在《明朝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中认为大慧法王张坚参可能来自河州弘化寺,而在《明代藏僧驻京的三大寺院考述——兼论教派色彩与法脉传承》一文中,进行了修订,认为他有可能是来自燕山以北的汉人。略有提及此人外,其他的论著多未涉及。事实上,以大慧法王为核心,明代五台山还有部分藏传佛教僧人担任了僧录、僧纲等职务。在捐款修寺、建塔的普通僧众中,也能看到藏传佛教僧人的名字。也就是说,以大慧法王为中心,明代五台山存在着一个数量较为庞大的藏传佛教僧团。根据嘉靖三十六年(1557)所立的《皇明五台开山历代传芳万古题名记》碑文记载,这其中地位较尊崇的主要有:制授静觉广智妙修慈应翊国衍教灌顶赞善西天佛子大国师桑节朵而只、钦差提督山西五台山钤制番汉一代寺宇兼住大圆照寺诰封万行通明妙悟大觉宣仁阐教崇禧广智护国衍梵普济大慧法王西天弘慈庄严大吉祥佛朵而只坚参、钦差提督山西五台山兼管番汉一代寺宇兼住演教等寺禅师朵而只乳奴、钦差提督山西五台山兼管番汉一代寺宇僧录司右觉义亦失坚剉、钦差提督山西五台山兼管番汉寺宇诰封清修禅师端竹班丹。④秦建新、赵林恩、路宁、徐翠兰点校:《五台山碑刻》,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17年,第374、377页。这些人中,又以大慧法王朵而只坚参地位最高。
一、大慧法王受册封时间
法王作为朝廷封授给藏传佛教僧人的最高名号,明初都授予了藏传佛教各派的领袖,使他们在藏地“化导弭患”⑤何孝荣:《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23页。。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就是藏地政教领袖,在受册封后,又进一步成为明朝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重要辅助者。但后来随着明朝诸帝对藏传佛教的崇信,留在京城的藏传佛教僧人不断地被册封为法王,这显然与明初统治者的施政初衷有了距离。新册封的法王,有的只是基于统治者自身的宗教信仰需求,甚至只是基于个人的好恶,因为在这些法王中,有些完全没有参与西藏事务的履历。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长期驻留在京城,去藏遥远,也难以在西藏事务中发挥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明宪宗在成化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484—1486)间,突击册封的10位法王⑥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升大慈恩寺西天佛子札失藏卜、札失坚剉、乳奴班丹,大能仁寺西天佛子锁南坚参、结斡领占俱为法王。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升大慈恩寺西天佛子舍剌星吉、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著癿领占、朵而只巴为法王。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升西天佛子卜剌加为法王,追封已故西天佛子端竹领占为法王。,他们中大部分人与西藏地方事务无涉。⑦详见《明宪宗实录》卷248—285,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4195—4828页。但明朝在五台山册封的大慧法王则具有特定的职能——管理五台山的汉藏佛教寺院。
关于大慧法王受册封的情况,依据五台山的碑刻资料,最详细的记载出现在圆照寺的“明成化皇帝圣旨碑”碑文中:奉天承运……皇帝……万物……要者,国家必礼遇褒嘉之。尔朵而只坚参□□□之法性,能融□□□□□□,宣如来之妙旨,眷慈善德,宜有褒崇,今特封为万行通明妙悟大觉宣仁阐教崇僖广智护国衍梵普济大慧法王西天弘慈庄严感应大吉祥佛。于戏!□□□□,□□清净之风,赞我鸿图,茂衍升平之福。允其祗服,用光训词……本峰顶盖造新寺,一□以为本寺院内铁瓦殿……铜佛,文殊菩萨像百尊,僧房六十余间,并石塔、□墙等具云。欲为服……尔□赐寺额曰演教。仍升剌麻僧朵而只乳奴为禅师兼住,亦室……本山番汉僧众人等,特命尔领敕提督管理兼住圆照寺,领□□□□,其□□□之。故谕。①《五台山碑刻》,第211页。

关于朵而只坚参受封为大慧法王的时间有待考辨。其一,虽然上述圣旨碑被《五台山碑刻》定名为“明成化皇帝圣旨碑”,其立碑时间也被整理者认定为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但根据现存拓片,“年九月十四日”之前的内容风化严重,难以辨认。③《五台山碑刻》,第212页。其二,时人谢兰撰《重修圆照寺碑记》④此碑是隆庆三年(1569)重立的,第一次立碑时间不详。提到圆照寺“于嘉靖丁未年欻燃焚之,苟延岁月”⑤《五台山碑刻》,第216页。,于是“自京城坚参师法王张”⑥此处指的就是朵而只坚参。等人参与重建,重建始于嘉靖丁未年,即嘉靖二十六年(1547)。如果朵而只坚参是在1471年被封为法王的,那么到1547年,时间过去将近80年了。即便以他在二十几岁便被封为法王计算,这时他也超过百岁之龄了。一位百岁老人登塔实地勘察、参与寺院重建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朵而只坚参册封时间应该晚于成化七年。实际上,参照明代的其他文史资料,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除了碑铭,在《明实录》《明史》等官方资料中,虽然并没有关于朵而只坚参被封为法王的记载,但《明实录》中有两条关于他的其他记载。第一条是正德四年(1509)八月,他被任命为左觉义:
癸亥,司礼监传旨升大隆善护国寺国师著肖藏卜为法王,剌麻罗竹班卓、班丹端竹、班卓罗竹、朵而只坚参俱为左觉义。
第二条是正德五年(1510)七月,他被升为国师:
令大隆善护国寺国师星吉班丹、禅师班卓罗竹俱升佛子,禅师罗竹班卓、班丹端竹、朵而只坚参升国师。⑦《明武宗实录》卷53,第1203页;《明武宗实录》卷65,第1429页。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朵而只坚参出家于北京大隆善护国寺,后入五台山管理僧众,因此明朝官方将其视为大隆善护国寺僧人。明朝藏传佛教僧人封号递进遵循的是“禅师—国师—佛子—法王”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他被封为法王一定在正德五年之后。而在正德七年(1512)十月所立的修建大隆善寺的“僧众职名”碑中,朵而只坚参的身份是国师(弘慈翊教国师)。①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3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9页。所以,可以将朵而只坚参被封为法王的时间,进一步确定在正德七年十月之后。如果再结合镇澄《清凉山志》所说的“正德间,封张坚参为法王,赐银印,兼有都纲印”②[明]镇澄撰:《清凉山志》,载白化文、张智主编:《中国佛寺志丛刊》第9册,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第69页。,则他被封法王,必定在正德年间。如此,朵而只坚参被封为大慧法王,只能是在正德七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间。
另外,在册封朵而只坚参为大慧法王的圣旨碑③《一 明成化皇帝圣旨碑》,载《五台山碑刻》,第211页。中,还有其他的线索可以佐证这一时间。这份圣旨的后半部分提到了当时新建的、有铁瓦殿的、被赐寺额的演教寺。《清凉山志》中关于演教寺有这样一条记载,即正德七年春季,又“敕梵僧朵而只坚,于中台顶,建寺一区,铸铁为瓦,赐额曰演教,并敕旨护持”④《清凉山志》,第215页。。这里的“朵而只坚”,应当是朵而只坚参漏写了“参”字。演教寺建成后,曾有“敕旨”,这与敕封朵而只坚参的圣旨后半部分内容相符合。演教寺从正德七年春季开始建造,建成时间缺乏记载,但应该是在正德七年十月以后。因为按照前面“僧众职名”碑记载,十月份时,朵而只坚参还是国师身份。但演教寺建成后,他被封为法王,这两件事出现在同一份圣旨里。藉此,顺带可以确定的是册封朵而只坚参为大慧法王的圣旨碑立于正德年间,而不是《五台山碑刻》所说的成化七年。
至于朵而只坚参被封为大慧法王的原因,按照圣旨的内容,是因为他能“宣如来之妙旨,眷慈善德”,也就是基于其佛教修为。但实质上,这一类说法基本上属于明朝圣旨中常见的套话,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正如下文所述,朵而只坚参属于岷州大崇教寺法系,所以他被封为大慧法王可能与此有关。明代,大崇教寺僧人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深受明统治者的倚重与尊崇,先后有多名僧人被封为法王、国师等,其中有史可查的主要有:明代宗景泰三年(1452),封班丹扎释为大智法王;景泰七年(1456),封沙加为大善法王;正统元年(1436),封绰竹藏卜为净觉慈济大国师;正统十年(1445),封班卓藏卜为清心戒行国师;景泰六年(1455)左右,封锁南领占袭为慈济大国师。成化二十二年,封著癿领占为法王,⑤杜常顺:《明朝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第119—120页。再加上国师西天佛子桑节朵而只和朵而只坚参师徒,数量不少。这些僧人大都留京居于大隆善护国寺(朵而只坚参师徒在五台山也多有活动),互相之间不仅具有法缘关系,部分人还具有血缘关系,例如沙加为班丹扎释的弟子,绰竹藏卜、班卓藏卜为班丹扎释的侄子。所以,明代岷州藏传佛教僧人互为援手,在京城和五台山形成了庞大的势力集团。朵而只坚参作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他受封为法王应该与此关系密切。
那么,如何解读五台山正德七年之前的碑刻中出现大慧法王的现象呢?在五台山出现这种现象的碑刻有两通,其中一通是刻于成化年间的圣旨碑;⑥《二 明成化皇帝圣旨碑》,载《五台山碑刻》,第213—215页。另一通是弘治十三年(1500)的“五台山重建殊祥寺记”碑。第一通立于圆照寺中,此碑分为上中下3栏,上中两栏分别刻写了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的两份圣旨,下栏是一份成化八年(1472)的圣旨。这3份碑文都与圆照寺的端竹班丹有关,成化八年的圣旨敕命端竹班丹住持圆照寺;成化十七年的两份都是擢升圆照寺都纲短竹班丹(应为端竹班丹)为清修禅师,并下令军民人等不得侵扰圆照寺的圣旨。在这3份圣旨的正文之后,陈列了5位具有管理身份的僧人,第一位便是“钦差提督山西五台山钤制番汉一带寺宇兼住大圆照寺诰封万行通明妙悟大觉宣仁阐教崇僖广智护国衍梵普济大慧法王西天弘慈庄严感应大吉祥佛”。①《五台山碑刻》,第215页。第二通碑——“五台山重建殊祥寺记”的后面,也列有“钦差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寺宇大慧法王朵而只坚参”。要解读此类碑刻中已经出现大慧法王的现象,就要结合两个方面的现象进行分析。第一个是五台山的明代碑刻具有一个普遍性的特征:在立碑之时,无论当时管理五台山佛教事务的高阶僧人是否真正参与过碑刻中所记的事件,他们的名字都会被列在碑文之后,以示尊崇,并彰显其作为管理者的身份。②例如,弘治元年(1488)所立的《重修旃檀林碑记》,碑末就列出了钦差提督五台山掌管番汉一代寺宇兼住大圆照文殊寺诰封清修禅师端竹班丹、钦差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寺宇僧录司左觉义兼大显通住山沙门旺署庵等管理五台山佛教的僧人(《五台山碑刻》第846页)。就碑文的内容来看,这些人并没有参与旃檀林的修建工作。弘治十七年(1504)所立的《敕赐普济禅寺孤月澄禅师行实塔铭》,主要讲述了孤月净澄禅师的生平,但钦差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僧纲司都纲兼广缘寺主持啰纳忙葛剌、钦差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僧纲司都纲兼大吉祥显通寺主持普显列在碑末(《五台山碑刻》第456页)。这二人虽然与孤月净澄没有关系,但作为五台山僧纲司的都纲,属于当时五台山佛教的管理者,所以就名列碑刻之上了。由此可以肯定这两通碑立于大慧法王在五台山行使管理权期间。第二个现象是明代五台山的少数石碑刻立时间与相应的圣旨颁发时间并不同步,应该是圣旨下达时所立的石碑损坏,后又重新刻立,但并没有改变碑刻的内容。对应到成化年间的圣旨碑,也应当是在朵而只坚参被封为法王后的某个时期,重立了石碑。成化八年和十七年的圣旨被刻在同一通碑上,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圣旨颁布时间和立碑时间非同步性。而在这通碑重立时,作为以圆照寺为活动基地的大慧法王,必然要位列众僧之首。另外,成化年间五台山树立的碑刻很多,只有一通碑文中有大慧法王的名号,如果按照《五台山碑刻》的解读,朵而只坚参在成化七年被封为法王,③《五台山碑刻》在碑文湮灭不清的情况下,将册封大慧法王的圣旨碑树立时间解读为成化七年,很可能是根据三栏圣旨碑中最早的时间——成化八年(这个时间在碑刻上是清晰的)推测出来的。那么,此后的碑刻中应该都列有他的名字,然而其他碑文中都没有,这就反证了朵而只坚参不可能在成化七年就被封为法王。根据五台山的碑刻记载,大慧法王在五台山集中活动的时间是在嘉靖年间(1522—1565),这个问题下文有详论。
另外,在声称立于弘治十三年的第二通碑——“五台山重建殊祥寺记”的阴面,所刻的前几位人物分别为:
钦差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寺宇僧录司左觉义明玄
钦差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寺宇大慧法王朵而只坚参
钦差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寺宇僧纲司都纲明续
敕建圆照寺住持圆□ □□④《五台山碑刻》,第541页。
居于首位的明玄,其被授予僧录司左觉义的时间是在正德十年(1515),这个有专门的敕封圣旨碑①即《皇帝敕谕五台山左觉义明玄碑》,载《五台山碑刻》,第11页。以及立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明代卷案碑”②《五台山碑刻》,第13页。可以佐证。因此,这通碑的正面与背面的事件、人物存续时间之间有明显的出入,即碑阴的人物所拥有相关封号、官职,都是出现于明武宗正德年间。这通碑立碑时间“大明弘治十三年岁次庚申秋八月 日立时”③同上,第541页。位于碑阳,说明其碑阴很可能是在正德或嘉靖时期才添加的,或者被磨平重新雕刻了内容,这种现象在碑刻中也屡有出现,④参见刘友恒、张永波、梁晓丽:《隆兴寺康乾御碑现状与记载不符原因探考》,《文物春秋》2020年第1期。当时为将乾隆四十五年(1780)《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御碑立于寺院显要位置,督造者周元理将立在大悲阁前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两通御碑一碑阳、二碑阴进行了改动。目的是为了凸显当时当权者的地位。具体到上述“五台山重建殊祥寺记”中,就是为了加入明玄、朵而只坚参等当时五台山的管理者。
二、大慧法王的族属及师承
朵而只坚参虽然被封为法王,但他本人并非藏族,而是一位汉人,一位修学藏传佛教的汉人,这点可从明代各类史料对他的称呼中得到印证。镇澄的《清凉山志》中称其为“张坚参”,甚至在提到法王寺时直接说“明张法王建”。⑤《清凉山志》,第70页。五台山的碑刻中也曾称其为“坚参师法王张”。⑥《五台山碑刻》,第216页。将这些材料综合起来看,他是一位张姓汉人,“朵而只坚参”是他跟随藏传佛教僧人学法后所起的法名。
在师承关系上,根据《明故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大国师张公墓塔记》的记载,朵而只坚参与前面《皇明五台开山历代传芳万古题名记》提到的西天佛子大国师桑节朵而只(1445—1512)是师徒关系,桑节朵而只去世后,正德七年朵而只坚参为其立塔。⑦详见杜常顺:《明代藏僧驻京的三大寺院考述——兼论教派色彩与法脉传承》,《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182页。《明故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大国师张公墓塔记》的碑头上刻的是《明故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大国师张桑节墓塔记》,说明朵而只坚参的师父也是一位汉人,因而又被称为张桑节,或者直接按照汉人的称呼习惯称其为“张公”。桑节朵而只虽为汉人,但他作为朝廷的特使去过西藏,并师从藏族僧人学习藏传佛教密法,这些都记载于他的《墓塔记》中:
公姓张氏,讳桑节朵而只,其先世山后人。景泰年未⑧未,疑为“末”——本刊编者。礼清心戒行国师为师。及长,成化庚寅奉敕命差往乌思藏,封阐化王国王,到彼处彰我圣朝及封恩赍之典。当时公之德化番夷,道□殊域,至于乙亥方回京师,蒙赐宴,升国师,封净慈利济。弘治乙酉,彰□请公于天宁寺讲习观法。庚戌隐迹于五台山圆照寺,修习本佛哑曼答葛功课,加持六字真言。逮正德辛未,崇尚秘教,命译写各佛修习讲说秘密成法,上闻大悦,遂宴赏。壬子加升西天佛子,……赐金印一颗,重三百五十两,加封清觉广智妙修慈应翊国衍教灌顶赞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公生于正统乙丑年十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八。
长徒国师卜以是年九月十五日葬公于塔,以谨终也。正德七年冬十月十七日立石。⑨参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3册,第181页;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115页。但二者的碑刻文字,在许多地方有明显出入。
因为朵而只坚参与其师父同为张姓汉人,所以他“很有可能与其师桑节朵儿只兼有法缘和血缘两重关系”①杜常顺:《明代藏僧驻京的三大寺院考述——兼论教派色彩与法脉传承》,《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182页。,也就有可能同样来自“山后”,即燕山以北地区。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曾经“徙山后民万七千户屯北平”②(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页。,朵而只坚参师徒应该就是此次迁到北京的“山后”人后裔。桑节朵而只之师“清心戒行国师”,就是来自岷州的大崇教寺僧人班卓藏卜,其于景泰四年(1453)被封为“灌顶清心戒行国师”③《明英宗实录》卷230,《废帝郕戾王附录》卷48,第5025页。,到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被升为灌顶大国师时,前面冠以“大隆善护国寺”的限定语。④《明宪宗实录》卷159,第2905页。所以,尽管朵而只坚参师徒是汉人,但在法脉上,则出自正宗的藏传佛教法系。桑节朵而只跟随班卓藏卜学法的地方是在大隆善护国寺,而朵而只坚参跟随桑节朵而只修学藏传佛教的时间,既有可能是桑节朵而只隐居圆照寺期间,也有可能是二人皆在大隆善寺期间。因为在《明实录》中,朵而只坚参也被归在大隆善护国寺僧人之中。
至于朵而只坚参具体修学的藏传佛教法门,目前不得而知了,只能根据其师桑节朵而只所修之法反推一二。在桑节朵而只《墓塔记》中提到,他所修的是“本佛哑曼答葛”,即本尊大威德金刚(Yamāntaka,阎魔德迦),为文殊菩萨忿怒相,在五台山修此法门,大约更为相应。除此之外,他还修持六字大明咒。朵而只坚参既然师从桑节朵而只,其所习应该也以这两种法门为主。
三、大慧法王在五台山的活动
在社会活动方面,朵而只坚参不像其师桑节朵而只那样具有被派往西藏的功业,他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促进五台山佛教发展方面。根据五台山碑刻,朵而只坚参被明武宗封为法王后,在五台山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明世宗时期,甚至可以说,他在五台山活动的活跃期主要就在明世宗时期。这一点从他在五台山碑刻中的出现情形便可呈现出来:⑤《五台山碑刻》,第541、465、829、474、428、63、1083、374、217页。

碑刻名称 时间 朵而只坚参名号五台山重建殊祥寺记 1500(?) 钦差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寺宇大慧法王朵而只坚参皇明五台山敕赐普济禅寺太空满禅师重修功德记并系 嘉靖四年(1525) 钦差提督五台山番汉寺宇圆照住山国师朵而只坚参塔苑沟经幢 嘉靖六年(1527) 兼住敕建大圆照寺大慧法王朵而只坚参空禅师灵塔记并铭(碑阴) 嘉靖十六年(1537) 钦差提督五台兼管番汉寺宇弘慈翊教国师兼大圆照寺住山朵而只坚参五台山敕赐普济禅寺开山第三代住持太五台山金刚窟般若寺重开山第一代住持嗣临济二十四世宝山玉公大和尚缘起实行功德碑嘉靖十七年(1538) 钦差提督五台兼管番汉一带寺宇弘慈翊教国师大圆照住山坚参佛真身舍利宝塔碑并铭 嘉靖十七年(1538) 钦差提督五台钤制番汉一带寺宇弘慈翊教国师兼大圆照寺住山坚参诰封西天佛子大慧法王五台山大塔院寺重修阿育王所建释迦文

碑刻名称 时间 朵而只坚参名号五台山紫府庙重修殿廊碑记并铭 嘉靖十九年(1540) 敕建大圆照寺主持坚参皇明五台开山历代传芳万古题名记 嘉靖三十六年(1557)钦差提督山西五台山钤制番汉一代寺宇兼住大圆照寺诰封万行通明妙悟大觉宣仁阐教崇禧广智护国衍梵普济大慧法王西天弘慈庄严大吉祥佛朵而只坚参重修圆照寺碑记(重立) 隆庆三年(1569) 坚参师法王张
可见,朵而只坚参在五台山碑刻中出现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明世宗的嘉靖朝,这也显示出明朝对五台山佛教的管理措施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随着明世宗的崇道而发生改变。至于他在五台山活动的具体起始时间,史料中并没有记载。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他为桑节朵而只立碑时,身份虽然还是国师,但称号前面已经有了“敕提督五台钤制番汉”①《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3册,第181页。的字样,也就是说他在正德七年以前,就在管理五台山的佛教事务。至少在政府层面,明代对五台山的佛教并没有“番汉”的区分。在许多圣旨碑里,皇帝给汉藏管理者的权限中都有“提督五台山”“管理番汉僧寺”的职权,②《皇帝敕谕五台山左觉义定旺碑》,参见《五台山碑刻》,第4页;《塔苑沟经幢》,参见《五台山碑刻》,第829页。而且,这些名号都不是虚称,拥有这些名号的僧人都实实在在地参与了五台山佛教事务的管理。
就朵而只坚参而言,他除了在五台山修成了前面提及的法王寺和演教寺外,还参与了五台山许多寺塔的重修工作,以此来维护和推进五台山佛教事业的发展。据嘉靖十七年所立的《五台山大塔院寺重修阿育王所建释迦文佛真身舍利宝塔碑并铭》记录,朵而只坚参在这次重修舍利塔中亲力亲为,与钦差提督五台兼管番汉一带寺宇僧录司左觉义兼大吉祥显通寺住山明玄、钦差提督五台兼管番汉一带寺宇僧纲司都纲兼大吉祥显通寺住山明续等人登塔查看,设计重修方案。在塔修成之后,“法王、觉义、彻天、天竺四师”又让祖印写了碑铭。③《五台山碑刻》,第62页。另外,在“嘉靖丁未年”(1547),圆照寺遭火灾之后,他偕同五台山的僧俗人众对之进行了重修。④《重修圆照寺碑记》,参见《五台山碑刻》,第216—217页。在这之后,五台山的碑刻中就没有关于他的记录了,直到嘉靖三十六年,他出现在具有总结性的《皇明五台开山历代传芳万古题名记》碑中。所以,朵而只坚参应该在1547—1557年间去世了。
因为大慧法王在五台山的主要活动以修建寺院为主,导致在他之后,五台山的僧人将许多寺院的修建都归功于他,充分说明五台山僧人对大慧法王的认可。在明人李维桢(1547—1626)的《五台游记》中,这种现象跃然纸上:
过罗睺寺,初有西域法王,至今奉香火者,多番僧,去来不常,悉能为汉语。问之,则河州弘化寺僧也,巳。过圆教寺,亦以法王建。有银印,曰清修禅师,后葬山中,巳。过广宗寺,亦以法王建,有铁瓦殿,欲置台上,而难以转运,遂置诸此……巳。过文殊寺,亦以法王建。永乐时,造六臂文殊像,甚奇。有鼓有柄,人皮冒之,径可二尺,亦内赐也。番僧精舍修整佛及供给,多西竺物。⑤[明]李维桢撰:《大泌山房集》卷6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0页。
李维桢所说的“西域”即西藏,明代内地僧俗人士,多有不区分这二者的。《清凉山志》中就将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回到西藏称为“旋西域焉”。①《清凉山志》,第83页。
四、小 结
通过大慧法王的生平事迹,我们可以看出明代五台山汉藏佛教已高度融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汉传佛教僧人和藏传佛教僧人都成为管理五台山佛教事务的主体,从封号上看,甚至藏传佛教僧人的地位要高于汉传佛教僧人。在1557年所立的《皇明五台开山历代传芳万古题名记》碑刻中,五台山被封为国师以及拥有“钦差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一代寺宇”“钦依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一代寺宇”身份的僧人,总共有16人,其中藏传佛教僧人5人,分别是桑节朵而只、朵而只坚参、朵而只乳奴、亦失坚剉、端竹班丹;另外还有来自中天竺等地的“西天僧”4人。而在这些具有管理身份的僧人中,朵而只坚参被封为大慧法王,桑节朵而只被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所以朵而只坚参属于16人中地位最尊崇者。由此可见,明朝虽然是一个以汉人为统治主体的王朝,但在五台山佛教管理与发展方面,则具有很强的跨民族性。
二是从佛法传承上看,汉藏民族的界线已经突破。在朵而只坚参的佛法师承上,他上承汉人桑节朵而只,而桑节朵而只受学于班卓藏卜。班卓藏卜来自岷州大崇教寺,是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侄子,为藏族。所以,到了明代,随着大量西藏僧人留居京城,内地出现了许多汉人、汉僧修学藏传佛教的现象,由之带来的不仅是佛教各传承派系之间的交流与往来,带来高原地方与平原地区之间的交流,更促进了汉藏民族甚至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交融。
三是汉僧的藏传佛教僧人身份得到广泛认可。从政府层面看,修习藏传佛教的汉人被政府封为法王、国师,并且被委以重任;从民间层面看,在朵而只坚参被封为国师、大慧法王后,五台山绝大多数碑刻,无论所记内容为何,无论与朵而只坚参有无关系,都会将其列在碑文后面或者列在碑阴僧众之首,显现出五台山僧众对他的尊崇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