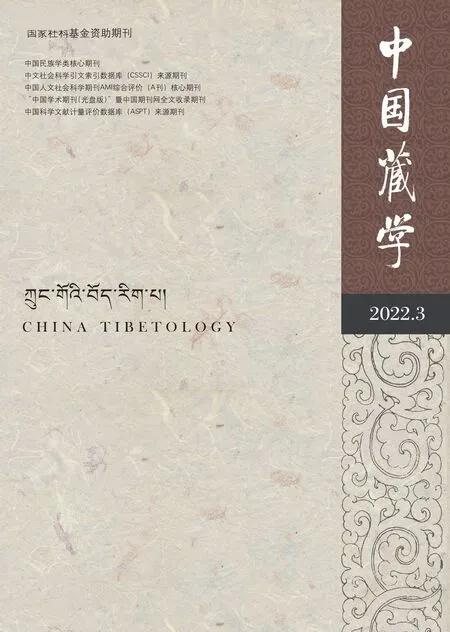新发现的藏东南地方志《喀木西南志略》及其重要价值①
黄辛建
程凤翔撰《喀木西南志略》,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四月,此后一直以抄本存世,至今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朱士嘉先生所编《中国地方志综录》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88年出版的《中国方志大辞典》等方志目录和词典中均未见收录该志,有关西藏方志研究的成果中亦无人提及。20世纪80年代,得到《喀木西南志略》抄本的吴丰培先生将其中部分内容以《喀木西南纪程》为名选辑入《川藏游踪汇编》之中出版。①吴丰培:《川藏游踪汇编·喀木西南纪程》,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441—467页。此后,公开出版的《喀木西南纪程》开始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或将所辑内容选摘入其他资料汇编之中,或对辑选内容进行专门研究,或在开展相关研究时参引辑入《喀木西南纪程》中的资料。②其中,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编写的《近代康藏重大事件史料选编》(下)(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01年)与任乃强、任新建的《清代川边康藏史料辑注》(成都:巴蜀书社,2018年)等系将吴丰培所辑摘入资料汇编之中;赵心愚的《清末藏东南方志类著作〈门空图说〉〈杂瑜地理〉考论》(《民族学刊》2013年第3期)等系对其中部分内容的专门研究;张钦的《〈藏行纪程〉所载滇藏交通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卢梅的《简析1909—1911年清军对藏东南地区的改流设治及其意义》[《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等成果则是利用吴先生所辑《喀木西南纪程》中的资料开展相关研究。然而,由于出版的《喀木西南纪程》仅为《喀木西南志略》中的部分内容,且吴丰培先生在辑录时对篇章结构、篇目名称有所调整,故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虽大都知道辑入《川藏游踪汇编》的《喀木西南纪程》,却少有人知道另有一部《喀木西南志略》存世,抑或虽知《喀木西南志略》之名而未见其书。笔者最近发现了保存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的《喀木西南志略》1959年手抄本一部。在通读全书并将其与《喀木西南纪程》进行仔细比对后,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清代这部专门记载我国藏东南地区的地方志作一专门探讨,并考察其在清代西藏地方志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对于在当前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维护我国主权利益的重要地方志资料价值。
一、程凤翔与《喀木西南志略》的编撰
程凤翔其人,生卒年不详,现有研究多以其为湖南武水(今临武)人。③任乃强:《任乃强藏学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第134页;赵心愚:《清末藏东南方志类著作〈门空图说〉〈杂瑜地理〉考论》,《民族学刊》2013年第3期,第40页。在《喀木西南志略》的自序中,作者落款为:“宣统辛亥清和月山武水梧冈程凤翔序。”④本文所引《喀木西南志略》中的内容,均据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1959年手抄本。清宣统三年为辛亥年,宣统辛亥清和月即宣统三年四月;梧冈程凤翔,即程凤翔,字梧冈。该书稿成后,由程凤翔秘书李介然作序,落款“宣统三年麦秋节雁江李介然拜序于龙川管次”,这里的“宣统三年麦秋节”,也是宣统三年农历四月,与程凤翔自序中所记“宣统辛亥清和月”在时间上是吻合的。“自序”落款中最难解释的是代表籍贯的“山武水”,大多认为此“武水”即湖南武水,这可能是将程凤翔视作湖南武水人的依据。但若如此,“山”又为何意呢?值得注意的是,刘赞廷对于程凤翔的籍贯有着另外一种说法,其在所著《三十年游藏记》中称程凤翔为“山东聊城人”。山东聊城,为古武水之地,隋唐时曾设武水县、武水镇。刘赞廷与程凤翔均为赵尔丰老部下,清末之际在康藏地区共事多年,关系熟稔,交往密切,程对刘有提携照拂之恩,刘称程为“程老友”,故刘赞廷之言当属可信。⑤刘赞廷:《西南野人山归流记》,参见《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2),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第47页。程凤翔为山东人,也可与《喀木西南志略》自序的落款相印证,“山武水”实际上应为“山东武水”,之所以出现“山武水”这一记载很可能是后来辗转传抄过程中将山东的“东”字漏抄所致。①吴丰培先生在辑录《喀木西南纪程》时就认为其“内多芜杂,错文误字极多”,笔者在整理时也发现该志缺字、误字、衍字的情况较为突出。而这一问题的存在,多是因辗转传抄造成的,故后来的传抄者将“山东武水”中的“东”字漏抄是完全可能的。参见吴丰培:《川藏游踪汇编》,第467页。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一日,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随员五十余人在巴塘被杀,造成近代康藏史上著名的“巴塘事变”。事变发生后,清廷令马维骐、赵尔丰率兵进剿。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清廷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经营川边,推行改土归流。②任新建:《凤全与巴塘事变》,《中国藏学》2009年第2期,第10页。程凤翔以武童投军,虽不通文墨,但却甚为机智、豪爽、勇猛善战,在桑披寺、腊翁寺平乱中战功卓越,迅速成为赵尔丰的左膀右臂。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次年秋,程凤翔奉赵尔丰之命进驻藏东南地区,积极安抚当地百姓,实施改土归流,开展划区设县工作,并亲自到压必曲龚,于此处插清朝国旗以示国界,后又带兵前往德格、波密等地平息地方叛乱,战功卓越,官至副将、总兵。刘赞廷对程凤翔评价甚高,赞其为“国防、西康建省战功之一人也”③刘赞廷:《西南野人山归流记》,参见《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2),第47页。。
《喀木西南志略·自序》中,程凤翔称:“凡有见闻,无不笔之于书,以志梗概”,并“就所过之山川、风土、人情、物理,信笔及之”。由此来看,《喀木西南志略》是程凤翔率部进驻左贡、桑昂曲宗、杂瑜(指今察隅地方)期间根据沿途经历见闻及调查资料撰写而成。然而,程凤翔是不通文墨的。刘赞廷曾在著作中非常详细地记载了与程凤翔初识时的情形。二人初次见面的时间是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地点在盐井,程凤翔当时自称“幼年失学,至从军无事,发奋读书,每日由秘书李介然讲《纲鉴》《春秋》或古文一段”④同上,第4页。。从这段文字来看,此时的程凤翔尚需秘书李介然每日讲解经典名著或古文,文字功底应该较弱,当没有能力来完成这样一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考据详细、体例完备且长达两万多字的方志著作。任新建先生在整理、辑注清末康藏地区地方文献时,就对《喀木西南志略》的作者提出质疑,他认为“程不通文墨,是书疑为其幕友李介然代笔”⑤任乃强、任新建:《清代川边康藏史料辑注》(3),巴蜀书社,2018年,第625页。。任先生的怀疑有一定道理,不过以李介然为《喀木西南志略》的作者也存在抵牾之处。
如果我们将《喀木西南志略》的内容与吴丰培先生所辑《赵尔丰川边奏牍》中收录的档案文书资料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一些问题。从程凤翔与赵尔丰的往来公文看,程凤翔部自盐井进驻桑昂曲宗、杂瑜一带的行程如下:宣统元年(1909)十月二十一日自盐井出发,二十九日攻克吞多寺,十二月十九日至工巴村,“二十七日宿俄拉,二十八日宿昌易,二十九日宿色龙,三十日越站宿坝雪换乌拉,耽延半日,初二日始至桑昂。”⑥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218—224页。但《喀木西南志略》的行军纪程与之大不相同,其记为: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八日自盐井“拔队西行”,十八日“至吞多寺宿”,十九日至工巴,二十七日至坡拉,二十八日抵昌易,二十九日“比至色龙”,二月初九日进驻杂瑜。两相对照可以发现,程凤翔禀文中的行程与《喀木西南志略》所记出入较大。首先,两处所记均从盐井出发,但时间并不相同。禀文中的出发时间为宣统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喀木西南志略》所记为十二月初八日,两处记载之间相差47天。其次,禀文中至吞多的时间为十月二十九日,十二月十九日至工巴;《喀木西南志略》所记达到吞多的时间为十二月十八日,次日至工巴。事实是程凤翔部与藏军曾在吞多发生了较为激烈的战斗,程部取胜后确实在吞多驻扎了较长一段时间。最后,两处记载虽均同时从吞多出发,至工巴、俄拉、昌易、色龙等处的时间也是一致的,但抵达桑昂曲宗的时间却不一致,且记载中同一地名的书写方式也不尽相同,如《喀木西南志略》所记坡拉,在程凤翔禀文中则记为俄拉。
程凤翔禀文当无虚假。那么,《喀木西南志略》中所记“行军纪程”当为他人所作。任新建先生在发现《喀木西南纪程》“所记行军纪程与程凤翔前禀不符”后指出,此明显非程所记,并认为该志中的纪程之作者“当为从盐井奉令赶赴军前的李介然,十八日至吞多会合后,一同前进,此后的日程才符合程凤翔禀文”①任乃强、任新建:《清代川边康藏史料辑注》(3),第625页。。如果仔细比对《喀木西南志略》的内容,也会发现一些新情况。例如,该志中的山川、河流及地名的汉文书写方式并不完全一致,试举几例:位于桑昂曲宗至下杂瑜之间的竹洼,该志中存在竹漥这一写法;鸡公,另有鸡贡之称;杂公,有杂贡的写法;对于距腊翁寺不远的中村,又有钟村的写法。此类情况在该志中较多,而这一情况的存在当是由于该志并非一个人撰写所致。
上述情况表明,《喀木西南志略》实际上是一部将多人所撰成果汇辑而形成的地方志著作,并非由某一个人单独撰写完成的。李介然在序中也称:“所辑《喀木西南志略》一书,陈险隘于简端,不同扣槃扪烛,辨关河于眼底,何烦聚米画山?”这一记载也说明《喀木西南志略》实乃一辑成之志。程凤翔作为清末藏东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积极主张和组织实施了《喀木西南志略》的撰写与汇辑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程凤翔明确为《喀木西南志略》的作者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二、《喀木西南志略》的体例、内容及地方志价值
从体例上看,《喀木西南志略》既吸收了清代西藏方志在篇目设置上的一般体例,又根据具体情况设计了一些比较有特点的篇目,体例设置及内容的地域特色十分突出。具体来看,该志开篇除有李介然“序”及程凤翔“自序”外,还手绘地图一幅。此图类似清代方志中常见的舆图、疆域图,整幅图横向绘制、装订、对折,右上角标注名称“喀木西南图略”,观图时需将折面展开,但图中并未注明作者是何人。目前来看,李介然与段鹏瑞二人绘制此图的可能性最大。李介然,字怀仁,四川雁江(今资阳)人,为程凤翔秘书,随程深入藏东南地区,深得程信任和器重。有学者在整理刘赞廷藏稿时发现,李介然曾绘有一幅名为《西南喀木图》的地图。②杨长虹:《〈刘赞廷藏稿〉研究》,《中国藏学》2006年第4期,第42页。虽然我们未能见到李介然所绘《西南喀木图》,但从该图与“喀木西南图略”具有相似的名称、李介然参与并承担了《喀木西南志略》的撰写工作,以及程李二人亲密的关系等因素来判断,《喀木西南志略》中的“喀木西南图略”有可能与李介然所绘《西南喀木图》是同一幅图。另外,段鹏瑞也可能是“喀木西南图略”的绘制者。宣统二年(1910),在盐井任调查委员的段鹏瑞奉命由盐井前往藏东南地区调查勘测,并在程凤翔的支持下绘制了这一地区的地图。在此次实地调查勘测中,段鹏瑞所访地区纵横数千里,绘制了《闷空全境舆图》《杂瑜全境舆图》和《桑昂曲宗大江西面舆图》等地图,《喀木西南图略》虽未出现在段鹏瑞所绘地图名录中,但其在藏东南的桑昂曲宗、杂瑜一带调查勘测后绘制《喀木西南图略》,并将其交给程凤翔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喀木西南志略》的正文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喀木西南纪程”“喀木西南群说辨异”和“汇志事实”。“喀木西南纪程”为第一部分。从内容上看,这部分实际上是清代西藏地方志中均普遍设置的纪程类篇目,主要记录了作者于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八日自盐井率队西行,至次年二月十四日抵达下杂瑜期间的行军过程及沿途的物产地理、见闻等多方面情况。此部分末另有附记一则,名为“诸路程站”,主要记从杂瑜出发至巴塘、察木多、倮、波密及从桑昂曲宗至波密的程站、里数情况。①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中,该部分名称为“喀木西南志略”,但文字上有人为的划痕。笔者以为,该抄本中之所以出现“喀木西南志略”这一名称,可能是抄录时误将书名《喀木西南志略》写于此,抑或是将“喀木西南纪程”中的“纪程”二字误写为“志略”。值得注意的是,吴丰培先生整理出版的《喀木西南纪程》中该部分的名称为“喀木西南纪程”,吴先生是最早发现并整理《喀木西南志略》抄本的学者,其之所出当有所据,故本文在论述中依据该部分的内容及吴先生选辑出版的《喀木西南纪程》中的名称进行了适当调整。第二部分为“喀木西南群说辨异”。此部分在实地考察和参考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辩驳了旧有文献中有关藏东南一带山川河流记载的模糊不清及错讹之处,厘清了藏东南地区的河流分布及地理状况,是20世纪初期人们对藏东南地区山川分布、河流源流与走向最为详细、准确的资料。第三部分为“汇志事实”,主要记藏东南地区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物产气候、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的情况,其下分“天时类”“地利类”“人事类”“物产类”“风俗类”五目,并有附记一篇,为“杂瑜边外风俗”。《喀木西南志略》稿成后不久,“保路运动”在四川爆发,赵尔丰商调程凤翔一营进省,以增其势。宣统三年九月,傅嵩炑调程凤翔、夏正兴进驻雅州,以备应援。辛亥革命爆发后,边军分崩离析,康藏纠纷迭起。边军在雅安、大相岭一带被保路同志军击败,傅嵩炑被俘,程凤翔则不知所踪。程凤翔在辛亥革命后隐去,后又历任北洋政府总统府侍从武官,大总统曹锟曾派其前往江西烧制瓷器,程凤翔嗜酒,烧制“程瓷”十窑。②刘赞廷:《西南野人山归流记》,载《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2),第42页。
由于世事变迁,《喀木西南志略》一直以抄本存世。目前,仅见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有1959年手抄本一部。吴丰培先生得其抄本后,于1985年将《喀木西南志略》中的“序”“自序”“喀木西南纪程”及其附记“诸路程站”“喀木西南群说辨异”“汇志事实”之下的“地利类”等部分内容选辑入《川藏游踪汇编》中公开出版。因吴先生主要选取的是《喀木西南志略》中的“喀木西南纪程”,故命名为《喀木西南纪程》,这也与《川藏游踪汇编》的出版旨趣契合。从正式出版后的编排布局来看,《喀木西南纪程》的内容首先为《喀木西南志略》中的李介然序与程凤翔自序,然后将该志中的“喀木西南纪程”作为《喀木西南纪程》的主体列于其后。此外,又将“喀木西南纪程”的附记“诸路程站”“喀木西南群说辨异”以及“汇志事实”之下的“地利类” (出版时更名为“杂瑜地理”)等内容作为附录依次列于文后。
实际上,自唐代开始,西藏与内地之间就有十分密切的交往与交流,有关西藏的记载也不断见诸汉文史籍。宋代,乐史在其所著《太平寰宇记》中设置《吐蕃》专门篇目,下分总述、四至、土俗物产、山、海等目,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今西藏地区的多方面情况。从体例、内容上看,《太平寰宇记·吐蕃》已具备我国传统方志的基本特征,属于寄存在《太平寰宇记》中的一部西藏简志,是目前所见西藏方志中的最早之作。①黄辛建:《〈太平寰宇记·吐蕃〉考论——兼谈西藏地方志在宋代的发展》,《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5—20页。清代是西藏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成书数量在20部以上。当中,雍正初年成书的《藏纪概》是目前公认的清代西藏地方志最早之作。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则为目前已知的官方编纂的、最早的清代西藏方志。许光世等纂、宣统三年八月刊印的《西藏新志》则是清代成书最晚的西藏地方志。②赵心愚:《清代西藏方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5页;肖幼林、黄辛建、彭升红:《我国首批西藏方志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第112—117页。《喀木西南志略》于宣统三年四月成书,在清代西藏方志中仅较《西藏新志》刊印的时间稍早一些。
从类型上看,清代西藏方志主要为通志,李梦皋撰、道光二十五年(1845)成书的《拉萨厅志》一直被认为是清代西藏方志中唯一一部府县志。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拉萨厅志》的内容、版本的仔细比对,并结合清代从未在拉萨设厅这一历史事实,质疑该书的真实性,也有学者根据其中所记程站认为《拉萨厅志》“实为伪作”。③赵心愚:《道光〈拉萨厅志·杂记〉的有关问题及作伪证据》,《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94—99页;房建昌:《伪造的吴丰培先生所藏〈道光拉萨厅志〉手抄本》,《西藏研究》2010年第6期,第90页。在西藏府县志如此缺乏的情况下,还有学者认为应该将段鹏瑞著、成书于宣统二年的《门空图说》,吴丰培先生所辑《喀木西南纪程》中的“杂瑜地理”等两部“初具地方志性质”,且均为记录藏东南地区的重要著作列入清代西藏方志目录之中。④赵心愚:《清末藏东南方志类著作〈门空图说〉〈杂瑜地理〉考论》,《民族学刊》2013年第3期,第41页。
如此一来,本文讨论的《喀木西南志略》在清代西藏地方志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从名称、体例及成书内容上看,《喀木西南志略》完全具备我国地方志的基本特征,属府县志这一方志类型。《喀木西南志略》中的“喀木”一词,是康区的另一种译法,在清代出现和使用频率较高;“喀木西南”则指位于藏东南的左贡、桑昂曲宗及杂瑜等地,即今西藏自治区的察隅县、左贡县一带。在西藏方志中,最早出现有关藏东南地区记载的是乾隆初年成书的《西藏志考》。该志是清代西藏地方志中成书较早的通志类方志著作之一⑤赵心愚:《略论乾隆〈西藏志考·历代事实〉的价值及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90页。,其中载:“(康熙五十八年)七月复差成都府同知马世烆、四川后营游击黄喜林招安乍丫、察哇、作工、奔达、桑阿却宗、察木多等处”,又记“五日至杂义”。⑥《西藏志考》(影印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这里的作工,即左贡;桑阿却宗,即桑昂曲宗;杂义,即杂瑜。此后成书的《西藏志》《卫藏图识》等清代西藏方志中,也有大体一致的零星记载。雍正三年(1725),清廷以“仅卫藏赋税,不敷尔喇嘛之费用”为由,将“坐尔刚、桑噶吹宗、衮卓等部族”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365—366页。划归西藏由达赖喇嘛管理。⑧黄辛建:《雍正时期行政划界研究》,《中国藏学》2018年第3期,第95页;赵心愚:《清代川、滇、藏行政分界的档案文献及史料价值》,《民族学刊》2020年第2期,第2—3页。这里的“坐尔刚”即左贡,“桑噶吹宗”即桑昂曲宗。自清廷将桑昂曲宗等地划归西藏管辖后,西藏地方随即在左贡、桑昂曲宗、杂瑜一带派设营官、协敖、古噪等进行管理和收税。如若《拉萨厅志》确为伪作,那么新发现的《喀木西南志略》不仅是清代西藏方志中唯一一部府县志,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藏东南地区的方志著作,甚至是清代唯一一部专门记载西藏边境地区的方志著作,是清代西藏方志中的重要成果。
三、《喀木西南志略》的资料来源与史料价值
从资料来源看,史籍和地方志是《喀木西南志略》的重要参考。翻阅该志可以发现,该志的撰写参考和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又以“喀木西南群说辨异”最为突出。“喀木西南群说辨异”虽仅近7000字,但参考和使用的文献达到20种以上,诸如《禹贡》《经书辨疑录》《黑水辨》《新唐书·吐蕃传》《元史》《五代史·吐蕃》《云南志》《大明一统志》《卫藏图识》《大清一统志》《西藏志》《西域闻见录》《海国图志》《云南通志》《西藏图考》《西輶日记》《西徼水道》,以及唐蕃会盟碑等史籍、地理书、方志、纪程日记、碑刻资料,均在“喀木西南群说辨异”中多次出现,有的段落甚至是在直接引用大量原文的基础上适当阐述自己的观点。此外,在该志的其他部分,也或多或少参考和采撷了其他的文献资料。如“汇志事实”中的“地利类”一目,在述及冈底斯山时就引用了《大清一统志》中的相关记载;在“人事类”一目记丧葬之法时,作者又使用了王我师著《藏炉述异记》中的材料。
作者的沿途经历、见闻和调查访谈资料,是《喀木西南志略》最主要的资料来源。浏览该志,此类材料主要有以下两类:一是通过亲身经历、见闻所获得的材料。如该志中的“喀木西南图略”,若无亲身经历和大量调查,是无法绘制出如此详尽、准确的地图的;“喀木西南纪程”所记自盐井出发,途经左贡,至桑昂曲宗、杂瑜路途中及驻扎期间的经历和见闻,以及“汇志事实”中有关藏东南地区自然社会与山川地理等各方面情况的记载,均属于此类情况。吴丰培先生在《喀木西南纪程》“跋”中就指出:“西南珞瑜一带,处藏地之边区,故记西藏舆地者,昔鲜论及。迨清光绪末季,川边大臣赵尔丰锐意经营西康,颇多建树,乃派管带程凤翔进驻此地。凤翔此作,即记当时行程,对于道里崎岖,地势险峻,均属身历之谈,固多可据。”二是专门的调查、采访资料。如“喀木西南群说辨异”就属此类。这部分内容被吴丰培先生辑入《喀木西南纪程》之中,吴先生在介绍该部分内容时称:“其《群说辨异》中,对于黄茂及黄沛翘所记该地形势,讥其方位不当、考述多误,因该二人均未身履其地,固不如此书目击之谈为可信。”①吴丰培:《川藏游踪汇编》,第467页。
可以看到,《喀木西南志略》的资料主要来自上述两个方面,其中又以亲历、见闻和调查访谈资料为主。程凤翔在自序中就称:“凡有见闻,无不笔之于书,以志梗概,……谨就所过之山川、风土、人情、物理,信笔及之”;在“汇志事实”中的“地利类”目中则言:“据其所闻所见而增补之,以备作者之采择焉。”也正因如此,《喀木西南志略》直到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与资料价值。
首先,关于此志中之舆图,吴丰培先生在整理、介绍该书时没有提及其中的“喀木西南图略”,后来的研究者皆以吴先生辑《喀木西南纪程》为依据,故大多不知道该图的存在。整体上看,该图不仅将藏东南地区的山川、城镇、村庄、河流、渡口一一标出,也对当地寺庙、四至界线及民族分布等情况有着明确的标识,较为直观地反映了《喀木西南志略》中不少文字记载的内容,甚至反映了一些用文字难以清楚表达的内容,既更清楚地反映当地多方面情况,又与文字记载互为补充。若我们将该图与段鹏瑞所绘《闷空全境舆图》《杂瑜全境舆图》和《桑昂曲宗大江西面舆图》等图对照,则可以对20世纪初藏东南地区历史地理情况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了解。因此,“喀木西南图略”的存在,使《喀木西南志略》更具资料价值。
其次,该志中对藏东南地区的山川地理、村落人口、寺院分布、民族宗教、风俗习惯、道路里程等多方面情况均有介绍。程凤翔在该志序言中称:“名公巨卿来西藏者,罔不各手一编,以志熙朝之盛”,然“独于喀木西南、怒江以外,悉以为野人而遗之,实为掌故之阙典”。在“汇志事实”之“地利类”中,亦写道:“藏卫记地诸书,惟评于前后藏及诸路之冲,而僻再一偏者,恒苦于繁不及备而遗之。喀木西南则偏之又偏者也。……左贡、桑昂曲宗所属之地,纵横千有余里,阙而弗及。”李介然在为《喀木西南志略》所作序中也有类似的一段话:“惟怒江以外,龙川之间,志乘阙如,等于瓯脱,幅员广莫〔漠〕,未载宝书。固为筹边所向隅,抑亦掌故之缺陷。”从这些记载来看,程凤翔等人注意到了清代西藏方志数量虽多但主要在卫藏,而今察隅县一带记载阙如,编撰《喀木西南志略》正是为了填补已有文献资料中对藏东南地区记载阙如这一遗憾,以之作为施政之参考及供他人之采择的目的。应该说,成书后的《喀木西南志略》达到了编撰的目的,无疑是了解20世纪初藏东南地区地理、社会与历史情况非常珍贵的地方志资料。
最后,《喀木西南志略》记载了程凤翔部在杂瑜地区“插立国旗,以阻英人前进”①吴丰培:《吴丰培边事题跋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清末英军在我国西藏边境地区的侵略行径,是我国在这一带行使管辖权和享有主权地位的有力历史依据。其中,该志的“喀木西南纪程”中记载了程凤翔部树清朝国旗的具体位置和“竖龙旗于溪上,以示国界”的历史事实;在附记“杂瑜边外风俗”中,对英军入侵的时间、经过、行为及影响均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饱含着作者对清末我国在西藏边境地区所面临的边疆危机的忧虑。如该志在记英军入侵阿子纳的情况时称:“先世本崇佛教,工藏文,常□佛经,输贡入藏。乾嘉以后,西人入境,改奉洋教,习洋文,正朔亦用西历,佛教浸灭,至今交涉,已无人能识藏文矣。”若将《喀木西南志略》中的记载与《赵尔丰川边奏牍》《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及刘赞廷藏稿等著作中收录的资料相对照,则可进一步丰富历史上我国政府在藏东南地区防御外敌侵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有关文献资料。
四、结 语
宣统年间,程凤翔部奉赵尔丰之命进驻藏东南地区并将这一带纳入清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之下,继而在当地发展经济,“划区分司”,将“桑昂曲宗改为科麦县、杂瑜改为察隅县、妥坝改为归化州、原梯龚拉改为原梯县、木牛甲卜改为木牛县丞”②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35—836页。。这些举措对于加强中央政府在藏东南地区的基层治理、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防御外敌侵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奠定了我国在藏东南地区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①秦和平:《20世纪初清政府对西藏察隅等地查勘及建制简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第41页。《喀木西南志略》正是程凤翔部进驻藏东南、藏南地区期间撰写完成的,属清代西藏方志中极为罕见的府县志类型,在我国西藏方志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不仅如此,《喀木西南志略》的撰写还参考了大量史志资料,使用了丰富的沿途经历、见闻和调查访谈材料,是了解20世纪初藏东南地区自然、社会与历史各方面情况非常重要的地方志资源。
近年来,印度屡屡在中印边界争议地区制造挑衅行动,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破坏边境地区和平稳定。针对印方在边界争议地区挑战我主权的行为,我方除了在军事、外交层面予以回应外,还应追根溯源、深入挖掘我国对这些地区拥有主权并行使有效管辖的最早历史记载,为维护我国的主权利益提供扎实的历史资料依据。这部新发现的地方志为目前所知最早的藏东南地区方志,也是清代唯一一部专门记载西藏边境地区的方志著作,其中有关记载是我国在西藏边境地区实施有效管辖和拥有绝对主权地位的有力证据。非常可贵的是,《喀木西南志略》还揭露了清末英军在这一带的侵略行径以及我国政府维护领土完整、防止英军入侵的历史事实。
继清之后,西藏地方志在民国时期继续发展。但与清代有所不同的是,民国时期西藏方志中府县志的数量要明显多于通志,其中还出现了刘赞廷一人编纂17部县志的情况。②刘赞廷所纂17部西藏方志为:《昌都县图志》《波密县图志》《太昭县图志》《冬九县图志》《嘉黎县图志》《贡县图志》《武城县图志》《察隅县图志》《科麦县图志》《同普县图志》《察雅县图志》《盐井县图志》《九族县图志》《恩达县图志》《定青县图志》《硕督县图志》《宁静县图志》。从所及区域来看,刘赞廷所纂17部西藏县志与清末改土归流在西藏东部地区所设县的名称、区域是相对应的,其中《察隅县图志》《科麦县图志》分别对应的正是程凤翔进驻期间在藏东南地区设置的察隅县和科麦县。从资料来源上看,刘赞廷所纂17部西藏县志参考和使用了大量清末川滇边务大臣时期康藏边务的档案和文书资料,其中包括程凤翔与赵尔丰之间往来的大量公函。可以说,程凤翔、刘赞廷等人所纂这批西藏县志,在西藏地方志发展史上是一脉相承、独具特色的一个整体,其编纂明显受到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及在康藏地区开展行政区划设置的影响,所载资料正是历史上我国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拥有主权并行使有效管辖的地方志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