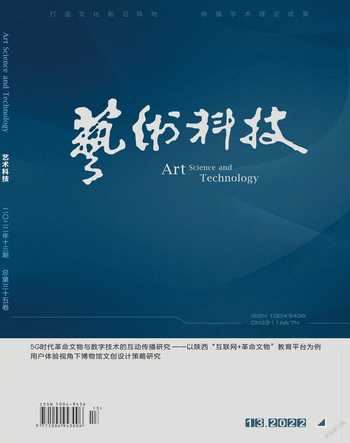古籍点校成果的法律保护研究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通信愈发便捷,古籍点校成果面临侵权的问题也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作为古籍原文的“注释”,古籍点校如果蕴含点校者独创性的表达,一般都可以作为演绎作品保护,但对单纯的点校而言,点校成果因为无法受到著作权的保护而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古籍点校者的智力劳动是否应当受到著作权保护,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无法定为“作品”的点校成果,可以设立特殊的邻接权保护制度。
关键词:古籍点校;独创性;演绎作品;邻接权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13-0-03
1 问题的提出
关于古籍点校成果侵权的经典案例当属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诉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侵害其对《镜花缘》校注版一书的专有出版权一案。案件的关键点在于,对于这本清代小说家李汝珍撰写的长篇小说《镜花缘》,经张友鹤标点和校注后,是否属于独创性表达。1955年,张友鹤校注的《镜花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7年张友鹤去世后,其后人又将该书的专有出版权授予该出版社。但201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和张友鹤校注版别无二致的《镜花缘》,其中注释几乎没有差别。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诉求法院,要求对方道歉并给予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古籍点校者对古籍所做的标点分段注释等是集自己的智力成果为一体而形成的区别于“原本”的独创性表达。正如张友鹤校注的《镜花缘》,应当视为演绎作品而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胜诉,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应当停止出版发行此书,并赔偿胜诉方经济损失300万元。
优秀傳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新时期创新与改革的源泉,而古籍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要传承古籍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古籍点校是一项基础工作。
古籍点校是对古籍进行编辑加工,或分段或加标点或补充或删减或修改,前提是结合客观的历史事实,加之综合点校者的历史文化水平、价值判断等因素而开展的一项古籍整理工作。“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不仅古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对这些古籍的点校,也需要耗费点校者很大的精力,花费自己的心血注释而成。然而,对古籍点校成果的保护存在争议,古籍点校成果频频出现被侵权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点校成果真的无法纳入著作权法的法律保护羽翼之下吗?
2 古籍点校成果能否被认定为作品
2.1 案例对比
上述《镜花缘》一案,法官对张友鹤的智力成果给予了肯定的判决,认为其最后著作的新版本具有独创性,能构成演绎作品,这无疑给了许多古籍点校者信心和鼓励。其实在此之前的许多案例中,针对同一个焦点问题,不同的法官作出了不同的判决。
中华书局诉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点校本“二十四史”与《清史稿》等电子产品侵权案,终审认为应当将点校智力成果视为作品。这个古籍点校“世纪第一案”中法官指出,古籍点校工作专业性较强,并非非专业的普通人可以完成,这需要长久以来的文化积累和扎实的文学功底。若只是将点校行为视作一种“机械行为”,相信所谓的点校版本会无人问津。国学时代公司电子产品中“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内容与受著作权保护的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内容差异很小,构成实质性近似,所以侵权。该案虽历经两审,但各审法官的观点基本一致,即充分认可点校成果的可版权性。独创性体现在从事古籍整理的工作人员所具备的成熟的业务技能以及丰富的文史知识储备,简言之,古籍点校成果是点校人基于自身的国学素养对古籍底本独立作出的现代化诠释,符合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定义和认定标准,应当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中。由此,法院将“二十五史”定义为“经整理产生的作品”,虽然并未就“二十五史”的作品属性作进一步认定,但法院基于此判决明确了保护的态度。
周锡山诉江苏凤凰出版社有限公司等侵害作品复制权、发行权纠纷一案中,一审和二审判决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判决指出:当点校成果目的在于复原古籍原意、点校者仅是按照语法规则揭示了客观事实时,点校成果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古籍点校有个明显的特殊之处,就是古籍点校在先者和在后者,因为古籍文献的有限和历史的客观现实,后面的点校存在与之前相似的表达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如果以此为依据认定其不具有独创性,未免牵强。换言之,不能因为一项成果的来之不易和千头万绪,进而撬动我国著作权法的理论根基,任何方式的法律保护都应当回归至理性,著作权法保护更是如此。
然而,该案在再审中发生了反转,再审法官认为点校为古籍原文带来了不同的阅读感受,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符合作品的特征,受著作权法保护。基于以上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古籍点校成果纳入著作权法保护受到更多司法界人士的支持。所以纵观司法实践,不同法官给出的裁判理由主要围绕古籍点校成果能否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归根结底还是看其是否能被认定为作品。如果能,作品的认定标准又如何在“古籍点校成果”上形成逻辑自洽?如果不能,又该如何保护点校者的成果呢?
2.2 学术争议
基于上述三个案例可以看出,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古籍点校成果是否形成新的作品存在不同的观点。
肯定者认为,古籍点校可以形成新的作品,因为古籍点校凝结了点校者的智慧与汗水,是以其广博的历史文献知识和大量的研究探讨为基础的高难度工作,点校者创作的点校读本,是全新的演绎作品。支持者认为也可以在著作权法中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著作权法第12条明确指出,“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同时,也有支持者指出,古籍点校工作需要点校者有深厚的文化积累和个性化理解,并且将这种理解融入古籍点校中。比如在进行标点和给段落分段的时候,学者就会根据自己过往的经历以及文献的阅读习惯,作出不同的选择,这也是因为某些古籍虽然标点断句不同,但都能自然通顺,更何况部分古籍保存得不完整,对那段历史的多样化解释也会导致最终的注释不同。因而,不能因为部分内容相似,就不认可古籍点校者的智力成果。这样既会导致古籍点校者心有余而“力”不足,也不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1]。
否定者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这种针对古籍文献本身的注释行为,只是一次技术处理,不能被视为作品,也自然不能受著作权法保护。在这些观点持有者看来,古籍点校是基于原作的,为了还原古籍内容的原貌,追求客观事实本身,而不是把自己的创作技巧、方法、风格等融入进去,形成新的作品。同时,在认定“作品”的范围内,有许多客体,只存在唯一表达形式,若是用著作权保护这类客体,就会妨碍科学与文化的发展,比如美国将这类作品称为“事实作品”,德国将其定义为“自然科学作品”[2]。因为在古籍原文的基础上,对其加标点、分段、补充或删改内容,都有一定的规范性、习惯性和历史渊源性,后人开展同样的校对工作,不可避免地具有极大的近似性。若是认定点校成果为新作品,不利于后人再次进行古籍整理,让人望而却步,又何谈对古籍内容真伪的追求,更不要说传承正确的经典著作了。
笔者认为,古籍点校成果是否构成演绎作品不能一概而论,对其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更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著作权法关于著作权作品的规定,作品的认定标准包括智力成果和独创性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是对“智力成果”的解读。一方面,“智力成果”在这里的表述,笔者认为有待商榷,思想亦是一种智力成果,公式也是一种智力成果[3]。所以此处不适合用“智力成果”作为“作品”的法定标准,将“作品”限定为“智力表达”更为恰当。古籍点校成果凝聚了点校者的智力创造,在充分发挥其所学的基础上,用能够为外界客观感知的外在表达表现出来,理应属于“智力表达”。
其次是对“独创性”的解读。独创性又可以分解为“独立完成”和“创造性”。“独立完成”即非抄袭、非剽窃。但这并不是构成作品的必要条件,仅仅自己动手,还不一定能形成作品,重点在于“创作性”。这就要求作者在创作时,要将具有一定高度、个人特色的表达体现在创作之中。部分古籍内容容易点校,仅需简单的标点和断句即可完成,想要构成独创性比较困难[4],加之点校工作的创作空间极为有限,对古籍内容真伪的证明材料也只会让这份古籍点校成果更加接近事实,“创造性”中的个性和高度就更加难以体现。《著作权法》保护古籍点校成果的最大呼声,是来自对点校者的专业知识和渊博学识的尊重。在《镜花缘》一案中,认定点校成果构成新作品的一大理由也是对点校者积极性的鼓励和对古籍点校行业形象的维护。
可以发现,这种出于还原经典著作目的的古籍点校,表达的内容确实倾向于事实,形式也比较单一。古籍点校同时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一旦有通行版本,就很少有学者或出版社重新对同样的古籍进行点校,因为缺少了新意和含金量。而对于古籍点校成果的独创性认定,不仅不易,且一旦将此种点校成果认定为作品,会使得点校市场趋向衰弱,反而有悖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初衷。
综上所述,这些通行版本的古籍点校成果,因为缺乏独创性,很难被称为作品,更不要说以著作权的名义为其提供法律保护。2002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后,删除了“整理”的定义,缺少了“‘整理’能够产生新作品”这一直接的法律依据。在立法演进的过程中,“整理”的含义从开始的明确可适用已经转变为模糊不可知,加上规范性文件效力的存废不定带来的干扰因素影响,点校行为是否还能被解释为“整理”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由此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扰[5]。纵观司法实践可以发现,不同的法官在主观上对作品的独创性有不同的认识,往往作出的判决也有所不同。
3 古籍点校成果保护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展开思考,市场上大量盗版、剽窃的点校读本该如何处置才能维护点校者的合法权益呢?
第一,完善著作权法司法解释,对古籍整理作出规范解释,在复杂的司法实践与抽象的法律规定之间,让保护点校成果有法可依。但此方法仍然是在特殊情况下,认定古籍点校成果为作品,并没有直面否定者“古籍是基于原作进行的一种客观现实的技术处理”“不利于后人的更新、整理工作”的观点,现在看来颇为勉强。
第二,将点校成果纳入民事权益保护范围,基于古籍点校所投入的资金与人力支持,应当合理保护古籍点校者的权益,让侵权者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给文献工作提供适当的激励。众所周知,古籍点校耗时耗力,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尤其是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更被称为“史上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所以选择此种路径也有弊端,容易增加古籍点校的成本。
第三,对于无法认定为作品的古籍點校成果,可以借鉴德国和意大利的著作权法制度,为古籍点校设立特殊的邻接权保护制度,将点校成果纳入邻接权保护范围内,比如以专有权的形式,将那些明显区别于他人点校的作品纳入合理的法律保护范围内。并且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邻接权的保护制度涉及古籍点校范围,保护期限较短,既能平衡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关系,又能激励广大古籍文化爱好者,积极参与到古籍整理工作中。
4 结语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几千年来,中国丰富的古籍文献资料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生哲理、道德规范是值得永久传承下去的,而古籍点校工作则让这些古籍文献变得更加通俗易懂,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点校者的贡献必须得到重视。保护古籍点校成果,不仅仅是为了那些已经点校过的巨作,更是为了中华文明源源不断的传承。点校行为的目的虽为释读古籍原意,但因古籍点校者知识积累、占有资料和主观认知程度的差异,必然会表现为不同风格、水平的个性化判断。点校者综合完成标点、分段、注释的智力成果整体产生的新版本作品应当根据是否符合独创性标准而得到不同保护,对符合著作权法“作品”标准的点校成果予以著作权法的保护,对于无法定为“作品”的点校成果可以设立特殊的邻接权保护制度,将点校成果纳入邻接权保护范围内,赋予其合理的法律保护。
因而,面对古籍点校成果侵权事件,不能忽视点校者耗时耗力完成的成果面临被侵害的风险,又要在进行文化保护的同时,认识到经济效益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需要双向均衡的论题,笔者认为著作权法第四次修订时,应当将保护古籍点校成果纳入其中,探讨对古籍点校成果更加恰当、长久的保护途径。
参考文献:
[1] 龚浩鸣.古籍点校成果构成演绎作品[J].人民司法,2020(29):90-93.
[2] 张彦民,郑成思.《版权法》探微[J].中国出版,1991(7):52-54.
[3] 何怀文.古籍点校本的法律保护:特设民事权益与著作权之外第三条出路[J].中国出版,2013(13):25-27.
[4] 王雅宇.网络时代如何保护古籍点校成果的著作权:以独创性分析为视角[J].传播与版权,2018(6):198-199.
[5] 刘玲玲.古籍点校成果的法律保护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0.
作者简介:李若(1995—),女,安徽萧县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法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