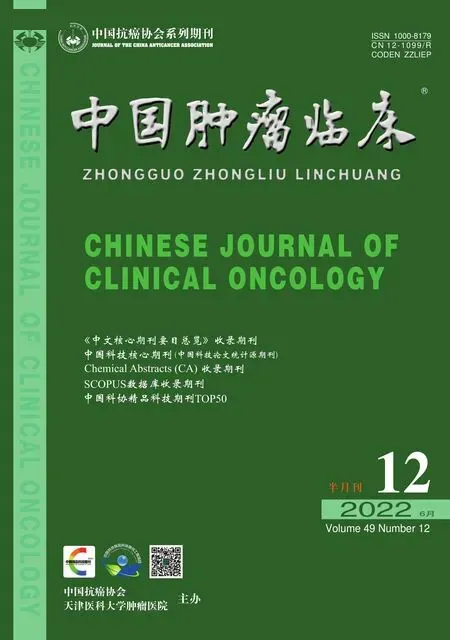炎症小体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肿瘤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张维红 魏枫
肿瘤免疫微环境主要分为3 种不同的免疫表型:免疫炎症型、免疫排斥型和免疫沙漠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免疫炎症型肿瘤与ICIs 的疗效有明确正相关关系[1-2],在肿瘤免疫治疗时代的环境下,通过调节炎症途径来达到增强抗肿瘤免疫疗效的研究日益增加,其中炎症小体及其分泌的相关细胞因子与ICIs 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本综述主要探讨炎症小体与免疫检查点的相互作用,从而寻找两者更好的联合治疗模式来增强ICIs 的疗效,同时降低免疫相关不良反应。
1 炎症小体
机体感受内外源性危险因素刺激后可以通过炎症小体(inflammasome)来清除受损细胞或病原体。炎症小体是在2002 年由Martinon[3]等发现的一种多蛋白复合物,主要由受体蛋白(NOD-like receptor,NLR 或AIM2-like receptor,ALR),接头蛋白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apoptosis- associated speck-like protein containing a CARD domain,ASC)和效应蛋白半胱天冬酶-1(caspase-1)组成,其中接头蛋白和效应蛋白的结构相对稳定,受体蛋白的种类比较复杂,因此炎症小体主要根据受体蛋白的不同来进行分类。炎症小体主要分为经典和非经典两大类,经典的炎症小体需要caspase-1 的参与,包括NLRP1、NLRP3、NLRC4、AIM2 和pyrin 等,是目前研究比较多的一类炎症小体;非经典的炎症小体主要依赖于caspase-4 或caspase-5,目前这方面研究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4]。经典通路通过激活的caspase-1 促进IL-1β 和IL-18 的成熟和分泌(图1),分泌到细胞外的IL-1β 可以促进IL-6、TNF-α 的促炎作用,而IL-18 可以介导中性粒细胞成熟并局部浸润,同时诱导适应性免疫向Th2 方向转化,Th2 细胞分泌的IL-4 和IL-13 可以诱导巨噬细胞向M2 方向分化,促使免疫系统产生抗炎作用。急性炎症过程中炎症小体的激活有助于清除受损的细胞并尽快启动组织修复,慢性炎症过程中炎症小体的持续激活则会损伤机体组织,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炎症都可以通过调控炎症小体来进行。慢性炎症和持续危险因素的刺激均与肿瘤的发生、发展、转移等有着密切关系,炎症小体在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和抗肿瘤治疗中也起到了“双刃剑”的作用,既能提高也会削弱抗肿瘤免疫反应。
2 免疫检查点
免疫检查点是指表达在免疫细胞表面能调节免疫活化程度的一系列分子,类似汽车的刹车系统,能够在免疫系统活化时起到“刹车”的作用,使免疫系统的活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5]。免疫检查点表达和功能的异常是多种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肿瘤细胞逃避免疫监视的机制之一是过表达免疫检查点配体,阻断肿瘤抗原递呈过程,抑制T 细胞的免疫功能。肿瘤细胞中PD-1/PD-L1 通路可被多种信号调节,并起到维持免疫耐受的作用。目前研究最成功的免疫检查点有细胞毒性T 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4,CTLA-4)、PD-1 等。ICIs 主要通过阻断CTLA-4 和/或PD-1/PD-L1 通路来解除免疫细胞的抑制状态而重启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目前ICIs 已经在多种肿瘤中显示良好的抗肿瘤疗效,但仅一少部分患者获益,与疗效相关因素主要包括PD-L1 表达、肿瘤突变负荷、嗜酸性粒细胞计数[6]、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和糖酵解活性[7]等,尽管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对于影响ICIs 治疗疗效的确切因素仍不十分明确。
3 肿瘤中炎症小体与免疫检查点的相互作用
经典通路的炎症小体NLRP1、NLRP3、NLRC4、NLRP6 和AIM2 等通过调节机体固有和适应性免疫反应、细胞死亡、增殖和(或)肠道微生物参与到肿瘤的发病机制中[8]。炎症小体和IL-18 信号通路的激活在结直肠癌中具有保护作用[9],而炎症小体或IL-1 信号通路导致的炎症反应则会促进乳腺癌、纤维肉瘤、胃癌和肺转移等等[10]。因此炎性小体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到“双刃剑”的作用。主要取决于炎症小体表达水平、下游效应分子(即IL-1β 或IL-18)、肿瘤类型、肿瘤发生的阶段等。炎症小体在多种肿瘤中的相关性显示其可以作为分子靶点的治疗前景。
3.1 NLR 家族
NLRP3 是目前研究最多的炎症小体,既参与调控肿瘤本身,也参与肿瘤微环境的组成,并对肿瘤的发生有促进和抑制的双重作用。NLRP3 炎性小体在多种肿瘤(如乳腺癌、结直肠癌、肝癌、胃癌等)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对结肠癌有抑制作用,对胃癌和前列腺癌有致癌作用。因此,NLRP3 在肿瘤中的作用与组织或细胞类型不同有关。NLRP3 炎症小体的激活受到胞质离子水平(如K+、Ca2+和Cl-)的调控[11-12]。NLRP3 可以被细胞外ATP(eATP)激活[13],肿瘤微环境中的炎症、缺血缺氧刺激使eATP 水平增加100~1 000倍[14],死亡的肿瘤细胞释放ATP,结合到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s)上的P2X7R[15],以炎症小体依赖的方式增强CD8+T 细胞免疫反应。eATP 的水平由CD39 决定,CD39 通过调节效应因子和调节性T 细胞、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细胞)和髓系来源的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等发挥重要的免疫调节作用[14]。因此,特异性阻断CD39 可能导致肿瘤微环境中eATP 升高,从而导致炎症小体激活,可能增强ICI 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动物研究表明,抗CD39 治疗与PD-1 和CTLA-4 抗体联合在控制B16F10 小鼠黑色素瘤肺转移方面具有协同作用[16]。Lu[17]的研究表明弥漫性大B 细胞淋巴瘤患者的免疫抑制微环境中IL-18 水平升高与PD-L1 表达呈正相关,活化的NLRP3 炎症小体在该肿瘤细胞中上调PD-L1 的表达,降低细胞毒性T 细胞的比例,推测NLRP3-IL-18-IFNγ-PD-L1 途径可能是NLRP3 炎症小体激活和PD-L1表达之间的桥梁。
3.2 ALR 家族
AIM2 在固有免疫和炎症中的作用已得到研究公认,但在肿瘤中的调节作用尚不明确。有研究表明[18]AIM2 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双重作用。AIM2 最初作为黑色素瘤的抑癌基因被报道,其在结直肠癌、肝癌中的表达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而在皮肤癌、子宫内膜癌中则呈现过表达,发挥其致癌作用。AIM2 在多种肿瘤组织中的差异表达提示其在不同类型的肿瘤中可能具有独特的作用。AIM2 可调节PD-L1 的表达,当巨噬细胞吞噬了死亡的乳腺癌细胞,细胞内AIM2 可以识别肿瘤DNA,激活caspase-1 和产生IL-1β,释放的IL-1β 能够增加巨噬细胞中PD-L1 的表达。虽然AIM2 或IL-1β 的应用能够改善小鼠模型抗HER2 治疗疗效,但阻断这一通路能否影响抗PD-1/PD-L1 治疗疗效尚缺乏研究。
3.3 IL-1β
IL-1β 可增加肿瘤细胞和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膜上的PD-L1 表达,IL-1β 抑制剂和PD-1 抑制剂联合应用显示出比较有前景的抗肿瘤疗效。BRAF V600E 突变可以诱导黑色素瘤细胞分泌IL-1α/β 从而增加PD-L1/L2 的表达,BRAF V600E 特异性抑制剂vemurafenib 可通过影响IL-1α/β 生成来调节免疫检查点表达[19]。IL-1β 也可通过诱导PD-L1 表达对非小细胞肺癌或胃癌产生直接作用[20-21]。重组IL-1β 和M1 巨噬细胞来源的IL-1β 诱导肝癌细胞和小鼠肝癌细胞表面PD-L1 的表达。IL-1β 通过肿瘤局部炎症免疫细胞浸润和抑制CD8+T 细胞功能增加导致小鼠乳腺癌的发展和转移。乳腺癌小鼠模型中在抗PD-1 治疗前应用IL-1β 抑制剂可提高抗PD-1 治疗的疗效[22]。尽管炎症小体/IL-1β 通路在不同类型的肿瘤中可能发挥不同的作用,但机制仍不明确。
3.4 IL-18
IL-18 能够刺激NK 细胞产生IFN-γ,通过增强NK 细胞的ADCC 效应达到杀伤肿瘤的作用。而肿瘤细胞释放分泌型的IL-18BP,竞争性结合IL-18,使其无法发挥抗肿瘤作用,与PD-1 抗体联合应用具有协同增效作用。抗PD-1/PD-L1 治疗可以影响肺癌患者单核细胞中的基因表达谱,抗PD-L1 单抗比抗PD-1 单抗更容易增加NLRP3 和IL-1β,同时抗PD-L1 单抗治疗可以诱导单核细胞来源的DCs 细胞成熟、caspase-1 激活、IL-18 和IL-1β 的产生,而抗PD-1 单抗则无影响[23],该研究指出抗PD-L1 单抗和抗PD-1 单抗之间的重要差异在于是否能活化抗原递呈细胞。肿瘤来源的IL-18 可以诱导NK 细胞上PD-1 的表达,从而使中性粒细胞通过细胞膜上的PD-L1 与PD-1结合抑制其活性[24]。在K7M2 骨肉瘤模型中,IL-18与MDSC 募集有关,因此抗PD-1 与IL-18BP(IL-18的抑制剂)的结合增加了CD8 IFNγ+GzmB+T 细胞浸润肿瘤的比例,降低肿瘤负荷[25]。抗IL-18 抗体被认为是增强ICIs 抗肿瘤功效的一种潜在治疗策略。
3.5 免疫相关不良反应
随着免疫治疗应用越来越多,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 irAEs)也引起重视。大部分irAEs 可通过临床干预和积极处理而改善,但少数严重或致命的irAEs 能够影响患者生存甚至导致死亡。本课题组前期研究结果表明,肿瘤患者外周血铁蛋白可以作为炎症性irAEs 鉴别诊断和判断预后的有效且简便的生物标志物[26],进一步动物实验表明ir-AEs 导致的铁蛋白升高主要由巨噬细胞活化产生。AIM2 炎症小体激活和IL-1β 产生可以促进细胞焦亡,形成正反馈导致巨噬细胞增加,进一步加重irAEs。已有研究表明,应用IL-17A 抗体可以减轻PD-1 治疗的转移性结肠癌患者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27]。随着对于炎性小体激活以及irAEs 发病机制认识的逐渐加深,探寻炎症小体在irAEs 治疗中的研究会越来越多。
4 激活炎症小体增强ICIs 抗肿瘤疗效的机制
最新研究表明在接受抗PD-1 治疗的黑色素瘤患者中,有效的患者肿瘤标本中NLRP3、NLRP6、NLRP7、AIM2 和CASP1 的表达明显增加,虽然不能明确炎症小体激活、IL-1β 或IL-18 分泌增加能改善PD-1 治疗疗效,但该研究观察到NLRP3 的表达与CD8+T 细胞和记忆CD4+T 细胞数量增加是相关的[28]。Theivanthiran[29]通过一系列体内及体外研究证实,应用PD-1 抑制剂治疗后,CD8+T 细胞活化会引起肿瘤内源性PD-L1/NLRP3 炎症小体信号通路级联反应,同时募集粒细胞髓源性抑制细胞(polymorpnonuclearmyeloid derived supressor cells,PMN-MDSCs)到肿瘤组织中,从而抑制抗肿瘤免疫反应。应用NLIP3 抑制剂治疗后可以抑制热休克蛋白70 的释放最终减少PMN-MDSCs 的聚集,提高抗PD-1 疗效。Chen 等[30]的研究表明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HNSCC)小鼠模型中应用NLRP3炎症小体的抑制剂MCC950 可以显著降低HNSCC中IL-1β 的产生,并减少MDSCs、调节性T 细胞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增加CD4+和CD8+T 的数量,耗竭PD-1+和Tim3+T 细胞数量明显减少。结果表明NLRP3/IL-1β 通路促进了HNSCC 的肿瘤发生,通过NLRP3/IL-1β 通路抑制肿瘤微环境可能成HNSCC 的治疗的新方法。
研究表明炎症小体释放时,CD8+T 细胞介导抗肿瘤免疫反应增强[30],但一些PD-L1 表达阴性肿瘤仍能对ICIs 治疗有效,表明PD-1 抑制剂起效前抗原递呈功能是必需的[31],这样才能活化肿瘤浸润CD8+T 细胞。NSCLC 新辅助免疫治疗患者外周血中突变相关的新抗原特异性T 细胞克隆增加表明PD-1 抑制剂可以增强淋巴结中早期T 细胞激活[32]。然而,MC38 结肠癌小鼠肿瘤模型中,抗PD-1 治疗并不依赖于淋巴结中T 细胞的激活[33]。最近来自基底细胞癌或鳞状细胞癌肿瘤的单细胞RNA 和T 细胞受体测序数据表明,T 细胞克隆的增加并非来自预先存在的肿瘤浸润T淋巴细胞,可能来自于包括淋巴结在内的肿瘤外部区域[34]。同样,炎症小体的激活可能通过增强肿瘤外部CD8+T 细胞的活化来增强抗PD-1 治疗疗效,活化的CD8+T 细胞可以通过穿孔素依赖性机制促进抗原提呈细胞的炎性小体激活,通过正反馈机制达到抗肿瘤作用[35]。
最近研究表明,Th17 细胞可能在炎症小体激活的下游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肿瘤内Th17 细胞不仅与良好预后有关,也与预后不良有关,根据免疫微环境的不同,Th17 细胞可以作为调节或者效应细胞存在,IL-1β 是决定Th17 细胞特性的关键因素。在黑色素瘤和前列腺癌患者中,PD-1 抑制剂的临床疗效与外周血中CD4+IL-17+T 细胞的增加有关,表明了Th17 细胞在抗PD-1 治疗中的作用[36]。Jiao 等[37]研究发现在前列腺癌骨转移患者中,CD4+T 细胞以TGF-β 依赖的方式向Th17 而非Th1 极化导致的ICIs 疗效降低。TMEM176B 和CD39 可能作为两种不同的治疗策略来削弱由炎性小体和Th17 细胞介导的ATP 诱导的炎症反应。TMEM176B 和CD39 靶向治疗可可能触发Th17 细胞依赖性反应,从而增强ICI 的疗效。
5 结论
活化的炎症小体通过分泌细胞因子IL-1β 和IL-18 等来调节ICI 的抗肿瘤治疗疗效在临床前模型中显示了较好的治疗效果,然而,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工作来了解这些联合治疗疗效背后的机制,同时确定这种治疗模式的最佳应用时间,确定哪一部分DCs亚群和辅助T 细胞对炎症小体的激活起到关键作用,此外,还需要对炎性小体激活的关键分子靶点进行验证,从而设计出具有更强选择性的抑制剂。同样也应考虑PD-1/L1/L2 对控制炎症小体转录因子的影响。综上所述,目前多项研究已经开始侧重于PD-1/L1/L2 抑制剂与针对炎症小体的特异性抗体的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了解如何及何时以炎症小体作为靶点,来改善ICIs 的治疗疗效,减轻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更好的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