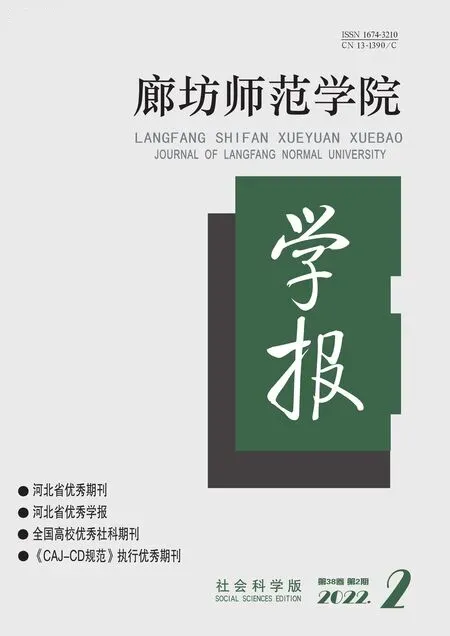《黄老帛书·十六经》之《立[命]》与《观》两篇考析
葛志毅
(大连大学 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622)
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汉墓出土之《黄老帛书》①其中《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四种,笔者不同意是即已失传的《黄帝四经》之看法,认为以称《黄老帛书》为宜,并撰写《〈黄老帛书〉与黄老之学考辨》,刊发于《炎黄文化研究增刊》1979年第4期;又收入《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之《黄老帛书》引文(包括《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主要据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集成》(四),中华书局,2015年版;间亦参考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一般径出其文,间亦包括自己的理解、判断与修正,但不另加注,如此只为避免繁复枝蔓,读者如若需要,可自行检对,敬希见谅。四种,其中以《十六经》特显重要,而《十六经》中最为独特者,乃是托为黄帝君臣问答讨论的九篇记事体裁文献。此九篇其实乃黄老学者托黄帝君臣之名自述其黄老思想之作,因此为黄老研究中弥足珍贵的文本。其中《立[命]②“[]”表示补缺文。》、《观》两篇内容尤应特予关注,《立[命]》乃其中唯一以黄帝口吻自述其志业者,《观》则记黄帝令力黑“周流四国,以观无恒善之法则”,布制建极,故所记有助于深入揭示黄帝所行政道、治法大纲之内容、性质,此两篇堪称黄老研究中罕见的珍贵资料。鉴于以往对其研究注意不够,尤其对《观》的研究缺乏深度,本文拟在深入剖析其自身内容的同时,以释论的方式,汲取相关记载参证比较,钩深致远,发覆探赜,彰显其补裨助益黄老研究的独到价值,以就教于黄老研究同仁。
一、《立[命]》与黄帝志业
《立[命]》记黄帝受命、立制、统天下之事。黄帝建国于天下之中,作为天下大君宗主,立四方辅相③《立[命]》“前参后参,左参右参”,参即辅相。见拙文《黄帝与黄帝之学》,载《炎黄文化研究》1996年第3期;又收入《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开创了“四达自中”的集权一统局面。黄帝自言受命配天,称“余一人”。其立制有两方面成就,其一,“乃立王,三公;立国,置君,三卿”,即在中央与地方建立王国与诸侯国两级政权,亦建立起以王、公、君(诸侯)、卿为代表的封建爵等,下启二帝三王以来的封建制度。《经法·论约》曰:“故能立天子,置三公”,《称》曰:“天子之地方千里,诸侯百里,所以朕合之也。”所言合于春秋之前的封建制度。其二,造历法。“数日,历月,计岁,以当日月之行”,即观测日月运行,制历明时,以应万民生活生产之需。
若论黄帝治世之道,乃以三才说为据,构建其法天则地治民之思想理念。如曰:“吾受命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又曰:“允地广裕,吾类天大明”;又曰:“吾畏天[爱]地亲[民],立有命,执虚信。吾爱民而民不亡,吾爱地而地不旷。”因受命于天地而得位,故以尊天法地为治道理念根本,其中天为受命登阼之本,地为生财养民之本,民为建国立邦之本,故必以天地人为治道根本。《十六经·果童》记黄帝曰:“夫民仰天而生,恃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是天地人三才紧密相关,是“君治”实现之根本。三才说反映出古代对自然和社会的整体性认识,因为天地人三者备具,方可形成对宇宙世界包举无遗的完整反映。
黄帝治世之道的又一层面即:“吾苟能亲亲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即认为亲亲而兴贤乃治道之至高准则,是乃取自儒家理念。亲亲,仁也;兴贤,义也,是亲亲而兴贤乃以儒家仁义标榜治道之完善。《礼记·中庸》曰:“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①《礼记·中庸》,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29页。故亲亲而兴贤乃儒家为政修道之仁义大节,礼制之枢纽。
《立[命]》大抵以黄帝自家口吻总括其政道治绩,为《十六经》开宗明义第一章。从黄帝受命—立制—统天下大业的叙述中,明显可见儒家治道理想之影响;是乃因儒家对三代以来帝王治道系统予以继承总结,代表着当时国家治道思想的主流。其实,无论当时哪一学派,只要欲平治天下,基本可谓舍此无为,大体皆难越出此模式,虽黄老道家亦不例外。此篇实乃《十六经》篇首叙论,记黄帝受命登极,始立制、统天下之事,意在引领以下诸篇记事。
二、《观》与黄帝治道之恒善法则
《观》记黄帝、力黑论布制建极,守天时以养民、正民之道。此篇所论重点乃其所言治世正民之纪纲大法,并从天地世界起源入手,进而释论国家社会治道法理等制度纲目之内容特质。本篇所述在《十六经》中特为重要,极值得关注。
力黑曰:“天地已成而民生,逆顺无纪,德虐无刑,静作无时,先后无名。今吾欲得逆顺之[纪,德虐之刑],静作之时,[先后之名],以为天下正;因而勒之,为之若何?”布制建极之要目总纲包括:逆顺之纪,德虐之刑,静作之时,先后之名。此俱关系到国家制度法理之大节,亦可谓布制建极之纲目要领。下面分别阐释。
(一)逆顺之纪
逆顺之纪,又可谓“道纪”。《经法·四度》曰:“逆顺同道而异理,审知逆顺,是谓道纪。”道纪为治乱存亡枢纽所关,乃必知之理。所谓逆顺同道,《经法·六分》有六逆、六顺,同为观国逆顺存亡之道,“六顺、六逆,死[生]存亡[兴坏]之分也”;所谓逆顺异理,即谓逆顺二者根本区别在是否合理,《经法·论》曰:“物各[合于道者],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顺]。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逆。逆顺各自命也,则存亡兴坏可知[也]。”按逆顺之异在于是否合乎道理,故二者必为“存亡[兴坏]之分”,亦必为“存亡兴坏可知”之道纪。既然逆顺之纪存在的前提与“道理”有关,那么,自相关“道理”意识在社会思想中萌发开始,逆顺之纪就应成为人们判断衡量国家社会存亡兴坏的一个原则标准。《经法·论》有曰:“察逆顺以观于霸王危亡之理”,反映出逆顺之纪在当时政论中意义不凡。诸子中亦有涉及,如《荀子·强国》曰:“故善日者王,善时者霸,补漏者危,大荒者亡。”①(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04页。是王霸危亡在当时政论中的影响,而逆顺之纪有助于对此的认识,其意义于此可知。《经法·论》又曰:“动静不时,种树失地之宜,[则天]地之道逆矣。臣不亲其主,下不亲其上,百族不亲其事,则内理逆矣。逆之所在,谓之死国,伐之。反此之谓顺,[顺]之所在,谓之生国,生国养之。逆顺有理,则情伪密矣。”是皆可证逆顺之纪在国家治道上所关之大。
(二)德虐之刑
德虐之刑在《国语·越语下》中作“德虐之行”,韦注:“昭谓德,有所怀柔及爵赏也;虐,有所斩伐及黜夺也。”②《国语》,(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35页。刑,法也,故德虐之刑犹赏罚之法。从历史发展看,至少从国家政法制度发生始,赏罚制度已开始成为必设的治理常法,其出现应较早。如果从概念形式上推断,德虐应与刑德有关联。如果说《越语下》与《黄老帛书》存有相互关联的话,那么,很可能《越语下》之“德虐”,在《黄老帛书》中又推衍出“刑德”。察《越语下》本无“刑德”,《黄老帛书》则“德虐”“刑德”两概念并见。虽如此,仍无足掩盖二者之关联。“德虐”又见于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作“德匿”,匿读作慝,与天象日月阴阳相关。《左传·庄公二十五年》载:“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杜注:“慝,阴气。”③《左传·庄公二十五年》,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80页。结合楚帛书所言,德匿与年岁之丰穰吉凶有关,《观》亦曰:“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此刑德与德匿义近。④李零:《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58页。刑德除与社会赏罚制度相关外,亦与年岁丰穰吉凶相关,亦即与社会赏罚相关的自然赏罚有关联,其中已杂入阴阳数术的内涵。刑德本指赏罚,经阴阳数术化之后,则主要指据历日干支推定吉凶祸福。近年出土文献中所见刑德者,多为阴阳数术性质。⑤胡文辉:《马王堆帛书〈刑德〉乙篇研究》,见胡文辉:《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黄老帛书》中的德虐之刑显然指赏罚制度,其刑德概念内涵较复杂,既指赏罚,又杂入阴阳数术色彩。《越语下》记范蠡之言有浓厚的阴阳家属性,德虐概念就在此思想语境中出现。综之,德虐与刑德间的联系区别须仔细辨析,这对认识德虐之刑的意义很重要。
(三)静作之时
《十六经·果童》曰:“地俗德以静,而天正名以作”,此静、作二者乃天地各自的属性特征。《称》曰:“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此外,《申子·大体》亦曰:“地道不作,是以常静。”⑥阮廷焯:《先秦诸子考佚》,鼎文书局,1980年版,第171页。天阳地阴,天德作,地德静,二者相应,故此实以静、作二者作为天地各自的属性。《经法·论》曰:“动静不时,种树失地之宜,[则天]地之道逆矣。”动静犹静作,由此动静之义,可推知静作应与四时农作之节有一定关联。静作不仅与“时”相关,更与“争”及“国家”“天稽”等天人大节相关。《十六经·姓争》曰:“争不衰,时静不静,国家不定。可作不作,天稽还周,人反为之[客]。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据此则静作之义较为广泛,不限于农作,还涉及社会事业活动诸多层面。《经法·君正》曰:“动之静之,民无不听,时也”,即政府出于各方面需求而必会征发民役,但必须合乎时宜,即所谓静作之时。黄帝令力黑周流巡视四国,“人静则静,人作则作”,此静作应包括人们社会行为的诸多方面。静作之时既应指人们行为须遵循天地时节,不得违碍,亦应包括人们静作行为须受社会法度规约节制。《果童》曰:“静作相养,德虐相成”,《姓争》曰:“刑德相养,逆顺若成”,由此可见静作、德虐(刑德)、逆顺三者间的关联性,亦可证逆顺之纪、德虐之刑、静作之时确实包括在布制建极之要目总纲中,是制度法理体制中关联密切的几大要素,上文言及的德虐与刑德在概念上的前后衍生关系,亦得到证明。
其实若仔细分析《经法·四度》,通篇用较多内容论证了逆顺之纪、静作(动静)之时、先后之名(形名)三者,其所谓文武其实相当于德虐之刑,亦即刑德,《经法·君正》论及文武概念,皆与刑德相当。其他如《经法·道法》关于刑名,《论》关于动静、逆顺、形名,《论约》关于逆顺、形名,《名理》关于动静、形名的论述,皆可与《十六经·观》之逆顺之纪、静作之时、德虐之刑及先后之名四者相参证,证明四者在布制建极中的核心地位。综之,“天地已成而民生”,在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之后,由逆顺之纪、德虐之刑、静作之时、先后之名共同构成国家制度法理体制,此四者作为体制要素的结构本元,亦即后文提到的“恒善之法则”(此在后文详论)。
(四)先后之名与形名源流
先后之名涉及黄老之重要内容——形名学,如细按《黄老帛书》全部内容,为反复出现的主旨要点,其重要不言可知,故予详实的阐释。
先后之名的名,应指形名,但绝非其时一般名家的形名研究,而是指黄老道德主导下的名法之治,包纳名、法两家的精蕴,此义须细加钩稽始明。
先后之名须参照《果童》内容阐释。《观》曰:“天地已成而民生,逆顺无纪,德虐无刑,静作无时,先后无名”,此乃初入文明,逆顺等四种制度法理尚未形成,因此为无纪、无刑、无时、无名之社会状态。《果童》曰:“地俗德以静,而天正名以作,静作相养,德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与《观》相比,此处少一“逆顺之纪”,余下“静作相养”“德虐相成”,这说明静作与德虐二者,各由两“名”(“静”与“作”、“德”与“虐”)之对立依存关系所构成。以静作、德虐为代表,对此类由两名之对立依存关系结构而成的概念及性质,再针对其相辅相成的特征,予以一般性概括,是即所谓“两若有名,相与则成”。上文所谓“地俗德以静,而天正名以作”之天地,在形式上亦与静作、德虐相同,亦由两名“相与则成”之对立依存关系结构而成。
“两若有名”与“先后之名”相当,名乃形名之名,只是特别强调了“名”的意义与地位,而名亦可作为形名概念之代表。总之可以说,“两若有名”及“先后之名”,皆用两个对立概念间的概念组合形式阐释定义形名学。形名学不仅关系一般事物的性状研究,大到国家治理形式及其制度方式的研究亦皆涉及,同时对形名的重视亦导致名法之治的产生,它反映了名家、法家的结合,值得关注。
《经法·四度》曰:“美恶有名,逆顺有形,情伪有实,王公执[之]以为天下正。”按互文之例,“美恶有名”之名,应兼下形、实而言,即兼形名、名实而言,所言乃黄老形名之治。由此推之,先后之名所谓名,必兼形名之言。
形名乃黄老学内容要旨之一,又称黄老刑名。据《史记》所言,黄老学乃由黄老道德与黄老刑名二者构成。形名之重要,首先在于从世界的最高本体道,直至构成世界全体的每一具体事物,无不可纳入形名范畴分析研究,用以探究世界存在之形式及本质,从而提供从内外全方位、多层次进行观察分析的阐释范式。
形名确定事物性质的方法乃据形以定名,用名以固实,使名实相符,是确定检核事物性质的可靠的逻辑思维方法,名家之形名论、名实论乃其代表。
名实论重在论证事物名实必须相符,《公孙龙子·名实论》曰:“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又曰:“夫名,实谓也……审其名实,慎其所谓。”①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9、61、62页。名实论乃以论辩检核的方式,保证名实相符,名实合同。名实论与形名论之认识方式符同无别,皆为获得对事物正确可靠的理性把握。名家之外,儒家很早就提倡正名,如《论语·子路》记孔子主张为政首务在正名,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进而会使礼乐不兴,刑罚不中,以至民不知所措等一系列过失,“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②《论语·子路》,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06页。,从而指出正名在政道治民上的重要性。《左传》成公二年记有孔子关于“唯器与名不可假人”之论,认为“器与名”乃身份与地位等级的象征,不可轻易授人,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即器与名乃“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①《左传·成公二年》,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84页。。正因其与政柄国道的关系,故正名论久已在儒家学说中占有不容质疑的重要位置。
儒家重礼教,礼教又称名教,因其注重君臣父子等级名分之别,礼制乃用来表现等级名分之别的工具。如,《国语·楚语上》曰:“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又曰:“明等级以导之礼”②《国语·楚语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91、192页。;《荀子·富国》亦曰:“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③(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8页。不同名分间借助礼制对言行规范及器用之名物度数作出等级性规定,为之标志。如关于丧礼之赗赠器币,《荀子·大略》记曰:“货财曰赙,與马曰赗,衣服曰襚,玩好曰赠,玉贝曰唅。赙赗所以佐生也,赠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故吉行五十里,奔丧百里,赗赠及事,礼之大也。”④(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92页。此将参与丧礼及助死者亲人守丧应送之货财器用,有关其种类、对象、用途、名称及赠予之时乃至奔丧道里等,尽数予以说明阐释。其中可见对赠予物事相关的名称、种类、用途之说明乃必要项目,因此所谓名物度数成为礼制研究中必及的相关内容。《汉书·艺文志》谓“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⑤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页。,甚为有理。如《周官·春官·典命》掌诸侯卿大夫的爵命器用封赠,其中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享用的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等,并与其命数相关,即分别以九、七、五三者为仪节;又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亦如之。”⑥《周官·春官·典命》,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80页。即王之公卿大夫众臣所享用的居宅器用等,亦以其爵等命数为仪节等差。可以说,礼制中的名物度数概念与形名学相关,或者说,形名学是借鉴参考了名物度数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如号称“三礼”之一的《周官》,记有丰富的名物度数相关概念。
此外,记载中亦见孔子关于概念辨析正名之事。《韩诗外传》卷五载:“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通曰:‘自今以来,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故孔子正假马之名,而君臣之义定矣。《论语》曰:‘必也正名乎。’《诗》曰:‘君子无易由言。’言名正也。”⑦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80页。又见于《孔子家语·正论》及《新序·杂事五》。孔子为“取”“假”两概念正名,其背后深义在为正君臣名分,此可见儒家正名学说的政治实用性,亦可见儒家正名思想与形名名家间的联系。
儒家后来确实发展起逻辑名学体系。荀子著有《正名篇》,曰:“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名而一焉。”⑧(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4页。即王者制名,乃为事物性质定名辨实,以利于政道推行,便于人们互通心志,并建立起统一的名物制度,使庶民臣下普率遵行。又曰:“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⑨(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5页。即王者制名乃为区别事物间的不同性质,重要在“贵贱明,同异别”的名分区别,使处于不同地位身分等级的人们,在交流中便于互通心志,保证事业成功。可以说,儒家对逻辑名学的发展自有其贡献,但儒家的逻辑名学体系主要是为其政治理论服务的工具,这点与黄老刑名之治的性质相关,但现在黄老对刑名之治的理解论述较儒家更为丰富深入,这是必须明确的。
《黄老帛书》论及形名研究之作用及意义,有独到之处,应予关注,这有助于理解黄老刑名的治道属性。《称》曰:“有物将来,其形先之,建以其形,名以其名,其言谓何?”《经法·论约》曰:“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必审观其事之所始起,审其形名,形名已定,逆顺有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然后参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是故万举不失理,论天下而无遗策。”是皆谓形名之术乃观察研究天下万物万事最基本的逻辑认识方式,从对一事一物的观察直至对天地大道的整体研究,形名可谓是对世界所有事物确定其基本性质的有效认识方式。《尹文子》对形名研究方法的意义,亦有可供比较参考的论述。如《尹文子·大道上》:“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又曰:“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圆白黑之实。名而不形,不寻名以检,其差。”又曰:“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不可相乱,亦不可相无。无名,故大道不称;有名,故名以正形。今万物俱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万名俱列,不以形应之,则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即形名二者相互密切依存,是认识和区分万事万物的基本入手根据。《大道上》又曰:“故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①以上《尹文子》引文见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2、474、477、475页。即据形名相互检核认定事物性质,则事物存在之理可明;而为究明事物存在之合理性,亦必须由形名为入手之资。以上《尹文子》所论,对形名方法之重要及其与事物存在关系之探讨阐释,极为明晰,可与前引《黄老帛书》所论互为参证发明。古书中有以名为治天下之具的记载,乃从政治角度揭示名的意义,亦从一侧面反映出中国思想文化充分政治化的特征。如《申子·大体》:“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圣人贵名之正也。”②阮廷焯:《先秦诸子考佚》,鼎文书局,1980年版,第169页。所言显与前引三名之义相关。又曰:“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③阮廷焯:《先秦诸子考佚》,鼎文书局,1980年版,第168页。《管子·心术上》亦曰:“名者,圣人所以纪万物也。”④黎翔凤:《管子校注》(中),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76页。名不仅是一逻辑思想概念,更是可用于统治世界万物的政治理想工具,故尤为先王治道所倚重。《韩非子》更从道的角度论述了形名的政治功效,其《主道》曰:“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事自定也……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⑤(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6页。即明君以道总统万物是非善败之大端,执形名以为治事驭民之具,进而可实现名自命、事自定的无为自然之治,亦即形名必须在道的主宰下方可发挥其政治效用。形名必须置于道的主导下,是黄老刑名思想的要旨。《经法·道法》曰:“见知之道,唯虚无有。虚无有,秋毫成之,必有形名。形名立,则黑白之分已。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形名声号矣,形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是谓形名的有效运用,必须以“虚无有”之道为主宰,是乃揭明黄老刑名自然无为之治的道学本质。
察黄老无为之治与形名术的推行,具有内在的思维联系。《称》曰:“世恒不可,释法而用我,用我不可,是以生祸。”法家与黄老俱主张去私智而用公法,故反对“释法而用我”,循此思路即产生名自名而事自定的认识,认为天下事物无不具自名、自正、自定的属性,这就是在黄老自然无为指导下的形名思想。它要求严格按照形名自身的考察方式,审核辨正事物的本然属性,使形名相符,名实合同。由于自然无为意识渗入形名概念,于是又体现出名自正而事自定的意识效果。《管子·心术上》:“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故曰圣人。”①黎翔凤:《管子校注》(中),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71页。《韩非子·扬权》曰:“上以名举之,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②(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5页。即在黄老刑名思想主导下,审核形名,确定事物性质,务必坚持形名参同的原则,乃可实现有如名自名、物自正、事自定那样的客观认识效果。《申子·大体》曰:“名自名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因名以正之。”③阮廷焯:《先秦诸子考佚》,鼎文书局,1980年版,第168、169页。即名自名、事自定,乃以大道为据审正形名的结果。《韩非子·扬权》曰:“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名,令事自定。”④(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5页。《经法·道法》曰:“凡事无小大,物自为舍。逆顺死生,物自为名。名形已定,物自为正。”此中道出一个道家哲理,即尽管人们自以为可据形名考核之法认识世界,其实外在于人们思想的事物,本乃一自在的物自体,其本身具有自名、自正、自定的本体自性;圣人执虚静之道认知者,不过此物自体的自性,别无其他。或者可以说,所谓名自名、物自正、事自定这样的认识结果,其前提必须是在黄老思想主导下审核形名方法之运用。那么,运用审核形名的方法在先,发现并建立起名实相符、形名参同的客观事物属性在后,所以乃是经过认识上的推究发明努力,才建立起的主观意识与客观事物属性间的联系统一,又使用自名、自正、自定这类黄老自然无为概念予以表述。其意义所在,乃相当于格外强调外在事物属性的客观性,但必须注意的前提是,只有在道主导下的形名方法,方可得此自名、自正、自定的结果。因以道为主导,可实现虚一而静的心境,避免内外杂念干扰,保证形名考察过程及结果之纯正、客观、公允,即所谓自名、自正、自定之本体自性。
对名法二家细加推究,若名家称形名,法家亦可称刑名,因法家刑名实兼形名与刑法二者,如在《经法·名理》中已见名法兼具的主张,由此形成黄老刑名的特征。《尹文子》号名家,亦主张名法之治,如《尹文子·大道下》曰:“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⑤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93页。此名即名家形名之谓。其《大道上》曰:“君不可与臣业,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与侵,谓之名正,名正而法顺也。”伍非百曰:“正君臣之名分,乃形名家之常谈。”⑥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87页。正君臣名分,乃名法之治中最根本的内容核心,因此形名家主旨与法家无异,亦与儒家相通。
黄老刑名吸纳名法之治的理念,但将名法二者置于道的督导下,是黄老刑名的最大特点。《韩非子·扬权》曰:“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⑦(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5页。,《韩非子·主道》曰:“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⑧(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6页。,《经法·道法》曰:“见知之道,唯虚无有。秋毫成之,必有形名”,皆为可证。相关如《尸子·分》的论述亦颇值得关注,其曰:“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不敬。”⑨(清)汪继培辑:《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按“正名”“执一”“赏罚”,正乃道家主导下的名法之治,故黄老刑名虽主名法之治,但为成其自然无为之治,必置名法于道的主导下,这点很重要。
《黄老帛书》认为形名思想产生极早,如《十六经·成法》曰:“昔天地既成,正若有名,合若有形,[乃]以守一名。上廞之天,下施之四海,吾闻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复一,民无乱纪。”是谓天地既成即有形名及据形名正定事物之法,而其功用则囊括遍施四海天地,且视之为“道”,称之为“一”、为“名”。《观》记黄帝谓天地混沌之初,“无晦无明,未有阴阳,阴阳未定,吾未有以名”。这相当于以形名原察事物之法,应发端于世界开始的阴阳产生之初。这为证明形名思想之久远渊源及其合理有效性,提供了论断根据。《黄老帛书》既认为道作为世界本原,又提出以形名称此道体之例。《十六经·行守》曰:“无形无名,先天地生”,《道原》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又曰:“显明弗能为名,广大弗能为形,独立不偶,万物莫之能令。”《经法·名理》曰:“有物始[生],建于地而溢于天,莫见其形,大盈终天地之间而莫知其名。”此皆以无名无形描摹称述道之广大,此盖因道异于众物万有之故。此以形名称道体,无疑可见形名概念在黄老思想中的至高地位,可谓形名与道体不二,故于研究黄老刑名时务必关注此点。《尹文子·大道上》曰:“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又曰:“大道不称,众有必名。”①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2、473页。道广大无极,异于万物之形名,故以无形无名特殊称之,以此见道作为世界本原超越有限万有之神秘特殊属性。此外,《观》中有值得提出之刑名二例,其“刑”皆当读为本字,不读为形。其一“正名修刑”,即准刑罚制度增修刑罚条例;其二“正名驰刑”,即准刑罚制度减损刑罚条例。是乃因时节变化失常,故主张改修刑律以应时变。此刑名乃法家概念,虽杂入阴阳家之影响,但无疑本为黄老刑名之法家属性反映,知此亦有助于认识黄老刑名作为道法家兼主名法之治的性质。
在《经法·名理》中出现与逻辑名学密切相关的名理概念,曰:“天下有事,必审其名。名[理者]循名究理之所之,是必为福,非必为灾。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审察名理终始,是谓究理……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见正道循理,能举曲直,能举终始。故能循名究理。形名出声,声实调合,祸灾废立,如影之随形,如响之随声,如衡之不藏重与轻。故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乃见[正道],乃得名理之诚。”是名理乃黄老刑名之说,以道为本,以法与形名为用,并从道法与形名角度探求名理概念的性质。可以说,此名理概念有明显的法家信赏必罚之彻底精神,但却与酷法严刑的苛刻精神有别;所谓名理概念内含道的意味,或者可以说,此名理即道之别名;其不仅借道的名义使自己升华,并使黄老刑名思想全体得以升华。名理概念的提出,是黄老道德与黄老刑名体系的最大思想成果与思想提升,必须予以充分关注。此欲就其与逻辑名学的联系略谈一二。
与形名相关的名辩思潮,乃中国古代逻辑名学及概念分析思想之发端。名理显然是在形名与名实讨论总结中提出的概念,尤其所谓“故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乃见[正道],乃得名理之诚”,更可见在与道结合时所能达到的理性抽象思辨水平,乃至下启魏晋玄学中的名理概念。有学者把魏晋玄学思想分为名理与玄论两派,其中“名理派虽也有老庄的思想,但以形名家为主”②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形名乃《黄老帛书》的核心内容,而且《经法》明确提出名理概念,可见其乃立于形名研究基础上。名理在魏晋玄学相关记载中,已成习见概念,此可证明《黄老帛书》中形名思想对魏晋玄学必有相当之影响。如西晋鲁胜不仅注《墨辩》,而且“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略解指归”③(唐)房玄龄等:《晋书》(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34页。可为证。其本应成为学术思想史上予以关注的现象,只是论者罕及。考名家最初产生,乃春秋战国诸子争鸣所致,它促使人们深入探求语言论辩艺术,并以此提升彼此的理性思辨水平。此应以荀子的论述最好,《荀子·正名》曰:“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势恶用矣哉!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①(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22页。也就是说,明君以权势刑禁就足以控制统管人民,因而无需辩说喻理的手段。至圣王没,天下乱,奸滑之言纷起,君子已无权势刑禁制御臣民,只得以辩说喻理的方式开悟说服臣民,于是必须讲究语言辩说技巧。这使语言辩说技巧的研究运用,成为君子达于文治和实现王业的有效工具。如此就揭示出诸子百家相互进行思想辩难及争鸣互诘的现实理论意义,亦揭明百家争鸣完全出于政治功利实用目的之本质。这样,荀子完全为建立和维护圣王之治,提出其逻辑名学体系,所谓“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他主张君子应简要明白地表明其政治主张,以正言达意为目的,对诡言繁辩、炫辞耀名者持反对态度。《荀子·正名》曰:君子“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外是者谓之,是君子之所弃……彼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故穷借而无极,甚劳而无功,贪而无名。故知者之言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是荀子特别反对碎辞辩难,极力主张明白易知,易言易行之论。为此,荀子列出当时辩者以惠施、公孙龙辈为代表的诡异怪妄辩题,予以批判。大致可将其归纳为“乱名乱实”的三点,即“惑于用名以乱名者”“惑于用实以乱名者”和“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且谓:“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与辨也。”②(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25—426、420—421、422页。不与惠施、公孙龙之辈论辩,即等于完全摈弃于形名家之外,不承认其逻辑名学的性质。荀子之论,代表了政治实用性逻辑名学论者的极端立场。
其实,惠施、公孙龙代表的逻辑名学成就不容轻否。惠施、公孙龙作为名家中坚,格外强调纯粹抽象的语言概念分析方法,尽管诸子多认为此论说方式支离繁碎,无裨实用,亦影响到政治伦理宣传功能的有效发挥,故多抵制抨弹,不予接受。这影响到名家中如尹文子亦极力反对他们,并提出三科之名、四呈之法这样功利实用的名学主张,与惠施、公孙龙立异。③伍非百提出,尹文一派形名家与其他墨儒辩者之形名家根本不同,此为“名法”与“名辩”分途所始也。见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6页。但这不足以完全影响惠施、公孙龙所倡导的抽象概念分析方法之推行,其作为逻辑名学发展中的一派,势头亦颇盛。只是限于诸子致治追求为主导的政治导向,使其难以得到充分发展的空间,惠施、公孙龙也始终受诸子主流排摈,在先秦及其后一直被斥为异端。后来鲁胜注《墨辩》,乃与魏晋玄学盛倡名理玄谈之风有关,再后来其说基本沉寂,虽然此抽象分析的逻辑名学受社会政治、文化的阻碍无法得以充分独立发展,但不能因此否认此逻辑名学体系在古代的存在。鲁胜注《墨辩》在西晋元康前后,他仍然认为:“墨子著书,作《墨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学,而不能易其说也。”④(唐)房玄龄等:《晋书》(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33—2434页。即惠施、公孙龙虽受诸子贬抑攻驳,但其代表的抽象概念分析方法,仍被尊为逻辑名学正宗,其成就造诣不容否定。还须指出的是,即使惠施、公孙龙自身特别强调其说之学术认知价值,但仍然难以完全摆脱政治实用取向的渗透影响。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名家首录《毛公》九篇,班固自注:“赵人,与公孙龙等并游平原君赵胜家。”颜注:“刘向《别录》云论坚白异同,以为可以治天下。”⑤(汉)班固:《汉书》(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36、1737页。这表明公孙龙学派自认其说可用于治天下。鲁胜在定义名学概念时有曰:“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⑥(唐)房玄龄等:《晋书》(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33页。“道义”“政化”等,带有明显的政治伦理色彩。可以说,政治实用性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影响颇深,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这也是逻辑名学未能在中国古代获得完全独立发展的最终原因所在。
以上为详实阐述《观》所记“先后之名”的内涵,扩及形名由来,形名与儒、法、名家的关系及其性质,形名在思想史上的久远影响,形名在黄老中的地位意义等问题,目的是借此加深对黄老刑名这一重要问题较全面的理解认识。虽似涉泛滥溢出之嫌,但作为研究提示,应对黄老刑名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同时亦可使形名作为黄老内涵主旨这一点,更为大家所认同。
综之,形名思想在《黄老帛书》中占比颇大,黄老思想之道法家性质决定其形名思想必须为此服务,因此黄老刑名思想亦无法摆脱政治实用型逻辑名学的性质。虽然黄老刑名与惠施、公孙龙一派名学基本无交集,但其提出的名理概念却应受到应有的关注,值得研究。
三、《观》之疑难内容解析
以上对《观》所述制度大法特别对其中的“先后之名”着重进行了深入的钩稽剖析。此外,《观》所述内容亦有难明之疑义待破解阐释者,如天地开辟与阴阳四时之生、民之生与食及继之关系、刑德之性质功用、圣人守时及顺天从人诸问题,皆试予阐释说明,以裨益对《观》内容之理解。
《观》中记述,黄帝曰:混沌未开之时,“无晦无明,未有阴阳。阴阳未定,吾未有以名。今始判为两,分为阴阳,离为四时(下缺11字),因以为常,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是混沌开辟之初,阴阳四时的生化作用最为根本,后来以阴阳二元解说宇宙构成及其运行模式时,多以阳明与阴微二者之依存互补为根本,即所谓“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淮南子·精神》曰:“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①何宁:《淮南子集释》(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04页。《文子·九守》所述同此。这里所阐明的阴阳四时在天地之结构生化作用中的根本地位,与《观》在混沌开辟之初首言阴阳四时之生相合。按《观》于上文所云“天地已成而民生”,与此所述开辟之初即言阴阳四时而似未及天地有异。按混沌初辟即出阴阳,阴阳化分天地,再化分四时。《观》之“今始判为两,分为阴阳,离为四时”即此义,因此“今始判为两”的两,兼指阴阳与天地。开辟之初的生生过程,应如图1所示:

图1 混沌开辟阴阳四时化生天地万物
《淮南子·天文》从天地未形成之前的虚廓宇宙讲起,曰:“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②何宁:《淮南子集释》(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5—166页。若仔细体会文义,大体可概括出混沌之气出阴阳、阴阳化分天地再化分四时、天地四时化生万物的过程。又《文子·九守》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浑而为一,寂然清澄。重浊为地,精微为天;离而为四时,分而为阴阳;精气为人,粗气为虫,刚柔相成,万物乃生。”③李定生等:《文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细读此文,亦可概括出混沌开辟、阴阳始出之后的天地四时生化过程。《淮南子·俶真》曰:“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④何宁:《淮南子集释》(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5页。,亦谓混沌开辟之后,阴阳、天地、四时、万物为生化过程经历的几大演变要素。《观》言天地开辟,仅言阴阳、四时之分离,此下叙及与阴阳相关的牝牡、柔刚之作用时,始言天地之成与民之生,如此乃承阴阳家言的性质以突出阴阳、四时的地位作用。其曰:“牝牡相求,会刚与柔,柔刚相成,牝牡若形。下会于地,上会于天。得天之微,时若(下缺11字)待地气之发也,乃萌者萌而孶者孶,天因而成之。”此处是谈天地阴阳之作用,孶萌生成人及万物之义。《汉书·律历志上》曰:“故阳气施种于黄泉,孶萌万物”①(汉)班固:《汉书》(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59页。。察上下文应含人父天母地之义。《十六经·果童》已曰:“夫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天地父母生斯民,民须仰赖天地才得存活,民的生存蕃殖问题有待天地。察所谓牝牡柔刚转自天地阴阳,天地阴阳合和生人,亦须养人。
《观》又曰:“夫民之生也,规规生食与继。不会不继,无与守地;不食不人,无与守天。是[故]嬴阴布德,[秉时以养]民功者,所以食之也。缩阳修刑,重阴长夜气闭地孕者,所以继之也。”是民生须密切仰赖天地者,乃民食与民继二者,民继即民庶之生生繁殖孳息。此外,所谓“嬴阴布德”与“缩阳修刑”所提出的阴阳刑德概念,是乃与民食与民继密切相关的天地之道。其解须参考《越绝书·外传枕中》,其曰:“冬三月之时,草木皆死,万物各异藏,故阳气避之下藏,伏壮于内,使阴得成功于外。夏三月盛之时,万物遂长,阴气避之下藏,伏壮于内,使阳得成功于外。”②李步嘉:《越绝书校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0页、第311页注释68。按:“嬴阴布德”即夏三月阴气下藏伏于内,阳成功于外;“缩阳修刑”即冬三月阳气下藏伏于内,阴成功于外。亦即春夏种树为德,滋长五谷以食养万民;秋冬收藏为刑,适当农闲嫁娶蕃殖民庶之时。“继”与合婚生子相关,所谓“缩阳修刑,重阴长夜气闭地孕者”,婚礼属阴,《周官·大司徒》十二教之三有“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③《周官·大司徒》,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03页。,阴礼谓男女婚姻之礼,宜于秋冬行之。《荀子·大略》曰:“霜降逆女,冰泮杀止”,王先谦引郝懿行之语曰:“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荀卿之意,自九月至于正月,于礼皆可为婚。”他又引《孔子家语》与董仲舒为证,董仲舒曰:“圣人以男女阴阳,其道同类。观天道,向秋冬而阴气来,向春夏而阴气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杀止,与阴近而阳远也。”④(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96页。这表明,秋冬为合婚孕子之时,适合安排蕃殖继民之事。由此民生之食与继引出阴阳刑德概念,此刑德当含二义,即四时生长收获之节序,与庆赏刑罚之治道。⑤简单说,刑德包括天时、人事二者,《经法·君正》曰:“天有生死之时,国有生死之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按天时死生与国政死生相应,二者各为文武之道,有养生与伐死之别,是可与刑德概念比较参证。
《观》又曰:“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姓生已定,而敌者生争,不戡不定。凡戡之极,在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即首先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农作节序作事,尽其生养万民之功。其次,针对人性好争生乱的特性,以刑德手段戡平之;但须以刑法月阴,以德法日阳之道,务求刑德之施用于赏罚公正合理。察刑德既与阴阳四时相关,其本出阴阳家无疑,本篇“春夏为德,秋冬为刑”亦可为证。此论亦为儒家吸收,《大戴礼记·四代》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谓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阴阳,阳曰德,阴曰刑。”⑥(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0页。法家则径以刑德称赏罚,《韩非子·二柄》曰:“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⑦(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9页。是可见刑德概念使用之广泛,意义影响之深远。相比较而言,本篇对刑德概念的引出值得关注,使用上亦兼农时养生与戡乱弥争二义,对刑德概念的使用在《黄老帛书》中最为典型,亦最值得关注。无论以刑德戡乱弥争,还是据刑德农时之序养民,皆须以“先德后刑顺于天”为上,故其下论述了“时嬴而事绌,阴节复次”,“时绌而事嬴,阳节复次”,此两种反天逆时之行皆足招致祸败。鉴于此,下文乃提出圣人当遵天守时,正静己身以顺天从人的主张。
《观》曰:“天道已既,地物乃备。散流相成,圣人之事。圣人不巧,时反是守。优未爱民,与天同道。圣人正以待天,静以须人。”此谓圣人顺天地之道经理世事万物,同时亦以天人之道持身律己,爱民守时是尚。所谓“优未爱民,与天同道”,指圣人并未加意爱民,不过遵循自然天道而已,却获致爱利万民之功。是乃畅达黄老自然无为之旨,即圣人持无心治天下,故本无慈爱可言;众庶亦不以圣人德己而怀感戴,一切皆循顺自然之道而已。此以《老子》五章所言为好,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①高亨:《老子注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此外还有一层意义,即赏罚准当,故受赏者不以为德,受罚者不以为怨,《经法·君正》:“受赏无德,受罪无怨,当也。”此既合法家赏罚公正之义,亦合黄老自然无为之义。
四、《立[命]》与《观》在黄老思想体系中地位之评价
《立[命]》以黄帝自家口吻叙述其生平志业,可借以窥见传说中黄帝的胸怀抱负及政道治绩,从而形成对黄帝人格较全面认识的大体轮廓,这在黄老研究中的价值勿用赘言。《观》以黄帝君臣之讨论为主,涉及政道治法中的纪纲大端,在《十六经》中堪称最为重要。所谓观,乃观国、观天下之法,《经法·论》曰:“执六柄以令天下……六柄,一曰观……观则知生死之国”,又曰:“察逆顺以观于霸王危亡之理”。《经法·六分》曰:“观国者观主,观家观父。能为国则能为主,能为家则能为父”,由是提出观国之六顺、六逆,二者事关存亡兴坏之分,乃治国治天下之所必执,因此“观”可谓是观察审知国家天下兴衰存亡之道的政治考察方式。②《荀子·强国》记应侯问入秦何见,荀子历言“观其风俗”,“观其士大夫”,“观其朝廷”,然后据以总括评说秦政之长短。此乃以“观”为入手之据,考察一国政教得失之显例。《管子·八观》所言观国之法尤详。《观》篇首记黄帝“令力黑浸行伏匿,周流四国,以观无恒善之法则”,即要力黑遍观四国,考察求觅“恒善之法则”。③按“无恒善之法则”,此“无”乃语首助词,无义,故“无恒善之法则”实即“恒善之法则”。“无”为语首助词,无义,见杨树达:《词诠》,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39页。按此句大多读为:“周流四国,以观无恒,善之法则”,我认为不妥,乃改读为“以观无恒善之法则”,其中对“无”的理解是此句意义关键,某种意义上亦涉及对《观》全篇的理解,必须审慎理解诠释之。力黑周流巡视之后,提出逆顺之纪、德虐之刑、静作之时、先后之名可为“恒善之法则”,可为天下正,可勒之“布告天下”,乃治国治天下者必据之大法纪纲,其政治上的鉴戒指导意义自不必言。《观》通篇围绕治天下之大法纪纲立论,但归宗结义实可综括为以自然无为之道为圭臬,可见黄老学旨归之明确,或可谓万法不离其宗乃道家之道的觉悟自性。
综之,《立[命]》及《观》内容义旨丰富,从制度道法角度总括黄帝思想,对认识黄帝人格及其政道理念颇具参考裨益,乃《十六经》标志性代表篇章,亦为认识黄老大法治道之纲领性篇章。所以,必须充分估价《立[命]》及《观》在黄老研究中的意义。可以说,在现有的黄老文献中,对于认识黄老学者心中的黄帝人格及其治道理想,这两篇文字当为首选,无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