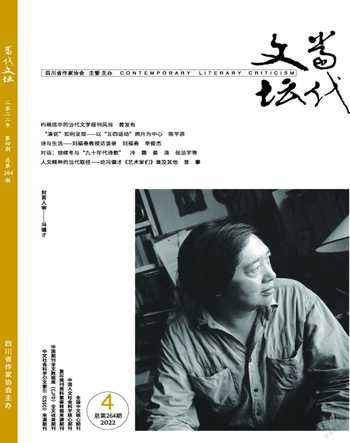现代生活图景的戏剧化呈现
冯涛
摘要:陈彦小说呈现出戏剧化的叙事艺术特征,主要表现为“代言体”的叙事特点、叙事场景的戏剧化以及视点转换下的多维度叙事。小说对于舞台艺术的借鉴,增强了文本的蕴藉,形成了互文的关系。戏剧化场景叙述在带来直接性審美体验的同时,彰显了小说的现实主义品质。视点的转换则多角度、深层次透视人物的心理,最大限度揭示表象背后的人性隐秘,呈现事件内在的肌理。
关键词:陈彦;戏剧化;代言体;场景;视点转换
小说与戏剧作为文学艺术的门类,二者有着内在的艺术关联,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彼此借鉴。戏剧的源起远早于小说,剧本作为戏剧文学性的主要载体,在古希腊时期就已成熟。中国现代小说家既受到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影响,同时自觉将西方戏剧理念融入小说创作之中,形成了小说戏剧化的文体特征。“中国现代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对戏剧手法的运用,在客观上就造成了现代小说的戏剧化,这决不是偶然的,它首先说明了小说与戏剧的亲缘关系以及它们的相互融合的关系。”①近年来国内小说创作中,陈彦的“舞台三部曲”(《主角》《装台》《喜剧》)颇为引人注目,呈现出独异的戏剧化叙事特征。戏剧人出身的陈彦,在其写作实践中自觉将戏剧与小说融通,他认为“戏剧需要文学的滋养,让故事变得底蕴丰厚起来……而小说也需要戏剧故事讲述的经典型概括能力和引人入胜的情节牵引力量,从而成为更加耐读的文本。”②陈彦小说叙事中主动借鉴舞台艺术元素,在时间维度上将现代生活与传统艺术融于一炉,极大提升了小说叙事的表现力。陈彦小说对于戏剧艺术的“引进”,既是当下小说创作面向文学传统的一种复归,又是对于新时期文学现代性呈现所做的有益尝试和重要实践。
一 “代言体”叙事特征
“代言体”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文体结构,其中包含剧作家代人物言、表演者代人物言、“行当”代剧作家言、人物代剧作家言,“内云”“外呈答云”代观众言等五种话语言说方式。③小说从本质而言就是作家代言的艺术,陈彦小说以戏剧人的生活为题材,并置呈现舞台生活与现实生活,将“代言体”创造性引入小说叙事之中,构成小说多元的话语结构,小说文本呈现互文的结构特征。陈彦小说中的人物以戏剧为生,其身份具有双重性,既是小说中的特定人物,又是小说中戏剧舞台的表演者。小说人物作为表演者与舞台人物在精神气质上有着高度的契合,小说人物在代舞台人物言的同时,又在通过舞台人物言说自身,形成“双重言说”的叙事效果。小说《主角》的叙事中,秦腔名伶忆秦娥从艺之路坎坷曲折,历尽艰辛,终在戏剧舞台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与此相对的是其舞台演出中剧情的跌宕起伏。小说叙事与舞台叙事的契合,实现表演者与舞台人物的共情,戏里戏外浑然一体,极大地延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小说“代言体”的叙事特征,以传统戏剧文化为底蕴,在小说人物与舞台人物、小说叙事与舞台叙事之间形成互文的结构,主角在舞台上演绎的生离死别、大起大落,与现实人物的荣辱悲欢相映照,形成互文关系,呈现出小说的蕴藉之美。
在“舞台三部曲”中,陈彦将戏曲唱词穿插于小说的叙事之中,丰富人物语言形式的同时又可在特定情境中代人物言说难以言表的复杂心绪。再婚的顺子迎来了难得的情感慰藉,哼唱戏曲《杨贵妃》唱词“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④将内心的欢愉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顺子再度的婚姻遭到女儿菊花强烈抵制,顺子为此身心俱疲,装台时他哼唱豫剧《清风亭》中《盼子》一折老生与老旦的对唱“老旦:非是为娘将儿怨,老生:你为何像流水一去不复还……”⑤以此排遣内心的苦闷。小说《主角》中一代名伶忆秦娥被养女宋雨夺取了主角的光环,内心涌起巨大的失落。小说叙事设置了一个虚实相间的场景,在古城墙上徘徊的忆秦娥吟唱苦音“主角是聚光灯下一奇妙,主角是满台平庸一阶高……”⑥将从艺之路的荣辱历数,深刻阐释主角光环下所承载的生命之重。小说通过戏剧唱词的形式对文本主题予以凝练和强化,小说结尾处意味深长的笔触增强了文本的审美蕴藉。
在戏剧中,“行当”是演员分工的类别,陈彦小说“行当”具有双重的含义。“行当”既是表演者的角色分工,又隐喻着小说人物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处境。“行当”决定着舞台人物的言行举止与命运走向,也映射着小说人物的现实生存状态。“行当”代言的是戏剧人特殊的生活体验,其中隐含着人物无法挣脱的宿命。小说《喜剧》中丑角贺加贝在舞台上极尽滑稽之能事,肆意夸张渲染只为搏观众一笑。而现实中的贺加贝为欲望所累,癫狂躁动,人生大开大合。台上台下上演一场场闹剧,皆是被他人所围观的“小丑”。小说在戏剧化叙事的背后,揭示喜剧与悲剧之间的辩证关系,喜剧在制造欢笑的同时,潜伏着悲剧的因子,二者相互转换,共同演绎着百态人生。小说中丑角的喜剧观,往往也是其内心价值观的折射。喜剧人贺加贝为了追逐利益,摒弃传统喜剧观,在所谓喜剧的革新中迷失了自我。戏外,他陷入畸形的情感追求中执迷不悟,上演了人生的荒诞剧。
透过戏剧的“行当”,小说言说的是作家深度的生命体验,是对于个体社会性存在的反思。小说《主角》中不同行当的戏剧演员皆以担纲主角作为自我价值衡量的标准,小说叙事围绕主角之争展开,在纷繁复杂的人事纠葛中,呈现人性深处欲望的复杂形态。只会下死功夫、无功利心的忆秦娥被推到前台,承主角之重的同时享主角之光环。而精于算计、步步为营的楚嘉禾却始终居于配角,这也导致她内心的扭曲与人性的堕落。小说《装台》中以顺子为首的特殊人群,以装台为生,依附于戏剧舞台来谋生,其装台的活计亦是戏剧的“行当”之一。小说的叙事围绕“装台”展开,将舞台生活与现实生活关联,在一次次看似重复的装台叙事中,深入呈现了装台人的现实生活图景。装台成就的是炫目的舞台艺术,幕后隐伏着社会底层人物生存的艰辛与沉重,小说对于城市边缘人群生活状态的观照,是作家深入体察生活,敏锐捕捉社会变化的体现。长久以来的戏剧生活积淀,促成了陈彦的写作选择,在最为熟悉的领域他的写作才情也得以充分的发挥。
二 叙事场景的戏剧化
亨利·詹姆斯作为小说戏剧化的倡导者,“提倡最大限度地降低作家的叙述声音,同时将作为完整有序的‘有机体’的小说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得阅读的过程与观看戏剧一样,具有直接的喜剧效果。”⑦对场景的描摹可以使读者获得与戏剧欣赏类似的直接性体验,增强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实现小说的有效叙事。
作为“喜剧人”的陈彦,在戏剧团体工作多年,对于戏剧舞台及相关的人事生活甚为熟悉,他的创作理念即是,作家一定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熟稔的生活经验构成了陈彦小说创作坚实的基础,反映在叙事层面即他对于小说中各类场景的叙述显得从容笃定、驾轻就熟,叙事自然流畅,一气呵成。小说《装台》中反复出现的装台场景,具象化呈现了装台人的生存状态。文本中装台活计的繁重、工时的紧迫,与装台人个体生活的境遇形成并行的两条叙事线索,相互交织又并行不悖。小说中每一次装台均像是进行一次战斗,时间紧、任务重,还要应对劳务费不能兑现的风险。每个行当皆有自身的门道,在顺子的带领下这个群体分工有序,配合娴熟,但是繁重的装台活计每次还是将众人的体力压榨的精疲力尽。为了生存,装台人的活计不能停歇,在“装台”与“找活”之间不断延续下去。顺子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即为叙事的节奏定了基调:“这几天给话剧团装台,忙得两头儿不见天,但顺子还是刁空,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了。”⑧新婚的顺子奔波于不同的舞台,整日熬夜装灯光、搬道具、布背景,痔疮犯了也硬顶着,直至晕倒。
亨利·詹姆斯认为小说创作应根据人物在不同环境中的意识活动建立“场景系统”,场景之间互为关联,展现小说“行动”的发展过程。⑨陈彦小说中的场景叙述,既有人物的生活场景,又有戏剧活动的场景,是人物在特定语境中意识流动的具象化展现,构建了小说多重的叙事空间,同时推动着小说的叙事演进。家庭生活是小说《装台》场景叙述的另一侧重点,也是造成顺子人生重负的另一源头。装台人的生活轨迹主要围绕舞台、家庭两个基点来展开,迫于生计时刻惦念装台的活计,在外操劳又为家庭事务所牵绊。小说中,顺子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外出装台任务繁重,处处为生计谋划,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家中女儿菊花对继母蔡素芬肆意谩骂,水火不容,一片狼藉。婚姻未能带给顺子稳定的家庭生活,反而激化了与女儿的矛盾。而顺子的一味妥协也导致了蔡素芬最终的离开。在装台场景与家庭生活场景的交错叙述下,小说的叙事逐步推进,“装台”所承载的城市边缘人生存主题不断被强化。结尾处菊花的返家,順子对于周桂荣母女的接纳,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装台”成为城市边缘人群的一种宿命,难以摆脱、无从化解。
小说中多次出现蚁群活动的场景,既有顺子视角的俯视静观,又有梦境中代入式的叙述,同时将人物对于现实人事的感触融汇其中,富有象征意义。“月光下,一支黑色大军,正以五寸宽的条形队列,从他家院墙东头翻进来……多数都用两个前螯,托举着比自己身体笨重得多的东西,往前跑着。”⑩顺子对于不知疲倦奔波的蚁群有着本能地怜惜,这与他生活中的劳碌状态向对应,不同的生命个体有着相同的生活轨迹。屡遭生活重创的顺子,在梦境中置身蚁群成为一只蚂蚁。顺子在装台活计中养成的谦卑性格与刻意讨好的举止在蚁群中格格不入,蚁群的行事风格与人类截然不同。有本事、努力干活的蚂蚁自然赢得同类的尊重与认可,绝无人群之中的龌龊与不公正。身处蚁群之中的顺子,他的诧异与不适折射出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异化与生存秩序的紊乱。现实生活中顺子靠劳动养家糊口,处于社会的底层,在人前从未挺直过腰杆,活得小心翼翼,唯恐得罪了领导影响到揽承装台的活计。劳动者不能通过劳动赢得尊重是顺子的悲哀与无奈,也是人类社会运行中的畸形现象。
蚁群在集体搬运庞然大物百足虫时呈现出忘我的协作精神,令顺子深受震撼,同时惭愧于自身的私心与狭隘的格局。蚁群在遭遇运输事故后,派出兵蚁沿途寻找伤员,对于同类的关爱诚挚、自然,坚持“继续找,一个都不能少”。11这样的情形使得现实生活中忍辱负重的顺子感动地流下了眼泪。蚁群与人类的两相对比,呈现出作家对于人性的深入思考和对于生命意义、价值的求索。奔走于生活底层的顺子并无内省的自觉性,作家通过对具有象征性的蚁群活动场景的叙述,将现实人事与形而上的人生诘问关联起来,构成了小说的隐喻性表达。
如果说生活场景是现实经验横截面的呈现,那么舞台场景的叙述无疑更加集中、典型,叙事视角也更加聚焦。小说《主角》中从小山村走出的忆秦娥,学艺之路崎岖坎坷,长期蛰伏之后终登上秦腔舞台一鸣惊人。小说中关于她演出场景的叙述,一步步见证了其艺术成长的历程,由县城的舞台到省城的剧院,再到首都的舞台,直至赴美国百老汇演出,其中的荣耀、光鲜与酸楚、艰辛并存。忆秦娥的艺术造诣在不同的舞台不断打磨提升,生活中她经历家庭变故、情感跌宕,人生体悟也日趋深入。小说叙事围绕“主角”这一主题展开,通过戏剧化的场景及纷繁复杂的现实人事揭示“主角”的深刻内涵。“主角”与“配角”相对而生,相互转化,并无绝对的主角与配角。人要找寻适合自身的位置,主角固然重要,但其价值的体现离不开配角的协作与团队的配合。广义而言,在艺术的舞台抑或人生的舞台,人人都是特定领域的主角,皆可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人生的价值,焕发出生命的光彩。
在舞台场景中,观众是重要的构成元素之一。演员与观众的互动,由观众反馈作出的调整,直接关系到舞台演出的成败。陈彦小说中对于观众观剧场景的描摹,与舞台表演有机地融为一体,二者相得益彰,共同营造出逼真的戏剧效果。在《喜剧》中,观众对于丑角的热捧使得贺家父子成为喜剧明星,一时风光无两。贺家贝为了追逐利益,留住观众,一味迁就观众的审美趣味,一再降低艺术表演的底线。丑角在舞台上趋势媚俗,以讨好观众为能事,丑态百出,严重折损了喜剧的艺术品质。台下观众沉迷于浅层的感官刺激,盲目跟风、哄抬,自愿放弃对于高雅审美的追求,助推了喜剧人艺术追求的堕落。喜剧人畸形的喜剧观构成了庸俗、芜杂的戏剧市场,也直接造就了浮躁、肤浅的喜剧观众。舞台场景的描摹使读者直面戏剧化的场景,更为集中的展现事件的矛盾冲突及复杂的人物关系,从而使文本具有典型化的特征,彰显小说的戏剧化艺术风格。
三 视点转换的多维度叙事
如果说场景化叙述呈现的是小说外在形态的戏剧化,那么人物视点的转换则是对人物内在心理戏剧化的透视。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戏剧化理论重视视点的选择,“将小说‘事件’的意义定位在人物的心理世界,并且采用故事中人物的眼光展现‘事件’在人物意识屏幕上投射的心理意义”12。在小说叙述中,作家通过不同人物视角的切换观照同一文学事件,深层次呈现人物的隐秘心理,同时实现对于事件的多重解读。
在“舞台三部曲”中,陈彦通过视点的转换呈现事件的丰富内涵及人物的深层心理。小说从不同人物视角去观照同一事件,形成叙事的并置,进而实现叙事空间的延伸。小说《主角》从不同人物的视点去观照“主角”的艺术之路,在重复性叙事中完成对于事件的多重解读。忆秦娥的奋斗史是小说叙事的主线,从艺道路上的勤学苦练成就了她艺术上的辉煌,从县剧团到省剧团她始终担纲主角。但是从楚嘉禾的视角来看,忆秦娥成名的背后伴随着她的“黑历史”,“真是一个表面颇似憨厚瓜傻,而内心却十分阴险狡诈的‘鸡贼女人’了。就这样一个女人,还总有男人飞蛾扑火,慷慨赴死”。13小说通过视点转换呈现“配角”对“主角”地位的觊觎及内心隐秘的复杂情绪,针对“主角”展开的角逐,呈现的是人性的欲望与自我认知的局限。楚嘉禾对于“主角”的渴求始终未能满足,导致其心理的严重失衡,乃至人性异化。由角色之争演变为对于忆秦娥个人的仇视,不惜以作践自身为代价抹黑对方,上演了一场人性的闹剧与悲剧。
小说通过视点转换形成并置叙事,也可辩证的观照事件,呈现事件内在的矛盾性。《喜剧》中史多芬主导的喜剧现代性创新,用电脑、数字模型计算喜剧的包袱、笑点,围绕观众的反应制造出爆炸性的喜剧效果。但是对于从乡村来到城市谋生的潘五福而言,面对这一新鲜事物毫无感觉,不能理解身边观众为何而笑,身处喧闹的剧场他竟然打着鼾进入梦乡。媚俗的喜剧表演迎合了观众庸常的审美趣味,营造了喜剧繁荣的市场假象,由潘五福的视点揭示了这一畸形的文化现象。不同的视点也呈现出不同喜剧观的碰撞与冲突,老一辈艺人火烧天注重艺德,强调从业者的尊严,认为丑角的演出要获得大众的共情,赢得观众的理解与尊重必须要为普通老百姓演出,与老百姓站在一起,在正经的舞台上演出,要有艺术的底线,不能沦为讨权贵欢喜的玩物。这也是陈彦本人戏剧观的体现:“戏曲这种草根艺术,从骨子里就应流淌为弱势生命呐喊的血液,如果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忘记了为弱势群体发言,那就是丢弃了它的創造本质和生命本质。”14小说中热衷于喜剧技术革新的史多芬,对于老艺人恪守的传统喜剧观不屑一顾,认为这是过时的陈旧思维,现代艺人应将知名度作为追逐的对象,要加强商业运作与包装,知名度可以为艺人赢得财富与尊严,赢得一切,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艺术观。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梨园春里你方唱罢我登场,镇上柏树不辞而别后王廉举崛起,王廉举被撬走后又请来了南大寿,南大寿被气走后又聘请了史托芬,传统喜剧被轮番折腾的面目全非,同时也上演着一出出人性的悲喜剧。不同视点背后折射出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喜剧艺术的时代传承交织着传统艺术观与现代艺术理念的抵牾与搏弈。
视点转换也可为小说叙事带来全新的视角,营造陌生化的阅读效果,强化小说的戏剧性。小说《装台》从装台人的视角观照戏剧艺术,看似褪去了艺术的光环,实则从别样的角度呈现了艺术的魅力。在顺子的视野里,戏剧行当里鱼目混杂,既有消极怠工、整日插科打诨度日的闲散人物,又有擅于经营、追逐名利的“成功人士”。所谓的艺术家们,在门外汉的顺子看来,其做派滑稽可笑、不可理喻,大师工作时助理紧跟左右侍候,其工作习惯是一边对光,一边摸炒黄豆吃,深夜工作时如若手头没有黄豆吃便会罢工。小说透过顺子的视点呈现装台人与戏剧人之间的隔膜,生活处境的差别与心理层面的距离造成二者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而顺子对于戏剧艺术却有着天然的亲近,劳作之余观剧成为其重要的人生慰藉,为其带来精神上的巨大满足。戏剧《清风亭》顺子看过无数回,里边的唱词都烂熟于心,但每一次他都是看得泪流满面。对于旁人的不解,他道出自身对于戏剧的朴素理解:戏剧的剧情是假的,但是其中的情感是真的。从顺子的视角观照戏剧,可以揭示出戏剧艺术何以能扎根民间、长久流传的原因所在。
小说中作为戏剧门外汉的顺子,通过戏剧舞台的浸染,竟然一步步触摸到艺术的本真感觉,在对艺术的逐渐参悟中升华了人生的境界。顺子等人在幕后的艰辛付出不为观众所知,却在戏剧演出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装台》与《主角》在创作主题上具有共同之处,均对于社会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进行辩证的思考。生活的舞台没有绝对的主角,身居幕后的人也在担当着特定领域的主角,装台看似在为他人做嫁衣,实则也是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人在成就他人的同时也在成就自我。在顺子对于戏剧艺术理解的前后变化中,小说叙事逐步推进,由表层进入肌理,由戏剧的舞台扩展至生活的舞台,人物的精神世界也次第向读者呈现。15无疑,陈彦在长期戏剧实践中孕育的艺术才情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其可以驾轻就熟地在小说与戏剧之间穿梭,为中国小说的现代性呈现做出富有深度和创造性的探索。
注释:
①张向东:《戏剧化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文学》,1998年第6期。
②陈彦:《从戏剧到小说》,《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1期。
③陈建森:《戏曲 “代言体”论》,《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④⑤⑧⑩11陈彦:《装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年版,第38页,第80页,第1页,第3页,第302页。
⑥13陈彦:《主角》(下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版,第1068页,第913页。
⑦⑨12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8页,第120—121页,第126页。
14陈彦:《现代戏创作的几点思考》,《中国戏剧》2011年第8期。
15钟海波:《论陈彦小说的戏剧化写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2021年第9期。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榆林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