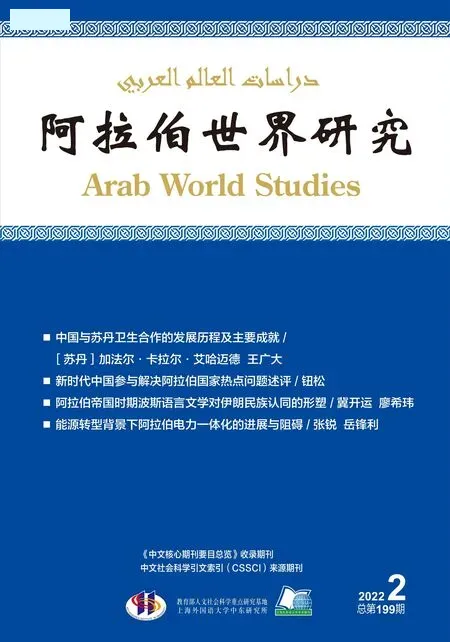阿拉伯帝国时期波斯语言文学对伊朗民族认同的形塑*
冀开运 廖希玮
民族身份或民族认同是民族内部成员对民族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等内涵的持续复制和重新阐释,以及带有这些传统和文化因素的民族共同体诸成员的个人身份辨识。(1)[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文化身份认同作为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两层含义:文化身份侧重于对外区分异己,文化认同则侧重于对内唤醒民族意识,凝聚民族向心力。在组成民族文化的诸多要素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宗教和语言,而语言相对而言又是更为外露的民族属性。(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园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因此,语言之于民族认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纵观当代的中东地区,许多国家都曾发生少数民族或部落的分裂叛乱,面临着“认同危机”的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伊朗借助波斯语言文学塑造民族身份认同的历史过程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国内学界涉及伊朗民族身份认同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近现代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阶段,(3)参见詹晋洁:《礼萨·汗时期(1921—1941)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路径选择与困境》,载《世界民族》2015年第2期,第1-12页;吕海军:《伊朗民族主义思潮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冀开运、母仕洪:《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认同的建构及启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4期,第19-35页;毕晓卉:《伊朗巴列维王潮的文化整合与民族建构研究》,西北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对于阿拉伯帝国时期波斯语言文学对伊朗文化身份转型和文化认同塑造的影响研究尚未深入(4)仅见于李彦军:《舒毕思潮与伊朗民族文化身份的重塑》,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地区研究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实际上,在伊朗民族(5)根据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历史上的“波斯人”是外界对于伊朗高原以及伊朗文化圈内全体居民的统称。因此,本文中的“伊朗人”与“波斯人”含义相同,“波斯语”即是指伊朗历代王朝版图内各民族的通用语。产生与演变的进程中,波斯语言文学一直是伊朗民族文化的缩影。阿拉伯帝国时期,伴随着阿拉伯人与伊朗人政治上的压迫与反抗、文化上的冲突与交融,波斯语言文学成为激发伊朗民族意识,塑造伊朗文化身份,回溯伊朗集体记忆的精神力量,不仅推动了伊朗由单一的琐罗亚斯德教文化向伊朗-伊斯兰双重文化身份的转型,而且维系了伊朗的民族文化认同。
一、 “舒欧比亚”——伊朗民族意识的觉醒
“舒欧比亚”(Shu’ubiyyah)一词是阿拉伯语音译,指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非阿拉伯裔穆斯林对阿拉伯人特权地位的反应,在伊朗表现为波斯释奴(6)亦称“马瓦里”,是阿拉伯人对皈依伊斯兰教的外族穆斯林的称谓,即获得人身自由的奴隶。恢复民族传统文化,反抗阿拉伯人入侵与统治的思潮,其主要以文化运动而非政治运动的形式表达(7)Roy P. Mottahedeh, “The Shuˈbyah Controversy and the Social History of Early Islamic Ir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7, No. 2, 1976, p. 162.,大约肇始于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一直持续至13世纪。
倭马亚王朝时期(661~750年),阿拉伯统治者将改宗伊斯兰教的波斯人称作“释奴”。根据伊斯兰教“穆斯林皆兄弟”的教义,波斯释奴与阿拉伯人原则上应当平起平坐,享有同等权利。但实际上,波斯释奴处于伊斯兰社会底层,被施以重税,受尽剥削和压迫。(8)李维建:《浅析“释奴问题”》,载《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3期,第67页。由于阿拉伯人文化水平相对落后,各类人才短缺,而波斯释奴中却有不少识文断字且博学多闻的文化精英,统治阶级“便利用释奴担任工艺、农业、教育、行政、翻译等活动”(9)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6页。,波斯精英因此得以广泛活跃于学术领域。但阿拉伯人并非真正赏识他们的才华,反而“对‘释奴’的才能深感不安,对他们施加种种压迫”(10)同上。,甚至蔑称他们为“阿贾姆”(11)意为“哑巴”,指母语不是阿拉伯语的人,后专指伊朗人。,将他们与“驴”“犬”视为同类。亡国的哀痛和身份的屈辱唤起了伊朗人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他们之中如巴尔马克家族、赛赫勒家族以及塔希尔家族等萨珊波斯的贵族精英(12)伊朗贵族精英指阿拉伯征服伊朗萨珊帝国后的有权有势的人,也包括精通中古波斯语,不忘前朝和文化传统的读书人或书吏。他们选择与阿拉伯帝国合作,但具有伊朗民族意识与情怀。们率先点燃了舒欧比亚之火,许多波斯诗人、学者和文人纷纷以代言人的身份围绕在他们周围。(13)转引自黄慧:《阿拔斯前期波斯文学对阿拉伯文学的影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言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4页。在这些波斯精英的支持下,舒欧比亚运动顺势而生。
直至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前期,仰仗以阿布·穆斯林(14)中世纪波斯呼罗珊农民起义领袖,阿拔斯王朝开国功臣,最终因功高震主而被谋杀。(Abu Muslim,718~755年)为首的波斯释奴在新王朝奠定过程中的突出贡献,波斯人逐渐从被统治者的身份中解放出来,进入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体系之内。随着波斯精英地位的提升和权势的增强,舒欧比亚运动迅速发展,文学创作领域成为舒欧比亚者的主要阵地。一方面,他们将巴列维语典籍翻译成阿拉伯语,借以向阿拉伯人展示波斯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又与阿拉伯人展开激烈论战,创作了大量带有舒欧比亚倾向的诗歌。
(一) 百年翻译运动
舒欧比亚者的积极作为首先体现在百年翻译运动中。这场声势浩大、以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宗旨的译介活动自阿拔斯时代兴起,持续百余年,是伊斯兰文化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出于巩固统治、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需要,萨珊王朝遗存的巴列维语著作首先受到阿拉伯统治者的重视,波斯人的治国经验与审美性情,是阿拉伯人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元素。在历代哈里发的重金聘请下,众多伊朗学者加入翻译活动中,将巴列维语著作译为阿拉伯语。在发掘和整理波斯古籍的过程中,伊朗精英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他们以伊朗人的身份为荣,将恢复古波斯文明视为己任,为伊朗民族文化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伊本·穆加发(Ibn al-Muqaffa,724~759年)是翻译运动中最负盛名且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波斯学者之一。伊本·穆加发生于伊朗西南部的法尔斯地区,早年是琐罗亚斯德教信徒,后改奉伊斯兰教。他自幼研习波斯文学,博览群书,著述颇丰,其中大多是对巴列维语典籍的译著,如以劝谏君王为主题的寓言故事集《卡里来和笛木乃》、波斯诸王的传记《帝王纪》、介绍波斯风俗习惯和典章礼仪的《阿伊拿玛》以及宣扬古波斯统治制度的《近臣书》等。伊本·穆加发译、著并重,擅于结合时代背景对译作进行重新解读和创新,将波斯思想文化传统的内涵置于伊斯兰风格的框架之下,使作品更加契合大众的审美情趣。在以伊本·穆加发为代表的波斯裔学者的努力下,浩如烟海的波斯古籍被翻译成阿拉伯文,源远流长的波斯古代文化由此植根于伊斯兰世界的沃土,使伊斯兰社会在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和文学风格上都趋于波斯化。关于波斯历史文献、文学著作、宗教经典的译著不仅深刻影响着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也使波斯文学的思想内容、形式体裁得以传承。
(二) 论战与诗歌创作
除了广泛参与译介活动之外,舒欧比亚者还与阿拉伯人展开激烈论战,以此宣扬舒欧比亚思想。他们主要分为两大派别:一派大力提倡伊斯兰教宣扬的平等主义,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不分高低贵贱。他们援引《古兰经》的经文与阿拉伯人进行论战,依据《古兰经》第49章第13节:“众人啊!我从一男一女创造了你们,且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shu’ub)和宗族,以便你们可以互相认识。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15)《古兰经》,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2页。以此说明真主对世界各族人民都一视同仁,阿拉伯人并非高人一等,只有坚定和忠诚的穆斯林才最值得敬佩,这实际上是波斯释奴对阿拉伯人统治的对抗和否定。
舒欧比亚者中的另一派则大肆贬低阿拉伯人,认为阿拉伯人是愚昧落后的游牧民族,在文明程度上远不能与伊朗人相提并论。他们用阿拉伯语创作诗歌,盛赞伊朗民族的荣光。波斯诗人白沙尔·本·布尔德(Bashar Ibn Burd,714~784年)在诗中愤怒地指责阿拉伯人,“你们的长袍怎能称之为衣裳?穿上这种袍子只配在荒野牧羊。你们的住处多么肮脏不堪,里面闷热,周围一片荒凉。”以阿拉伯人简陋的服饰与住处公然讽刺他们是尚未开化的野蛮人。与此同时,他还在题为《矜夸》的诗中夸耀自己的出身,“我是贵胄子孙,出身于望族名门:科斯洛(Khosrow,531~579年在位)是我的祖父,萨珊王是我的父亲。”(16)张鸿年:《波斯文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诗人以波斯血统和伊朗身份为荣,反复重申先祖的光辉业绩,言辞中流露出波斯诗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贾希兹·巴士里(Al-Jahiz al-Basir,776~869年)在《修辞与释义》一书中也记载了舒欧比亚诗人夸耀自己的民族,抨击阿拉伯人的场面。例如:“你们长期只能与骆驼交谈,所以你们的语言粗俗下流,你们的口音不堪入耳。”(17)黄慧:《阿拔斯前期波斯文学对阿拉伯文学的影响》,第4页。针对波斯诗人的这类攻击,阿拉伯人通常也以诗歌的方式进行反击。这些论战虽然有过激的方面,但客观上也增进了双方思想的碰撞与交融,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
萨珊王朝的覆灭并未导致波斯语言文化的消亡,以舒欧比亚者为代表的伊朗贵族精英功不可没。他们既是伊朗民族意识的先觉者,同时也是伊朗文化身份的建设者,使伊朗在阿拉伯文化的冲击下依然保存着自己的民族语言与文化传统。他们作为连接伊斯兰前后波斯语言文学的纽带,为伊朗文化注入了伊斯兰元素,为伊朗—伊斯兰文化身份的塑造奠定了基础。
二、 新波斯语的涅槃重生——伊朗文化身份的塑造
萨珊王朝时期,巴列维语(18)“Pahlavi”亦称钵罗钵语、帕拉维语,是中古波斯语的主要形式。是伊朗的行政、宗教和文学语言,其书面语形式相对固定,而口头语则随着交往传播不断变化,最后形成伊朗各地的方言,如巴列维语、达里语(19)亦称“新波斯语”,是现代波斯语的早期古典形式。关于达里语的起源学术界仍存有争议,一说其诞生于萨珊家族崛起的伊朗南部法尔斯地区。226年,萨珊王朝建立,达里语遂流行于萨珊宫廷所在地泰西封,“达里”即宫廷之意。277年,摩尼教创始人摩尼遇害,大批摩尼教徒逃往呼罗珊,达里语随之传播至东伊朗。651年,阿拉伯人攻占泰西封,萨珊末代国王耶兹德卡尔德三世逃亡伊朗东部,大批随从迁徙此地,进而巩固了达里语在呼罗珊的地位。另一种说法是达里语本就是呼罗珊的方言,被地方王朝萨曼宫廷采用后称为“达里波斯语”。、法尔斯语、胡泽里语等,它们被统称为波斯语。(20)Richard N. Fry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4: The Period from the Arab Invasion to the Saljuq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98.阿拉伯人入侵后,安息和萨珊时期的巴列维语文献典籍大多在战乱中佚失,巴列维语随之走向衰落。公元8世纪初,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阿卜杜·马立克(Abd al-Malik,724~743年在位)正式规定阿拉伯语为官方通用语,并且在强制推行阿拉伯语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伊朗民族语言的流行。在阿拉伯语浪潮的侵袭下,巴列维语逐渐消亡,达里语却在呼罗珊异军突起,不仅成就了伊朗灿烂辉煌的波斯文学,而且发展成为跨地区的文学媒介,对中亚、南亚以及阿拉伯世界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伊朗民族语言的涅槃重生。阿拉伯帝国时期达里波斯语的兴起具备以下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
(一) 中立的语言属性为新波斯语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达里波斯语本身不带有任何民族、宗教色彩。首先,达里波斯语在发展之初仅作为一门地区性的口头语言,不能代表伊朗民族的身份。早在萨珊王朝时期,伊朗各地就出现了与官方语言巴列维语并行的地方方言,达里语是其中一种。阿拉伯人征服伊朗时,巴列维语既是伊朗的民族语言,也是琐罗亚斯德教的语言,其独特的民族和宗教属性与阿拉伯语水火不容,自然成为阿拉伯统治者首要攻击的目标。在哈里发强制性的伊斯兰化政策下,许多巴列维语典籍被毁于一旦,巴列维语随之淡出伊朗人的生活,而达里波斯语作为口头语却仍在伊朗东部地区保有活力。
其次,达里波斯语不是宗教语言,不对伊斯兰教构成意识形态上的威胁。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呼罗珊的宗教信仰并不统一,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景教、佛教在呼罗珊都有信徒,这四大宗教都有较为发达的宗教文化,它们之间相互牵制,无一能在呼罗珊占据主导地位,其各自所代表的文字(分别为巴列维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和梵文)也无法在呼罗珊得到统一。(21)许序雅:《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20页。阿拉伯帝国时期,伊斯兰教的扩张和阿拉伯语的传播对呼罗珊原有的宗教语言构成沉重打击。以巴列维语为例,“琐罗亚斯德教徒一旦改宗伊斯兰教,往往就会弃巴列维语典籍于不顾而转身投向阿拉伯语经典。因为巴列维文字不但晦涩难懂,而且其本身便夹杂着对伊斯兰教的不忠。”(22)[伊朗]阿里帕夏·萨利赫:《伊朗文学史》(波斯文),德黑兰:阿米尔卡比尔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0页。随着呼罗珊的伊斯兰化,原有的宗教及其语言难以摆脱被取代的命运,统治范围不断缩小。因此在呼罗珊地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远不如大多数琐罗亚斯德教徒所聚集的法尔斯地区那么尖锐,(23)Richard N. Fry, “History of the Persian Language in the East (Central Asia),” Richardfrye, http://www.richardfrye.org/files/History_of_the_Persian_Language_in_the_East.pdf,上网时间:2021年10月8日。从而为达里波斯语的涵化与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在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的背景下,达里波斯语得以在夹缝生存的首要因素。
(二) 语言涵化与文字简化为新波斯语的推广铺平了道路
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阿拉伯士兵与波斯人的杂居状态加速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同化与融合的进程。随着阿拉伯语的广泛通行,波斯语与阿拉伯语相互碰撞、渗透,随之发生语言涵化。语言涵化属于变迁理论中的主要概念,指两种异质语言在长期的接触和交流中引起一方或双方原有语言发生改变的过程。其可能导致一种语言受主流语言的影响,或在结构和内容上发生变化形成混合语,或被主流语言逐步取代,丧失其自身的语言特质。语言的内部结构、使用频率和流利程度是语言涵化的关键性指标。(24)庄孔韶:《人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5页。在阿拉伯语的影响下,波斯语的书写体系、词汇和语法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涵化。波斯语的涵化过程具有以下特点。

第二,语音和语法的涵化程度较低。阿拉伯语在语音和语法方面并未对波斯语造成太大影响。语音方面,受阿拉伯语外来词的影响,新波斯语的音素与巴列维语相比有所增加,其中最独特的新音素是声门塞音,它起源于两个阿拉伯语音素,“hamza”和“ayn”。(29)Stefan Weninger, The Semitic Language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p. 1019.这两个音素的存在使波斯语中的阿拉伯语借词具有高度的可识别性。语法方面,新波斯语的语法体系基本上与巴列维语一脉相承,受阿拉伯语的影响较小:句法上,阿拉伯语属于VSO(30)即动词(Verb)+主语(Subject)+宾语(Object)的语序类型。语言之列,而波斯语仍然遵循SOV语序;词法上,阿拉伯语对波斯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构词法的规则方面,比如复数的规则与不规则变形,单词的派生法等。(31)Stefan Weninger, The Semitic Language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p. 1019.总的来说,由于伊朗人在日常生活中依旧频繁使用波斯语进行交流,波斯语的语音、语序、语法的等核心特质得以较好地保留,基本结构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第三,具有包容性。阿拉伯人的入侵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伊朗各民族的融合,因此波斯语的涵化过程并非只受到阿拉伯语的影响。以达里波斯语为例,其不但吸收了大量阿拉伯语词汇,而且在留有个别巴列维语成分的同时还融合了少量粟特语的特征,由此催生出一种伊朗东部方言与阿拉伯语混合下的“克里奥尔语”。(32)克里奥尔语是一种“混合语”,泛指混合并简化而生的语言,由皮钦语加上文法演变而来。参见陈满华:《从威廉·琼斯的著作看古波斯语及其与周边语言的接触、融合史》,载《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55页。新波斯语的包容性特征使其在伊朗东部拥有广泛的受众,成为萨曼王朝将其选作官方通用语的原因之一。
总体来看,语言涵化既是历史发展和文化交融过程中难以规避的自然现象,也是群体内部自主调整以适应外界环境的过程。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阿拉伯语与波斯语的关系既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也不是平行独立的共存关系,而是持续且积极的互动关系。在伊朗人对阿拉伯语和巴列维语有选择地扬弃与更新中,新波斯语的书写体系发生颠覆式变化,但语言的基本结构和核心特质得到较大程度的保留。经简化的波斯文字是典型的表音文字,不仅便于识读、书写,而且有利于广泛传播,为萨曼王朝的语言统一和文学繁荣埋下了伏笔。
(三) 纸张的运用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新波斯语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因地处中亚的特殊区位,呼罗珊曾经既是中原与西域兵戎相见的战场,也是东西贸易、文化交流的枢纽。公元751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军与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交战于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唐军兵败,战俘中恰有不少造纸工匠。阿拉伯将领齐亚德·伊本·萨里(Ziyad ibn Salih)将他们押解至怛逻斯附近的撒马尔罕,利用他们娴熟的造纸工艺,在这里建造了阿拉伯帝国的第一座造纸工场,(33)转引自[伊朗]阿赫玛德·达斯图旺:《伊斯兰时期纸张和造纸术的演变》(波斯文),载《历史研究》2019年第23期,第22页。造纸术由此传入波斯。有学者推测,纸的波斯语名称“卡噶兹”(kaghaz)很可能就来源于回鹘语的“卡伽斯”(kagas)。(34)[伊朗]巴赫拉姆·雷扎伊:《造纸历史》(波斯文),德黑兰:文化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至8世纪后期,撒马尔罕已成为阿拉伯帝国最重要的造纸中心,“撒马尔罕纸”不仅能供应呼罗珊地区的需要,而且成为大宗贸易品远销阿拉伯帝国各地。10世纪中叶,“撒马尔罕纸”成功取缔莎草纸,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通用的书写工具。阿拉伯史家萨阿里比(Thaalibi,961~1038年)曾赞美道,“欲举撒马尔罕之名产,则惟有纸。撒马尔罕纸因其美观、便利、平滑,已取代埃及之苇纸与羊皮之书卷……此物仅产于撒马尔罕及中国。”(35)罗新:《撒马尔罕纸》,载《读书》2020年第3期,第154页。与莎草纸、羊皮纸相比,中国发明的纸张造价低廉,质地轻软,平滑耐磨,极大地满足了文化创作与传播的需要。
纸张的量产助长了抄书的风气,呼罗珊的图书数量与日俱增,书店、图书馆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遍及皇宫、清真寺、学校甚至私人宅邸各处。事实上,这些图书馆是集藏书、翻译、研究于一体的学术机构,不仅馆藏丰富、种类齐全,涵盖天文、医学、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等各类书籍,而且布局合理,管理严密,具备较为完整的知识传播体系。一是目录按类编制,一目了然。各学科书籍分别放置于不同的书架,书侧还标注有书名、作者、书籍编号等关键信息,便于读者查找。此外,不少图书馆还附设演讲厅、辩论厅和展览厅,为学术研讨活动提供便利。二是借阅制度宽松,程序便捷。此时的图书馆不再只是贵族、学者私人藏书的场所,也对外界开放。借阅人只需经过图书管理员的许可签署借阅本即可借阅书籍,普通人曾经难得一见的书籍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三是馆员人数众多,分工明确。图书馆馆长大都由著名学者、诗人担任,终身从事学术工作。馆内还雇有专门的抄写员、图书管理员、警卫员等工作人员,负责维系图书馆的日常运作。
如果说发达的图书馆事业为学术活动提供了便利的外部条件,那么伊朗人对知识的热衷便为波斯语的复兴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伊斯兰教在呼罗珊广泛传播后,随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治学之风盛行。伊斯兰教崇尚科学,鼓励求知。在圣训中就有诸如“求知,须始自摇篮,终于坟墓”;“求知是每个穆斯林的天职”;“谁踏上求知的道路,真主已使他踏上直达乐园的坦途”等教诲,充分证明了伊斯兰教对求知的重视。伊斯兰教所提倡的求知并不仅仅局限于宗教知识,而是包含所有有益于人类发展的学科。在这些至理名言的影响下,众多伊朗穆斯林以治学为追求,视书籍如珍宝,共同推动了波斯语的复兴。
怛逻斯之战掀起的蝴蝶效应推动了呼罗珊地区造纸术的兴起,进而影响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繁荣。在阿拔斯王朝的落日余晖中,一场由此带来的令阿拉伯人望尘莫及的文化运动席卷而来,不仅保存了波斯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振兴与传承了伊朗的民族语言,成就了达里波斯语的“黄金时代”。
(四) 地方王朝的资助和诗人学者的创作为新波斯语的繁荣提供了保障
随着阿拔斯王朝在伊朗政治势力的衰落,伊朗人开始建立起地方王朝,它们名义上仍臣服于哈里发,实际上已逐渐脱离了阿拉伯帝国的控制。这些独立、半独立政权不仅在政治上进一步瓦解了哈里发的统治基础,推动了伊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文化上也对语言统一和文学创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促进了波斯语言文学的复兴。
伊朗土著王朝萨法尔王朝(867~1002年)和萨曼王朝(874~999年)统治者对恢复伊朗传统文化和鼓励波斯文学创作的贡献最为突出。萨法尔王朝的创立者亚古伯·列斯(868~878年在位)虽出身于工匠世家,却自称是萨珊王室的后裔。据《锡斯坦史》(著于11世纪)记载,当亚古伯征服赫拉特时,他的侍从穆罕默德·本·瓦西夫(Muhammad b. Vasif)向他进献阿拉伯文赞歌,然而未曾受过教育的亚古伯听不懂阿拉伯语,便鼓励瓦西夫用伊朗地方方言进行创作。(36)[美]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李铁匠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74页。此后,萨法尔王朝的宫廷诗人们纷纷效仿,波斯语诗歌的体例和主题渐成定规,为波斯语言文学的复兴开辟了方向。
萨曼王朝是继萨法尔王朝之后兴起于伊朗东部的地方王朝,公元874年建立,定都布哈拉,统治范围囊括呼罗珊和中亚河中地区。萨曼王朝的艾米尔出身于德赫干(37)萨珊王朝贵族中的最低等级,但在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后,贵族各等级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德赫干成为一个通用类别,指代伊朗各等级的贵族。参见Edmund Hayes,“The Death of Kings: Group Identity and the Tragedy of Nezhād in Ferdowsi’s Shahnameh,” Iranian Studies, Vol. 48, No. 3, 2015, p. 370.家族,自称是萨珊君主巴赫拉姆·楚宾(Bahram Chobin,590~591年在位)的后裔。受萨法尔王朝的影响,萨曼人也开始使用波斯语。他们援引《古兰经》的经文,“真主不会向人们派遣不说自己语言的先知”,认为世上的国王和先知从阿丹到伊斯迈伊尔时代都说波斯语,而真主传授的《古兰经》之所以为阿拉伯语,是因为先知穆罕默德是阿拉伯人,那么伊朗国王自然也就应该说波斯语。(38)Behrooz Mahmoodi-Bakhtiari, “Planning the Persian Language in the Samanid Period,” Iran & The Caucasus, Vol. 7, No.1/2, 2003, p. 253.萨曼人的语言意识为波斯语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他们中的文化精英普遍认为,“保护民族语言不受外来冲击有多种方法,比如编纂完整的词典,发展散文、诗歌等文学,建立学院,培养有才能的文人等,而民族意识是促成这一伟大文化运动的最关键因素。”(39)[伊朗]穆罕默德塔基·巴哈尔:《风格鉴赏》(波斯文),德黑兰:燕子图书出版社1970年版,第21页。萨曼王朝统治者将继承前伊斯兰时期的伊朗身份,坚守伊朗民族属性视作自身统治正统性、独立性的来源。出于团结民心、凝聚民族向心力的政治目的,也出于促进沟通交流的现实因素,萨曼统治者就地采用当地居民用于日常交流的达里波斯语作为宫廷官方用语,试图通过语言认同推动文化认同乃至民族认同。
第一,通过语言规范树立语言身份。萨曼王朝对语言认同的塑造首先体现在对语言标准形式的规范上,具体包括正字法的规范、专业术语的整合以及词典的编纂等。为完成这一任务,萨曼王朝统治者招贤纳士,网罗各地的文化精英,给予丰厚的赏赐鼓励他们用达里波斯语进行科学文化创作,致使这一时期汇聚萨曼宫廷的诗人达上百位之多。当时的布哈拉曾被称作“光荣之家,帝国之庙堂,君权之卡巴(天房),当代名人会集之地”(40)Edward G. Browne,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Vol. 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8, p. 365.。在萨曼王朝开明的政治宗教环境、自由的学术氛围之下,伊朗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学者,波斯文学创作蔚然成风,各类学术著作层出不穷,谱写了波斯语言文学史上的光辉一页。
鲁达基(Rudaki,859~940年)是萨曼王朝第三代艾米尔纳赛尔时期(914~943年在位)的宫廷诗人,相传其一生创作的诗歌多达百卷,被誉为“波斯诗歌之父”和“诗人中的阿丹”。(41)哈全安:《伊朗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06页。鲁达基最卓越的成就是将《卡里来和笛木乃》从阿拉伯语译为达里波斯语,并将其诗体化。虽然鲁达基生活的时代距离伊斯兰教传入伊朗已过去200余年,但在他的诗中不仅看不出伊斯兰教的影响,反而能看到琐罗亚斯德教“善思、善言、善行”思想的痕迹。(42)张鸿年:《波斯文学史》,第41-42页。诗人塔吉基(Daqiqi,935~977年)为萨曼王朝效力时正值第七代艾米尔曼苏尔·本·努赫(961~976年在位)当政。塔吉基不仅不信仰伊斯兰教,而且对外来宗教和外国统治者极其反感,他不无自豪地作诗宣称自己的琐罗亚斯德教信仰:“这世上的事物万种千般,我只把四宗挑选……和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43)同上,第47页。塔吉基曾奉命创作诗体《列王纪》,可尚未写成便死于非命,他所开创的波斯史诗传统后由菲尔多西继承。菲尔多西(Ferdowsi,935~1020年)出身于呼罗珊图斯的德赫干贵族家庭,通晓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巴列维语。为发扬波斯民族反抗外族统治与压迫的历史传统,菲尔多西广泛收集历代伊朗国王的传说和英雄事迹,耗时40余年创作《列王纪》,这部伊朗民族的伟大史诗几乎用纯波斯语词汇写成,其中不乏反对外族侵略与统治的思想。以鲁达基、塔吉基和菲尔多西为代表的波斯诗人笔耕不辍,不仅向大众宣扬了舒欧比亚思想,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波斯语的内涵,提升了波斯语的地位。
除文学作品外,历史、地理、医学等著作也相继出现。比鲁尼(Al-Buruni,973~1048年)和伊本·西拿(Avicenna,980~1037年)作为这一时期最高产的科学家,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科学文化遗产。他们虽然大多使用阿拉伯语写作,却强烈抵制存在于波斯语中的阿拉伯语词汇,并创造了许多与之等同的达里波斯语词汇,实现了波斯语的旧词新用。(44)冀开运:《中东国家语言政策与实践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8年版,第104页。伊本·西拿创造了千余个医学和自然科学词汇,比鲁尼也在其著作中创造了许多关于几何、代数和天文学的术语。(45)Behrooz Mahmoodi-Bakhtiari, “Planning the Persian Language in the Samanid Period,” p. 258.这些术语不仅在当时被广泛采纳,有部分甚至沿用至今。
随着科学文化创作的繁荣,达里波斯语的词汇和表达亟需统一,词典编纂学应时而生。现存最早的达里波斯语词典(Loghat-e Fors)由阿萨迪·图西(Asadi Tusi,1010~1072年)主编,成书于1050年左右。(46)Brian Spooner and William L. Hanaway, Literacy in the Persianate World,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p. 85.词典的内容大多是对日常生活各领域的常规词汇以及新兴科学文化术语的解释,而词典的分类与布局则是以萨珊王朝的巴列维语词典为蓝本。此时的波斯语词典按主题而非字母归类,更像一部伊朗百科全书。词典的编纂和词汇的系统化表明达里波斯语已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科学文化领域的成熟语言,波斯语相较于其他语言的优势得以凸显。
第二,通过语言推广促进语言认同。萨曼王朝为推广波斯语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政策。除奖赏机制外,统治者还发布了关于强制使用波斯语的诏令。在一份授权用波斯语写成的法令中,萨曼王朝当局明确宣布:“在这里,在这个地区,语言是波斯语,这个王国的诸位国王是波斯国王。”(47)[美]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第77页。阿布法兹尔·伯勒阿米(Abulfazl Balami)任伊斯迈伊尔时期(Ismail,874~907年在位)的宫廷大臣时,曾下令所有的行政文书均用波斯语书写,类似的政策至伽兹尼王朝(962~1186年)和塞尔柱王朝(1037~1194年)时期仍在沿用。(48)Behrooz Mahmoodi-Bakhtiari, “Planning the Persian Language in the Samanid Period,” p. 260.实际上,出于对哈里发形式上的服从以及对外交往的需要,萨曼王朝仍保留了阿拉伯语官方语言的地位,将其作为第二语言和外交语言。在哈里发的统治体系内,波斯语也被作为行政管理和科学人文学科的补充语言,与阿拉伯语建立了某种程度上的伙伴关系。(49)Brian Spooner and William L. Hanaway, Literacy in the Persianate World, p. 73.与阿拉伯语相比,达里波斯语在社会上的推广较为容易。由于波斯语本就是当地居民的母语,人们对达里波斯语的接纳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出于沟通交流的需要,许多阿拉伯人也自觉学习和使用波斯语。萨曼王朝对语言认同的塑造耗时不长却成效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元9~10世纪时波斯语已取代阿拉伯语,重新成为呼罗珊、河中地区乃至整个伊朗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
在伊朗地方王朝和波斯诗人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波斯语重新焕发出活力,大量的文学瑰宝和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延续和发扬。在被阿拉伯人统治的两个世纪后,波斯文化不仅没有被阿拉伯文明的浪潮所淹没,反而从中脱颖而出,独放异彩。萨曼王朝末期,以波斯语为纽带的伊朗—伊斯兰文化共同体已初具雏形。随着王朝的更迭,相继入主伊朗的突厥人、蒙古人和土库曼人都成为了波斯模式的继承者,将波斯语和伊朗—伊斯兰价值观延续了下去,使波斯文化历久弥新,成为伊朗不可分割的民族属性。
三、 《列王纪》——伊朗集体记忆的回溯
阿拉伯人的入侵使伊朗人面临严重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重塑伊朗人的集体记忆、维系民族身份认同成为伊朗民族的当务之急。异族统治之下,前朝遗存的波斯古籍和民间传说故事成为伊朗人集体记忆的重要来源。“同一时期有多人创作关于波斯帝国光荣历史的题材,这是舒毕思潮与伊朗的修史传统相结合的明证。舒毕思潮给帝国古老的历史注入了新的生命,使这一时期创作出的《王书》带有强烈的反抗异族侵略的色彩。”(50)[伊朗]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张鸿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3页。菲尔多西以巴列维语的伊朗正史《帝王纪》为蓝本,以各地搜集来的民间传说为主要资料,耗时40余年将伊朗人对前伊斯兰时期伊朗的记忆碎片整合成《列王纪》这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使其通过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两种形式重构和传承了伊朗人的集体记忆。
(一) 书面文学
《列王纪》卷帙浩繁,全长6万联,主要叙述了从开天辟地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入侵之前伊朗国王和英雄勇士的传奇轶事,从神话传说、勇士故事和历史故事三个部分再现了前伊斯兰时期伊朗历史、文化和宗教的集体记忆。《列王纪》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是伊朗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而且在艺术创作上也取得了高度成就。其艺术特色和思想内涵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思想架构上,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菲尔多西具有萨珊王朝德赫干贵族后裔和伊斯兰教什叶派信徒的双重身份背景,这一特点似乎就决定了他在撰写《列王纪》时需要在前朝的集体记忆与伊斯兰框架下的世界观、价值观之间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平衡。因此,“菲尔多西在琐罗亚斯德教遗产和已经开始取代它的伊斯兰文化政权之间走了一条折中的道路。”(51)Ken Seigneurie, A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19, p. 5.在《列王纪》的序言部分,包含菲尔多西对真主的颂词、对四大哈里发的赞颂。在正文部分,菲尔多西刻意弱化了对琐罗亚斯德教起源的描述,并将重心放在了对伊朗国王与民族英雄的世俗故事的叙述上,从而避免对伊斯兰教构成意识形态上的威胁,保证成书后传播的畅通。《列王纪》的思想架构体现出两种宗教观点的杂糅。在关于世界起源的叙述中,天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形象虽源自琐罗亚斯德教,但它被塑造成唯一的神,这显然与伊斯兰教的一神论创世观相契合。与此同时,琐罗亚斯德教中最为核心的“善恶二元论”思想又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列王纪》的叙事中,从神话部分人与恶魔的对抗,到勇士部分伊朗人与图兰人之间的战争,都是善恶对立的体现。即便菲尔多西刻意模糊善恶的界限,使人魔混为一体,我们依然可以从个体的思想矛盾中感受善恶元素的斗争。菲尔多西选择以两种宗教观来构建伊朗的民间传说、神话和历史叙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伊朗与伊斯兰文化的妥协与融合。
第二,在故事情节上,反映伊朗民族自豪感。菲尔多西不仅从正面颂扬了伊朗历代国王的文治武功和英雄勇士们忠于祖国、保卫祖国的伟大业绩,而且通过描写异族暴君的苛政与残暴,使《列王纪》增加了反抗异族统治的色彩。其中最精彩的诗章当属铁匠卡维率众起义和英雄鲁斯塔姆英勇杀敌的故事。铁匠卡维是伊朗平民百姓的代表。当时阿拉伯族人祖哈克受恶魔安哥拉曼纽引诱,弑父称王,入主伊朗。他因与恶魔勾结,双肩长出两条毒蛇。为安抚毒蛇,每日需供上两颗人脑。卡维共育有18个孩子,其中17个均已葬身蛇腹,无奈之下,卡维请求国王给他留下最后一个儿子,国王却提出条件,让他以此证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忍无可忍的卡维扯下皮围裙以长矛挑起,作为旗帜率领百姓起义反抗,推翻祖哈克的统治。鲁斯塔姆则出身伊朗贵族。他忠诚勇敢,对伊朗国王的忠心矢志不渝。国难当头,他率军杀敌;国王有难,他舍身相救。每次对抗外敌时总有鲁斯塔姆的身影,而每当他出现,伊朗必将化险为夷,克敌取胜。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上,菲尔多西以伊朗为善,以外族为恶,认为伊朗是世界的中心(52)伊朗古代有天下七国的说法,即伊朗居天下之中,此外还有西方、东方、东南、西南、西北和东北六国。,伊朗民族优于其他民族,体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第三,在人物刻画上,去英雄人物之神性。《列王纪》中几乎不存在绝对的英雄主义,没有一个英雄人物是完美无缺、无可挑剔的,几乎每个人物都有一定的道德缺陷,即便伊朗国王也是如此。以《列王纪》中着墨最多的勇士形象,鲁斯塔姆和埃斯凡迪亚尔为例。他们是最为经典的两大悲剧人物。鲁斯塔姆一向以忠心报国、胸怀宽广、深明大义的正面形象示人,却在与苏赫拉布的战斗中暴露出性格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阴暗面。苏赫拉布是鲁斯塔姆素未谋面的儿子,由鲁斯塔姆与萨曼冈公主所生。苏赫拉布长大后,为追寻父亲的脚步,执意率兵进攻伊朗,立志推翻伊朗当朝国王卡乌斯,立父亲鲁斯塔姆为王。父子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却丝毫没有认出对方。儿子首先将父亲打倒,鲁斯塔姆却以君子不杀第一次打败的对手为由躲过一劫。待再次战斗时,鲁斯塔姆抢占先机,却没有信守诺言,最终酿成杀子悲剧。埃斯凡迪亚尔是伊朗国王戈什塔斯帕之子。他与鲁斯塔姆一样英勇无畏,坚毅果敢,但与此同时他也自恃功高,权欲心切,急于登上父亲的王位而去挑战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因此丧命。菲尔多西所刻画的世俗民族英雄不同于宗教中予以神化的英雄形象,它们虽然建立在菲尔多西对前伊斯兰时期英雄的共同记忆和崇敬之上,却有着复杂多变的性格特征。对人性的真实描绘使《列王纪》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也更能引起读者的共情。
第四,语言表达优美、朴实、流畅。《列王纪》是以优美流畅的达里波斯语写就的。与菲尔多西同时代的诗人虽然也用达里波斯语写作,但他们的作品多为短篇散章,不论是从思想内涵上,还是语言表达上,都不足以与《列王纪》相媲美。《列王纪》不仅规模宏大、故事生动、思想深刻,而且用词纯粹。正如菲尔多西在诗中所说,“我三十年辛劳不辍,用波斯语拯救了伊朗。”菲尔多西有意运用纯波斯语词汇写作,与同时代其他诗人相比,他使用的阿拉伯外来词相对较少。(53)Ken Seigneurie, A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p. 3.据调查,在阿拉伯语词汇大量进入波斯语的情况下,《列王纪》六万联的诗句中只含有大约8.8%的阿拉伯语词,出现频率约为2.4%;而同时代诗人昂苏里(?~1039年)创作的诗歌则分别为32%和17%。(54)Brian Spooner and William L. Hanaway, Literacy in the Persianate World, p. 79.诗人伊本·亚明(?~1367年)曾这么赞扬菲尔多西对波斯语的贡献,“语言已经从宝座跌落平地,他重又把语言安置在宝座里。”菲尔多西有意清除阿拉伯词汇的举动,不仅是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的表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阿拉伯语的侵扰,维护了达里波斯语作为民族语言的地位。此外,菲尔多西在诗中大量使用对话体,通过人物的交谈、劝喻、书信和辩论等形式,直接引用他们之间的对话,在使语言更为生动活泼、形象传神的同时也有助于《列王纪》作为口头文学形式的传播。
(二) 口头文学
集体记忆不仅可以通过书籍保存,还能以口述的方式延续。口述传统在伊朗有着悠久的历史,是自古就在伊朗宫廷与民间广泛流行的表演形式,是继承与传播伊朗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菲尔多西所处时代,由于印刷技术尚未发展,《列王纪》手抄本的传播范围又十分有限,通常只有王公贵族能够收藏,且容易佚失,因此在民间,《列王纪》通常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播。
口述艺术的表演形式因时代、地域和政府的政策各异。比如在萨珊王朝时期,这样的演出更盛行于皇室,且往往与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相结合。但在阿拉伯人入侵伊朗之后,受伊斯兰宗教法令的压制,口述传统中的音乐与舞蹈元素被迫革除,表演者只得借助各种特殊的演出技巧丰富表演层次,营造氛围感,将《列王纪》中的英雄主义和民族意识更好地传递给观众。
萨法维王朝(1501~1736年)建立之后,伊朗的口述传统基本以吟诵(Shahnameh-Khani)和纳卡利(Naqqali)两种艺术形式固定下来。这两种艺术在表演形式上有明显区别。吟诵通常在正式场合中演出,要求表演者确切地吟唱《列王纪》中的原文诗句,因此观众需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才能够欣赏。而纳卡利则是一种戏剧化的叙述方式,其特色是一人演出。表演者纳卡尔往往一人分饰多角,用特殊的声调、表情、手势和动作讲述《列王纪》中的故事情节。例如,在叙述英雄故事时,纳卡尔会通过踱步、拍手、跺脚等各种各样的肢体动作来营造紧张氛围,结合特殊的发音技巧,包括停顿、颤音、长音、重音、叫喊等抑扬顿挫的语调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必要时,他们还会不停地重复某个词语以表示强调。为了更加生动形象地再现故事情节,有些纳卡尔还会铺设相关故事的画卷作为舞台背景布,演出时还会身着戏服,如伊朗古代的头盔或战甲,来帮助重现故事中一些战斗场面。有时纳卡尔还需演奏古典乐器,边说边唱,用传统音乐渲染氛围。(55)Mitra Jahandideh and Shahab Khaefi, “The Most Important Performing Arts Arisen from Shahnameh of Ferdowsi: Shahnameh-khani and Naqqali of Shahnameh,” Journal of the Indiana Academ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6, No. 2, 2017, pp. 83-85.因此,纳卡尔必须熟悉伊朗民间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他们需要熟读《列王纪》、精通伊朗历史和传统音乐的演奏,甚至要熟练掌握地方方言,为此他们需要具备一定的表演天赋、超强的记忆力、即兴发挥的能力以及吸引观众的能力等等。正因如此,纳卡尔被认为是伊朗民间故事、民族史诗和传统音乐的传承者与守护者。与纯粹的吟诵相比,纳卡利的受众更广,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生动传神的表演深受伊朗平民百姓的喜爱。时至今日,纳卡利都是伊朗各大茶馆、咖啡馆、“力量之屋”和家庭聚会的固定节目,成为了伊朗人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这种形式的表演,伊朗的普通人也能对丰富而灿烂的波斯文学艺术有更深入的了解。
总的来说,伊朗的口头文学是一门雅俗共赏的艺术。通过口述传统,《列王纪》渗透到了伊朗各个社会阶层的意识之中,成为伊朗民族精神的支柱。不仅在王朝宫廷中有《列王纪》的诵诗人,民间的市井茶楼也都把演出《列王纪》作为日常节目。《列王纪》既是伊朗文化的百科全书,也是伊朗民族的集体记忆。作为异族统治下舒欧比亚思想与达里波斯语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为伊朗民族语言的传播和波斯文学的复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抵御文化侵略,维系民族身份,强化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四、 余论
阿拉伯人的入侵使伊朗陷入身份认同危机。此时,对于广大伊朗平民百姓而言,民族仍然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伊朗贵族精英作为民族意识的先觉者,率先举起舒欧比亚的大旗,他们以波斯语言文学为武器,一方面推动了舒欧比亚运动的兴起,将波斯元素注入伊斯兰文化之中,引领着伊朗人抵抗阿拉伯文化的侵袭;另一方面又促成了波斯语言文学的复兴,使波斯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重构了伊朗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在此背景下,以琐罗亚斯德教文化为根基,伊斯兰教文化为血脉的伊朗文化身份初具雏形。
阿拉伯帝国时期既是波斯语言文学的滥觞,也是伊朗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分水岭。中世纪的伊朗虽然在政治上支离破碎,呈现分裂状态,且常年屈居异族统治之下,但文学艺术的辉煌却始终将伊朗联系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文化共同体,为此后的波斯文艺复兴以及萨法维时期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对后世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萨法维王朝(1501~1736年)时期,为了便于统治疆域辽阔的广大地区,统治者采取了波斯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混用的多语制度,以波斯语作为帝国行政用语、宗教教学用语,形成了以波斯语为主,少数民族语言为辅的语言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民族的融合,波斯语的主体地位被广泛接纳,土库曼语、蒙古语等少数民族语言逐渐退出“核心地带”,伊朗呈现出以波斯语言文学为纽带的多民族大一统局面。
随着伊朗步入近现代时期,统治者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进一步意识到统一语言对提高人民对国家忠诚度的重要性,语言问题开始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恺加王朝(1779~1921年)末期,伊朗首相穆罕默德·阿里·福鲁吉(Mohammad Ali Foroughi)提倡以温和的手段宣传波斯语言文学和文化,使波斯语自然地同化少数民族语言,实现各族人民对国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56)Mehrdad Kia, “Persian Nationalism and the Campaign for Language Purificati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4, No. 2, 1998, p. 25.1906年,伊朗第一部宪法将波斯语确定为国家唯一的官方语言,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波斯语的国语地位。巴列维王朝(1925~1979年)时期,为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打破各族群间的文化隔阂,礼萨汗和巴列维国王将波斯语言文学作为实现民族认同的支柱,一方面大力发展波斯语纯洁运动,成立“波斯语言协会”清除波斯语中的阿拉伯词汇(57)冀开运:《中东国家语言政策与实践研究》,第101页。;另一方面强制推行波斯语单语政策,命令所有的政府官员和国家机构都应使用波斯语作为管理日常事务与沟通交流的语言,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使波斯语在行政、司法、教育等领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巴列维王朝还通过波斯语言文学塑造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以考古活动、文物展览和戏剧表演等形式不断强化现代伊朗与古代波斯的历史联系,借此促使伊朗各族人民形成广泛的国家认同。
时至今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依然延续着波斯语的核心地位,支持波斯语言文学的发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15条明确规定,“伊朗人民通用国语是波斯语,官方文件、书信和教科书应使用波斯文书写。”该条款再次证明了波斯语作为国语的重要性和优越性。作为一个拥有多民族、多语言的中东大国,波斯语是伊朗民族团结与稳定的黏合剂。波斯语言文学的地位通过伊朗历朝历代的不断巩固,如今已深深植根于伊朗人民的心中,成为伊朗人民身份认同的核心依据,伊朗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的关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