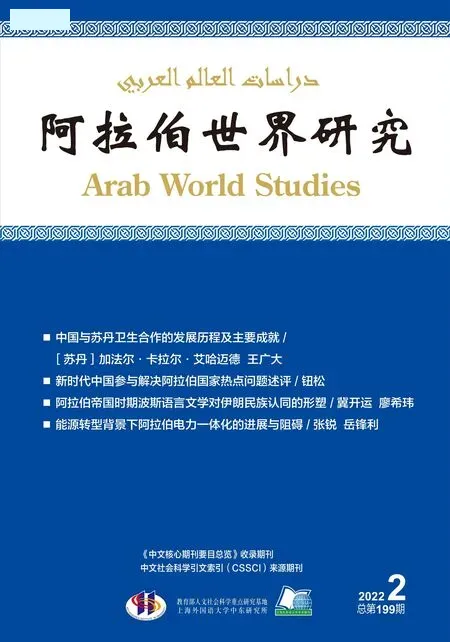伊斯坦布尔寮屋区选民与土耳其繁荣党的崛起*
丁雨婷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开启了新一轮城市化浪潮。在城市边缘地带形成的规模庞大的寮屋区(squatter area)成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由于寮屋区的发展根植于一国特定的历史、经济和社会文化之中,各国的寮屋区在具体形态、内部结构乃至名称上都存在巨大差异,成为反映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棱镜。土耳其共和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历了迅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从1945年的近343万人增长至1990年的3,180余万人,(1)从具体数据看,1945年土耳其的城市人口数量达3,427,053人,1990年该数字上升至31,804,551人。参见Sedat Avc, Two Papers About Urbanization in Turkey: Cities and Urban Population & Faults, Earthquakes and Cities, Istanbul: Çantay, 2005, p. 12。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则从1960年的25%增长至1997年的65%。(2)Nihal nciolu, “Local Elections and Electoral Behavior,” in Sabri Sayar and Ylmaz Esmer, eds., Politics,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 73.然而,土耳其工业化速度相对滞后,城市无法容纳短期内大量涌入的乡村和小城镇人口,这导致城市外围地区形成了大规模寮屋区并不断扩张。1950年至1990年间,土耳其的寮屋区人口从25万迅速上升至875万,其占城市人口的比例从4.7%增长至33.9%。(3)Ruen Kele, Kentleme Politikas, Ankara: mge Yaynevi, 1990, p. 369.在土耳其多党制的政治背景下,城市中迅速增长的寮屋区人口之于政党选举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有学者甚至提出,“寮屋区的选票对于决定城市选举的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4)Kemal H. Karpat, “The Genesis of the Gecekondu: Rural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1976),” European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Vol. 1, No. 1, 2004,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ejts/54,上网时间:2020年7月30日。。

寮屋区的迅速发展是二战后土耳其重要的社会现象,土耳其学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关注这一问题。阿里木·阿勒(Alim Arl)的综述性文章《共和国时期土耳其的城市化与寮屋研究》详细列举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土耳其学界有关城市化和寮屋区的研究成果。(7)Alim Arl, “Cumhuriyet Döneminde Türkiye’de ehirleme ve Gecekondu Aratrmalar,” Türkiye Aratrmalar Literatür Dergisi, Vol. 3, No. 6, 2005, pp. 283-352.整体来看,学者们通常将寮屋区置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着重选取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大城市的寮屋区进行个案研究。例如,凯末尔·H.卡尔帕特(Kemal H. Karpat)是最早关注寮屋区问题的学者之一,他的《寮屋:乡村迁徙与城市化》(TheGecekondu:RuralMigrationandUrbanization)是关于土耳其寮屋区研究的代表性著作。(8)Kemal H. Karpat, The Gecekondu: Rural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卡尔帕特深入伊斯坦布尔的寮屋区进行调研和访谈,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视角,探讨了当地寮屋区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20世纪80年代之后,土耳其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成为其社会和城市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寮屋区的状况和政治选择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穆拉特·杰马尔·亚勒辛坦(Murat Cemal Yalcintan)和阿德木·埃尔德木·埃尔巴斯(Adem Erdem Erbas)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伊斯坦布尔地方选举的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寮屋区民众已经成为城市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借助政党政治表达自身诉求,其政治选择成为土耳其亲伊斯兰政党崛起的重要因素。(9)Murat Cemal Yalcintan and Adem Erdem Erbas, “Impacts of ‘Gecekondu’ on the Electoral Geography of Istanbul,”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 64, 2003, pp. 91-211; Özlem Güzey, “Türkiye’de Kentsel Dönüüm Uygulamalar: Neo-Liberal Kent Politikalar, Yeni Kentsel Aktörler ve Gecekondu Alanlar,” dealkent, Vol. 3, No. 7, 2012, pp. 64-83.
国内学界对土耳其的政教关系、亲伊斯兰政党的发展及其政治理念等问题已有详细探讨,(10)相关研究参见昝涛:《延续与变迁:当代土耳其的政教关系》,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2期,第31-65页;刘云:《当代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变迁——从救国党到繁荣党》,载《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第118-123页;赵娟娟:《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发展——基于正义与发展党的考察》,载《新疆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79-88页;郭长刚:《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与伊斯兰政党的发展》,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5期,第4-21页;杨晨:《伊斯兰认同的历史演进——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反思》,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第54-60页。然而相较于国外学术界对土耳其城市化进程以及寮屋区的深入研究,中国学界多从宏观角度讨论土耳其的城市化问题。例如,邹高禄和罗爱玲曾介绍过土耳其城市化的动因和城市化发展不平衡等问题。(11)参见邹高禄:《土耳其的城市化》,载《世界知识》1988年第20期,第28页;罗爱玲:《城市化:解开“土耳其魔咒”的钥匙》,载《解放日报》2013年1月9日,第14版。车效梅对历史上伊斯坦布尔城市的演变、西方冲击下伊斯坦布尔的现代化进行了详细分析。(12)参见车效梅:《中东伊斯兰城市研究——对开罗、伊斯坦布尔、德黑兰的比较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车效梅:《挑战与应战 冲突与融合——伊斯坦布尔城市现代化历程》,载《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第59-70页。过去国内学界较少讨论社会发展和城市化与土耳其政党政治之间的关系,直到近年来才有学者着重关注这一问题。例如,王龙林的《城镇化与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一文探究了城镇化与本国伊斯兰政党崛起的密切关系,指出城镇化所带来的大量乡村居民向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迁移,因土耳其的选举制度的特殊性而强化了伊斯兰政党的选举优势。此文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伊斯坦布尔棚户区的情况,这与上述穆拉特·杰马尔·亚勒辛坦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处。(13)王龙林:《城镇化与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载《世界政治研究》2019年第2期,第154-207页。作者在此文中将“gecekondu”译为“棚户区”。
既往研究表明,伊斯坦布尔始终是学界在探讨土耳其寮屋问题时关注的重点地区。作为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在城市化浪潮中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形成了土耳其国内规模最大的寮屋区,而繁荣党在伊斯坦布尔地方选举中的胜出,则是土耳其亲伊斯兰政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本文试图以伊斯坦布尔的寮屋区为切入点,探究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繁荣党的崛起与寮屋区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城市化进程、多党制度与土耳其政治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 伊斯坦布尔寮屋区的历史形成
在土耳其,寮屋在本地语言中被称为“gecekondu”,意为“一夜之间建造的住所”。“gecekondu”一词最早产生于土耳其民间,并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开始被使用,(14)Sabri Çakr, Kentleme ve Gecekondu Sorunu, Pamukkale: Fakülte Kitabevi, 2007, p. 21, 转引自Sabri Çakr, “Türkiye’de Göç, Kentleme/Gecekondu Sorunu ve Üretilen Politikalar,” SDÜ Fen Edebiyat Fakül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No. 23, 2011, p. 212。该词既可以用来指寮屋区,也可以指寮屋区中单独的寮屋。土耳其学者对“gecekondu”的定义基本一致,即移民到城市的乡村/城镇人口违反公共工程和市政法律/条例,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违规建造的、不符合健康与居住条件的临时住所。(15)Sabri Çakr, “Türkiye’de Göç, Kentleme/Gecekondu Sorunu ve Üretilen Politikalar,” p. 213.从本质上讲,该词是一个法律术语,描述了违反建筑法规和财产权而一夜之间在归国家、市政当局或他人所有的土地上建造的临时性的、不舒适的简易住所。(16)Kemal H. Karpat, “The Genesis of the Gecekondu: Rural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1976)”.从这个意义上看,伊斯坦布尔的寮屋区与土耳其其他城市的寮屋区别无二致,但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城市中首屈一指的地位和影响力,决定了其寮屋区在政党政治意义上的特殊性与典型性。
1923年1月,凯末尔在西安纳托利亚视察期间宣布安卡拉将成为新政权的首都。随着同年10月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伊斯坦布尔这座千年帝都失去了其政治中心的地位。由于共和国早期大量资源被用于建设新都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作为旧政权的象征一度成为“被忽视的城市”(17)Murat Gül,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Istanbul: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sation of a City, London: I.B. Tauris Publishers, 2009, p. 72.。然而,伊斯坦布尔始终保持着土耳其经济、历史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土耳其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伊斯坦布尔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人口的迅速增长与日益提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成为乡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重要推力;另一方面,土耳其政府以工业化为重心的发展政策,也吸引着移民向城市,尤其是西部发达地区的城市迁徙。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激化促使东部和东南部省份的库尔德人向西部和西北部经济发达的地区迁移,伊斯坦布尔同样成为库尔德人移居的主要目的地。目前伊斯坦布尔的库尔德人口已达300万,占当地总人口的17%,因此伊斯坦布尔也被库尔德移民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库尔德城市”(23)Onur Günay, Becoming Kurdish: Migration, Urban Labor,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Turkey,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7, p. iii.,该群体主要聚集在寮屋区中。此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伊斯坦布尔也已经出现阿莱维派(Alevis)的寮屋区。
来自同一地区或相近地区的移民往往在民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同质性,这就使“乡谊”成为暗含民族、宗教信仰等元素的亲近关系。“来自相同地区的人们,居住在同一区域并在城市中形成了封闭的‘文化屋’(kültürodacklar)。所有街区(mahalleler)或居住区(semtler)中的这种‘文化屋’都是人们所离开地区的一个缩影。”(24)Ahmet Nuri Öktem, “kili Kültürel Yapda Kültür Bütünlemesine,” in Korel Göymen, ed., Bir Yerel Yönetim Öyküsü: 1977-80 Ankara Belediyesi, Ankara: Özgün Matbaaclk Sanayii, 1983, p. 226, 转引自Muharrem Es and Tuncay Gülolu, “Bilgi Toplumuna Geçite Kentlileme ve Kentsel Yoksulluk: stanbul Örnei,” Bilg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No. 1, 2004, p. 89。因此,埃尔祖鲁姆人(Erzurumlular)、埃尔津詹人、锡瓦斯人(Sivasllar)、里泽人(Rizeliler)人看似生活在城市里,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家乡”。(25)Ibid.

伊斯坦布尔的寮屋区居民在宗教信仰上呈现出较为温和的特征。虽然他们大多来自安纳托利亚东部、东南部、中部和北部等较为保守闭塞的乡村或小城镇,这些地区的现代化水平远落后于大城市,相较于城市而言,受世俗主义的冲击也相对有限,但是寮屋区居民的宗教信仰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极端主义倾向。尽管绝大多数寮屋区居民都声称自己是穆斯林,但是很少有人能够严格按照伊斯兰教的要求进行礼拜。一些宗教人士在为寮屋区的儿童提供免费的宗教教育的同时,也积极捍卫工人权利,并提倡全面采纳现代教育和科学技术。在一些寮屋区中,宗教人士还极力倡导民主并力劝民众参与选举。(29)Kemal H. Karpat, The Gecekondu: Rural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p. 128.

二、 寮屋区与土耳其的政治发展



由于乡村移民在许多方面将城市原有居民的生活方式视为自己的最终目标甚至典范,获得寮屋的正式土地所有权以及就业机会,便成为寮屋区居民的主要诉求。(38)Kemal H. Karpat, “The Genesis of the Gecekondu: Rural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1976)”.为获取寮屋区居民的支持,政党通常在选举前向他们承诺发放地契并授予寮屋区“街区”或者“市政”(belediye)的资格以使之合法化,进而国家将为这些原本没有电力、污水处理系统、公共交通和电路的区域提供基本服务。(39)Zeynel Abidin Klnç and Bünyamin Bezci, “Kentleme, Gecekondu ve Hemerilik,” pp. 327-328.共和人民党(CumhuriyetHalkPartisi)在20世纪70年代转变为中左政党,该党在1973年全国大选前向寮屋区居民承诺将为1973年底之前建造的所有住房颁发地契,(40)Kemal H. Karpat, The Gecekondu: Rural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p. 65.从而赢得了寮屋区居民的支持,并在大选中名列前茅。20世纪80年代寮屋区居民选择中右政党祖国党(Anavatan Partisi)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也是祖国党承诺将既有的寮屋合法化。为了更有效地争取自身权益,寮屋区还建立了诸如“寮屋区改善协会”(GecekonduyuGüzelletirmeDernei)等正式组织,其在致力于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还具有沟通居民与政党、同城市乃至国家政要进行交涉的功能。(41)Ibid., p. 200.《经济学人》(TheEconomist)评论文章曾指出,恩庇政治防止了土耳其寮屋区的贫民窟化。(42)“Turkey: Cities and People,” The Economist, Vol. 307, No. 7555, 1988, p. 28.
土耳其的政党更替频繁,且同一政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主张也时常发生变化,因此寮屋区居民并未与特定的政党形成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而是理性地选择支持能够使寮屋区利益最大化的政党。当寮屋区居民所支持的政党无法满足其诉求时,他们便会转而支持其他政党。但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寮屋区居民在地方选举和全国大选中通常支持中左或中右政党。相较于巴西等国的贫民窟,土耳其的寮屋区明显是安全且温和的。(43)Kemal H. Karpat, “The Genesis of the Gecekondu: Rural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1976)”.处于社会底层的寮屋区居民并未在政治中走向极端,这主要便是得益于政党政治为寮屋区居民表达自身诉求和获取物质利益提供了途径。寮屋区居民利用政党政治争取自身权益同时改善了本群体处境,等于缓和了城市化过程中的主要社会问题,继而有利于土耳其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平稳推进。

三、 繁荣党在伊斯坦布尔寮屋区中的经营
1994年繁荣党在地方选举和次年全国大选中所取得的成功,对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主义政治传统构成巨大冲击,深刻影响了土耳其政治的发展路径。尽管土耳其军方因不满埃尔巴坎政府的伊斯兰主义政策与活动,于1997年2月再次发动“软政变”,迫使埃尔巴坎辞去总理职务,繁荣党也在次年被土耳其宪法法院宣布为非法,但繁荣党短暂的胜利却为此后的亲伊斯兰政党的发展乃至执政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的政策为亲伊斯兰政党的壮大提供了发展空间,那么亲伊斯兰政党能够通过选举的方式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便离不开其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式下在城市底层民众、尤其是寮屋区居民中的经营。


寮屋区租金收益的上涨和城市中土地竞争的日趋激烈也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寮屋区居民的生存空间,弱势阶层被排斥于寮屋建造的过程之外。土耳其政府于1983年3月颁布的赦免法在承认既有寮屋区房屋合法性的同时,还禁止建造新的寮屋。(53)即土耳其2805号法案,于1983年3月21日颁布。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轮城市化浪潮中的乡村移民来说,大多数人只能选择租赁房屋,而日益上涨的租金和这一时期收入的相对下降,无疑造成了其生存的困境。寮屋区住房的商业化与政府、房地产商和非法组织等多个行为主体的介入,还对寮屋区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强烈冲击。再加上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等思想空前盛行,寮屋区内部的传统秩序和社会关系网络逐渐遭到侵蚀。
20世纪90年代初,繁荣党在“民族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公正秩序”(AdilDüzen)的政治理念,将其重点放在社会经济问题之上。(54)Banu Eligür, The Mobilization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p. 148.繁荣党把一千年前土耳其人皈依伊斯兰教作为本国历史的起点。它批评自奥斯曼后期以来两个世纪的西化改革,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瓦解是由于西方化导致民族信仰、传统与文化(伊斯兰)的力量在社会中的衰落。繁荣党认为,西方文明与犹太复国主义是万恶之源,也是国家落后的原因。(55)Ibid., p. 145.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正在推行一种有意识的“现代殖民主义”政策,在土耳其造成了社会经济问题。在强调土耳其的失序状态的同时,繁荣党还为国家的发展构建了一套新的“公正秩序”。繁荣党批评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将“公正秩序”定义为“以私人企业家精神为基础并摆脱垄断的秩序”,主张建立公平的经济秩序,强调平等的收入分配以及改善穷人物质状况的道德义务。(56)Necmettin Erbakan, Adil Ekonomik Düzen, Refah Partisi, no publisher, 1991, pp. 3-4.在土耳其社会贫富分化与寮屋区内部的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公正秩序”对城市底层民众的吸引力大大提升,繁荣党的支持者由此从安纳托利亚乡村扩展至城市,尤其是数量众多的城市底层选民。

繁荣党还不忘援引奥斯曼帝国后期的市政改革来为自身的市政理念与实践辩护。时任繁荣党主席助理的里扎·乌鲁贾克(Rza Ulucak)在1994年地方选举前夕的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我们(繁荣党)所主张的市政体系曾在奥斯曼帝国的进步时代(ilerlemedevrinde)得到施行。当时担任市政长官的人被称为‘ehremini’,意思是担任市长的人。我们的市政长官也将会是24小时的城市长官(ehrinemri)。”(60)“Yerel Yönetimlerde ‘Adil Düzen’ Dönemi Balyor: Refahl Belediyelerde Osmanl Modeli,” Cumhuriyet, March 30, 1993.奥斯曼帝国现代意义上的市政建设是在伊斯坦布尔的西方势力主导下开启的,且专门的市政机构在建立之初主要服务于欧洲人的利益,但此后奥斯曼政府的介入进一步扩大了市政机构的职权范围,逐渐直接地与所有人建立联系。例如,奥斯曼政府任命市政医生管理为穷人设立的免费诊所、在遭遇鼠疫时为儿童免费接种疫苗、打水井缓解加拉塔夏末的缺水问题等措施,无不体现出伊斯兰慈善理念中关注穷人和普惠性的特征。(61)Steven Rosenthal, “Foreigners and Municipal Reform in Istanbul: 1855-186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1, No. 2, 1980, p. 242.由此看来,繁荣党的市政实践与理念的确与奥斯曼时期的市政管理具有共通之处。当然,繁荣党也受益于伊斯坦布尔丰富的伊斯兰遗产。当地数量众多的清真寺、伊斯兰组织和基金会为繁荣党的活动提供了支持。
繁荣党在向社会底层民众提供具有伊斯兰慈善性质的市政服务的同时,也在其管辖范围内限制并打击与伊斯兰理念相悖的行为与活动。例如,腐败问题一直是困扰土耳其市政工作的顽疾,繁荣党在批判其他政党市政管理中的腐败行径的同时,致力于在其管辖的市镇中建立“公正秩序”,构建一套高效廉洁的市政管理模式。苏尔坦贝伊里(Sultanbeyli)是伊斯坦布尔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寮屋区,繁荣党在1989年的地方选举中赢得了该区。苏尔坦贝伊里区政府通过规定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不准收受贿赂和每天五次礼拜以杜绝腐败问题。身为繁荣党成员的区长阿里·纳比·科查克(Ali Nabi Koçak)对这一规定做出了如下解释:“每天礼拜五次的人知道他将在末日审判时进行汇报,因此他不会受贿,也不会偷窃。”(62)Banu Eligür, The Mobilization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p. 170.繁荣党当局还在市政大楼中竖起了写有“受贿和行贿者是邪恶之人”的警示牌。(63)“Seçim Bitti, Ortalk Toz Duman,” Cumhuriyet, April 3, 1994.繁荣党在苏尔坦贝伊里的市政管理获得了巨大成功,该区的选民人数从1989年的8,937人增加到1994年的43,700人,而在地方选举中繁荣党在该区的得票率则从1989年的30%增长至1994年的近60%。(64)Banu Eligür, The Mobilization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p. 170.繁荣党在苏尔坦贝伊里区的成功经营也为其赢得了良好声誉,从而使伊斯坦布尔的于斯屈达尔(Üsküdar)、卡尔塔尔(Kartal)、于姆拉尼耶(Ümraniye)和艾郁普(Eyüp)等区的选民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也选择支持繁荣党。(65)Ibid.
繁荣党还注重深入到底层民众中,与民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这首先体现在繁荣党的竞选方式上。土耳其海峡大学教授埃尔森·卡拉伊杰奥卢(Ersin Kalaycolu)认为,繁荣党是土耳其唯一一个具有明确的纲领且有组织地建立起募集选票(oytoplamak)机制的政党。这是因为繁荣党不仅在选举前通过挨家挨户走访的方式(kapkapdolamaksureti)进行宣传和游说,在投票阶段也始终有人员在现场为选民提供各种帮助,而其他政党的领导人却没有能力运用本党的人力资源,组织性远逊于繁荣党。其他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将上述工作交给国家,而没有适当的代理人深入现场。(66)“Seçim Bitti, Ortalk Toz Duman”.在繁荣党胜选的地区,会定期召开所谓的“人民议会”,并宣称“人民议会”是“直接民主”以及“真主赋予民众的权利”。(67)Yael Yashin-Navaro, “Uses and Abuses of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urkey,”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Vol. 18, 1998, p. 12.繁荣党区长每周都会到当地的咖啡馆听取市民对市政当局的诉求。耶勒·亚辛-纳瓦罗(Yael Yashin-Navaro)在观察繁荣党在伊斯坦布尔卡厄特哈奈(Kathane)的寮屋区的活动后,对“人民议会”作出了如下描述:“在开始交流之前,他(区长)总是提醒居民,这些集会是仿照伊斯兰教早期哈里发欧麦尔的治理模式……出席每周的‘人民议会’的几乎都是男性,且大部分是繁荣党的支持者。他们表达自身对于社区中的管道破裂、垃圾未收集、交通事故、道路未铺砌、缺水、缺电等问题的关切。”(68)Ibid., pp. 12-13.此外,在宗教节日期间,繁荣党的市政长官也会到访疗养院、学生宿舍、被遗弃儿童的宿舍(abandoned children dormitories)、医院和监狱,并分发食物和衣物等物品。(69)Banu Eligür, The Mobilization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p. 171.
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宗教、教派等认同被政治化。这一趋势也对土耳其的寮屋区产生了影响,寮屋区居民中出现了基于种族、教派和性别的分化。这与兴起于西方世界的、强调身份认同和差别的后现代思潮相一致。此外,在城市中长大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寮屋区居民也意识到了自身内部的差异。(70)Tahire Erman, “Gecekondu Çalmalarnda ‘Öteki’ Olarak Gecekondulu Kurgular”.例如,在库尔德人聚居的寮屋区中,普遍失业和高度不安全的生活处境,致使库尔德人产生了怨恨和被剥夺感。由于库尔德人通常会从种族角度看待社会不平等,使其更加重视自身的种族纽带和身份,(71)Ümit Özda, Güneydou Anadolu Bölgesi’nde ve Dou ve Güneydou Anadolu’dan Batya Göç Edenlerde Kültürel Yap ve Kültürel Kimlik Sorunu, Ankara: Türk Metal Sendikas, 1995, 转引自Aye Güne-Ayata and Sencer Ayata, “Ethnic and Religious Bases of Voting,” in Sabri Sayar and Ylmaz Esmer, eds., Politics,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 p. 140。进而成为“威胁”土耳其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潜在隐患。繁荣党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政治主张和市政实践,则超越了寮屋区民众之间的教派、种族和地域差异,对具有不同背景的寮屋区居民产生了广泛吸引力。例如,居住在寮屋区中的底层库尔德人更愿意支持繁荣党,而非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土耳其《共和报》(Cumhuriyet)曾指出了这一点:“……经受贫困的人明显倾向于繁荣党,(繁荣党)在大城市和东南部选票激增背后存在这样的事实。繁荣党获得了东南部的库尔德人的选票,大城市中库尔德人的选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看到,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中繁荣党的选票背后也存在一定比例的库尔德选票。”(72)“Kürt Oylar Yeniden slami Partiye Yöneldi,” Cumhuriyet, March 29, 1994.
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寮屋区房屋的商品化、多种外部力量对寮屋区土地和住房资源的竞争和干预造成了寮屋区居民内部的分化,底层寮屋区居民的处境愈加艰难,寮屋区内部以乡谊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也逐渐被削弱。在此情况下,繁荣党以伊斯兰教信仰为内核的“公正秩序”迎合了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寮屋区居民的诉求,其致力于提供具有伊斯兰慈善性质的市政服务则为伊斯坦布尔的寮屋区居民带来了切实的物质利益。此外,繁荣党通过多种途径渗透到寮屋区社会中,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寮屋区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功能。上述因素共同构成繁荣党赢得寮屋区居民支持的关键。
四、 结语

城市化看似是城市对乡村、现代化对传统的一种侵蚀与剥夺,而实际上乡村与传统却以自身独有的方式反作用于前者。一方面,安纳托利亚移民的涌入改变了伊斯坦布尔的人口结构,城市原有居民的比重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来到城市的乡村和小城镇移民并没有被动地融入城市生活之中,他们在寮屋区中保留并延续着安纳托利亚的传统,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形塑着城市景观。更重要的是,寮屋区居民还不断借助政党政治施以对市政管理和国家政治的影响。土耳其的多党政治不仅构成以寮屋区民众为代表的社会底层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其地方选举和全国大选的规则设置以及独特的行政管理结构也为寮屋区民众表达自身诉求提供了有利条件。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繁荣党在伊斯坦布尔等城市的寮屋区居民的支持下取得了实质性的政治地位,而至今已经主宰土耳其政坛近20年的埃尔多安也正是在当年的伊斯坦布尔市长任上获得了第一笔政治资本。由此看来,寮屋区居民是土耳其政治由激进的世俗主义向伊斯兰主义转型的推动力量。在正发党长期执政的今天,寮屋区依然是土耳其面临的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溯源寮屋区在亲伊斯兰政党崛起过程中的作用,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当今土耳其的社会和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