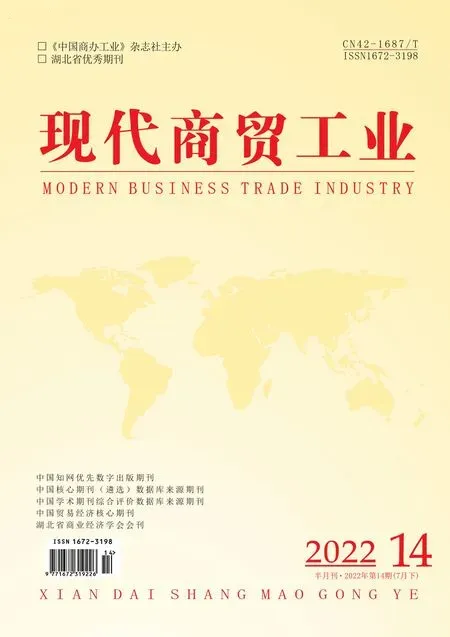海南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摘要:海南黎族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承载着海南黎族人们生活的风貌和精神,对其有效保护不仅有利于海南历史文脉的延续,更能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推动文明交流。运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海南黎族非遗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但亦存在相当的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有必要找到问题症结,以期更好地实现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对非遗产最大程度的保护。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南黎族;知识产权;困境;出路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2.14.060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及问题引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承载着一个国家文化的气息和底蕴,承载着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与成果,承载着人们生产生活的风貌和精神。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接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海南黎族拥有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有黎族民间故事、黎族方言长调、黎族共同舞、黎族传统游艺与体育竞技活动等民间文艺,还有黎族泥片贴筑制陶、藤竹编、絣染、双面绣等技艺,还有黎族传统婚礼、三月三庆典等民俗。因此,作为极具地方特色的海南黎族非遗的保护之于海南之于国家都至关重要。对于非遗的保护,理论界的研究视角和切入点丰富,有者从产业文化的视角探讨,有者从数字化、智能化角度切入,有者从法学保护模式入手,有者从公众参与社区推广方式讨论等。无论哪种方式方法,“目前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恰当、最有效的法律保护方式之一,就是通过知识产权体系进行权利确认和利益分配”然而,知识产权框架下海南黎族非遗的法律保护仍存在相当的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有必要找到问题症结,以便对症下药更好地实现知识产权法律对非遗最大程度的保护。
2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问题与困境
关于非遗的法律保护问题,理论界始终存在两种观点:肯定说认为非遗理应适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否定说认为非遗兼具公有性和私有性的双重属性,因此其与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不能完全契合;知识产权保护注重主体的经济利益和市场垄断地位,其与非遗保护的意旨相矛盾;而且,非遗的客体难以完全纳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范畴等。因此,否定说认为非遗不适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也不能对其进行全面保护。实际上,运用知识产权法保护非遗已渐进被学术界和实践界所认同。第一,非遗虽兼具公有性与私有性双重属性,但其具备的私有属性足以为其适用知识产权规范提供可能性;第二,非遗与知识产权客体同属于智力成果,两者在尊重智力劳动成果和促进创造性活动,实现创新与传承方面的意旨和本位是相同的,因此非遗具备适用知识产权规范的必然性;第三,纵然知识产权规范的客体与非遗的客体非具同一性,但在知识产权范围内极尽可能运用其保护非遗,不但符合法律规定,更有助于增加非遗保护的“厚度”,之于非遗保护具有必要性。因此,运用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保护非遗是非遗保护的应有之意,也符合国家的管理政策和导向,亦有国外立法例的实践。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在谈及“保障措施”时明确指出“要综合运用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地理标志等多种手段,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由此,笔者认为,应当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将非遗纳入知识产权框架内予以保护,实现海南黎族非遗的传承与发展。那么,除上述论述之“非遗是否能纳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框架”这一困境外,非遗纳入知识产权法律框架保护仍存在诸多困境和瓶颈,因此,厘清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是为构建非遗知识产权法律保護的必由之路。
非遗在适用知识产权法规的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的困境主要集中在:非遗能否适用知识产权法规(前文已详述)、非遗主体的确定、知识产权对非遗客体保护的边界等。
3非遗主体的确定
“权利主体是指参加法律关系而享有法律权利并且需要承担法律义务的人”,具体到非遗,其主体系非遗权利义务之所属。确定非遗的主体资格是构建非遗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的关键,只有主体明确才能在知识产权框架下确定由谁享有、主张、行使、保障权益,才能更有效地承担维护非遗权益,防止其被侵害的义务,更好地传承和发扬非遗。因此,主体的确定是非遗受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关键困境,是实现非遗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必经之路。然而,非遗主体如何确定理论界观点众说纷纭,各国实践虽各具特色但操作亦十分困难。
关于非遗主体的主要理论观点,有者基于创造者的角度来认定,认为非遗的创造者即为权利主体;有者据非遗主体是否能确定之具体情况来认定非遗主体;有者认为非遗的主体为多元的,细化有二元主体论、三元主体论等。立法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非遗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将非遗主体界定为“各族人民”。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二条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上述理论与实践在确认非遗主体上,主要是从主体不同的组织形态出发,以列举方式界定主体的外延,认为非遗的主体可为个人、社区、群体等,且在界定上倾向创始价值和传承价值的考量。各理论与实践虽切入点不同,视角下的主体范畴亦有差异,且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定论和通说,但却不同程度地揭示了非遗的主体特征和适格标准。笔者认为,非遗的主体之所以能构成主体,第一,应具备能成为权利义务主体的可能,能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第二,鉴于非遗的特殊性,在主体的厘清和确定上应兼顾非遗的公有性和私有性双重属性,且应既注重非遗的创始价值,又注重非遗的传承和保护价值;第三,认定非遗主体,要尊重既有客观事实、传统认知和习惯惯例。
笔者认为,非遗主体在范畴上,创造者为非遗的当然主体,自不待言。若创造者系明确的自然人,其自然为非遗主体。然而,非遗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和区域性,往往是长期由某个群体或地区集体创造的结果,非单一个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创造该非遗的群体、地区亦为非遗的主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亦表明作为群体、社区可为非遗的主体。
非遗被创造出来后,“其会被不断地传承和发展,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可见,非遗的活态流变性和传承者对非遗创新发展的持续贡献力决定了非遗的“传承者”亦应为非遗的主体。无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还是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白沙黎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保亭黎族苗族黎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都规定了传承人制度。而且,海南上述保护条例还明确了符合条件的团体和组织之传承单位的“非遗的传承者”地位。由此,作为非遗主体的传承者,个体和群体均可担当。
非遗的创造者和传承者能为主体,除其能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外,更多系基于非遗的私权性质及其创始价值和传承价值的考量,但非遗的双重属性决定了非遗除强调私有性外还要兼顾公有性,除体现创始价值和传承价值更要注重保护价值的追求。而非遗的保护者,或因具有承担非遗保护的公共权力和责任,或因认同非遗作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情感和精神财富,自觉予以保护,其均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承担责任和持续输出力量。因此,笔者认为,非遗的“保护者”理应成为非遗的主体。非遗保护者最典型的代表即是国家或政府,其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在保护和防止非遗被侵犯被滥用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和强制力后盾保障。另外,其他以公益为目的以保护非遗角色出现的组织体和个人皆可成为非遗主体,也有必要成为非遗主体,如专业团队、公共事业组织、群体、社区、个人等。其成为非遗主体不但符合非遗保护宗旨与本位,更能在非遗创造者和传承者不能或怠于主张和行使权利时,作为兜底主体来保护非遗,维护权益。因此,非遗的保护者成为主体,不但体现了非遗的公有性特征及其对保护价值的追求,亦是对保护者对非遗潜在保护力的肯定与支持,更是具有兜底保护的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非遗主体在确定上应从创造者、传承者和保护者三个维度“内涵式”界定,兼顾了非遗的私有性和公有性,兼顾了非遗的创始价值、传承价值和保护价值。一方面避免了以主体的组织形态的差异来界定非遗主体造成的外延不周全,防止列举式界定主体的不全面;另一方面有利于解决非遗主体认定上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能发展性地解决非遗主体认定的困难,避免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使内涵上属于非遗主体但因有限列举使本应成为非遗的主体无法成为主体,又能因兜底功能保护主体的介入避免“维权不能”的情况。因此,创造者、传承者和保护者三个维度内涵式主体的界定,具有适应性和发展性,符合人们的逻辑认知和客观实践,具有理论和实践,实体法和诉讼法上的意义,不失为有效的非遗主体判断标准,不失为非遗主体认定困境的解决出路。
另需注意,在非遗主体认定困境和解决出路上,上述分析虽厘清了主体的内涵,明确了适格非遗主体之社会存在,但其意欲具备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主体,能借助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其权益,仍需国家立法对其主体资格的确认。因此,在立法层面,需明确非遗的创始者、传承者和保护者均为非遗的主体。另外,在明确主体的基础上需要相关的配套和制度的协助,如对于集体权型主体建立权利代表制度和代理制度,形成相应的运行机制和程序等,明晰三类主体在行使权利上的优先顺位,增加公益诉讼对非遗保护的支持等。
4知识产权对非遗客体保护的边界及出路
知识产权法规对非遗客体保护的边界或说保护范畴上的困境主要在:非遗的客体范畴和知识产权的客体范畴并非完全重合;且能适用知识产权保护的非遗客体在保护路径上不甚清晰。如何条理清晰、路径明确地将非遗纳入知识产权框架为非遗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必要出路。具体而言:
非遗客体的范围广泛且复杂,理论与实践亦存在不同观点,这直接影响非遗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和制度建设。我国立法非遗的客体包括:民间文学艺术、传统知识、民俗,还包括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即物化的文化空间。那么,如何划定知识产权法规对非遗客体保护的边界?笔者认为,非遗的客体和知识产权的客体系不同的集合范畴,但两集合存在交集,因此,就交集部分即可适用知识产权法规予以调整。两者的交集主要体现在民间文艺作品、传统知识中的传统技艺、民俗类非遗中传统识别性标志等。
对于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由此明确了民间文艺作品之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且为保护民间文艺作品的著作权及其有序使用,国家版权局起草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由此,海南黎族民间文艺作品,如黎族的民间故事、方言长调、共同舞等均可受著作權法予以保护。
对于技艺类的非遗:一方面,若其技术可凝聚于特定的实物形态存在,如海南黎族基于酿酒、藤编、双面绣技艺凝结的山兰酒、藤编品、黎锦双面绣品等,符合条件者,可运用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等专利法规保护,可借助商标法注册相应的商品和服务商标,更可充分运用地理标志制度系统保护。另一方面,若技艺技能非以实物为载体或不满足知识产权较高的客体保护标准,不能直接适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为更好地传承与保护,可将相关的技艺技能以数字化或纸质化等载体进行固定和保存,从而间接借助著作权及相关权利予以保护。若相关的技术技能不宜公开属商业秘密范畴,可借商业秘密保护相关规范调整之。是以非遗主体应在现有知识产权法律框架下直接或间接充分运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保护非遗。
对于民俗类非遗,其中的传统识别性标志,可借助商标法对其进行保护。传统识别性标志可注册商标,但未经原住民社区许可,原住民社区以外的人不允许将原住民社的原有标记、徽章、符号等注册。对符合证明商标标准的民俗,亦可运用商标法的证明商标制度予以保护。2004年国家商标总局核准重庆铜梁县高楼镇火龙文体服务中心注册“铜梁火龙”为证明商标的申请,使龙具造型、队员着装、龙舞套路、火花施放、吹打乐等内容纳入商标保护范围。由此,非遗项目可以通过商标法进行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另需注意,对于非遗客体的保护,非遗主体须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内化非遗保护既是义务又是责任,积极主张权利,防御侵权,积极利用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保护海南黎族非遗。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Z].2021-08-12.
[2]胡世恩.回族传统医药“汤瓶八诊”商标系列诉讼案的法文化反思[J].回族研究,2016,(2).
[3]刘雪风,王家棋.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研究综述[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3-41.
[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词典》编委会.法律词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96.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Z].2003.
[6]李佳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探析——以海南为例[J].学理论,2012,(12).
[7]胡光,孔丽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基于宁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知识产权构架下海南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困境与出路”(HNSK(JD)18-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博文(1981-),女,汉族,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