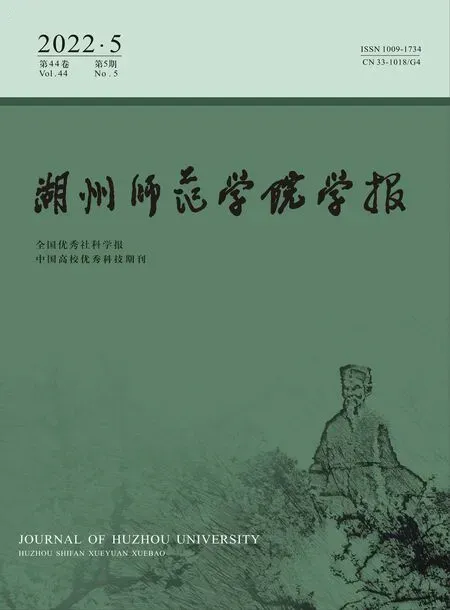天一阁藏书制度及借阅史实补考*
张银龙,迟 语
(1.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2.清华大学 图书馆,北京 100084)
宁波的天一阁,因其保护了大量珍贵古籍闻名于中国藏书史。民国以来,针对天一阁的研究颇多,而围绕藏书保护的成果却较少,且基本是从建筑构造、防虫防霉与规章制度三方面展开简要论述,如霍艳芳与万亚萍合作的《范钦与天一阁藏书保护措施研究》[1]76-79、王茂法《宁波天一阁保护藏书的启示》[2]52、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3]等,但是均未能在制度方面给予较可信的文献为据。而对于天一阁藏书的使用,除了不少学者诟病其藏书制度谨严是封闭的藏书楼外,亦有少许学人从文献中挖掘出范氏供人抄读的事例,期以实例证明典范如天一阁的中国传统藏书楼的社会功用并未缺失,如武汉大学刘水养的《天一阁藏书及社会贡献史考略》[4]54-56一文考证登阁读书者有十余名,虞浩旭的《历代名人与天一阁》[5]46-47考证有四十余著名学者登楼。但是仍有不少疏漏。
若能从文献角度对上述两方面做些许补证,对于天一阁乃至整个古代藏书楼的相关研究当有所裨益。
一、天一阁的藏书制度
天一阁由明代范钦建造于嘉靖四十年(1561),至今已屹立四百余年,为中国保存了大量珍贵古籍,历来文人学士褒扬有加。
关于天一阁藏书制度,今得见的较早文献为清代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一文:“余闻明范司马所藏书,本之于丰氏熙、坊。此阁构于月湖之西、宅之东。墙圃周回,林木荫翳,阁前略有池石,与阛阓相远,宽闲静谧。不使持烟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又司马没后,封闭甚严。继乃子孙各房相约为例:凡阁橱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其例严密如此,所以能久二也。夫祖、父非积德则不能大其族。族大矣,而不能守礼读书,则不肖者多出其间。今范氏以书为教,自明至今,子孙繁衍,其读书在科目学校者彬彬然,以不与祭为辱,以天一阁后人为荣,每学使者按部,必求其后人优待之。自奉诏旨之褒,而阁乃永垂不朽矣。其所以能久者三也。”(1)(清)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M]//揅经室集:二集卷七.四部丛刊清道光本.为便于较为全面地理解文意,此处所引原文较长。
览此段文字,不难理解,阮元认为天一阁藏书楼能够长久保存下来的原因有三:一是科学的建筑结构,二是严格的入阁制度,三是族人自律。此番言论,衷心地赞誉了范氏家族及所造天一阁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古籍的不朽功绩。
关于天一阁制度的记载,尚未得见范氏有正式文字流存,除阮元文字外,亦仅见数人零星描述。
清沈叔埏(1736—1803):“范氏之守世书也,余尝求其故而不可得。或曰其家奉司马公遗训,代不分书,书不岀阁。有借钞者,主人延入,日资给之,如邺侯父承休,聚书三万余卷,戒子孙,世间有求读者,别院供馔是也。或曰,阁扄鐍惟谨,司马后人分八九宅,各司其管,一管不至,阁不能开,借书者以为难,书得不散。”(2)(清)沈叔埏.书天一阁书目后[M]//颐彩堂文集:卷九.清嘉庆二十三沈维鐈武昌刻本.清石韫玉(1756—1837):“而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自明至今,岿然独存,其守之必有道焉。子弟虽多,产可析,而书不可析;键其户,必子孙群集,然后启,虽有显者不借。此范氏藏书之法也。”(3)(清)石韫玉.凌波阁藏书目录序[M]//独学庐稿:四稿卷二.清写刻独学庐全稿本.清张鉴(1768—1850):“其阁之久远而已。阁一直七架,左一稍杀,置桄以登,即所谓天一生水也。阁非至戚密友不易至。至者,先告于其家主阁者,至期,启阁,则有人焉;登桄,则有人焉;启柜,则有人焉……”(4)(清)张鉴.冬青馆集:甲集卷四文一[M].民国吴兴丛书本.清陆以湉(1802—1865年):“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凡五万三千余卷。阁在月湖之西,宅之东,墙圃周回,林木蓊翳,与阛阓相远。明嘉靖中,尧卿少司马钦归田后构以藏书。其异本得之丰氏熙、坊者为多。书藏阁之上,通六间为一,而以书厨间之。其下仍分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司马殁后,子孙各房,相约为例: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以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乾隆间,诏建七阁,参用其式,且多写其书入《四库》,赐以《图书集成》。嘉庆间,阮文达公巡抚浙江,命范氏后人编成目录,并金石目录刻之。自明嘉靖迄今三百余年,遗籍常存,固由于遭遇之盛,抑亦其立法严密,克保世泽于勿替,宜名垂不朽,为海内藏书第一家也。”(5)(清)陆以湉.天一阁[M]//冷庐杂识:卷七.清咸丰六年刻本.陆氏恐引阮元文。
古人文字记载范氏“不借人”之法,从文意看应是指书籍不可携带出书阁,即今人所言“不能外借”之意,并非如今人所理解的藏书“不能借阅”。可见“借”字的古今语义衍变也是导致今人理解出现分歧的原因之一。古之言“不借人”核心意义为“不外借”,实为读者可在阁内阅览而不可将书籍携带出阁;今人之言“借阅”包括“借出”与“阅读”两个相关的连续性行为。古之“借阅”则为“假借别人书籍得以阅览”,并不包括“携走”之义。
以上关于天一阁藏书制度的文字,其核心内容未出阮元所述。这些制度应是范氏在总结藏书楼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所定。
天一阁严格的藏书制度,是用来保护藏书与建筑的。正是制度谨严与执行坚决,保证了天一阁藏书及楼体的长久存在。但是保护好的书籍是要被社会使用才能实现其本来价值,史实表明,范氏家族深明其义。
二、天一阁藏书借阅史实
如上所述,范氏明令书籍不可出阁楼,只可阁阅,看似无情,其实,深挖文献可知,范家对于来阁阅书者的态度颇好,往往以盛情待之,如:
胡文学记述:“适余选里中耆旧诗,公曾孙光燮为余扫阁,尽开四部书,使纵观。因得郑荥阳、黄南山、谢廷兰、魏松云诸先生集诗。”(6)(清)胡文学.甬上耆旧诗:卷十七[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范光燮“扫阁”待客,可见范家盛情;“尽开”“使纵观”,尽显范家之热心与大度。
“四明范侍郎天一阁藏书,名重海内久矣。其藏弆碑刻尤富,顾世无知之者。癸卯夏,予游天台,道出鄞,老友李汇川始为予言之。亟叩主人,启香厨而出之,浩如烟海,未遑竟读。”(7)(清)钱大昕.天一阁碑目序[M]//潜研堂集:文集卷二十五.清嘉庆十一年刻本.“亟叩主人,启香厨而出之”,可见对于钱大昕来请,范家也未怠慢,而是很快开橱让其观阅。
“范菊翁、李渭川、卢月船、范莪亭、卢东溟,招饮天一阁,观藏书。”(8)(清)钱维乔.竹初诗文钞[M]//诗钞:卷十三,清嘉庆刻本.此为钱维乔所作一诗之引言,可知范家引友朋观览藏书,甚至宴饮待之。
再者,许多人所抄写书籍,或为当世珍本,或数量庞大,并未有人记录范氏或有吝惜之色。如:
清丁丙记:“《新编姓氏遥华韵》九十八卷,扬州阮氏钞天一阁本。”(9)(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M].清光绪刻本.清潘祖荫记:“《后村集》,文胜于诗,然诗亦有新隽不可到处,在读者分别求之耳。世所传本多六十卷,张月霄从天一阁钞得一百九十六卷,为《后村大全集》。”(10)(清)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卷三集部[M].清末刻民国增修本.清陈寿祺记:“其后邨词,则取于余所录天一阁大全集,多至百三十余首,盖诸家所未及见,亦足征网罗之富矣。”(11)(清)陈寿祺.左海文集:卷六[M].清刻本.清顾广圻记:“柯溪居士得《夏竦集古文韵》钞本,首有绍兴乙丑齐安郡守晋陵许端夫序,以其与乾隆闲歙人汪启淑刻本夐乎不同,属予审定。予案英公此书从前甚秘,近因汪刻,遂得颇行,汪所据者影写北宋本也,而此乃南宋本,未经重刊,故见者绝少,唯全谢山从天一阁借钞。”(12)(清)顾广圻.题钞本集古文韵癸未[M]//思适斋集:卷十四题跋.清道光二十九年徐渭仁刻本.
事实上,若不惮其烦,搜检文献,可发现历史上受益于天一阁藏书的学者数量之多令人讶异,仅目前得见于清代文献记载的登阁者或假他人抄得书籍者即近60人,他们是:陈石琴、陈寿祺、丁丙、东海先生、董沛、冯古椿、冯某、何焯、何凌汉、何绍基、何松、胡文学、黄群、黄冈张学使、黄宗羲、璜川吴氏、江珧柱、姜炳章、李渭川、卢月船(名镐字配京)、范莪亭、卢东溟、李邺嗣、厉樊榭、凌廷堪、罗正季、缪荃孙、梅谷主君、潘衍桐、彭元瑞、钱大昕、钱维乔、秦瀛、全祖望、任宏远、阮元、沈家本、孙星衍、陶元藻、万祖绳、汪照、翁方纲、杨文骏、姚鼐、徐石客、姚佺(山期)、葛世振(字仞上号同果)、董次公(字天鉴名守瑜)、万考叔、张鉴、张芑堂、张月霄、赵怀玉、郑耐生、张秋水、夏闰枝、戚学标等。其中不乏大家熟知的黄宗羲、阮元、全祖望、钱大昕、潘衍桐、缪荃孙、沈家本、姚鼐等著名学者。此名单中有大量为虞浩旭先生著《历代名人与天一阁》一书所未记者,若将二者合一,则今之所知受益于天一阁藏书者已近百人。而未知者又有几多?
史实表明,范氏对于来鄞请求观书者之宽容足可令今人惊讶。有的人为了抄书,甚者竟至于长期吃住于主人家,有的人多次登阁抄阅,有的数人结伴而来,而范氏一一容之。
长期住下抄阅书籍者,如:“蠧斋先生《铅刀编》三十二卷抄本,【宋】周孚信道撰,友人解百禴伯时编集……某氏手跋曰,《铅刀编》三十二卷,海内藏书家概不见,东海先生过访天一阁,范氏所藏有宋椠本,登阁影抄,四旬始竟,携归,过予斋头,余即欲传抄,不克是愿。今忽三十余年,先生已归道山,抚卷感往,不胜凄怅,聊书数语于首,以为后人珍重之意。”(13)(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八十六集部[M].清光绪万卷楼藏本.东海先生竟至于花了四个月呆在天一阁影抄《铅刀编》。
“适海盐张芑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14)(清)钱大昕.潜研堂集:文集卷二十五[M].清嘉庆十一年刻本.“寓”即“居住”之意,张芑堂为了摹石鼓文也是住在了范家。
有的人多次登阁观览书籍,如:钱大昕“亟叩,主人启香厨而出之,浩如烟海,未遑竟读。今年,予复至鄞”(15)(清)钱大昕.潜研堂集:文集卷二十五[M].清嘉庆十一年刻本.。钱维乔多次登阁,留诗《偕同人再登天一阁观藏书并披阅金石文,仍用集禊帖诗原韵》(16)(清)钱维乔.竹初诗文钞[M]//诗钞:卷十四.清嘉庆刻本.。阮元至少两次登临天一阁:“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之家,惟此岿然独存。余两登此阁,阁不甚大,地颇卑湿,而书籍干燥,无虫蚀,是可异也。”(17)(清)阮元.定香亭笔谈:卷二[M].清嘉庆五年扬州阮氏琅嬛仙馆刻本.赵怀玉“又至范氏天一阁,抄其阙者补之”(18)(清)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文卷二序[M].清道光元年刻本.。张鉴“又尝因海上之役,两登天一阁。其一仅阅宋拓石鼓文,匆匆即返。翌日,歙凌仲子至,邀重登,检阅唐宋人集十余种,胡身之注通鉴,即近江西本所自岀”(19)(清)张鉴.冬青馆集:甲集卷四文一[M].民国吴兴丛书本.。“姜炳章,字石贞,号白岩,馆于郡城,尽读范氏天一阁藏书,所学极博。”(20)(清)周春.耄余诗话:卷八[M].清钞本.“尽读”或有夸张,但是由此可知姜炳章登临天一阁之频繁。
而全祖望前后数十年屡次登阁观书、抄书不辍。全祖望《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铭》记载:“少时,从天一阁范氏得见袁尚宝公所刻《先进士忠义录》。其中有蒋教授景高所作传,较详于旧志。及自京师归,求是书于范氏,则无有矣。近忽从董氏得之,惊喜。(21)(清)全祖望.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铭[M]//鲒埼亭集:卷二十三碑铭.四部丛刊景清刻姚江借树山房本.“雍正元年癸卯先生十九岁。先生尝再登天一阁借书,当始于是时。”(22)(清)全祖望.全祖望年谱[M].清嘉庆九年史梦蛟刻本.“乾隆三年戊午,先生三十四岁,侍两尊人家居,冬丁太公艰。先生既归,侍庭闱有间,益广修枌社掌故,并桑海遗闻,著作日富。重登天一阁,搜括金石旧搨,编为天一阁碑目,又为之记。又钞黄南山仪礼、戴记附注四卷,王端毅公石渠意见,皆阁中秘本,世所仅见者。又编曹远思葬杨氏忠烈录。”(23)(清)全祖望.全祖望年谱[M].清嘉庆九年史梦蛟刻本.
更有多人搭伴登阁的,如《跋圉令赵君碑旧拓本》:“道光壬辰春仲,先文安公按试宁波,余随侍,登范氏天一阁,见此碑及刘熊碑。”(24)(清)何绍基.跋圉令赵君碑旧拓本[M]//东洲草堂文钞:卷八题跋.清光绪刻本.此文所记为何绍基陪同其父何凌汉登阁浏览。“十六日,先生同陈石琴、张秋水,登范氏天一阁。”(25)(清)张其锦.凌次仲先生年谱:卷四[M].民国安徽丛书本.此为凌廷堪与陈石琴、张秋水同登阁。“内兄夏闰枝太守署宁波府,去秋到任。荃孙欲访天一阁,闰枝与范氏定约三月十八日开阁观书,遵旧例也。”(26)缪荃孙.艺风老人年谱[M].民国刻本.此记缪荃孙与妻舅夏闰枝相约登阁。
清钱维乔诗《范菊翁、李渭川、卢月船、范莪亭、卢东溟,招饮天一阁,观藏书,即席索和》(27)(清)钱维乔.竹初诗文钞[M]//诗钞:卷十三.清嘉庆刻本.,所记为钱维乔与好友李渭川、卢月船、范莪亭、卢东溟等人同登阁观书。
清全祖望作诗《丁酉小春同姚山期、葛同果、万考叔、董次公天鉴、徐石客,集天一阁,和姚韵》(28)(清)全祖望.续耆旧:卷六十三思旧馆八子之二[M].清槎湖草堂钞本.,记全祖望与姚山期、葛同果、万考叔、董次公天鉴、徐石客等人集聚于天一阁。
《天一阁碑目序》:“今年,予复至鄞,适海盐张芑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而侍郎之六世孙苇舟,亦耽嗜法书,三人者晨夕过从,嗜好略相似。”(29)(清)钱大昕.天一阁碑目序[M]//潜研堂集:文集·卷二十五.清嘉庆十一年刻本.此文所记为钱大昕与张芑堂、范苇舟多次同登阁。
亦有请他人代为登阁抄书者,如吕留良《与万祖绳书》:“天一阁中闻有袁清容桷、戴剡源表元集,为刻本所无者,并望为弟全抄见寄。”(30)(清)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复姜汝高书[M]吕留良请万祖绳代为抄写天一阁书。“吾友马氏嶰谷半查兄弟,……而遽罢官,归途过之,则属予钞天一阁所藏遗籍,盖其嗜书之笃如此。”(31)(清)全祖望.藂书楼记[M]//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记.清嘉庆十六年刻本.全祖望代马氏兄弟入阁借抄。《崇文书目跋》:“《崇文总目》六十六卷,予求之四十年不得,归田之后,闻四明范氏天一阁有藏本,以语黄冈张学使按部之日,传抄寄予,展卷读之,只有其目。”(32)(清)朱彝尊.崇文书目跋[M]//曝书亭集:卷第四十四跋.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朱彝尊请张学使代为抄写。
观以上文献,范氏家族将藏书的保护与使用紧密结合起来,严格的制度并未约束范氏向外人开放阅览与抄写珍籍。作为私家藏书楼,这样的行为是难能可贵的,褒扬与赞叹也是连绵不绝。
三、对天一阁的评价与效仿
检索古时学人对于天一阁的评价,赞誉之情溢于言表,如:钱大昕《题范氏天一阁》:“天一前朝阁,藏书二百年。丹黄经次道,花木陋平泉。聪听先人训,遗留后代贤。谁知旋马地,宝气应奎躔。”(33)(清)钱大昕.题范氏天一阁[M]//潜研堂集·诗续集:卷四.清嘉庆十一年刻本.钱泰吉《跋甬上范氏集古印谱》:“若天一阁之碑、之书,藏弆三百余年,为海内巨观。今览其目录,亦恐如子宣书帖之亡也忽焉。呜呼!岂独范氏一家之厄也哉?近闻天一阁书完守无恙,亦幸事也。冬日附识。”(34)(清)钱泰吉.跋甬上范氏集古印谱[M]//甘泉乡人稿:卷四.清同治十一年刻光绪十一年增修本.阮元:“海内藏书之家最久者,今惟宁波范氏天一阁岿然独存。”(35)(清)阮元.揅经室集:二集卷七[M].四部丛刊景清道光本.细察之下,诸评价多集中于其书与阁能长久保存这一点,为中国文化留下诸多珍贵遗产。
正因天一阁藏书制度带来的效果之佳,令人印象深刻,故后人在建设藏书楼时纷纷仿效,或参考其建筑设计,或学习其藏书制度,乾隆帝建设四库七阁参照天一阁的做法已广为人知,其他亦为数众多:

晚清学者志刚游历西方参观私立学校图书馆时说:“同治七年……闰四月……初七日,观书院。本地富人古博尔者,老而无子,乃竭产独力建造大书院,凡西国所应学者,区以别之,各有教师,又各有学习之所。藏书之室,镕铁为架,倚壁成城,择人专司,许观不许借,略同宁波天一阁之制。可谓善用其富者矣。”(39)(清)宜垕编.初使泰西记[M].清光绪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同治七年为公元1868年,此时西方图书馆的开放性为中国学者所敬仰,视之为中国藏书楼封闭性的对照。而志刚却认为此时西方的学校图书馆借阅制度略同已建成达300余年的天一阁之制,说明时人眼中中国藏书楼的开放性绝不逊于西方的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