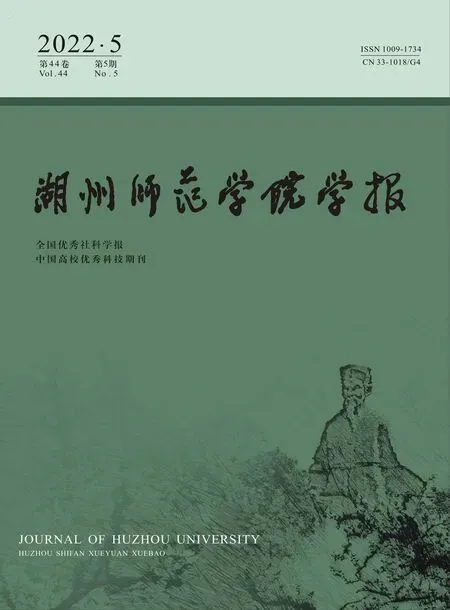明代太湖地区筹办水利经费的经验与教训*
钱克金
(湖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太湖地区经济的崛起和持续发展,水利的有效开发和适时治理对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然而自宋代以后,太湖地区无序盲目开发较为严重,不仅加剧了既有的水利废坏,而且增加了水利治理的成本和难度,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发展的空间,可以说,宋元明清农业经济是在艰难修建水利的过程中曲折前行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而农业的充分发展是工商业兴起的基础,更何况水路交通的便利亦是工商业兴盛的重要条件。明代该区农业和工商业皆名列全国前茅,这与其水利建设是分不开的。诚如时人所言:“国家财赋多出东南,而东南财赋尽由水利。”[1]422据已有研究来看,其水利修建并非一帆风顺,根本原因在于工费筹措之艰难。如所周知,水利治理必须要有相应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撑,否则难以有效进行。明代自中叶以后不仅土地兼并加剧,而且因北边少数民族的入侵、东南倭寇的肆虐,军饷有增无减,国家财力不济,民间供输益艰,水利经费的筹办亦越来越困难。就此,万历初水利监察御史林应训有切肤之言:“所需工费不赀,搜刮库藏,既无锱铢之余;加编民间,又苦供输之困,措处财用为艰。”[1]459然而费用无法筹措,民工就难召集,而水利失修,灾害荐臻,民益贫,国益困,可谓是恶性循环。这在中国古代历朝多有不同程度的重演,对历史进程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学术界,仅见熊元斌就清代江浙的有关事宜做过专门探讨,在述及明代水利修建时,其认为原则上主要是以徭役征发方式进行[2]88-96。其实有明一代就太湖地区来看,以徭役征发方式进行的水利修建所占比重有限,即使如此,亦得具备相应经费方能有效进行。因为一些较大水利工程所需劳力,并非完全可以就近征发,而搭棚、建灶以及柴薪等皆需费用,甚至口粮、医药亦不例外,更何况还有水利本身所需的材料费。水利经费筹办的好坏,无疑是水利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据史志记载,总体而言,历史上水利经费主要来源于备荒的仓储积粮,或有关政府机构的财政支持,且无具体数量规定,只是在修建时根据实际需要和存粮的多少或财政状况酌情划拨,我们不妨称之为隐性数据。而自明代中期以后太湖地区出现了专门为修建水利征收银两的导河夫银制,其余可谓是名目繁多的临时性应急筹措,这些经费数目记载相对明确,可称为显性数据。通过对这两组数据的求证,并将其与水利治绩相对应进行分析,发现仓储粮食充裕、政府财政收入较为稳定时,水利建设相对为好,而显性数据门类越多,水利修建却越不尽如人意。后者经费则是在前者亏空的情况下,另辟蹊径艰难筹措所得,有些甚至带有搜刮性,尽管门类多,却很难满足水利修建的需要。本文就此作一初步性的探究,以便总结其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当今水利建设事业提供些借鉴。
一、洪武至景泰:经费以仓储积粮为主、政府财政扶持为辅
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水利经费是指用于水利修建所支付的货币与粮食。而水利经费的筹办,包括筹备与筹集两个阶段。前者是指在水利未兴修前就进行的未雨绸缪的钱粮储蓄;后者是指为修建水利临时性地筹措。明朝初期从洪武到景泰八十九年间,相关史籍中罕有直接筹集经费数据的记载,如果简单依靠直接数据来分析问题,自然会得出:明初要么没有水利修建,抑或完全以自带口粮和工具的方式征集劳力进行。然而从文献记载来看,其初期水利建设是中、后期所不能及的,亦不是不费一钱一粮地以徭役方式来进行[3]35-42[4]29-35;与中、后期截然不同的是水利经费难以筹措的记述可谓罕见。那么明初经费又是从何而来?
从所见史料来看,一为永乐初夏原吉治理苏、松水利,支取官粮三十万石[5]850;另一则为宣德八年修建常州武进孟渎闸,是支取往年节省的赋税费,买材料雇募工徒进行的。时人杨荣有记:“工部侍郎周君忱,巡抚苏、常诸郡,常之武进,故有孟渎河闸,以通东南漕运,及商贩之舟;且溉傍近田数千顷,岁久闸坏,公私病焉。常守莫君愚,图改作之,以役费繁重,谋于周君,议以克合,遂发往岁节省税赋浮费,以市材僦工,砻石积渐,……其下先错列巨杙,贯以长松,而后宜石焉。东西石甃,纵以丈计,为十有六;崇以丈计,为二有五;中广视纵当八之一;南北为雁翅状,以杀水势,中夹水石,凿以纳悬板,而上下之。……用徒匠以日计,二万三千七百六十;木以株计八千九百;石以丈计三千九百;灰以斤计二十二万;砖以片计十有二万。”[6]910-911由此可见,该项工程使用经费是不少的。再者,为正统元年,重建常州江阴蔡泾闸,其费用源于诸郡仓储积粟。史载:初,周忱“因民有余粟,积于诸郡仓庾皆充。至是,会计其用,可数十年矣。乃发粟市材用,诸物惟石艰得,乃取于姑苏洞庭山,工者亦苏人,令琢磨以舟载至,皆给粟偿其力。石计四千五百丈;木二万二千株;砖二十万;铁一万斤有奇。工匠计百人,役民二千五百人。食以粟计,二千九百余石。始于正统元年八月,以是年冬十一月成”。正统十年,“周忱修吴江石塘、土塘三十里,间亦以石固之,费出于官,但日役千夫而已”;同年,杭州府钱塘县化湾塘闸遭洪水冲毁,周忱又“动支广丰仓米三千七百石有奇,抽分厂木三千余株,筑治如故”[7-9]。以上修建水利的费用皆取之于官,主要是仓庾积粟,言之凿凿。还有二条分别为:“洪武二十七年浚孟渎,工省费俭”;及正统五年正月,罚苏、松、嘉、湖、常五府囚徒,由巡抚侍郎周忱总督修治太湖堤岸[10]340[11]。前者引文间接说明此次修浚是有所花费的,而后者亦得支付口粮,但并没有说明经费的来源。而完全由民间负担修建的水利,仅为宣德三年开浚的七鸦浦,“令受利人户出力开浚”[12]。史籍中有关明代初期水利建设临时性筹集经费罕有记载,但以备不测筹备钱粮的史料还是不少的,从记述来看该项事业颇有建树。
朱元璋起自民间,深知百姓之苦,甚为关心民生,不仅用心于积谷备荒,而且注重平均赋役。史载:“太祖洪武初,设预备仓,朝廷出楮币,诏行省各选耆民,运钞籴粮,储之乡村,以备振济,即令掌之。其后州县充积,而籴犹未已。至二十四年八月,帝恐耆民缘此以病民,乃罢耆民籴粮。”[13]不仅“京卫有军储仓,……各行省有仓,官吏俸取给焉”,而且“州县则设预备仓,东南西北四所,以振凶荒”[14]1924。立国之初,百废待兴,他担心役重伤及贫民,“命中书省验田出夫”,并令户部“谕各府州县官,凡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赋役均,则民无怨嗟矣。有不奉行役民致贫富不均者罪之”[15]。据此我们不难推定洪武年间水利修建应该是按丁粮多寡、产业厚薄来征集民夫的,口粮则是支取预备仓的积粮,材料费支用官银。太祖上谕亦可佐证这一推断,洪武二十六年,“上谕都察院,凡各处闸坝陂堰,引水可灌田亩,以利农民者,务要时常整理疏浚。……若隶各布政司者,照会各司直隶者,札付各府州县,或差官直抵处所,踏勘丈尺阔狭,度量用工多寡。若本处人民足完其事,就便差遣,倘有不敷,著令邻近县,分添助人力,所用木石等项,于官银见有去处支用,或发遣人夫于附近山场采取,务在农隙之时兴工,毋妨民业”。洪武三十一年,又钦颁教民榜文:“民间或有某水可以灌溉田苗;某水为害,可以堤防;某河壅塞,可以疏通。其当里老人,会集踏看,丈量见数,计较合用人工;并如何修筑,如何疏通,定画计策,画图贴说,赴京来奏,以凭为民兴利除害。”[16]357-358可见永乐初,夏原吉能够支取官粮三十万石以有效治理苏、松水利,其前有效储备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水患得以消除,然因“东南数郡之民频年厄于水患”,饥荒仍有待于救济,以故永乐帝又敕谕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官员,“往督郡县,亟发仓廪赈之,所至善加抚绥”[17]360。上文清楚说明:洪武年间的有效粮储建设不仅保障了水利的兴修,亦为灾荒赈济提供了支撑,而这一积谷备荒之制永乐朝亦应有所继承。
其后由宣德五年至景泰元年,周忱受命巡抚江南,整顿赋税,治理水利,“民不扰而廪有余羡”,“当时水利疏通,为国大利”[18]4217[19]635。此并非虚言,有史为证:“初,太祖平吴,尽籍其功臣子弟庄田入官,后恶富民豪并,坐罪没入田产,皆谓之官田,按其家租籍征之,故苏赋比他府独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万石,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二万石,民不能堪”。以致宣德年间,“苏州一郡,积逋八百万石”。周忱到任后,与苏州知府况钟进行了认真的实地调查,“曲算累月”,将苏州官田之租减省了“七十二万余石,他府以次减,民始少苏”。同时,对“加耗”赋税实行贫富均征,并将其中节省的税粮连同官钞平籴的粮食,设立济农仓储之,以备振贷;且规定修建水利,可无偿支取,诚然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农。有史可证: 宣德“七年,江南大稔,诏令诸府县以官钞平籴备振贷,苏州遂得米二十九万石。故时公侯禄米,军官月俸,皆支于南户部。苏、松民转输南京者,石加费六斗。忱奏令就各府支给,与船价米一斗,所余五斗,通计米四十万石有奇,并官钞所籴,共得米七十万余石,遂置仓贮之,名曰济农。振贷之外,岁有余羡,凡纲运、风飘、盗夺者,皆借给于此,秋成,抵数还官。其修圩、筑岸、开河、浚湖所支口粮,不责偿。耕者借贷,必验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给之,秋与粮并赋,凶岁再振。其奸顽不偿者,后不复给。定为条约以闻”。在其有效治理下,“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赋”;甚至“诸府余米,数多至不可校,公私饶足,施及外郡”(1)《明史》卷153《周忱传》,第4212-4213页、第4216页(注:原文为“减至七十二万余石”,据注释6实为“减省”);“加耗均征”,参见:伍丹戈《明代周忱赋役改革的作用和影响》,《明史研究论丛》(第三辑)1985年。。这一充足的粮食储备为兴修水利提供了根本性保障,亦即:周忱“兼理浙西,粮储均平,赋额节省,仓庾甚裕,便宜动支廪粟,故得奏用多官”[1]502,以兴修水利。周忱在任期间,不仅水利经费筹备有方,而且对水利修建的规划亦堪称典范,尤其圩岸的修筑与防护,其规定:“岸高六尺,以平水为定,高下增减,基阔八尺,面阔四尺,谓之羊坡岸。其内有丈许深者,于大岸稍低处,植以桑苧,谓之抵水;环圩植以茭芦,谓之护岸;其遇边湖边荡,甃以石块,谓之挡浪。又于圩外一二丈许,列栅作埂,植茭树杨,谓之外护。……每年县官于农隙时,诣看坍损,督塘长、圩甲修之”[20]683-684。其实,永乐年间夏原吉治水亦复如此,史载:“永乐中,治水东南,尚书夏忠靖公创于前,通政使赵君继任于后,无不注意于堤防,皆妙选官属,分任诸县。而二公则周爰相度,而考课焉。其法常于春初编集民夫,每圩先筑样墩一为式,高广各若干尺,然后筑堤如之。其取土皆于附近之田,又必督民以杵坚筑,务令牢固。既讫工,令民罱泥填灌取土之田,必使充满。复于堤之内外增广其基,名为抵水。盖堤既高峻,无基以培之,则岁久必颓矣。又课民于抵水之上,许其种蓝,而不许种豆。盖种蓝必增土,久而日高;种豆则土随根去,久而日低矣。……厥后,二公去任,二三十年间,岂无水患,而不至于大害者,良由堤防犹存之力也。”[5]800
总之,有明一代治理水利最为有效的是初期的夏原吉与周忱,其后有关论及水利者无不称誉。嘉靖朝凌云翼即道:先朝“尚书夏原吉、侍郎周忱等,皆久任地方,累岁经画,伊时,百姓乐业,库藏充盈,诚有所自。”其后万历年间的徐桓与薛贞亦交相称道:“尝考先朝,屡命大臣经理吴中者,前后不下数十人,而其有功于水者,则惟尚书夏原吉与巡抚侍郎周忱尔”;“粤稽古昔,历代治迹昭然,即我朝留心水利,如夏原吉、周忱等诸臣,经画灿然”[1]446、483、487。而最为称道的是周忱,嘉靖年间身任巡按御史的水利专家吕光洵,在条陈水利五事中即道:“先朝大臣经理吴中水利,惟巡抚周忱功最著。”[21]两位大臣之所以能有效修建水利,根本原因在于初期钱粮储备有方,仓廪充裕,否则再贤能亦难成无米之炊。诚如时人所论:“工役、计费二事,常相须,计费足则工役举。”[5]809此并非妄议,因周忱整顿赋税有方,水利治绩显著,名声显赫,为朝中少数大臣所不容,不断遭到弹劾,于景泰二年被迫致仕。其后太湖地区储备渐至萧然,水利懈怠,灾害频仍,吴中道殣相望。《明史·周忱传》有载:“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无轻易忱法。然自是户部刮所积余米为公赋,储备萧然。其后吴大饥,道殣相望,课逋如故矣。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处处祀之。……诚异夫造端兴事,徼一时之功,智笼巧取,为科敛之术者也。然河渠之利,世享其成,而忱之良法美意,未几而澌灭无余,民用重困。”[18]4217可见钱粮储备对修建水利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周忱离去,但其储备的粮饷和修建的水利还是可以惠及一时。至天顺年间,吴中又遭大灾,朝廷特派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崔恭来治,这亦是本文以此作为中期上限的原因。
二、天顺至隆庆:导河夫银及以权宜之计获得各类公私钱粮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明代中期水利经费筹办的状况及对治理的影响。天顺二年,右副都御使崔恭集常州、苏州府三万人疏浚运河镇江京口至常州奔牛闸河段;“又设法得公余白镪九百八十两,俾修砌京口甘露、吕城奔牛旧闸;于郡城西南二门,各置浮桥,以通往来;于朝阳门外,増建新闸,以防水涸”。随之,又令昆山、嘉定、上海三县各出夫一万疏浚吴松江,三县县令“乃选夫长,乃立藁舍,乃赈钱米”,始于次年二月,至三月功毕,“夫工计一百九十八万;米石计二万七千;钱文计二十万五千。江深一丈一尺;阔十丈二尺;长起夏驾口,至孙基浜,共长一万三千七百一丈,江复通流,迤逦入海”(2)参见:(明)吴节《镇江重开漕河记》、范纯《嘉定县重修沪渎龙王庙记》,载《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五《记》,第912页、第912-913页。《明史》卷159《崔恭传》载:“凡浚万四千二百余丈”,第4339页,与引文有出入。。由引文可见,这两次大规模修建水利的经费应取自于官,且疏浚吴淞江的钱米由三县赈济,应该说济农仓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余力。
其后,成化二十三年间,除海塘工程外,本区最大水利修建则数吴淞江,亦即:成化“八年,浚吴淞江。东自嘉定县徐公浦,西至昆山县夏界浦,凡一百三十里”;十年,巡抚都御史毕亨与苏州知府丘睿,又议开吴淞江西段,“自夏界口至西家庄,嘉定县分浚六千三百五十三丈六尺;昆山县分浚五千三百五十三丈七尺,用夫四万六千八百三十工”(3)参见:同治《苏州府志》卷十《水利二》(志文注:前一次开浚,沈启《吴江水考》为七年);崇祯《松江府志》卷十八《水利三》,载《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因史料阙如,前一次经费情况,及第二次议开是否实践,不得而知。然而从成化十四年巡抚直隶右副都御使牟俸奏疏来看,其吴淞江疏浚应有“虚应故事”之嫌,否则不可能出现:“近见浙西各府地方,濒年旱涝,田谷不登。人民出常赋输官之外,室如悬磬,日不聊生。”[22]其余水利修建,稍具规模的:一是成化八年,吴县知县雍泰筑西华石塘,历时一月而成,“凡为塘三千一百丈有奇;博其址,广十尺;而杀其上广,得八尺;高如其上之数”,“凡廪食之费,皆取之公帑羡钱”;其次乃为成化十一年,巡抚都御使毕亨等筑常熟县尚湖西北赵段圩田围,“堤之袤延亘数里,丈一千有奇;用木为橛,橛之内编以竹;甃石为址,而高与土等;上广八尺,而下加三之一,固基本也”,所用“木以万计,竹倍差于木;石以舟计,及二千艘。钱谷之需,累钜万有奇,工役则五万三千有奇”。因“财获于官,力借于民。……量田授役,获利者倍出其工,邻壤者半焉”,以故“用虽伙,而民不见扰也”[8]。显而易见,以上水利修建的费用皆取自于公帑与积粮。而规模相对小的:一是成化八年,无锡县知县佟珎浚走马塘,为“县民赵汝明捐赀独浚”;另为成化十九年,宜兴县知县袁道募工“浚便民河并观鹤溇”,费用应是出于官,因其是募工开浚,且“开毁官民田百八十亩有奇,皆公偿其值而别均其税”[10]342[6]917。
由上文我们清晰可见,成化二十多年,兴修水利虽以官府出资为主,然而除吴淞江外,其余主要是局部的小规模修建而已,难免水旱频仍(4)从《明宪宗实录》记载来看,其水旱灾害颇为严重,赋税蠲免亦非同一般。。水利缺乏应有修治,一旦阴雨连绵,抑或大雨滂沱,必然会发生大灾,其后“弘治四年、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饥疫,死者不可胜数”,即是明验。而水利懈怠的根本原因乃是经费不济,时任南京户科给事中杨廉言之凿凿:“有司非不欲浚治,而阻于工费,制于豪右,束手观望,卒不能成。”[19]639[1]419据此,我们不难想象起初周忱创设的济农仓储制度,至此已废坏殆尽。时任提督苏松水利、工部主事的姚文灏即道:其“历岁既久,名存实废。水旱之备日弛,公私之积渐微”[23]。
为了能有效修建水利,弘治七年,被派往江南治理水利的工部侍郎徐贯,不得不重新开启水利经费的筹备工作,亦即:“设导河夫于沿江(吴淞江),每岁于均徭内编银贮库,以备兴修雇募之用。”[24]然而据相关史料记载,这一措施到弘治十年才成为定制。杨循吉《导河夫志略》有载:“弘治十年,水利主事姚文灏奏设,比照江北运河捞浅及嘉兴海塘夫例,每年于均徭内定拔,工部为覆奏备行;巡抚都御史朱瑄会同本官,议行苏、松、常、镇四府,将本年均徭,除崇明、靖江二县隔截江海不编外,其余每年每里各佥导河夫一名,每名折收工价银六两,悉听提督水利衙门支取,就近雇夫开挑河港,行一年矣。其次年,……减作银三两,编则照旧不改。”[20]673这一制度的实行,由此开启了以雇募劳动力为主的水利修建方式。以下将弘治及之后有关水利经费的数目及由来作一胪列,以便揭示其特点。

表1 弘治及之后的水利经费数目及由来

表1 (续)
从以上不完全统计的水利经费来看,仍以官方提供为主,其中明确具体来源的有导河夫银、豪民私占芦苇与茭蒲之罚金,或围垦河湖之罚赎,以及其他罚征的钱粮,借支的军饷等。其余则是官民捐资、捐粮,以及犯科者出资、出力等。官方提供的经费,除导河夫银、各类罚赎及借支军饷,来源明确,其余不少来源及筹措方式不得而知,但这些信息有助于从一定层面更好地揭示该时段水利治理得失的原因。我们不妨来继续深入求证。
诸如:弘治七至八年,不仅给过修建水利劳动力口粮153 507石,材料费860两,还“赈济过苏州并嘉、湖等府县贫民二十万八千四百三名,给过米三十四万二千一百四十七石八斗,麦千四百九石,谷二十二万一千九百七十四石,银三千九百五十三两。于是,民颇获安,东南水患亦自是少衰息矣。”[25]用于救济灾民、治理水利的钱粮,数目如此之大,又是如何筹集而成?时人王鏊的记述给予了答案:“当臣(何)鉴巡抚之时,江南大饥,上救荒十二策,得兑军留州禄米、军储诸费八十余万,于是江南诸府在在充牣。时朝议浚吴淞、白茆等河,众方持其议,以费无所出也,鉴内请以兑军诸费充焉,其事始济。……此役成,而东南无水患。”[26]1156-1157由此可见,其费用主要是支取“兑军留州禄米、军储诸费”。其后,水利经费筹备,虽以征导河夫银方式继起,并为弘治后期有效治理水利提供了一定保障,但亦未能善始至终。因“江南粮差繁重,兼征此银,民实不堪,往往有致卖鬻子女、房屋以输者;既入于官,又不全给公用,势豪之家,指以造桥为名,多有求索,士民皆言未便”;而抚按衙门亦认为历年所征导河夫银“贮库银两数多,设若修河,足以够用”,为“苏民困”,“决请停止”,弘治十四年迫不得已被革除[20]673-674。嗣后,正德四年、五年,江南连遭大水,时任巡按御史的谢琛,欲用“以工代赈”的方法进行治理,然因所在府县钱粮空乏,上书请求“借取浒墅、北新等关课钞,以凑支用”[1]425。谢琛的请求并未得到批准,水患亦难以有效治理。两年后被派往江南治水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俞谏,同样面临难以筹集治水经费的问题,对一些规模较小的河道、圩岸工程,他采取了“照田多寡,分派丈尺”,“督令得利之人,趋时浚筑”。然工程浩大的白茆港等,因经费“无从措办”而难以兴工。其在奏疏中道:“欲便起工开浚,但查苏、松等府仓库皆虚”,欲加征百姓,而“地方人民连遭灾疫,逃亡数多,凋瘵之余,疮痍未复。……不无逼民失所,致生他患”。以故,他亦不得不上书请求存留“浒墅钞关正德六年春夏秋三季船料银”“正德七年四季船料银”,及“两浙两淮运司”积余盐等银,作为开浚之用,如“数内不敷,于苏、松等府征收正德六年分免剩余米数内,量支补助”[1]428。俞谏的请求同样没有结果,吴淞江、白茆港的治理亦不了了之。可见自弘治十四年导河夫银制被革除以后,以备兴修水利的费用,早已耗费无余。时人柴奇《上阁部请兴水利书》即道:“为此大举,所费不支。欲取之郡县耶!则饥馑迭臻,公私告竭。欲请之朝廷耶!则司农少府,辄以匮闻。”[19]634然而水利不修,灾害荐臻,百姓困苦流离,赋税亏空不已,事关重大。在朝中大臣接二连三上书请求下,正德十四年以后,水利经费方有着落。该年钦差总理粮储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充嗣,再次上书请求预处修建水利经费,其请有三:(1)按给事中柴奇奏请,“各府每里编佥导河夫一名,每名出银六两,如其不足,预编一二年,以周急用”。(2)据给事中吴岩所奏,“每田一亩科钱一文,每田一顷,科钱百文,秋成之时,折收白银,解府贮库”,以备兴修之用。(3)“乞敇该部,仍准将浒墅钞关船料银两,并两浙两淮运司盐银,或抄没叛贼钱宁等入官赃银,量为给发十余万两”,作为修建之费。“如或不敷,听臣仍查所属各衙门应支桩草银钱,并无碍赃罚官银,及量行增添均徭银两,或催河夫田亩银钱充用”[1]432-433。应该说正德十六年至嘉靖元年大修水利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此。其后,水利经费无外乎来源于导河夫银,“或动支衙门之赃罚,或查处无碍之官钱,或量罚有罪之豪右,或激劝尚义之巨室”,抑或借支军饷等[1]447-451。导河夫银自弘治十四年被革除以后,在水利经费无着落情况下,时常加以重启征收,并成为明代中期水利经费的主要来源,亦是唯一预先设处的经费。从嘉靖四年蔡乾所上《计处导河夫银呈》来看,正德十五年就已重启征收导河夫银之制,苏、松、常、镇四府,除松江府华亭、上海、崇明三县,因特殊原因暂“未经派征”,其余例行征收,并“奏准永为定例”[27]531-532。其后,沈启《导河夫银议》又道:“导河之役,始于吴越钱氏撩浅卒,……迨至熙朝,额定派征若银,而本县岁征里甲,以备浚瀹、修筑之需,惟嘉靖十六年,均一田粮时,无水患,尽厘革之”;然“至二十六年,议复派征如其前;三十六年,郡改为驿递修船之费,余待水利之用焉”[5]807。上文清楚说明自正德十五年重征导河夫银起,断断续续行使计有二十七年之久。此后,万历、天启、崇祯年间,皆有过导河夫银之征。
纵观明代中期水利经费的筹备,是以征收导河夫银为主,其余皆为权宜之策。明代役法,原则上“以里而派者,谓之里甲;以田而派者,谓之均徭”。导河夫银,即为“毎年于均徭内定拨”人夫,“毎里佥夫一名”,出银若干,由官府雇人应役,理应是按田征收。然而明代均徭法,弊端丛生,有“大户之诡寄也;奸猾之那移也,花分也,贿买也;官户之滥免也”,导河夫银势必以中、下户承担为主;加以该区赋税綦重,百姓自然难以完纳[28]294-295。而所得之银又未能专用于水利,或“挪移支销”他用,或“久为豪猾所侵”[1]448、442。以故该项经费的筹办,难能有效保障水利治理的正常进行。至于“罚赎锾”,除犯罪赎金外,主要是对豪民围垦河湖追征的产业税,虽有所得,却相应地给予了盲目围垦的官方依据,不免给水利带来潜在危害。由此可见,明代中期水利修建不能有效进行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费难以筹办,更确切地说是经费筹备无方。时人吕光洵就此有切中之论:“水利为三吴急务,计费实兴修大端。设使计费不足,虽欲兴修,得乎?……召募不患无人,给散不患无制,所患者计费不足耳!尝考往岁兴修,其出银之法,皆临时取办,艰难百端。数年以前,各州县尚有导河夫银,后皆视为不急之务,虽在官者,亦为有司别项支销,而导河夫不复雇募。”[27]543
三、万历至明末:有限导河夫银及临时的应急筹措
明代嘉隆万时期,农村贫富两极分化最为迅速,主要表现为:官豪势要之家大量兼并土地,且千方百计规避应尽的赋税义务[29]11-15。由此,广大农民拥有的土地变少,而承担的赋税额加大,不仅影响国家赋税的征收,水利经费的筹措也更为艰难。早在隆庆三年,海瑞为大修吴淞江和白茆港等,因经费难以筹措,迫不及待地私自借发兵饷兴工。其在《请补河工钱粮疏》中道:“其吴淞江工,候旨未下,臣权宜借发松江府、苏州府练兵银各一万两;镇江府银二万两。白茆河,借发常州府练兵银一万两,苏州府四千两。”而白茆港,因海瑞调离,“功竟不就”[1]452[8]。如所周知,海瑞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清官,他之所以能够“奋然独任”,未等皇帝下旨允请,就敢“借支军饷”大修水利,这与其“志切匡时,祸患不顾,心急扰民,嫌疑不惜,注厝施为,出人情意料之外”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可这样的官员在明代却是绝无仅有的[30]712[24]。自万历以后社会矛盾益发尖锐,国势每况愈下,水利经费的筹措可谓是举步维艰,基本上是临时应急筹办为主。从以下胪列的历年水利经费及来历情况可见一斑。
从表2所列情况来看,明后期治理水利经费的来源主要为:导河夫银,修河米折银,公帑银,有关衙门追赃、罚赎银,存留宗人府银,违占河湖滩地等追征税,门摊钞租地价,湖墅关捐羡银,吏农超参办复纳例银,官民捐资,以及田主按亩出资贫民出力等。其中修河米折银为运河专项经费,是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为协力修浚境内运道而专门筹备的银两;所谓“门摊钞租地价”,是指“侵占傍郭河渠”所建屋宇,主要为商铺,而未经拆除“存留征价”之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门摊税;吏农超参办复纳例银,又曰超参办复吏农河工银,则为修建水利时,分督官吏与应役农民未按规定或式样完成任务,而被罚用于重新修建的罚金(5)参见:(明)林应训《开浚孟渎河工疏》《开浚吴淞江工完疏》(皆万历五年上),载《吴中水利全书》卷十四《章疏》,第464-465页、第471-473页。另据范金民《明代嘉靖年间江南的门摊税问题——关于一条材料的标点理解》,门摊原指临街摆摊,其买卖逊于铺面,所纳之税为门摊税,但实际征收时铺面、门摊部分,合而为门摊税,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这一期水利修建经费的来源可谓五花八门,除导河夫银是唯一预先设处,但其在总经费中所占比例已无足轻重;而其余则为临时性东挪西凑的应急筹措,甚至极尽搜刮之举,亦难满足水利修建的需要。自万历以后水利经费难以筹措的困境,崇祯初年工科官员言之真切:“朝宗故道,弥望桑田,海忠介而后,非阻于虑始之难,则苦于经费之窘;屡烦盈庭之议,而迄无成说者。”[1]492

表2 万历之后的水利经费数目及由来

表2 (续)
纵观明代后期,唯有万历五、六年及十六年对太湖地区实施了大规模水利修建,其余皆因经费问题只能作局部性的小规模修补。万历五年,兼督水利监察御史林应训为开浚吴淞江、白茆港等,经查“各县虽有淘河夫银,多者不过三百两,少者仅二百两耳,施之平时,尚不足以应一枝河之役,……至于库藏,则连年织造,搜括无遗”,为筹措相应经费,绞尽脑汁。一方面极尽所能地清查“滩占田荡,及侵占傍郭河渠”等,定价征银;另一方面不得不借支运河专项经费,亦即修河米折银。其间经费筹集可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苏州府并各州县,解各年导河夫银,七千六百六十四两七钱一厘二毫二丝;长洲县解征完滩地价银,二千九百九两三钱四分九厘九毫;吴县解征完滩地价银,六千六百四十三两三分二厘六毫;昆山县报征完滩地价银,三千五百二十二两三钱三厘二毫;吴江县解扣省厂夫银,七百二十两,水夫银,九十六两,又解河工银,六十三两一钱八分三厘三毫;嘉定县解扣省厂夫银,五百五十一两二钱;苏州府并长、吴二县解社仓米谷易银,四百七两二分二厘;苏州府解追完罚犯河工银,三百五十八两三钱,又辩(疑为“办”)复吏河工银,四十两;太仓州解加纳阴阳官河工银,三十两;常州府县解罚犯河工银,二百两,超参辩复吏农河工银,一百五十两;苏州府县解完按院赃罚助河工银,一百九十三两二钱二分七厘;镇江府解嘉靖四十四年分存剰练兵银,四千八百八十八两六钱七分七厘八丝二忽九微五沙八尘,辩复承差河工银,五十两;江阴县解军犯长解银,二十两;苏州府借支征完各州县解各年修河米银,二千四百五十一两六钱七厘二毫二丝二忽;常州府解修河米折银,五千三百五十七两二钱一分六厘八丝五忽四微;镇江府解修河米折银,五十八两八钱五分七厘五毫九丝七忽九微四纤一沙一尘一埃。又各府州县解兵备道项下赃赎助河工银,共五千九百二两五钱一分六厘七毫四丝,万历钱十万文。以上共银四万二千二百七十七两二钱三厘九毫四丝七忽二微四纤六沙九尘一埃,万历钱十万文[1]462、471-473。
时至万历十六年,江南“水患叠仍”,“民穷财尽”,地方再已无力筹集相应治理经费,而“堪借京师内帑,亦无多余可发,惟查南京户部颇有积蓄”,不得不动支其帑银十万两,以根治水患。然而这一次修建,因管理不善,“工竟无成,……十万帑银付之东流”[1]482-483[29]712。其后因经费问题,水利修建几无建树,由此,水旱频仍,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国运难维,对明王朝的灭亡无疑起了加速作用。
综上所述,有明一代太湖地区水利经费筹办的状况及对水利建设的影响,已较为明晰。初期水利经费主要来源于预备仓和济农仓,兼由政府财政辅助,因仓储经营有方、积蓄充裕,加以财政收入稳定,为其水利修建提供了根本性保障。其后,由于仓储经营不善,钱粮储蓄日渐式微,水利治理举步维艰,但继起的导河夫银征收制度,亦为中期水利事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明后期济农仓已名存实亡,财政亏空,水利经费的筹备虽仍以导河夫银征收为主,然而其本身存有较大不合理性,自然未能有效实行,所起的作用亦只是杯水车薪;其余经费筹措,乃是临时性的应急之举,自然困难重重,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从本质上看,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性原因乃是,该地区财富的占有与公共水利建设费用的承担,在中央与地方以及行政区间、自然乡村之间,甚至家庭间的分配上,是不成比例的,甚而是逆反的。水利经费固然是水利建设的根本性保障,然而劳动力起用和分配方式,以及任职官员的经营能力和责任心等,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此将作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