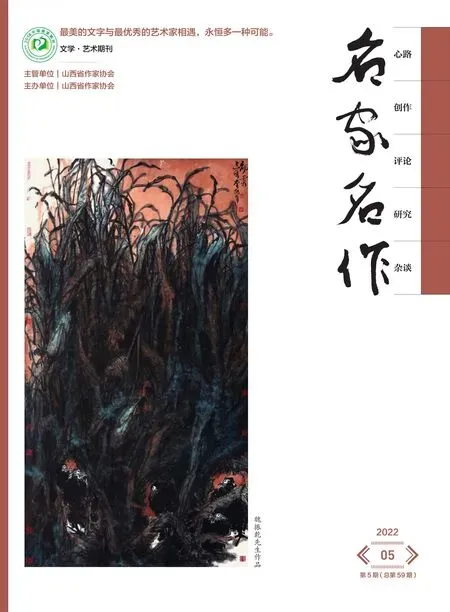《果园城记》的复调性解读
李 谦
1938年,流落他乡的师陀和许多游子一样,总是忍不住对故乡的怀想。于是,他在远离故乡的上海展开一次次深情的回望,经过八年之久完成《果园城记》这部系列小说。作者通过回忆、观察和想象串联起18篇小故事。每个故事有一个主要的思想主题,它们相互联系又各不相干,有的相互发生对话,有的相互冲突,这些不相融合的声音在小说中此起彼伏。从中原小城到摩登都市,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让师陀对故乡乃至民族的文化氛围和现实环境产生新的思考,一方面是作者对乡土落后、停滞、愚昧的极力批判,另一方面是在抨击都市文明病的同时亲近乡土。风景描写弥散着故乡温情,但在人事叙写时又爆发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恨,牧歌情调与挽歌气氛的融合并存形成《果园城记》独特的复调氛围和美学风格。
一、叙事的复调性
小说的开篇《果园城》是以马叔敖偶然还乡的所见所闻为机缘,故事随着马叔敖的视线和回忆徐徐展开。对于马叔敖而言,此时的故乡只是封存童年记忆的小城,而“我”(马叔敖)只可怀着看客之心踏上这片土地,“我”的回忆、观察和想象为读者展现了果园城的风物及与城中人物各自不同的命运。从叙事本身来看,小说大部分采用马叔敖的叙事角度,作者企图借马叔敖之口描绘一个内涵丰富的小城世界,但作为小说人物会受到人物自身视角的限制,所以需要嵌套一个“说书人”的叙述声音来跳出人物立场进一步填充故事空白。换而言之,马叔敖在大多数时候扮演还乡者“我”的角色,但部分叙述话语并不符合人物本身的立场,这时候人物角色的声音被隐含作者的声音——说书人所遮盖,构成小说的双重叙事声音。马叔敖的人物形象就像被戴上隐含作者的面具一样,变得模糊不清,而非独立的“故事中人”。“说书人”声音的介入不仅帮助主人公马叔敖填充了人物自身无法见闻的事物,构建出一个更加翔实的果园城,而且能与故事拉开一段距离,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冷静洞察城内的悲欢离合,坐看城内的兴衰沉浮。
小说中常常出现人物马叔敖借助“说书人”口吻讲述故事的情况,在每个故事的开局、结尾和起承转合处都有明显的痕迹,譬如《塔》《说书人》《一吻》《狩猎》《三个小人物》等。其中《狩猎》讲述一个寻梦与失意的故事,刚过二十岁的孟安卿一心只为追寻梦想,他卖掉全部家产,离开果园城踏上了狩猎之旅。十二年后,偶然记起故乡的青梅竹马——姨表妹,索性回乡寻初恋之梦。在孟安卿的心中故乡似乎没有改变,但向熟人打听后发现,自己早已被这座“最熟悉”的小城遗忘,心爱的姨表妹也早已嫁人,“一阵失望压倒了孟安卿,突然间他感到兴亡变迁,时间加到人身上的变化”。狩猎多年的结果却是被家园和时间所抛弃,失落感和无力感回荡在故事结尾:
请不要说这种话:“那么我们应该含垢忍辱。一生老死乡井吗?”请不要这么责问我,我讲的只是平常故事。你如果高兴,我将告诉你:你不妨顺从你的志愿尽量往远处跑,当死来的时候,你倒下去任凭人家收拾;但记住一件,千万别再回你先前出发的那个站头。至于孟安卿,他珍重地将在果园城买的香烟塞进口袋,然后向车站那边走去,火车在等候他,一切旅馆和按月出租的房子都在等候他。
设置的隐含作者“说书人”打断了马叔敖(表面叙述者)转述故事的声音,从故事中抽离出来,直接与隐含读者进行对话和互动,读者就会不自觉地产生情感回应和价值认同。最巧妙的是作者用一句话交代了孟安卿别无选择的继续漂泊之旅,再将叙述者切换为马叔敖,企图控制住前面强烈的情绪渲染,将马叔敖的情思一步步转化为对精神返乡的思考。作者在马叔敖与“说书人”之间来回跳转,人物的话语同说书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复调氛围,这是师陀独具匠心的叙事策略。
二、思想的复调性
《果园城记》通过城中经典的生活样式和穿插在叙事中的风景描写来塑造小城的性格、情感和思想。自然风景作为含蓄的抒情文字,却深藏着作者无数情感的辗转与冲撞,承载着师陀感性与理性并存的精神世界。当师陀叙写故土的难堪不免生出绝望的哀叹时,那么自然风光便会将其缓缓冲淡,形成挽歌与牧歌的双重变奏。小说是从“回忆”的视角开启叙事,而在接受美学中就将“回忆”视为诗意生成的原因,小说开篇就以火车长的提问拉开了回忆的序幕:
我到哪里吗?他这一问,唤醒了我童年的回忆,从旅途的疲倦中,从乘客的吵闹中,从我的烦闷中唤醒了我。我无目的地向窗外望着。这正是阳光照耀的下午,穿越无际的苍黄色平野,远山宛如水彩画的墨影,应着车声在慢慢移动。
当回忆视角打开时,风景画立马就出现在车窗外,因为回忆拉开与当下时间的距离后会产生美感,从而过滤掉部分愁苦,渴望归属感的作者无意识地制造出美好的故乡幻象。自然景物营造了一种温柔宁静的意境,为小城增添了诗情韵味。师陀的写作时间正处于抗战年代,他屈身上海,面临民族危难与个人生存危机双重考验,回忆中的果园城自然成为可以寄托心灵的精神家园。果园城的美丽在于自然风光、人和动植物三者的完美融合,还有“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这里有姑娘门前的桃红,有酸甜可口的花红果,还有纯洁的白云、湖泊。葛天民享受平凡、知足常乐的旷达令作者羡慕不已,躺在小船上听“阿嚏”传说的愉悦,以及熟悉每家每户的邮差先生和卖油郎都带给作者难以忘怀的亲切感。
师陀辗转到上海后逐渐认识到现代都市文明与传统乡土文明的差异,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下,他更倾向于熟悉的乡土文化。从对自然景物的温情处理可以看出,师陀热爱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和淳朴真挚的乡民。但小说的后半部分对小城衰落的叙述取代了大量风景描写,原本故事中仅有的温存被喧嚣、躁动打破,暗示了果园城内某种秩序的崩塌。从《一吻》可洞见果园城新事物带给村民的巨大冲击,从前的火车站变成现在热闹的商场,原来的旷野建造了更多更怪的房子,过去手艺高超的匠人们被迫丢掉饭碗,街道萧条,人走茶凉。“小车夫、驴夫、脚驴、褡裢、制钱的是带过去了,和那个时代好的声音一同消失了。”故事主人公原本是一对甜蜜的青梅竹马,但因不同命运而分道扬镳,留在城里的虎头鱼失去手艺后改做车夫,为繁重的家庭负担日复一日地劳作,前途灰暗,令人沮丧。选择嫁到外地的大刘姐早已失去少女的清新气息,满身肥肉和金子,最终沦落风尘。《三个小人物》中的胡凤梧开办赌场打破了夜晚的宁静,有的村民输得倾家荡产甚至产生卖掉儿女妻子的念头;胡凤英的男友为了满足私欲不惜剥削庄稼人,用卑劣的手段骗取乡下人的钱……就此,果园城的美景遭到城市文明的侵袭后一去不复返,往日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和安分守己的乡民们早已被湮没在现代文明的废墟之下。师陀用色彩分明的眼光看待两种不同的文明,他厌恶都市金钱至上的思想观念,深刻批判人们为了满足欲望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
看似散乱的小说结构,实则是精心设计的结果:从开头到结尾演绎了果园城诗意逐渐消逝的过程。被破坏的自然风光以及遭污染的乡村文化生态带给作者深入的反思,他将都市文明视作一种异己力量,是束缚人的精神枷锁,压抑人的本性自由,而回归自然的田园式生活才能让生命个体重获自由,因此师陀就是在自然与文明、现代与传统的双重意蕴中构建美好的精神家园。
三、话语的复调性
师陀在文学史上的流派划分一直存在争议,他的小说既有怀念乡土、歌颂自然的“京派”风格,又有30年代左翼的主流话语,师陀的审美选择恰好处在中间位置,而这两种风格的对抗与平衡却形成了《果园城记》的美学张力。师陀1910年出生在河南的小地主家庭,先后接受了新文化的熏陶和左翼思潮的影响,1931年在北京参加革命运动。因此,在师陀的创作实践中存在两种话语,即“五四”时期启蒙者话语和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主流话语,两种话语的交织重叠丰富了作品的精神内涵,形成了新的审美景观。
前面论述了自然风景作为作者心灵的投影,幻化出一个丰富且复杂的精神世界,可从叙事学的角度看,风景描写有拉长叙事时间、减慢叙事节奏的效果,以便制造出一个“永恒”的果园城,巴赫金认为田园诗里的时间和空间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
田园诗的生活和生活事件,脱离不开祖辈居住过、儿孙也将居住的一角具体的空间。这个不大的空间世界,受到局限而不能自足,同其余地方、其余世界没有什么重要的联系。然而在这有限的空间世界里,世代相传的局限性的生活却会是无限的绵长。
果园城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虽然给予了乡民们平静和满足,无形中却成为亘古不变的封闭空间。乡民们依赖于这有限的空间过着重复单调的生活,以至于精神被禁锢在这里日渐委顿。城里的“塔”就是象征凝滞的空间意象,它见证小城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死离别,目睹一场又一场走向死亡的历史文化悲剧。作者通过“塔”的象征意义打开了一个启蒙者关注个体生命状态以及审视国民人格的叙述话语空间。过去技惊四座的说书人,虽然被视为卑贱的职业,但给沉闷的小城带来快乐和幻想,“我”的心灵不经意间被引向远方,可晚年的说书人贫病而死,在一卷破芦席包裹之下葬入荒野(《说书人》)。原本可以和虎头鱼终成眷属的大刘姐,只因被母亲当作谋利的工具,痛失真爱,坠入红尘(《一吻》)。接受新文化教育的油三妹,敢于追求自由和公平,但并没有得到城中人的尊重和理解,反倒成为他人口中的“疯子”,最终吞下颜料以死抗争(《颜料盒》)。从外地引进种植技术来改造家乡的傲骨,同样未能逃脱被同乡人捉弄的命运(《傲骨》)。作者并没有一味沉浸在对乡土文化的留恋中,而是看到乡村宁静之下的吞噬力量,更是看到容不得半点新事物的果园城不断地腐化、败落,带来新事物的人总会被无情地摧毁。作者以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情怀实践对生命状态以及底层妇女的现实关怀,而这种关注健康不悖于人性的生命形态恰好跟京派文学不谋而合。
师陀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并未将自身置于时代和政治之外。21岁的师陀就来到北京投身革命运动,参与过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在《北斗》杂志上发表过《请愿正篇》。1933年,师陀决定专职文学创作并坚定自己的文学观念,即不应在创作中用政治话语压抑自我。但救亡心切的师陀仍然将革命战斗的怒吼迁延到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写于抗战时期的《果园城记》潜伏着一套革命叙事话语。暗中统治果园城15年的巨绅——鬼爷联合胡左马刘四大士绅家族形成官绅勾结的统治秩序,鬼爷不担任任何职务,只负责扶植自己的势力安插在各部门,通过士绅包揽诉讼铺开利益网。此类权力结构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出身平民的社会精英也没有机会走入内部,久而久之城内社会结构得不到及时更新。即便如此,城内也不乏怀揣变革理想的青年,傲骨在师范学院看了《辩证法》《意德沃罗基》等相关理论书籍,试图传播新思想又试图利用理论重整家业;从小被布政第家两兄妹欺负的小张,强烈的阶级压迫使小张出走投奔革命;年轻的马瑶英和徐立刚也纷纷走上革命的道路……虽然一部分革新者以失败告终,但觉醒的革命意识和革命主动性在死水般的小城里显然是振奋人心的力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过于欧化的缺憾。双重话语结构蕴含了作者复杂的创作心态和身份认同,或者说是在上海沦陷区这一特殊时空语境折射出果园城形象的多重含义。
四、结语
师陀经历漫长的漂泊岁月,试图在北京寻找出路可又辗转到上海从事写作,像风雨飘摇的年代里许多青年一样迷茫、孤独和彷徨,在家国沦陷的痛苦里寻找精神家园,可又在寻找中幻灭与失落。回不去的故乡却在作者的回忆中充满抒情意味,多声部的叙述方式、复杂的精神世界以及多元的话语结构共同增强了小说的复调色彩。今非昔比,在救亡视野、启蒙者以及左翼思想的视野下描绘的故乡,已是作者回不去的故乡,即便真正踏上故土也找寻不到心灵栖息之处。
——师陀小说《争斗》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