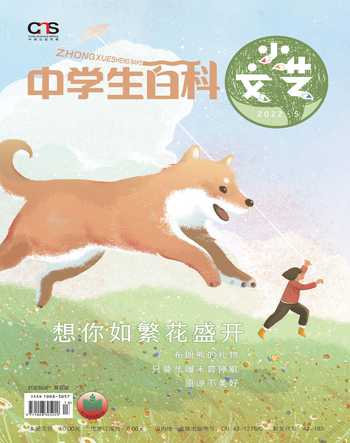他 国
小学时某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我和好朋友疯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梧桐树荫连成长廊,我满头大汗,书包背带垮到手臂。经过路边一辆轿车时,我看见深灰色的车窗上映出一张笑脸。突然,身体里仿佛有另一个我远远跳开,对整个场景安静一瞥,想:不知道过很久再回头看,还会不会记得现在的开心。——多年后,我得知这种生命体验或许叫作“解离”。
短暂的解离属于正常现象,不为我所独有。但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有意识地跳出自己所处的境况,对自己“冷冷一瞥”,并将之写进日记。
与此同时,语文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长期的作业:接龙写故事。一人一天,不设任何限制。我爱死了这项作业,甚至在接龙结束后,还继续写续集,一直写到小学毕业。
也是在写这个故事时,我按照自己名字的谐音,随口给自己取了如今的笔名。开始发表文章后,我无数次嫌它幼稚,甚至在编辑向我要作者简介时,写了一首藏头打油诗来增添内涵。可是某日,身体里的我又“跳出来”想,等到未来有一天,自己白发苍苍垂垂老矣,还在用童年时取的名字写故事,这是件多么浪漫的事呀!八岁时,我读秦萤亮的《阁楼上的公主》会哭泣,二十岁时读她的《百万个明天》仍会流泪。我的泪点长在盆地,写字是保护良田、防治洪灾的引水渠。我终于完全接受了自己的笔名,作为坚持写到八九十岁的决心。
一次又一次,我逮着缝隙从学业和现实的疲惫中“跳出来”,站在状况和时间之外,审视自己,游荡四野,然后形成文字,构筑城池。
生活在别处,文学是他国。“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陆机所言,然也。
不断生成的文字如此确凿,每个人物和情节都有来处可寻,我的生活在故事里留下印记,我的阅读在书写中展现履痕,我的偏爱和厌恶都如此昭然。彼方的国度并没有飘在云端,反倒日复一日使我的心愈发安定,感觉自己仍脚踏实地,从土壤中汲取養分,形成经验和观点,在思考和自省。只不过,印成铅字的国度如同孤城,鲜有回声。
去年8月,奥运会乒乓球混双夺银的遗憾经过数天的发酵,将“许昕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推上了知乎热榜首页。对他的谩骂和否定甚嚣尘上的那几天,我无力地落泪,在日记里写:我会记得你,用微不足道的笔。
始料未及的是,我为了安慰自己而在这个问题下写就的一篇独白,成了最高赞的回答。
评论里开始有人说:“原来他是这样的。”“祝福他。”“很感动。”“他很好。”
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这支笔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原来我还可以让看见他光芒的人多几个,让误解他的人少一点。
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文学是他国,是乌托邦,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但语言本身是桥梁,任何城邦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外交。我一直对网络环境下的“输出”感到消极、失望,但其实不必输出,“分享”自有其力量。爱与美、盈眶之热泪、诚挚的情感,它们不在真空中,可以借由文字抵达、叩击另一颗心。这也是文学的意义。
我还是想写到白发苍苍,造许多城邦,都坐落在大地上,敞开城门,迎四方客。
程夏怡,笔名遐依,于千禧年生于武汉。遐思悠悠不可裁,依依遣笔舒此怀。书尽胸中十万兵,醉卧江南呼快哉。在《中学生百科》发表了《变成兔子的牙齿》《心照不宣》《忘记爱江河》等作品。
编辑/胡雅琳175467BE-6D46-43F0-8EC6-0CB9ADBBA4E1